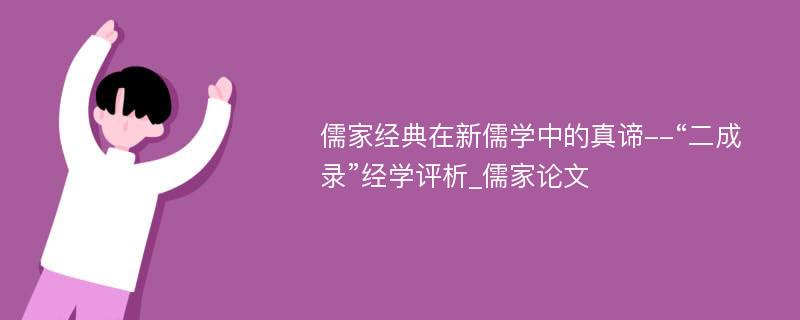
新儒学的经学真谛——二程洛学之经学评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学论文,儒学论文,真谛论文,二程洛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自汉代“独尊儒术”始,经学作为古代中国具有官方哲学意味的儒家经典阐释学逐渐演变为统治阶级的主要思想工具;经学又与儒学天然相关,要求体道宗经、致用重文的一体化,进而成为钦定之学。这不但影响着封建大一统之下的皇权意识形态及其专制政治体制的沿革,而且也决定着经学自身的发生、发展与终结。更为重要的是,这也注定了儒学与经学的不同历史命运,显示出学术思想发展与伦理政治教化的文化层次分野来:儒学作为中国文化的传统之学,从先秦到当代,在社会生活中一直发挥着不容忽视的文化影响;而立于学官的经学,在辛亥革命后遂成为绝学。但不应忽视,就经学而言,其兴衰在一定程度上曾决定着儒学自身的发展,而经学同时又作为通向儒学的中介以实现儒学的“独尊”,运用经学方式传播的儒家思想更多地与经世致用的政治需要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儒家思想当是中国古代文化传统中的轴心意识的重要构成,其价值观念系统核心即内圣外王之道,由经学而具体体现为中央集权之下的思想大一统。有宋一代,虽通常史称积弱积贫,然而正是在“一道德”以巩固皇权统治的现实需要之下,促成了经学的复兴,出现了所谓“宋学”,使儒家思想对社会的文化影响更为广泛和深入。〔1〕就人称的“新儒家”而言,程颢与程颐兄弟“倡明道学于孔孟既没,千载不传之后”,〔2〕二程洛学遂成为北宋时期儒家思想发展的代表, 通过义理之思而推进了内王外圣之道,开创了“理学”这一学术思想体系,致而引发了对于理学及其正统学派的普遍关注与多重肯定。但是,不应该忘记理学的形成与发展,确有着其特定的经学背景,显示出儒学与经学的交叉与混融,其表现形态即为“道学”:“道之在经,大小远近,高下精粗,森列于其中”;“为学,治经最好,苟不自得,则尽治‘五经’,亦是空言”,要之,“治经,实学也”。故以治经来倡道者学,就不是空言儒学而是以经学方式来弘扬儒学;以治经贵自得,就是通过解经而求道以达至理。这样,“道”与“学”也就成为趋于一致的传道居业之举:“道之浩浩,何处下手?惟立诚才有可居之处,有可居之处则可以修业也”。〔3〕不过,“道学盛于宋,宋弗究于用, 甚至有厉禁焉。后之时君世主,欲复大德王道之治,必来取法矣”。〔4〕由此可见道学的儒学地位与经学地位之间此时尚未协调,其关键在于有宋一代君主基本上未取道学为法。〔5〕
正是在开始将理学认定为经学主流的元代,此时所修官史《宋史》把“道学”从“儒林”中分离出来,设立史无前例的专传,其理由自然就是:“西汉而下,儒者之论大道,察焉而弗精,语焉而弗详,异端邪说起而乘之,几至大坏。千有余载,至宋中叶,周敦颐出于舂陵,乃得圣贤不传之学,作《太极图说》、《通书》,推明阴阳五行之理,命于天而性于人者,了若指掌。张载作西铭,又极言理一分殊之旨,而后道之大原出于天者,灼然而无疑焉。仁宋明道初年,程颢及弟颐寔生,及长,受业周氏,已乃扩大其所闻,表章《大学》、《中庸》二篇,与《语》、《孟》并行,于是上自帝王传心之奥,下至初学入德之门,融会贯通,无复余蕴。”〔6〕可见,二程洛学以道学宗主自居, 固然是承袭了道学先驱:考究理及性,“君子乾乾不息于诚,然必惩忿窒欲,迁善改过而后至”,故“诚者合内外之道,不诚无物”;〔7〕又穷索仁及乐,“为天地立心,为生良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故‘博施济众’,乃圣人之功用”。〔8〕
更为重要的是,二程洛学认为“天下之习,皆缘世变。秦以弃儒术而亡不旋踵,故汉兴,颇知尊显经术,而天下厌之,故有东晋之放旷。”至于“宋兴百余年,而教化未大醇,人情未尽美”,则为“方今人执私见,家为异说,支离经训,无复统一,道之不明不行,乃在于此”。故要求“一道德同风俗”,“其要在于择善修身,至于化成天下,自乡人可至于圣人之道,其学行皆中于是者为成德”。简言之,“当陈圣学之端绪,发至道之渊微”,所谓“窃以圣人之学,不传久矣,臣幸得之于遗经,不自度量,以身任道”。〔9〕虽然仍旧作大经与小经之分, 但已将《论语》和《孟子》并提,且仅以《大学》、《中庸》为《礼记》中的完全合于圣人之意者,故称《大学》“乃孔氏遣书,须从此学则不差”,《中庸》“一卷书,自至理便推之于事”。〔10〕这样,从儒学看,不仅将孔孟之说提高到经典地位而确立道统,而且对儒家后学之作进行梳理并提取精义向原儒认同;从经学看,不仅为“十三经”的最终形成提供了道统之轨范,而且也将“四书”的弘道地位提高到学传之主科,从而在治经求道中奠定了二程洛学作为北宋经学主要流派之一的独立地位。与此同时,正是由于二程洛学未得经世之用,反而促成其于治经中的不断自得,也就相应地推动理学的进一步发展,使儒术与经术能够逐渐统一起来,通过其经学地位的确立以确保其儒学地位。这样,新儒家的程氏兄弟也就在治经中成为“宋学”的开创者。
二
“宋学”在经学史上,是相对于“汉学”而言的,就这个意义上讲,宋学即宋代经学的简称。不过,正如汉学具有今文学与古文学这两种解经方式一样,宋学的解经方式自然会随着时代变化而发展出新的类型来。汉学两家与宋学一家代表了经学史上三种不同的立要解经方式:“今文学以孔子为政治家,以《六经》为孔子致治之说,所以偏重于‘微言大义’,其特色为功利的,而其流弊为狂妄。古文学以孔子为史学家,以《六经》为孔子整理古代史科之书,所以偏重于‘名物训诂’,其特色为考证的,而其流弊为烦琐。宋学以孔子为哲学家,以《六经》为孔子载道之具,所以偏重于心性理气,其特色为玄想的,而其流弊为空疏。”〔11〕不同类型的解经方式是由不同的文化层面、价值取向、阐释形式建构而成的完整体系,并各有其长处,从而形成了解经的多样性特征,对经学自身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实际意义。同时,三大解经方式的渐次形成,不但呈现出由汉学向宋学发展的过程阶段性,而且也成为贯穿有宋一代及其之后的儒家经典解读的主要经学手段。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下,可以说“自汉京以后垂二千年,儒者沿波,学凡六变”,而“要其归宿,则不过汉学、宋学两家”。〔12〕可见,宋学又可视为宋代经学发展中形成的一种具有代表性的解经方式。这样,宋学就具有了经学史与解经方式两个向度上的界定,前者仑容着后者,是广义上的“宋学”,而后者产生于前者,是狭义上的“宋学”。这狭义上的宋学,也就成为号称义理之学的道学的代名。
对此,程氏兄弟应该说是有所意识的:“今之为学者岐而为三,能文者谓之文士,谈经者泥为讲师,惟知道者乃儒学也”。在这里,他们首先是将知道者与文士、讲师相区别,主要着眼于明道与解经之间的关系,指出古之学者,因孔氏门人的系统传授,“由经以识义理”,而今之学者,在学统中断,道统不继的状况下,“都先须识义理,方始看得经”。故认为文士、讲师者流虽欲效古人“因经以明道”则不可能,这也是汉代以来解经者的流弊。进而强调了知道者治经当先明古今为学之别,“后世失其师传,故非明道,不能以知经”,因而倡道为学便是当务之急。同时,在以道学自任中不乏这样的雄心:当重建系统,继承道统,追随颜孟,“入圣人气象”,“为万世之师”,来发扬光大儒学。〔13〕
由此,程氏兄弟又提出:“古之学者一,今之学者三,异端不兴焉。一曰文章之学,二曰训诂之学,三曰儒者之学。欲趋道,舍儒者之学不可。”这表明,儒学虽然随世势变化而发生古今之变,其正宗地位却能借助经学而愈加巩固,佛老之说终为异端而难与之争锋。然而,在一分为三之中,能够延续儒学正统的仅是以“知道者”自命的“儒者之学”。自然这就不能不带上几分偏颇:文士、讲师这类“后之儒者,莫不以为文章,治经术为务。文章则华靡其词,新奇其意,取悦人耳目而己。经术则解释辞训,较先儒短长,立异说以为己工而已,如是之学,果可至于道乎?”所谓文章之学与训诂之学不过是汉学两家之流变,无论是新奇其意还是较先儒之短长,都难以表达圣人之道,唯有儒者之学可以明道知经,而后“由经穷理”,此即所谓“经所以载道也”。〔14〕这就与由唐入宋以来,在经学复兴中率先出现的以“文以载道”为主旨的治经主流相映成趣。不过,“文以载道”者讲体用,贵经世,力尊王,其解经与汉学两家一脉相承;“经以载道”者究又理,斥功利,尚诚心,其解经则学宋学一家独出蹊径。具体言之,就是从北宋经学四大家到南宋经学两大派,无论是荆公新学、温公朔学、苏氏蜀学、二程洛学,还是朱陆理学派与浙东事功派,都分别体现出“文以载道”与“经以载道”的治经意识。仅就同一时期的“经以载道”的二程洛学,与“文以载道”的荆公新学、温公朔学、苏氏蜀学相较而言,在解经过程中,前者讲求由经穷理,而后三者则坚持通经致用。〔15〕当然,在道学家看来,荆公新学“只是说道”而“佗不知道”,温公朔学则“元不知学”更何惶论道,至于苏氏蜀学于党争之中当不屑一提。〔16〕
就经学发展而论,有宋一代“文以载道”者在经学复兴中成为经学主流派,就在于其坚持通经致用的解经主张适应了巩固皇权大一统的迫切需要。无论是变法还是一道德,都要求通过对儒家经典的再阐释来建构一个具有规范性和可行性的制度化体系。随着疑经、变经、易经之风的兴起,最终出现官修群经文本,从而使这一体系成为教化与治世的有力工具,经学发展显示出政治化的趋向。这样,“经以载道”者意在由经穷理就显得不合时宜,自然难以得到统治者的亲睐。至此,可以说二程洛学的经学意义在宋代确实远逊于其儒学意义。然而,二程洛学作为非主流学派从事治经,正是通过义理之思将对儒家经典的再阐释提高到了哲理高度,赋予经学以哲学化的发展潜质,这对于宋代之后经学发展以理学为正宗无疑是至关重要的。二程洛学进行天理人欲之辨,虽然从官方哲学的经学看来,“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确实有以理杀人之过。但是,从百家之一的纯粹儒学来看,不过是对于特定伦理原则进行哲思的一种简略口头表达。〔17〕正是由于对之加以经学式的运用而成为所谓礼教的重要内容,此一说法因此而难免倡导以理杀人之嫌,从而构成了学术思想史上的冤案。
三
这一冤案的造成,除了前述原因外,也与二程洛学的不重文直接相关。程氏兄弟论道与解经,多用“口义”,即通过口头进行当下即是的一问一答,企图在“论语”式的传授氛围中完成圣人之道的世代承传。这就是所谓“以书传道,与以口传道,煞不相干。相见而言,因事发明,则并意思一时传了;书虽言多,其实不尽”。可见,“以口传道”无论是从道统还是从学统,均被其视为回到述而不作的孔子去的主要途径。这样,即使难成圣人气象,至少也可作万世之师,此即二程洛学主张将《孟子》升格为经的一个原因。值得注意的是,“口义”一旦用文字记承下来之后,脱离了话语的活泼样态,也就失去了特定语境及超语境的语义效应,成为僵死的言语记载,就是较之传道之书,也因其意不明而远不及,难以引发对其所传之道的共鸣,必须纳入一定的阐释过程中方能再现其真意。否则,就会发生那种导致冤案似的误解。可见,以口传道更需要坚持传道的连续性,众多书院的设立则从空间与时间这两个向度上予以了有效的保障。〔18〕
同时,“圣人之语,因人而变化;语虽浅近处,即却无包含不尽处”,相形之下,“他人之语,语近则遗远,语远则不知近,惟圣人之言,则远近皆尽”。所以,今之学者与古之学者相比,最根本的差别就是“传经为难”。这表现在由汉及宋的经学中就是:“汉之经术安用?只是以章句训诂为事”,既“不知要”,更“不足道”,至于“本朝经术最盛,只近二三十年议论专一,使人更不致思”。改变这一现状就要求致思明理,然后方可使传经不再难,此即所谓“造道深后,虽闻常人语,言浅近事,莫非义理”。〔19〕故治经之要,二程洛学以为首在“识义理”,第一步就是进行关于圣人之道的体系性阐释。
“圣人德盛,与天为一”,故圣人之道即天之理。在此前提下,程氏兄弟不无自得地指出:“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都是自家体贴出来的”。于是,展示出如下的哲思:“上天之载,无声无臭之可闻。其体则谓之易,其理则谓之道,其命在人则谓之性,其用无穷则谓之神,一而己矣。”要言之,“道之外无物,物之外无道,是天地之间无适而非道也”。〔20〕因此,进而提出“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义、礼、智、信皆仁也。识得此理,以诚敬存之而己”。这样就达到了形而上的体道:首先是“仁者,天下之正理。失正理,则无序而不和。”“仁”不仅是人格精神的最高境界,而且也是社会秩序的最高准则,此即所谓“仁道难名,惟公近之,非指公为仁也”。可见“仁”确为天下正理。〔21〕其次是“诚则合内外之道,不诚无物”,而“纯于敬,则己与理一”。存仁必须诚与敬相辅相成:“诚则无不敬,未至于诚,则敬然后诚”,由此而仁理自明。〔22〕至此,通过对于天理的致思,进行了道归于仁的范畴体系建构,成为解经的明道基础。
“进学莫先乎致知,养心莫大乎理义”。〔23〕这是二程洛学关于为学途径的总命题。
首先,“学以知天为本”,“不知天,则于人之贤否愚智,有所不知,虽知之,有所不尽”。故“学莫大于知本末始终。致知格物,所谓本也,始也;治天下国家,所谓末也,终也。治天下国家,必本诸身”;“格犹穷也,物犹理也,若曰穷其理云尔。穷理然后足以致知,不穷则不能致也”。简言之,致知在格物,“不知格物而欲意诚心正而后身修者,未有能中于理者也”。由此可证《大学》之为二程洛学所推崇的原因之一即在其提供了进学之途:“致知则明,明则无不胜其任者,在强勉而已”。〔24〕
其次,“学也者,使人求于内也,不求于内而求于外,非圣人之学也”。“中理见乎事,敬在心,义以方外,然后中理矣”;“敬,所以持守也。有是有非,顺理而行者,义也”;“义有至精,理有至奥,能自得之,可谓善学者矣”。由致知到养心,惟以诚一以贯之,所谓“学在诚知诚养”,一方面“进学不诚则学朵”,即如“今末习曲艺,亦必诚而后精;况欲趋众善,为君子者乎?”另一方面,“学之而不养,养之不能存,是空言也”,故此“学至涵养其所得而至于乐,则清明高远矣”。“《中庸》言诚便是神”,以此亦略见二程洛学善用《中庸》指导为学之一斑。〔25〕
“仁”作为儒学的普遍价值原则,是圣人之道的人文体现,故“学者须先识仁”,这对于切于人事的经学来说就至关重要:以仁为核心就能将明道与为学统一起来,“仁则一,不仁则二”,“在物为理,与物为义”,从而识义理而后方治经。所以,“学者识得仁体,实有诸已,只要义理裁培。如求经义,皆裁培之意”。至此,二程洛学已经开出切实可行的治经路向来。〔26〕
虽然孔孟无书皆口义,但“孔子言语,句句是自然,孟子言语,句句是实事”,皆有功于圣人之道。相对而言,“佛氏之道,一务上达而无下学,本末间断,非道也”;“老子语道德而杂权诈,本末舛矣”,异乎圣人之言,故“学佛者,于内外之道不备”,而学老庄者多“谨礼而不达者”和“放情而不庄者”。可见,程氏兄弟虽曾出入过佛老,其所受影响主要在致思方式上,所谓“异端之说,虽小道,必有可观也。”〔27〕但二程洛学最终恪守圣人之道,以“救诸六经”为己任。这从其对《大学》与《中庸》的推崇中即可见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明此理也”;《中庸》之理,在“忠恕违道不远”,传夫子之道矣,〔28〕从而直接促动其在理学形成中最终成为“四书”中的典籍,对宋以后的经学发展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四
虽然程氏兄弟通过“口义”就群经进行不同形式的关说。但一方面主要是从明道的层面上分述各经之义,较少对各经文本进行解读;另一方面由于多借答门人问来解经,留下的记录显得颇为支离与混乱,且流传范围较狭窄。这就自然会不利于二程洛学的经学影响在当时的扩散,以及对其经学地位的广泛社会承认。因此,在论及程氏兄弟的治经时,就不得不主要借助其成文之“书”,来考察其解经方式不同于汉学两家的独特之处,此当有益于对所谓宋学一家的进一步认识。
治群经而欲穷经旨,以何经为先?对于这一提问的回答是:“于‘论’、‘孟’二书知其要约所在,则可以观‘五经’矣。读‘语’、‘孟’而不知道,所谓‘虽多亦奚以为’?”这样,由《论语》、《孟子》而渐及五经,就是所谓“知道者”的解经顺序,其根基依然在明道以知经。〔29〕
《论语解》系按章句进行有选择的阐释。在《学而》一篇中,就首先指出“为仁以孝弟为本”,而“论性,则仁为孝弟之本”,“本立则其道充大”。从性与道出发,强调了以仁孝为本,又区分了仁与孝的体用关系。此外还分别涉及到有关义、礼、智、信诸方面的内容,所谓“仁民”、“德容”、“思绎”和“忠信”,提出君子具诚敬之心,则“贫无谄,富无骄,能处其分也。乐与好礼,能自修也”。这就实现了“知道者”在解读《论语》中明仁理而达经义的目标。《论语解》中以后的各篇保持了这一解经的哲思意向,从而成为解读其他各经的始基。〔30〕
《孟子解》现存者,“则皆后人纂集《遗书》、《外书》之有解者也”,故全为“口义”。今试用“河南程氏粹言卷第一”之《论书篇》作一概观:“由《孟子》可以观物”。其一,“孟子言三代学制,与《王制》所记有所不同,《王制》有汉儒之说矣”;其二,“孟子养气之论,学者所当潜心也。忽忘,忽助长,养道当然,非气也”。一方面,这可以看出“孟子之时,去先王未远,其所学于古者,比后世为未缺也”;另一方面,这也就更为强调“是故语其体则与道合,语其用则无非义也”。〔31〕《孟子》虽无《论语》那样的“圣人气象”,但的确可作“万世之师”,提供了救正养心之理,并借此作为观经的立足点。
对于《周易》,当系用力最勤,《周易程氏传》至少有四卷,但仍系“草具未成”之作。不过,“程子不信邵子之数,故邵子以数言易,而程子此传则言理”——“一阐天道,一切人事”,同样也展示了明理而知经的治经轨迹。〔32〕首先,“其为书也,广大悉备,将以顺性命之理,通幽明之故,尽事物之情,而示开物成务之道也”;其二,“其道至大而无不包,其用至神而无不存”,“圣贤德业久大,得易简之道也”。由《周易程氏传》看来,天理与人事也无非是圣人之道的体与用,诚所谓“天下之理,易简而已。有理而后有象,‘成位乎其中’也。”〔33〕
《书解》首先针对《尚书》中的三墳五典承认其有大道与常道之分,然后提出质疑,其要在“使诚有所谓羲、农之书,乃后世称述当时之事,失其义理”;其次认为孔子删“书”的根据在子“旧书之过可见也,芟夷繁乱,翦截浮辞,举其宏纲,撮其机要”。之所以如此,即在于“设若其书足以垂范,不可去之,而其或有害义,圣人不得不有芟除更易也”。仿此,《书解》中仅为《尧典》、《舜典》、《武成》作解,是因为“至尧而与世立则,著其典常,成其治道”,概言之,圣人于此始为天下立法。〔34〕
《诗解》中指出孔子删诗“得三百篇,皆止于礼义,可以垂世立教”。故所解读之诗也就经过有意选择,着眼点在“所以风化天下”以求天下之治。正是由于“天下之治,正家为先”,而“正家之道,王化之所由兴”,也就是“《关睢》之化行,则天下之家齐俗厚,妇人皆由礼义,王道成矣”。结果,《诗》成为自周文王以来人文化成之道的历史见证,所谓“史氏得《诗》,必载其事,然后其义可知”,“故曰《诗》之至也,得失之迹,刺美之义,则国史明之矣”。〔35〕
《春秋传》一开始就总称:“夫子之道既不行于天下,于是因《鲁春秋》立百王不易之大法”,然后选择能体现此说的有关条目作“传”,既反对将《春秋》当作历史看,又要求把握《春秋》中的“大义”,尤其是“隐义”,并认为解读《春秋》的关键在于:“夫观百物而后识化工之神,聚众材然后知作室之用,于一事一义而欲窥圣人之用心,非上智不能也。故学《春秋》者,必优游涵泳,默识心通,然后能造其微也”。显然,极力主张依据《春秋》也可穷理。〔36〕
《礼序》称“礼经三百,威仪三千,皆出于性,非伪貌所情也”。然后并不专解“三礼”,反而强调圣人制礼以行义,“其形而下者。具于饮食器服之用;其形而上者,极于无声无臭之微;众人勉之,贤人行之,圣人由之。故所以行其身与其家与其国与其天下,礼治则治,礼乱则乱,礼存则存,礼亡则亡”,造成了“世有损益”的后果。“然岂礼之过哉?为礼者之过也。”这就提出了返朴归真的要求,而实际上为礼者有众人、贤人、圣人之分,“故天尊地卑,礼固立矣;类聚群分,礼固行矣。”〔37〕
程氏兄弟虽然遍论各经,但基本上都未能解其全经,即使是《礼记》中的《大学》和《中庸》,对于前者也不过是两人各自单独分别进行“改正”,而对于后者两人似乎均曾为之作解,然终不得见。〔38〕这种治经遗憾也许当归之于“知道者”偏重于明理以知经的玄想中所产生的空隙吧。当然,这并不是否认二程洛学开创宋学一家的经学地位和经学影响。将上述解谈各经的特点总括起来看,可以说它是从明理以知经的哲理层面上,通过经以载道的价值取向,借助由经穷理的阐释形式来建构出一个哲学化的解经方式雏型。
注释:
〔1〕参见《宋史》卷157《选举三》,中华书局1977年版。
〔2〕朱熹:《河南程氏遗书·识后》,《二程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
〔3〕《二程集》第2页。
〔4〕〔6〕《宋史》卷427《道学一》。
〔5〕道学在南宋末才始获统治者的认可,论为学官, 这与宋理宗本人并非宗室近支所出,而为权臣废太子而拥立为帝直接相关,他在心理上更欣赏“正心诚意”的性理之学,以确保自己的政治地位。至于元明清的后世君主以理学为经学正宗,自然也是有着复杂的文化顺应背景的,此当另作专论。参见《宋史纪事本末》卷88《史弥远废立》,中华书局1977年版。
〔7〕《周敦颐集》第38页,中华书局1990年版;《二程集》第9页,参见第2页。
〔8〕《张载集》第376页,中华书局1978年版;《二程集》第15页。
〔9〕儒术与经术不同:儒术更注重儒家思想作为一家之言的学术传统;经术则偏向儒家经典归于独家阐释的教化正统。《二程集》第70、448、546页。
〔10〕《二程集》第562、580、18、2页。
〔11〕周予同:《经学历史·序言》,皮锡瑞《经学历史》,中华书局1959年版。
〔12〕《经部总叙》《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年版。
〔13〕《二程集》第95、164、165、77页。
〔14〕《二程集》第187、580、158、95页。
〔15〕以王安石为首的荆公新学,以司马光为首的温公朔学,以三节为首的苏氏蜀学,在通经致用方面,亦分别以依经诠义、通经溯义、明经正义而显示出其学派差异(此当另分别讨论)。其中,温公朔学较类二程洛学,司马光本人也入祧《伊洛渊源录》,是所谓“六先生”之一,但毕竟格物未精而终难入其流。参见《湅水学案序录》、《宋元学案》卷7,中华书局1986年版。
〔16〕《二程集》第6、27页,参见《蜀洛党争》, 《宋史纪事本末》卷45。中华书局1977年版。
〔17〕参见贺麟:《宋儒新评价》,《文化与人生》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
〔18〕《二程集》第26页。
〔19〕《二程集》第176、232、178页。
〔20〕《二程集》第424、1170、73页。
〔21〕《二程集》第17、1173、1171页。
〔22〕《二程集》第9、1171、1170页。
〔23〕《二程集》第1188页。
〔24〕《二程集》第1191、1197、1190页。
〔25〕《二程集》第1198、1188、1189、119页。
〔26〕本文将仿效由其门人编定的,现收入《二程集》中的“河南程氏粹言”,对其“义”进行语境设置,以图使之显现出内在的逻辑性与外在的延伸性,从而俨然自成体系。《二程集》第16、1175、15页。
〔27〕《二程集》第76、1179、1180、1194、1196、1176页。
〔28〕《二程集》第638、136、8页。
〔29〕《二程集》第1204页。
〔30〕《论语解》至《止罕》即中断,其后为后人“纂集《遗书》、《外书》之有解者的附益之”,且均为口义。《二程集》第1133、1134、1150页。
〔31〕《二程集》第1151、1204、1206、1205页。
〔32〕宋伊川宋子撰《易传》,《四库全书总目·经部》。
〔33〕《易传序》、《易序》、《易说》、《二程集》第582、 668 、1027页。
〔34〕《书解》,《二程集》第1032、1033页。
〔35〕《诗解》,《二程集》第1046、1048、1047页。
〔36〕《春秋传》、《春秋传序》,《二程集》第1086、583页。
〔37〕《二程集》第668、669页。
〔38〕《明道先生致正大学》、《伊川先生致正大学》,《二程集》第1126—1132页,参见116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