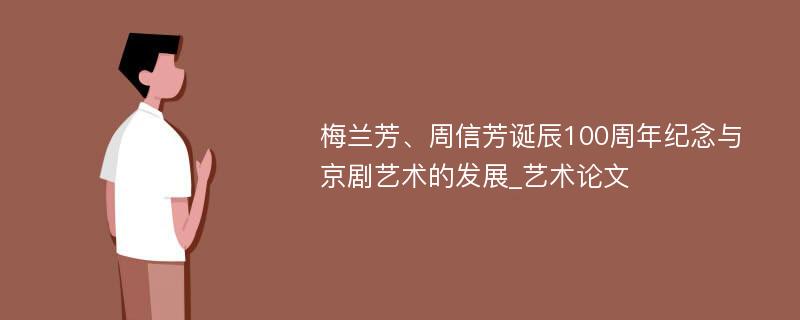
纪念梅兰芳、周信芳诞辰100周年振兴、发展京剧艺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梅兰芳论文,诞辰论文,京剧论文,周年论文,艺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编者按 12月9日,为纪念梅兰芳、周信芳诞辰100周年,本刊邀请首都部分戏剧家、理论家座谈,畅谈梅兰芳、周信芳生前为京剧做出的巨大贡献,并联系当前京剧艺术创作现状,就京剧艺术的继承、发展以及提高京剧演员道德修养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座谈发言摘编如下。
开场白
郭汉城 在即将举办的纪念梅兰芳、周信芳诞辰100周年活动的时候,我们《中国戏剧》杂志社邀请各位专家、学者座谈,纪念这两位大师,总结他们的艺术经验、成就,学习他们的品格,这在戏曲发展处于转折时期的今天,是有意义的。
中国戏曲的发展,就剧种的角度来讲,曾经出现过两个高峰,一个是昆曲成为全国的大剧种,这是古典戏曲的高峰;另一个是京剧成为全国性大剧种,这是民间戏曲的高峰。这两个高峰,前一个以产生了许许多多伟大的古典戏曲名著为标志;后一个以产生了众多群星灿烂的大演员为标志。他们的共同点则都是通过对艺术革新,达到了时代的高峰。从昆曲的魏良辅到京剧的程长庚,一直到梅兰芳、周信芳,都是杰出的革新家。他们对于艺术的革新,采取既积极又慎重的态度,即革新必须继承,继承的目的还是为了革新。因此他们反映了时代,符合了人民的审美需求,获得了广泛的群众。纪念梅兰芳、周信芳,对于今天的京剧最根本的仍是继承他们的革新精神,只有这样,才能够把就剧推进一步、提高一步,赋予它以时代的、生命的活力。梅兰芳、周信芳的艺术成就很高,经验很丰富,有许多值得学习、总结的地方,希望各位从各个方面谈一谈。
正确对待推陈出新提高演员道德修养
马少波 我和梅兰芳、周信芳两位大师都属马,他俩比我年长“两轮”,我们却有一段特殊的缘份,曾经有过较长时间的合作关系,接触较多。彼此相知也较深。
梅兰芳、周信芳的艺术成就,在中国京剧发展史上,具有继往开来的划时代的作用。他们的艺术革新精神是空前的。在短短的几十年中,他们在艺术创造革新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和对中国京剧艺术的贡献,是超越前人的。
京剧的形成和逐渐成熟经过了一个漫长的时期,以程长庚为首的许多前辈艺术家至少经过半个世纪到一个世纪的渐变过程。梅兰芳、周信芳二人在京剧史上奇峰突出,在民族虚无主义和国粹主义相对峙的夹逢之中,开辟出新的途径。他们的艺术创造符合了艺术的发展规律,适应了时代潮流,所以他们各自在艺术上取得了辉煌成就。我们历来提倡创造革新,问题是怎样革新。要正确地继承传统,正确地创造革新。创新莫离传统,借鉴勿失自我。如果继承传统是陈陈相因、抱残守缺,是没有出路的,现在就有这样的倾向;如果创造革新是把外来艺术和兄弟剧种的东西原封不动地照搬,违背京剧本身的艺术规律,丢掉自己的个性和特色,也是没有前途的。
50年代,在纪念梅兰芳、周信芳舞台生活50年时,梅演出了《穆柯寨》,周演出了《扫松下书》,给我留下的印象都十分深刻。《穆柯寨》是梅兰芳年轻时第一次去上海演出的大轴戏,50年代演出仍然精彩,身上、扮相、表演,充分体现出一位英雄少女的妩媚、英武、京白真是漂亮,音色美,节奏感强,表现青年穆桂英的情态很迷人。周信芳的《扫松下书》,对张广才耿直淳厚的形象刻画非常精妙,感情很细腻,性格十分鲜明,浑身是戏。当时我对他们的表演创造,对他们在对待艺术上推陈出新所走的途径进行了一些思考,曾经写了一篇文章(载《戏剧报》1955年第5期)。这两出戏是他们各自的代表作之一,研究他们的艺术,要从各个侧面,从他们所演出的各个剧目及他们所塑造的各种不同性格的人物等方面去探讨。我们不难看到,他们的艺术道路是正确的推陈出新的道路。他们演出的剧目,无论是整理、提高了的传统剧目,还是创造的新戏,如梅兰芳从他的《穆柯寨》到《穆桂英挂帅》,周信芳从他的《追韩信》到《义责王魁》、《海瑞上疏》,都是从剧目到表演、化妆、舞台装置等各个方面加以改革,一直坚持正确地继承传统,正确地创造革新,成为这方面的典范。
谈梅兰芳、周信芳的艺术成就,应该很好地研究一下,他们为什么曾在国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两面夹击下,能够自觉或不自觉地走了正确的道路?他们是如何推陈出新的?他们的诀窍在哪里?这些问题,直到现在我们还没能很好地加以总结。要不就是老戏老演,唱词也不顺,甚至不通,唱腔也仅仅是模仿,剧目不认真整理,艺术上不精心加工,是这些年的缺陷。如果当年梅兰芳、周信芳是这样对待艺术,他们能有杰出的成就吗?我们也主张充分运用现代的科技条件,像舞台灯光,但毕竟这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表演艺术,是塑造人物,要充分发挥京剧的特色,用特有的表演技巧去着力塑造人物,在这方面,我赞成探讨、尝试。现在的观众既不愿看老戏,也不愿看“革新创造”离谱的新戏。问题在哪里?值得认真研究。
保持艺术的特色很重要。比如戏曲的综合性、虚拟性,在这方面我们高于外国人。外国人如果演《三岔口》,就要压暗灯光,这是非常笨的方法。我们去丹麦皇家剧院演出时,丹麦有一个人称“丹麦梅兰芳”的著名芭蕾舞蹈家雷乌麦尔,她看完演出很兴奋,冲上台去抱着演员一个一个地亲吻,那天大轴是《闹天宫》,站在前排谢幕的演员全是猴子、巨灵、天王等花脸,最后她变成了大花脸。她说:“感谢上帝让我欣赏到这样美妙的艺术!面对着你们古老的文化传统,我们没有话可说,只感到自己是白痴!”丹麦皇家剧院的院长布朗斯台特说:“我也愿无条件地、心甘情愿地拜倒在你们面前!”在明亮的表演区里去表现黑暗,去表现各种不同的生活场景,这是艺术。毛主席就说过,“还是中国人聪明嘛。”这方面的革新创造,梅兰芳、周信芳就十分重视、讲究。周信芳的《跑城》可以跑几个圆场,富有表现力,现在的舞台堆满了障碍物,怎么跑?在如何学习梅兰芳、周信芳,如何正确地继承传统、创造革新方面,值得探讨。
另一个问题是演员的道德修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党中央在戏曲界坚起了4面旗帜──梅兰芳、周信芳、程砚秋、袁雪芬。那时推出他们4位,当然考虑到他们的艺术成就和他们对戏曲艺术的贡献,但更重要的是他们的高风亮节道德修养。我们的艺术要发展,如果不着力提倡道德修养,艺术是不可能正常发展的。因为首先是人的思想、品德高,再加上艺术修养高,才能成为一个艺术家。要爱祖国,爱人民,爱艺术,爱集体,舍己从人,扶掖后进……。在50年代,以梅、周为代表的全体艺术家在这些方面,可以说都作到了。而现在,爱不爱国、爱不爱艺术,都成了问题。拜金主义、腐败现象司空见惯,不以为怪,以后怎么办呢?搞戏脱离群众,不是准备给群众欣赏的,是给领导报帐的,是给评委要奖的。培养出来的人才有的刚露头角,就飞了,改行了,……。有时国家枉费了那么多人力、物力,老师枉费了那么多心血,令人痛心!
纪念梅兰芳、周信芳,要着重发扬他们的道德精神。梅兰芳比较温文、含蓄,周信芳比较刚强、豪放,但共同点是,他们都有一副热肠刚骨。记得1959年我在青岛,周信芳也从上海来到青岛,事前托我为他安排住处。我去码头接他住下,坐下来就兴奋地畅谈自己的来意。同来的有许思言。他们此来是创作《海瑞上疏》,征求我的意见。且不说《海瑞上疏》的艺术效果以及后来引起的祸端,周信芳在交谈时的忧患意识,他那爱国爱民的一片赤子之心,当时令人深深感动,迄今音容宛在。1956年,我陪梅兰芳、欧阳予倩率团访日,在东京帝国剧场开幕演出那天,大轴是《贵妃醉洒》。正演出时,三楼上突然撒下一批传单,观众席中有人立起,出现了骚动。遇到这种情况,观众难免顾虑:若再扔一颗炸弹怎么办?一般说,演员就可能退入后台,如果那样,全场就会大乱,就决定了日本之行难获成功。周总理在我们临行时嘱咐过我们,说你们不是一般的演出团体,你们是人民的使者,要通过艺术交流打开中日关系这条冰河。如果开幕演出就乱了,以后怎么办?梅兰芳当时的表现了不起!他非常镇静、从容,“泰山崩于前而心不惊”,照演不误。观众受到了梅的感染,缓缓地坐下来,安静地看完了演出,天皇的弟弟三笠宫夫妇和很多日本名流上台祝贺,梅兰芳的镇静、从容保证了演出胜利。这就是梅兰芳。第二天,又有人把86份假人民日报分送代表团的86人,样式同《人民日报》完全一样,内容却是反共的,是策反梅兰芳的。梅兰芳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表示了严正的立场。他说:“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艺术家,是为了增进中日人民的友好,是为了维护世界和平而来的。”日本有的报纸以醒目的标题报道了这件事,慨叹:“撼山易,撼梅兰芳难!”
全世界没有一个伟大的艺术家不热爱自己的祖国、自己的人民。我们纪念梅兰芳、周信芳,就要发扬他们这种精神。
这两位艺术家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又升华到更高的境界。梅兰芳在他的入党自传里曾经写道:“我在抗日时期有点爱国表现,党肯定我,人民鼓励我,我感到莫大安慰。我知道,党和人民鼓励我,是体谅我当时的实际处境,能够保持气节,觉得难能可贵。可是我认识到自己做得还是很不够的。比如说,当国家危难的时候,中国人都像我那样隐居起来,中华民族能解放吗?所以比起八路军、新四军,特别是那些为中华民族解放事业和人民解放事业而英勇奋战、流血牺牲的文艺战士,我感到惭愧,我今后要向他们学习。”这就是梅兰芳!他是发自内心的严格要求自己,是多么崇高的思想境界和道德精神!
梅兰芳、周信芳无论是艺术创造和道德情操都为我们留下了一笔非常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应该好好向他们学习。
京剧要反思
刘厚生 关于梅兰芳、周信芳两位艺术大师,我已经写了几篇文章,意见都谈出来了。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想法,一是关于周信芳在现代京剧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一是谈如何理解梅兰芳的艺术风格。另外还想谈一点,就是对梅兰芳、周信芳的艺术要不要一分为二?我觉得要。
一分为二并非单指缺点。它的范围很广,譬如他们的艺术达到了什么程度,哪些是他们当时的历史局限性,当然也包括他们的不足之处。一方面对他们的成就、历史地位要有足够的评价,另一方面在艺术上。也要进行一分为二的研究。是看他们的艺术比前辈增加了什么?哪些地方超越了前辈,他们还有哪些没有达到的,我们如何达到等等。梅兰芳、周信芳在这方面是十分谦虚的,梅兰芳在50年代的演员讲习会上就诚恳地说过,你们都在说我的优点,而我所希望的是想知道自己的一些缺点。这些话不是虚情假意的,周信芳也有过类似的表示。梅接受别人对他表演上的意见改正自己的例子就太多了。周信芳在黄浦江边送客人,看到江上渔民撒网,就想到自己演《打渔杀家》,撒网的力量不够。这说明他认为自己在艺术上还有不足的地方,有改进的必要。我强调一分为二的想法是针对当前有些青年演员学前辈只是一味模仿的现状而发的。学习前辈艺术的最高理想应该是为了超越他们,不能仅仅停留在模仿他们,当然不是不需要模仿,初学阶段你学得好,我们承认。但整个京剧艺术如果只靠这个去发展,只能模仿,不能大过流派宗师,那就只能是小×××,小小×××,一直小下去,京剧就小没了。当然,所谓超越,也不是空口说大话,而是要踏踏实实地走自己的路,应该向流派宗师学习,但最后的理想则应是如余叔岩之于谭鑫培,张君秋之于梅兰芳才好。
占祥同志最近谈到京剧要进行反思,我理解就是要总结京剧几十年的经验。建国45年来,各种经验教训都有,现在已有了条件和能力,所以把今天的京剧同45年前的京剧做比较,它所达到的程度同过去有什么不同,还有哪些可以达到而没有达到的地方,今后我们主要力量要往哪方面走?这些都很需要我们反思。学习梅、周,也必须学习他们常常回顾过去,展望将来的精神。
同以前相比,京剧现代戏就有了很大的进步。抗战时期有现代戏,它的艺术表现还很幼稚,建国初期也有一些现代戏,1957年、大跃进时期出了不少现代戏,一直到1964年,发展到现在的现代戏,这里面有很大变化,它的得失都值得我们很好地总结。
同过去相比,京剧表演艺术上是突出个人还是强调艺术上的整体性,今天在观念上、实践上,同过去比有很大的不同。这里面有丰富的内容值得探讨。
这里我想谈谈程式问题。无可否认,程式是根本性的特点,但在新戏里,好多程式不用了。现代戏很难用旧程式不去说它了,就是新编历史戏里也是很多程式不用了。应该怎样去理解?也创造了一些新程式,但不是太多,所谓根据新生活创造新程式,这句话不是完全能做到。比较站得住的我看只有湖南湖北的骑自行车程式。许多个人表演程式是随人的形体动作而创造出来的,随着机械化的发展,在许多方面人体动作越来越小,程式的生活基础也越来越小。过去,开打、骑马、坐船,动作多而大,可以有很多程式,骑自行车时人体动作也还比较大,所以还可以创造程式,那么现在坐飞机、汽车坐着不动,就很难创造程式了。我们到现在也没有很好解决现代战争如何开打的问题,还是用步枪当红缨枪使,每有战斗,必定肉搏。
龙套的程式运用也发生了变化,新编历史戏里已经很少用老戏中那种龙套了,不是那种打着旗子上的龙套,而是具体化为军士,已经变形了。比如中国京剧院演出的《承天太后》,也是4个人一堂、8个人一堂,这是程式的东西,但辽国的士兵穿辽国的服装,宋朝的士兵穿宋朝的服装,而且都是新设计的,在化妆、动作上也有很大变化和发展。我以为程式是广场演剧的产物,观众和舞台的距离很远,听不清、看不清,依靠程式远远一看就看出这是老头,这是青年;这是富的,这是穷的;这是骑马,这是上楼,……基本上归于类型化。现在是剧场艺术,需要更多的个性化。其实程式在老戏里有许多也并不是通用的。《跑城》里的许多身段、动作,除了圆场是通用的程式,其他都是这个戏里特有的东西。《醉酒》里的8个宫女扶着杨贵妃,向左一歪,向右一倒,这是《醉酒》这出戏里特有的。前不久有一出地方戏用了这个动作,大家马上说,这是《醉酒》。可见这是《醉酒》特有的。总之,对比今天的和45年前的程式,可以看到很多不一样的东西,这就是发展、变革。
作为综合艺术,京剧对文学和舞美的重视,同45年前比,也大不一样。翁偶虹老先生写了那么多好戏,大都是为了给程砚秋大师提供唱的机会,在这方面很精彩,但文学本身的深刻性、完整性,次要人物的个性则讲究不够。现在就不一样了,文学上的要求更高了。
这许多同过去不同的地方,哪些是属于必然的趋向?哪些地方是过于超前或运用不当,要进行这方面的总结。
在音乐上,从梅兰芳加二胡起,乐队里增加乐器和运用西洋乐器好像是挡不住的一种趋势。是不是趋时,我看不是,是大势所趋。但也有用得好和用得不好的问题。唱腔上同几十年前比也有很大的不同。舞台美术用平台,我们有时看着不满意,可是偏偏许多导演都在用。有的还放烟,配合舞蹈等等。是不是用得恰当?有的用得并不恰当。但也有用得很好,还是能够增强艺术表现力的。梅兰芳几十年前在《洛神》里就用过平台,关键是要对戏有好处。要把这些东西进行分析、对比、总结。
京剧表演的艺术追求,一般讲要在行当基础上强调个性,强调塑造人物,但在某些青年演员中,往往把学前辈、学流派宗师当作最高理想。我深感对中青年演员的教育是大问题。如果理论上说了半天革新的必要,而主要演员不想革新,那是谁都没办法。我最近听袁世海同志说,他在电视上看了一出《玉堂春》,苏三唱“飞来飞去”那段,演成了打情骂俏的苏三。把袁世海气坏了。舞台上不少青年演员的艺术追求和我们想得不一样,和观众想的也不一定一样,从这个角度看,我们要进行哪些研究?这方面问题很复杂,未必能很快作出结论,但是应该逐渐有所积累。
有个大问题,我们现在实在还摸不清观众到底喜欢什么。老观众喜欢什么比较明显,到叫好的地方他叫好。青年观众正在培养,他们到底喜欢什么,摸不清楚。可能他们自己也在摸索。整个观众群体的需要,如何适应他们,这个问题研究得不够。一出新戏搞出来,用了很大的力量,但常是导演、作家自己发挥,到底适应不适应观众的要求?文化部最近强调新戏,我觉得是对的。但现在的观众对新戏的要求,同50年代、60年代,以至70年代相比,不一样了。过去搞历史剧强调教育作用,观众常常像上历史大课,现在则强调审美作用、认识作用,艺术趣味不太一样,需要考虑,要做很多调查研究,逐渐明确今后一、二十年京剧革新发展的主要趋向。这一点越剧可以参考。袁雪芬革新的时候很明确,要向话剧学习:幕表制改成剧本制,戏班制改成剧团制,强调导演作用,讲究创造人物,讲究交流、反应;表演形式则向昆剧学习,美化身段,唱腔讲究好听。这些做法很快得到越剧界的共识,大家都往这方面走,很快就发展来了。这些经验值得参考。当然,越剧同京剧不一样,越剧年轻,可塑性强,京剧相对地凝固,它走哪条路,向哪个方向迈进,不一定都很明确,要一步一步地来。但在指导思想上要常常想到,要学习越剧的革新积极性。这些方面需要京剧界要做更多的工作。
京剧同地方戏的关系这个问题也要研究和重视。梅兰芳、周信芳对地方戏不仅是尊重和热爱,他们是真的认为地方戏对京剧有很大帮助。地方戏剧团到北京上海演出,他们几乎是无戏不看。出外旅行演出,也尽可能挤时间去观摩,并且还参加座谈,写文章。现在地方戏经常有好的演出来北京,北京的青年京剧演员却大都不爱看戏。都说学梅兰芳、周信芳,首先在这一点上应该向他们学习。地方戏有许多新鲜、活泼的特色,值得学习借鉴。地方戏的唱腔能不能吸收,是不是吸收了地方戏唱腔就不成京剧了?其实,京剧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吸收了地方戏的因素,为什么不可以再吸收?你不吸收,将来别人逐渐把你吸收过去了。沪剧的邵滨逊多年前就大唱〔拨子〕了。
今天我仅是把想到的问题提出来了,怎么样解决这些问题,这里不可能多谈,也还需要同仁志士在实践中探讨。
京剧要出大演员、大评家
叶秀山 作为知识分子观众,我有两个要求:希望出大演员;希望出大评家。
为什么人们那么重视梅兰芳和周信芳?因为他们是不可抗拒的。无论中外,无论懂戏或不懂戏、喜欢还是不喜欢戏,你只要看他们的戏,就还想看,看多了,不喜欢的也就喜欢了,这就是不可抗拒。
我在上海长大,周信芳的戏看了不少。后来在北大,看梅兰芳、谭富英的《御碑享》,半夜排着队买票。有些情况,戏剧界圈里的人不一定知道,譬如,我的老师辈的教授们大部分都喜欢京戏,有些是搞西洋的,喜欢得很。钱穆在他写的书里也提到京戏,他说,那个时候他坐黄包车去学校教课,走在路上,听路旁店里的无线电放京戏,那是最大的享受。已故的贺麟先生,他是西方哲学史和黑格尔哲学专家。他并不懂戏,但梅兰芳的《舞台生活四十年》,他看过两遍。我说那里面谈表演谈得很细,他说,他读里面连贯的意思,在怎样做人、怎样做工作,以及如何体现传统文化上,对他有启发。北大的教授,除了齐良骥(他是齐燕铭的堂弟,懂戏,会唱昆曲)外,像任华是搞古希腊哲学的,也会唱一些。有个姓杨的教授,他是校过叔本华的书,年轻时长期在国外,他特别喜欢京戏,能学两口杨小楼。还有个姓温的教授在美国16年,归国后研究古希腊,他后悔当年在北大没钱买票看戏。而现在又总是抱怨电台播放戏曲的时间太少。有一位搞语言学的朋友,唱花脸,会武场,在干校时唱样板戏他是总指挥。但现在不看戏,电视里的戏也不看,他认为没有好演员。
现在的京戏演员不大讲究表演技巧,老戏迷也不大愿意看了。京剧要振兴就要出不能抗拒的大演员,使得你必须看。以前谁要是不知道梅兰芳,人家说你没文化。
要出大评论家。五、六十年代我们喜欢京戏,看在座各位的文章我们受益不浅。现在的戏剧界,理论批评不活跃,要有领衔的评论家。这出戏经他评了,人家就信服,这就能带动相当一大批知识分子观众,因为他们平常都要看文章么。这方面的工作,戏曲界做得不如书法界。书法界是新起来的,现在搞得不错,他们的理论也很活跃。他们有一批人,大学里教书的,或者是做研究的,书协还有个研究部。他们的材料很丰富,他们从新的心理学、文艺学、文学批评,还有一些比较现代化一点的,如解释学、结构主义,用各种思想去理解传统书法艺术。当然也有一些问题,但这是一个起步。他们也有争论,争论很激烈,曾经有中国的书法所谓抽象、具象之争,有人说是抽象艺术,其实不是,后来逐渐闹清楚了,我们中国根本就不大分抽象、具象。书法界有个计划,他们请了搞美学的人开了会,还请了搞文学的人开会,就怎么理解我们的书法座谈。据说,他们还要请搞心理学、社会学的谈谈。我们戏剧界的评论赶不上,包括研究梅、周的,好像没有太多有份量的东西。
要有专门的研究,有活跃的讨论,各方面协作,互相交流。演员不大愿意听我们讲,我们讲得太抽象。有一次也是讨论梅兰芳,讲着讲着就收到了几个条子,说你要多讲梅兰芳。梅兰芳我讲不了太多,只能讲讲边边沿沿。演员不爱听,他们说,我们不懂理论,只知道演戏。这很好,但我们也要考虑观众,观众看戏是去理解你。怎么培养观众呢?当然首先得靠演员本身,然后还要看理论,靠评论去引导观众,提高观众的兴趣和理解力。
西方的艺术,我了解得很少,但像音乐界就有阿多诺这样的人,他是哲学家,又懂音乐,他把音乐带进哲学界,影响哲学。勋伯格的音乐很新,他十二音系谁懂啊?也不悦耳。有些人帮他讲,阿多诺帮他讲,讲得有道理,人们慢慢觉得这是创新,同“新古典主义”不一样,这是比较成功的经验。当然音乐界本身也喜欢理论,也写一些文章。绘画界也一样,比如理解梵高,都是通过一些评论家、哲学家,如海德格尔等的介绍、议论、研究,中国也有哲学家探讨他的画,读了这些文章,再去看梵高的作品,体会就不一样了。
扩大戏曲的影响,第一需要大演员,第二需要大评论家,你评了这个戏,我就放心了,你说好的,我要是不太懂,不能领略这出戏的好处,但我又相信你的评论比我强,于是我再去看,再去体会它,这就是评论家的威信。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继续奋斗
龚和德 19世纪的京剧,是以唱工老生领衔的,被观众称颂为“老三鼎甲”和“新三鼎甲”的演员,都是唱老生的。民国四年出版的王梦生的《梨园佳话》说得很清楚:“京师每一班中必有善唱之‘生’乃能成立,否则虽有佳伶妙剧,究嫌群龙无首,观者相率裹足矣。”到了20世纪,旦角的地位上升了,京剧才真正进入生、旦并重的新时期。梅、周二人,一旦一生,一北一南,为20世纪京剧的发展,都做出了辉煌的贡献。在19~20世纪的“世纪之交”,对生旦并重的新时期的到来,起着“导师”作用的,是谭鑫培和王瑶卿。可以说,梅、周是站在这两位巨人的肩膀上,继续奋斗,把京剧推向新和境域。当然,同时还有许多优秀演员在努力奋斗;梅、周是这个群体的杰出代表。
京剧是替代昆曲成为全国性大剧种的。昆曲该不该被替代?今后还能否保持一席之地?这都是学术问题,可以讨论,更需要用实践来作出回答。但,一个时期被替代了,是客观事实。过去曾有人认为,这种替代是历史的退步,胡适之则认为,“可算得中国戏剧史上一大革命”。田汉很欣赏这个说法,说过:“这却是胡适之留给我们的辉煌的思想遗产。”现在我们常把京昆并提,其实两者是有区别的。说昆曲是古典艺术,大概不成问题。那么京剧呢?能不能说京剧是同昆曲一样也是古典艺太呢?值得研究。京剧本质上是俗曲,是以两种花部声腔即北方的西皮和南方的二黄为其基本曲调的俗曲,它接受了昆曲的艺术遗产,才成为南北花雅的一种综合体。有些人把京剧接受昆曲的艺术遗产也是看作是一种退化,或者看作是今天的京剧之所以不景气的一种历史根源。事实上,如果京剧不在一定程度上“雅化”,特别是表演艺术上的精致化、规范化,它是成不了雅俗共赏、流行全国的大剧种的。各地有许多皮黄声腔剧种不能像京剧那样流行起来,就是有力的反证。京剧在北京成熟的时候,可以说它是中国古典戏曲的终结。它毕竟也是古典化了的,只是它以语言的通俗;曲调的单纯化而又富于戏剧性,表现形式的简洁和自由,比之地道的古典艺术──昆曲来,是一种带着许多活性、可塑性和发展潜能的新古典艺术。经过100多年的变化创造,京剧实际上已具有古典性与现代性双重品格的戏曲艺术了。如果它一点现代性都没有,它在本世纪前60年中是不可能那么流行的。
如果我上述的理解还可以成立的话,那么,我要说,梅、周二位大师,对于京剧这种双重品格的建构,都是起了很大作用的。
京剧的这种双重品格,在某种意义上体现为京朝派和海洋派的两种趋向及其互相影响。海洋派又称海派,是从上海兴起来的。1908年,南派艺人潘月樵与夏氏兄弟创办的新舞台及其创演的新剧,是海派京剧崛起的标志。这是当时京剧改革的一面旗帜。由于海派京剧带有全方位变革的性质,从而把原来的南北区别,激化为京海对峙。在对峙之中,梅、周取什么态度呢?他们各有自己的起点,各有自己的文化环境,但他们又都能从对方接受东西,起了融通作用,从而使各自的艺术都起了深刻的变化。他们这样做的起步都很早,民国元年~二年(1912~1913年),在不足20岁的青年时代,都已确立了艺术上的大致方向。
梅兰芳于1913第一次到上海。他后来回忆说:“我觉得当时上海舞台上的一切,都在进化,已经开始冲着新的方向迈步朝前走了。”五十几天在上海逗留,深感新鲜事物太多了,“要想吸收,可真有点应接不暇了”。他在回京的列车上,对着包房里的一盏昏黄灯光,彻底难眠,上海所见的一切,一幕一幕地在脑海里盘旋。他说:“我第一次到上海表演,是我一生在戏剧方面发展的一个重要关键。”梅后来在服装、化妆上的创新,表演上的改进,戏路上的拓宽等等,大多同从上海获得的启发分不开的。在梅去上海的前一年──1912年,谭鑫培第五次到上海,这对周信芳来说,同样是“一个重要关键”。周是南派出身,从小在南方流浪生活中习艺。12岁时与梅兰芳一起进过北京喜连成,带艺入科、借台唱戏。那时他就对谭鑫培“羡慕得不得了”,但无缘领略;后在京津看过三次,还领悟不了谭的妙处。直到1912年,在上海新新舞台,才有机会与谭同台献艺40天,并经人介绍,向谭学艺。对这件事,周在文字上从不提起,为的是不愿借谭自重,也不愿给尊谭派以某种口实。谭鑫培是京剧有史以来,在老生行当中唱念做打全能化与性格化的第一人。周信芳要走的就是谭的路子,他是谭氏之后最出色的全能化的性格演员。从梅、周的成长过程中可以看出,梅是“坐北朝南”,是最有革新精神的京朝派演员;周是“坐南朝北”的,用马彦祥的话说,是“最正派、最规矩的”海洋派演员。我这样说,并不想把他们“抹平”;他们还是有区别的。梅的艺术成果,更带古典色彩,而周比较激进,似乎更富于现代色彩。这是需要我们深入研究的课题,我只是谈点感觉。
目前京剧处于一种非常尴尬的境地。首先是振兴京剧的艺术基础已经非常薄弱了。京剧艺术的积累主要不是体现在《传统剧目汇编》这类书本上,而是体现在演员的身上;现在演员身上保留的传统剧目已经不多了,有的虽然还能演出,但真正演得到位的很少。大量的传统技艺已经失传。有些高难度技艺比过去有发展,如转体180°变为360°之类,但表演艺术水平──用唱念做打以刻画人物的综合水平,比梅、周均已下降。所以一个重要任务,必须抢救一些即将失传的传统剧目和传统技艺;抢救下来之后,还要加工提高,把它精致化、典范化。像于魁智抢救李少春的《响马传》工作,应当提倡大家努力去做。另一方面,京剧与当代观众的疏离又是相当严重的。光靠演老戏,难以争夺新观众,就是老观众也要看新剧目。所以,创造新剧目,在艺术上有新的发展,新的创造,也是当务之急。这种双重任务,在某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京剧的古典性与现代性双重品格的继续发展所必需的。譬如说,三国戏中的《群英会》我们要,它是古典的代表;《曹操与杨修》我们也要,它是现代的代表。两项任务不要对立起来,应当互补。我们看梅、周一生的演出剧目,也是新的老的都有,不是只顾一头。他们常常把老戏演出新意、新水平;把新戏演得有老的“骨子”。这样,才能吸引广大的新老观众。所以梅、周两位大师正确解决继承与革新关系的丰富经验,值得我们认真总结。他们两个人,不但京海融通,而且注意从整个戏曲文化中汲取营养。他们还关注现代艺术,包括西方艺术,从中获得借鉴。他们都是搞大综合的。可以说,作为一个剧种,没有大的综合,就形成不了全国性大剧种;作为一个演员,没有大的综合,就成不了大艺术家。
现在又到了“世纪之交”了。我们希望进入21世纪的新一代演员,能站在梅、周两位巨人的肩膀上,继续奋斗,再把京剧推向更新的境界。
结束语
郭汉城 今天这个会开得很好,大家发表了不少很好的见解,研究了梅兰芳、周信芳的艺术成就、道德品质和敬业精神,同时也同当前京剧发展的形势结合起来,提出了有价值的意见。梅、周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不是两三个小时就谈完的,研究他们的成就,学习他们的品德,这是长时期的重要课题。这个工作今后要不断地做。
一个时代的艺术总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的,这是客观规律。梅兰芳、周信芳的艺术发展,有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的条件、特点;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戏曲处在新的转折时期,面对着一个多元的、竞争的局面。不仅各种艺术之间有竞争,戏剧内部的不同剧种之间也有竞争。竞争的结果如何?谁优谁劣?谁胜谁败?谁执剧坛的牛耳?谁处于微弱的地位?在今天纪念梅、周二位艺术大师的时候,这是一个值得提出来研究的问题。
历史是公平的,又是无情的。它对谁都提供了机会,但并不特别地眷顾哪一个。我以为在我们这个时代的各个剧种,谁都有资格为盟主,但不是命中注定非谁莫属。从建国以来许多剧种消长变化中,已经包含着这种端倪。我不赞成京剧灭亡论,但是问题要看自身的努力。在这个转折时期,要不要改革,要不要反映这个时代,要不要进行艺术改革去满足广大群众的需求,这要靠自身的努力,任何人也不能给予,任何优越的条件也不能代替。京剧界发扬梅、周二位艺术大师的精神,立大志,办大事,出大演员、大作家、大艺术家,出艺术精品,皇天不负苦心人,经过这样努力,继续在中国戏曲领域里保持盟主的地位,这不是没有可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