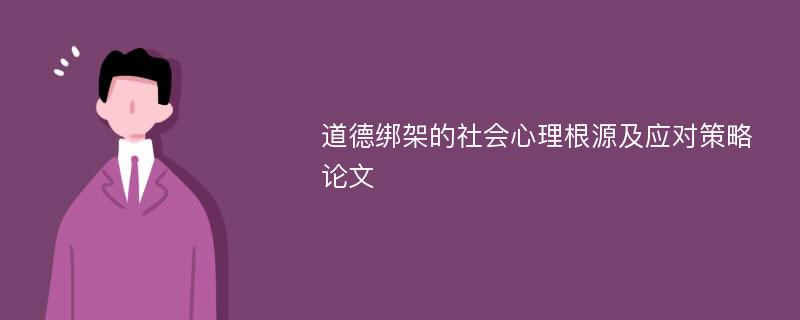
道德绑架的社会心理根源及应对策略
黄 岩,唐青青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8)
摘要: 道德绑架是人们以道德的名义,按照其认定的道德标准,通过舆论压力干涉他人道德行为选择的一种现象。道德绑架的发生既与道德本身的性质有关,也与一定时期内人们的社会心理有关。道德绑架具有善恶并存性、软约束性以及公开性等主要特征。作为一种道德异化,道德绑架既损害了人们的意志自由,又增加了社会的不稳定因素。消减或规避道德绑架的主要途径为加强公民道德知识教育,完善社会公正制度,引导新闻媒体正确行使话语权等方式。
关键词: 道德绑架;社会心理;道德义务
道德绑架顾名思义就是利用道德进行绑架,即绑架主体按照自己认定的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通过强迫手段,迫使绑架对象放弃其自由意志从而按照绑架主体的意志行动。道德绑架的立场是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依据是“善意”的情感,手段是制造舆论漩涡,最终结果就是“以道德之名,行绑架之实”。近年来,道德绑架现象频繁出现在公众视野,例如QQ、微信等交流平台使朋友圈变成“绑架”拉票圈;公共场合老人倚老卖老强迫他人为其让座;社会公众“劫富济贫”胁迫强势群体帮助处于弱势地位的群体……学界对这类现象主要聚焦于伦理学或传播学的视角,侧重分析道德绑架与道德自由的关系,道德何以能“绑架”人,以及网络舆论中的道德绑架现象等。事实上,道德绑架现象的出现既与行为主体的活动有关,更与行为主体的社会心理密切相关。如果离开了社会心理角度,将很难透彻分析参与者的动机和心理,难以探究出道德绑架的实质。因此,只有从社会心理的研究视角,综合运用多种学科知识,才能拓展我们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并提出相应的解决路径。
一、道德绑架的主要特征及其危害
道德绑架的主要特征是指道德绑架区别于其他事物的主要性质与特点。总的来说,道德绑架主要有三个方面特征:善恶并存性、软约束性以及公开性。
三是加强网络反恐刑事司法合作。为有效预防和打击国际性犯罪,国家之间往往在刑事领域开展多种形式的合作,从早期的文书送达、调查取证,到罪犯的引渡、被判刑人的移送、刑事诉讼移转管辖、合作执行刑事判决等。网络恐怖主义不同于传统恐怖主义,其在边界上的模糊性导致管辖权的不明确,网络反恐合作中首先应当解决管辖权的归属问题。网络恐怖主义国际性因素导致流动性更强,为有效惩治恐怖分子,还有必要具体细化关于引渡的具体规定。同时,鉴于网络恐怖主义高度的隐蔽性,国家之间应当采取高效的刑事司法协助,重视调查取证、送达等后期合作的内容,保障网络反恐合作顺利进行。
第一个特征是善恶并存性。通常情况下,道德绑架者的出发点是具有道德性的,其动机大多是为了维护确实需要帮助的弱势群体的真正权益。说他们的出发点是具有道德性的,基于两方面理由:一是它以道德的理由而非其他理由展开;二是它要求完成的行为是道德行为而非不道德行为。因此,绑架者在“绑架”他人时,总是显得理直气壮。然而,从事件性质和解决手段来说,道德绑架又是恶的。当今社会,诸多道德绑架行为都是通过网络媒体,借助网民的力量,强制性敦促或要求处于社会优势地位群体公开帮助弱势群体。在这一过程中,绑架主体按照自己认定的道德原则,完全不顾及被绑架者的感受,甚至视自己为正义的化身,公开要求他人履行或终止某些行为。诚如列宁所言:“善良的愿望往往把人引入地狱”[1],道德绑架“善”的出发点往往妨碍他人道德自由甚至侵犯个人隐私等“恶”的结果产生,这就是道德绑架善恶并存的特性所在。
第二个特征是软约束性。道德绑架的软约束性是与法律意义上绑架的强制性相对而言。法律上的绑架主要是通过违法犯罪手段在时间和空间上限制他人的人身自由,这种绑架行为多以暴力方式呈现,具有强制性和胁迫性,对被绑架者的身体和心理造成双重伤害。而道德绑架不是一种赤裸裸的暴力行为,它一般通过社会舆论这种相对温和的方式迫使他人履行不属于自己的义务,社会舆论的软约束性决定了道德绑架的软约束性。道德绑架一般通过网络媒体平台对被绑架者进行口诛笔伐或者人身攻击,要挟或者强迫被绑架者做自己不愿做的事情。而当事人为了维护自己的声誉和形象,不得不按照社会舆论要求去做。这样就将应该做的变成了必须做的,或者是不一定要求这个人做的变成了一定要这个人做的。如果此时被绑架者不按照社会舆论的要求做,就会受到绑架主体的谴责和攻击,这样不仅造成被绑架者精神和心理上的压力和伤害,而且会对他们的道德品质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道德绑架的软约束性体现在无形中,虽然表面上看人们没有被强制着做某事,但实质上被绑架者的自由和权利受到了极大的限制,使其不得不被置于一种“非善即恶”的道德环境之中,按照“绑架者”们的意愿去进行自己的行为。
对“道德绑架现象”社会心理成因的分析,不是为其存在寻找借口,而是为了正视其存在的现实与危害,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有针对性地消减这一不良社会现象,进而净化整个社会的道德风尚。
通过对道德绑架特征的分析发现,道德绑架其实是一种道德异化,是把政治义务、法律义务同道德义务相混淆,进而强置于普通人身上的枷锁,严重危害人的主体性和自由性发展。第一,道德绑架是对人的道德自由权利的否定。道德绑架的主体自以为站在道德制高点,公然要求被绑架者让渡自己的权利以满足他人的利益,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被绑架者的合法权利,剥夺了当事者的道德自由。人们在这种情况下是无从选择的,而这种对人的道德自由的侵犯与剥夺往往是最大的不道德,因为“自由既是道德的前提,又是道德的表现。作为道德的前提,自由赋予了人类以选择自己行为的可能性,而正是这种可能性使人的行为获得道德意义,成为可以在道德上进行褒贬的对象。”[2]第二,道德绑架是对道德基础的曲解。道德的基础是人类精神的自律。伦理规范是人类社会一种自然法则,是在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国家的相互交往中产生的,表现着人类活动自主、自觉、自律的行为准则。而道德绑架则把道德当成胁迫他人的工具,是强加于人类社会的一种行为准则,它要求具有一般道德责任感的“强者”按照崇高的美德标准行事,体现着人类活动的被动性、被迫性、他律性。第三,道德绑架是对道德调节作用的弱化。法安天下,德润人心。与法律规范不同,道德规范主要依靠社会舆论、风俗习惯和人们的内心信念来进行调节,因而是一种柔性的调节。道德调节能够真正触动人的心灵,是提高人的精神境界、促进人自我完善的内在动力。而道德规范从内容上看,是有层次性的,从“底线道德”到“崇高道德”存在着一个由低层到高层的级差序列。如果不能正确区分道德的层次性要求,对所有的人都要求达到“忘我利他”的道德境界,不仅不能发挥道德触动人心灵的应有价值,反而会滋生社会道德逆反心理,不利于促进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
Petter Neksa[26]等通过研制的试验样机对以CO2为制冷工质的热泵热水器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在90℃的高温水下样机仍可正常运行,在0℃的环境温度下样机平均COP达到了4.3。
二、道德绑架产生的社会心理原因
自民国至今以来,虽以赞同“以诗为词”为主流,但仍存有个性化的反向论辩。施议曾在《词与音乐关系研究》中指出,苏轼“以诗为词”并没有很大的改革词风,其“独立抒情诗体只是其著作的一少部分,并没有彻底地打破‘诗庄词媚’、‘词为艳科’的传统观念”[12]230。崔海正在《东坡词研究中几个问题的再思考》中,则认为否定“以诗为词”这个命题比高举它好,因为“以诗为词”是从诗的立场来看词体,而不是立足于词本身来观察它的发展[4]330-331。
(一)非理性的“道德义愤”心理
随着科技的发展,社会已经进入了一个大数据时代。为了管理海量的数据信息,越来越多的企业需要引入数据库技术,这必然对各行各业的工作人员提出了新的要求,也对高校的非计算机专业的数据库课程教学提出了新的需求。
首先,网络环境的心理暗示催生了从众心理。网络信息的心理暗示主要是指人们接受来自网络平台五花八门、鱼龙混杂的信息,进而被这些信息所传递的情绪、态度、观念所影响。道德绑架事件开始往往会引发莫衷一是的声音,不同意见在网络平台上有意无意的传播,给其他人发出暗示,导致他们忽略理性思考、动摇价值立场、失去批判能力。其次,网络媒体的情绪传染激化了从众心理。网络媒体的情绪传染是媒体在与网民的互动中,将原来不同的态度、观点,逐渐整合为几种具有代表性的意见,从而误导公众选择。一定事件被媒体公开渲染后,一开始公众会有着几种不同的评价倾向,但部分网络媒体依靠其在专业知识、传播技术等方面的优势,垄断了网络话语权,它们在求新、求快、求奇的报道原则下,迅速将碎片化的信息整合成代表性意见。而一般公众囿于信息来源的局限性以及对媒体公信力的认可,往往自觉地接受媒体意见,对主流舆论偏听偏信。最后,网络大众的主动模仿实现了从众心理。网络大众的主动模仿是在心理暗示和情绪传染达到一定程度后,遵循主流舆论的做法,以实际行动表示支持或反对。2017年11月份发生的“红黄蓝幼儿园事件”虽然最后被证实只是谣言,但在事件的发酵过程中,公众对事件不进行简单筛选和判断,以主流舆论为标杆,自动屏蔽相反意见,最终“自动站队”,一致声讨、谴责红黄蓝幼儿园行径。因为在快节奏的今天,网民不愿花时间在海量的信息中辨别真伪,更倾向于依赖媒体的把关、引导作用,从而接受意识形态泾渭分明的信息,快速做出价值判断。
“强势群体”是指在经济水平和社会地位上处于主导地位的群体。“强势群体”偏见是指处在社会弱势地位的人,公开强迫处在社会优势地位的群体,无私地为陷入困境中的人伸出援助之手,并且认为这是他们应尽的社会责任和义务。传统上,中国是个道德社会,民间弱势群体在解决问题时往往有一种“依赖心理”,即寄希望于强势群体的同情和“施惠”。所以,在经济相对落后、贫富差距突出、制度无法解决相对不公、法律相对不健全的情况下,会本能地做出道德绑架的行为选择。当今,从表面上看,强势群体在医疗卫生、住房、教育等领域都比弱势群体享受更多的发展机遇,这导致弱势群体片面认为是不公平的社会制度造就了强势群体。比如,天津港爆炸事故发生后,不少网友纷纷在马云微博下留言,质问马云为什么不捐款?要求马云捐款的理由主要集中在“你有钱,你应该捐款”“人家娱乐明星都已经捐款了,你更应该捐款”“如果不捐款,迟早你会身败名裂”。事实上,马云作为强势群体的一员,他的成功并不是因为不公平的社会制度产生的,但网民却错误地认为马云的成功利用了社会不公,侵占了弱势群体的利益。究其原因,产生这种偏见主要是因为强弱势群体之间不管是在经济水平、社会地位上还是在话语权上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导致处于弱势地位的群体产生社会不公的心理,认为处在优势地位的群体有责任、有义务帮助身陷困境之人,而当强势群体没有采取援助时,他们就会聚集起来用言论“绑架”他人。
(二)社会不公引起的“强势群体”偏见
事实上,在善与恶之间,还存在广阔的中间地带,这些行为通常被人们称之为“正当”。比如,商人在公平规则下牟利的行为,就属于正当行为。我们经常在网络上看到“逼捐”的报道,往往就是公众对道德层次认识不清,把“自然义务”与“允许的义务”相混淆,误把“正当”行为当作“恶”行,从而站在道德制高点,导致道德义愤的产生。
2011年,人民日报曾刊文称“社会不公致国民‘弱势心理’蔓延”。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有了大幅度提升,为什么还会存在“弱势心理”蔓延的社会不公现象?这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分析:第一,从经济方面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不成熟,不同阶层利益分配不均衡。如:城乡二元结构导致教育制度、医疗保险制度、社会救助制度城乡差别化对待明显;收入分配制度不完善,初次分配中劳动收入比重低,津贴、补贴等隐性福利项目多;税收制度、税务法制不健全,工薪阶层监管严,富裕阶层逃税手段多……这些现象极大地加剧了贫富差距,增强了弱势群体的被剥夺感。第二,从政治方面看,政治参与体系不完善,弱势群体话语权缺失。在精英主义传统盛行的我国,强势群体能最大限度利用媒体表达自己的意愿,对政府政策有着较大的影响力,而弱势群体的呼声则常常难以得到响应。此外,贪污腐败和权力寻租现象的存在,更是极大地加剧了弱势群体的愤怒和无助感。第三,从民生保障方面看,尽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新时代,但不可否认的是,“入园难”“看病难”“就业难”“买房难”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依然存在。这些问题导致社会心理失衡现象蔓延,进一步催生着“强势群体”偏见现象的发生。
主要有专题分类、统计分析及查询检索等功能。数据可以通过图表展示的方式,按水利工程、农村水利、河湖开发治理、行业能力等四大专题进行统计分析。查询检索主要分为简单检索和高级检索,实现对数据的模糊查询、属性查询、多条件联合查询、详细信息查看、定位等功能。
(三)网络舆论引导下的“从众心理”
从众心理是指个体在社会群体的无形压力下,不知不觉地与多数人保持一致的社会心理。“道德绑架是典型的媒体逼视,即媒体对私人领域过度公开的报道行为,并给被报道的个体带来他们本不应该承受的压力,是新闻媒体社会角色的错位”[4]。在网络环境下,由于信息发布迅捷性、内容海量性、交流互动性等特征,一个事件能够在短短几秒之内聚集大量的关注者。在网络世界中,关注者们会迅速成为一个群体,诚如社会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在其名著《乌合之众》中所述“群体最主要的特点表现为冲动、急躁、缺乏理性、没有判断力和批判精神,以及夸大的情感等等。”[5]受群体的影响,关注者们会形成与单独一个人迥然不同的感情、思维和行为。他们认为自己是理性的,但事实上,他们绝大多数行为的动机连他们自己都无法进行合理性解释。从社会心理学层面剖析网络舆论引导下的“从众心里”引发机制,主要包括网络信息的心理暗示、网络媒体的情绪传染、网络大众的主动模仿这几个阶段。其中,心理暗示是基础条件,情绪传染是必经之路,主动模仿是输出产品。
公众道德认知出现偏差往往是由于很少注意到道德要求的层次性,把普通人当作圣人,把道德当成美德。罗尔斯在其《正义论》中就曾对道德层次进行区分,把道德义务分为自然义务和“允许的义务”。他认为,自然义务是从契约论的观点中产生的,即“不以人们的明确的或默契的同意行为甚或自愿行为作为先决条件”[3]87-90,是一种不以人的自由意志为转移的义务。自然义务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要求我们做好事的义务。在他人处境艰难时及时给予帮助(假定帮助者在给予帮助时不会造成自我牺牲或伤害),这是一种肯定性质的义务。另一方面是要求我们不要做不好的事的义务,即不损害或者伤害他人、不对他人施加不必要的痛苦的义务,这是一种否定性质的义务。在这两种义务中,否定义务比肯定义务更加重要。同时,他又认为自然义务具有两个特征:其一,自然义务与制度和社会实践没有必然联系,不是由社会安排的规则确定的,不需要经过人的允诺,是人与生俱来的,不管愿意与否都必须承担,不以人的同意与自愿为前提;其二,自然义务是绝对的,对公民具有普遍的约束力,“不管人们隶属于什么制度而始终有效,它们在所有作为平等的道德个人中间得到公认。”[3]87-90相对于自然义务而言,还存在一种在道德判断上属于中立性质的行为,即人们可以自由地选择做或者不做,不违反任何职责或自然义务的行为,罗尔斯称其为“允许的行为”。“分外行为”从属于“允许的行为”,它并不是一个人的义务或职责,因为它经常涉及到行为者本人的很大牺牲或冒险。在罗尔斯看来,“仁慈”“怜悯”“英雄主义”“自我牺牲”等行为都是“分外行为”。
目前学术界虽然对道德绑架的理论研究成果不多,但是随着近几年道德绑架现象的不断增多,作为和谐社会中的“不和谐”音符,也逐渐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与探究。道德绑架问题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与人们某些社会心理密切相关。
三、消减道德绑架现象的三维路径
第三个特征是公开性。道德绑架不是私人间的道德劝说,而是公开胁迫他人违背自己的意愿做某事。公开性是绑架主体站在道德制高点,通过公共媒介形成一定社会舆论压力,胁迫他人从事道德行为的前提。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为道德绑架行为的发酵提供了滋生的土壤。求助者往往通过社交媒体寻求救助,同时媒体为迎合大众,也乐于曝光、炒作这种争议性较强的新闻,加上广大网民的推波助澜,被绑架者很快暴露于公众视野,站在舆论的风口浪尖上。比如,吉林贫困农民刘福成因女儿患有先天性心脏病,在积蓄花光、求助好友无果的情况下,他向国内六位富豪发去求助信。这本来只是私人间的求助,但是在经沈阳《华商晨报》报道,以及广大网民的“亲切关怀”之下,公众开始了对富翁行为的道德审判,最终私人求助演变成了道德绑架。事实上,对处于困难中的人进行救助属于救助者的自由意志,他们有权利决定是否对求助者进行救助,但是当这种行为被媒体报道之后,他们在舆论的巨大压力下不得不屈服于被绑架者的无理要求。因此,公开性是道德绑架的前提和必要条件。没有公开性,没有形成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就不能称之为道德绑架。
(一)以道德知识教育培育理性道德心态
道德绑架现象的滋生与人们对道德义务的曲解和道德知识的匮乏息息相关。相比较法律义务而言,道德义务不具有法律义务的强制性,而且,由于道德义务本身的层次性,导致道德义务的约束性也存在差异。比如,公平、诚信等维护社会有序运行的基本道德义务往往具有较强的约束力;而仁慈、慷慨等促进社会和谐的崇高道德义务的约束力则相对较弱。然而,由于公众对“自然义务”和“允许的义务”没有正确区分,把带有“理想期待”性质的行为当作“现实必须”,就必然会造成对他人道德权利的侵犯。一个人的行为是否道德,主要取决于他的行为是否有利于社会或他人,但这种“有利于”对应的是“有害于”,而不是“不利于”。只有其行为给社会或他人造成了危害,才能算作恶的行为。我们没有权利“绑架”任何人为了他人的利益而牺牲自己的利益,否则就是对“被绑架者”的不公。
在一个文明、法治的社会中,每个人都应该谨守基本的道德底线,同时也应该站在“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立场上,对他人的道德行为选择予以尊重和理解。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培育理性平和的社会心态,培育广大公众理性平和的道德心态,除了要厘清道德义务的底线和边界外,还要引导公众运用全面的、发展的、联系的观点审视和把握社会现象,避免对道德问题采取情绪化、简单化、散漫化的行为方式。尊重他人选择自由,才能有自身的选择自由。在快速变革的社会环境中,公众只有具备足够的道德知识,保持处变不惊,理性平和的道德心态,才能理性认知他人的道德行为及道德生活,做出有利于社会和他人的道德选择。
简单说,义愤就是人们对社会上非正义事情所产生的愤慨,而道德义愤就是指人们对违反道德规范行为的愤怒与厌恶。道德义愤有理性和非理性之分,理性的道德义愤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不道德行为起到监督作用,减少社会上不道德行为的发生,推动社会的良性互动;而非理性的道德义愤往往会加剧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导致社会秩序的混乱。事实上,理性道德义愤往往在群体的作用下演变成非理性的道德义愤,因为个人在群体中就像“失去理性的乌合之众”,在“意见领袖”的带领下做一些极端行为,而正是这一非理性的道德义愤加剧了道德绑架。非理性群体一致对外地指向别人,仿佛自己拥有道德豁免权。他们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完全符合道德要求和道德规范,在没有全面掌握事情的来龙去脉之前歪曲事实,以讹传讹,完全按照自己的利益偏好做出道德评判,影响大众的道德判断。不管是在现实生活中还是在网络空间中出现的道德绑架以及道德失范现象都受到公众非理性道德义愤情绪的影响。而这种非理性的道德义愤的产生主要由于公众不具备完善的相关道德理论知识,没有形成正确的道德认知,因而在面对需要做出道德选择的情况下难以进行正确的道德判断。
(二)以公正社会制度消减公民“群体性偏见”
习近平同志2014年在主持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曾指出:“治国要道,在于公平正直”,营造良好社会道德风尚,同样需要建设公平公正的社会环境。诚如威尔逊所言:“要使一个人因为社会规范的合理性而遵从它,关键是要向他表明什么是公正。”[6]唯有公正社会制度的建设,才不会有大量“弱势心态”群体的存在,才会逐渐减少因自身利益得不到满足而采取极端暴力的方式博取社会眼球的道德绑架现象的发生。
首先,以“提低、扩中、调高”为导向,进一步完善分配机制。习近平指出:“我国经济发展的‘蛋糕’不断做大,但分配不公问题比较突出,收入差距、城乡区域公共服务水平差距较大。在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上,无论是实际情况,还是制度设计,都有不完善的地方。”[7]社会公正分配要以共享发展为基本理念和核心要义,通过调节国民收入的分配方式,着眼于缩小不同社会群体间的收入差距以及提高普通劳动者的收入,切实减轻弱势群体的“相对剥夺感”。
其次,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让弱势群体感受到制度的温暖。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是人们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有效保证。在共享发展的理念中,弱势群体应成为关注的焦点。要在发展中补齐民生短板,通过建立完善的失业保险制度、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合作医疗制度等,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和力度,让弱势群体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真正消减“强势群体”偏见心理产生的土壤。
最后,加快政治体制改革进程,完善弱势群体利益表达机制。传统模式下的政府决策方式具有浓厚的精英主义倾向,导致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难以得到表达。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要求,“保证人民在日常政治生活中有广泛持续深入参与的权利。”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是人民民主的真谛。完善弱势群体利益表达机制,既要拓宽弱势群体政治参与的渠道,也要限制强势群体在政治领域中的话语权。同时还要支持新闻媒介以及民间力量以理性、合法、正当的方式,为弱势群体发声,形成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的合力。只有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得到切实维护,才能从根本上调整“弱势群体”的暴戾心态,减少道德绑架等暴力行为的发生。
Criteria for the AD:AD was determined by the following manifestations:erythema,pimples,scab,exudation,epidermal stripping off,and scales.
统计学分析采用SPSS13.0统计软件。数值以均数±标准差(±s)方式表示。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检测统计学显著性。当P<0.05时认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三)以强化媒介素养营造良好舆论氛围
信息时代的发展,网络媒体的兴起,拓宽了人们关注社会的渠道,也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社会舆论对社会心理的多元化导向。人们极易在群体暗示、传染等非理性心理的影响下,无意识地模仿他人的行为,对他人的言论不加筛选和判断地进行传播,偏听偏信。十九大报告指出:“加强互联网内容建设,建立网络综合治理体系,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道德绑架问题的日益凸显不仅与公众自身的道德素质密切相关,而且与媒体从业者、信息把关人能否正确、理性的引导舆论导向、行使话语权有一定的联系。不容置疑,部分媒体从业者为了博得公众的眼球,谋求自身的利益,在信息生产的过程中根据自己的主观因素对客观事实进行道德审判,对真实事件进行非理性的表达和传播,误导了舆论方向,极大地造成社会生活的无序化。为此,我们应监督引导媒体从业者在信息的生产和传播的过程中,严格约束自身行为,积极引导舆论导向,构建健康有序的舆论氛围。
首先,培育正确的传播价值观,提升新闻媒体人的职业操守。目前,一些新闻记者受金钱和权力的“绑架”,丧失了作为社会公众人物的基本责任心。在他们心中,作为国家“第四权力主体”的新闻媒介已经异化成用来绑架大众情绪、干涉他人选择、损害公众利益的“合法工具”。因此,新闻媒体人作为信息传播的主要把关人,除了具备专业的知识素养之外,更应具备正确的传媒价值观,谨慎行使自己手中的话语权力。其次,培育理性的新闻收集观念,注重新闻内容的多元化收集。道德绑架作为弱者与强者的博弈,很容易触动社会大众的同情心,使大众不自觉地移情去感受弱者的命运,使得社会舆论中蔓延着消极的情绪和非理性的价值判断,这就导致在新闻内容的收集过程中总是存在虚假信息。因此,新闻媒体人一定要注重信息收集的多元化,既要关注公众的舆论,也要考虑当事人的态度,要从全局分析新闻事件,避免片面的、不实的新闻报道。最后,培育监管部门的法治意识,加大传播平台的监管力度。客观上来说新闻传播平台本身的自由性,使其难以得到有效的监管;从主观来说相关监管部门“老好人”心理作祟,往往是导致他们不愿“得罪”媒体,遇事相互推诿的重要原因。因此,培育监管部门的程序意识、制度意识、规则意识,进一步加大传播平台监管力度,是确保新闻媒体正确行使话语权的重要一环。
四、结语
道德绑架作为一种不良社会现象,其形成有着深刻的社会和个体原因。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现象是一种长期的历史性存在,只是在网络信息技术的助推下,演变得尤为激烈,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也日趋显现。但只要我们有足够智慧,理性看待这一现象,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导下,坚持多管齐下、综合治理,可以预见,我国公民的道德素质必将极大提高,道德绑架现象也一定会逐步消减。
参考文献
[1]列宁.列宁全集:第1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256.
[2]沈晓阳.论“道德应当”与“道德必须”[J].东方论坛,2002(1):52-57.
[3]罗尔斯.正义论[M].何怀宏,何包钢,廖申白,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4]陈力丹,王辰瑶.“舆论绑架”与媒体逼视—论公共媒体对私人领域的僭越[J].新闻界,2006(2):24-26.
[5]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M].戴光年,译.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0:24.
[6]约翰·威尔逊.道德教育新论[M].蒋一之,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2:90.
[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87.
On Social Psychological Source and Countermeasures of Moral Kidnapping
HUANG Yan, TANG Qing-qing
(School of Marxism ,Hangzhou Dianzi University ,Hangzhou Zhejiang 310018,China )
Abstract : Moral kidnapping is a phenomenon that people interfere in others’ choice of moral behaviors in the name of moral cognizance, with their moral standards and through the pressure of the public opinions. Not only is the occur of the moral kidnapping related to the moral nature itself, but also it is related to a certain period of people’s social psychology. The mai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moral kidnapping are in coexistence of the good and the evil, the soft restraint and the publicity. As a phenomenon of moral alienation, the moral kidnapping damages the freedom of people’s will, and increases unstable factors of society. The chief methods to reduce or avoid the moral kidnapping are as follows: strengthening the moral education of citizens, improving the social justice system, and guiding the news media to exercise the right of discourse correctly.
Key words : moral kidnapping; social psychology; moral obligation
中图分类号: B8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1-9146( 2019) 02-0037-06
DOI: 10.13954/j.cnki.hduss.2019.02.006
收稿日期: 2018-06-06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5ZDC023);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14MKSZ01ZD-3YB)
作者简介: 黄岩(1971-),男,江西都昌人,法学博士,教授,德育理论与实践研究.
标签:道德绑架论文; 社会心理论文; 道德义务论文;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