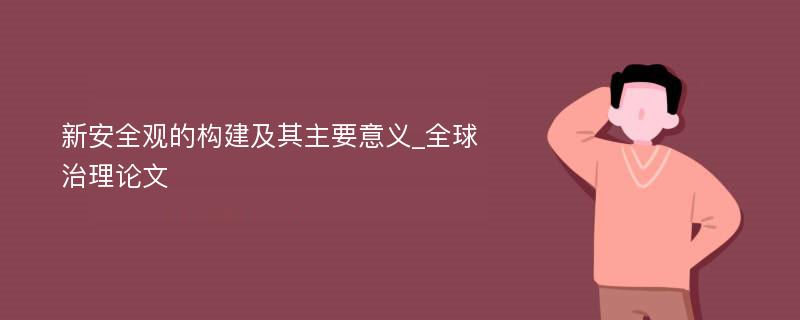
新安全观的建构及其要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要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241(2015)06-0061-21 二次大战后尤其是冷战结束后,传统的大战威胁减弱,非传统的安全威胁层出不穷且扩散至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2014年以来,从西方到东方接连爆发重大安全事件,如马航客机事件、乌克兰危机、极端组织伊斯兰国(IS)突起、非洲埃博拉病毒蔓延、中日钓鱼岛争端加剧、巴黎两次连环恐怖袭击事件等。物质文明的巨大进步未能保全人类平安,反而在某些时空里成了安全威胁的渊薮。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人类的安全观念没有跟上安全形势的变化,以致缺乏有效对策。本文尝试系统探讨新安全观的建构,就新安全观的架构和逻辑进行一些研究和思考,以期有助于把握和应对复杂多变的安全现实。 一、新安全观的出发点 新安全观基于新的安全情势,其出发点就是当今世界复杂多变的安全现实,涉及安全情境、安全行为体、安全问题等方面的具体状况和变化轨迹。 从全局和深层次看,自二战结束以来,国际局势相对稳定,世界大战未再发生且潜在危险大为降低。但小规模的武装冲突和局部战争从未停息。据美国统计,1946-1989年间、1989-2013年间,全世界共爆发各类武装冲突分别是144起、254起。①这些武装冲突绝大部分发生在国家内部。据瑞典学者统计,1960-2013年,全世界共发生武装冲突205起,其中仅36起为国际冲突,占比17.6%;其余169起皆为国内冲突,占比82.4%,②对国际、地区安全影响有限。同时,由于没有美苏对抗的背景,这些武装冲突、局部战争的规模、暴烈度和残酷度均显著下降。除了冷战后的海湾战争及波黑战争、科索沃战争、车臣战争规模较大外,绝大多数武装冲突的规模不足万人,甚至仅有数百人而已。与过去相比,其暴烈度大减,致人伤亡数量占总人口之比一路走低,大致从原始时代的15%降为20世纪的3%。③ 然而,从局部和表象看,世界似乎更不安全。饥饿、流血、死亡等动荡、危险的报道充斥各种媒介,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当今安全形势的复杂性。 第一,安全问题复杂多样。当今人类面临的安全威胁和安全问题涉及世界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指向、来源于各类行为体,并且不断衍生出新的变种。按照形式,可以分为显性的和隐性的两类:前者有外露、易于感受的表象,如战争、武装冲突、恐怖主义袭击、民族分离、网络攻击与窃密、走私与贩毒、地震与海啸、传染病、饥荒等;后者则比较隐蔽且较慢释放出恶果,包括放射性物质、病毒病菌、转基因物质等对于人类神经系统和遗传基因的损害以及废气和化学品对于空气、水、土壤、生态系统的侵蚀及其引发的问题,如物种减少或灭绝、战争后遗症、出生缺陷、酸雨、大气污染与气温变暖等。按照逻辑,可以分为三个大类:一类是人类社会机体上的重大问题,涉及政治、经济、信息、文化等方面的安全;另一类是人类与大自然的关系问题,涉及环境、资源、石油、水资源等方面的安全;第三类是人类自然肌体上的重大问题,主要涉及公共卫生和社会方面的安全。按照领域,可分为军事安全、政治安全、经济安全、环境安全、食品和卫生安全等,囊括了人类生活和生产的各个方面。1994年,联合国开发署在首份《人类发展报告》提出“人类安全”概念,将人类安全归纳为经济安全、粮食安全、卫生安全、环境安全、人身安全、共同体安全、政治安全等7大类。④英国学者巴瑞·布赞与其欧洲同行提出了5个安全领域(军事、政治、经济、社会和环境等)的著名分析框架。⑤美、日学者在传统的军事安全、政治安全之外,列举了环境恶化、资源问题、恐怖主义等8类非传统安全问题。⑥中国学者在军事安全、政治安全之外列举的安全问题多达30种,分为7大类。⑦按照指涉对象和威胁来源,可划分为两个层次:外延层次上有个体安全、社区安全、国家安全、国际安全、世界安全、全球安全等;内涵层次上有合作安全、共同安全、综合安全、集体安全、人类安全等。这些分类虽视角不同但可以相互参照和补充,总体上反映了当今安全问题的全貌。这些问题尤其是工业化时代的核、化学和生物等具有潜在毁灭性的环境问题都与人类自己脱不了干系,缘于人类的决策和功利性追求。 第二,安全基础松动。行为体的数量、种类大增,推动其相互关系重组或新建,总体安全格局尚未定型。一是国家行为体作为安全的主要实践者和保障力量在角色定位与相互关系架构方面仍在调整。二次大战以来,国际局势急剧变化,两极对抗转变为和平与斗争相交织的后冷战状态,围绕美、苏(俄)关系转轨,国家间关系大分化、大组合。中国因为快速崛起而成重要变量。国际制度建设步入转型期,新型国际组织20国集团、金砖国家集团等突起,传统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纷纷重新分配国家代表权。唯一全球性政府组织——联合国关于国家代表权再分配的安理会改革问题至今未解。因此,主要国家间的矛盾不断凸显,妨碍了重大安全问题上的合作应对。 二是非国家行为体迅速增多,其影响日益上升。这些行为体既有政府间和非政府间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机构等,又有后起的分离主义势力、恐怖主义组织、跨国犯罪团体。最主要的当属国际组织和跨国公司。有据可查的国际组织总数从1970年代末的1.5万个迅速增至2013年的6.7万个,其中绝大多数是非政府组织。⑧跨国公司及其海外分支机构则分别从1990年代初约3.7万、17万⑨猛增到2013年的约11万、90万。全球恐怖主义组织目前已超过2,000个。⑩2013年,可确认参与恐怖袭击的组织超过220个,包括“基地”组织的分支IS。(11)另外,还有许多其他组织、机构和团体。这些非国家行为体无处不在,并以其特有的方式表达诉求、显示影响力,成为参与解决全球性问题或者制造麻烦的重要行为体,如绿色和平组织在生态环境保护中的积极作用、“基地”组织在中东乃至世界格局中的破坏性影响。由此产生了国家行为体与非国家行为体如何相处的问题,对国家作为主要行为体的角色定位调整提出更高要求。两类行为体间利害关系的多元性使国内、国际的安全问题频密交织在一起。 三是全球安全领域的议程建构、问题治理困难重重。由于主要国家间的分歧和斗争,气候变化、温室气体减排、军事安全等重大安全问题的全球治理一直不顺。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简称《公约》)为例。《公约》自1990年代初即获绝大多数国家签署、批准而生效,但由于美、加等国不愿意接受强制性减排义务,《公约》的补充条款《京都议定书》2012年后第二承诺期的减排计划无法如期实施。与此密切相关的是,1992、2000年先后通过的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及其框架下的《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涉及转基因生物安全问题),由于美国等极少数关键国家拒绝签署而一直难以有效实施。(12)全球贸易经济一体化议程的推进更是举步维艰。全球多边谈判自WTO诞生以来一直僵持,2013年12月才在印尼巴厘岛签署了首份全球多边贸易协议。(13)联合国作为唯一全球性治理平台和机制显得能力不足、效率低下。事关全球民众安全的常规武器管控在联合国议程中长期得不到美、俄等武器产销大国的支持,《武器贸易条约》(ATT)的签署1980年就提上议程,却拖至2013年4月才尘埃落定。然而,全球武器进出口交易仍在走高,非法的武器出口也未停止。据统计,2013年,世界军费开支总额为1.747万亿美元,其中约有1/3用于武器采购。(14)主要国家武器出口占常规武器贸易交割额的90%以上。(15)武器扩散的威胁可见一斑。 第三,安全边界模糊化,安全问题在放大。一是安全的物理边界已经洞开。宏观上,安全的物理边界不再局限于传统意义中国家的领土、领海和领空,而是在其基础上延伸到太空和外太空。一般参照国际航空联合会(FAI)接受的标准,以海拔100千米高度为大气层与外层空间的分界线,即“卡门线”(Kármán line)。卡门线以外的外层空气空间则不属于任何国家主权控制的范围,(16)实际上就是无国界空间,如今日益成为航天技术大国显示实力和开展技术竞争的重要场所。微观上,安全的物理边界不再局限于政府和军警驻地及相关建筑设施、器械用具等国家安全载体,还包括象征公共利益的公共安全和社会安全载体。美学者认为,全球化经济正在降低各国边界的重要性,世界人口的跨境流动,使民族之间界线越来越模糊。(17) 二是安全的虚拟边界正在无限扩展。电子技术和信息技术已能突破地球上几乎所有的屏障。物质进步显现出高度透明和快速变动的双重特点。(18)这在大数据时代更为突出。一切介质性的文件、资料、信息等都可以数据化,并通过互联网和其他存储、传输设备供全人类即时共享。对数据的存储、提炼、应用、解读和判断,都在挑战和改变人类的交往方式、生活方式、思考方式以至思想认识。(19)这种空前的共享便利带来巨大安全隐患,所有涉及国家利益、安全机密和个人隐私的数据化信息都可能遭遇棱镜门式渗透、病毒式破坏、黑客式攻击,从而暴露于众或被窃取。故而,世界各国纷纷打造信息边疆,加强信息安全系统的建设。 三是安全的场域界限日益模糊,安全化现象不断扩散。各种安全问题交叉、重叠的现象越来越多,安全的问题领域日益混淆、界限日益模糊。人口爆炸可谓典型案例。它聚合了几乎全部的安全问题,带来发展和分配的严重失衡,引发一系列社会矛盾、冲突,而且加速了传染病的蔓延和犯罪活动的实地勾联,以致人本身成为活的安全威胁源。经济问题安全化更是常态化、广泛化。在国家内部,各国普遍急功近利地实行指标化、物质化、市场化的经济发展模式,极大地刺激了物欲并过度消耗能源、资源,带来经济、环境、社会等领域的安全问题。在国家外部,国际关系的主题从军事政治对抗转向经济竞争,政治目的主要通过经济的形式、手段加以实现。经贸合作乃至反面的经济、金融制裁都成为许多国家安全利益的一部分,也是重要的国际政治或安全议题。例如,在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贸易、援助、发展及国际经济秩序改革等议题成了斗争焦点。发展中国家受到贸易、金融、服务全球化的巨大冲击,其重大安全任务就包括反对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干涉、贸易干预主义和保护主义等,抵御西方倾销其“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又比如,恐怖主义兼具国内与国际、经济与政治相互转化的特点,本质上是经济社会资源分配失衡引起的社会矛盾白热化,如今已成为安全化程度最高的全球性议题。 二、新安全观的架构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指出:“要跟上时代前进步伐,就不能身体已进入21世纪,而脑袋还停留在冷战思维、零和博弈的旧时代。”(20)新安全观必须贴近当今的安全现实,以更广阔的视野、更理性的价值标准去判断安全利害,去看待国家实力及其运用,归根结底要有超越传统惯性的时空观、价值观和战略观。 第一,建构跨时空观。古往今来,世界上的和与战、治与乱、安与危皆非一时一地之事,也非一国一朝之事,而是有着深刻的历史继承性和广泛的地理关联性。所谓:“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这就要求将长时段与大空间相结合,综合运用历史规律论与地理作用论,同时避免将视野和思维局限于一时一事的危机表象及应对。由此形成的安全观才能真正高瞻远瞩,增强战略决心和战略定力,如习主席所说,“不惹事、也不怕事”。(21) 一是强化宏观和长远的安全认知,把握安全形势变化的主线和规律。这需要以开放性和立体化的视野关注安全大势。从自然安全看,最大莫过于气候变化问题。众所周知,全球气候几百年来一直在冷暖之中交替、循环。近代工业革命以来,全球气候总体变暖,国际社会从20世纪中后期开始对此关注并加以遏制,如缔约、减排等。然而,科学界从长时段进行考察后日益坚定地认为,全球气候不是在变暖,而是变冷。2005年,荷兰地质学家提出,气候变暖等所有自然变化,从地球的立场出发都是正常的;大自然有其四季更替,周期是一万年,“春季”始于万年前,现今在“夏季”——气温本该升高,再过万年将入“秋季”、继而“冬季”。这个长周期“超越了现阶段人类思考的尺度”,因为人类通常只考虑一代人、最多几代人的事,否则“也许四百代以后的人类会为我们现在排放二氧化碳而高兴,他们的秋天因此而变得不太寒冷”。(22)2013年3月,美国学者在最新研究中称,地球上的气温从约7,000年前起一直在下降,降温的平均值和最高值分别为0.7℃、2℃,至近代工业革命时期转暖。(23)同年4月,俄罗斯科学家指出,人类可能处在一个200—250年的气候变冷期。(24)如果各国政治精英认同这个结论并据此应对气候变化,则气候变暖将会退出安全议程,合作减排的行动计划势必终结。 从社会安全看,最大莫过于和与战的问题。考察两次世界大战,从国家诞生以来的5,500多年和总共14.5万次人类战争看,(25)就会更关注大战与其他战争之异同,有感于历史长河中的小水滴、历史和文学作品中的壮美篇章;从20世纪看,那是规模最大、卷入国家最广泛、参战与伤亡人员最多的许多战役;再从战争过程看,那是一次次血腥厮杀和决斗,是工具利器的性能较量,由此就会悲叹正义的来之不易和人类文明的惨烈倒退。正是殷鉴于历史教训,如今大国如美俄,相互之间虽然分歧和矛盾不断,但都力避撕破脸皮,在斗争中谋求合作。仍在继续的美西方与阿拉伯国家间矛盾,原本是其历史冲突的延续,并非亨廷顿所谓基督教世界与伊斯兰教世界间的“文明冲突”,上可及两大宗教早期的正统地位之争,下可至7世纪阿拉伯帝国对罗马帝国的征战及1096-1291年的“十字军远征”,中间还掺进了犹太教因素,总体上是三大宗教同源不同流背景下的兄弟阋墙,始终有美西方的身影,可谓欧、美、中东地缘政治关系的剪影。 二是坚持关联性的安全思路,探究安全问题的重要变化及其内在动力。这需要基于大空间的长历史,关注安全问题的连接因子及其相互作用原理,因而必须将“历史”看成一个个国王、一场场战争、一次次革命的连续演出。(26)2010年底以来中东剧变的生动画卷表明:安全事态不是断续的片段,而是随时可以串起并酿成新事件的酵母;任一不起眼的安全事件都可能发散成巨大安全乱局。中东剧变正是信息技术和互联网这种“无组织的组织力量”催发的众多安全事件之串连,一个人、一批人借之可以迅速动员、聚合而成庞大的群体,去实现与回报、利润无关的共同社会目标。(27)2010年12月,突尼斯一名失业大学毕业生因为无证自营水果的摊车被没收而自焚,其后数百名年轻抗议者遭警察以催泪瓦斯驱赶,该事件影象通过社交网站Facebook、YouTube等广泛传播,引发全国性的骚乱和抗议直至政权更迭,后不断扩散到大中东近20国,至今余波未平。期间,美西方领导北约组织借机对利比亚实行新军事干涉,拉开了该国动乱的帷幕。在大数据时代,过往与当下、远处与眼前通过数据化的文字、音像紧密相联,(28)在突发事件的触动下形成蝴蝶效应,引发大乱局。 第二,建构人性化导向的价值观。在安全事务中,人是最活跃的因素和主角,既主导行为体之间的关系,又对大自然施加作用。新安全观需要遵从这个基本事实,超越传统安全中国家中心、军事政治挂帅的价值取向,转而确立一切目标都要确保人命安全、一切手段都要合乎人性的价值定位和方向。 一是以人的福利、生命安全和人格尊严为最高目标。本质上,各种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最终落点都是个人或人类整体。因此,二战结束以来,世界发展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日益受到关注,并作为重大迫切问题进入联合国的议程。从1990年至今,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每年围绕不同主题发布《人类发展报告》,提出了一系列有益的意见和建议,以促进充分而公平、可持续的发展。其中,1994年《人类发展报告》提出并系统阐释了“人类安全”概念。(29)关于“人类安全”的标准解读即由此出。之后,“人类安全”的思想日益受到各国和国际社会的重视,并不断吸纳和突出平等、合作、人权、民主以及人与自然共生的话语和概念,影响到一些国家的安全政策、对外行为和地区秩序的规范基础。(30)例如,在主权与人权的关系问题上,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激烈争论有所缓和,或有让步和靠近。2005年9月,联合国大会第60届会议通过的《2005年世界首脑会议成果》中,重申了原由西方国家所提的“保护责任”概念并做了规范性定义,得到包括中国在内的150多个与会国家领导人的一致认可,即在一定条件下对发生践踏人权罪行的国家进行干预。(31)在实践中,发展中国家普遍比过去更加重视保障人权,例如,中国在1991-2014年间发布了11份人权白皮书。 二是坚持宏观把握、多种手段并用的安全治理思路。从应对主体看,国际安全问题关乎国家层面的人群关系,必须依靠相关国家的平等协商、协力合作加以解决。即使纯粹的国内问题在全球化时代也会与他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治理过程中必须从其国情出发,自力更生为主;外力只能扮演辅助的角色。如果外部大国仅凭一己私利而施压促变,必然会损害国际关系、恶化安全形势。美国国际问题专家卡赞斯坦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你试图塑造这个世界,世界将重塑你。正如美国在伊斯兰世界所做的事,这个世界会反弹。”(32) 从应对方式看,越是复杂的问题越需综合治理,越要经济、政治等多种手段并用。物质实力是必要但非万能的,使用什么力量,是由所要应对问题的性质决定的。一味地恃强、过度使用物质工具尤其是武力,只会造成生命伤亡以及心理创伤,难免引发敌意和报复。人类诞生数百万年来都无法揭示自身生命和宇宙生命系统的奥秘,遑论改造自然、征服自然。司马迁早就正告过:“恃德者昌,恃力者亡。”(33)故而,物质化的强力杀伐和征服必须无条件退居最后选择的位置,由此才有可能化险为夷,甚至消除滋生危险的土壤,实现可持续的安全。美国提出和实行“巧实力”外交,就有意于在外交上汲取恃强的教训,寻求使其实力运用可收预期效果的适当路径。(34) 三是从人性的特点出发探寻安全问题的源头,力避以主观臆断代替理性思考,以防陷入安全困境。人类追求的安全,是没有威胁的客观现实和不受威胁的主观感受,国家间安全尤其如此。没有威胁的客观现实意味着国家等各种行为体之间没有相互威胁的力量和行为反应。尽管权力政治观具有片面性,但国家追求权力是事实。这种追求的程度、所用方式和手段,取决于政治精英的主观选择,包括价值认知等理智成分和恐惧、好恶等情感成分。政治精英对某一特殊问题过分关心的情绪高度唤醒时,情感的卷入会妨碍正确地认识和成功地应对与自己目标有关的形势、方式和障碍,反应的灵活性就降低了。(35)安全威胁认知和安全困境事实作为一种负面状况,源头就是主观上的不安全感,即恐惧。安全困境的经典定义即指:“一个国家多方加强安全的行动必然削弱他国的安全感。”一国安全的加强常常引起他国恐惧,国家间相互恐惧就导致相互间意在增强自我安全感的军备扩充,从而加剧所有国家的不安全感,形成安全困境。(36) 世界历史和国际政治现实为此提供了一系列例证。美国专家研究发现,自远古以来,集体的安乐现状面临某种损害的政治恐惧一直影响着西方乃至世界的政治和文化。(37)著名的“修昔底德陷阱”虽然无法使其新老大国对抗的“宿命论”放之四海,但揭示了历史真相:伯罗奔尼撒战争之所以爆发,“真正原因是雅典势力的增长”以及由此引起的“斯巴达的恐惧”。(38)冷战时期,美苏之所以长期对抗,就是由于社会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而相互恐惧,进而相互攻讦、对立直至军事对抗。后冷战时期,美国害怕并防范的首要对象依然是俄,其在中东欧部署反导系统、力推北约、欧盟东扩就是以攻为守的对俄战略,结果导致俄的不满和对抗。美西方近些年来一直挑剔中国、不断炒作“中国威胁”论,则是由于害怕中国挑战其世界主导地位。卡赞斯坦谈到,他在美国内就“中国化”问题举行讲座时,所有听众都觉得中国化可怕、危险。(39)西方新近的研究指出,在冲突的决定性因素中,最重要的是人的因素(领导人)和重大危机中点燃火药桶之不可预见的火花因素。(40)因此,要想走出国家之间的“修昔底德陷阱”,根本途径是政治精英要努力化解本国和他国的恐惧。首先要分清恐惧的真伪;然后面对不同的威胁,力求戒除或克制恐惧,以免为恐惧所驱而临时做出针对性加强实力的偏激选择,从而引发难测的过激反应或对抗——恐惧循环和安全困境。 第三,建构大战略观。现今所说的大战略,指的是“运用国家力量,在一切可能想象的情况下满足国家安全目标的需要”之根本大计。(41)适用于安全领域的战略观,应是大战略观。(42)安全治理的大战略观就是道术结合观、本末相生观,亦即安全治理的系统论。它要求各国、国际社会在实行安全治理时,超越以行为体、问题、物利、时空为本位的思维定势和行动惯性,胸怀国家安全的大局,放眼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大潮。 一是明确高远的安全目标。国家是主要国际行为体,各国和世界安全的最高目标是以国家安全为中心、所有行为体的共同安全,是各种行为体均不受威胁且无威胁感、平等享有发展机会和分享发展成就的综合安全。各个具体安全目标的实现必须既分轻重缓急,又相互配合,并共同服务于国家、民族、人类发展的长远大局。因此,安全治理应该兼顾国家、个人、组织、社会、全人类的安全需要,坚持生命至上、义利兼顾的原则,以防出现本末倒置的结局,其中,主要应处理好主权与人权、国家之间以及人与自然等三组对立统一关系。为此,在国家间应摈弃冷战思维、零和思维,在人与自然间要破除奴役思维,以谋求人类群体关系的协调共生及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永续。 二是手段要适应目标。由于安全问题复杂多样且相互关联、相互交织,当今安全目标的实现不再如过去那般通过战争等军事行动消灭或者征服敌人,而要慑止现实的、潜在的或假想的敌人,解除其安全威胁,有效保障自身生死攸关的利益。(43)因此,手段与目标的关系要点不再是相互适应,而是手段要适应目标,即实力运用要服务于最高安全目标。在实力运用上,要根据实力的不同类型——硬实力、软实力和中间性实力(如美方所称“巧力量”)及其不同作用,加以既有区别又相互协调的运用。硬实力如军事、经济、科技等力量的运用效果日益让位于其静态价值——战略威慑作用,软实力日益重要但更需耗时积累和相宜运用(44),唯有巧实力可以粘合软硬实力、连接各种潜在力量并使之发挥作用,因而具有酵母的特性。(45)巧实力的运用本质上都是沉着、冷静地发挥战略定力,可以避免正面冲撞。如此一来,总体力量对比和相互信任就大有可能保持动态平衡,进而可在安全态势的良性循环中实现弹性安全。 三是坚守道义原则。国家行为体追求自我安全是天经地义的,但若损及其他行为体的安全会造成对抗和冲突,最终反害诸己。人类的文明演进过程就是崇尚理性、遵守道德、规制本能的过程,如此才能实现互尊、互信、互爱、互利。在安全治理中贯彻这种自利而利他的理念,有助于共同安全。因此,在没有统一权威的国际社会,多元行为体理应而且必须坚持合乎道义的规范原则,其实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倡导的道德仁义。道,就是自然和社会的法则,所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46)道的践行要依靠德、仁、义,所谓“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47)如何践行仁、义?“仁者,人也”(48),“克己复礼为仁”,(49)就是克制自己、关爱他人,追求自利和利他。“义”的繁体为“義”,从羊,与善、美同意;“义者,宜也”。(50)在实践中,道、德、仁、义主要体现于对利的态度。“利者,义之和也”,“物各得宜,不相妨害,于人则为义”。(51)“德者本也,财者末也。”(52)义利关系就是本末关系。本末相生,来自义利相和,定助道兴,则天下太平;舍本逐末,就是见利忘义,必使道废,终将乱。对外,如果国家恃强掠取,“往往会自讨苦吃”,直至衰亡。对内,如果全民逐利,则全国乱;如果国君心在功利,甚至让贪悭者掌管国家,则会“灾害并至”。(53) 三、新安全观的逻辑 新安全观应突出主观与客观方面各安全要素之间的关联性、协调性和变动性,体现出与安全本质、安全现实相契合的应然性。 第一,安全的本质在于平衡。当今世界的安全问题包含传统和非传统的安全问题,几乎涵盖了全部难题,造成发展失衡的困境。一是人类群体之间关系失衡,引发社会机体的病变,如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安全问题。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是权利分配、治理效果、经济发展等方面不平衡的结果,缘于人类群体的主观愿望与客观现实失衡,或者某类群体将自己的主观意志强加给另类群体,抑或人类群体的合理需求被忽视或压制。欧美在这个问题上充当了鲜活的反面教材。如英国学者所称,在世界范围内扩张“军事实力、权力”,“必要时通过武力将我们的生活方式强加给他人的欲望,是欧洲故事之根本”。(54)同样,中东国家目前之所以接连陷入动乱并成为恐怖主义的重灾区,主要原因即美国无视中东国家实际、一味推行西方模式,打破了中东原有的政治与战略平衡。二是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失衡,造成地球生命系统的病变,引发大自然对人类正常供给的不可持续,如资源枯减或短缺、环境污染、气候暖化、酸雨等。这种失衡主要集中在环境、能源和资源领域,完全是人类对自然资源和自然条件的不当利用、过度开发造成的。物质主义、技术工具打破了地球生态平衡后,人类就更加要以它们为“安全”保护伞,结果陷入更大危险。(55)三是人类精神与肉体的关系失衡,导致人类自然肌体的病变,如传染性疾病、艾滋病等。这种失衡主要涉及公共卫生安全、社会安全,同样要归咎于物质主义刺激下的人欲膨胀,以及人类认识水平、应对能力的不足。这一切的失衡和病变关乎各国和全人类的共同安全,关系到人类种群与作为其物质基础的生物圈乃至整个地球能否持续存活。 要想从根本上解决各种安全问题,就需要实现人类社会的平衡发展。这就要求全面实现平衡发展的目标:工具力量与价值力量之间的平衡发展,军事、政治与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之间的平衡发展,国家之间、非国家行为体之间及其相互间的平衡发展,以及所有生命体之间的平衡发展。其中,人类主体的本能与理性能否平衡发展就成为关键。因此,人类实现平衡发展的唯一途径只能是,改变甚至去除残酷相待、榨取和征服自然的认知惯性与行为模式。西方世界的环保运动→绿色运动→绿色政治和绿色经济、循环经济,东西方之间的文明对话→跨文化交流和二轨外交,以及政府和政府间国际组织主导的多边、双边合作,大国之间的军备裁减和核不扩散等等,都是对发展失衡问题的再平衡。东西方关于全球生存危机解决方略的理论探讨也不断升温,聚焦的主题就是人类和平相处与天人关系。许多人向往东方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希望从中国智慧里求道。汤因比与池田大作的著名对话就谈到,未来世界要想解决各种棘手难题,需要借助中华民族独特的思维方式及和平主义,必须汲取中国人“融合”、“协调”的智慧。(56)德国前总统赫尔佐克则希望,在看重权力、公民自由的西方文化与看重伦理及公民义务的儒家文化之间,找到“趋近于平衡的中点”。(57)美国总统奥巴马也曾承认,“仅仅建立在狭隘利益追求之上的战略不会让人吃饱肚子或者敞开心扉”。(58) 第二,安全的基础是行为体的多样性。一方面,多样性是地球生命繁衍不息的自然法则。对人类来说,生物多样性是福祉的来源,(59)还是文化和精神认同的基础。如果生物物种大量灭绝,则地球生物链条就会断裂,剩余物种甚至人类的生存都会陷入绝境。另一方面,多样性是人类文明绵延不绝的社会法则。人类历史约5,500年,(60)世界公认的文明发源地有5个。汤因比更列举出在时空上大于民族国家的26个文明单位,有16个已经消亡。(61)随着文明的演进,现代民族国家15—16世纪萌芽,至20世纪完全形成并覆盖全世界,到2011年共有195个主权国家。民族、种族或者族群等更是多得难以确计,按通行的种族标准可分4大类,而按语言计则有7,106种。(62)世界各大文明以国家为中心,在艰难曲折中与时俱进。它们之间相互交流和融合而日益发达、繁荣,形成了几大文明圈。其中,唯有中华文明没有分裂、没有中断,并且最为成功地继承自我传统,又吸收外来文化。相反,曾经盛极一时、最后衰亡的不少文明或国家,几乎都因过度的外在扩张而耗竭能量。世界文明史的正反两面充分证明: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越是包容、共享,越是长久、共荣。 第三,安全是相对的。一是安全具有开放性。安全是关系性话语和状况,国家等各种行为体之间在安全上是绑在一起的。一国的安全是相对于他国而言的,取决于两国甚至多国之间的力量对比和关系状况。国家之间的力量发展及其主观意图应有一定的透明度。客观上,国家实力的发展是互为参照系的,相互间的实力对比和消长变化保持动态平衡、总体均势,才能维系相互关系的稳定。因此,国家在发展自身实力时,首先是为了自利、自保,但应顾及不对他国构成巨大压力,因而应该有限度。否则,必然造成实力对比和关系的严重失衡;再若舞弄大棒以争夺和扩张权力,更会引发新一轮挑战、对抗。主观上,国家间外交、安全上的战略和政策都有对外指向性,本质上是为了消除外来安全威胁、促进对外关系的积极发展。但是,这种对外指向性如果过度,对外战略与政策有意、无意地显露出对他国的侵犯性,无疑是有害的。比如,美国派军机、航母抵近中国领空领海进行侦察等活动,以及大量发展并对外部署无人机,在巴基斯坦、阿富汗、伊朗、伊拉克、也门等地投入侦察甚至作战行动,都是侵犯或接近侵犯他国的主权,是硬实力的过度发展及进攻性使用,对他国构成安全威胁。在核不扩散问题上,西方国家更是奉行多重标准,按照与其关系的亲疏,区别对待以色列、印度与伊朗、朝鲜这两类国家的核开发,对前者网开一面而对后者穷追猛打。国家间交流、磋商应常态化,其实质是使国际安全的公开性机制化。只有战略意图和政策目标的透明度越高,负面知觉的可控度才越高,正面知觉的影响力就会越强,国家间的安全互信才有可能增进。 人与大自然的关系同样应该是各种生命体之间的循环生克关系。因此,必须改变人为主体、大自然为客体的定位,承认和尊重大自然作为生命体而与国家等各种人类群体组织相同的主体性,具有平等权利,以扭转人与自然之间单向榨取和征服的关系。这就要求恢复地球生命圈对所有生命体的开放性,重接人类与大自然之间的生命链条,以缓解生态环境危机。 二是安全具有主观性。各种行为体是否安全,在一定程度上是由精英们感到的、制造的。所谓“感到”即主观判定,指的是各行为体是否安全是由代表它们的精英人士来判断的,反映了他们对于国家、国际关系、自然环境的知觉。各国政治精英由于个人原因及所属阶层、政党的差异而有不同的知觉,从而具有不同的安全观,进而实行不同的安全战略与政策。在国家诞生以至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国家无限追逐权力、国家利益至上的现实主义权力政治思想广泛传播并占了上风。安全的关注重点是国家以及国家之间的权力争夺,安全的内容主要是军事、政治安全。二次大战尤其是冷战之后,随着安全问题的扩散,影响政治的思潮除在现实主义之外,又有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新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等,安全的关注重点逐渐转向所有行为体的平衡发展及行为体之间的协调、合作,共同安全、综合安全日益成为国家和国际社会的重要目标。所谓“制造”即指安全价值是人为赋予的。不同国家甚或同一国家不同届别的政府由于不同的政治需要及对于威胁的不同知觉,对安全威胁有不同的判断,甚至会夸大或者制造出一定的安全威胁,因此有了特定的安全政策选择。美国在不同时期就为自己寻找或者建构起不同的“敌人”或“对手”,(63)如共产主义和冷战时期的苏联、冷战后的中国,“9·11”后的恐怖主义等。甚至有人以反恐名义制造恐怖者:“形形色色为国家安全利益工作的安全情报员以各种方式使用他们的胁迫力,将那些并不构成可以想象到恐怖威胁的异见者定为目标。”(64)同样,苏联-俄罗斯对美的认知经历了从敌人到对手的变化,这是双方摩擦不断、对抗难除的一个重要原因。 最后,安全是动态的。国家行为体或者非国家行为体的安全不是一劳永逸的;不安全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从宏观看,由于经济、政治和社会等方面的发展,各行为体有盛衰、起落和兴亡的变化,主要表现为实力对比的消长。随着实力的变化,各行为体的安全感知就会变化,安全政策就会调整,它们恐惧、防范、对抗和结交、合作的对象都会变动,引起相互关系的变化、重组。从微观看,行为体间某种细节变化都会触发安全政策的调整和安全环境的巨变,结果使得国家、地区乃至世界变得更加安全,或者更加不安全。有时,这种变化源自一个行为体或者其领导人的某一信念或念头。比如,希特勒因为接受了社会上关于德国人是“没有空间的民族”的恐惧论调而不惜发动战争、夺占他国土地;(65)新时期的德国人反行之,西德末任(新德国首任)总理科尔不顾多方阻力推动德国的重新统一,加速了冷战和全球对抗大局的终结。有时,这种变化发端于一项科技发明及其应用。比如,DDT等农药的发明和使用,引起大量益虫和鸟类的毒亡,造成生态环境的死寂。(66)甚至,某种资源开发、气候变化都有可能让某些民族亡国灭种。在历史上,玛雅文明因为滥伐森林和反复干旱而灭亡,蒙古帝国因为气候由干旱突变为湿暖而崛起(67);如今,由于气候变暖、海平面持续上升,基里巴斯、图瓦卢、马尔代夫等岛国及一些沿海国家国土逐渐沉没,面临消失的危险。 总而言之,世界上没有永恒和完美的事物,安全也不例外。只有一则通行无阻的道理:人人都平安,人类才安全;国国齐发展,世界才和谐。 ①Lotta Themnér and Peter Wallensteen,"Armed conflicts,1946-2013",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Vol.51,No.4,July 2014,pp.541-554. ②UCDP/PRIO,Armed Conflict Dataset Version,Uppsala University,Sweden,Vol.4,2014. ③Steven Pinker,The Better Angle of Our Nature:Why Violence Has Declined,Viking Adult,2011,pp.48-50. ④UNDP,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1994,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pp.24-25. ⑤[英]巴瑞·布赞、[丹]奥利·维夫、[丹]迪·怀尔德:《新安全论》,朱宁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0-11页。 ⑥Paul B.Stares,ed.,New Security Agenda:A Global Survey,Japan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Exchange,1998. ⑦陆忠伟主编:《非传统安全论》,北京:时事出版社,2003年;王逸舟:《论“非传统安全”:基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一种分析思路》,载《学习与探索》,2005年第3期;余潇枫、潘一禾等编著:《非传统安全概论》,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 ⑧Union of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s,The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Online Edition,2014,Brussels,Belgium;根据The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1909-2013(UIA)计算而来,Samuel J.,"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http://catallaxyfiles.com/2014/03/17/international-organisations/. ⑨根据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UNCTAD)出版的2012-2014年各年度《世界投资报告》(World Investment Report)相关数字计算而来;彭敬、李蕊:《跨国公司发展的新趋势》,http://www.china.com.cn/aboutchina/data/txt/2006-11/07/content_7327430.htm。 ⑩Institute for Economics and Peace,2012 Global Terrorism Index,IEP Report 19,Australia,p.41. (11)"Annex of Statistical Information",Country Reports on Terrorism 2013,U.S.Department of State,Washington,April 2014. (12)"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List of Parties",http://www.cbd.int/information/parties.shtml#tab. (13)WTO,Bali Ministerial Declaration and decisions,http://wto.org/english/thewto_e/minist_e/mc9_e/balipackage_e.htm. (14)SIPRI Year Book 2013,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3; SIPRI Year Book 2014,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4. (15)"World Military Spending Out Does Anything Else",http://www.globalissues.org/article/74/the-arms-trade-is-big-business; SIPRI,"The Financial Value of the Global Arms Trade",http://www.sipri.org/research/armaments/transfers/measuring/financial_values. (16)UN,GA Resolution 1962(X VIH):Declaration of Legal Princles Governing the Activities of States in the Exploration and Use of Outer Space,http://www.un.org/Docs/asp/ws.asp?m=A/RES/1962(XVIII). (17)Gerald F.Seib,"New Cold War? Obama,Putin Are Split",The Wall Street Journal,March 4,2014. (18)Shanthi Kalathil,"Transparency and Volatility: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the Information Age",Diplomacy,Development,and Security in the Information Age,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Diplomacy at Georgetown University,2013,p.3. (19)[英]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肯尼思·库克耶:《大数据时代》,盛杨燕、周涛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 (20)习近平:《积极树立亚洲安全观共创安全合作新局面》,载《人民日报》,2014年5月22日。 (21)《习近平在德国发表重要演讲》,载《人民日报》,2014年3月30日。 (22)[荷兰]萨洛蒙·克罗宁博格:《人类尺度:一万年后的地球》,殷瑜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1年,第1-12页。 (23)Shaun A.Marcott et al,"A Reconstruction of Regional and Global Temperature for the Past 11,300 Years",Science,Vol.339,pp.1198-1201,March 2013. (24)Anthony Watts,"Russian Scientists Say Period of Global cooling Ahead due to Changes in the Sun",Radio Voice of Russia,April 29,2013. (25)Conway W.Henderson,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Law,John Wiley & Sons,2010,p.212. (26)Simon Kuper,"Why the World is Getting Safer",The Financial Times,September 19,2014. (27)Clay Shirky,Here Comes Everybody—The Power of Organizing without Organizations,The Penguin Group,2008. (28)[英]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大数据时代》,盛杨燕、周涛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 (29)UNDP,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1994,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pp.22-23. (30)[加拿大]保罗·埃文斯(Paul Evans):《人的安全与东亚:回顾与展望》,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6期,第43页。 (31)UN,Resolution adopted by the General Assembly:60/1.2005 World Summit Outcome,A/RES/60/1,United Nations,New York,September 16,2005. (32)[美]彼得·乔希姆·卡赞斯坦:《世界政治中的文明:超越东方和西方》,蒋估颖译,载《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6期,第7页。 (33)司马迁:《史记卷六十八》(第7册),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2235页。 (34)Suzanne Nossel,"Smart Power",Foreign Affairs,Vol.83,No.2,March-April 2004,pp.131-142. (35)[美]威廉·F.斯通著:《政治心理学》,胡杰译,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8-39、143页。 (36)Robert Jervis,"Cooperation Under the Security Dilemma",World Politics,Volume 30,Issue.2,1978,pp.169-170;秦亚青:《译者前言——杰维斯及其国际政治心理学研究》,载[美]罗伯特·杰维斯:《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秦亚青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 (37)[美]柯瑞·罗宾:《我们心底的“怕”——一种政治观念史》,叶安宁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 (38)[古希腊]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谢德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上册:第19页。 (39)[美]彼得·乔希姆·卡赞斯坦:《世界政治中的文明:超越东方和西方》,蒋估颖译,载《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6期,第7、8页。 (40)《西报:乌克兰事态发展与一战初期惊人地相似》,《参考消息》网站,http://k.cankaoxiaoxi.com/weizhan/article/101399975/31119435507/236492。 (41)[美]约翰·柯林斯著:《大战略—代序》,解放军军事科学院译,北京:战士出版社,1978年。 (42)Liddell Hart,The Strategy of Indirect Approach,Faber and Faber Limited,London,1941,pp.192、202、205. (43)Op.cit.,Liddell Hart,The Strategy of Indirect Approach,pp.191-192. (44)Op.cit.,Liddell Hart,The Strategy of Indirect Approach,pp.205-208. (45)[美]罗伯特·杰维斯著:《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秦亚青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第51页。 (46)老子:《道德经》,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52页。 (47)孟子等:《四书五经·论语》,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7页。 (48)孟子等:《四书五经·中庸》,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55页。 (49)孟子等:《四书五经·论语》,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27页。 (50)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633页;同前引(战国)孟子等:《四书五经·中庸》,第55页。 (51)朱熹撰:《周易本义》,李一忻点校,北京:九州出版社,2004年,第20页。 (52)孟子等:《四书五经·大学》,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48页。 (53)孟子等:《四书五经·大学》,第48、49页。 (54)Martin Jacques,"What Kind of Superpower Could China Be?" BBC News,October 19,2012. (55)[美]戴维·埃伦费尔德:《人道主义的僭妄》,李云龙译,国际文化出版社公司,1988年,第90页。 (56)[日]池田大作、[英]汤因比:《展望二十一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荀春生、朱继征、陈国梁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7年,中文版序言、第272-285页。 (57)[德]赫尔穆特·施密特:《全球化与道德重建》,柴方国译,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261页。 (58)The White House Press Secretary,"Remarks by the President on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The U.S.State Department,Washington,D.C.,19 May,2011,p.2、p.1. (59)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全球生物多样性展望》报告,第3版,《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蒙特利尔,2010年,第40页。 (60)Conway W.Henderson,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Law,John Wiley & Sons,2010,p.212. (61)汤因比:《历史研究》,曹未风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64年,下册:第452-455页。 (62)Lewis,M.Paul,Gary F.Simons,and Charles D.Fennig(eds.),Ethnologue:Languages of the World,17[th] edition,Dallas:SIL International,2014. (63)David Rothkopf,"The Enemy Within",Foreign Policy,No.3,2012,pp.211-239. (64)[美]柯瑞·罗宾著:《我们心底的“怕”——一种政治观念史》,叶安宁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44-247页。 (65)[德]赫尔穆特·施密特:《全球化与道德重建》,柴方国译,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235页。 (66)Rachel Carsen,Silent Spring,Mariner Books,Anv.Edition,October 2002; First serialized in The New Yorker in June 1962; Best-seller lists in newspapers from around the nation included "Silent Spring" for 1962. (67)[美]贾雷德·戴蒙德:《崩溃——社会如何选择成败兴亡》,江滢、叶臻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第117-134页;"Mongol Empire Rode Wave of Mild Climate,Says Study",Earth Institute,Columbia University,March 7,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