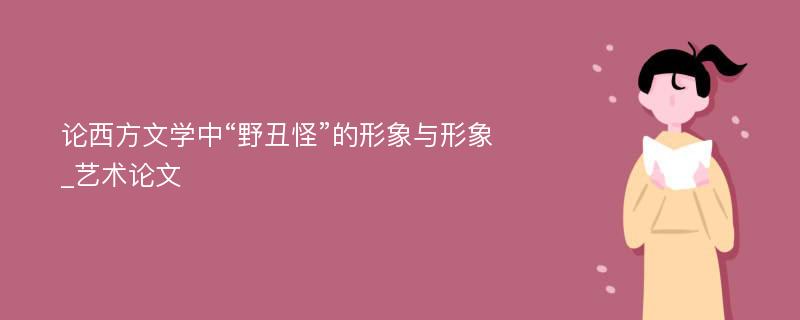
漫议西方文学中“野、丑、怪”的形象与意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意象论文,形象论文,文学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18世纪启蒙运动以来,在西方文学作品中出现了大量的“野、丑、怪”的形象与意象。
将“野、丑、怪”的形象与意象引进一向被认为是神圣的、高雅的、美的文学艺术领域。不论从思想内容看,还是从艺术形式看,它大都意味着对传统、对时尚、对文明的一种抵制与否定;对现存社会秩序、现有艺术法则的一种反叛,同时也是对扩大艺术表现范围、增强艺术活力及艺术表现力的一种呼唤与努力,标志着审美意识或美感向深度与广度的拓展。
一
在18世纪的启蒙运动中,为了反封建反教会斗争的需要,为了用近代文化启迪人们的理性和智慧以批判封建社会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针对着苍白柔媚、曲雅华贵、虚伪腐朽的封建主义的文明与时尚,和毫无创造性的古典主义和洛可可式艺术表现的贵族艺术,狄德罗在《论戏剧诗》中提出了“诗需要的是巨大的、野蛮的、粗犷的气魄”①,诗应该表现未经雕琢的动荡的自然;诗应该表现狂风呼啸电闪雷鸣的黑夜的恐怖;诗应该表现苍凉悲壮述说着伟大历史内容的废墟;诗应该表现古老的森林、荒野间的野穴以及奔腾不息的瀑布……。因为在这些表现对象中,蕴含着原始的、粗野的力之美,是纯朴、强悍有力、生气勃勃的象征。它能引起心灵的颤栗,增强文学艺术震撼人心的力量。他提出作家们“要住到乡下去,住到茅棚里去”,应以一个“自然人”、“野人”的目光观察社会,批判社会。“自然人”、“野人”意即质朴的人。批判贵族阶级的文明,是18世纪启蒙学者爱用的一种方法。
同是处于启蒙运动中的卢梭则更加厌恶封建贵族的腐朽与文明,向往接近原始人类的自然状态。他认为,文明腐蚀了人的灵魂,造成了人的堕落,同时它还扩大了对人的奴役,加深了对个人欲望及本性的压抑,减少了自由,人与人只有在自然与野蛮状态中才是自由平等的。
在卢梭生活的时代,古典主义在法国文坛上占据着统治地位。古典主义崇尚高贵与优雅,这特别体现在爱情的描写中。与此相对,卢梭则表达处于自然状态的爱情。《新爱洛绮丝》中平民知识分子圣·普乐同贵族小姐尤丽之间的爱情,就是一种猛烈的、不可抗拒的、顺乎自然法则的纯洁的爱情,他们的爱情与雄浑壮丽的阿尔卑斯山的大自然的律动相谐合。在这里,卢梭提出以真实自然的感情为基础的婚姻理想,批判了以门当户对为基础的封建婚姻。另外,圣·普乐还将巴黎的文明生活同他到过的未被文明开化的岛屿与山区野蛮人的生活作了对比,他否定了巴黎,狂热地赞美生活在大自然怀抱中的接近自然状态的人民,以及他们跟大自然永恒规律相协调的生活及高尚的道德风尚。
《爱弥儿》是一部讨论教育问题的哲理小说。卢梭认为穷人接近自然,没有进行教育的必要,富人的阶级偏见背离自然状态必须进行教育。他将封建社会、封建的文化教育视为损害人的自然本性的渊薮,将城市视为使人类毁灭的深渊。在这里,他明确提出了“返回自然”的口号。
在卢梭“返回自然”口号的召唤之下,对大自然的爱好,在19世纪初期像巨大的波涛席卷了欧洲,特别是对浪漫主义思潮产生了尤为巨大的影响。这种影响有两种,一种是积极的,它鼓励人们冲破现存秩序的藩篱,向往未来;一种则是使人回避现实,倒转历史,缅怀古代。
19世纪初期的浪漫主义者诅咒城市文明,陶醉在大自然的怀抱之中。英国诗人华兹华斯、雪莱、拜伦等都以歌颂大自然的壮丽诗篇著称于世,并因此给诗歌带来一种新的精神。华兹华斯提出诗应“选择轻贱的田园生活作题材”,因为“在这种生活里,我们的各种基本情感共同存在于一种更单纯的状态之下”②,他认为,普通人的纯朴生活比贵族生活更有诗意,乡间的田园生活比城市生活更富有自然美。
法国浪漫主义者夏多布里昂、拉马丁等则受到卢梭更为深刻更为直接的影响。在小说《阿达拉》中,夏多布里昂在充满了原始气息的、粗犷的、雄奇的北美荒原里,在响彻着猛烈风暴、电闪雷鸣和有野兽出没的大森林里,在超凡脱俗的、弥漫着神秘神奇之美的自然环境中,描写了一对未开化的青年男女的爱情,夏克达和阿达拉都是自然之子,他们的爱情猛烈、真挚、自然,充满了纯朴的诗意。
由于西方文明的衰微,“返回自然”的口号被一再提出,并多次重复出现。
19世纪的中长篇小说,非常重视人物性格的塑造,因此这一时期对自然对野性的向往,主要体现在人物形象中。梅里美笔下未开化的野性十足的村姑高龙巴(《高龙巴》)、敢于向资本主义文明公开挑战的吉卜赛女郎嘉尔曼(《嘉尔曼》);爱米丽·勃朗特笔下的未被文明玷污的荒原之子希刺克厉夫;托尔斯泰笔下的离开上流社会到居住在雄伟群山与美丽大自然中的纯朴的哥萨克山民中寻找真理的奥列宁(《哥萨克》)等,都体现了作者对野性、对原始性的一种追寻与向往,对资本主义虚伪文明与道德的批判。在这里,我们应该特别提出的是劳伦斯的《查特利夫人的情人》,这部小说通过性爱方式,深刻体现了自然与文明的冲突,体现了作家对文明的唾弃和对自然的向往。查特利夫人离开丈夫投入庄园守林人的怀抱,体现了文明人向自然人转化这一象征性的主题。
自城市文明出现以来,对大自然的向往就成了许多文学艺术家的共同梦想。到了20世纪,热爱自然厌恶文明,不仅体现在文学艺术家创作的作品中,也往往体现在艺术家本身。奥地利诗人里尔克,出于对充满激烈斗争的资本主义社会和物欲横流的大城市的异常反感,他或浪迹天涯,或隐居在乡间的古堡之中,也不愿生活在罪恶渊薮的巴黎。里尔克在孤独中从大自然里寻求理解与安慰,在他的创作中,始终贯穿着对资本主义文明和现代生活的怀疑和否定。
二
19世纪初期兴起的浪漫主义思潮,不仅诅咒城市文明,讴歌大自然之美,追求山野异域情调,而且针对着古典主义崇尚典雅的贵族阶级的艺术情趣和不容许非美和丑的东西介入艺术的戒律。它的代表人物雨果在《克伦威尔·序言》中提出了著名的崇高优美与滑稽丑怪相对照的创作原则,将粗俗平凡、滑稽丑怪引进了文学艺术的领域,扩大了文学艺术的表现范围。
在这之前,狄德罗虽然并不完全反对艺术按照真实表现丑陋的东西,但他认为,艺术对自然的模仿应有所选择,“摹仿自然并不够,应摹仿美的自然”。他在自己的美学著作里,提出了真、善、美统一的理论,要把美建立在真与善的基础之上,“真善美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在真或善之上加上某种罕见的、令人注目的情景,真就变成美了,善也就变成美了”③。
在德国,以温克尔曼为代表的美学家的理论中,“客观的美被看成是古代艺术的原则”。莱辛虽然认为丑可以入诗,但不可以进入造型艺术,他在《拉奥孔》中指出,造型艺术“作为摹仿的技能来说,绘画有能力去表现丑;就它作为美的艺术来说,绘画却拒绝表现丑”④。德国考古学家兼艺术史家希尔特在《古代造型艺术史》中提出了不同意见,他说,从大量考古中发掘出来的古代艺术品表明,“这些不朽的作品,用一望而知的证据证明,这些不朽作品表现了各种各样的姿容,既有最美的,也有最普通的,甚至有最丑的……”⑤。这就向人们提出了一个问题,艺术的品质是不是真的在于表现美?
德国美学家博克在《论崇高与美》中提出,丑和崇高具有亲缘关系,丑同崇高是部分地相一致的,但崇高是在美之外与美无关,崇高与美是相互并列的。康德也认为崇高的对象包括着畸形和丑陋,在《判断力批判》中,他将崇高与美分属于审美判断的两个不同的品种。随着近代社会的出现,随着浪漫主义的萌生,人们关于丑的研究与分析,很快发展成为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于是,丑和崇高终于都划入了美的总的范围以内,而这种划入是通过特征或意蕴学说实现的。
一般说来,美总是给人以快感,而丑按照常规则不能给人以快感。将丑划入美学的范围,反映了人们审美范围的扩大。因此,处于一体的真善美彼此分离了,美同艺术也剥离了。
这种美学范围及欣赏范围的扩大,是同西方社会生活的发展变化,以及人们对生活的认识有着密切联系的。雨果认为,宇宙万物的美与丑往往是处于一种复合状态之中,即“丑就在美的旁边,畸形靠近着优美,丑怪藏在崇高的背后,美与恶并存,光明与黑暗相共”⑥。既然生活本身充满了美丑对照,那么真实反映生活的戏剧,就无权把二者割裂开来,应“把阴影掺入光明、把滑稽丑怪结合崇高优美而又不使它们相混”,“滑稽丑怪作为崇高优美的配角和对照,要算大自然给予艺术的最丰富的源泉”⑦。雨果美丑对照理论,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审美情趣的独特要求,和对古典主义审美情趣的不满和厌倦。但我们必须指出,雨果美丑对照原则的最终目的,是为了突出美,是为了对崇高对伟大的追求,对照只是一种途径、一种手段,是为克服表现上的单调与平淡。这样,丑在艺术中就不可能具有独立的存在,它只是美的一种参照物、衬托物。
到了19世纪后半期,自然主义、唯美主义、象征主义相继出现,文学艺术呈现出一种多元化的格局。继现实主义之后的自然主义将自然科学中的新方法引入了文学艺术的领域,使文学艺术导向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倾向,追求严酷的真实。他们认为,要想完整地描写客观现实,就不能回避对现实中丑陋、丑恶、畸形、堕落、粗俗与残忍的描写。他们直面现实中的丑恶,敢于并乐于表现与描写各种形状各种性状的丑恶:社会生活的、人性的、道德的、生理上的、人物形体上的、两性关系中的等等;写下了许多触目惊心、骇世惊俗的篇章。自然主义作家对丑恶肮脏事物的描写,由于不加选择提炼,不加节制,不进行评价,成了对客观平淡生活现象的实录,令人不能卒读,但却达到了暴露的目的。而且由于自然主义是从生理的角度观察人、理解人、表现人,将血与肉带进了文学,从而开拓并充实了对人的描写,为人的描写提供了新的艺术经验。
自然主义由于强调分析实验,就竭力反对想象,但没有了想象也就没有了文学。由此可见,自然主义将各式各样的丑恶作为文学作品的重要对象与内容,主要目的是为了暴露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丑恶与病态,而较少美学上的考虑。而且自然主义的理论与创作实践并不是一致的,有些甚至是相互抵触的。
19世纪后半期,浪漫主义运动衰落之后,在法国出现了以波德莱尔为代表的早期象征主义和唯美主义。产业革命给城市生活带来了巨大变化,在给人们提供高度物质文明享受的同时,也造成了美的丧失,人性的丧失。由于艺术的商品化,市侩习气的泛滥,许多希望落空了,许多幻想破灭了,各种丑恶、罪恶、病态成了资本主义特别是大城市的重要现象,人们陷入了丑恶事物的包围之中。为了保护艺术的纯洁,唯美主义提出了“为艺术而艺术”的主张,逃避到自己所创造的理想世界中去,以和现实生活中的丑恶现象相对抗。但波德莱尔不只不回避现实中的丑恶,而且大胆地去面对丑恶的事物,将丑恶作为艺术的材料和对象。在《恶之花》草拟的序言中,波德莱尔提出:“什么叫诗歌?什么是诗的目的?就是把善同美区别开来,发掘恶中之美。”在这里,波德莱尔抛弃了真善美不可分割的传统理论,将恶引进了文学艺术,使之成为文学艺术重要的表现对象,这在当时确实意味着一种叛逆。因为“平常的人总以为凡是在现实中认为丑的,就不是艺术的材料——他们想禁止我们表现自然中使他们感到不愉快和触犯他们的东西,这是他们的大错误”⑧。在将善与美区别开来以后,波德莱尔提出了美的定义:“忧郁才可以说是美的最光辉的伴侣”;“最完美的雄伟美是撒旦——弥尔顿的撒旦”。这其中同样包含着对现实深刻的不满与反抗叛逆的内容。波德莱尔又将美分为绝对美与特殊美,他强调特殊美,认为“每个时代,每个民族都拥有自己的美和道德表现”。在波德莱尔的时代,由于社会生活中充满了各式各样的丑恶,因而提出将恶作为艺术表现的对象,使艺术美突破美的规则成为时代的需要。
《恶之花》就是他的这种理论的实践。《恶之花》即病态的花,恶之为花就是将丑恶在艺术上加以表现。《恶之花》反映了诗人对法国社会生活,特别是巴黎下层社会生活的感受、看法和理解。巴黎是一座盛开着恶之花的病态之城,巴黎下层社会的不幸、贫困和痛苦是波德莱尔挖掘美的场所。处在丑恶事物的包围之中,诗人仍在渴望着追求着美与善良,追求着健康、光明和理想。但由于诗人长期生活在病态的巴黎,在诗人的心灵与精神中也势必烙下了肮脏与丑恶的印痕,这就造成了诗人既有暴露社会罪恶又有悲观沉沦的复杂的内心世界。
“发掘恶中之美”,一方面是通过对丑与恶的表现,从中引出道德教训与哲理,由于诗中蕴含着对于理想对于善与美的追求,所以在恶的表现中,会激起高尚的人的道德上的愤怒、思想上的反抗和精神上的追求;另一方面是通过艺术手段,将恶变为一件美的艺术品。《恶之花》是艺术之美不是丑恶之美,因为一切美从根本上说都是表现力,艺术不是追求美而是追求某一特定内容的最好表现,不管它表现的内容是善良还是丑恶,成功的艺术处理,最高的意蕴就是美。这正如波德莱尔所说:“丑恶经过艺术的表现化而为美,带有韵律和节奏的痛苦使精神充满了一种平静的快乐,这是艺术奇妙的特权之一。”⑨《恶之花》这部以丑恶为对象的作品,正是通过波德莱尔卓绝的艺术表现力,呈现出一种艺术之美,从而成为人们欣赏的对象。
在波德莱尔的创作中,丑的、恶的、病态的事物是作为一种独立存在纳入艺术,而且成了他进行艺术创作的主要材料与对象。与自然主义不同,他不只写了外在现实生活中的丑恶,而且写出了他内心真实而又复杂的感受,表现了他的心灵,所以能激起人们心灵的颤抖、忧虑与悲哀。在《恶之花》中,他“能够发现在外形下透露出的内在真理,而这真理就是美”⑩。波德莱尔在《恶之花》中,用丑的、恶的、畸形的意象,创造出了一个美的艺术整体。但也不能否认,在西方精神世界的一片危机之中,确也产生了不少心如死灰的丑的艺术,表现了颓废沉沦的内心世界。
另外,还应特别指出,在美与丑、善与恶、意义与荒谬颠倒的世界中,在常人眼中的丑也会蕴含着一种富有刺激性的美;恶中也会含有反叛与对立,孕育着生命与创造,荒谬也几乎变得有了意义。因此,在一个美丑、善恶颠倒了的世界中,一切否定的、冷酷的、奇异的、怪诞不经的可怕事物中,似乎都有一种值得赞誉的积极的东西。一些先锋派的艺术家们,他们常常有意避开美的美学领域,专门去表现恐怖怪诞、原始丑陋和恶剧丑角,以表达他们报复与破坏心理,显示他们的叛逆及力量。由此可见,现代艺术突破美的规范是理所当然的了。
三
19世纪末20世纪初,精神上的压抑与惶惑不安,生活里的孤独、焦虑、空虚与苦闷,成了西方世界一种普遍的精神状态。20世纪两次世界规模的残酷战争,使人们感到我们人类所生存的这个世界是受一种盲目的、非理性的荒唐意志所统治,是一个天翻地覆、善恶混淆、一切都颠倒了的荒诞世界。在这个世界上,一切都是可疑的。偶像坍塌了,信仰破灭了,人生的意义失落了,以往遵守和恪守的价值体系崩溃了,瓦解了,西方世界处于一片危机之中;人们失去了立足点和方向,精神世界处于一片荒原之中。
20世纪初,由于认识论的发展和心理学的新发现,使人们对反映世界、认识世界的客观性和精确性产生了深深的怀疑和动摇。人对世界的认识是无比复杂多变的,因为它要经过许多中介环节,这些中介环节会改变客观现实本身的形态与特征,甚至会改变真理的意义。由于认识主体——人的内心世界、情绪状态、态度、个性特征、价值观念等的不同,认识对象的意义就会不同,它跟随着自我体验的变化,跟随着自我情绪和行动的变化而变化,同一现象同一事物,用不同的眼光、从不同的角度看,就可以有完全不同的意义,导致相异甚至相悖的结论和结果。在这种理论的启示之下,人们认识到,文学艺术作品中所呈现出来的艺术世界,文学艺术所表达的,是作家艺术家本人对世界的独特发现、体验和艺术表现。这是对文学艺术认识意义上的巨大转变,由于这种转变,在文学艺术的创作中,反映论的意识淡薄了,艺术家着力于从独特的视野去表现自己的时代,着力于对人生哲学的追求和体验。有些作家艺术家为了表达自己对生命对社会的独特思考与感受,往往将生活内容加以扭曲和变形。
20世纪,在存在主义哲学影响下,人类的主体意识进一步深化并走向成熟,由于世界的巨变和人类面临的灾难,人们更加关注人的生存状态、人的命运。具有现代意识的读者也更加迫切地需要从不同角度,以不同的方式,认识当代人无比丰富的生活、无比复杂的处境与命运,认识人的本来面目。
在19世纪的现实主义文学中,艺术家们对外部世界的描写已达到了顶点,要想超越它是极端困难的。20世纪的文学要想得到发展与进步,要想超越它,只有另辟蹊径,朝着人类待认识与待解释的范围与方向前进,这就是现代主义高举反传统的根本理由。传统文学是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反映生活,作品中的生活形式基本上是与生活的实际样式相一致的,是常态的,反对这种传统,势必走向变形与怪诞。
在这样的世界情况和文化背景下,文学艺术真实地描写、反映外在世界不再具有重要意义,而是要从人的心灵中,从人的情感生活中,从人对外部世界的感受中去寻找意义。更何况,文学艺术作为精神产品,它最终所关心的究竟不是物质而是精神。而人的情感生活,人对外在世界的感受与体验,也不能再从外在事物的描写中,而是要从它本身得到显现。人的心灵生活,往往凭幻想想象任意驱遣,这幻想与想象在外界生活外在事物的刺激影响下,处于十分不稳定的状态,或清醒或颠狂;或正常或病态,它可以把眼前事物照实地反映出来,也可以任意更改现存世界,把它弄得颠倒、错乱、怪诞与离奇。
由于艺术表现的对象,主要不再是外在世界而是具体的内心生活,它要诉诸于人的情绪与情感,而这些都是心灵性的,是内在的,是无形的,是不可视的,是无法直接表现的,要借助于象征才能使其具有一定的意义,借助于抽象才能证明其存在。文学艺术从外在的感性世界退隐到人的心灵的内在生活,感性形象的意义大大减弱了,因此,变形、分裂、模糊含混、抽象的、带有寓意的形象出现了,这些形象正是处于现代的西方人心理状态的一种具体可视的象征。
20世纪的西方社会是一个病态的社会,深刻的忧患意识与危机意识,必然导致人产生病态的心理;生存的孤独感、恐惧感、严重的心理不安,造成了人物的不完整、畸形与怪诞。文学艺术要表达这种病态的心理,要表现由现实生活激起的忧愤,要传达被压抑的心灵的痛苦,就必然会出现颠狂的幽默、荒诞与怪异、夸张与变形。因为只有在荒诞、怪异、变形的描写里,才能真实地传达出艺术家对世界对人生的体验与感受,才能使作品产生一种深刻的寓意。
这种观察世界的方式,这种表现生活的手法,是20世纪不同艺术领域的共同特征,是文学艺术家们的一种共同现象。这种体现在艺术创作中的现代色彩是时代所造成的一种集体意识的反映,它反映了时代的荒谬和不可理喻,反映了艺术家们强烈的批判意识和彻悟。
最早出现的荒诞作品是卡夫卡的《变形记》,主人公葛利高尔在一天早晨突然发现自己由人变成了甲虫,这是人的现实处境及命运荒谬的反映,并造成了一种荒诞的艺术效果。这种荒诞是人生固有的,也是卡夫卡对人生本来面目、对人的命运本质感受的真实表现,是他对人生体验的特殊的艺术表达。这种夸张变形怪诞的艺术手法,比起19世纪如实地直接地表达小人物命运的现实主义作品,能更加深刻地揭示现实生活的本质,表现下层人物的辛酸悲苦,激起更为深沉的悲怆,引起心灵更为强烈的震撼。
荒诞派戏剧和“黑色幽默”小说,是现代荒诞艺术的典型代表。它们以滑稽丑怪为艺术的表现对象,在形式上追求支离破碎的艺术形象,对传统艺术进行全面的背叛与颠覆,完全以反艺术反传统的面目出现。贝克特《等待戈多》中两个流浪汉等待的徒劳而无望;《剧终》中四个人物处在黑暗的深渊里,不死也不活,忍受着痛苦,无可奈何地走向死亡,都反映了人生极为艰难的处境。尤奈斯库的《椅子》、《未来在蛋中》反映了人受物的排挤与压迫,在生活中已无立足之地;《犀牛》中,人都变成了犀牛,在舞台上乱跑,人已无法保持自己独立的人格。这就是人的生存状态,这就是人的命运。这些剧本在艺术形式上完全抛弃了传统的戏剧冲突、舞台规范等,故意采用破碎不整的舞台形象和夸张、变形、怪诞等荒谬悖理的表现手法,以求得荒诞内容与荒诞形式的彻底统一。“黑色幽默”则以喜剧形式表现悲剧性内容,将可怕与可笑混合。它使用强烈的夸张到荒谬程度的幽默嘲笑手法,使现象放大、扭曲,这既显得怪诞不经、滑稽可笑,同时又让人感到极端的沉重、残酷与绝望。黑色幽默传达的是作者对现实的厌恶、绝望和思想上的苦闷,它表面上荒唐无稽,实际上则是扎根于强烈的痛苦之中。约瑟夫·赫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是“黑色幽默”的代表作,它揭示了小人物走投无路的处处被捉弄的生活处境,作品的结构松散随意,情节混乱重叠,但却深刻展示了人的生活的毫无意义和个人奋斗的无望。在滑稽幽默的笑声中,包含着某种令人震惊的可怕的东西。
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神奇怪异,是拉美人民审视和表达现实的方法。由于拉美地区的落后、孤独,他们信仰变形、还魂、巫术、因果报应等原始信仰,而“信仰可以使人产生幻觉”,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变形、怪诞,正是通过幻想幻觉对拉美现实与历史的艺术表现。
其他如意识流小说中的时空颠倒、错乱、重叠,未来主义形式上的荒唐古怪,达达主义的疯狂杂乱,超现实主义形式上的荒诞离奇等等,这一切说明,到了20世纪,荒诞怪异已成为一个重要的审美范畴。
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野、丑、怪”进入文学艺术,并发展成为重要的审美范畴,是与西方社会的发展有着密切联系的,它的演变反映了西方社会的历史运动。
注释:
①③ 《狄德罗美学论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06、429页。
② 华兹华斯:《抒情歌谣集·序》,《十九世纪英国诗人论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5页。
④ 莱辛:《拉奥孔》,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35页。
⑤ 转引自鲍桑葵《美学史》,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255页。
⑥⑦ 雨果:《论文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第30、35页。
⑧ 《罗丹艺术论》,人民美术出版社1978年版,第23页。
⑨⑩ 《象征意义·意象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4、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