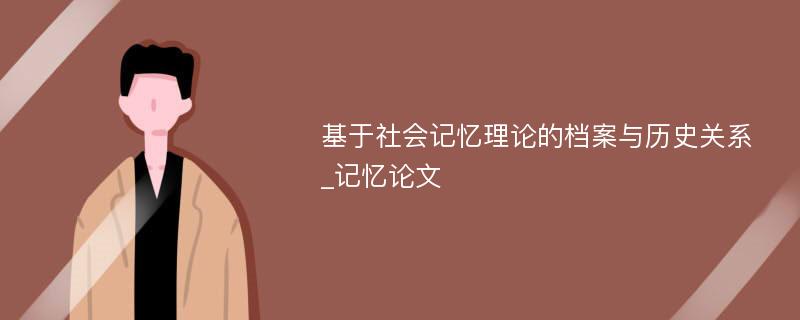
基于社会记忆理论下的档案与历史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记忆论文,理论论文,关系论文,档案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102(2008)02-0098-06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倡议并牵头实施的“世界记忆工程”项目的展开,“记忆”成为档案界继“信息”与“知识”之后的又一个重要概念。2000年在西班牙召开的第十四届国际档案大会上,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在开幕式讲话也指出:档案馆是保存人类记忆的各种表现形式,是保存社会记忆、个人记忆的最权威场所。从此以后,社会记忆成为档案学研究的新视野。通过近几年的国际学术界的学术探讨,基本上得出这样的共识,档案是社会记忆的工具或存在物,档案是寻找遗忘记忆和发现过去记忆事实真相的主要载体,是保护过去,记录现在和联系未来的桥梁。把档案看成文件库的传统认识正在被记忆库所取代。档案馆是保存记忆的宫殿。社会记忆理论使档案与历史关系这一传统命题注进新的诠释。
1 “档案——社会记忆”理论历史背景
国际档案界提出档案是社会记忆的新说法的历史背景是:社会的发展需要满足公民不断增长精神文化的需要。当代公民有两种精神文化需要:一是精神家园的文化休闲需要;二是民主政治的需要。
休闲是当代发达社会最典型的特征,第14届国际档案大会的主题就是档案休闲社会中的作用。现在人民群众在解决衣食住行最基本的问题后,就要休闲,所以有人说小康社会是一个休闲社会。那么老百姓要休闲,他有许多地方可去的。可以到酒吧,KTV,可以到风景区去旅游,也有到博物馆、科技馆、文化馆、档案馆去参观学习研究,进行文化休闲。档案馆是公民文化休闲的一个重要场所,因为档案馆本身就是一个文化事业单位,档案馆是具有休闲消遣的功能。随着中国人生活的富足,“休闲社会”也将成为我国未来社会重要特征之一。在许多人心目中,一向顶着“红头文件”的帽子,板着“衙门”的面孔,神神秘秘而且与百姓生活相距甚远的档案,却与“吃喝玩乐”“琴棋书画”的休闲扯到一起,连档案圈子内的人都不可理解。其实,在发达国家,档案走向大众已成为一种趋势,随着大众休闲时间的增多,休闲产业已在国民经济上有了重要地位。国外在档案馆为公众休闲服务方面做得较好,一是利用的手续简单,二是保存的档案贴近公众生活,三是对外开放。以美国为例,美国有两个国家档案馆,国家一馆在华盛顿,国家二馆在马里兰州。马里兰州与安徽省是友好省市,马里兰州的国家二馆保存有原时任安徽省委书记万里在文革时期红卫兵小将批判他的小字报、大字报等其他历史材料,万里书记及随行人员就是搞不清美国人是怎么把它搞过去的,这东西在中国档案馆也不会保存的。在美国利用档案的手续极为简单,原安徽省档案馆长严桂夫先生以一个学者的身份在美国国家二馆查60年代美国总统档案及外交档案,只要出示中国的身份证就行了,也就是说外国人在美国查档案是不受国籍的限制。而且在这个档案馆他看到了在中国档案人看来是核心机密档案。如:他甚至于看到了1964年北部湾事件后,由于越南战争迅速升级,美国五角大楼的军事家制订的三个对中国作战计划,分别叫“阿乐法”“布雷特”“查利列”在这个计划中提出使用核武器。美国人也强调保密,但可开放的档案比中国多。另外,美国档案馆还要利用公众的心理来聚集公众的热点,为公众休闲服务。如电影《泰坦尼克号》曾红极一时。当时,世界各国出现了泰坦尼克号热。美国国家档案馆立即将有关文献资料放到网页上,并在其在线展厅中放置泰坦尼号的照片,一时间看热闹和利用这些文献的研究者们蜂拥而至,造成了网络拥挤,这在网速居世界之首的美国是不多见的。
公众对我国档案馆的服务总体评价不高。主要原因就是档案馆在公众的服务的时间、态度和手续上仍然表现为“衙门作风”。我国档案馆节假日、双休日是不对外开放的。公众不愿到档案馆休闲,另外一个原因,利用手续严,我国档案基本上是不对外开放,即使已过了三十年的保密期。再就是保存的档案多是公务文件,私人事务的档案少,与百姓生活有距离。在我国到档案馆来利用档案因公务需要的占80%以上,在美国,法国私人利用者占50%以上。档案不仅保存官方的历史记录,也应是保存老百姓档案的地方。即档案应该是全社会的记忆。保存老百姓如家谱、族谱、房地产档案、当地风土人情、社会保险、历史典故、地理风光、文化遗产等等方面的档案,那里有民生档案,老百姓才会去休闲。比如:2005年台湾有两大政要连战、宋楚瑜先后访问大陆。4月29日,国民党主席连战在北京大学接受了该校赠送的其母亲赵兰坤女士76年前在燕京大学的学籍档案照片复印件,新民党主席宋楚瑜在家乡湘潭见到了1941年的《湘潭昭山宋氏族谱》证明他是昭山宋氏第32代传人,而且有1947年全家福的照片,这两个人都激动不已。档案可以提供人们的家族记忆,可以提供乡情的记忆,可以提供寻根追祖的记忆。档案馆保存社会记忆,档案馆就是休闲的地方。
2 民主政治的需要
信息化与民主化是当今世界的大趋势。民主社会是以信息公开为前提,随着我国政治文明的不断进步,民众的民主意识日渐增强,对平等占有信息资源提出了政治层面的需求。大力开发利用档案信息资源,确保公民知情权,监督权,公民有权要求国家权力按照公开、公正的原则行使。档案信息资源要为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服务,要把档案馆列为公众获取政府公开信息的基地,更好地贴近民众,方便民众,档案馆要开“文件超市”,更多地开放现行文件,使民众有更多知情权,发言权,参与权,监督权,因此,找到解决自身问题的依据,能够更好地、保护自己的权益。加内彼得生在《利用与开放》一书中指出:寻找和接受信息是一项人权,这项权利允许公民参与政务,有助于加强民主的原则,档案工作者应广泛地提供档案资料并竭诚为他们服务。在西方国家维护公民信息权的概念已普遍确立,通过查阅公共档案知悉和监督政务作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被明确。
但是我们精心保存的作为社会记忆的档案,却很少引起民众的兴趣,档案馆缺少反映民众生活的档案和为民主服务的档案利用措施,民众远离档案,档案馆前门庭冷落。正是以上两点的公众需要,那么档案馆要满足民众的需要必须保存公民的记忆,也就是全社会的记忆。正如加拿大档案馆长库克说:我们的记忆宫殿是为人民服务的,不是为国王服务的,绝大多数公民不同意用纳税人的金钱建成的仅仅是反映官僚活动的档案馆,而应是更多地为他们提供根源感、身份感和集体记忆。在这种背景下,档案是社会记忆的概念也就呼之而出。
3 社会记忆理论下档案如何真实的反映历史
3.1 传统的档案与历史关系观
传统的档案与历史关系观:史料即是档案,档案是原始历史记录,档案是研究历史的第一手材料,档案工作者是历史真相的守卫者
史料即是档案。档案与历史是紧密相连的。历史的“史”究竟指什么?《说文》解释为“记事者也”,即古代从事记录并保存档案文献的官员。世称“史官”“令史”或“太史”,由史官记录保存的文字材料称为“史料”。历史上讲的史料就是指档案。沿着“史料即是档案”理论思维,在过去档案学是作为“历史学的一个辅助课目”,这个学科属于历史学的一个分支,一般大学中是在历史系下设档案学专业。当然,今天,档案学属管理学。
档案是原始的历史记录。档案定义是这样的,档案是国家机构、社会组织和个人在社会活动中形成的保存备查的文字、图像、声音及其他各种形式的原始记录。把这个定义缩写一下:档案是原始的历史记录。档案定义的本身揭示了它与历史的关系。档案的本质属性是同时具有原始性、记录性,揭示了档案与文物、图书资料的区别所在。图书、文物也是历史研究的条件。但图书虽然同档案一样具有记录性,但它不具备原始性。所以图书它只具有参考性,不能作为证据。因为档案是人在社会活动中直接形成的,如文件、会议记录、录音带、录像带等等,最初是为了处理当时某种事务的需要而产生的,事后仍有某种利用价值,所以保存下来成为档案,它是人们社会实践活动中的副产品,是自然形成的,不是纯粹的人为的结果。而图书不一样,图书是人们事后编写的,因而不是可靠的。它具有记录性,不具备原始性。所以,只是研究历史参考资料,不能是直接的史料证据,档案可以。例如:现在很多人喜欢写书,自我炒作。倪萍写了本书叫“日子”,来自东北铁岭的农村大娘白云她写了本书叫“月子”。很多已退休的革命前辈喜欢写回忆录,回忆那艰苦而又光荣的革命年代,讲那些亲历的故事。这些回忆录不能作为历史研究的证据材料,只可做参考,很多当事人都在书中自我美化、甚至是胡扯,张国焘的回忆录就是胡说。这就是图书与档案区别,档案是有原始性,是可信的。图书是人们事后编写的。同样,历史研究也依靠文物,文物和档案一样有原始性,但不具备记录性。比如古代一把剑、一个瓷罐,人们生产它不是为今天的人们考古研究,而是为满足当时的生活需要,今天从地下挖掘上来就成了历史文物了,他之所以留下来是无意识的。而档案不一样,它是人们有意识保存下来以备日后查考的。古代的有钱人也好,帝王也好,在墓穴里放了许多宝贝是为了陪葬,而最怕的是你以后盗他的墓,否则就不会把它的墓隐藏那么深,真真假假有好多处。出土文物有原始性,但是不具备记录性。若有记录性那就不叫考古了,叫读古了。就是个剑呀,罐呀,玉器呀,上面古啥也没有,要考证,若出土的是个档案库房,那一切历史问题就明朗了。档案是同时具备记录性和原始性,因此档案是研究历史最可靠的研究材料。
档案是研究历史的第一手材料,研究历史离不开档案。正是因为档案是同时具备记录性和原始性,因此,档案是研究历史最可靠的研究材料,是历史研究的第一手材料。尤其是搞历史研究的,离开了档案,就不可能有什么新的学术研究成果。档案是研究历史的最基本条件,历史上很多档案工作者都成为了历史学家,或者说历史上的有些个大学问家他同时是一个档案工作者。《史记》司马迁所作,司马迁所以能写《史记》,是因为他们父子两人在当时是汉代专职记录和保管皇家档案的,他的官职是太史令,所以他在占有了历代帝王和当朝的皇家档案的基础上,同时根据其父司马谈利用档案整理编写的大量历史资料和他个人的历史研究成果,写出了不朽之作《史记》。所以,我们敬爱的周总理说:档案工作者都要像司马迁那样。历史上的老子,春秋战国时代的,他是档案界最古老的前辈,他当时身份是周王室的“柱下史”,专门负责保管王室档案的。孔子是我国最早利用档案材料编书的,孔子编印的“六经”,即《诗》、《书》、《礼》、《乐》、《家》、《春秋》。章学成说过:“六经皆史”、“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也就是说六经就是过去的文件材料汇编成册的。孔子也说了,他编订“六经”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六经”不是孔子的原创之作,只是对官府案牍经过整理、删订而成。尤其是孔子编的《尚书》,就是当时典型的一部王室文件汇编,收录了从传说中的尧、舜、禹到春秋时期各种公文59篇,它是研究我古文起源,典章制度史的一块奠基石。另外,司马光主编的《资治通鉴》,与史记被称为古代史学的“双璧”,司马光是把档案文件汇编与史书撰写结合最完美的一个人。《资治通鉴》的编修大体分三步:先作丛目,次作长编,最后是定稿成正文。先作丛目,干什么,就是把能搜集的历史档案文件列出来,主要以《实录》为主,长编就是把这些个历史文件按照它的观点进行取舍,该留的留,该去的去,汇编成册。然后,第三步在这基础上著作成书。
当今中国有三大学问:敦煌学、徽学、藏学。20世纪中国文献史上有五大发现:甲骨(古)文、汉晋简帛、敦煌文书、明清档案、徽州文书。敦煌学就是对敦煌藏经洞出土文书进行研究,有学者提出敦煌学研究应正名为“敦煌文献研究”。现在的徽学就是以徽州文书为中心,探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发展变化规律的一门学科。周绍良先生在《徽州文书与徽学》中认为:徽学之所以成为一门新学科,决定性因素是大量徽州文书的发现,没有徽州文书就没有徽学研究。1930年,陈寅格在《敦煌劫余录叙》中说:时代之学术,必须有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新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王国维说过“古来就新学问起,大多缘于新发现。”新学问新发现,就是发现了新的档案资料,可用于研究。可见,研究历史必须依靠档案材料,所谓“档案是没有参过水”的历史资料。没有档案,历史将是一片空白。历史学家翦伯赞说过:“最好的裁缝,没有布帛,怎么能做衣服,最好的历史学家,没有资料,怎么能写出历史来。”他认为充分地占有档案史料是进行史学研究的基础。
档案工作者是历史真相的维护者。档案馆主要保存的是官方历史文献,档案是阶级统治的利器。它表现为档案馆被动地接收官方移交的档案,档案保存地是保密场所,历史上“三百年不得一窥”,档案工作者被赋予保护历史维护统治阶级的重任。
3.2 社会记忆理论对传统档案与历史关系观的冲击
社会记忆理论对传统档案与历史关系进行了修正,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档案是权力选择的结果,它没有反映真实的历史;档案工作者不仅是历史真相的维护者而是历史主动建构者。
3.2.1 权力对档案反映真实历史的影响 在传统的档案学研究中,权力关系一直是隐藏而不见的,我们虽然强调档案的形成、积累是“人们有意识地挑选和留存的记录,所以档案又是人类自觉活动的产物”。但我们所强调的“自觉活动”产物,仅止于人们有目的地保存起来以备日后查找,档案只是人们处理社会事务活动中形成的“副产品”。档案工作者只是记录和保存过去,而不是在建构历史。但是,从社会记忆构建的视野看,档案及其管理活动是一个权力场所,它既是国家、民族、阶级权力意志的展现,同时也是档案工作者发挥职业权力的场所,这个权力就是在建构历史中发挥主动作用,而不单纯是保管档案。
档案工作者在各种工作中不可避免地会掺进自己的价值,美国历史博物馆信息技术文化专家史蒂文说:实际上他们是“现实的政治结构和权力关系的共谋”。档案工作者所从事的工作在某种程度上是在构建未来的文献遗产,他们决定哪些社会生活将传递给后代,什么被记忆什么被忘却,谁能够声名远播,谁最后无声无迹。传统的档案馆与档案工作者业已形成的顽固偏见相呼应,那就是为主流文化和当权者服务。这种做法让官方记忆占有特权,却忽视了社会中的个人和群体的记录。“档案记录着谁的记忆”,“档案中能找到过去的什么记忆”,“记忆是如何形成的”。权力对档案选择反映历史真实的影响巨大。巨大到什么程度,就是让我们的子孙后代或者当今的公民看到的大部分只是历史,而且都是一个模式——官方的历史教科书,而将大量有血有肉的民众记忆拒于馆门之外。
例如:中国每个朝代都要修史,所谓:盛世修史。而每个朝代都借修史之名,在征集大量档案史料之后,按照统治者的意志取舍,不用的或对本朝代不利的都销毁。在明代初期靖难之役中,燕王朱棣夺取政权后,就将建文帝包括实录在内的全部档案都销毁。清代统治者为防汉人反清复明,又多次销毁明代档案。所以,今天存世的明代档案很少。文革时期,安徽省档案馆内存有大量的民国时期的旧政权档案,当时的革委会主任说:全部烧掉,反动政权的档案也企图混进我们革命政权的档案馆里来。他这一烧,烧掉安徽省的现代史真相。1990年六四学潮,全国大学生几乎卷入,上街游行、到市中心静坐、搞空校运动、贴标语、贴大字报在各高校都发生过。后来,上面通知,凡是参加六四学潮的学生组织为非法组织,凡是涉及六四学潮的各种照片、录音、录象、大字报、小册子等全部上缴并销毁。很显然这些材料是研究这一历史的第一手材料,但从档案上看历史好像曾经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
权力的影响及其对社会产生的后果,已使档案所反映的历史真实受到众多学者的诘难。档案涉及权力,这就意味着权力借助档案而留存于史。卡罗琳·斯特德曼(Caroline Stedman)认为:欧洲的档案馆是为了巩固和纪念先前的君权及后来的国家权力而产生的。在现实的档案馆里,虽然成包成捆的文件堆积如山,但事实上,真正有用的东西并不多,档案馆里保存的文件是人们有选择有意识地从过去的已用过而无意留存的文件中挑拣出来的。拥有权力的人利用创建文件来巩固权力,并为自己行为的动机和意图涂脂抹粉。档案是有选择、有意识的记忆,因而也是有目的记忆。历史学家肯德里克指出:“那些控制国家的人,只告诉我们他们想要了解的事,而且有时候就像近几年的英国,统治者甚至尽其所能地压住那些可能导致政府政策遭受批判的资料”。权力对历史记录形成和构建的介入,已使作为人类记忆储存所的档案馆产生腐败,它动摇了档案馆和档案文本在重建过去的过程中所享有的特权和无可争议的地位。
3.2.2 档案工作者如何能公正的对待历史,构建社会记忆 档案工作者作为构建社会和历史记忆的积极因素。随着档案工作重点的变化,有必要非常审慎地检讨自己在档案生成和记忆形成过程中所做的选择,从消极的文献记录保存者变为档案遗产的积极塑造者,从仅仅继承文件的公正的,不带偏见的保管者变为在档案形成过程中明确历史责任感的积极干预者。在档案的选择、保护过程中,不仅有义务保护或记录过去,而且有责任把未来铭记于心,增强自身在社会记忆构建中的主体意识,关照整个社会和人类全体的历史经验而不只限于充当国家和公共文件的保管者,惟有如此,才更能反映社会的价值而不只是传统用户或某些重要用户的价值。肩负起“为子孙后代保存社会事实,为人类文明保存社会记忆的重要使命”。就是说,档案工作者仅仅做一个“历史真相”的守护者是不够的,档案界要将自身从事的工作视为保卫社会记忆工作,采取历史干涉主义。如:电子档案的鉴定,就要采取历史干涉主义。现在电子文件不再有“原件”的概念。电子文件的产生,一是海量,二是易更改,变异,失真,损毁,失密。怎样维护电子文件的真实性、可靠性。这就要求档案人提前介入,主动介入,在文件转化成电子档案之前,进行鉴定,进行前端控制。要求档案工作者在文件形成时就要确保有价值的电子文件不被丢失,必须采取干涉主义,更重要的是电子文件是海量产生的,那么你从中只挑选1-2%的典型文件来作为档案保存,那么这种为社会记忆挑选历史素材的主动建构性就是必要的。
2007年5月10日的新浪网报道:题目是《布什档案:有多少不可告人的秘密》。2007年3月号的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刊登了一篇预测未来的文章,列举了五个将在未来引起轰动的事件,其中就包括即将在2014年1月20日解密的小布什总统的档案。根据美国《信息自由法案》,总统退职5年后公众有权查阅前任总统的白宫档案。但是根据美国《沙龙》杂志披露,小布什总统首席政治顾问干若罗夫在发送电子邮件时,没有用白宫的电脑,而是使用了由美国共和党委员会提供的一部黑莓手机。干若罗夫巧妙地规辟了美国法律要求对白宫官员的电子邮件存档的要求。这些电子邮件中到底隐藏什么秘密。正当美国国会准备调查这些邮件时,再次爆出惊人的消息:白宫已经丢失了500万份电子邮件。根据《总统记录法》规定,白宫必须存档并定期公开总统有关政府事务记录,然而在2003年3月至2005年10月间,白宫服务器上超过500万封电子邮件没有保存。这些邮件是故意删除的?有什么秘密?成了美国媒体关注的热点。因为2003年3月至2005年10月间,正是伊拉克战争关键时期,这些邮件有重要历史研究价值,它关系到布什本人和美国共和党的声誉,也许是这些电子邮件神秘消失的原因。更为重要的是布什总统的白宫档案是否会送交档案馆,送到追查真相的历史学家和民众手中。小布什,到底还有多少不可告人的秘密?只有到2014年1月20日以后了。
档案工作者从事的工作,“是在构建未来的文化遗产”。他们决定什么被记忆,什么被忘却。在这样的建构活动中,档案鉴定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为它选择哪些文件成为档案。它最终决定哪些文件被销毁。
加拿大著名的历史学家说过:历史的诠释始于他们在档案馆阅览室打开档案盒那一刻。从某个档案盒里史学家只选取阅读某些档案,只注意某些作者,群体或地区,只摘录或复制某些文件,然后利用他们所选取的特权文件片面地打造某一特定的叙述。加拿大档案馆长库克认为:“事实上远比这个可怕,主要的历史诠释行为并非在史学家打开档案盒之时,而是在档案工作者装盒之际,在于另外98%被销毁的未装进档案盒的文件潜在影响。这是档案工作者和史学家之间最大的沉默,它被称为档案鉴定”。所以,档案界的一位影响巨大的前辈就要求,档案工作者是“现代世界制造的最无私的真理奉献者”,请注意这里的真理用的是大写。为了在浩瀚的文件宇宙中确定一小部分档案,档案工作者如幽灵般地隐形于社会,我们委托人不知道我们广泛地销毁可能对他们有用的资源?过去,档案界做法是在浩瀚的文件中,98%被销毁,2%才保存。而且,档案工作者一直非常幸运,我们作出的鉴定始终逃脱了公众和法律的监视。因为利用者就只能看到一个预先设定的世界——一个由档案工作者和其他人员预定的世界。他们得到的其实仅仅是他们看到的东西,他们见不到的是我们档案工作者在做出鉴定之前所看到的更多的文件,档案工作者在构建社会记忆活动中未受挑战和监督。所以在面对浩如烟海的文件,只能选择小部分保存的情况下,时代要求要关照整个社会和人类全体的历史经验而不是只限于充当国家和公共文件的保管者,这一代档案工作者要作历史真相的维护者和历史主动建构者。
4 当代史学研究新趋势与档案是社会记忆
自古以来,传统史学都以研究精英人物的行为和活动为主线,中外都是如此,平民百姓生活几乎没有。我国的史学界长期依据官方史料叙述正史,在20世纪前,中外史学都是局限于政治史,传统史学研究的理论基础是以“今天的历史即过去的政治,今天的政治即未来的历史”,这样使政治成为史学研究的唯一领域,使史学背离了探索人类社会整个历史存在和各个领域的初衷,造成了历史即是政治史的畸形学术,使史学远离科学,远离民众和实践。单一的政治史研究,日益引起各国史学家的不满。到了20世纪中期,中外史学界掀起了一场新史学运动,新史学不仅包括上层政治,还包括经济、文化,甚至是特定时期内普通人的思想和生活。这一理论与档案是社会记忆是共通的。当代新史学研究开始在最大范围地运用和发掘非官方的档案史料。美国的新史学派发起人历史学家鲁滨逊首先举起了“史学革命”的旗帜,他写了一本20世纪世界史学名著,叫《新史学》。在这部著作里,他要求冲破以政治史为研究中心的传统,扩大历史认知的视野,“大到可以描述民族的兴亡,小到描写一个平凡的人物习惯与感情。”
史学研究的新领域的开拓,必然使得可供利用的档案范围相应扩大。这一新趋势的主要特点表现为:
4.1 可作为史料的档案在内容上更加广泛
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现在特别重视,例如,傩戏史料,过去的档案馆认为这是民间的文化,反映的是山民的生活是不会保存的,这些是社会记忆的缺失。档案馆认识到他的重要性,开始收集傩戏等相关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传统历史研究偏重于在行政档案中挖掘材料,那么现在呢?新的史料被源源不断地发掘出来,诸如选民登记,教区档案,法庭记录,公私帐薄,病史记录,结婚登记,死者遗嘱,家谱,税单等等。都可以视为“史料”。例如,菜谱都可以是历史研究史料,清代的宫廷档案,解决了一桩历史悬案,历史上曾认为光绪皇帝是慈禧害死的,经过新史学家的研究,这不是史实,从当时宫廷每天给光绪皇帝的食谱当中。可以知道,光绪皇帝得了不治之症,那些食疗的菜说出了真相,光绪是自然死亡。看菜单研究历史,过去的史学家是不可能这么干的。又比如:1975年法国出版了一部典型的心态史学研究著作《蒙塔尤:1294-1924年奥克西坦尼的一个山村》。这部论著是因为作者勒华杜里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中发现了一批13世纪宗教裁判所的档案,共有578件详细的审判记录,全部是农民自己的证词。勒华杜里敏锐地意识到这批档案为了研究农村普通人民的精神观念提供了机会。他利用农民自己提供的证明,再现普通农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世界。
4.2 可作为史料的档案在载体和记录形成上发生变化
那就是口述史学和影视史学的出现。口述档案或者叫“口碑档案”是可以作为档案史料加以利用的,例如,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珍本和手稿图书馆(即档案馆)就收藏有大量中国口述历史资料。哥大东西研究所收藏有包括张学良将军在内近60个民国时期重要人物的口述材料,是研究中国现代史的重要材料。过去的史学家认为这种口述历史材料不可靠。今天新史学研究者认为是可以作参考的,可以利用的。另外就是影视史学,影视史学是当代欧美史学大家族中的一个新事物。1988年,美国史学家怀特首创“影视史学”这一新名词。他是希望通过视觉影响和相配套的话语传达历史以及对历史的见解。如反映历史题材的纪录片,就是新史学与档案史料有效结合的典型例子。最近中央台播放《大国的崛起》、《百年中国》等等,收视率很高,这一题材的片子无一例外是利用档案馆珍藏的文件及过去的录音、录像档案来述说历史。
总之,新史学研究内容不仅是官方叙述,更多反映社会史,文化史,经济史,还有人民群众的生活史,他要求案馆更多地关注民众生活,社会生活,经济生活等反映整个社会记忆的档案。反过来,这些档案又促进了新史学研究取得越来越多的成果,更加贴近历史科学,贴近社会生活,贴近民众。
收稿日期:2007-10-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