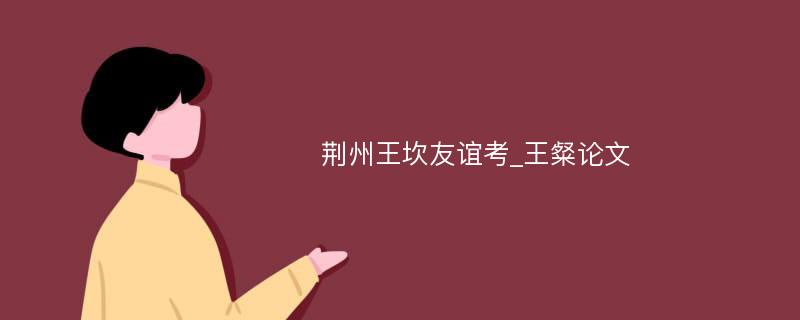
王粲荆州交游考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荆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09)-0439-06
目前,学界关于王粲的研究日趋成熟,但王粲荆州交游似乎少有学者关注。就王粲现存诗文来看,除《登楼赋》和《七哀诗》[西京乱无象][荆蛮非我乡]外,他投靠曹操前的诗文创作皆与其荆州交游有关。本文拟通过考察王粲在荆州的交游情况,以探讨其对王粲的诗文创作和思想的形成所产生的影响。
一、王粲的荆州交游
东汉末年,王室极度衰微,各地群雄并起,割据一方,互相残略。在战乱频仍的中国,只有荆州刘表、辽东公孙度以及西蜀刘璋父子治下为当时相对太平之地。许多士人为躲避战乱,纷纷奔入荆州。刘表对他们施以安抚政策,并大力兴办官学,使得荆州聚集了众多文士。《后汉书·刘表传》载:“表招诱有方,威怀兼洽,其奸滑宿贼更为效用,万里肃清,大小咸悦而服之。关西、兖、豫学士归者盖有千数,表安慰赈赡,皆得资全。”[1]王粲亦于初平三年(192年)① 避难荆州。他在荆十六年,主要过着“振冠南岳,濯缨清川。潜处蓬室,不干势权”[2]的生活。虽然政治上不得刘表重用,但他在荆州文化建设及交游方面收获颇丰。笔者据《三国志》《后汉书》及其他相关史料考得王粲荆州交游凡十二人,大致分两类:当权者、同僚友人。
(一)当权者
1.刘表
刘表字景升,山阳高平人,早年师从王粲祖父王畅。《三国志·魏书·刘表传》裴松之注引谢承《后汉书》曰:“表受学于同郡王畅。”[3](211)后领荆州牧,割据一方。王粲避难荆州,投入刘表幕下。建安三年(198年),刘表领兵攻打长沙张羡。王粲作《三辅论》为刘表制造舆论宣传,文曰:“天生五材,金作明威。长沙不轨,敢作乱违。我牧睹其然,乃赫尔发愤,且上征下战,去暴举顺。”[4](133)
建安九年(204年),刘表的同盟袁谭、袁尚兄弟相争不和,王粲为刘表作文与袁氏兄弟。建安十年(205年)②,刘表在荆州兴办官学,卓有成效,王粲作《荆州文学记官志》:
有汉荆州牧刘君,……乃命五业从事宋衷新作文学,延朋徒焉,……耆德故老綦毋闿等,负书荷器自远至者,三百有余人。……六略咸秩,百氏备矣。[4](137)
王粲的《英雄记》对此亦有记载:“州界群寇既尽,表乃开立学官,博求儒士,使綦毋闿等撰《五经章句》,谓之《后定》。”[4](252)由上可知,王粲在荆州政治和文化上的活动,都与刘表的立场与举措有直接的关联。
2.刘琮
刘琮,刘表第二子。刘表病亡,他袭荆州牧一职。建安十三年(208年),曹操攻荆州之际,王粲劝其投降曹操。《三国志·魏书·王粲传》裴松之注引《文士传》载王粲劝说刘琮:“如粲所闻,曹公故人杰也。雄略冠时,智谋出世,……将军能听粲计,卷甲倒戈,应天顺命,以归曹公,曹公必重德将军。……粲遭乱流离,托命此州,蒙将军父子重顾,敢不尽言!”[3](598)王粲因劝降有功,被曹操封为关内侯。
(二)同僚友人
1.士孙萌
士孙萌,字文始,扶风人。初平三年(192年),王粲与其一起投奔荆州刘表。二人在荆州过从甚密。后士孙萌因其父士孙瑞有功于汉帝,被封为澹津亭侯。他离荆就职之际,王粲作《赠士孙文始诗》。《三国志·魏书·董卓传》裴松之注引《三辅决录注》曰:“瑞字君荣,扶风人,世为学门。瑞少传家业,博达无所不通,仕历显位。卓既诛,迁大司农,为国三老。每三公缺,瑞常在选中。……天子都许,追论瑞功,封子萌澹津亭侯。萌字文始,亦有才学,与王粲善。临当就国,粲作诗以赠萌,萌有答,在《粲集》中。”[3](186)
士孙萌的《答王粲诗》现已不存,但王粲《赠士孙文始诗》保存完好,诗曰:
天降丧乱,靡国不夷。我暨我友,自彼京师。宗守荡失,越用遁违。迁于荆楚,在漳之湄。在漳之湄,亦尅晏处。和通篪埙,比德车辅。既度礼义,卒获笑语。……尔之归蕃,作式下国。……既往既来,无密尔音。[4](81-82)
王粲与士孙萌皆为名公之后,又一同避难荆州,两人谊深情契。诗中所谓“和通篪埙,比德车辅”,前半句出自《诗·小雅·何人斯》“伯氏吹埙,仲氏吹篪”。篪、埙是两种乐器。孔颖达疏:“其情相亲,其声相应……其恩亦当如伯仲之为兄弟,其情志亦当如埙篪之相应和。”[5]后半句“比德车辅”,“比德”意谓同心同德。《国语·晋语八》:“君子比而不别。比德以赞事,比也。”[6]车辅谓牙床与颊骨,比喻关系密切,相互依存。诗中言二人恩如兄弟,和谐相应,又称道君子之交,同心同德,可见王粲与士孙萌关系甚为密切。
2.蔡睦
蔡睦,字子笃,陈留考城人。蔡睦早年与王粲共同避难荆州,后归故里,王粲作诗以赠。王粲《赠蔡子笃诗》曰:
翼翼飞鸾,载飞载东。我友云徂,言戾旧邦。……君子信誓,不迁于时。及子同寮,生死固之。何以赠行?言授斯诗。中心孔悼,涕泪涟洏。嗟尔君子,如何勿思
《晋书·蔡谟传》载:“(谟)曾祖睦,魏尚书。”[7](2033)《文选》李善注王粲《赠蔡子笃诗》引《晋官名》曰:“蔡睦,字子笃,为尚书。”[8](334)五臣注《文选》吕向注曰:“蔡子笃为尚书,仲宣与之为友,同避难荆州,子笃还会稽,仲宣故赠之。”[9](417)据此诗,可知王粲与蔡睦为朋友兼同僚的关系,所谓“君子信誓,不迁于时。及子同寮,生死固之”。在这首诗中,诗人流露出了深厚的情谊。诗以“翼翼飞鸾,载飞载东”起兴,引出友人东归故里,结尾四句写惜别时的涕泪交加及对友人永不忘怀的盟誓,都反映了王蔡二人的交好之深。
3.文颖
文颖,字叔良,南阳人,为刘表荆州从事,与王粲交好。文颖后归曹,任甘陵丞。颜师古《汉书叙例》载:“文颖字叔良,南阳人,后汉末荆州从事,魏建安中为甘陵府丞。”[10]王粲集中有《赠文叔良诗》,诗曰:
翩翩者鸿,率彼江滨。君子于征,爰骋西邻。……既慎尔主,亦迪知几。探情以华,睹著知微。……惟诗作赠,敢咏在舟。[4](82-83)
《文选》李善注曰:“干宝《搜神记》曰:‘文颖,字叔良,南阳人。’《繁钦集》又云:‘为荆州从事。’文叔良作《移零陵文》,而粲集又有《赠叔良》诗。献帝初平中,王粲依荆州刘表,然叔良之为从事,盖事刘表也。详其诗意,似聘蜀结好刘璋也。”[8](335)文颖奉刘表之命出使益州,王粲作为同僚以诗赠行,劝戒其言语须谨慎得当,以免生祸害身。
4.潘文则
潘文则,生平事迹不详。王粲集中有《为潘文则思亲诗》,诗曰:
穆穆显妣,德音徽止。……庶我刚妣,克保遐年。亹亹惟惧,心乎如悬。如何不吊?早世徂颠。……仰瞻归云,俯聆飘回。飞焉靡翼,超焉靡阶。思若流波,情似坻颓。诗之作矣,情以告哀
潘文则的母亲逝世,王粲为其写哀情切切的《思亲诗》,可见王粲与潘文则交情匪浅。
5.宋衷
宋衷(又作宋忠),字仲子,南阳章陵人,任荆州官学五业从事。建安十三年(208年),归曹。《经典释文·序录》载:“宋衷字仲子,南阳章陵人,后汉荆州五等从事。”[11]王粲《荆州文学记官志》也有记载,见上文刘表条引文。
王粲撰《荆州文学记官志》以总结荆州官学的成就,说明他是荆州官学的重要成员。宋衷本为荆州官学的主要负责人,则两人在官学中应有较多的交往。沈玉成《王粲评传》即言:“从一些迹象来看,王粲在荆州十五年,曾和经学大师宋忠有所交往。”[12]
6.裴潜
裴潜,字文行,河东闻喜人。避乱荆州时,裴潜认为刘表坐拥荆州却不图进取,其势必败,故而弃表而去。《三国志·魏书·裴潜传》载:“裴潜字文行,河东闻喜人也。避乱荆州,刘表待以宾礼。潜私谓所亲王粲、司马芝曰:‘刘牧非霸王之才,乃欲西伯自处,其败无日矣。’遂南适长沙。”[3](671)从裴潜与王粲私下评论刘表来看,二人私交很深。
7.司马芝
司马芝,字子华,河内温人。早年避乱荆州,与王粲、裴潜私交甚深,参见上一条交游考引文。司马芝于建安十三年(208年)归曹,在此之前其“居南方十余年,躬耕守节。太祖平荆州,以芝为菅长”。[3](386)司马芝“居南方十余年”,而王粲在荆州十六年,可知两人留居荆州的时间一致,又是知交,因此他们长期的交往势必对彼此都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这表现为他们在具体的政治思想上有较多的共通性。
8.王凯
王凯,王粲族兄。初平三年(192年),与王粲一起离开长安,投奔荆州刘表。刘表纳其为婿。建安十三年(208年),归曹。建安二十四年(219年),王粲二子因参与魏讽谋反事件,而被曹丕斩杀。后曹丕将王凯子王业过继给王粲。《三国志·魏书·钟会传附王弼》裴松之注引张华《博物记》载:“初,王粲与族兄凯俱避地荆州,刘表欲以女妻粲,而嫌其形陋而用率,以凯有风貌,乃以妻凯。凯生业,业即刘表外孙也。”[3](796)
9.潘濬
潘濬,字承明,武陵汉寿人。早年从宋衷受学,为刘表江夏从事。后归吴。潘濬在荆州时,王粲赏识其“对问有机理”。此见其本传裴松之注引《吴书》曰:“濬为人聪察,对问有机理,山阳王粲见而贵异之。由是知名,为郡功曹。”[3](1397)
10.繁钦
繁钦,字休伯,颍川人。繁钦能文,有辩才,长于书记,又善为诗赋。汉献帝初平间避乱荆州。后投曹操,为豫州从事。据《晋书·习凿齿传》载:
每定省家舅,从北门入,西望隆中,想卧龙之吟;……裴杜之故居,繁王之旧宅,遗事犹存,星列满目。[7](2153-2154)
又据《太平御览》卷一八○引《襄沔记》记载:“繁钦宅、王粲宅并在襄阳,井台犹存。”[13]由此可知,繁钦与王粲在荆州所居应相距不远,二人可能有所交往。
以上所列是有史料可考的与王粲在荆州有交游行为的十二人。此外,东汉末年,与王粲一样避难荆州的士人有很多,如邯郸淳、和洽、傅巽、杜裘、赵俨、韩暨、刘廙、杜夔、桓阶等。王粲在荆州十六年,可能与这些人也有交往,只是材料不足,不敢妄作猜测。
二、荆州交游对王粲诗文风格的影响
今存王粲投归曹操前的作品大致可分为三类:赠答类,如《赠蔡子笃诗》《赠士孙文始诗》等;政治功用类,如《为刘表谏袁谭书》《为刘表与袁尚书》等;自我抒情类,即《登楼赋》《七哀诗》[西京乱无象I等。前两类占其投曹前诗文的绝大部分,且都与其荆州交游有关,可以说,王粲的荆州交游极大地促进了其当时的诗文创作。
钟嵘《诗品》评王粲曰:“其源出于李陵,发愀怆之词。”[14]王粲入邺后,诗文风格以积极昂扬为主,少有“愀怆之词”,因此钟嵘这一评语主要针对王粲投曹前所表现出来以情见长的诗文风格而发论。赞誉极高的《登楼赋》和《七哀诗》无疑为此风格的代表作品,但与王粲荆州交游有关的其他两类作品亦充分表现了这一以情见长的风格。
王粲在赠答诗中既流露出对友人的难舍之情,又注入自己的身世之感和对世路的忧虑,可谓情挚婉凄、愀怆动人。如《赠蔡子笃》“我友云徂,言戾旧邦。……悠悠世路,乱离多阻。济岱江衡,邈焉异处。风流云散,一别如雨。人生实难,愿其弗与。……及子同僚,生死固之。……中心孔悼,涕泪涟洏。”王粲涕泪交加不舍友人蔡子笃离荆归故乡,亦感叹世路乱离,人生多违。一句“风流云散,一别如雨”道尽了人生的无奈和无常。陈祚明曾言:“情至语反质直,不务繁绘。‘风流云散’八字,飘渺悲凄。”[15]《赠文叔良》一诗为王粲送文颖出使蜀地以结好刘璋。王粲对文颖去蜀之言行叮咛备至,“君子慎始,慎尔所主。……既慎尔主,亦迪知几。探情以华,睹著知微。……成功有要,在众思欢。人之多忌,掩之实难。”王粲生性谨慎,其对文颖多番强调须“慎始”“慎尔主”“睹著知微”,可以说是王粲在倾其人生经验以告文颖,望其出使顺利,两邦成泰。两人的深厚情谊亦显然可见。《为潘文则思亲诗》则站在潘文则的立场上,抒发对逝去的潘母绵绵无绝的深切哀痛,“形景尸立,魂爽飞沉。……仰瞻归云,俯聆飘回。飞焉靡翼,超焉靡阶。思若流波,情似坻颓”,悼诗充满了哀婉悲凄之情。
王粲赠答诗以四言为体,以离情、悲情、悼情渗透其中,充分反映了其以情见长的风格。这正如韩国学者崔宇锡所言:“王粲诗多以“情胜’,其四言诗,亦不例外,处处流露出浓厚之抒情色彩。”[16]
不唯赠答诗以“情胜”,王粲在荆为刘表所作的政治应用文也表现了这一风格,如《为刘表谏袁谭书》[4](115-117)、《为刘表与袁尚书》[4](118-120)两篇。刘表同盟袁绍病亡,其二子相争于内,王粲因此为刘表致书袁谭和袁尚,意在劝和。两书中,王粲紧紧抓住“一理两情”,即和能成事,争则败事之理及父子之情和兄弟之情,对袁氏兄弟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王粲在两书中首先陈理以谏袁氏兄弟,“未有弃亲即异,兀其根本,而能全于长世者也”“二惠竞爽犹可,又弱一个,姜氏危哉”。在这一道理下,王粲抓住袁绍因曹操而死这一事,谏劝袁谭、袁尚二人应子承父业,报仇为先。王粲举齐襄公灭纪国为其九世祖齐哀公报仇和士匄承荀偃之业继续伐齐终使荀偃死而瞑目为例,以劝袁谭明确报仇的重要性和首要性,“昔齐襄公报九世之雠,士匄卒荀偃之事,是故《春秋》美其义,君子称其信”;另一面,王粲亦劝袁尚以报仇为先,“当惟曹是务,不争雄雌之势”;“有难忍之忿,且当先除曹操,以卒先公之恨”。此外,王粲还假设袁氏兄弟相争,曹操乘虚而入后的后果“则是太公坟垅,将有汙池之祸,夫人弱小,将有灭族之变”。王粲通过陈理、举例、叙情等方法,试图让袁氏兄弟认识到当务之急是除曹操,报父仇。在把握住父子之情的基础上,王粲在两书中又强调兄弟之情。在《为刘表谏袁谭书》中,王粲将袁谭比为贤明的郑庄公和舜,希望袁谭本于兄弟之情,能够像郑庄公和舜一样以宽容为怀,接纳其后母,原谅其弟。《为刘表与袁尚书》则通过批评袁谭“迷于目前”,赞扬袁尚“智数弘大”这一贬彼褒此的方式,劝袁尚基于兄弟之情以宽和为本,“以大包小,以优容劣”。
尽管袁氏兄弟最后还是难止干戈,相争而败,但王粲“一理两情”的两封劝谏书写得真挚感人,情理兼具,极尽劝谏之思。明人张溥对此二书予以充分肯定,其曰:“袁显思兄弟争国,王仲宣为刘荆州移书苦谏,今读其文,非独词章纵横,其言诚仁人也。昔颍考叔一言能感郑庄,使母子如初。仲宣二书,疾呼泣血,无救阋墙。袁氏将丧,顽子执兵,即苏张复生何益哉?”[17]
无论是赠答诗还是政治应用文,王粲这些与交游有关的诗文都突显其情感作用,它们与《登楼赋》《七哀诗》一样,皆为“愀怆之词”,都表现了王粲为世人所称誉的以情见长的诗文风格。
三、荆州交游对王粲政治和学术思想的影响
王粲客居荆前后有十六年之久,在此期间,除为当权者刘表制作一些政治应用文外,他的其他作品大部分与其交游有关,可见与同僚友人的交往应为他生活的重要部分,其以情见长的诗文风格即在荆州形成。此外,他的政治、学术思想及处世之道亦与其荆州交游有较大的关联。
政治思想和处世之道的影响一般需要在情投意合的基础上,假以相当的时日方能产生。据上文所考,与王粲有笃厚情谊的友人不为少,但多交往时间较短,如士孙萌、蔡子笃等,因此他们对王粲思想的影响较难看出。而兼具知交和长期交往两个条件的司马芝,对王粲思想的影响痕迹十分明显。这不仅表现在两人皆尚儒法并用的思想,如司马芝宽以待民,严以治“妖刑”[3](388);王粲作《儒吏论》《爵论》《难钟荀太平论》等提倡儒法兼济,而且他们在具体的政治思想和为人之道方面都表现出较多的共通性。
1.反对吏之“苛暴”
《三国志·魏书·司马芝传》载一官吏发现被盗“官练”挂于“都厕上”,而怀疑其系女工所为,并将她收押入狱。司马芝则认为:“刑罪之失,失在苛暴”,他反对官吏“脏物先得而后讯其辞,若不胜掠,或至诬服”的“苛暴”断案方法,并要求官吏应当遵从“简而易从,大人之化”之政,宽宥断狱。[3](388)
王粲《儒吏论》[4](131)批判刀笔吏的“察刻”,提倡“吏服训雅”。这与司马芝的思想大体一致。只是王粲比司马芝更进一步,他分别分析了刀笔吏之“察刻”和缙绅儒之“迂缓”的成因:“(刀笔之吏)起于几案之下,长于官曹之间,无温裕文雅以自润,虽欲无察刻,弗能得矣。竹帛之儒,岂生而迂缓也?起于讲堂之上,游于乡校之中,无严猛断割以自裁,虽欲不迂缓,弗能得矣。”针对刀笔吏和缙绅儒自身弊病,王粲提出“吏服训雅,儒通文法”的解决方法,以达到“宽猛相济,刚柔自克”的效果。
2.提倡以农为本
《三国志·魏书·司马芝传》载司马芝就当前社会从商弃农的现状,提出“王者之治,崇本抑末,务农重谷。……国家之要,惟在谷帛。……臣愚以为不宜复以商事杂乱,专以农桑为务,于国计为便。”[3](388-389)司马芝十分强调“农桑”的重要性,提出谷帛为“国家之要”。王粲《务本论》[4](135)的主旨也是以农为本,他认为“八政之民也,以食为首”。此外,王粲还进一步提出兴农的具体措施,即将赏罚与兴农结合,提出设官吏以监督农业生产每一个环节,农兴则赏吏,农败则罚吏。“设农师以监之,置田畯以董之,黍稷茂则喜而受赏,田不垦则怒而加罚。……种不当时、耘不及节、收不应期者,必加其罚;苗实逾等,必加其赏也。农益地辟,则吏受大赏也;农损地狭,则吏受重罚。”监农官吏在这种责任制下,势必尽职以促进农业生产,国家也就达到兴农固本的目的了。
3.亮直的为人之道
司马芝为人刚直堂正,与他人交往有不满之处或异已之言,皆当面说出,从不背后议论他人。《三国志·魏书·司马芝传》载:“芝性亮直,不矜廉隅。与宾客谈论,有不可意,便面折其短,退无异言。”[3](389)王粲《反金人赞》[4](130)亦有相似的思想流露,“金人”事见《孔子家语》,“孔子观周遂入太祖后稷之庙,堂右阶之前,有金人焉,三缄其口,而铭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无多言,多言多败;无多事,多事多患,安乐必戒……。’”[18]孔子赞扬闭口不语以避祸的金人,王粲则态度鲜明地反对孔子对金人的赞美,并提出“一言之赐,过乎屿璧”,批评“面言匪忠,退有其谪”的“不敦”风气。他认为应做一个亮直之“君子”,对朋友有益的话应及时当面说出,是为“诲焉是益”,而非三缄其口。这与司马芝的为人之道比较一致。
从这三个方面可以看出,司马芝与王粲在荆州长期的交往,对王粲政治思想和处世之道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此外,裴潜对王粲也有所影响,如王粲评价刘表“自以为西伯可规”,实本自裴潜的“乃欲西伯自处”[3](671)。
在学术思想影响方面,首推刘表。五经之中,刘表重视《易》《礼》,其著有《周易章句》和《新定礼》。王粲对此二经也研习较深。据《汉晋学术编年》载,王粲著作除诗赋外有:《尚书问》四卷、《汉末英雄记》十卷、《新撰杂阴阳书》三十卷、《去伐论集》三卷、《算术》《荆州文学官志》《魏国登歌》《魏国安世歌》《魏国俞儿舞歌》四篇及《魏朝仪》。[19]《新撰杂阴阳书》现只存书名,但就是从书名也可知其应与《易》有关,而《去伐论集》今业已亡佚,但刘勰在《文心雕龙·论说》中将其与魏晋玄学著作并列,“详观兰石之《才性》,仲宣之《去代(伐)》,叔夜之《辨声》,太初之《本玄》,辅嗣之《两例》,平叔之《二论》,并师心独见,锋颖精密,盖人伦之英也。”[20]这说明《去伐论集》即使不是《易》学著作,也应与《易》有涉。在礼乐制度方面,王粲投曹后,司侍中一职,他的主要职责是典定朝廷礼仪制度、改制宫廷雅乐等,《三国志·魏志·王粲传》载:“时旧仪废驰,兴造制度,粲恒典之。”[3](598)王粲不仅擅长典定朝仪,撰有《魏朝仪》,还著有《爵论》,且熟谙服佩之法,其本传裴松之注引挚虞《决疑要注》曰:“汉末丧乱,绝无玉珮。魏侍中王粲识旧珮,始复作之。今之玉珮,受法于粲也。”[3](599)由上可知,王粲和刘表两人皆重《易》《礼》。刘表为荆州官学的领导者,他的学术倾向必然会对官学产生导向作用。王粲是荆州官学的骨干,刘表对他影响较大,因而两人治经有相同之处。
除了刘表,宋衷对王粲的影响也是比较明显的。宋衷治经迥异于北方郑玄,时人虞翻即指出“若乃北海郑玄,南阳宋衷,虽各立注,衷小差玄而皆未得其门,难以示世”。[3](1322)师从宋衷的王肃撰文讥斥郑玄,《三国志·魏志·王肃传》载:“(肃)年十八,从宋忠读《太玄》,而更为之解。……肃善贾、马之学,而不好郑氏,采会同异,为《尚书》、《诗》、《论语》、《三礼》、《左氏》解,……肃集《圣证论》以讥短玄。”[3](414-419)间接师从宋忠的李譔亦与郑玄治经相左,《三国志·蜀志·李譔传》:“父仁,字德贤,与同县尹默俱游荆州,从司马徽、宋忠等学,譔具传其业,……著古文《易》、《尚书》、《毛诗》、《三礼》、《左氏传》、《太玄指归》,皆依准贾、马,异于郑玄。与王氏殊隔,初不见其所述,而意归多同。”[3](1026)与王肃、李譔一样,王粲治学倾向同于宋衷,异于郑玄。王粲曾作《尚书问》以难郑玄,据《颜氏家训·勉学》篇载:“吾初入邺,与博陵崔文彦交游,尝说《王粲集》中难郑玄《尚书》事。”[21]《旧唐书》卷一百二《元行冲传》载元行冲《释疑》曰:“自此之后,唯推郑公。王粲称伊、洛已东,淮、汉之北,一人而已,莫不宗焉。咸云,先儒多阙,郑氏道备,粲窃嗟怪,因求其学。得《尚书注》,退而思之,以尽其意,意皆尽矣。所疑之者,犹未喻焉。凡有两卷,列于其集。”[22]另外,据侯康《补后汉书艺文志》载,王粲撰《尚书问》难郑玄,引起郑玄弟子田琼、韩益的不满,他们就王粲《尚书问》作《释问》以反击。《隋书·经籍志》载王粲著《尚书释问》,实际上是王粲《尚书问》和田琼、韩益《释问》的合并。[23]王粲治学倾向与宋衷一致,与郑玄相异,表明王粲受到了宋衷的影响。
综上所述,王粲荆州诗文创作多与其交游有关,它们反映了王粲备受世人认可的以情见长的诗文风格;王粲与司马芝的交游影响表现在两人的具体政治思想的形成和处世之道的诸多相似之处;与刘表、宋衷交游影响则表现在王粲治学重《易》和《礼》,且不同于北方郑玄之学。可以说,王粲荆州交游是研究王粲的一个重要切入口,而王粲荆州交游的考论对学界王粲研究走向全面、成熟也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收稿日期:2008-09-27
注释:
① 目前学界对王粲投奔荆州刘表的时间有多种说法,其中俞绍初《王粲年谱》持初平三年说,其考证翔实可信,故本文取其说。详参俞绍初校点《王粲集》,中华书局,1980年5月,第97页。
② 王粲《荆州文学记官志》作年有二说:建安五年说和建安十年说。前者以俞绍初为代表,后者以曹道衡和沈玉成为代表。曹沈二人考证更精详,本文取其说。详参曹道衡、沈玉成著《中国文学史料丛考》,中华书局,2003年7月,第65-6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