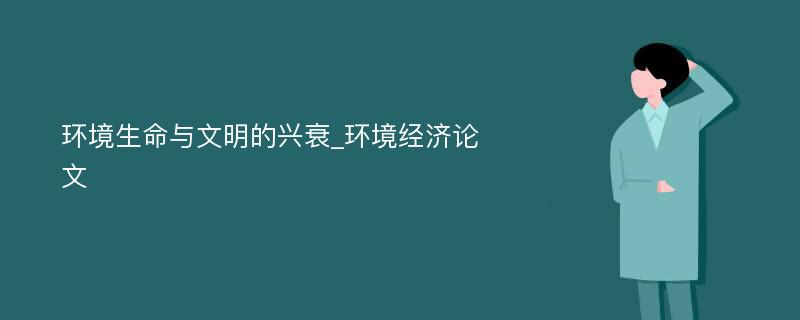
环境寿命与文明兴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兴衰论文,寿命论文,环境论文,文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拟通过对人与自然本质关系的讨论,探讨环境寿命与文明兴衰的内在联系,以及缓和人与自然和其他生命的矛盾,延长环境寿命的基本对策。祈请读者和学者指谬。
人与自然
退化是进化之梯。生命的进化,可区分为自然的进化和反自然的进化。
自然的进化指作为退化结果的进化。当退化作为进化的原因,而进化作为退化的结果时,这种进化便是自然的,如生命的发生。自然的进化是这样的一种进化——不论有无这种进化,作为原因的退化照样发生。地球自然系统的退化为生命的进化提供了条件——地球内部能量的耗散,海陆差异的形成,全球地化物质循环和外力侵蚀等的存在,但地球自然系统的退化并不是以生命的进化为目的的,并不是为了生命的进化。即使没有生命的进化,自然系统的这种退化依然进行——如同太阳系其他没有生命的星球上自然界所发生的退化那样。
反自然的进化指作为退化原因的进化。当退化作为进化的结果和代价,而进化作为退化的原因时,这种进化便是反自然的,如人类的出现。反自然的进化表明了与自然的进化截然相反的另一种客观事实——只是由于这种进化,才导致了与之有关的自然界的退化。
每一生物物种为了生存下去,都必须保持一定的种群数量和密度。低于这一数量和密度,种群便会不可避免地灭绝。此即生物的“最小数量原理”或“最少种群原则。”[1]种群数量也不能超过生境允许的最高数量。多于这一数量,种群生存同样要受到威胁。此即生物的“最大数量原理”或“最多种群原则”。
当种群数量超过生境容量时,生物便会通过“提高”死亡率,“降低”出生率或迁徙维持与环境的平衡。此即生物的“抑制反应”或“自我限制”。[2]当种群数量减少时,生物便会通过“补偿反应”——“提高”出生率——使种群数量得到恢复。
在严酷的环境和激烈竞争的背景下,每一物种为了种群在延续,都须具有无限扩充其种群数量之势。但由于大自然的法则——营养、食物的缺乏或被捕食,其数量则被限定在环境允许的范围之内并与环境保持平衡。此即生物与环境关系的“增殖原理”、“限制原理”和“平衡原理”。[3]
生物的进化在于对自然的遵从。“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大自然通过食物链和食物网,将一切生命置于自己不容违背的法则之下——所有生物都必须处于食物链的某一环节,在食物网内找到自己的位置,并在其“生态位”允许的范围内活动;所有种群都不得超越生境容量。一旦超越,便不得不进行“自我限制”。以体能被动适应环境而生存的生物,只能遵从自然的一切法则。而正是这种对“自然法则”的绝对遵从,生物才得以在地球环境严酷化的背景下,沿着进化的阶梯拾级而上。
人类的进化在于对自然的异化。与生物“体能适应”完全不同的“文化适应”——发达的智慧、制造工具和从事劳动,使人类从诞生的那一天起,便把自己同其他生命对立了起来,便开始了对自然的异化——处于食物链的各个环节和食物网的任一位置,活动于从陆地到海洋,从地下到天空的几乎所有场所——“生命之网”由此被撕碎,“自然的秩序”由此被破坏,生态环境由此而退化——生物栖息地被侵占,物种退化和灭绝,自然环境恶化——人类反自然、反生命的本质即在于此。而不如此,人便不成其为人,人的本质便在于反自然。正是由于对自然的异化,人类才得以远离动物界,人类社会才得以走上繁荣、昌盛和文明之路。[4]
环境寿命
“环境寿命”概念是对生态退化过程和生态退化累积观察的“拟生化”。
环境寿命可分为自然寿命和利用寿命。
自然寿命指生态系统从发育到完全退化所持续的时间长度。一些系统的寿命可与一个相对稳定的地质时期持续的时间相当,如山地、平原等。经过一次大规模的构造运动之后,再重新开始新的环境系统的持续;一些系统则在该地质时期内,经过多次变化,如各种生物群落的生态演替;一些系统则横跨两个,甚至多个地质时期。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地质时期内,环境的自然寿命具有三个方面的特征。
一是循环再生。赖于太阳能量源源不绝的输入和水分、大气及其他地化物质的全球性循环,土壤、矿藏等非生命系统,都通过成土过程、成矿过程再生着,只是从人类眼光看太慢而已(故有非再生资源之说)——生成12英寸(约30厘米)的表土需要1000年时间,而强烈的剥蚀只需数十年即可将此层表土全部冲走(按10000吨/km[2,]·年的侵蚀模数,所需时间为25年)。全世界每年铜的开采量为900万吨,而板块活动生成的可供开采的仅1万吨。[5]
二是寿命转移。全球性循环不仅是一个环境寿命再生的过程,而且还是一个物质和能量,从而环境寿命转移的过程——以水、风为动力的剥蚀(水蚀、风蚀)→搬运→堆积过程,将物质由陆地转移到海洋,由山地转移到平川,由此地转移到彼地。对剥蚀区来说,这是一个物质和能量损失,环境寿命减少的过程;而对堆积区来说,则是一个物质富集,能量增加,环境寿命增加的过程——海岸水体营养带的形成,河口三角洲的产生,平原和川区土壤的肥沃化……
风力对物质的转移常被忽视,但规模也是惊人的。每年春季被风扬起的黄土高原(其亦由风力作用而成)和更远沙漠中富含营养的碱性尘埃,缓和了日本岛三至五月酸雨对作物的危害,并为夏威夷与阿拉斯加之间海洋的浮游生物送去丰富的食物。[6]大西洋上空由东而西的信风,则定期将撒哈拉大沙漠富有营养的沙尘送到亚马逊河流域的热带雨林地区,以弥补该地磷酸钙的不足。
如果是有害物质的转移,则是流失区环境寿命的增加,堆积区环境寿命的减少。
三是死而复活。对局部、小范围的环境来说,在一定条件下,如物质的输入,如外界干扰(特别是人类)的排除,可出现死而复活的情况:朝鲜“三八线”地带因禁止任何人入内,几十年来成了以鸟类为主的野生动物的乐园;科威特的沙漠因海湾战争所布数百万枚地雷的“看守”而恢复了生机——水鸟数量大增,过去罕见的沙生植物以惊人的速度增长,20年来环境的恶化得到了根本的扭转。[7]
利用寿命指生态系统在人类活动背景下所能持续的时间长度。环境的利用寿命与以下三个方面的因素密切相关。
一是自然本底,即环境质量。(1)自然条件。包括降水(降水量、降水强度、季节分布和年变率等)、气温(温和、酷热、严寒)、地形(山、川、坡度)、植被(覆盖度、森林、草场)、水文地质条件等。(2)资源性质。可重复利用的再生资源、一次性的非再生资源,以及资源储量。(3)生态特征。从生态特征看,系统大致可分为两类:多样性和复杂程度高的稳定系统和简单、多变的不稳定系统(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应从抵抗力和恢复力两个方面去观察。此处仅就抵抗力而言)。一般而言,自然条件好,再生性资源和稳定生态系统的环境寿命长。
二是利用方式。即合理还是不合理或掠夺性利用。如对矿产的综合利用与单一开采,统筹开发与采富弃贫和乱挖乱采;对森林的间伐还是平面推进;对草场利用的轮流放牧还是集中使用;对耕地的休闲、轮作与连续使用等。耕地的休闲、轮作可恢复地力,延长利用寿命,连续使用和一年数作则导致地力衰退,缩短利用寿命。如在热带的贫瘠土地上,传统的刀耕火种一般是栽培1~2季作物,然后休耕10~15年或更长时间。而人口数量增加对食物的压力,则使休耕期缩短至5年以内,林木不能恢复,土地退化。[8]
三是利用强度。利用强度同环境利用寿命成反向相关。过度利用会极大地缩短环境寿命,且总是同不合理的、掠夺性的利用相联系。如土地利用中的过度垦殖和陡坡耕作,草场利用中的超载过牧,对森林的过伐、滥樵,对鱼类的过度捕捞,对矿藏的过采,对地表水和地下水的过度利用等。
以上叙述表明,环境利用寿命是自然本底、利用方式和利用强度的函数。特别是利用方式和利用强度,对环境利用寿命有着根本性的作用。而且,自然本底愈差,这种根本性作用便越明显。在生态脆弱地区,一次强度的不合理利用,便可造成永久性的生态退化。而对环境利用的方式和强度,又决定于人口的数量,以及人们的欲望、知识和理性。非洲因饥荒饿死的人口,70年代初为100万人,80年代中期则达300万人,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即是人口过多增加和在人口压力下对土地的不合理和强度利用。如土地休耕期的缩短、草场的垦殖,由游牧到定居引起的对居民点周围土地、水源的过度利用等。[9]
文明兴衰
资源,也即环境是经济发展的“阿基米德支点”。从能源的生产和消费来看,1990年美国、日本、前苏联、原西德、法国、意大利、英国、加拿大、巴西和中国等按国民生产总值计的十大经济国,能源生产量占世界的59.9%,消费量占71.6%。全球十大能源生产国中(1987),十大经济国占其五;十大能源消费国中,十大经济国居其九。虚拟十大能源出口国中(以生产和消费为基础的虚拟),十大经济国仅占其一;虚拟十大能源进口国中,十大经济国居其六;[10]1988年,铝、铜、铅、锡、铁矿石等重要矿产的生产,十大经济国多排在前十位之后,而消费则多排在前十位,且对这些矿产的消费量,又多占到全球的60~70%以上。[11]
对资源的大量消费,构成了庞大经济的基础。穷国与富国,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重要差异,也同样表现在对资源的消费量上。1990年,人均商业能源的消费量(油当量),低收入国为339千克,中下等收入国1025千克,中上等收入国1818千克,高收入国5158千克,对应比(以低收入国家为1.0)顺次为:1.0:3.0:5.4:15.2。[12]
非再非资源是个常数,环境是有寿命的,对之的利用时间,从而对环境寿命的消耗程度,便成为文明兴衰的重要因素。
当宏观纵横历史时,便不难发现:古代文明不是早已沦为废墟(如巴比伦文明、玛雅文明等),便是演变为当代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印度、埃及等)。而在发展中国家的先人创造辉煌业绩时还处在茹毛饮血阶段的野蛮民族或几百年前还是处女地的地区,则创造了现代文明或在其上发展起了发达的经济(美国、加拿大、澳洲、欧洲——古希腊、古罗马等亦创造过灿烂的古代文明)。而且,与古代文明相联系的发展中国家,生态环境又都差于同近代文明相联系的发达国家。二者的差异,除经济外还表现在农业生产上,古代文明的发展中国家依赖粮食进口,近代文明的发达地区出口谷物。由此,便可形成以下近似的对应:
古代文明→当代发展中国家——环境条件差——进口谷物
近代文明→当代发达国家——环境条件好——出口谷物
以上的“巧合”,是否表明了这样一种历史过程——在过度利用(由于人口数量和欲望压力的存在,以及人类目的与自然演化方向的矛盾,对自然的利用在大部分时间里是过度的)从而消耗超过再生的背景下,历史悠久的利用创造了古代文明,但却消耗了环境的许多寿命,使之进入明显退化的衰老阶段。自然条件变差,土地瘠贫,一些死而复活的环境,其质量也大大下降了。于是,古代文明或消亡,或演变和再生为当代的发展中国家。短的开发历史对应于寿命消耗少的环境。如同古代文明当时在历史上的发生一样,在这年轻的环境中,发展起了近代文明并演变为当代的发达国家。
环境是有寿命的,在其上生长的文明总是会衰退的。这种衰退,往往又呈现出先发展先衰退,后发展后衰退的规律。依据对环境的利用历史,可区分出先发展国家(地区)与后发展国家(地区)。大体而言,先发展国家对应于发展中国家,后发展国家对应于发达国家。
除自然本底和利用时间外,资源从而环境寿命的转移是影响文明兴衰的又一重要原因。历史上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对发展中国家资源的掠夺和当代发达国家利用政治、经济手段和不平等的国际贸易秩序对发展中国家资源的转移——不仅利用,而且储存起来所导致的,即是对近代文明和发达国家发展的促进,环境寿命的增加,和古代文明国家衰退的加速,环境寿命的减少。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这是环境寿命的一种非发展性减少,也是一种非自然性减少。一些发展中国家利用土地(资源)换“香烟”(非生产性奢移品等)的行为,则是对上述情况的推波助澜。输出“公害”也是一种环境寿命转移——输入国环境寿命的减少和输出国环境寿命的非道德性延长。
环境衰老派生的另一些问题,如土地肥力下降,农业衰退,以及由之而来的贫困和低生活质量等,也是构成文明衰退的重要因素。
人类与自然、环境寿命与文明兴衰的关系表明,未来将瞩目于那些环境年轻、人口少和资源丰富,而且重视生态保护的国家和地区。
生存对策
人们常常以为,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生产力的发展,改造自然能力的增强,人类在逐渐摆脱自然的束缚。然而,事实是随着社会的进步,人类更加依赖于自然而不是逐渐摆脱自然的束缚。对此,可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观察。
首先,人类虽然由于制造工具和从事生产而使自己不再象其他生命那样固定于某一个或某几个食物链,局限于一定的“生态位”,虽然打破了食物链的束缚,撕碎了“生命之网”(食物网),但由于要吃饭,最终还是无法摆脱环境—绿色植物系统的制约。而且由于自身数量的增加,这种依赖反而更增强了——食物系统产量稍有波动,便会导致饥荒,带来几百万人的死亡;而且,人口数量的增加和广泛分布也导致了对自然灾害易感性的增强。
其次,对非再生资源的利用使人类在依赖再生资源系统时,又离不开这些终将枯竭的资源,形成对自然的双重依赖,对自然的依赖由此被进一步强化。
第三,人口数量增加和可供拓展生存空间的减少,进一步限制了人类的活动余地即选择机会(对“边缘土地”的利用即表明了选择机会的受限性)。而选择机会的减少,则意味着对自然依赖性的增强。
此外,对生态退化、环境污染、资源短缺、石油危机、水资源危机,以及“人类困境”等诸多问题的关注,则从另一个侧面表明了人类对所处环境依赖的加深。如果人类真的随着生产力的进步而可以逐步摆脱自然的束缚,那各种忧虑岂不都是“杞人忧天”?
“民以食为天”。人可以摒弃一切,但绝不可以不吃饭。“人类困境”的核心,即是提供食物的生态系统的退化。人类在关心发展的各类问题时,必须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这一根本问题上。所谓生存之路、生存对策,归根结底是保护地球环境—绿色植物系统。
地球生态系统是一个通过食物链、食物网对一切生物的制约所形成的负反馈维持稳态的控制论系统。人类由于反自然的本质使自己变成生态系统内导致系统不稳定的正反馈因素。人口数量和欲望增长所强化的人类目的与自然演化方向的矛盾和为此所必须的对环境愈加扩大规模的索取,则使这一正反馈变得十分强大,构成对地球生态系统最根本的威胁。于是,人与自然和其他生命的关系,便由人类初期的异化和矛盾,演变至当代的不相容和尖锐对立。保护地球生态系统,既是人类生存的必须,也是缓和人与自然、人与其他生命矛盾的必须。这两个必须,在各方面又是同一的。而正是由于存在这种同一,才可能有问题的缓解。
保护地球生态系统,缓和人与自然、人与其他生命的矛盾,延长环境利用寿命之根本在于节育——控制乃至减少人口数量;节欲——节制追求享受的欲望和贪婪;节约——珍惜和爱护万物,用生态科学知识指导利用自然的活动。L·考尔德勋爵尖锐地指出,“过去的人类文明社会都因贪婪、疏忽以及衰退这些其本身的过失而自食其果,走向死亡。随后,新的便又步其后尘”。[13]许多研究者也均认为,“无计划的繁殖人口,无限度地增加生产和消费……是人类对自然环境产生不良影响的根本原因”。[14]对此,人类应引以为戒,把节育、节欲、节约作为自己的共识。只有如此,才能减少对环境的索取,从而才会有人与自然和其他生命矛盾的缓和,才会有环境寿命的延长和文明(农业文明)的持续。
“公地的悲剧”是缓和人与自然矛盾重大且易被忽视的问题。G·哈丁在其名著《公地的悲剧》中做了这样的描述:在一个公共牧场中,增加一头牧畜的负效益由全体放牧者承担,每个放牧者只分摊到若干分之一,而正效益则全部属于某一个放牧者。对每个放牧者来说,不言而喻的决策是,在自己的畜群中“再增加”一头牧畜。[15]在资源、环境利用中,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问题。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个人,都像公共牧场中的放牧者那样行事。在人口、经济“零增长”的辩论中,“谁先停下来”即属此类问题。谁也不愿意先停下来,结果仍是为取得资源原的竞争和环境过度利用的继续。“公地悲剧”导致的是全球生态系统的持续破坏。对此,G·哈丁写道:“毁灭,这是所有人的终点,每个人都在一个信奉公地自由享用的社会中追逐自身的最大效益,公地的自由享用会给所有人带来毁灭”。[16]这一点,是值得每一个人深省的。罗马俱乐部的创始人O·佩西倡导“人类革命”,其良苦用心即在于克服人类自身的弱点,克服“生存之路”上的障碍。
生存的对策有许多,但关键是行动——从每一个人做起,“从我做起”。
注释:
[1][法]R·达若:《生态学概论》(张绅等译校),第176—177页,甘肃人民出版社,1981,兰州。
[2]《生态学概论》,第178—179页。
[3][英]马尔萨斯:《人口论》(郭大力译),第5页,商务印书馆,1959,北京。
[4]原华荣:《人类与生态退化》,《中国人口与环境(二)》,第73—77页,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5,北京。
[5]金性春:《漂移的大陆》,第260页,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0,上海。
[6]朱祖希:《春天风沙的受益者》,《北京晚报》,1992年4月2日。
[7]曹立:《百万地雷作看守,科国沙漠泛生机》,《科技日报》,1993年1月27日。
[8]中华人民共和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等:《人与生物圈展览》,第24页,1985,兰州。
[9]世界银行:《1991年世界发展报告》,第61页专栏3.4,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1,北京;世界银行:《1992年世界发展报告》,第27页专栏1.1,第31页专栏1.2,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2,北京。
[10]世界资源研究所、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世界资源报告(1990—1991)》(叶汝求、夏坤堡等译校),第559—566页表21—1,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1,北京。
[11]《世界资源报告(1990—1991)》,第583—587页表21—4。
[12]《1992年世界发展报告》,第226—227页表5。
[13][苏]E·费道洛夫:《人与自然——生态危机和社会进步》(王炎痒等译),第62页,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86,北京。
[14]《人与自然——生态危机和社会进步》,第63页。
[15][美]G·O·巴尼:《公元2000年环境》(尚忆初、刘静华等译校),第6—7页,科学出版社,1986,北京。
[16]《公元2000年环境》第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