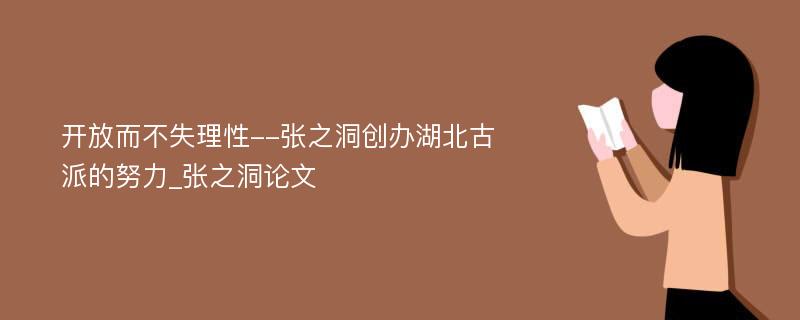
开放而不失其故:张之洞兴办湖北存古学堂的努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湖北论文,不失论文,学堂论文,努力论文,张之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4)06-0145-16 光绪三十年(1904)①,湖广总督张之洞倡设存古学堂,是清季官办保存国粹学堂的发端和各省仿办的范例。至宣统元年(1909)初,学部奏准将存古学堂纳入翌年各省“筹备立宪”的办学规划。[1]该校成为清季官方在“新教育”体系中尝试保存国粹的主要形式,有全国性的办学规模和长远影响。②过去对此研究非常不足。③以存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湖北存古学堂为例,通常是在研究张之洞的论著中涉及其创办该校的活动,但重建和梳理相关史实的基础性工作仍有相当大的提升空间。如美国学者William Ayers的考察是早期研究中较中立而详细的,但只叙述到光绪三十四年初该校开办第一学期为止。[2]另一位美国学者Martin Bemal进而表示,除了张之洞在光绪三十四年初曾致电继任湖广总督赵尔巽,希望将湖北存古学堂接续办理下去以外,“再找不出学堂在1908年以后仍然存在的证据”。[3]实际上,该校的办学进程一直延续至辛亥鼎革(详后)。 近些年来,存古学堂开始得到一些不论正面负面的关注。部分学人已将其视作近代知识与制度转型进程中不容忽视的一环。桑兵教授将该校置于晚清“科举与西学之争以及中西学校(堂)之争”的脉络中,“重新检讨清季教育变革的因缘得失”。[4]左玉河研究员考察经学在“中国现代学科体系”形成过程中的命运时,关注清季官方在存古等学堂中维护经学地位的努力。[5]笔者曾考察清季中央政府对保存国粹学堂的态度演变、当时朝野各方在兴办存古学堂问题上的分歧与论争等面相。[6]但整体看,专门的研究仍相当不足。不少人将其视为“新教育”的对立面而一笔带过,多数提到存古学堂者仍延续了因张之洞而约略述及该校的作法。相关史实缺乏梳理和重建的情形没有得到显著改观,尤其是直接以湖北存古学堂为题的研究,笔者迄今未见。 其实湖北存古学堂存留的资料相对充盈,对此个案的研究可以增进我们对清季官方保存国粹努力和清季鄂省“新教育”的整体认识。本文以相关档案和当时报刊、文集等为基本依据,初步考察张之洞创设湖北存古学堂的努力,侧重张氏竭力彰显该校“管理”之“新”,同时又试图暗承传统的办学取向,兼及该校的独特地位、学脉传承及其办学运作与张氏原拟办学预案异趣的面相,希望能成为研究全国范围内存古学堂的一块铺路石,并为我们进一步认识清季湖北“新教育”提供一个具体而微的例子。 一、张之洞晚年“最关心”的文教事业 清季湖北的“保存古学”努力发端甚早,存古学堂的筹建历时较长。大约在光绪三十年四月初,湖北有将经心书院改建为方言学堂之议,当时人在江宁的湖广总督张之洞“反复思之”,认为经心书院“不可废”,故于当月七日致电湖北巡抚端方及署理武昌知府梁鼎芬(节庵),提出留经心书院“为保存中国古学之地”,方言学堂“仍照原议,就农务学旧堂改用为善”。[7]两天后,端方回电说,方言学堂“即遵就农务学堂旧堂改用。节庵意亦如此。保存古学,至急之务,方与节庵均所兢兢也”。[8]最后一句的刻意“表态”,或正提示着他和梁鼎芬作为当时湖北负责兴学的主要官员,此前对“存古”皆不怎么积极。④张之洞倡办存古学堂之初,在鄂省多少有些“孤怀闳识”的意味。 张之洞为筹办湖北存古学堂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他“殚心竭虑,筹计经年,并督同[湖北]提学司及各司道并各学堂良师通儒往复商榷数十次”,拟定出该校的一整套分科教学模式以及具体的课程设置和钟点配备方案。[9]不仅如此,他还亲自过问招生、聘请师资等具体筹办事宜。为“鼓舞多方、网罗殆遍”,他示谕:存古学生凡“入堂以后,如果于所认习之学科曾经用功、具有门径者,准其于定章七年毕业之期减一二年以示优异”。原拟招收生员入学的规定也被放宽,具体作法是:“悬一特别之格,招考举贡考职、生员考优之正取、备取并各师范学堂毕业生,列为优待一项”。⑤这些灵活变通的举措显然有助于该校在较广的范围内网罗到具有天资且诚挚“存古”的高才士子。“备取”考生总计达142人,超过正取名额22人。首届学员中甚至有已经派充师范学堂、高等小学堂教员者,说明该校确有相当的吸引力。[10] 最棘手的筹备工作是聘请教职员。许同莘在《张文襄公年谱》中说,张之洞办湖北存古学堂,“先后延孙仲容[诒让]主政为监督、曹叔彦[元弼]中翰为总教习,皆不就。会赵侍御[启霖]罢职归,敬其风骨,延之主讲,已允矣而不果来。最后奏留杨惺吾[守敬]大令为总教习,称为鄂省旧学宿儒之首选。”[11]这里所言较简略,部分地方也与事实有出入。 在张之洞的主导下,湖北方面将“延访名师”作为最重要的筹办工作,提出了规格相当高且规模较恢宏的聘请师资计划:总教四人、协教四到六人、分教六到十人。[12]张之洞或托嘱亲信代请,或亲自出面,先后敦请孙诒让、钱桂笙、赵启霖、杨守敬、缪荃孙、叶德辉、曹元弼、王先谦等人出任湖北存古学堂监督或教职。张氏对所欲聘请的“通儒宿学”相当优容宽待,提出了较周到而宽松的牵就方案。如在礼聘门人孙诒让时,因礼部奏派其充任“礼学馆总纂”,张之洞主动提出孙氏可以“半年留京,半年住鄂”,甚至可将在京师未完成的工作“携至鄂办理,或即以三个月住鄂,固亦甚好”。湖北存古学堂“尚有协教、分教各员,分任教课。劳剧之事,不以相烦。但望到堂时开导门径,宣示大义,为益已多”。[13]而在敦请叶德辉出任“协总教”未果后,张之洞考虑叶氏或“不愿为皋比所困”而“久居鄂堂”,故请他担任“名誉教师”,“暂来一行”即可。[14]对于另一位湘籍名儒王先谦,张氏同样考虑其“未必乐于远游”,故拟聘为“名誉总教”,只需“每年春秋佳日,随意来鄂一次与诸生讲论数日”。[15] 不过,即便是张之洞等人如此努力,效果仍不理想。上述诸人中,仅杨守敬、曹元弼受聘。[16]孙诒让认为存古学堂可以缓办而辞任监督一职。钱桂笙、叶德辉、王先谦皆以病辞。[17]赵启霖“已允矣而不果来”,是因张之洞卸任湖广总督进京,加之湖南方面对于办学员绅的争夺。⑥缪荃孙出任“名誉教长”,只在学校“开学时到堂一次,未领薪水”。⑦至光绪三十三年(1907)七月学校正式开办时,仅有总教三人、协教五人、分教二人、体操教员一人到任。由于“一时暂难选得其人”,监督和提调分别由张之洞和湖北提学使黄绍箕兼任。 该校正式开办后,张之洞随即离鄂进京。尽管远隔千里,湖北存古学堂仍是张之洞“最关心”的文教事业。尤其是学校开办后的一项重要工作——延聘专职监督,张氏不仅亲力亲为,而且在他的意愿主导下,包括陈夔龙、端方、高凌霨、樊增祥等在内的官方大员皆参与其事,他们看好的最佳人选是梁鼎芬。光绪三十四年正月二十九日,张之洞致电继任湖广总督赵尔巽,表示“存古学堂系奏明办理,关系紧要,区区最所关心,万不可令其废坠,必需主持得人”,希望留刚刚辞去湖北按察使一职的梁鼎芬出任该校监督。[18]赵尔巽翌日回复说,先已敦请梁氏“监督存古,渠力辞”。[19] 同年二月陈夔龙接任湖广总督后,也有意请梁鼎芬出任存古学堂监督。张之洞并有函电促成此事。但梁氏仍坚辞不就,并推荐纪钜维出任该职。[20]张之洞虽认可纪钜维是梁鼎芬以外的适宜人选,但并未听任梁氏坚辞存古学堂监督。[21]九月六日,时梁氏已至江宁,拟启程回粤,张之洞电请两江总督端方“切实挽留”梁氏,力劝其允就湖北存古学堂监督。张氏还嘱新任江宁布政使的门人樊增祥和端方“面商”此事,并与梁氏“详谈”。[22]陈夔龙则致电端方转致梁鼎芬,再次敦请其就任该校监督。⑧端方、樊增祥也分别致电梁鼎芬“劝驾”。端方还请樊氏电恳张之洞再次电促梁鼎芬“勉就存古”监督一职。[23]不过,众人的合力没有劝动梁鼎芬。[24]当月二十七日,张之洞因梁鼎芬“决意不回鄂”,致电陈夔龙、高凌霨、纪钜维,希望纪氏尽快出任湖北存古学堂监督。[25]翌月,纪氏正式到任。[26] 按梁鼎芬是张之洞兴办湖北“新教育”最为倚重的亲信之一,⑨在清季湖北学界威望昭著且根基深厚。⑩无论从资历威望、人事关系,还是办学观念和经验来看,梁鼎芬确为湖北存古学堂监督一职的最佳人选。就人生志趣言,梁氏不接受张之洞“辞官而为师”的劝言,显然是不愿在仕途受阻后再选择“为人师”的身份和办教育的人生道路。(11)另一方面,多位官方大员如此同心协力为一所学堂延请监督,这在清季“新教育”中即便不是特例,也相当鲜见,从一个侧面提示着该校确非一般学堂可比。 二、非同寻常的办学规格、投入和条件 光绪三十年颁行的《奏定学堂章程》没有专门“存古”的学堂建制,故张之洞在《创立存古学堂折》(以下简称《存古奏折》)中将该校称为“创举”。(12)实际上该校虽为高等专门性质,但确有不少与《奏定学堂章程》的规定明显异趣之处:学制七年而以高等小学堂毕业生为招生定位,涵盖中、高两等学程,较《奏定学堂章程》规划的五年中等、三年高等模式反而少一年。而该校的课程设置又极倾重中学内容,“普通学”课程远不能达到《奏定学堂章程》对中、高等专门学堂的统一规定(详后)。故《存古奏折》提出,存古学生“若兼习洋文,毕业后可照高等学堂例奏请奖励,并准送入大学堂文学专科肄业,将来递升入通儒院。其不习洋文者听,惟奖励须量减一等,毕业后止能送入大学堂文学选科肄习,以示区别”。在时人相当看重的“奖励出身”方面,存古学堂由于学制年限和研习内容的特殊性,尚不能完全等同于《奏定学堂章程》规定的高等性质学堂。 尽管如此,由于张之洞的格外重视,湖北存古学堂自兴办之初即有非同寻常的办学规格和经费投入。该校创始之初,张之洞以湖广总督身份兼任监督,湖北提学使黄绍箕兼任提调。这固然是“一时暂难选得其人”的权宜之计,也从一个侧面彰显出该校远非鄂省其他学堂可比拟的地位和规格,后更为江苏、陕西、安徽等省兴办存古学堂时所效仿(详另文)。经费方面,广东学务公所“普通课副长”陈佩实光绪三十四年初实地考察湖北存古学堂时了解到,虽然学生人数只是张之洞原拟定额的一半,“所支开办经费以建筑精良、规模阔大,已达十余万金”。[27] 档案显示,湖北存古学堂的操场“占地面二百方丈”。堂舍“占地面二千三百一十六方丈”,包括讲堂五间,自习室、寝室共楼房三座计七十二间,礼堂两重,职员、教员、司事、仆役室共六十三间,另配备有石经楼、储藏室、浴室、理发室、轿厅、会客所、接待室、器械室、厨房、厕屋等共二十余间。至宣统元年和宣统二年(1910),空闲的讲堂、自习室、寝室被暂时改为阅报室和调养室。宣统二年上学期校方甚至出租空屋,说明校舍完全能满足教学运作的需要,且有富余。(13) 该校的经费支出远非同时期鄂省其他“阖省公共”性质的专门学堂可比。湖北方言学堂光绪三十三年经费支出按学生人数平均为200.1银元。而湖北存古学堂当年七月下旬才正式开办,且十月以前并未进入常规的教学运转,其岁出按学生人数平均已达162.23银元。[28]光绪三十四年、宣统元年的该项统计数字为328.025、385.653银元,均为当年鄂省所有专门学堂中最高者,大约比同期湖北所有“阖省公共”专门学堂支出按学生人数的“总平均数”多一倍。[29]实际上,湖北方面在该校“月支尚无定额”时,即在编制的学堂统计表中,将其排在包括两湖总师范学堂在内的各校之前,列所有学堂之首。[30]由目前掌握的资料看,这样的列表次序在此后清季鄂省官方的学堂统计文件中,似乎是一种常态。 该校优越的办学条件尤其体现在典籍配置方面。《存古奏折》在光绪三十年的《札设存古学堂文》(以下简称《饬设札文》)基础上添有“书库多储中国旧学图书、金石、名人翰墨、前代礼器”一语,说明张之洞在筹建过程中对此较为重视。[31]该校正式开办当月,《大公报》《申报》皆有报道说,湖北存古学堂“建造书库已成,备极宏阔”。张之洞“特拨款十五万金”,札委专员赴各地“采买古籍,存诸其间,以供诸生浏览”。[32]档案显示,光绪三十四年上学期和宣统元年上学期学校的“图书标本器具”支出分别为1065、645银元。[33]存古学堂“注重研精中学”,用于图书方面的费用恐怕在上述款项中占有相当比重。实际上宣统元年底学部调查员即以该校“书籍原系旧藏”,“堂内古书颇多,足资参考”,质疑校方当年所列六百多银元的“书籍购置”费。(14)至翌年上学期,该校的“书籍及排印课程”支出剧增至1362两,折合近2000银元。[34]此外,也有热心官员捐助购书经费,如光绪三十四年上半年度支部“土税统捐督办大臣”柯逊菴(逢时)即捐“购书费银一万两”。[35] 学生在书籍配置方面的待遇也相当优厚。据该校“监学”兼教员萧延平所述,堂中“诸生,认习专经者,如正、续《皇清经解》之类,每五人合给一部;治史则《御批通鉴》之类每人各给一部”。(15)另据该校学生罗灿回忆,首班学生“由公家发给《十三经注疏》、前四史、《二十二子》《汉魏六朝一百三家集》各一部及其他小部书籍”。[36]这样的待遇在目前所知清季各存古学堂中尚无他例。陈佩实即认为,湖北存古学堂实际上是将“他校所目为参考之书,未必尽能全备者”,“胥发为教科之本,无不人手一编”。他建议当时正在筹办中的广东存古学堂不必如此办理。此外,湖北存古学堂还印行部分中学典籍和教员的讲义。已有学者注意到该校刊印典籍的版本价值。(16)目前暂不清楚湖北存古学堂具体的藏书和印书数量。但其规模确实远远超出了清季中央政府的规定。宣统三年(1911)夏,存古校方参照同年三月学部颁行的《修订存古学堂章程》(以下简称《修订新章》)拟订了“详细规则”。湖北方面将其移送学部备案时,特别声明该细则第四条所列“管书员”本为修订新章所无,实因“该堂另有藏书楼”,故“不得不量为添设,以资管理”。实际上该细则还列有专门的“藏书楼规则”,也是修订新章没有的条目。(17) 另一方面,就在湖北存古学堂办学经费仍在增长的宣统二年,[37]鄂省财政已“入不敷出、为数甚巨”,学务又是官方力行节约的“一大端”。存古学堂因地位特殊,在诸多官办学堂中首当其冲。当年署理湖北提学使马吉樟所拟省城各学堂节费清单的首条即是存古学堂月节银210两。[38]至翌年上半年,鄂省办学经费更加紧张。[39]官方决定变通存古学堂办法:“缩短年限,所有一切均归学生自备”,[40]贫困学生因此“纷纷退学”。[41]而该校停办的消息也见诸报端。台湾学者苏云峰研究员注意到宣统三年四月七日《时报》的报道,认为湖北咨议局“以存古学堂开办数年,‘毫无成效,徒耗巨款’,议决将之停办”。[]实际上,时任湖广总督瑞澂、湖北提学使王寿彭等人与湖北咨议局最终达成共识,后者议决通过的存古学堂宣统三年经费预算确实较去年削减不少,但学校毕竟得以庚续办理下去。[43]整体看,鄂省官方在宣统二年、宣统三年对存古学堂拨款的屡屡削减并未决定性地影响到该校的日常运转。 三、自经心、两湖书院以降的学脉传承 张之洞以“经心书院不可废”而在其故址上办存古学堂,作为“保存古学之地”,是将其视作传统学术在湖北薪火相传的事业。实际上,该校的师资、典籍、教学乃至办学功能皆有自经心、两湖书院以降的学脉传承轨迹。 在师资方面,虽然名师难筹,但张之洞择聘教职员的眼光较高,实不愿“降格以求”。湖北存古学堂中确不乏当时相当有声望的名流士绅和“耆德宿儒”。纪钜维、张仲炘先后出任监督。蒯光典、缪荃孙任“名誉总教”。两任教务长分别为王仁俊、姚晋圻(兼任史学总教)。经学总教为曹元弼、马贞榆;史学总教为杨守敬。此外,学校还先后聘有经学协教王代功(王闿运子)、钱桂笙(仅校阅课卷)、黄燮森、连捷;经学分教李文藻、傅廷仪;史学分教傅守谦、左树瑛;史学教员周从煊、雷豫钊;词章教员陈德熏、龚镇湘、顾印愚、李元音(兼经学教员);词章协教吕承源、黄福(兼经学协教);词章分教金永森;舆地教员熊会贞、戴庆芳(兼外史教员);庶务长陈树屏;斋务长兼史学并外国史教员杜宗预、王邵恂、李哲暹;监学萧延平、闵豸。(18) 教职员多与张之洞关系密切,且两湖、经心书院师生占相当比例。其中如曹元弼、马贞榆、王仁俊、杨守敬、蒯光典、姚晋圻等人早年在两湖书院共事时即“相与论学”。[44]这样的氛围对原两湖书院教员确有吸引力。湖北存古学堂开办伊始,时任安徽提学使的原两湖书院教员沈曾植即在致缪荃孙的信函中流露出向往之意。[45]同样的学脉传承也体现在典籍配置方面。湖北官方将原“两湖书院内南北二书库分拨其一”给存古学堂。[46]据该校学生罗灿晚年回忆,学校“聚集了两湖书院、经心书院以及所有湖北官书”。[47]师资与典籍方面的薪火相传为教学授受上的沿承提供了可能。曹元弼在两湖书院与监督梁鼎芬同辑的《经学文钞》,后经曹氏审定后由湖北存古学堂印行以作教学之用。[48] 实际上,作为湖北存古学堂主要的经学教程制订者和经学讲义编撰者,曹元弼不仅传授其早年“告两湖书院之士”的“治学之方”,而且相当强调张之洞在《劝学篇》中所言的“守约之法”,可从一个侧面看到该校教学授受在承继两湖书院的同时也有发展的一面,部分体现出清季“新教育”的时代风貌,相当值得注意。按张之洞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刊行的《劝学篇》中提出,按照“损之又损”的“守约之法”编纂中学各门教科书,以便所有学堂学生“通晓中学大略”。就经学而言,拟依“明例、要指、图表、会通、解纷、缺疑、流别”七原则,“节录纂集”成“浅而不谬,简而不陋”的“十三经学”教科书。[49] 受张之洞委托编纂经学教科书的正是曹元弼。曹氏为此辞去两湖书院讲席,归里专意著书。至光绪三十三年七月,曹氏赴鄂出任存古学堂经学总教,向张之洞面呈“十三经学”中的《周易学》《礼经学》《孝经学》,得张氏嘉许。[50]曹氏并将其光绪三十年在苏州刊行的《原道》《述学》《守约》三文“稍润色”后,传授给湖北存古学堂学生。(19)其中《述学》所举“各经传述源流、定治经者不易之途径”,正是其早年“告两湖书院之士”者。[51]而《守约》则意在宣扬《劝学篇》的“守约之法”: 存古即守约也,新政新艺约之以古学;古学子史百家约之以经学;经学汉宋以来聚讼纷纭,约之以所定各书;各书卷帙已多,约之以人习一大经,一中小经,余祗诵经文、识大略;治经之法约之以《劝学篇》所举七事。 曹氏并指出,“守约七原则”可“櫽括”《奏定学堂章程》列出的所有“经学研究法”,他会“随时为[存古学堂]诸君子指说之”。[52] 唯存古学堂旨在“专力中学,务造精深”。张之洞所拟经、史、词章各科教法皆是先博览再专精的学程。以经科为例,第一年“先看《御纂八经》一遍,传、说、义、疏均须依篇点阅”。第二年看“有关群经总义诸书”。前两年“遍览九经全文,讲明群经要义大略”,意在“使学者统观群经大指,胸有全局,以为将来贯通群经之根基,且使学者自揣性之所近,以定择习一经之趣向”。(20)这样的“通大义”学程,从学时、内容到目标皆与《劝学篇》所言经学教科书异趣。 问题的潜在核心可能是“不讲西学则势不行,兼讲中西则力不给”这一困绕清季“新教育”的难题。《劝学篇》将“存古”分为“举要切用,有限有程”的“学堂教人之学”和“求博求精,无有底止”的“专门著述之学”。所有读书人自幼“诵《孝经》《四书五经》正文,随文解义,并读史略、天文、地理、歌括、图式诸书及汉、唐、宋人明白晓畅文字有益于今日行文者”,从15到20岁以“守约之法”通晓中学大略,其间尚可兼习西文。此后绝大多数人“专力讲求时政,广究西法”,极少数“好古研精、不鹜功名之士”则任其博观深造“专门著述之学”。[5] 与《劝学篇》“先中后西”的模式不同,《奏定学堂章程》力图“中西学并行不悖”,实较《劝学篇》的“守约”方案远更挤压缩简中学。读书人自7岁入学,要到中学堂毕业时才基本读完五经,时已21岁。[54]关键是高等学堂的中学课时配置较中小学堂更少且学制三年,(21)而《劝学篇》的“守约”学程虽已“简之又简”,仍以五年为期且以中学为主。也即是说,按照《奏定学堂章程》,新式读书人要到大学堂阶段(至少26岁)才可能完成《劝学篇》的“守约”学程从而“通晓中学大略”。 张之洞已注意到新式学堂“经史汉文功课晷刻有限,所讲太略”,[55]距《劝学篇》所言通晓“中学大略”的目标相去甚远,故其所拟存古学堂课表章程完全抛开《劝学篇》的“守约”学程,而在“新教育”体系中另行特制一条“求博求精”之路。(22)大幅增加中学课时也是势所必然。《存古奏折》强调,《奏定学堂章程》“务在开发国民普通知识,故国文及中国旧学钟点不能过多”;而存古学堂“重在保存国粹,且养成传习中学之师,于普通各门止须习其要端,知其梗概,故普通实业各事钟点亦不必过多,以免多占晷刻。”[56]如此刻意诠释存古与其他新式学堂的区别,正是为了在课程配置上最大限度地向中学倾斜。实际上,张之洞为该校拟订的中学课时数已占课时总数的近90%(详后),大体可说是在专精或者说“提高”层面力图应对《劝学篇》所言“不讲西学则势不行,兼讲中西则力不给”的两难困局。 进而言之,这可能涉及到清季民初士人在试图传承中国传统学术时持续思考的问题:“普及”与“提高”孰轻孰重及其相互的关系。张之洞指出存古学堂与《奏定学堂章程》“互相补益,各有深意,不可偏废,不相菲薄”,当然是理想的“存古”模式。在实践层面,“普及”因与“救亡大局”和“世道人心”关系更为密切而得张氏较多关注,故《劝学篇》以专章详述“义主救世”的中学守约之法。后来张氏在“普及”努力出现诸多问题的情形下办存古学堂,也在《存古奏折》中有意彰显其基于“国家”和“世道”希图“裨益世教”的“苦心”,更强调该校在办学功能上可承继经心、两湖书院,为“新教育”养成中学师资,显然极看重旨在“提高”的存古学堂对“普及”层面的推动和影响。 不过,无论是在《劝学篇》的存古设想中,还是在《奏定学堂章程》和存古学堂的办学规划中,“普及”与“提高”毕竟是两个界域分明的层面。曹元弼在用于湖北存古学堂的教案中直接以“守约”诠释“存古”,为该校学生“随时指说”张之洞所拟存古学堂经科教法中只字未提的“守约七原则”,后来更在江苏存古学堂任经学总教时将“十三经学”中的《孝经学》列为点阅书目。[57]这些作法不仅与张之洞的办学设想明显不合,且在一定程度上已突破了存古学堂研习“专门著述之学”的性质,多少有些混淆“普及”与“提高”二者界域的意味。(23) 实际上,曹元弼心仪的“专门著述之学”是较张之洞所拟存古学堂经学授受方案更长的学程。他所以在该校力倡“治经简易之法”,或与其深受《劝学篇》影响,将张氏交予的编书事宜视作“名教纲常之责”,急于在“新教育”中挽回“学术人心之弊”有关。(24)他在《守约》一文开篇指出,“经学渊深,非博稽载籍,旁推交通,无以究极古义,精发圣言”。(25)以《周易》为例,其治学基本路径“当由李[鼎祚]、惠[栋]、张[惠言]、姚[配中]以达郑[玄]、荀[爽]、虞[翻]”。[58]此外,另有14部“最切要之书”,“遍读尽通,已非十余年不为功”。但“今日之学,如理军市,如救水火,如医急证,如求亡子。风雨漂摇,危急存亡之秋,岂能从容待此”?故《劝学篇》“守约之说”实为善策。在他看来,“湖北学堂为各省所取法,而存古学堂尤为各学之标准。”存古学生“他日学成,各本经义,施政立教”,“枝蕃流衍”后,“士农工商兵,凡习声光化电各学者,皆有与国为体,忠爱利济之心”。相对于“究极经义之学”,曹氏明显更强调“略举大要之学”,较看重存古学堂在整个“新教育”体系中的示范效应,以及存古毕业生对新式读书人群体的教化作用。(26) 四、力图不失其故的新式学堂办法 力图用学堂这一新形式保存国粹,是张之洞自倡办存古学堂之初即一以贯之的办学取向,他在《饬设札文》和《存古奏折》中皆明确提出,该校“规矩整肃,衣冠画一,讲授皆在讲堂,问答写于粉牌,每日兼习兵操,出入有节,起居有时,课程钟点有定,会食应客有章,与现办文武各学堂无异”。(27)奏折更在札文基础上加有一语,强调该校与“旧日书院积习绝不相同”,并特意声明湖南拟设景贤等学堂、河南拟设尊经学堂“似与向来书院考课相仿,与鄂省存古学堂之办法判然不同”。 《存古奏折》如此刻意彰显存古与其他新式学堂“无异”而与“旧日书院积习绝不相同”,或与清季日益激进趋新的世风有关。该折并提出,该校课程应“略兼科学以开其普通知识,俾不致流为迂拘偏执,为谈新学者所诟病”。就在进呈该折大约三个月后,刚刚奉旨主管学部的张之洞曾私下问询罗振玉对存古学堂的看法。后者表示,“国学浩博”,湖北存古学堂“年限至短,复添科学,恐成效难期”。张之洞“首肯曰:‘此论极是。但不加科学,恐遭部驳。至年限太短,成效必微,但究胜于并此无之耳’”。(28)可知“谈新学者”的“诟病”、学部的批驳皆是张之洞办存古学堂时切实考量并试图避免的因素。 就在上述会谈中,罗振玉还提出,“修学一事,宜多读书;而考古则宜多见古器物”,故各省可设一所“国学馆”,内分“图书馆、博物馆、研究所”三部分,“研究所”选“国学有根抵者,无论已仕未仕及举贡生监,任其入所研究,不限以经、史、文学、考古门目,不拘年限,选海内耆宿为之长,以指导之,略如以前书院”。张之洞对此赞许有加,甚至允诺“当谋奏行”,从一个侧面提示着张氏“存古”的本意或许并不完全排斥“略如以前书院”的办学取向,至少是可以接受一个没有科学课程的存古学堂。显然,张之洞言说中的“书院”各有其特定所指,他欣赏的“书院办法”与其在《存古奏折》中针对的“书院积习”、“书院考课”意指完全不同的面相。 进而言之,张之洞固然竭力厘清存古学堂与书院“积习”和“考课”间的界域,并力主发挥“新教育”在“管理”方面的长处,祛除“书院积习”,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将该校视为与传统书院完全对立的全新办学形式。实际上,湖北存古学堂从拟办预案到具体作法皆未完全否定,更在一定程度上承继了中国传统学术授受方式(尤其是张氏本人此前兴办书院的举措和经验)。该校力图祛除“旧日书院积习”,加强对学生的管理,具体举措当然鉴取学堂办法,但其办学的大方向实与《尊经书院记》中所言一脉相承。(29)张之洞在《存古奏折》中声明河南尊经、湖南景贤等学堂与“书院考课相仿”,与存古学堂办法“判然不同”,当然与豫湘两省学堂被学部奏驳有关。(30)但他此前所办书院一直将科举应试摒除在教考范围之外,也是不容忽视的事实。(31) 就具体的办学举措而言,虽然书院与学堂的具体招考规程不同,但前文所述张之洞招考存古学生时灵活务实的作法与其《尊经书院记》的主张在精神上是相通的:即放宽招生范围但严把取录关口,从而最大限度网罗真材实学者。(32)张氏“以延访名师为第一义”的筹建存古学堂方针是其历来尊师重道传统的延伸,甚至其为存古学堂而与他省争夺师资的情形也是他此前办两湖书院常有之事。(33)在教学授受方面,张之洞为存古学生所拟专经学程以清代汉学为研习重心,是他此前极力推重清代解经著述作法的延续。(34)张氏要求存古学生毕业时须呈出所习“专门之学”的“心得、著述、札记”,说是清代研治“经史实学”的书院注重读书心得和研究札记传统的延续,似不为过。(35) 整体看,张之洞理想中的存古学堂是不失其故的新式学堂。可能是出于减少办学阻力和压力的缘故,其办学运作并未着力宣扬(甚或可以说是有意避而不言)该校“不失其故”的一面,而是在彰显该校“新教育”属性的同时,静默地将其认可的传统办学取向“见之于行事”。湖北存古学堂正式开办后,确有教员试图“不失其故”。曹元弼即提出该校经学课程“每日按时程功”,取《礼记·学记》“藏、修、息、游之义,勿蹈进锐退速、百事俱废之覆辙”。[59]而校方也不乏变通学堂办法以切合中学特点及研习方式的努力。如在宣统三年夏出台的“办学细则”中,所有学生的主课学时皆明显倾重“点读”、“点阅”而轻“讲授”,应是力图契合“重在自修”这一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学术研习取向。(36)中等科经学、词章两班开“点读”主课而史学班开“点阅”主课,显然是考虑到经学、词章两门在较基础的研习阶段需要更多诵读。 该细则还新设“管课员”一职,负责“稽查[学生]勤惰并掌旷课簿之登记”,并“秉承教务长、商同各主课教员指定该级学生诵读点阅书籍,限定每课页数、行数,当堂课诵,于每课起迄处盖章记之。不及程者,记入课程簿。学生点读错处管课员指教之。如有疑义,由学生笔问,当堂交管课员转请教务和各主课教员笔答”。这样的读书日程依稀可见尊经、广雅等书院的“定课”传统,(37)但管理方式明显不同。实际上“管课员”一职在目前所知清季“新教育”系统中尚未见有他例,大体可说是为存古学堂的教学授受量身定制,以“新教育”在管理方面的长处,改进明清书院较松散的簿记制度。(38)这正契合张之洞的办学初衷。校方确实有意承继张之洞“开放而不失其故”的办学取向,并将其体现在规章中。但该校的实际办学运作却与张之洞等人的办学理想有相当大的差距。 五、办学理想与实践的迥异 张之洞在湖北存古学堂正式开学后即离鄂进京,尽管他对该校乃至湖北学务仍有相当的影响力,但该校的实际运作自开办伊始即与张氏的办学理想大异其趣,尤其体现在课程教学和校务管理方面。 在课程教学方面,前文说过曹元弼的经学授受偏离张之洞原拟教学取向的情形。实际上学校的西学通习课配置更为严重地背离了张之洞的初衷。张之洞原拟为存古学生每学年开设一门西学通习课,依次为“外国历史、博物、理化、外国政治法律理财、外国警察监狱、农林渔牧各实业、工商各实业”,只是让学生“略知世间有此各种切用学问,即足以开其腐陋,化其虚矫,固不必一人兼擅其长,每一星期讲习一点钟即可”。[60]具体就外国历史课而言,张氏要求“先讲近百年来之大事,渐次及于近古、上古,使知时局变迁之所趋”。[61] 但档案显示湖北存古学堂首届学员的外史课是自上古、中古到近代的“通史”课,历时四个多学期,才被“博物”课替代。宣统二年上学期史学科学生的外史课甚至与经学、词章两门“辅助课”同为每周三个钟点。[62]校方似乎相当看重“外史”对研习中学(尤其是中国史学)的助益,而非仅仅是让学生“略知世间有此各种切用学问”而已。但问题是这样一来,若七年学制不变,外史课已将其他六门西学通习课的学程挤压到平均不足一学期的程度。增加这六门课的周课时数固然可以弥补学程压缩后学时的不足,但“多占晷刻”势必影响到中学课程的教学授受,正是张之洞力图避免的情形。(39) 不仅如此,该校自开办之初即没有落实张之洞殚精竭虑拟订的一整套教学计划。陈佩实光绪三十四年初观察到,虽然新学期已开学,但该校“教员、学生尚未毕集。到者先行上课。诸生能否按照原章,分经分史,从事丹黄,切实研究,实未可知。第视其教授方法,似乎仍与寻常学堂无异,学生之领受主要课程亦与其领受辅助及补习课程无异”。[63]时任湖广总督赵尔巽对此颇不满意,大约在同年二月,特饬湖北提学使兼该堂提调高凌霨与曹元弼“遵章分课教授”。[64] 高凌霨认为该校有“三大病”:“一、管理乏人。二、教习非专到堂即不能开讲。三、学生招时迫促,挑选未精。设不设法极力整顿,恐办无大效。然三病尤以乏管理人为最要关键”,故“以速得一驻堂监督为整顿入手第一方”。[65]唯张之洞等人竭力聘请梁鼎芬出任该校监督未果。梁氏推荐的纪钜维得张之洞认可后,高凌霨与纪氏面谈数次。纪氏“略以为难。意谓欲加整顿管教,各员必须更易数人。然撤一旧人,既招怨尤;思委新人,又无佳选。因而踌躇不决”。高氏“再三敦促,纪尚非决辞,然亦总未首肯”。(40) 光绪三十四年八月十六日,纪钜维交给高凌霨一份电稿,请其“用密本代禀”张之洞。高凌霨认为纪氏意在“求有便宜用人之权”,故而在代禀电稿时,电请张之洞“念该堂关系重要,得人不易,俯准径与一电,略加奖词,并许其得便宜更易数人,则纪必欣然,庶该堂渐有起色”。同日,纪钜维也致电张之洞说,湖北存古学堂“如更张,力微任重,同事乏人,召怨无济,非敢推诿,实难着手,希训示”。[66]纪氏并告诉高凌霨,他已将该校“应典各事先电商”张之洞,等张氏回复后再酌定是否应聘。[67]同年九月底张之洞致电时任湖广总督陈夔龙等人,希望纪氏允就存古监督一职。翌月,纪氏履任。显然,纪氏履任前应该是就该校的整顿事宜与张之洞达成了某种程度的共识,其整顿设想至少是得到张氏默许的。 按纪钜维对于出任存古学堂监督如此郑重而审慎,应是基于对鄂省学务弊端的整体观察,(41)可能也与该校的师资特点有关。前文说过,张之洞为该校礼聘师资倾注了大量心力,这固然使得该校在时局动荡中汇聚了相当数量的“耆德宿儒”,但几乎所有教职员皆不同程度地与张之洞本人有交谊。在张之洞虽远在京师仍对该校有极大影响力的情形下,错综复杂的人脉关联自然成为学校改弦更张的障碍和阻力。纪钜维向张之洞“求有便宜用人之权”,显然对此有较充分的估计和预见。实际上,纪氏本人即与张之洞过从甚密,(42)后更被舆论视作他陷入被控风波的因素之一。 大约在宣统元年秋,湖北拔贡刘尚桓等人“陈请[湖北]咨议局核示”纪钜维“办事种种不善情形”,又有存古学堂学生“缮具纪监督劣迹在督、学两署呈控”。署理湖北提学使齐耀珊“恐有挟嫌主使等弊,当即函请学务议长、议绅妥议见复。旋据复到,亦不以纪为然”。齐氏“又移请咨议局公议,以定[纪氏]去留”。咨议局常驻员开特别会时,议员阮次芙报告审查刘尚桓等陈请书的意见,认为纪钜维“办事认真,公论自在”。“陈请书肆口诬蔑,恐有挟嫌主使等弊。咨议局主张公道,自应请留”。阮氏“措词激烈”,而吴庆焘议长“则主张去纪,与各议员又不相合,致议场内小有冲突,此案遂未能决定”。(43)后吴氏更以阮次芙作为纪钜维门人,自行承担审查刘尚桓陈请书的工作,其审查报告书又“词多过当,气欠和平,惧涉党伐之私而开攻讦之渐”,他“实不能赞成”,故而“宣告辞职”。宣统元年十一月十日,咨议局常驻议员开会复议,左树瑛、胡柏年等非常驻议员“亦先后莅会,意欲设法取消‘报告书’,旋经阮君辩驳”,且常驻各议员“皆据所见闻以证‘陈请书’逐条之妄诞,卒决议将‘陈请书’全行废弃,‘报告书’则由局保存,预备上宪查询时得以详覆”。[68] 值得注意的是,咨议局开会时有议员因阮次芙“审查报告书”措词激烈,担心“开罪某某等绅,意欲再行修改,然后宣布”;而吴庆焘在辞去湖北咨议局议长时说,自己与纪钜维“及本省诸名宿大老均系知交,无左右袒”,故对纪氏被控一案,只能“付之不理,庶几不着色相”,从不同侧面提示着刘尚桓背后确有鄂省“名宿大老”的身影。湖北提学司对“挟嫌主使”之弊的忧虑或非空穴来风,此事可能还隐伏着张之洞的人脉因素。《申报》的报道即反复强调这一点,先是说纪钜维与张之洞“有乡年谊”,张氏去世后,湖北“绅学界群起排斥”纪氏;后更在“时评”栏公开质疑鄂省咨议局议员所以竭力维护纪钜维,是因为张之洞的影响犹在。[69] 学部右参议戴展诚在纪钜维离任后曾实地“查视”湖北存古学堂。他向学部报告说,该校自光绪三十四年冬“变通从前办法。于本堂特设监督。该监督到堂以后,欲照学堂章程办理,事未能行而受怨已多。宣统元年九月,当举行月考之期,已经牌示,学生乃以东省有变,不得复行考试为辞,竟至罢课。监督遂辞职。事闻于提学司,亦不能为理,其上堂与否听之而已”。戴氏“查视”时,斋务长及监学“全不到堂,堂内一切事宜尚无人管理”,虽“见各班学生在堂自习,然亦非其真相也”。[70]可知纪氏的“整顿”努力确不成功,大体如其事先预料的那样“召怨无济”。 至宣统二年下半年,湖北官方对存古学堂的办学状况仍不满意,又感到“整顿不易”,故咨请学部尽快修订该校章程,“鄂省可藉以整饬”,避免“仍蹈前辙”。(44)同年底,湖广总督瑞澂“访查”湖北省城各学堂,发现诸多问题,要求王寿彭“严行考核”。翌年初王氏回复说,“从不到堂、徒领干薪”的情形“近来尚无此弊。即如存古学堂教员曹元弼、顾印愚”,“亦因各以事牵,不能按时到堂,旷误颇多。曾经禀明饬令销差,未敢曲为迁就”。但“兼任教科钟点过多、时时旷堂”的情形最为严重,“贻误实深”。去年曾严加整顿,如“存古学堂斋务长王劭恂等兼任两湖师范学堂教科,均饬令一律销去兼差,不稍宽假”。(45)大约同时,有报道说,湖北学堂“校规之坏无逾存古。教员、学生均以旷课为常事。彼此皆不责难。兹届年假期满,各级学堂均于[正月]十日开学。惟存古学堂仅有家居武汉学生七八人来校。其余籍隶外州县诸生一概未到。而教员之在省者亦只二三人”。[71]无论是在官方的公文中,还是在舆论报道中,湖北存古学堂已俨然是鄂省“新教育”的负面典型。 而学部《修订新章》的颁行也未成为湖北方面“整饬”存古学堂的契机,反而在招生取录、课程设置和钟点配备等方面体现出与张之洞办学主张相当不同的倾向,为该校赓续办理首届学员的学业增加了相当的难度。新章以“古学精深”为由将学制延为八年(中等科五年、高等科三年),但“古学”课程反而成为了被缩简的对象。西学“通习课”的设置则不仅更加细密周详,且授课钟点也有大幅增加。(46)此举不仅没有缓解反而进一步加剧了张之洞、罗振玉等人担心的“国学浩博”,与存古学堂“年限至短,复添科学”的矛盾,正与张之洞竭力倾重中学的办学方针背道而驰。 《修订新章》其实是要求学生中西学都要有相当的基础。中等科除招考高等小学堂毕业生外,“暂准招收读完五经、文笔通适之高才生”。前者因未读完五经,故前两年须“补读《易》《书》《春秋左传》”;后者则以上述钟点“补习高等小学应授之格致、算学、地理、历史等科”。贡生、生员只要“中文优长”,经考试合格后可“插入中等科第三年级”,但入校后需完成几乎所有的西学通习课程。举人可直接考入高等科,但要求不仅“中文优长”,还要“兼习普通学”。[72]上述规定以科举出身的有无和高低严定入学资格,与前文所述张之洞看重学生的中学实际学力,学制和规章皆较灵活而有弹性的作法适成鲜明对照。(47) 正因有上述较根本的改变,《修订新章》的颁行意味着湖北存古学堂身份驳杂的首届学员已不可能照张氏的设想完成学业。尤其是其中67名非“贡廪增附出身者”,“多系毕业之师范生及方言、自强各堂之[修业]生”,学程未满五年,按照新章应仍作为中等科学生。但校方认为,他们入校后一直与贡廪增附生同级授课,均已“分治专经、专史、名家专集”,其“程度已早毕部章所定之中等科课程”。且张之洞当年曾谕示:存古学生若专业学术优异,可减一二年毕业。故校方宣统三年四月呈请由湖北提学使司对首届学员“分门严试。其及格者升入高等科,不及格者仍归中等科肄业”。(48) 但学部对缩短学程一事相当审慎,同年六月四日覆电驳回上述提案。后经湖北方面再次力争,学部同意首届学员中“实系中学毕业”者“援照贡廪增附生办理”,未经中学毕业者仍“责令补习”,不得径入高等科。校方对此仍不满意,翌月底再申前议。(49)同年八月二十一日,学部终同意首届学员中的“师范简易科毕业生及方言、自强学堂修业生,即照该学堂前次所请办法”办理。但高等小学堂毕业生,“程度相差太远,不得与简易师范各生相提并论,应仍归原班教授以资深造”。 湖北方面在与学部的反复协商中固然有不小收获,但学部“于权变之中仍示核实之意”,且双方协商的毕竟只是首届学员的“权变”之策。对于同样是在《修订新章》出台前招入的新班学生,校方协商之初即主动表示一律照新章办理。在时局动荡的辛亥鼎革前夕,湖北办学官绅虽有相当的话语权,但中央政府的教育规章和政令在湖北仍有相当的效力。 宣统三年七月底,湖北存古学堂举行“中等毕业考试”。翌月十九日,武昌起义爆发,军事行动迅速影响到该校的办学运作。不仅学生的“中等毕业证书”未发,且学校改驻军队后,书籍、图表、分数册及所有公文案卷皆“荡然无存”,学生“纷纷解散”。(50)1913年春,湖北方面据该校原斋务长王劭恂重新造具的学生名册,发给“中等毕业证书”,呈请教育部按照“部令专门学校例”,为其“换给毕业证书”,被教育部专门司覆电驳回。[73]实际教育部1912年10月公布的《专门学校令》开列十类专门学校,无一与“古学”有关,显然是将前清存古学堂完全摒除在新教育系统之外。[74] 张之洞办湖北存古学堂,力图以不失其故的新式学堂办法保存国粹。可能出于减少办学阻力和压力的缘故,他并未着力宣扬(甚或可以说是有意避而不言)该校办学“不失其故”的一面,而是在着力彰显其“新教育”属性的同时,试图静默地将其认同的传统办学方式“见之于行事”。既存研究或将存古学堂视作“新教育”的对立面,或注意到张之洞“彰显其新”的努力,相对较忽略该校与“书院”等传统办学形式相联的面相。实际上,湖北存古学堂从拟办预案到具体作法皆未完全否定,更在一定程度上承继了中国传统学术授受方式(尤其是张氏本人此前兴办书院的举措和经验)。该校在师资、典籍、教学以及办学功能等方面皆有自经心、两湖书院以降的学脉传承轨迹。 这里所言“彰显其新、暗承传统”,是指张之洞的实际办学运作而言。盖学堂既以“存古”为名,则其“保存国粹”的意趣实已相当明确而醒目。唯“古学”当然是“传统”中相当重要的部分,但“传统”毕竟不仅指“古学”本身而已,恐怕至少还包括“古学”的传承和授受方式。而即便是相对具有较多共性的清季官方“存古”努力,对“国粹”本身的理解、对中学保存方式的认知也多有不同。在清季时人的“体用之分”中,教育建制和授受方式通常被归入“用”的范畴,既然张之洞所欲存之“古”不仅仅是“古学”,还包括一部分传统的办学方式,意味着至少就“存古”而言,作为当时“中体西用论”的代表和典型,张氏未必认为“中学之用”全是消极负面的因素,有些可能还是欲保存“中体”而不能全然摒弃者。他在实际的政务(尤其是当时被视为“重要政务”的教育)中,究竟秉承和践行着怎样的“体用”观,相关面相或许还有进一步讨论的空间。 张之洞对该校倾注大量心血,实有较深远而重大的寄托。他认为“新学”不足以“救危亡”,存古不仅无碍“救亡大局”,而且本身即是其中应有之义。但这样一种基于“国家”和“世道”而希图“裨益世教”的“苦心”,即便是在张之洞欲引为同道的门生故吏和友人圈中,也难觅真正的知音和愿意鼎力襄助者。(51)而少数对张氏“苦心”极表同情而全力投身于该校者,如曹元弼,又因受张氏影响过深,反而在实践中明显偏离了张氏原拟的办学思路。这一颇具诡论意味的情形或可从一个侧面折射出清季的社会情势与存古学堂间的张力:士人迫于“救亡”的焦虑情绪和急于在普适层面“存古”的“救世”心理,对于需要较长时间沉潜和积累的古学研究而言,即或不是阻力,恐怕也不全是正面的影响。 学校实际的管理状况更严重地偏离张之洞以“新教育”克服“旧日书院积习”的初衷。而未能礼聘到最理想的专职监督以及鄂省学界错综复杂的人脉关联,又使官方的整顿努力收效甚微。张之洞卸任湖广总督后,无人有能力和威望可以震慑、制衡和调解湖北学界各方势力,以致鄂省学务深陷激烈内哄、相互倾轧而自耗严重的泥潭。(52)纪钜维被控引发的不小风波正是上述局面的缩影。 张之洞不仅参与制订晚清学制,更是少数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乃至挑战既存体制的晚清重臣之一。存古学堂本身即是张氏力图补益既存学制的“创举”。实际上,张之洞兴办该校,确实充分利用了自己的权势、威望和影响力,在招考录取、中西课程配置、学制年限等方面明显突破常规,这当然使该校一度获益匪浅,但也使其办学运转明显依赖张氏个人而难以持久。宣统三年颁行的《修订存古学堂章程》即在相当程度上将该校重新纳入“规范划一”的轨道。张氏突破常规的作法不仅被中止,更成为湖北存古学堂赓续办理的障碍。 另一方面,张之洞兴办存古学堂的努力,浸透着他对“国粹”及其保存方式的理解和思考,其中的部分面相其实是长期困扰中国学界的难题,如国学研究和教学机构如何安顿“普及”与“提高”的关系;究竟应否添加以及怎样添加西学内容;如何面对“国学浩博”与学制“年限至短,复添科学”的矛盾;如何看待传统的中学传承方式(尤其是书院办学形式);就保存中学而言,西式学堂办法真正的长处何在。张之洞的观念和作法在当时多少有些“曲高和寡”,也算不上成功,但未必不是值得我们注意的面相。 本文曾提交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10-20世纪中国社会与文化”讨论会,得到不少指教,并承匿名评审专家纠谬,谨此致谢! ①本文所用清季史料皆为阴历,其中不少图表档案尤以阴历编排统计年度和月份,不便精确对应到阳历年月,故以下所述凡民元以前者皆依照当时人的作法和习惯出以清帝年号纪元及阴历日期。又,本文以下引用作者全名时一概不尊称先生,谨此说明。 ②目前所知清季湖北、安徽、江苏、陕西、广东、四川、甘肃、山东等省皆正式办有存古学堂,京师、江西、浙江、福建、贵州、湖南、江宁、广西、河南、云南、直隶、吉林、黑龙江等地也都有仿办存古学堂的提议或规划。 ③笔者曾在《四川存古学堂的兴办进程》(《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2期,83-84页)一文中简述2007年以前有关存古学堂的既存研究,这里仅举与湖北存古学堂相关的典型实例,并概述2008年至今学界相关的研究进展。 ④端方稍后在任两江总督时对于江苏、江西两省的兴办存古学堂计划都不甚积极,时中央政府已将该校确定为“新教育”体系内保存国粹的主要形式,并提倡各省参照湖北章程“量力建置”(详另文)。一般认为梁鼎芬较“保守”(苏云峰:《张之洞与湖北教育改革》,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1976年,67-69页)。唯张之洞光绪二十九年(1903)在京修订学堂章程期间,梁氏曾提出“学堂必办,科举必废,书院速改学堂”等“要旨”,被张氏采纳。可知梁氏办学似较开放而前瞻,其对张之洞影响之大也超过我们此前的认知。梁鼎芬:《致张之洞电》(光绪二十九年闰五月五日发),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张之洞档案,甲182-163;梁鼎芬:《致张之洞电》(光绪二十九年七月廿四日发、光绪二十九年七月二十八日发、光绪二十九年八月初四日丑刻发未刻到、光绪二十九年八月初四日午刻发亥刻到),张之洞档案,甲182-165。 ⑤张仲炘:《详署理湖北提学使王寿彭文》,引在瑞澂《湖广总督为存古学堂事咨学部文》(宣统三年四月),台北“国史馆”藏清学部档案,195/135。 ⑥光绪三十三年上半年赵启霖以言官纠参权贵未果而革职返乡,途经武汉。同属清流的张之洞对其“特别尊礼”,并力邀赵氏主持存古学堂。时湖南方面也电促赵氏担任湖南高等学堂监督,张之洞为此专电湖南提学使吴庆坻,希望湘中“慎勿强留”。唯张氏不久后离任湖广总督,赵启霖“遂未赴鄂”。赵启霖:《瀞园自述》,《赵瀞园集》,湖南出版社,1992年,335-336页;吴庆坻:《蕉廊脞录》,中华书局,1990年,194-195页;张之洞《致吴庆坻》(光绪三十三年五月二日),张之洞档案,甲182-422。 ⑦本段所述除特别注明外,皆参见《湖北省官立存古学堂光绪三十四年上学期一览表》,清学部档案,195/135。 ⑧陈夔龙:《致张之洞》(光绪三十四年九月七日),张之洞档案,甲182-451。陈氏是在得樊增祥“传述”张之洞仍欲请梁鼎芬出任湖北存古学堂监督后,遂有此电。 ⑨张之洞在光绪三十三年七月二十八日所呈《请奖梁鼎芬片》(苑书义等编:《张之洞全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1816页)中说,湖北在设提学使前,所有“学务均委该员办理”。 ⑩光绪三十四年正月十日,刘洪烈、刘邦骥等九位鄂省人士联名电请张之洞设法让梁鼎芬“仍居鄂中,俾得所瞻依,裨益实多”。《刘洪烈等致张之洞电》(光绪三十四年正月十日发),张之洞档案,甲182-449。 (11)一年多后,学部奏准由梁鼎芬出任曲阜学堂监督并一再电催其就职,梁氏友人也致函婉劝,但梁氏一直坚辞不就(详另文)。梁氏在辛亥鼎革及民元后一直竭力为满清皇室奔走,并未再办理学务。参见吴天任编《梁节庵先生年谱》,台北:艺文印书馆,1979年,271-369页。 (12)本段及下段除特别注明外皆参见张之洞《创立存古学堂折》(光绪三十三年五月二十九日),苑书义等编:《张之洞全集》,1762-1766页。 (13)本段所述使用的资料有:《湖北存古学堂光绪三十四年上学期一览表》《湖北存古学堂宣统元年上学期一览表》《湖北存古学堂宣统二年上学期一览表》,清学部档案,195/135。 (14)《湖北存古学堂调查意见》,《学部官报》总第158期,宣统三年六月十一日,“京外学务报告”,页码残。该《调查意见》并提到,该校“石经楼高爽明敞,尤饶清旷之致”。 (15)本段所述除特别注明外,皆参见陈佩实《考查湖北存古学堂禀折》,《广东教育官报》,宣统三年第5期,“附篇”,104A-106B页。 (16)参见张国淦《历代石经考》,1930年铅印本;刘起釪《〈尚书〉与历代“石经”》,《史学史研究》1983年第3期,45-54页;赵俊芳《〈华阳国志〉汉魏丛书本述略》,《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8年第6期,42-44页。 (17)王寿彭:《详请将湖北存古学堂详细规则移送学部备案文》,引在瑞澂《咨呈湖北存古学堂详细规则文》(宣统三年闰六月二十四日),清学部档案,195/135。 (18)本段所述师资依据的资料除前文已列外还有:《湖北存古学堂职员调查表》,《学部官报》总第158期,宣统三年六月十一日,京外学务报告,页码残;《宣统二年八月委派[鄂]省内外学务职员一览表》,《湖北教育官报》宣统二年第9期,同年九月,“纪事”,1A页。 (19)参见曹氏在1917年初刊印《复礼堂文集》时为《原道》《述学》《守约》三文所写的“后记”,《复礼堂文集》,台北:华文书局,1969年影印1917年刊本,卷1,59页。 (20)张之洞:《咨学部录送湖北存古学堂课表章程》(光绪三十三年五月),苑书义等编:《张之洞全集》,4386-4396页。该章程中举列的“有关群经总义诸书”包括:《经典释文》叙录、传经表、通经表,历代正史《艺文志》《经籍志》之经部,《四库全书提要·经部》,历代正史《儒林传》,惠栋《九经古义》,余萧客《古经解钩沉》,王引之《经传释词》《经义述闻》,陈澧《东塾读书记·经类》《九经古义》。《劝学篇·守约第八》在举列“清代解经之书”时说,“五经总义止读陈澧《东塾读书记》、王文简引之《经义述闻》”。二者形成鲜明对照。而“十三经学教科书”则是在“清代解经之书”基础上专意为普通学堂学生设计的更简约的“经学通大义之法”。 (21)即便是作为经学科、政法科、文学科、商科大学预备学程的“高等学堂第一类学科”,其中学课时平均每周也不到10个钟点,约占总课时的1/4。《奏定高等学堂章程》(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收入璩鑫圭等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328-339页。 (22)张之洞将存古学堂的招生定位在高等小学堂毕业生,唯“以目前初等、高等小学尚未造有成材”,故先“就各学生员考选,不拘举、贡、廪、增、附皆可”。其实高等小学堂毕业生并未读完五经,故学部《修订新章》规定存古学堂经学中等科前两年须“讲读《周易》《尚书》《春秋左传》三经,以符中学堂学生必须读完五经之通例”,此后再照张之洞所拟学程“讲明群经要义大略”。此举意在寻求存古学堂与普通“学堂教人之学”的衔接,实际大大降低了经科的研习起点。 (23)实际上,该校办学员绅对于经学授受方案确实存有异议。光绪三十三年八月初,曹元弼与梁鼎芬、黄绍箕“商榷授经详细章程”,具体办法是为张之洞所拟章程中的“经学教法”作注,但因“往复商论未定”,至同年底仍未将“授经详细章程”寄呈张氏。曹元弼:《上南皮张孝达相国书》(光绪三十三年十二月),《复礼堂文集》,860-861页。 (24)顾颉刚已注意到,曹元弼“以昌明圣学,恢弘文化自期”,并“受张之洞《劝学篇》之影响,必欲措诸实用”,而与“求知而已”的清代学者不同。顾颉刚:《苏州史志笔记》,苏州市政协文史资料编辑室编,王煦华辑,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182页。 (25)本段所述除特别注明外,皆参见曹元弼《守约》,《复礼堂文集》,45-59页。 (26)曹氏晚年仍以“守约”为其著书之要义,他从1941年5月17日开始纂著《尚书学》一书,时已75岁高龄。参见曹元弼《复礼堂日记(辛巳年、壬午年)》,湖北省博物馆藏手稿。 (27)本段及下段所述除特别注明外,皆参见《鄂督张设立存古学堂札》,《湖南官报》第891号,光绪三十年十二月初九日,“时政录要”,33A-34B页;张之洞《创立存古学堂折》,光绪三十三年五月二十九日,苑书义等编:《张之洞全集》卷68,1762-1766页。 (28)本段及下段所述张、罗二人的私下会谈,皆参见罗振玉《集蓼编(雪堂自述)》,《罗雪堂先生全集》,第5编第1册,台北:大通书局有限公司印行,1973年,21页。 (29)《尊经书院记》(苑书义等编:《张之洞全集》,10078-10080页)的“慎习”条明确指出,“今天下之书院,不溺于积习者罕矣”。对于“人多则哤,课无定程则逸,师不能用官法则玩,嬉游博簺、结党造言、干与讼事、讪谤主讲”等书院积习,要“屏惩不宥”。“约束”条进而提出“牖导必宽,约束必严”的办学方针。 (30)豫、湘两省的办学预案皆是因应中央政府停废科举的政令,为旧式读书人“宽筹出路”,并为科举停废后保留的优拔贡考试作准备,明显疏离于清季“新教育”通行的西式“学堂”办法。张氏奏折所言大体是针对上述面相而言,详郭书愚《为“旧学应举之寒儒筹出路”兼彰“存古”之义:清季豫、湘、赣三省因应科举停废的办学努力》,《社会科学研究》2013年第3期,154-164页。 (31)《尊经书院记》(苑书义等编:《张之洞全集》,10080页)有专条规定“不课时文”,但允许学生“自为之”,或“应他书院[时文]课”。张氏后来办广雅、经心、两湖书院大体延续了上述作法。苏云峰研究员已注意到张氏“排斥八股制艺在书院课考之外”,但乐见广雅、两湖书院士子中举,详《张之洞与湖北教育改革》,43-58页。 (32)《尊经书院记》(苑书义等编:《张之洞全集》,10078-10080页)的“恤私”条规定,“调院之外投考者不禁……收录须稍严”。 (33)参见张之洞档案甲182-77、79、92、93、95、99、100、159、160、219、405、468中的相关电稿。清季不少存古学堂皆有明显贴近传统的重“师”轻“官”之风,与清季“新教育”将教员列为“职官”的官僚化倾向明显不同(详另文)。 (34)光绪元年(1875)时任四川学政张之洞在《輶轩语》(苑书义等编:《张之洞全集》,9771-9822页)中即倡导士子读“国朝人经学书”。后《劝学篇·守约》举列经学参考书,“国朝经师之说”也占相当比重。 (35)王汎森教授在《近代中国私人领域的政治化》(《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吉林出版集团,2011年,168页)中已注意到明清书院士子将记载读书心得的日记呈送师长检查的制度,并指出,“清代考据学盛行时,一般书院看重的是读书考据的札记”。 (36)本段及下段所述除特别注明外皆参见张仲炘《湖北存古学堂详细规则》,附在瑞澂《咨呈湖北存古学堂详细规则文》,宣统三年闰六月二十四日,清学部档案,195/135。 (37)《尊经书院记》(苑书义等编《张之洞全集》,10076页)“定课”条规定,“人立日记一册,记每日看书之数,某书弟几卷起,弟几卷止,记其所疑,记其所得……监院督之,山长旬而阅之,叩诘而考验之”。张之洞光绪十五(1889)年订立的《广雅书院学规》(陈谷嘉、邓洪波主编:《中国书院史资料》下册,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2297页)规定:“各生各立课程日记,按日注明所业于簿,诵习钞录,记其起止,解说、议论有得即记,以便院长按业考勤”。 (38)有关明清书院较松散的簿记制度,可参见王汎森《近代中国私人领域的政治化》,《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168页。 (39)实际上,张之洞原拟课程也到了“钟点已多,讲堂已满”的程度。故张氏虽然认为“洋文为将来考究西籍之基,为用尤大”,但只能在存古学堂附近设一所外文学堂,准许学有余力者附入“自行兼习”。张之洞:《创立存古学堂折》(光绪三十三年五月二十九日),苑书义等编:《张之洞全集》,1762-1766页。 (40)本段及下段除特别注明外,皆参见《高凌霨致张之洞电》(光绪三十四年八月十六日),张之洞档案,甲182-450。 (41)纪钜维在光绪三十二年即认为鄂省学务“条理纷杂,向无章法”,且因“虚声在外”而“不易整顿”。纪钜维:《与刘仲张亲家书》,《泊居賸稿续编》,1924年排印本,14A-B页。梁鼎芬也有类似感受,从一个侧面提示着清季湖北“新教育”在“盛名”之下不那么正面的实况或许超过我们此前的认知,详另文。 (42)纪钜维曾助张之洞撰《劝学篇》,书中“变科举”部分援引的《朱子语类》“论罢科举语”,即是张氏命纪钜维“查检”出来的(纪钜维:《禀张之洞文》,张之洞档,甲182-218)。张之洞后又委托纪氏校勘其所选“亲故九家诗文稿”。纪钜维:《与刘甥札》,民国3年9月,《泊居賸稿》,1924年排印p本,5A-B页。 (43)本段及下段所述除特别注明外,皆参见《鄂省常驻员会议纪监督控案(武昌)》,《申报》,宣统元年十一月十三日,第1张后幅第2版。 (44)王寿彭:《详请湖广总督瑞转咨学部从速修订存古学堂章程文》,引在瑞澂《详请从速修订存古学堂章程文》(宣统二年十二月五日),清学部档案,195/135。 (45)本段所述除特别注明外,皆参见王寿彭《详督宪考核各学堂教员办理实在情形文》,《湖北教育官报》宣统三年第9期,“文牍”,1A-2A页。 (46)详郭书愚《清季中央政府对保存国粹学堂的态度演变》,《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117-130页。 (47)张之洞在《存古奏折》中提出给举贡廪增附生以平等的应考机会,只是将监生和童生摒除在外。他在选录学生时似乎不那么看重科举出身的高低,至少是不认为其与实际的中学程度之间有明确的对应关系。 (48)张仲炘:《咨呈湖北存古学堂宣统三年下学期改办方案文》(宣统三年四月),引在瑞澂《咨请学部查核湖北存古学堂宣统三年下学期改办方案文》(宣统三年四月十七日),清学部档案,195/135。 (49)本段及下段所述除特别注明外参见《学部专门司电覆瑞澂文》(宣统三年八月二十一日),清学部档案,195/135;瑞澂《咨请学部查明湖北存古学堂办理实在情形及窒碍之处文》(宣统三年七月二十四日),清学部档案,195/135。 (50)本段所述除特别注明外,皆参见姚晋圻《呈请学部照部令专门学校例换给前清存古学生毕业证书文》,民国二年3月,清学部档案,195/135。 (51)张氏门人孙诒让即认为当时应“以救亡为急”,存古学堂“似可略缓”,故而辞任湖北存古学堂监督。黄绍箕:《致张之洞电》(光绪三十年六月十日),张之洞档案,甲182-168。 (52)这一情形民元后仍在延续,参见李骧五《湖北教育界的派系斗争概略》(1905-1938),《湖北文史资料》,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总第10辑,1984年内部发行,105-10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