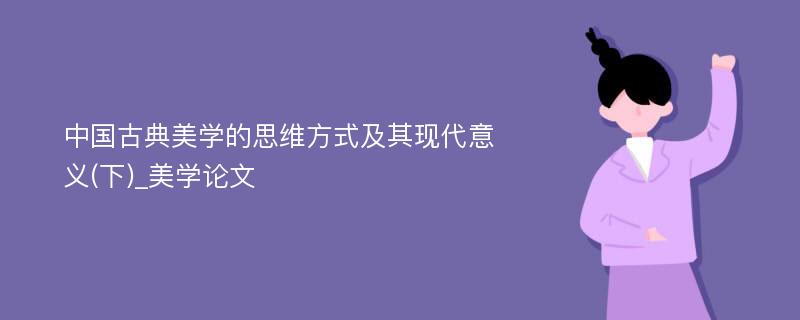
中国古典美学的思维方式及其现代意义(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学论文,思维方式论文,中国古典论文,意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01)02-0075-05
四、圆形思维
从以上所论可见,中国古典美学是非常讲究圆整、圆通、圆融的,这正显现了圆形思维的特征,而这一点又突出地表现在中国古典美学的理论逻辑上,它往往将事物的发展演变理解为其状如环的逻辑圆圈。
在这方面清代学者刘熙载的论述具有代表性,他将作家、艺术家在长期艺术实践中创作水平的提高概括为一个迂回曲折、终始相迭的逻辑圆圈。他论词曲创作说:“古乐府中至语,本只是常语,一经道出,便成独得。词得此意,则极炼如不炼,出色而本色,人籁悉归天籁矣”[8]。又论书法创作说:“学书者始由不工求工,继由工求不工。不工者,工之极也”,“书当造乎自然。蔡中郎但谓书肇于自然,此立天定人,尚未及乎由人复天也。”[8]
刘熙载的这几段论述虽略有差别,但总体上是将文艺创作分为三种水平,它们前后相续、首尾衔接,构成一个圆整有序的逻辑进程,将其规整一下的话,可以见出这样几个逻辑圆圈:“不炼-极炼-不炼”,“本色-出色-本色”,“天籁-人籁-天籁”,“不工-工-不工”,“天-人-天”。其中第一种水平(不炼、本色、天籁、不工、天)是指创作还处于不成熟、不自觉的状态,还没有脱离素朴、幼稚的原生态,还没有经过千锤百炼,还没有受到理性之光的照耀,就像小孩最初学步一样,总是免不了蹒跚和摇晃,但这是不可缺少的第一步,是迈向更高水平的逻辑起点。其中第二种水平(炼、出色、人籁、工、人)则是指经过学习、培养、训练和实践,脱离了那种素朴、幼稚的原生态,逐步走向成熟和自觉,创作活动在理性的指导下进行,能够按照既定的意图,遵循预先铺设的轨道,有效地达到预期的目标,但其不足在于创作行为受到理智和意志的严密控制,表现出过强的目的性和人为性,不能消除人工斧凿痕迹,其至流于雕琢和做作,而这必须以牺牲艺术规律和美学特征为代价,使得丰富多采的文艺创造心理诸如感知和意象、想象和幻想、灵感和激情、理想和情怀在冰冷的理智和意志面前显得过度的顺从和服贴,从而丧失了灵气,泯灭了个性,变得过于拘谨、呆板、僵硬。这种创作活动工则工矣,炼则炼矣,但全凭人力,非关天巧,拘囿于必然性的轨辙,很难凭靠心灵的创造性和原创性获取那种不期然而然的自由,因此无法上升到更高的境界。其中第三种水平(不炼、本色、天籁、不工、天)则是从第一种水平的起点出发,经由作为中间过程的第二种水平而达到的最高境界,这是经过理性的升华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在这里无理性不行,但唯理性不够,这是在理性活动的基础上创作水平的更上层楼。这时,文艺创造心理的丰富形式在理智和意志面前变被动为主动,变自在为自为,反过来牵引着理智和意志向前走,甚至起来反抗理智和意志的安排和控制,表现出明显的不自觉性和无目的性。然而,这种不自觉性和无目的性恰恰是孕育出上乘之作的母体,因为这是文艺创造心理的自身规律纯任自然、无拘无碍地发挥作用的最佳状态,只有到这时,创作活动才既富于生机和活力,显得空灵洒脱,又不悖离生活逻辑,显得逼真可信,消除了过强的理性控制所带来的强制性和刚性,获得了高度的自由,而其作品也犹如神工鬼斧、天造地设,透出一种人力所不能达致的素朴自然的气象。总的说来,中国古典美学的圆形思维有以下特点:
首先,这一思维方式其状如环,它不是从起点直达终点,从初始水平一蹴而就到达最高水平,而是经过一个中间过程,转向它的对立面,从“不炼”到“极炼”,从“本色”到“出色”,从“天籁”到“人籁”,从“不工”到“工”,从“天”到“人”,曲线上升,迂回前进,然后再到达最终目的。而这最终目的、最高水平又向着逻辑起点、初始水平回归,当然这并不只是在同一层次上与起点的简单重复,而是在更高水平上向起点的复归,这后一个“不炼”、“本色”、“天籁”、“不工”、“天”与前一个“不炼”、“本色”、“天籁”、“不工”、“天”尽管在表面上极为相似,但二者的本质已相去不可以道里计,有着自发与自由、自在与自为的区别。钱钟书先生曾引用唐人张志和的《空洞歌》来说明这一思维特点:“无自而然,自然之原。无造而化,造化之端。廓然悫然,其形。”[9]总之这一思维过程终始若环,状如西方人所说的“蛇咬尾巴”,但究其实则是一种螺旋式的上升运运。
其次,中国古典美学总是表现出对于自然之美、天工之美的大力崇尚,把回归自然、与天为一视为审美活动和艺术创作的螺旋式上升运动之最高境界。在审美活动和艺术创作中有一个永恒的矛盾,即天然之美与人工之美的矛盾,天然之美就是所谓“不炼”、“本色”、“天籁”、“不工”、“天”,而人工之美就是所谓“极炼”、“出色”、“人籁”、“工”、“人”。中国古典美学历来重“天工”而轻“人工”,褒“天籁”而贬“人籁”,左“本色”而右“出色”,这从刘熙载所论可见一斑。除此之外,相关的论述可谓多多,如徐渭说,世事有本色,有相色,“本色,犹俗言‘正身’也;相色,‘替身’也”,“故余此本中贱相色,贵本色”[10]。李贽说,作品有化工,有画工,“造化无工,虽有神圣,亦不能识知化工之所在,而其谁能得之?由此观之,画工虽巧,已落二义矣”[11]。袁宏道也说:“世人所难得者唯趣”,“夫趣得之自然者深,得之学问者浅”[12]。当然这里所崇尚的天然之美是指经过螺旋式上升运动所达致的返朴归真之美。中国古典美学对于天然之美与人工之美的褒贬抑扬之基本立场作为一种理论规范和学术参照,恰恰构成了审美活动和艺术创作提高的一种驱动力。
再次,中国古典美学十分重视超理性思维的作用,认为自然之美只是在意境神王、若有神助的状态中不思而得、不期而遇的东西,只有在直觉、灵感、激情、才赋、潜意识等超理性思维的帮助之下,审美活动和艺术创作才能进入那种“极炼如不炼,出色而本色,人籁悉归天籁”的极境。关于这个问题,李渔有一个很好的说法:“然亦知作者于此,有出于有心、有不必尽出于有心者乎?心之所至,笔亦至焉,是人之所能为也。若夫笔之所至,心亦至焉,则人不能尽主之矣。且有心不欲然,而笔使之然,若有鬼物主持其间者,此等文字,尚可谓之有意乎哉?文章一道,实实通神,非欺人语。千古奇文,非人为之,神为之,鬼为之也!人则鬼神所附者耳。”[13]这里又是一个逻辑圆圈。李渔说神道鬼不过是对于文艺创作超理性思维的一种形象的说法而已,说的是创作在超理性思维的驱动下进入那种自由任运、无法而法的最佳状态,它超越了前此在理性主导之下“心之所至,笔亦至焉”与“笔之所至,心亦至焉”两个阶段,恰恰对应着返朴归真的创作极境。但是无论中国古典美学如何强调超理性思维在审美活动和艺术创作中的神奇作用,它也不曾忽视一个重要前提,即通往最高境界的道路,终究是由潜心的学习、长期的实践和艰苦的磨练铺就的,也就是说,那种妙然天成、下笔如有神的佳境决不可能从天而降,并非真正鬼使神差,而必须以紧张的理性活动为必由之路。一则禅宗公案可以彰明其理:“当药山坐禅时,有一僧问道:‘兀兀地思量甚么?’师曰:‘思量个不思量底。’曰:‘不思量底如何思量?’师曰:‘非思量。’”这里药山禅师铺设了一条从“不思量”到“思量”再到“非思量”的精神历程,所谓“不思量”就是尚未被思想之光照亮,尚未受到思理和智慧清理和提纯的原始冲动、官能快感、自然本能、感性体验等低级的心理状态;所谓“思量”就是由逻辑思考、名理概念和自觉意识所构成的充满理性色彩的心理状态;所谓“非思量”则是在前二者的基础上所达到的“悟”的超理性思维。日本学者阿部正雄对此所作的阐释是可取的:禅“建立在非思量的基础上,这超越了思量与不思量。当不思量被当作禅的基础时,反理性主义就会变得猖獗。当思量被当作禅的基础时,禅就会丧失其真正的基础,蜕化成单纯的概念和抽象的冗词赘语。然而,真正的禅把非思量当作它的最终基础,从而可以根据情况的需要,通过思量或不思量而任运自在地表现禅的自身。”“禅宗的目标永远在于把握生命中活泼泼的实在,而这不是光凭理性分析就能完全把握住的”,但“这决不能被当作只是反理性主义。禅虽然超越了人的理性,但并没有排除理性。”[14]总之,在对待超理性思维的态度上,任何走极端的想法都是行不通的,非理性主义如此,唯理性主义亦然。而中国古典美学对此始终持积极、健康的理性主义态度,在大力推重超理性思维的同时,不至于滑向这两个极端,而是主张天才与人力、性情与理智、先天禀赋与后天磨练相结合,对审美活动和艺术创作水平提升的逻辑之圆持一种圆通和圆融的立场,表现出较高的合理性和科学性。
五、中国古典美学思维方式的现代意义
研究中国古典美学的思维方式说到底仍是为了发掘其强大的生命力和健旺的生长性,发扬其现代意义,为建设现代美学体系提供必要的思想资源。
首先,中国古典美学的思维方式对于美学研究中某些思维片面性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防范作用。美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乃是近代的分析思维之功,鲍姆加通将美学从逻辑学中独立出来,康德将审美关系与认识关系、实践关系区分开来,从而为美学圈出了一块特有的领地,使之拥有了自己特殊的对象、范围、目的和方法,这大大促进了美学的进展,但同时也造成了美学的某些弊端,在一定程度上并不利于保存事物本身固有的天然联系并从而把握事物的美,生硬地将人与自然、主观与客观、内容与形式、功利与非功利等分为二橛,仅仅对事物的某一端作孤立、片面、抽象的研究,使得许多美学问题在这种人为的二分所留下的缝隙之中泄漏掉了,反而显得于理不通、于事无补;这种二分思维也容易造成那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顾一点、不及其余的偏致,或者太过强调某一方面而对另一方面有所偏废,或者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例如黑格尔的理性主义美学过于倾重理性化的先验存在“理念”,而作为一种反动;其后以叔本华、尼采、柏格森为代表的非理性主义美学则对理性采取了绝然拒斥的态度。相比之下,中国古典美学的整体思维、中和思维、类比思维等就显出其优长之处了,中国古典美学总是在大千世界错综复杂的关系之网中确认事物美的价值,重整体结构而不重个别元素,重相互关系而不重个体实存,对于那种仅仅停留于支支节节的琐碎分析而疏于总体把握的做法无疑具有防范作用。如宋儒张载从传统的阴阳五行说生发出著名的“民胞物与”思想,宣称“惟大人为能尽其道,是故立必俱立,知必周知,爱必兼爱,成不独成”,“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这种素朴的人道主义和环境意识在现代社会尤其值得肯定,其美学意味也将重新焕发出耀眼的光彩。
其次,中国古典美学的思维方式对于美学研究方法的欠缺之处具有弥补和完善的作用。西方美学历来从属于哲学,成为哲学的一个分支,这也决定了它的研究方法往往以概念、判断、推理、演绎以及三段论、二分法等形式为主,表现出过强的思辨色彩。中国古典美学也不乏思辨,但更多凭借直觉、感悟和测度,包含大量体验、内省、猜测、臆想的成分,带有非概念、非逻辑的色彩,美国学者F·卡普拉说:“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直接的直觉领悟往往是短暂的。但在东方的神秘主义中就不同了,他们把它延长并最终成为一种持久的意识。”[15]F·卡普拉站在西方思想本位上将东方思想称为“神秘主义”是偏颇的,但他指出直觉和领悟在东方思想中的重要地位不无道理。中国古典美学的种种思维方式主要不是思辨的结果,而是直觉和领悟的产物。例如刘勰在《文心雕龙》《物色》等篇中运用类比思维打通天时、地理、心理、生理之间的联系,如“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是以献岁发春,悦豫之情畅;滔滔孟夏,郁陶之心凝;天高气清,阴沉之志远;霰雪无垠,矜肃之虑深。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发”云云,就不能简单地斥之为穿凿附会的臆说,这种人与自然之间情往似赠、兴来如答的感应传通及其对于文艺创作的影响是人们实际感受和体验到,并对文艺创作起到实实在在的作用的。然而刘勰把握到这一点不是靠思辨,而是靠直觉和领悟,尽管缺乏实证材料,未经科学分析,无法量化,但却像中医的经络学说一样很管用。问题在于,西方式的思辨和分析可能将活生生的生命体当成尸体来解剖,而中国式的直觉和领悟则更注重把握事物内在的关联性、有机性,完整地保存了生命体本身固有的精气和血脉,这对于重思辨重分析的现代理论思维是一个必要的补充。
再次,中国古典美学的思维方式中某些富于生命力的因素可以整合到美学研究的现代思维之中。中国人的圆形思维很早得到发展和普遍运用,老子早就提出“反者道之动”的观点,形成了“观复”的思想方法:“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是曰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周易》也一再阐发“反复”、“往复”的思想:“无平不陂,无往不复”,“反复其道,七日来复”,“无往不复,天地际也”。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人往往将事物的发展演变看成一个逻辑圆圈,老子所谓“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应是最早的表述,到晚近人们的论述更加确切明了,焦循说:“由反而复为进,由复而反为退”,龚自珍说:万物之数括于三:初异中,中异终,终不异初。……万物一而立,再而反,三而如初。这些论述与现代理论思维中正、反、合的三段论何其相似乃尔!但不可否认,这两者之间尚不可等量齐观,这种圆形思维尚带有循环论的性质,思维的循环运动是封闭的、平面的,而不是开放的、立体的。究其所以,原因在于其仍不脱古代思维素朴、混沌的特点。然而拉动思维水平提升的最终是实践,正是实践引领着这种本来带有自发性质的圆形思维凿破了以往混沌未开的思想空间,将周而复始的循环运转改造为螺旋式的上升运动。这一情况在中国古典美学中尤其显得突出,以上所引刘熙载、李渔等人的论述已足以证之,说到底,正是长期的审美实践和艺术实践对此起着有力的拉动作用。而这一宝贵的思想成果,恰恰可以整合到现代理论思维中去,对于现代美学的构建发挥积极的作用。
收稿日期:2000-05-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