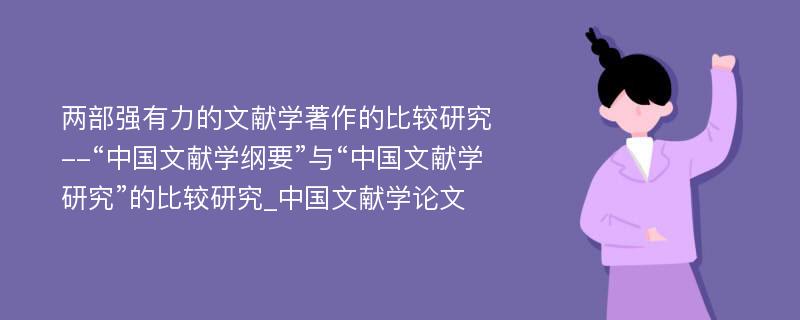
文献学的两部力作——《中国文献学概要》与《中国文献学》之比较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献论文,中国论文,概要论文,力作论文,两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献一词是个历史范畴,最早见于《论语?八佾》篇中。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们对文献概念有不同的理解。汉、宋学者都把“文”解为典籍,“献”解为贤人。以“文献”二字自名其著述,源于元代的马端临,其在《文献通考》自序中称“引古经史谓之‘文’,参以唐末以来诸臣之奏议、诸儒之议论谓之‘献’”。此后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中,大都把“文献”作为书籍资料的代称。自从人类有了文献,就有了关于文献的各种活动,在文献和文献工作的发展基础上,逐渐积累了经验及其知识,形成人类社会一个相对独立的知识门类,这就是文献学。[1]
“文献学”一词始见于1920年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全相望亦私淑宗羲,言文献学者宗焉。”我国第一部直接以“文献学”命名的著作是郑鹤声、郑鹤春合著的《中国文献学概要》(1928年版),此书首次以“文献学”冠为书名,标志着人们对文献的认识已从感性认识阶段上升到理性认识阶段,同时也标志着人们对文献的研究已进入系统的科学研究阶段和文献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正式诞生。[2]20世纪80年代初,张舜徽的《中国文献学》(中州书画社1982年版)一书打破近半个世纪的沉默,继之而起,成为我国文献学领域的奠基性著作。两书在我国文献学领域均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因此本文试对两书作一比较,以窥见文献学的发展面貌。
1
两书作者和成书背景
孟子曰:“读其书,诵其诗,不知其人,
可乎?”我们主张知人论事,因此,要对两部书深入了解,首先要对其作者作一概括了解。《中国文献学概要》(以下简称《概要》)[3]的作者是郑氏兄弟。郑鹤声(1901-1989),字萼荪,浙江诸暨人。1925年毕业于东南大学(即今南京大学) 文史地部,解放前曾供职于国立编译馆任常务编审,并曾任中央国史馆馆长,兼任中央政治学校和中央大学(今南京大学)教授。解放后一直担任山东大学历史系教授,是50年代全国赫赫有名的山大历史系八大教授之一,在中西交通史、中国史学史、中国目录文献学、中华民国史、中国民族史、华侨史、亚洲史等领域均有精深造诣。一生著述浩瀚,多达160余种,2000万字。
郑鹤春(1892-1957),字萼邨,为郑鹤声长兄,是我国著名教育家、实业家。先后执教于浙江省立第二师范、杭州之江大学等多所学校。1925年应聘至云南昆明高等师范学校任教授,后在上海、浙江、湖北、安徽等省市教育厅、局任职,并兼安徽大学教授。
《概要》写作和出版的年代,正是中西文化冲撞日益加剧的年代。《概要》自序指出“吾国文明发展进行之程序,约可分为三期:自邃初以迄两汉,是为吾国民族本其创造之力,构成独立之文化时期;自东汉迄明季,是为印度文化输入吾国,与吾国固有文化由抵牾而融合之时期;自明季迄今日,是为中印两种文化均已就衰,而远西之学术思想宗教政治以次输入,相激相荡,而卒相合之时期。”在第三时期,由于国势日衰,列强不断入侵,我国在军事上屡战屡败,有一些知识分子对中国传统文化发生了疑问,“以吾国固有文献,为腐败物质之渊薮,非廓而清之不为功。因噎废食,甚可慨焉!”针对这种情况,作者著述此书,以期改变当时“号为学人,而叩以本国文献之要略,瞠目而不知所对”的情况,达到“睹乔木而思故家,考文献而爱旧邦”的目的。可见,本书的写作是充满了强烈的爱国热忱的,这种感情在文中亦有表露,《概要》在引梁启超的论述指出:“故合世界史通观之,上世史时代之学术思想,我中华第一也。中世史时代之学术思想,我中华第一也。惟近世史时代,则相形之下,吾汗颜矣。”但中国人应当有信心,重新登上世界学术文化的高峰,绝不应“妄自菲薄”。读来确实令人振奋!
《中国文献学》[4]的作者张舜徽(1911-1992),湖南沅江人,自学成才。崇尚乾嘉朴学,治学以文字、音韵、训诂为根柢,长于版本、目录、校勘、考据,在经学、小学、史学诸领域均有成就。曾任兰州大学教授、中文系主任。建国后,历任华中大学教授,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历史文献研究所所长,中国历史文献研究学会第一至第三届会长。一生笔耕不辍,共撰写了论著52种,结集为专著25部,另主编5部著作。内容涉及经、史、子、集,体现了一位国学大师的风采。张先生学识渊博,贯通古今,他在长期的治学生涯中进行了大量古典文献整理工作,为其文献学思想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因此,从这位典型学者身上我们可以窥见20世纪中国古典文献学理论研究发展的全影。[5]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随着政治形势的改观,经济的繁荣,学术文化氛围逐渐活跃,加上社会对文献的需求和认识的普遍提高,中国文献学理论研究进入一个兴盛时期。张先生恰好在此时进入到他学术研究的丰收季节。1979年,他与学界同行在桂林发起,成立“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被推举为会长。1980年,国务院颁布学位条例,他随之被评为全国首位历史文献学专业博士生导师。客观形势催促着他继续思索,为历史文献学的学科建设提出系统的理论与方法。张先生整理旧稿,重新补充归纳,写成《中国文献学》。这部文献学著作最终将我国古典文献学的范围推至至极。[6]
2 两书的内容和体系结构
《概要》例言中,作者指出:“典籍结集,为文献学上最重大之事业,故首及之。然结
集而不施以审订,则无以取精而用宏,择要而去微,故审订又次之。既审订矣,……。并次而论之。”由此可知本书的内容和结构,先讲结集,再论审订、讲习,次论翻译、编纂。郑一奇在对之作导读时指出,这样的研究体系,既继承了古代的广义校雠学,是古典文献学的体系,但又有了新的突破。因为文献的中外交流正是现代文献学的特点之一。但也有人认为此书体系结构缺少内在逻辑性,体现了古典文献学脱离“校雠学”之名初期理论研究的片面性和迷盲性,因而该书问世后未能引起学术界的必要的重视。此后50余年间,尚无一部文献学理论著作出版。[7]
《中国文献学》全书分十二编六十章。
第一编绪论概述了文献学的范围和任务、记录古代文献的材料和书籍、古代文献的散亡;第二编叙述了古代文献的著作、编述体例、钞纂、写作的模仿、伪托、类辑等,其余各编分别介绍了整理古代文献的基础知识——版本、校勘、目录,前人整理文献的具体工作和丰硕成果,历代校雠学家整理文献的业绩;最后就今后整理文献的主要目的、重大任务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该书前后连贯,浑然一体,结构合理,条理清晰,较之《概要》更加完善。
3 两书的主要学术观点
3.1 关于文献的含义
《概要》在例言中对文献的定义引用了孔子和元代马端临的说法,显然这里的“文献”是指典籍记载与宿贤的言论。
张氏认为古代历史书籍以“文”和“献”作为主要内容,起源很早,早在司马迁写《史记》、班固写《汉书》时,都已将史实和言论并重。“‘文献’既是一个旧名词,自有它原来的含义和范围。我们今天既要借用这一名词,便不应抛弃它的含义而填入别的内容。”张氏对“文献”概念的认识是与他对“史”字的认识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他说:“‘史’的本义,既是文字,那末,用文字记录下来的材料,都可称为史料。”但作者并不主张将“具有历史价值的古迹、古物、模型、绘画,概称为历史文献”。由此可见,郑氏和张氏对文献二字含义的理解是一脉相承的。
3.2 关于文献学的含义
《概要》在例言中指出“结集、翻译、编纂诸端,谓之文,审订、讲习、印刻诸端,谓之献。叙而述之,故曰文献学。”就其全书内容来看,他们所说的“文献学”是指考订和论述古籍图书在分类、目录、校勘、编纂、翻译、版本和印刷方面的源流和概况。仔细考察各章节内容后,便可发现郑氏兄弟的文献学,实与刘向、刘歆父子开创的文献学一脉相承,即以目录、版本、校雠为重心,但论述范围有所扩展。[8]
张氏在书中指出,“我国古代,无所谓文献学,而有从事于研究、整理历史文献的学者,过去称之为校雠学家。所以校雠学无异成了文献学的别名。”同时,作者继承梁启超的观点,认为“文献学的范围包罗本广”,文献学就是广义的史学,内容是很丰富的。张氏提出文献学研究的宏伟目标在于编写一部中华人民通史。可见,“文献学”比“广校雠”具有更深广的内涵和外延,作者主要从史学角度考察文献学,认为中国文献学就是古代校雠学的延伸和发扬。[9]
3.3 关于文献的价值和文献学的研究范围
《概要》在谈到文献价值时指出“典籍者,思想之结晶,学术所由寄也。所以考制度,稽意识,文化之积业,政道所由系”。又指出“不治史学,不知文献之可贵,舆夫文献散佚之可为痛惜也”。作者指出,提倡科学救国,不能废弃对中国固有文献的研究。作者还确定“文献学”的研究范围,即对中国古代文献的研究、整理以及开发、传播、利用。
张氏在谈及文献价值时指出,“过去封建学者们所强调的‘徵文考献’,便是说要了解过去的历史,一方面取证于书本记载,一方面探索于老旧言论”。“对历史上人、事、物的评论和见解,可为后来治史的参考,价值也很高”。张氏认为,文献范围包罗本广,不独刘向、刘歆父子校书秘阁是整理文献,郑玄遍注群经、司马迁写成大著作等也属于文献学的内容。“所以我们整理文献,绝不可局限于校勘、注释几部书便够了,而要担负起的任务,却大有事在。”对图书、资料“进行整理、编纂、注释工作,使杂乱的资料条理化、系统化;古奥的文字通俗化、明朗化。并且进一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这是文献学的基本要求和任务。”在提出基本要求和任务后,张先生认为这还不够,应该在整理、研究的基础上写出总结性的著作来。“只要我们不是为研究而研究,为整理而整理,而是心怀大志,朝着一个宏伟目标而努力,不仅大有出息,而且可以对人类作出较大贡献。”
4
两书的特色和地位
《概要》在中西文化冲撞的时代背景下,
重新审订、申明中国文献学的世界地位、价值,总括了古典文献学的研究对象、范围、内容,初步奠定了研究体系。把“讲习”作为文献学的研究目的,总结了我国古代对文献传播、利用的概况。这是全书中分量最重、下功夫最多、也是颇有特色的部分,对我们了解中国古代思想流变、学术特色、师承关系均有帮助。“翻译”是《概要》中最有特色的部分,在近代中西文化冲撞的背景下,“翻译”对中外文献交流、研究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翻译”既与古典文献学的研究密不可分,对现代文献学的研究更是题中应有之义。因此,把“翻译”引入文献学研究体系,实际上已突破了古典文献学的研究范围。翻看后来的多种中国古典文献学专著,均未涉及文献之翻译。
《概要》出版后,受到广泛欢迎,一些大学的相关专业将其列为教材,并多次重印。屈指数来,郑氏兄弟的《中国文献学概要》已独领学坛风骚50余年,他是本世纪中国古典文献学领域当之无愧的巨匠。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看问题要全面,要把人物放在具体的时代背景下来考察。郑鹤声写本书时才二十七八岁,由于学识的积累以及时代背景的局限,该书在内容和体系结构上仍有一定的局限性。有人认为它和真正意义上的文献学还有一段距离。[10]但在当时蔑视民族文化思潮的背景下,作者能写出这样一部中国文献学的开山之作,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作者在文献概念、文献价值和文献学体系方面,还是提出了较为新颖的看法,代表着当时文献学家对文献学的认识。因此,本书不失为一部具有历史意义的文献学论著。
《中国文献学》不仅确定了文献学的范围和任务,而且总结了前人整理文献的经验和业绩,并提出了今后整理文献的重要工作。作者指出,文献学的落脚点和最大目的在于“创立新的体例,运用新的观点,编述为有系统的、有剪裁的总结性的较全面完整的中华通史”。作者把文献学研究与史学研究结合起来,以增强文献整理、研究工作的实用性,有助于推动文献整理工作的开展以及文献学学科的完善,具有积极意义。
《中国文献学》的写作时代正是中国学术界欢呼进入“科学的春天”的时期,而此时的张先生已近古稀之年,硕果累累,享誉国学大师、史学大师、古典文献学的奠基者之称。其文献学思想已达到登峰造极的学术境界,体系构建亦显高屋建瓴之势。《中国文献学》体现出的思想更为宏伟壮阔,是以“国学”为底蕴,以“史学”为归宿的一部通人之学,称其为“经、史、子、集无所不包的国学即神州之学”亦不为过。[11]因此,这部著作在我国古典文献学领域达到了至高点,享受极高的地位和价值。
由上可知,两部著作各有千秋,不失为我国文献学领域的两部力作。但由于时代所限,两部著作均属于古典文献学的范围。两部著作的问世均是与两作者踏实的学风和刻苦钻研学问的精神分不开的。郑鹤声天生性情沉静,闲时便埋头于群书之中,昼夜苦读。张先生不仅是一代学术宗师,也是品行高尚的典范。他视学术为生命,不为名不为利,生命不息、著述不止,继承和发扬了中国知识分子固有的那种遗世独立的人格和献身学术的精神。他们的精神对我们现代的研究者将是一个极大的激励!
(本栏目责任编辑 宋雅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