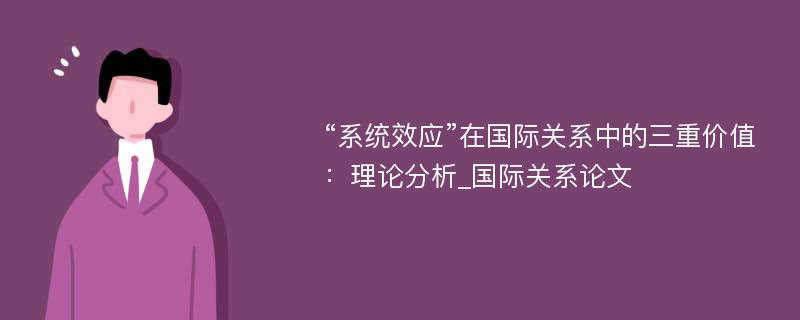
国际关系中“系统效应”的三重价值:一种理论的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际关系论文,效应论文,理论论文,价值论文,系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修订日期:2015-01-26 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8049(2015)04-0012-11 DOI:10.14015/j.cnki.1004-8049.2015.04.002 20世纪末以来,随着美国学者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出版《系统效应:政治与社会生活中的复杂性》一书,“系统效应”一词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国际关系分析中。同时,由于“系统效应”本身具备的强大解释力以及杰维斯自身享有的崇高学术地位,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倾向于接受这一理论,并尝试发掘其实践指导价值。①然而问题在于,“系统效应”是否真的那么美好?学界对它的理解是否已经足够透彻?“系统效应”能在多大程度上解释现实,又有多大能力去预测未来?它是否真的能够有效地指导实践? 通过对系统效应的分析,本文认为,挖掘“系统效应”实践价值的尝试是对其的一种误解,也是对理论所具备的三重价值——启示价值、解释价值和实践价值——的混淆。因此,本文将首先介绍国际关系理论的三重价值分析框架,然后简要评述“系统效应”的发展历程,依次阐明其启示价值、解释价值和实践价值,并得到相应的启示,包括如何在战略制定中应对“系统效应”和如何在理论上完善“系统效应”,以加深对其的理解。 一、国际关系理论的三重价值分析框架 对于国际关系学科而言,理论究竟应具备怎样的价值?或者说,理论到底应具备怎样的功能才能算作一个好的理论?本文所讨论的理论价值不是理论内蕴的价值(如秩序和正义等),②而是理论对实践的作用,也就是理论的功能。 詹姆斯·多尔蒂(James Dougherty)和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Robert Pfaltzgraff)将社会科学理论分为三种:历史描述理论、科学预测理论和思辨—规范理论。历史描述理论的功能是“寻求对过去和当前的事实概括”,科学预测理论的功能是“利用数学上的相互关系来指示未来的可能性”,思辨—规范理论的功能则是“用演绎方法推理改善世界的可能性和应该做的事”。③对国际关系学科来讲,这样的划分显然是有问题的,问题不在于划分的标准,而在于历史描述理论和思辨—规范理论能否被称为国际关系理论。对国际关系的历史还原和事实概括是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一项基本工作,对国际关系理论建构具有重要意义。④但从研究的基本内容来看,它显然是历史研究而非严格意义上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就思辨—规范理论来说,它所涉及的内容更多的是价值判断,即正义和秩序等问题。实际上,思辨—规范理论通常具有一定程度的国家属性,即被具体的国家利益绑架,⑤如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的霸权稳定论和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Keohane)的国际制度理论,前者有为美国霸权寻求合法性基础的色彩,⑥后者则有为美国霸权相对衰落后的出路进行战略谋划的嫌疑。⑦毫无疑问,这样的理论具有重大的价值。但这同时损害了理论的科学性,即理论对客观世界的普遍解释性遭到损害。这样看来,除了科学预测理论之外,多尔蒂和普法尔茨格拉夫两人眼中的其他两种理论都算不上真正科学的国际关系理论。进一步讲,它们对理论功能的理解不能适应理论的科学化发展。 对于科学预测理论,另一种广为接受的理论界定来自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Waltz)。⑧华尔兹首先区分了理论与规律,并强调理论的功能是用自身的概念和逻辑链条来解释规律。在华尔兹看来,理论的根本价值就在于解释现象或者规律。在华尔兹强大的影响下,理论的解释价值成为人们判断理论好坏的主要标准。 在华尔兹那里,“理论可能会帮助我们理解和说明现象和事件,但理论不是用于预测的有效工具”⑨。华尔兹的理论框架将理论与现实区分得如此明晰,认为“科学的进步标志就是对经验世界进行高度的抽象”⑩。也就是说,华尔兹的理论侧重点在于理论的抽象简约和解释规律,而忽视了理论的实践功能。 在同样的科学理论标准下,外交政策理论的出现正是为了弥补这一不足。以现实主义为例,新古典现实主义就是建立在结构现实主义解释功能基础之上的,前者通常将结构现实主义的某一理论抽象进行还原,并将之作为一个干预变量来解释并预测实践。(11)它在高度的抽象简约与低层次的经验事实中找到了一条理论建构的折中途径。实际上,外交政策理论追求的是理论的实践价值。也就是说,理论不仅要自圆其说,更重要的是能够指导和参与实践。自此,科学性理论的解释价值和实践价值逐渐成为人们思考和评判理论的主要模式。然而,解释价值和实践价值不是理论的全部功能,很多重要的理论,其价值在于启示后续的研究。本文认为,科学性的理论至少有三重价值,一是启示价值,二是解释价值,三是实践价值。 启示价值是指理论对相关研究的启发意义,如提供一种新的研究视角或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启示价值高的理论有利于综合、提炼或发现新的变量或思路来解释实践,高屋建瓴,为后续的研究提供分析框架,所以往往能直接刺激学科理论的发展。启示价值高的理论一般是多尔蒂和普法尔茨格拉夫所谓的宏观理论,(12)而建立在已有宏观理论框架下的中层或微观理论的启示价值一般是有限的。 在国际关系学科中,肯尼斯·华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理论就是高启示价值理论的典型。(13)结构现实主义以一个全新的视角来解释国际政治现实,直接促成了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分析方法——层次分析法的形成,并提供了一个新的分析框架。启示价值低的理论在国际关系理论中也很多,如奥根斯基(A.F.K.Organski)建立在摩根索经典现实主义理论框架上的权力转移理论以及属于同一框架中的均势理论。(14)需要注意的是,拼凑并不是综合,拼凑是将变量机械相加,综合则是有机融合。如法里德·扎卡里亚(Fareed Zakaria)将政权模式作为一个变量与国际结构拼凑在一起,提出了一套所谓政府中心型现实主义理论,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启发价值。(15) 解释价值是理论的核心价值。理论的基本任务就是解释研究对象,包括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对象(如将研究对象分层或分类)和明确对象的运行机理(如对象行为的归因)。理论解释价值的高低取决于其能多大程度以及多大范围地解释研究对象及其变化。如理论将研究对象分类,却忽视了某一部分或只重视某一类对象;又如理论对研究对象的行为进行归因,但归因不完整或只强调某一种因素,这样的区别都会使理论的解释价值存在高低之分。 在国际关系学科中,理论的解释价值一直是难题。首先,国际关系的研究对象一直在扩大。从成立之初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史到现在几乎囊括所有国家间事务,包括国家战略、大国关系(双边和多边关系、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关系)、地区关系、地区问题(如中东、北非、东亚、东欧等)、全球格局和全球问题(如裁军、导弹防御计划、核扩散、恐怖主义、联合国、人权等)。迄今为止,国际关系学科只能笼统地给出一个研究范围,其具体边界在不断变化,而理论通常无法自动适应这种变化,结果自然是理论的解释范围逐渐缩小。所以,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到现在,许多盛极一时的理论都被指责只能解释一部分现象,具有广泛解释力的理论很难出现。 其次,国际关系学界对本学科的理论要求越来越高。在华尔兹之前,国际关系学界对理论的要求不是特别严格和科学的。理论工作通常是列举现象、理清变量、归纳因果和得出结论,人们对理论的形式并无特别要求,所以那时的理论往往较为庞杂。华尔兹的最大功绩是使人们认识到,优秀的理论需要具备某种简约性,理论的简约性意味着自变量的减少和逻辑链条的清晰。同时,他还强调共时性,认为社会科学理论要像自然科学理论一样在不同时间(时代)都能解释实践。此外,在社会科学理论“科学化”的大趋势下,人们又开始要求量化分析。但是,对于社会科学尤其是国际关系来说,简约、共时、可量化的理论标准是非常高的。过度追求理论的高标准往往导致理论华而不实,陷入“只论主要不论次要,只看共时不看历时,只要数据不要判断”的极端,使理论的解释价值降低。华尔兹自己的结构现实主义理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最后,一个比较客观的原因是,国际关系学科仍处于爱德华·卡尔(Edward Carr)所谓的初生阶段。(16)初生阶段的学科往往具有理想主义情结,并且在理论上不能统一目标。虽然这种情况早已被人们深刻反思,但理想主义情结到现在仍然活跃,美国鼓吹的“民主和平论”就是显例。学科初生期,理论的目标也不一致,正如本文所区分的,有的追求启示价值,有的追求解释价值,有的追求实践价值。再加上国际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是一门显学,其实践指导价值往往十分重要,而国际关系研究的范围广、问题多,从而使更多的人去研究具体问题而不是基础理论。总之,学科大环境使国际关系理论难以具有较高的解释价值。 实践价值是指理论对相关实践的指导能力。实践价值的衡量标准是理论指导实践的效果如何,即实践能否根据该理论得到相应的结果。追求实践价值的理论一般能够给出“if A,then B”的直接因果关系,从而能直接指导国家的外交战略或政策。从这个意义上讲,外交政策理论更可能是实践价值高的理论,如均势理论。均势理论基本不具备多大的启示和解释价值,但它可以直接指导国家的外交战略,在过去的大部分时期也取得相当不错的实践效果。 在学科的发展过程中,不同的阶段需要不同价值的理论。在初生期,学科一般更需要启示价值和解释价值高的理论。这些理论为学科确定研究领域和提供基本的研究变量。在国际关系学科,摩根索的经典现实主义就是典型代表,他确定了“国家间政治”的研究领域,又提供了“权力”这一基本变量来分析这一领域。更有甚者,某些学科本身就是由一些启示价值高的理论创立的,如量子力学。当确定了研究领域和变量时,人们需要用这些变量来解释实践。在摩根索之后,奥根斯基的权力转移理论就是追求解释价值的代表。当一种解释价值高的理论出现时,一种相应的理论模式——即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所谓的理论范式(17)就出现了,学科因此进入成熟期。在成熟期,学科一般更需要实践价值高的理论。理论与实践是紧密相连的,理论的最终目的是服务于实践。学科成长期理论解释价值的高低直接决定了学科成熟期理论的实践价值高低。当成熟期的理论无力指导实践时,人们开始反思基本的研究领域和变量是否足够,学科的突变期——即库恩所谓科学革命时期——就此发生,大量启示性理论及其附属解释性理论将出现,学科呈现出前所未有的争论状态,直至一种广为接受的解释价值极高的理论出现,使学科再次进入成熟期。 准确地讲,与其他成熟的自然科学相比,目前国际关系理论处于最为关键的突变期。就目前而言,“国际关系理论发展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最明显的特征就是,不同研究方法之间关于理论发展的争论不断地重复和持续。我们看到的,是多种国际关系范式和理论同时存在并相互争论,而不是由一个公认为理论发展基础的范式代替另一个原来占支配地位的范式”(18)。按照本文的话语来讲,就是国际关系学科内部充斥着大量的启示性理论(或称为宏观理论、元理论、规范性理论)以及依附于它们的解释性理论(或称为微观理论、外交政策理论)。由于启示性理论质量不高,始终没有出现一种解释价值极高的理论来使学科进入成熟期从而能够指导实践,因此也基本没有实践价值高的理论。 需要注意的是,理论的三种价值没有高低之分,每一种都十分重要。在学科突变期,由于始终无法出现解释价值高的理论,人们往往认为解释价值是最重要的。就国际关系甚至所有社会科学学科而言,启示价值、解释价值与实践价值似乎处于对立的状态,这种现象值得注意。比如追求启示价值的理论往往需要强调新的视角或领域,所以可能相对忽视旧有的合理要素,容易导致其解释价值和实践价值降低;追求解释价值的理论,由于解释变量的庞杂而实践价值降低;追求实践价值的理论(如华尔兹所谓的外交政策理论),由于需要给出明确的因果关系而没有精力解释“why”。 二、系统效应的发展历程 系统思维是一种思维方式,它首先区别于人类历史上的两种主要思维方式——整体思维方式和还原思维方式。(19)在西方科学史上,古代的思维方式是整体论占优势,其方法是思辨的、逻辑的,但这种整体思维方式仅是一种直觉、原始、模糊的认识;近代的思维方式则是还原的,其特点是强调现象的划分及其组成部分,以定量方法描述现象之间的线性因果关系,但这种思维方式牺牲了对客观事物全貌的认识以换取对事物各个局部的分析,因此不能系统地把握对象,也不能从整体上统观全局。系统思维是对上述两种思维方式的继承发展,它根据系统概念和系统的性质、关系和结构,把对象有机地组织起来,研究系统的功能和行为,把重点放在分析事物整体的、综合的属性上,着重揭示其多样的联系、系统、结构和功能。系统思维的特点不仅是考察事物侧重点的转变,更是考察事物的方法。系统思维默认把部分联系起来研究,比对这些部分独立地进行研究更能揭示复杂事物的运动规律。 莫顿·卡普兰(Morton Kaplan)是第一位以系统思维来思考国际政治的国际关系学者。1957年,卡普兰出版了他的成名作《国际政治的系统与过程》,(20)并且再版至今。他在该书的序言部分指出,该书的灵感来源是一本控制论的代表性著作——《为大脑而设计》。(21)《为大脑而设计》的主要内容是对复杂生命体的适应性行为的分析。如果从一切细节出发,如从具体的经济过程、政治事件、文化地理、人口资源以及人们的心理性格特征出发,就等于是以无穷多的变化为起点来研究社会结构,正如从生物体的一个个神经元出发来理解生命的学习功能一样,问题会复杂得无从下手。罗斯·艾什比(Ross Ashby)开辟了一条全新的思路来解决这个问题:只要从结构上把握这类高级行为,那么原则上我们就可以用某种实体或效应来组成表现这一行为的机器。(22) 卡普兰对国际政治系统的研究方法和思路都来自于艾什比的研究方法。然而,卡普兰对系统中结构和功能的认识不够准确。他按照一体化程度来排列六种国际政治系统,也就是六种不同结构的系统,每种都具有自身的规则和特征,就好像一种结构决定一种规则特征一样,而规则特征则是系统功能的具体体现。卡普兰的逻辑似乎是结构决定功能,特定结构的系统有特定的功能。这样,在系统功能上,卡普兰就忽略了系统组成要素和系统环境这两大决定性因素,而只考虑了结构这一个变量。但是,卡普兰对系统本身的认识却是十分正确的,诚如他自己所说:“华尔兹提出的……是一个结构,但还构不成一个系统,因为它没有具体说明有关角色、能力、信息或者与平衡相一致的边界条件的规范性规则。我的理论,即使在三十年之后的今天,仍然是做到这一点的唯一理论。”(23)无论如何,卡普兰的理论正如他所希望的那样,“至少选择了一条适当的道路”。 肯尼斯·华尔兹是继卡普兰之后首先深入介绍并应用系统思维的著名国际政治学者。华尔兹认为,“我们可以尝试以与系统论和控制论的用法相一致的方式来构想政治系统”。于是,“系统就被定义为一系列互动的单元,从一个层次来说,系统包含一个结构……在另一个层次上,系统包含互动的单元”(24)。华尔兹将其称为系统方法,并清晰区分这两个层次,力图解释为什么即使个体行为随时间改变,而在系统中的行为却如此有规律。华尔兹认为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抛弃从国家层次即单元层次入手的幻想。其基本结论是,在国际政治中,行为体的行为随着结构的变化而变化,而不是根据自己属性的变化而变化。结构是系统中一系列约束条件,是系统中单元运转的原因,可以确定单元的形态,并最终使单元的运转产生某种性质相同的结果。 我们不妨用系统论的语言来表达华尔兹的思想:国际政治是一个大系统,国家是这个大系统下的子系统和行动单元。在国际层次上,国家的功能和行为主要取决于大系统,而不是国家本身。想要寻找国家的行为规律,则必须从大系统入手。大系统对国家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大系统的结构上,即系统的结构决定了系统中单元的行为规律。华尔兹对国家的简化则进一步体现了其系统思维。在华尔兹眼中,国家是同质的,并没有因为其国内官僚体制、意识形态、宗教信仰等不同而不同,因为华尔兹是依据国家在国际政治大系统中的功能和行为来定义国家的。在这个分析模式下,由于国家都具备谋求安全和权力的功能和行为,所以所有国家都是一样的。 可见,华尔兹对系统思维的应用比卡普兰要更加全面和深入。第一,华尔兹全面介绍了系统方法和与之相对应的还原方法。这是华尔兹为国际政治理论做出的最突出的贡献。他通过对若干还原主义国际政治经济理论的分析和对系统方法的介绍,指出并强调了国家行为规律的结构性因素的极端重要性。第二,华尔兹不仅用系统思维去看待国际政治系统,还指出了系统结构对行为单元的作用。相比于卡普兰对系统规则和运行方式的简单假想,华尔兹则进一步接近了其制定的理论要求。第三,华尔兹不仅视国际政治为系统,还视国家为系统。在一定意义上,华尔兹采用了功能模拟方法来研究国家。他并没有将国家还原为政府机构、高级官员、大众舆论等方面,而将国家按其统一的功能和行为归为同类行为体。这样,国家的重要性就彻底体现出来,其作为独立追求安全和权力的国际行为体就能够与其他国际行为体如国际组织、跨国公司等彻底区别开来。 虽然华尔兹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但他对系统思想的应用仍然存在不少问题。(25)其中最重要的问题是,华尔兹过于追求理论的简约、精确和抽象而忽视了政治与社会生活中的复杂性,也就是系统的非线性属性。而杰维斯的研究恰好能够证明这一点,那就是他的“系统效应”理论。 三、“系统效应”的三重价值分析 “系统效应”是杰维斯在交叉学科领域的研究成果。在国际关系学界,杰维斯是第一个注意到复杂性现象并对之进行系统思考的学者。他将系统科学中的复杂性原理引入国际关系研究,并将其命名为“系统效应”,这一说法也一直被沿用至今。系统效应的直接理论来源应该是复杂性科学,(26)而复杂性科学则是系统科学在20世纪70年代后的新成果,这或许是杰维斯将他观察到的“政治与社会生活中的复杂性”称为“系统效应”的原因。复杂性科学则以路德维希·冯·贝塔朗菲(Ludwig Von Bertalanffy)创立的一般系统论为源头,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逐渐发展为由耗散结构论、协同学、突变论和超循环理论构成的自组织理论以及包括混沌理论和孤立子理论等非线性科学在内的复杂性理论。复杂性科学虽然以有组织的复杂系统为初始研究对象,但它在研究复杂系统的运动规律时还关注其涌现性质(即整体特性),其主要研究方法是混沌理论、隐喻分析和后常规科学。(27) 无论如何,尽管复杂性科学的建模研究具有极大局限性,但作为定性分析的复杂性科学引起了国际关系界的强烈兴趣,直接原因可能是传统国际关系理论流派在20世纪末遭遇重大挫折,其解释力受到强烈质疑,人们不得不重新思考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路径。严格地讲,国际关系中的复杂性研究始于罗伯特·M.阿克塞尔罗德(Robert M.Axelrod)和托马斯·C.谢林(Thomas C.Schelling),(28)但直至杰维斯1997年出版其书,复杂性研究才开始真正进入国际关系领域。杰维斯认为,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存在一种系统效应,这种效应十分复杂并且往往不可预知。在这种复杂系统中,很少存在简单线性的因果关系,有目的行为产生的副作用很可能改变预定结果,也就是说,间接的、延迟的和非意图性的效应很可能使苦心经营的详细计划功亏一篑。杰维斯提出的国际政治系统效应颠覆性地挑战了传统由简单线性因果关系得来的国际关系认知。由于杰维斯的突出贡献,人们至少对复杂系统的性质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对于如何解决不确定性这一问题,杰维斯提出的方法是“多头并举”,也就是同时进行多个目标一致的行为以增大确定性。(29) 那么,对国际关系学科而言,“系统效应”的启示价值、解释价值和实践价值究竟如何呢? 首先,“系统效应”的启示价值是较高的。正如杰维斯所言,系统效应“能改变人们看待世界的方式,能够赋予他们一套概念工具,这样的工具能产生更出色的理解并导致更有效的行动”(30)。无论系统效应能否导致更有效的行动,它确实能够提供一种全新的视角来审视国际政治现实,并且它所提供的基本分析框架也能够较好地解释某些传统社会科学理论难以解释的现象,因此可以说它能使人们对国际政治产生更深刻的理解。《系统效应》一书中数以百计的翔实案例可以证明这一点。更为重要的是,系统效应将系统科学中的复杂性原理引入国际政治分析中,这种跨学科理论建构的意义重大。回顾过去数十年的国际政治理论研究,我们可以发现,卡普兰和华尔兹的理论尽管可能是有所缺漏的,但其提出的系统和结构的概念却始终激发着国际政治理论的不断创新和发展,他们所提出的理论的启示价值是有目共睹的。而杰维斯通过《系统效应》一书带给国际政治理论界的就是系统科学中的复杂性原理,更为准确地讲,是复杂性原理的定性分析。它所提供的思维方式有别于传统的线性因果分析模式,这种思维方式更加接近事件发生的真实过程。它将无法用传统理论囊括的政治社会现象在统一的话语体系中表达出来,并予以归纳和总结,从而形成了一种新的分析模式。这种创见性理论的启示价值是极高的,近两年基于复杂性原理的战略分析不断涌现足以证明这一点。(31) 其次,“系统效应”的解释价值是较高的。启示价值高的理论必然代表了某种正确性。对于系统效应而言,它的正确性主要在于其解释价值。对于事件,杰维斯指出了滞后、间接和非意图性的结果的重要性。对于互动,杰维斯强调了两个行为体之间的互动常常取决于它们各自与他者之间的互动,并且人们不能通过线性相加来理解互动。杰维斯这种对于事件结果和行为体互动的描述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因此也极具解释力。它的包容性在于对事件结果的界定并没有具体涉指,而仅限于一般描述。如“滞后”、“间接”和“非意图性”这些一般性描述使系统效应几乎可以囊括除了事件原始目的之外的所有事件结果。所以,分析任何业已发生的事件,我们都可以采用这一分析框架进行研究,而得出的结论往往都令人信服并耳目一新。如《理解国际安全战略中的“系统效应”》一文,作者利用系统效应的分析框架详细解读了中苏同盟破裂的直接与间接的、即时的与延迟的、意图性的和非意图性的结果,基本上完整地还原了这一事件的全面影响。(32)系统效应对于互动的分析也同样具有较高的解释价值。杰维斯对互动的理解首先建立在事物的普遍联系性之上,即双边关系通常不是由双边决定;其次建立在系统的涌现属性(即非线性属性)之上,即线性相加无法理解互动,这亦是我们所谓的整体性原则。事物的普遍联系性和整体性原则的正确性无需多讲,在这里只不过是换了一种话语体系表达出来。 最后,“系统效应”的实践价值不高。最关键的问题是,系统效应既然如此具有启发性,解释力又非常强,那么它是否能指导实践呢?它是否可以像杰维斯所声称的那样“导致更有效的行动”呢?答案是否定的,原因有三:第一,系统效应并没有提出人类或国家等行为体的行为规律。在杰维斯建构的话语体系中,并没有一个“if A,then B”之类的逻辑链条,也没有出现能够指导实践的因果关系。它只是提出了一些概念,指出了一些过去被学界忽视的现象。第二,杰维斯的理论分析框架有天生的不足。如上文所言,杰维斯对现象的归纳是一般描述性质的,其所反映的规律则是联系性和整体性两大基本辩证法原理。但这种对基本原理的反映很难直接指导现实行动。换言之,尽管滞后的、间接的、非意图性的效应可能非常重要,但人们在行动时却很难去考虑,因为这些效应太多并且相互之间的影响太复杂,而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即使按照杰维斯所言根据间接效应去制定战略,(33)但间接效应又会有其滞后的、间接的、非意图性的效应,那么是否需要继续考虑它们呢?如果考虑,就将陷入一个无穷死循环,战略决策者将无所适从。第三,杰维斯对系统科学诸多概念的理解出现了偏差。他以联系性和整体性来定义系统是对系统的极大误解。其实,系统思维也是一种还原,只不过它不是把对象还原为简单构成的堆积,而是还原为系统的功能和行为。传统还原论寻找对象共同的物质实体(如原子、分子等微观粒子),将之作为差异的共同基础;而系统思维则把对象相似或相同的功能和行为作为差异的共同基础。例如,把办公楼、教学楼、澡堂和食堂还原为砖头、混凝土和水泥确实能使人们把握这些建筑的特点,但却丧失了其最本质的差异——这些建筑的不同功能。(34)杰维斯对反馈的概念也存在误解。反馈是与系统的目的(功能)共生的。更为准确地讲,反馈是为系统目的(功能)服务的。在行为体达成某一目的的过程中,负反馈意味着这一目的完成不力,需要行为体调整(多则减,少则增),正反馈意味着这一行为的有效性。特定的负反馈和正反馈对应特定的目的。不谈行为体的目的而大谈特谈正负反馈是讨论跛子赛跑,毫无意义。 综上所述,“系统效应”的启示价值和解释价值都很高,但实践价值却比较有限。这与它的理论特性有关,也与它的理论缺陷有关。明确“系统效应”的三重价值构成十分必要,因为只有知道了“系统效应”在国际政治理论发展阶段中的地位和作用,才能更好地发挥其价值。 四、“系统效应”的应对与完善 上文明确了“系统效应”理论是国际关系学科在特定时间的产物,其启示价值和解释价值高而实践价值低。无论如何,它确实揭示了传统研究所忽视的一些现象,为了更好地利用系统效应,有必要对其应对措施和完善措施进行探讨。 (一)应对“系统效应” 有目的行为是人类行为的主体构成,是人类理性行动的基本要素。但“系统效应”所揭示的现象会对有目的行为形成一定干扰,正如杰维斯一直强调的,这种干扰极有可能至关重要。因此,如何应对“系统效应”是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相对于其他路径而言,较为成熟的系统科学是一个唾手可得的选择路径,它至少可以在理论上提供一些思路。在系统科学的话语体系中,“系统效应”所揭示的现象被统一称为系统的干扰源,即阻碍系统达成目的或行使功能的外界要素。那么,将系统科学的处理思路与传统战略学结合起来,本文提出三个可供选择的应对手段。 第一,战略权衡。对于国家战略而言,每一个战略行为都是要付出代价的。也就是说,战略上的全胜很难实现,而且一个阶段的全胜往往意味着下一阶段对手的更大报复,所以全胜也是不明智的。一个合理的战略选择必然意味着战略权衡。对于滞后的、间接的和可能发生的非意图性的效应,我们不应以之为基础去制定战略,因为它们自身就具有相当的不确定性,在战略上最合理的处理办法是比较它们与主要战略目的之间的重要性。以中苏同盟破裂一事为例,决定是否解除同盟的战略权衡在于充分比较所获得的国家和民族独立自主性与所失去的经济、地缘和其他方面的利益。也就是说,是否考虑系统效应的关键不在于它的可能性多大,而在于它是否足够重要。 第二,多管齐下。在明确了战略目标之后,战略制定过程中应保证多种、多重手段来达成战略目标,这就是所谓“多管齐下”战略。杰维斯将之解释为“利用约束系统动态并且同系统动态一同起作用的多元政策”(35)。也就是说,无论单一战略行为出现滞后、间接和非意图性结果的可能性如何,从概率论的角度,多个战略行为同时出现意外的可能性会降低。只要其中一个战略行为成功,就能达成基本的战略目标。所以,尽管“系统效应”确实存在并且难以控制,但如果想要保证战略目标尽可能地顺利达成,进行多种目标一致的战略行为是可取的战略选择。但需要注意的是,采用“多管齐下”战略会增加战略成本,这也需要权衡。 第三,信息反馈。在理论上,系统科学中的控制论是解决系统效应的直接有效手段。控制论中的反馈控制原理是在技术上解决系统效应的有力武器。一般而言,行为达成目标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行为体需要不断从目标处得到反馈,以便于下一步的判断。这种不间断的反馈能够最大程度地减小系统干扰源的影响。这里的反馈主要是从信息角度出发的。(36)整个反馈控制的过程就是信息的产生、保持、传递和接受的过程,每个控制环节是信息源的同时也是信息接收体,控制过程的进行和系统目标的达成都围绕信息来进行。因此,通信过程在整个反馈控制方法中起到核心作用,系统各环节之间良好的通信过程决定着系统的效率。也就是说,战略制定中应尽量保证反馈信息的对称、及时和准确。 (二)完善“系统效应” 就目前而言,我们根据“系统效应”进行的理论研究主要集中于复杂性科学本身,(37)鲜有涉及更为根本的系统思维层面;而战略研究(即实践价值的挖掘)则主要集中于借鉴其中的联系性(38)和整体性(39)。显然,这些零散的应用成果无法完整地体现“系统效应”的战略价值。 更为重要的是,一项基础性的工作至今仍未完成,那就是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系统思维进行全面的梳理与评述,这也是上述成果无法形成系统性思考的原因。如前文所述,杰维斯揭示的这种“社会与政治生活中的复杂性”的直接理论来源是复杂性科学,而复杂性科学的基础则在于20世纪中叶兴起的系统论,包括同为“老三论”的信息论和控制论。我们现在所重视的包括联系性和整体性在内的某些系统特质,其实是从系统论开始就一脉相承的。也就是说,“系统效应”中某些重要战略价值的根源其实是更广义的系统思维,而不是所谓复杂性科学。无论如何,要想进一步挖掘“系统效应”的战略价值并形成系统思考,应该首先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系统思维甚至包括更广义的作为一种科学哲学的系统思维进行全面的梳理和评述。只有这样,有关系统效应的战略研究才不会显得生搬硬套和人云亦云,才有可能更好地体现“系统”这一重要思维工具的战略意义。 理解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系统思维,应该从系统思维本身着手,而不是盲目地去比较它与其他方法或视角的优劣。系统思维对国际关系理论的影响是重大的,但人们通常从传统学派的视角去看待这种影响。到最近,又开始进行一系列的横向比较,试图去研究早前的科学行为主义与后来的经济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等学科对国际关系理论影响的优劣。(40)其最终的落脚点是从哪里去寻找“社会科学的牛顿理论”这一根本命题,但目前也尚未得到答案。但是,横向研究只能得出各种范式各有优劣的结论,只有将政治理论与其来源结合起来进行纵向研究,才能知道某一种范式到底有什么问题以及如何改进。有意思的是,人们在借用经济学和社会学的理论来分析政治问题时,通常会带来这些理论的特有假设(如经济学的理性假设),这自然使人感到理论水到渠成。但似乎没有人注意到,政治理论家特别是国际政治理论家在借用科学哲学的概念时,却没有带来其中的有益假设,其结论难免出现一些问题。在理解诸如结构现实主义等经典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系统思维时,如果不去深刻思考这些经典理论的思想和方法来源,而直接去批判或超越它们,只会事倍功半。只有认识到为什么那个时期的理论家以那样的方式思考问题,才能更好地理解为什么他们的理论不能或能够解释后来的客观事实。 (三)“系统效应”的实践出路 在一定程度上讲,杰维斯的“系统效应”理论是一个描述性理论,它指出了政治与社会生活甚或更为广义的人类世界中存在的复杂性。但是,如果“系统效应”理论想要进一步具备较高的实践价值,其出路恐怕还需借鉴系统科学的其他分支理论。其中,最为关键的可能是控制论。(41) 控制论和复杂性科学是一脉相承的。两者都是研究复杂系统的现代科学,都采用系统思维去认识世界,都认为复杂系统中的因果关系具有相当的不确定性。但是,对于国际关系学科而言,控制论在学科成熟程度、理论性质和不确定性的解决思路上都优于复杂性科学。 首先,控制论较复杂性科学更为成熟,其应用效果也更好。早在20世纪中期,控制论的研究成果就已迅速传播和应用,并激起了数学界、工程界、生物学界、心理学界、政治学界等学科的兴趣,还引发了一系列冠以控制论之名的交叉学科的创立和发展,如生物控制论、经济控制论和社会控制论等。(42)而复杂性科学是20世纪末期才逐渐发展起来的,无论是其本身还是拓展应用,都还仅是尝试性的成果。准确地说,其理论建模研究过于复杂,并脱离经验事实,因此模型的分析和应用价值极为有限。(43) 其次,控制论能直接适用于国际关系经验研究。虽然控制论也认识到人类世界的这种不确定性,但是它更倾向于如何解决这一不确定性,也就是利用负反馈,确保信息的准确及时来保证行为目的的顺利达成。“从这点出发,控制论就像博弈论一样,如果我们并不把控制论当做一种全面理论,而仅仅看作一系列观察复杂系统的视角,它就可能十分有用。”(44)其实,控制论本身就是一种工具性理论,为我们观察世界特别是复杂事物提供了更好的方法,在国际政治系统也尤其如此。 再次,控制论对不确定性的解决思路可能更有效。杰维斯认为,负反馈的效应可能由于信息的不准确和信息接收体的错误认知而失败,也可能由于相关的复杂影响而失败,因此反馈作用对解决不确定性的帮助十分有限。而控制论则认为假使有反馈行为失败,那也不会否定反馈本身的效应。复杂生命体和高级自控机器在反馈效应上的成功不容否定,人类有目的行为的顺利达成离不开这一共有规律。控制论强调,反馈的效应正是在于处理一些不确定的干扰因素,只要对预定结果的干扰能够在第一时间被行为体知晓并处理,有目的行为就有可能顺利达成。 最后,系统科学中最为成熟的部分仍是“老三论”——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由于包括卡普兰和沃尔兹在内的诸多国际政治学者在20世纪60—70年代的卓越贡献,国际政治学界对“老三论”并不陌生。比如,由于华尔兹对系统思维的极端强调,对现在的国际政治学者来说,结构并不是什么新奇事物。这些理论家为在国际政治领域全面系统地应用控制论思想体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本文提出了理论的三重价值评判标准,尽管这是一个初步的评判标准,但其有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理论的功能,从而将理论的价值最大化。通过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系统效应”理论进行三重价值评判,本文发现“系统效应”的启示价值和解释价值是较高的,却基本没有实践价值。也就是说,“系统效应”所提供的分析框架无法有效指导实践,利用“系统效应”进行战略制定,只能是无谋之略、无功之事。“系统效应”理论的未来首先在于指导人们如何去应对系统效应,然后在于完善自身的理论概念与框架。 曾亚勇:“国际关系中‘系统效应’的三重价值:一种理论的分析”,《太平洋学报》,2015年第4期,第12—22页。 ZENG Yayong,"Three Values of 'System Effect'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A Theoretical Analysis".Pacific Journal,Vol.23,No.4,2015,pp.12—22. ①唐世平、王凯、杨珊:“理解国际安全战略中的‘系统效应’——以中苏同盟破裂的多重影响为例”,《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8期,第4—20页。 ②这方面的讨论参见李开盛:“国际关系理论的价值透视”,《外交评论》,2006年第2期,第51—58页。 ③[美]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著,阎学通等译:《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世界知识出版社版,2013年版,第18页。 ④时殷弘:“关于国际关系的历史理解”,《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年第10期,第20—25页。 ⑤王义桅将国家属性视为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属性。参见王义桅:“为什么没有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1期,第21—22页。 ⑥Robert Gilpin,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 ⑦Robert Keohane,After Hegemony: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4. ⑧Kenneth N.Waltz,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The McGraw—Hill Companies,1979,pp.1—17. ⑨[美]罗伯特·基欧汉编,郭树勇译,秦亚青校:《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06页。 ⑩Kenneth Waltz,"Neorealism:Confusions and Criticisms",Journal of Politics and Society,Vol.XV,2004,http://www.columbia.edu/cu/helvidius/archives/2004_waltz.pdf. (11)Stephen Van Evera,"Primed for Peace:Europe after the Cold War",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15,No.3,Winter 1990/1991,pp.14—15;Randall Schweller,"Tripolarity and the Second World War",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Vol.37,No.1,March 1993,pp.73—103; Jack Snyder,"Introduction",in Robert Jervis and Jack Snyder,eds.,Dominoes and Bandwagons:Strategic Beliefs and Great Power Competition in the Eurasian Rimlan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1. (12)[美]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著,阎学通等译:《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世界知识出版社,2013年版,第18—19页。 (13)Kenneth N.Waltz,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The McGraw—Hill Companies,1979. (14)A.F.K Organski,World Politics,Knopf Press,1968. (15)[美]法里德·扎卡里亚著,门洪华等译:《从财富到权力》,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 (16)[英]爱德华·卡尔著,秦亚青译:《20年危机——国际关系研究导论》,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第6—8页。 (17)Thomas Kuhn,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2. (18)[美]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著,阎学通等译:《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世界知识出版社,2013年版,第652页。 (16)[英]爱德华·卡尔著,秦亚青译:《20年危机——国际关系研究导论》,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第6—8页。 (17)Thomas Kuhn,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2. (18)[美]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著,阎学通等译:《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世界知识出版社,2013年版,第652页。 (19)刘永振和傅平将这两种思维精辟地概括为古代模糊性笼统思维和近代精确性分析思维,以区别于现代系统性整体思维。参见刘永振、傅平:“系统思维方式的哲学探讨”,载魏宏森主编:《系统理论及其哲学思考》,清华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56页。 (20)Morton A.Kaplan,System and Proces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John Wiley and Sons,1957. (21)[美]莫顿·卡普兰著,薄智跃译:《国际政治的系统和过程》,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2005年版作者序。 (22)[美]罗斯·艾什比著,乐秀成等译:《大脑设计:适应性行为的起源》,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iv页。 (23)同(21),1989年中文版序,第19页。 (24)[美]肯尼思·华尔兹著,信强译,苏长和校:《国际政治理论》,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年版,第42页。 (25)黄真、曾亚勇:“国际关系结构主义理论的控制论透视”,《教学与研究》,2012年第9期,第81—83页。 (26)虽然杰维斯说《系统效应》一书并没有简单和直接的来源,但书中所使用的话语体系(如系统和反馈等)显然来自于系统科学和复杂性科学。参见[美]罗伯特·杰维斯著,李少军等译:《系统效应:政治与社会生活中的复杂性》,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中文版序,第Ⅲ页。 (27)刘慧著:《复杂系统与世界政治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96—107页。 (28)Robert M.Axelrod,The Complexity of Cooperation:Agent-Based Models of Competition and Collaborati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7; Thomas C.Schelling,The Strategy of Conflict,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0. (29)[美]罗伯特·杰维斯著,李少军等译:《系统效应:政治与社会生活中的复杂性》,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30页。 (30)同②,中文版序第I页。 (31)王帆:“如何认识当今世界?——复杂系统观的启示”,《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年第10期,第41—50页;王帆:“复杂系统思维的整体观与中国外交战略规划”,《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9期,第145—154页。 (32)唐世平、王凯、杨珊:“理解国际安全战略中的‘系统效应’——以中苏同盟破裂的多重影响为例”,《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8期,第4—20页。 (33)[美]罗伯特·杰维斯著,李少军等译:《系统效应:政治与社会生活中的复杂性》,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5、321—329页。 (34)[美]E.拉菲洛著,闵家胤译:《用系统论的观点看世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 (35)[美]罗伯特·杰维斯著,李少军等译:《系统效应:政治与社会生活中的复杂性》,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5、329页。 (36)王雨田主编:《控制论、信息论、系统科学与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66页。 (37)王帆:“如何认识当今世界?——复杂系统观的启示”,《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年第10期,第41—50页;刘慧著:《复杂系统与世界政治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38)唐世平、王凯、杨珊:“理解国际安全战略中的‘系统效应’——以中苏同盟破裂的多重影响为例”,《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8期,第4—20页。 (39)王帆:“复杂系统思维的整体观与中国外交战略规划”,《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9期,第145—154页。 (40)David Easton,"The Current Meaning of 'Behavioralism'",in James C.Charlesworth,ed.,The Limits of Behavioralism in Political Science,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1962,pp.1-25; Thomas Spragens,The Dilemma of Contemporary Political Theory:Toward a Post-behavioral Science of Politics,Dunellen,1973; John C.Wahlke,"Pre-Behavioralism in Political Science",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73,No.1,Mar.1979,pp.9-31; John G.Gunnell,"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Liberalism,and the Invention of Political Theory",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82,No.I,Mar.1988,pp.71-87; John G.Gunnell,"The Real Revolution in Political Science",Political Science and Politics,Vol.37,No.1,Jan.2004,pp.47-50; Jon R.Bond,"The Scientification of the Study of Politics:Some Observations on the Behavioral Evolution in Political Science",The Journal of Politics,Vol.69,No.4,Nov.2007,pp.897-907. (41)对控制论的基本介绍,参见黄真、曾亚勇:“国际关系结构主义理论的控制论透视”,《教学与研究》,2012年第9期,第81页。 (42)参见Dechen,The Social Impact of Cybernetics,Simon and Schuster,1966;彭永东著:《控制论的发生与传播研究》,山西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 (43)刘慧著:《复杂系统与世界政治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22、231页。 (44)Robert Lieber,Theory and World Politics,Winthrop Publishers,1972,p.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