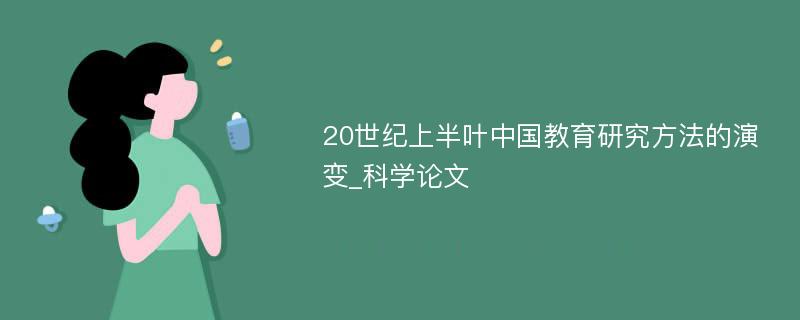
20世纪上半期中国教育研究方法之演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教育论文,方法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类号]G40-0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597(2001)04-0065-04
关于教育研究方法的认识,我国迄今为止主要存在三个层次:一是“教育研究—方法—论”,其意为有关一种具体的研究活动的方法的理论;二是“教育—研究方法—论”,它强调的是研究教育这一特殊对象时所采用的方法的理论;三是“教育研究—方法论”,它侧重于“方法论”在教育研究中的特殊应用与体现,属于方法论的“特化研究”[1](p2)。本文把20世纪上半期我国的教育研究方法定位于第二个层次,通过对一些典型教育家及其教育思想的剖析和梳理,透视近代中国教育研究方法的演进过程。
一、从古代“独居深思”、“述而不作”到近代“沿袭陈法”、“仪型他国”
“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2](p11)。作为观念形态之一的教育研究方法固然受到时代政治经济的制约和思想文化的影响,同时由于教育本身具有人为性、历史性、社会性,所以教育研究与哲学有着更为密切的联系。哲学在理论和思维方法两个方面对教育研究具有方法论意义,它的主题及其研究成果直接构成教育研究的前提性认识,对教育研究具有基础性作用;它关于人与社会发展的价值取向直接影响教育的价值取向,对教育研究具有定向作用;它提出的思想方法及对思维等认知方式的研究,对教育研究的思想方法同样具有战略性指导意义。
在我国古代,封建君主专制的政治体制和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使得以伦理为本位的儒家思想在文化教育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儒家在哲学上强调“天人合一”、政教统一、文道结合、知行一致,结果导致以直觉思维代替了科学实证,以道德实践代替了生产实践。这种思维方式和实践方法渗透到教育中来,便演绎为“述而不作”的研究方法。“述而不作”是中国古代教育研究的基本特征,它在理论上“重在独居深思,重在深思明辨,把自己的思想与古人的思想比较,取他人之长,以补充推证自己的学问,而建立自己的思想系统”[3](p125),在实践中基本采用“六经注我,我注六经”的办法进行教育研究。这就是陶行知所说的“吾国数千年来,相传不绝之方法”,即“致知在格物”[4](p60)。实际上,格物致知大都孕育在哲学、政治、伦理思想之中,带有经验概括的性质;其论述方式多是“谚语”、“格言”,大量原则、方法仍然停留在感性的经验归纳阶段,缺乏必要的论证。
20世纪初期,近代中国教育研究方法发生了第一次重大变化,从古代“独居深思”、“述而不作”,演进到既“沿袭陈法”,又“仪型他国”。发生这种变化的原因除了中国由封建社会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之外,更重要的是,以往处于独尊地位的儒家哲学受到了西方科学思想的冲击,教育的指导思想代之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体西用”的根本特征在于以旧学为主,以新学为用;不改中学之旧,仅增西学之新。尽管它在哲学上仍然属于中国古代传统的体用说,但它背离了“体用不二”的原则,冲破了长期以来儒学教育只讲“中学”的樊笼,为传统教育打开了一扇吸收新学气息的天窗。因此,这时期的中国教育研究方法不但采用古代格物致知的方法,更重视引进主要是德国赫尔巴特及其学派的教育研究方法,对赫尔巴特由目的而手段的研究思路,尤其是赫尔巴特学派的“五段教学法”几乎是吸收无遗。应该肯定,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的确是难能可贵的。毕竟中国传统文化经历了数千年,由孔子开创的“述而不作”的研究方法,长期占据了中国教育的研究领域,并且与儒家独尊地位相应地控制着研究的主潮。因此,能够打破这种垄断局面,引进西方较为先进的教育研究方法,无疑是近代中国教育研究的一大进步。
必须指出的是,“沿袭陈法”和“仪型他国”并行的现象将近20年,其弊端也渐渐地显露出来,甚至日趋严重。当时的情况正像陶行知所言:“吾国办学十余年,形式上虽不无可观,而教育进化之根本方法,则无人过问。故拘于古法,而徒仍旧贯者有之;慕于新奇,而专事仪型者有之。”[4](p62)“沿袭陈法”主要表现在“彼泥古之人以仍旧贯为能事。行一事,措一词,必求先例。有例可援,虽害不向;无例可援,虽善不行”。[4](p93)“仪型他国”则表现为那些“号称新人物者,辄以仪型外国制度为能事”[4](p94),“忽而学日本,忽而学德国,忽而学法国、美国”[4](p122)。面对如此状况,一些教育家提出要用审视的态度来对待中西文化教育及其研究方法。陶行知严厉地批评那些“仪型者”的盲目引进,说他们“或出于误会,以误相传,为害非浅”[4](p94),弄得中国的教育研究“终究是无所适从”[4](p122)。认为“今昔时势不同,问题亦异”,“方法当殊”[4](p93),主张改变“沿袭陈法”和“仪型他国”的研究方法。在《我们对于新学制草案应持之态度》一文中,他明确指出:“我们应当用科学的方法态度,考察社会个人之需要能力,和各种生活事业必不可少之基础准备”,“至于外国的经验,如有适用的,采取他;如有不适用的,就回避他。本国以前的经验,如有适用的,就保存他;如不适用,就除掉他。去与取,只问适不适,不问新与旧”。[4](p191)陶行知的这一论述,为我国教育研究方法的再改造提供了理论基础。
二、从20世纪初期的“盲从”研究到20年代的“试验”研究
进入20年代,中国教育研究方法发生了重大转变,即从“盲从”研究转为“试验”研究。这次转变与民主共和政体最终代替了封建帝制,“民主”与“科学”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的主流是密切相关的,也同当时世界教育研究领域刮起的两股强劲风有着重要联系。这两股强劲风,即是杜威以实用主义为哲学基础的教育理论上的哥白尼式革命和西方以实证主义为哲学基础、以自然科学研究方法为范式的研究方法实证化运动。两股风经过杜威等美国学者的来华讲学,以及胡适、陶行知等留美学生的广泛宣传,在中国盛极一时,有力地冲击了近代形成的教育研究传统。当时,中国教育学界一方面重视介绍西方教育研究状态和研究方法,另一方面开始反思以往“盲从”的研究。他们发现“沿袭陈法”和“仪型他国”的研究方法主要以四种方式出现:一是“以古进今”;二是“依外国的方法”;三是“闭门空想”;四是“不依古,也不依外,是以不了了之”[4](p291)。因为两种错误倾向的原因主要在于缺乏试验,所以这四种方式,无论哪一种都不能解决中国的教育问题。因此,他们在批判“盲从”研究的基础上,构建起以“去与取,只问适不适,不问新与旧”为指导思想,以“试验”为核心内容的科学研究方法。
陶行知是这一时期“试验”研究的杰出代表。他在1918~1923年间,先后发表《试验主义之教育方法》、《教育研究法》、《教育与科学方法》等文章,系统地论述了试验主义的研究方法。陶行知首先强调“试验”研究的重要性。认为试验研究不仅关系到教育革新的成败,而且关系到国家的生死存亡。他说:“欲教育之刷新,非实行试验方法不为功”,“非试验的教育方法,不足以达救国之目的也”。[4](p62)接着,陶行知提出了研究的依据。他认为,“教育之举措,悉当根据学理”;只有“学理幽深”,才能“研究始明”;要求教育理论家和实践家应当以科学的理论和研究方法指导教育研究,使研究活动符合教育的客观规律,这样才能“庶南辕无北辙之虞”[4](p66)。在研究方法中,陶行知特别强调行动的作用,认为试验方法最要之点就是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能力和实践能力。他说:“杜威先生所叙述的过程是单极电路,通不出电流。他没有提及那思想的老祖宗。这位老祖宗便是行动。”“所以我要提出的修正是在困难之前加一行动之步骤。”[5](p361)在如何使试验方法的运用能收到成效的问题上,陶行知还提出了三点要求:一要有关方面的知识素养;二要有关方面的才能;三要有坚强的毅力。由此可见,陶行知在20年代的“试验”研究方法,一方面反映了王阳明“知行合一”的学说,另一方面又体现了杜威关于注重行动,加强知与行,理论联系实际,以及注重科学方法,以科学方法办教育的思想。这些方法尽管尚有种种缺憾,但对近代中国教育研究方法来说,却有着重大的意义。从此以后,人们从传统“盲从”的研究转到“试验”的研究。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人们在研究教育问题时注意到三个方面:一是注意虚心讨论,研究,实验,力求面面顾到;二是注意明辨择善,不舍己从人,轻于吸收;三是注意反思,回头总结经验教训。
对于近代中国教育研究从“盲从”到“试验”的转变,雷沛鸿曾作了精辟的总结。他说,到20年代之后,教育研究工作“除了静态思辨工夫,还注重现实环境的调查、观察、实验”[3](p125)。研究工作“倾向于群的活动,倾向于大众化,倾向于平凡化,倾向于实际化”[3](p126)。雷沛鸿把这一时期的研究方法归纳为三种:一种是“从历史的远景,追溯这个教育制度在历史上的演进,而从事于搜集资料,辨别问题”的“历史方法”;另一种是“从现实社会中应用社会科学原理教育学原理,推究这教育制度在生长时所必须具备的社会条件”的“社会学方法”;还有一种是“务期室内研究工作与室外园地垦辟工作相互联系,以求理论与实际问题,均得满意的解决”的“观察方法实验方法”[3](p255)。
这一时期,除了陶行知和雷沛鸿的上述见解外,俞子夷也对教育研究方法展开了论述。1922年,俞子夷在《小学教员该注重理论,还是注重经验?》一文中,论述了理论和经验的关系。他认为,“理论有可靠的,也有不可靠的。从科学方法研究得来的结果是可靠的,凭空臆造的议论是不可靠的”,“理论决不能代替经验;然而理论却可以做经验的指导”,主张教育研究要“拿可靠的做标准”,“最好要把学习的理论和自己的经验化成一起”。[6](p49~50)
总之,20世纪二三十年代,试验主义的科学研究方法比起初期的“沿袭陈法”或“仪型他国”显然更加进步了。它否定主观臆造、向壁虚构之弊端,将教育研究对象转向实理、实事、实际生活;它否定以圣言、圣教作为立论根据的陋习,主张任何教育理论、方法都必须接受怀疑、质问;它纠正了只重理论演绎不重实行的偏颇,将教育从单纯的理论研究延伸到实践探索;它还超越了事实性描述,更关注教育研究的功利价值。这种科学研究方法应用到中国的教育实践上,很快显示了它旺盛的生命力。在陶行知、俞子夷等人倡导的教育研究方法影响下产生的“壬戌学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壬戌学制克服了“壬子癸丑学制”的“过重划一”等种种弊端,表现出高度的灵活性和弹性,使之更加适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和需要,成为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实施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一个学制。
三、从试验主义的科学之方再到40年代的辩证唯物主义方法
到40年代,我国的教育研究方法再次发生重大的突破。教育研究者沿着20年代试验主义的科学之方,一方面积极投身于中国的教育实践活动,另一方面对从西方引进来的试验方法不断进行理性的思考,同时更加注意从苏联引进并吸收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因此,在对近代中国教育改造的同时,教育研究方法也随之改变。它不仅在认识论上实现了从唯心主义的经验论到唯物主义实践论的转变,而且在方法论上也由试验主义的科学之方演进到实事求是的辩证唯物主义方法。
陶行知是这一转变的典型代表之一。他从杜威手中接过试验的研究方法,并将它赋予中国化的特色,又通过生活教育实践不断予以改造。到30年代,陶行知在认识论上先由相信“知行”到坚信“行知”的转变,然后又由“行知”向“行知行”转变。到40年代,陶行知的思想已经基本达到了辩证唯物主义的高度,而且在实践中并能以此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来指导自己的教育活动。1943年,他在《创造年献诗》中指出,“以为武断靠不住,存在从来决意识”,这表明他承认“存在决定意识”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命题,认为存在是第一性的,意识是第二性的。他又说,“矛盾相生复相克,数量满盈能变质”[7](p586),这说明他不仅看到了事物内部存在矛盾,而且认识到矛盾促进着事物的发展变化;还看到了数量达到饱和之后就会引起质变。由于认识论的发展,陶行知能够用辩证唯物主义实践论解决了教育哲学的几对基本范畴,即行与知、劳力与劳心、做与教和做与学、生活与教育、社会与学校的关系问题。对于陶行知的这一转变,徐特立说他是“从实用主义翻过来变成实践论”[8]。
雷沛鸿在1946年发表的《“实事求是”的再估价》,也体现了近代中国教育研究方法从试验主义的科学之方到辩证唯物主义方法的转变。他用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观点对“实事求是”进行估价,认为所谓“实”就是科学的事实,所谓“是”就是科学的真理。实事求是“就是运用科学的实验方法、观察方法、统计方法等,去作实事求是的实践,求取科学真理”[3](p352)。雷沛鸿作这样的阐述分析,与以往把“实事求是”看作是“中国人做人做事的一种经验”相比,更具有现代科学的进步性。同时,从概念“试验”到“实践”的变化,也反映了教育研究方法重心的变化,即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的演进。比如20年代的“统计方法”主要用在自然科学的研究,在教育上只是使用数据进行简单的统计和排列,到40年代,统计方法“就被运用于社会科学,把许多事实加以搜集、统计、排比,从而分析其因果关系,诠释其可能趋向,而求取科学真理”[3](p352)。
40年代我国教育研究方法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在徐特立和俞子夷身上有着更为集中的反映。早在1940年,徐特立就明确提出用辩证唯物论的方法来研究科学,包括教育科学。他指出:“研究科学不是凭空创造,所以需要实践和学习,同时要吸收过去人类历史的科学遗产”,“要把教条化的、神秘化、庸俗化的科学转化为辩证唯物论的科学”[9](p85~86)。1949年徐特立还进一步提出,“必须把握住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与观点,解决某一范围内的具体的特殊的问题”,主张“学术的研究必须从材料的搜集、整理、分析出发”,“对于旧的文化遗产我们应该批判地接受而不能一笔抹煞”[9](p180~183)。俞子夷则从自己的切身体验,以及对唯物史观的学习中,提高了对辩证法和实践论的思想方法的认识,所以“在算术上反对了唯心论和机械论”。徐特立赞扬俞子夷“在中国教育界有极大的贡献”[9](p110)。也正因为这样,俞子夷在1844年发表《教育上全体与部分的关系》一文,具有系统论思想,其中包含着辩证法的因素。俞子夷在文中批评了教育上“全体等于部分的和”的机械论,结合教育中许多事例分析了全体与部分的辩证的关系。他认为,“全体等于部分的和”,只不过是一种数量方面的关系。凡是全体的事物现象,各部分间除数量关系外,还有空间关系,热量关系,电荷关系等。各部组成全体,最重要的是关系。“没有合理的关系,部分决不能组成全体”;“只有部分,不成全体。各部分不发生关系,决不能成功全体”;“但是我们的教育方法却只教了部分,竟把组织全体最主要的关系完全搁置不理”[6](p393~396)。
总而言之,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教育研究方法是随着西方教育研究方法的引进,并在陶行知、俞子夷、雷沛鸿、徐特立等教育家不断吸收、实践、改造的基础上,实现了一次又一次的飞跃。这50年的历史演变,既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经验,也蕴藏着深刻的教训,还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启示。笔者认为,至少有以下几点是值得我们今后要关注的:1.教育研究要与一个国家社会状况和个人生命状况相联系。中国近代教育家的一条成功经验就是,他们不是简单地移植西方当时流行的实证型的研究方法,而是围绕教育与社会改造的核心,积极地展开大规模的社会调查,建立实验区或试验点,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以探索性、改革型的实践为主的研究之路。2.教育研究只有对本国的教育传统作应有的提炼与升华,才能使民族精神在研究方法的演进中得以弘扬,否则就会导致“中断”。3.教育研究要重视对理论与方法本身的关注,对外引的研究方法的本意以及在中国实行的可能性要深刻地领会和作批判性的思考。4.要对教育研究方法“价值中立”问题进行具体分析,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理论研究的独立性和深刻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