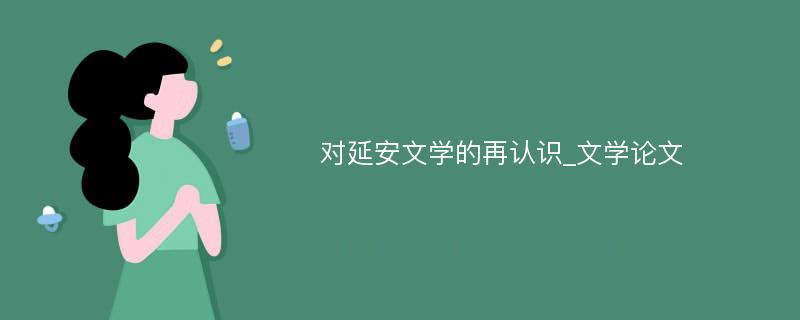
重新理解延安文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延安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3926(2006)05—0088—06
现代中国左翼文学在中国与世界相呼应的激进政治文化思潮的裹挟下曾经创制了自己的文学形象,绘制了自己的文学地图。由于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剧烈变迁的原因,也由于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本身善于依附主流意识形态从而亦善于见风使舵的奴性品格的持久存在,左翼文学在研究者那里也经历了一番惊天动地的价值性变迁,不是被捧之上天,就是被按之入地。尤其对延安文学的评价更是如此。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人们对左翼文学表现了一种较为浓厚的研究兴趣,也因之对现代中国左翼文学发展之独异一脉的延安文学表现了这样那样的关注,人们在力图进入延安文学形成与发展的历史中理解延安文学,力图借助这样或那样较为新潮的文化研究与批判理论去诠释延安文学,这些努力也曾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是,毋庸讳言,在现代中国左翼文学乃至现代中国文学研究中,延安文学仍然是目前研究得最为薄弱的一片学术领地,在这方面,似乎只有文革文学研究可与之相比拟。因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认为,现代文学研究界应该重返延安文学场域,对延安文学做出一些较为符合历史本真的梳理,在重新勾勒延安文学总体面貌的同时,力求对延安文学有所全新的理解,并由此对现代中国左翼文学乃至现代中国文学的总体性构成形成一种新的理解。
一、“延安文学”的命名
我想首先考论一下“延安文学”的命名。倘若从延安文学生产的体制化过程及其意识形态本性来看,从它所隶属的革命大众文艺之一端来看,延安文学当然可以被置换为具有更大内涵和外延的延安文艺。“延安文艺”从字面上说当来源于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但它是指称在延安召开的革命文艺工作座谈会,而非指称作为革命文艺本身的延安文艺。何其芳在谈到“鲁艺”(鲁迅艺术文学院)于文艺整风后应该开设的文学教育课程时曾说:“应有专课经常研究文艺现状,其内容应包括对于抗战当中大后方和目前延安及其他根据地的文艺作品,文艺问题,文艺活动的研究。”[1] 何其芳在此其实已经提到了延安的文艺,而这,正是“延安文艺”这个概念即将呼之欲出的前奏。1946年8月23日, 全国文艺界协会延安分会和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以“延安文艺社”的名义刊出了一篇表明即将创办《延安文艺》杂志的文稿,号召延安文艺工作者和文艺爱好者“用大众作风,大众气派”来写“延安,陕甘宁边区的人民生活,写人民的生产、政权和武装,写人民各种各样的斗争和创造。”并且解释说,“这刊物叫《延安文艺》,就是我们有决心要照毛主席‘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的精神,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加倍的努力往前做去。”[2] 该刊最终虽没能出版,但它在此明确提出了“延安文艺”这一文艺性概念,而且从写什么和怎么写两方面凸现了延安文艺的意识形态本性,所以值得注意。有人说,延安文艺或延安文学这个名称的正式提出“应是1984年《延安文艺丛书》的出版以及这一年年底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延安文艺研究》的创刊”,[3] 我认为这显然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因为如上所述,“延安文艺”的名称应该说源起于延安时期。在延安文人眼里,延安文艺无疑是指发生在延安以及陕甘宁边区的文艺运动与文艺作品,显然,这是一种狭义的理解。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延安文艺的理解日渐呈现出广义的色彩。1980年代中期,丁玲、贺敬之等老延安文人曾经率先对延安文艺进行了广义的理解。丁玲说,“延安文艺是抗战时期,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直接关怀和正确领导之下,向人民学习,和人民一起共同斗争的结果,是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它不仅仅局限于延安地区,局限于抗战时期。我们不能把它看小了,看窄了。”[4] 贺敬之也提出了跟丁玲相类似的看法,而且还参照中国文学史上的“建安文学”阐述了构建“延安文艺学”的主张。在谈及延安文学史上的作家时,他跟丁玲一样都是把整个根据地和解放区的作家含括其中,并不局限于延安及陕甘宁边区。[5] 显然,这是一种广义的理解,延安文艺(文学)也就与沿用至今的解放区文艺(文学)这个概念在内涵和外延上相当或平行了。众所周知,解放区文艺(文学)在文学研究史上源起于周扬在第一次文代会上所作的报告《新的人民的文艺》,是一个为学界普遍使用的概念。那么,丁玲、贺敬之等人为何又想以“延安文艺”这个概念去取代它呢?对此,原左联作家林焕平在1992年做了清楚说明。他认为,延安文学“从整体上说来,就是在延安思想指导下,表现以延安为中心的解放区的那个历史时期的革命与战争的生活”的文学,所谓延安思想,就是指毛泽东思想。又说,“延安文学所体现的文艺观,就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文艺观,它突出地体现在毛主席的代表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里。”而且,由革命事业总体上说,“从红军到达陕北,建立陕北根据地到全国解放,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革命都是以延安为政治中心、思想中心和指挥中心。”因此,他明确指出有必要把“解放区文学”更名为“延安文学”,在他看来,后者较前者更能准确体现延安时期此类文学的“政治思想性”,即此种文学的政治意识形态属性。[6] 应该说,林焕平的看法是有一定道理的,而且,说延安文学较解放区文学更能体现其本身所内含的意识形态属性,更是显得准确而犀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本文赞同“延安文学”的广义说法。但是,如果我们真要把探究延安文学意识形态化的形成作为延安文学研究的重要出发点的话,那么,由于论述对象的特别限定,自可在选用“延安文学”这个概念时偏重于对之作狭义的理解,即主要论述以延安及陕甘宁边区为中心的延安文学,或许唯有如此,涉及延安文学的某些根本性问题才会研究得更加清楚。
我们把延安文学作为现代中国文学中的一支重要流脉加以研究,自然应该在文学史意义上对其起止的上下限时间做一界定。一般而言,人们把延安文学的下限大体设定在1949年7月第一次全国文代会的召开,而不是划到1947年3月中共中央机关撤离延安,在我看来,这是易于为大家所认可的。较有争议的是它的上限。有研究者把它的上限设定在中共中央率领工农红军到达陕北的1935年10月,也有研究者把它设定在中共中央进驻延安的1937年1月,更有研究者由于认为此前的苏区文学是延安文学的先导和源头,所以甚至主张把它的上限设定在苏区文学时期。我认为,延安文学史形成的开端自有其富有标志性的文学事件存在,这个事件乃是“中国文艺协会”于1936年11月22日在陕北保安的成立。因此,延安文学的上限应该设定在这里。之所以如此,是由于中国文艺协会的成立是中共文艺史上的重要事件。其重要性主要表现在:它是由刚刚奔赴保安的左联作家丁玲等人与原苏区作家李伯钊等人共同发起成立的,并且得到毛泽东、洛甫、博古等中央领导的大力支持与充分肯定。它的成立表征着左联作家与苏区作家在新的历史阶段的汇合的开始,表征着中共中央在新的历史时空对文艺等意识形态领域予以构建的开始,正因如此,毛泽东才会极力称誉它的成立“是近十年来苏维埃运动的创举”。[7] 自此之后,延安时期的文学发展才可以说终于走向了一个新的自觉阶段。因此,本文认为延安文学的上限应该主要设定在1936年11月,而下限自可设定在1949年7月。 此种文学既是指延安文人创作的文学,也是指一种广泛意义上的大众文艺运动,因为自文艺整风后,延安文学活动的开展在本质上与其说是一场文学运动,毋宁说是一场富有宣传鼓动性的政治文化运动来得更为恰切。整风之后的延安文艺在那贫瘠的黄土高原上终于亘古未有地发挥了大众文艺的神奇力量,曾经默默出生又默默枯死的陕北农民在延安文艺运动的搅动下终于被发动、组织起来,因之也就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新的意识形态启蒙。在我看来,倘若人们真把那种狭义的延安文学理解透了,那么在意识形态本性上自可借此去理解广义的延安文学,而且,愈是接近文艺整风后的延安文学发展阶段,其情形更是如此。
二、延安文学的性质
延安文学是一种历史性存在物, 是一种经历了较大自我嬗变的文学形态, 以1942年夏季开始的延安文艺整风为界,大体上可分为前后两期。1949年7月,周扬在第一次文代会上指出:“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规定了新中国的文艺的方向,解放区文艺工作者自觉地坚决地实践了这个方向,并以自己的全部经验证明了这个方向的完全正确,深信除此之外再没有第二个方向了,如果有,那就是错误的方向。”[8] 这表明,延安文学所代表的方向最终被规定为传统学科意义上的“当代文学”的新方向,延安文学也终于由党的文学或党派文学转换为一种新的民族——国家型文学。显然,这里的延安文学并非是指前期延安文学,而是指文艺整风后产生并发展起来的后期延安文学。在当代文学的一元化过程中,成为其直接理论来源和文学资源的乃是后期延安文学,这在1950年代经历对丁玲、萧军等人的“再批判”之后表现得更其明显。
我在这里想探讨的其实就是这个后期延安文学的性质。如上所述,后期延安文学是在文艺整风的语境中逐渐型构而成的一种文学形态,它的实践形态及其后所产生的文本内在地决定于它所依附的一种意识形态话语,这就是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话语。因而,探讨后期延安文学的性质在首先应该明了延安文学观念的性质。而从文学观念的发展嬗变来说,延安文学的历史无疑呈现了它的复杂性,这主要体现在它的艺术观念和审美形态的形成均经历了一个较为复杂的动态过程。我认为,在延安文学观念的演变过程中,民族主义是一个贯穿其发展始终的重要因素,但它在前期更多地倾向于一种为国共两党都能接受的较为普泛的民族主义,这在延安文化界倡导的“民族形式”论争中得以充分地表现出来,在理论形态上形成了一种较为开放的以民族——现代性为内涵的现代性形式。但发展至后期,民族主义由于阶级论观念的切入而在新的意识形态话语中嬗变为阶级——民族主义,延安文学观念随之走向了“党的文学”阶段,延安文学观念的现代性也就由“民族形式”论争时期的民族——现代性转换为阶级——民族——现代性,进而言之为党的——民族——现代性。这个“党的文学”在我看来乃正构成了后期延安文学的性质。延安文学因之不仅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化的文学,而且真正成为一种党派文学或党的文学。党的文学不仅凸现为一种文学观念,而且在事实上成为一种文学样态。① 人们以往总是依凭《讲话》中的字面含义把后期延安文学的发展方向称之为文学的“工农兵方向”,并因之把延安文学称之为“工农兵文学”,倘若单从题材着眼,这种命名或许还有几分真实性,但从其意识形态本性看,则此种说法显然是不符合延安文学之本真的,是不确切的。因为延安文学的本质是由文艺服从政治这一根本原则所决定,再后来“政治”实际转化为党的政策和个别领袖人物的指示,在此种状况下,工农兵怎能会有自己的话语呢?怎能会有自己的文学呢?关于这点,只要我们真正深入理解了整风期间所发生的文学事件、延安文学形成的历史及其意识形态化品格,也就不难得出这样的判断。
罗迈在延安指出:“共产党员的立场,就是无产阶级的立场,换句话说,就是观察问题和处理问题是立足在无产阶级的利益和党的原则之上。一个共产党员在任何事变的面前,首先要求自己站稳立场,立场不对,就是根本不对,立场错了,就是根本错了。”[9] 这里至少贯彻了一个原则,即党的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由此出发,无论是经济、政治还是文化等各方面的建设都是党的利益的具体体现,都得隶属于党的总体利益,尽管它对外打着的是民族利益和人民利益至上的旗号。按照毛泽东的理论,无产阶级的利益跟民族利益是一致的。在理论上,毛泽东显然经过一番严密论证,有其合理性。但即使如此,在实际生活中,在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实践中,却可能在言行或名实之间产生某种不可弥补的裂缝。马克思、恩格斯曾经针对尚未取得政权的资产阶级说过如下一段话:“事情是这样的,每一个企图代替旧统治阶级的地位的新阶级,就是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抽象地讲,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理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10] 所谓“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其实正表征着意识形态话语的结构性力量,它反映了一种政治实用主义态度,因此,在话语形式和实在之间无疑存在着一定的裂缝。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意识形态本来就是一种虚假的意识,他们认为,“合理性、合法性、普遍性、永恒性、目的性和观念对实在的支配性,乃是意识形态作为‘虚假的意识’的最普遍的表现。”[11] 马、恩的上述表达无疑具有相当的普遍意义,它提醒人们在社会实践和日常生活中碰到以意识形态话语面目出现的种种理论形态时,必须保持一种独立的、批判的识见,并对之给予充分反思。但是,延安文学作为一种历史性存在物,我们首先必须在最大意义上承认其合理性,这是我们重新理解延安文学的一个重要基点,在此之上,才可给以必要的反思性观察。
众所周知,文艺整风后,毛泽东在文化上想以党的文化观念来统摄整个民族国家的文化,必然地,也想以党的文学观来统摄整个民族文学的现代发展。今天看来,站在一个民主的立场上,延安文学是完全可以发展为“党的文学”的,因为任何党派正如任何个人一样在一个真正民主的话语空间里都有发展自己文学与文化的权利,所以,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作为一个以求真为目的的研究者,我们都有必要明确地指出这一点。我之所以认为以往那种说延安文学为“工农兵文学”的说法有其不够确切之处,那是因为它只触及到了延安文学的表象。当然,话要说回来,如果把“工农兵文学”的说法置放到一定的历史语境中去考量,它的提出也是自有其合理性的,至少触及到了延安文学赖以发展的修辞与题材等层面。但是,在当前我们党中央一再强调要持续发展党的先进文化的新的历史时刻,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在延安文学中寻找一些可供构建党的文化的资源呢?为什么就不能坦率地指出“党的文学”就是后期延安文学的实质呢?在这问题上,我以为,作为一个在时刻关注着党的先进文化建设的研究者,完全没有必要在直面历史的时候遮遮掩掩,党的文学就是党的文学,它在历史上本就涵盖了所谓的“工农兵文学”。只要你认为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伟大的执政党,不仅在历史上保持了那种合理性,而且在今天仍然具有毋庸置疑的合法性,那么,党的文学作为党的文化之一种,完全有必要加以重新提出和肯定。正是在这意义上,重新理解和探究延安文学的历史,不仅具有较大的学术价值,而且具有很大的当代性价值。当然,历史的复杂性在于,共和国成立后,党的文学已在事实上转换成了一个新的民族—国家型文学。这种转换也有其历史的合理性,诚如周扬在延安期间阐述毛泽东的“讲话”时所指出:“我们今天在根据地所实行的,基本上就是明天要在全国实行的。为今天的根据地,就正是为明天的中国。”[12] 因之,不仅延安文学本身成了一种必然如此发展的历史性存在物,而且延安文学在时代转型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和自身的转换也成了一种具有历史合理性的存在物。当然,延安文学由延安时期党的文学转换为新的民族—国家型文学后,也带来了一些毋庸讳言的矛盾性。如何对这些矛盾性问题进行富有学理性的探讨,也是值得学界予以认真思考的。
三、直面与重写延安文学的复杂性
我认为,在探究现代中国历史的时候,应该在力求重返历史场域的同时去想象和理解历史,只有理解了历史,才能合乎逻辑地建构历史。重新探究延安文学的历史,当然也应该在力求重返延安文学形成与发展场域的同时去想象和理解延安文学的历史,只有做到了这点,我们才有可能合乎逻辑地构建一部较为符合历史本真的延安文学史。
而要真切地进入延安文学的历史场域,首先必须感受延安文学赖以成形的历史氛围。因此,有必要对延安时期的原初资料做一个较为细致的梳理性阅读。因为延安时期特定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思想观念等在总体上构成了延安文学得以形成的复合性语境或场域,所以我在此处所指原初资料既包括《文艺突击》、《文艺战线》、《大众文艺》、《草叶》、《谷雨》等文学性刊物,也包括《中国文化》、《中国青年》、《解放》等一类的综合性刊物,还包括《红色中华》、《新中华报》、《解放日报》等一类的报纸媒体;所言出版物那就更多了,除了以当时出版发行的文艺类书籍为主外,还应包括当时出版的各种军事、政治、文化类书籍。当然,研究者根据研究的需要,在查阅原初资料时理应有所侧重,没必要对它们平均使用力量,否则,人们往往会陷入浩如烟海的资料之中而不能自拔。
在我看来,只要你真正朴质地触及了跟延安文学形成与发展之历史相关的大量原初资料,你就会有所新的发现,新的感受。但是,因为延安文学赖以成形的历史中蕴含了不少晦暗不明的因素,所以,研究者要想把自己的真实感受毫不遮掩地表达出来,那还需要一定的良知和勇气——这在当代中国这个特定的语境中,往往是不言自明的。因此,对延安文学展开新的研究,并非一般学者所能胜任,在我看来,只有当你首先具备了一个批判性人文知识分子所具有的胆识和勇气,你才有可能深切地把捉到延安文学的灵魂,并才有可能让它在历史的叙事中得以灿烂地敞开。
延安文学发展至后期,虽然在意识形态本性上呈现了一种日趋单一的状态,形成了一种党的文学观念和党的文学形态,但是,前后期之间发展与嬗变的历程是非常复杂的,党的文学观念在话语实践层面上表现出来的东西也是非常复杂的。因此,在我看来,延安文学史具有非常复杂的一面。新的延安文学研究应该以之作为起点,直面与重写延安文学历史的复杂性。比如,延安文学在其资源的取舍和重新整合上显现了它的复杂性。延安文学的形成既跟20世纪30年代的苏区文艺有着直接的承继关系,也跟30年代的左翼文学有着同样不可忽视的承继关系,不仅在其写作人员的构成上,而且在其艺术表现形态上,它都体现了这两方面传统的冲突和汇合,用毛泽东的话说,这是“亭子间的人”和“山顶上的人”的冲突和汇合。延安文学也在一定程度上承继了“五四”启蒙文学传统,这在前期延安文学——比如丁玲等人的小说和杂文——中表现得非常明显,人们以往对此表现了足够注意,但是对后期延安文学中的“五四”因素却表现了一种盲视和漠然的态度。其实,后期延安文学并没有完全斩断“五四”文学传统,因为在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话语构建中,他对“五四”并非如蒋介石一样采取了一种冷漠的态度,而是采取了一种改造和转换的态度。正是在这转换中,“五四”在新的意识形态话语中表现了一定的灵活性,它并没有完全消失,而是发生了新的变异。正因为如此,延安文学发展至后期,它在跟“五四”文学传统的关系上显现了更为隐蔽和复杂的一面,需要我们对之做更为细致的历史性清理。此外,延安文学在其发展过程中跟民间文艺形态也发生了这样或那样的历史性关联,对民间审美文化形态的重视,其实贯穿了延安文学发展的始终。以上所言是从纵向来说的,倘若把考察的视野拓宽些,考虑到俄苏文学和世界范围内红色文学的影响,那么,延安文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呈现出来的面影就显得更为复杂了。
又如,延安文学的复杂性表现在它的发展始终是与延安文人的命运联结在一起的。在一定意义上,延安文学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正是延安文人不断被予以意识形态化形塑的历史。这在文学形态上其实是为“党的文学”所内在决定的,在话语形态上其实是为新的意识形态话语的不断膨胀所内在决定了的。站在党的立场上,这有其历史合理性。须知,《讲话》的产生确乎并非空穴来风,它在当时是有其明确的历史和现实依据,也是有其鲜明的针对性的,不承认这点,恐怕并不是一种历史主义的态度。但是,在延安文人的思想整治和形塑中,其间本来存在的历史残酷性却在以往的延安文学史书写中被人轻易地遮蔽甚或抹杀了。其实,延安文学尤其是后期延安文学赖以形成的隐秘机制之一正在这里。在我的阅读印象中,中共党史研究界在这方面倒是走到了延安文学研究界的前头,就连一些老一辈革命家——比如薄一波在《七十年奋斗与思考》一书的上卷中——直面延安整风与抢救运动的姿态,也要比延安文学研究界来得更为真切和动人。在我看来,后期延安文学中某些审美形态的形成其实包括了一部知识分子的心态变迁史。在这方面,现代文学研究界的探讨显然是严重滞后了。毛泽东曾言:“在艺术工作方面,不但要有话剧,而且要有秦腔和秧歌。不但要有新秦腔、新秧歌,而且要利用旧戏班,利用在秧歌队总数中占百分之九十的旧秧歌队,逐步地加以改造。”在人员方面,“我们的任务是联合一切可用的旧知识分子、旧艺人、旧医生,而帮助、感化和改造他们。”[13] 其中所谓旧艺人是指民间艺人。毛泽东在此说得非常明确具体,他希望文化工作者不仅要改造和利用民间艺术,而且要改造和利用旧戏班和民间艺人。而在这个收编和改造过程中,民间艺人的真切感受和他们所能被利用的限度却被我们的研究界长久地忽略了。正因为如此,倘若人们在研究中能够真切地触摸和认知延安文人以及民间艺人所曾具有的灵魂震荡,深入探讨其所曾具有的独特心理机制,并且把延安文学中的某些审美形态的形成与之结合起来进行考察,那么,延安文学的历史就会更为复杂而丰满地呈现在世人面前。
基金项目: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编号:2005037096);浙江省哲学社科规划课题(编号:N05WX02)。
收稿日期:2006—02—04
注释:
① 详见拙作:《党的文学:后期延安文学观念的核心》,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5年第3期“头条”。此文被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2005年第11期全文转载,《新华文摘》2005年第20期摘录要点。文中提出的观点由于较为客观地揭示了延安文学的形态,也有助于为党的先进文化样态的构建提供历史和文学的资源,因而受到学界的较大认同。当然,也还可就此展开更为深入的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