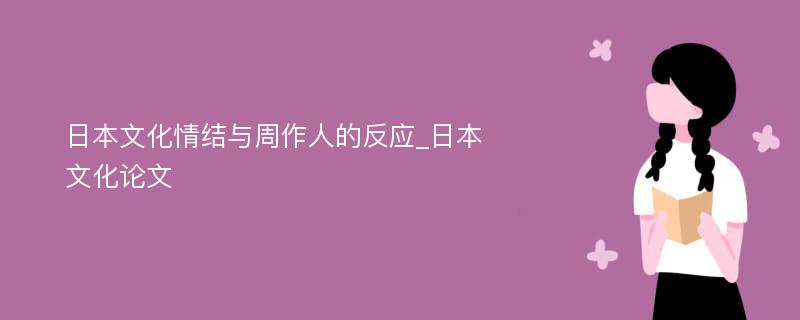
日本文化情结与周作人的附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情结论文,日本文化论文,周作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53(2004)06-0136-05
一
历史是公正的,但也是无情的。周作人的附逆已成为历史的化石,无论人们怎样为之 痛惜,也无法改变他背叛民族的事实。可是周作人的附逆却像一个不可化解的迷,并未 因此而烟消云散。经过半个多世纪不同角度的破解,关于周作人附逆的原因,大体上形 成了三个看法:“对民族和人生的悲观”,“无气节意识”,“个人主义”。但是,却 无人提及“日本文化情结”与周作人附逆的必然联系。
周作人早年长期留学日本、娶日本人为妻、切身体验了日本的民俗风情,接受了日本 的各种文化思想,为一生深爱日本文化打下了坚实的情感基础。回国后,执教日本语言 文化,发表了大量与日本文化有关的文章,晚年竭尽余生翻译了《浮世物语》、《万叶 集》、《古事记》、《日本狂言》、《原野物语》、《浮世澡堂》等多部日本古典文学 作品。纵观周作人的一生,可以一目了然,周作人与日本和日本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 透过周作人的作品和思想,能够窥见到他对日本文化铭心刻骨的体悟,以及深沉、厚重 的日本情缘。在他的文章中,凡涉及到日本文化或中日文化对比时,周作人的语气中总 是流露出鲜明的感情色彩。他说:“日本文化里边尽有比中国好几倍的东西。”[1]“ 我对于日本,如对希腊一样,没有什么研究,但我喜欢他的所有的东西。我爱他的游戏 文学与俗曲,浮世绘,瓷铜漆器,四张半席子的书房,小袖与驹屐,——就是饮食,我 也并不一定偏袒认为世界第一的中国菜,却爱生鱼与清汤。是的,我能够在日本的任何 处安住,其安闲决不下于在中国。”[1]1934年周作人第三次去日本时,日本记者井上 红梅问周作人:“日本菜合先生的口味吗?”周作人回答:“没问题,日本的东西我什 么都喜欢。”[2]其中的“比中国好几倍”,“喜欢他的所有”,“决不下于在中国” ,“日本的东西我什么都喜欢”等这种充满强烈感情色彩,过分夸张强调的字眼,对于 一向以追求含蓄冲淡而著称的周作人来说,确是一个令人不可理解的特例。
在精神分析学看来,当一个人长期沉溺于某种事物中不能自拔,那么,表明他已被一 种强有力的“情结”所控制。荣格认为情结是自主的,有自己的驱动力,可以强有力地 控制我们的思想与行为,“不是人支配情结,而是情结支配人。”[3]正如周作人自己 所说:“概括的说,大概从西洋来的属于知的方面,从日本来的属于情的方面为多,对 于我却是一样的有益处。”[1]“人终是感情的动物,我恐怕理性有时会被感情所胜。 ”[1]显然,在周作人的内心深处有一种日本文化情结,周作人对日本文化强烈、持久 而又深广的爱正是这一情结的外在表征,是被日本文化情结控制、支配的结果。
情结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常常使人产生灵感和动力,在事业上取得巨大的成就; 另一方面,情结往往也成为心理的障碍,控制人的行为与思想,对人产生较大的负面影 响。受日本文化情结强大动力的支配,周作人不断地探究日本文化的卓越之处和独特价 值,发表了许多独到的见解,为深刻地认识日本文化和促进异文化的交流做出了巨大的 贡献,这对周作人产生了积极的意义。而另一方面日本文化情结又成为周作人更深刻地 研究和冷静客观地认识日本文化的巨大阻力。过多个人情感因素参与,使他更多看重日 本文化美好和优秀的方面,而不愿更深剖析日本文化不好的一面。当然,对日本和日本 文不好的一面,也不是没有认识。他也意识到日本帝国主义的军国欲望和对中国的侵略 野心,并对日本人的军国主义和“武士道”丑行以及日本记者对中国的不友好态度、错 误谣言予以抨击与驳斥。但是,对于日本文化情感上的过分“爱着”情结,使周作人在 日本文化研究和与日本的对处时,往往处于理性与感情的冲突之中,而往往又是感情战 胜了理性,导致他不愿承认也解释不了日本民族文化与侵略中国的现实反差的矛盾。他 不得不痛苦地承认:“我用了日本反汉文化的反动来说明近来许多离奇的对华行动,自 己知道不见得怎么靠得住,但是除此以外更没有方法可以说明”[1],“只能正直的自 白云不懂耳。”[1]周作人意识到了自己的这种缺陷,但却无法摆脱。可以说,日本文 化情结成为周作人附逆的隐形动因,为其附逆提供了心理准备和情感支持。因此,我们 不能回避也无法否认日本文化情结与其附逆的必然逻辑关系。
二
周作人的日本文化情结以强烈、巨大和持久的日本文化情感为核心,包含着复杂的多 重思想内涵:一是对日本文化的认同,体现为对民风民俗、日常生活等的“爱着”;二 是对同为“东洋人”的文化身份确认,体现为对“中日文化共同体”的想象。
人类学家麦克杜格尔认为:“任何动物,其群体冲动,只有通过和自己相类似的动物 在一起,才能感到心满意足,类似性越大,就越感到满意。……因此,任何人在与最相 似的人类相处时,更能最充分地发挥他的本能作用,并且得到最大的满足,因为那些人 类举止相似,对相同的事物有相同的情感反应。”[4]应当说,在日本文化中周作人读 出了自己的理想与趣味,与日本文化特性诸如调和中庸,含蓄暧味,自然简素等方面达 到了某种默契,引起了周作人内心的共鸣。周作人刚踏上日本的土地,马上就感到了日 本民族衣食住与民族风情的亲和力。初次到东京的那天“第一个遇见的人”即馆主的妹 妹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感到她“最是特别的是赤着脚,在屋里走来走去”的样子, 这令他震惊和欢喜。五十年后当他谈起最初的感受时,依然深情写到:“这是我和日本 初次的和日本生活的实际的接触,得到最初的印象。这印象很平常,可是也很深,因为 我在这以后五十年来一直没有什么变更或修正。简单的一句语,是在它生活上的爱好天 然,与崇尚简素。”[5]周作人还多次在《日本之再认识》等文章中对日本人对待裸体 的态度和赤足大加赞赏,认为,日本文化“没有宗教与道学伪善,没有从淫逸发生出来 的假正经”,肯定赤足“实在是一件很健全很美的事”。实质上对异质文化的认同不是 孤立、单一的价值取向,它包含着对异质文化的认同和对自身文化否定的双重含义,人 们在接受相似性的同时必然会排斥相异性。所以,对日本文化的赞赏和认同的同时,相 应就会表现出对中国文化“恶俗”的厌恶和失望,他说:“我所嫌恶的中国恶俗之一是 女子的缠足,所以反动的总是赞美赤足。”[6]周作人在《日本的衣食住》中谈到对日 本文化有一种“爱着”的原因时说:“我是生长于东南水乡的人,那里民生寒苦,冬天 屋内没有火气,冷风可以直吹进被窝里来,吃的通年不是很咸的腌菜,也是很咸的腌鱼 ;有了这种训练去过东京的下宿生活,自然是不会不合适的。”一些中国留学生刚到日 本的时候,“都憎恨日本饭菜清淡,枯槁,没有油水,都大惊小怪的”。周作人却说“ 的这是大可原谅的,但是我自己却不以为苦,还觉得这有别一种风趣。”[1]从中,我 们就可以看到周作人的文化性格和审美情趣与日本文化的某种一致性或相通性,而与中 国文化存在着某种差异和疏离。
正因此,他对日本文化理解得特别深、特别独特,并能够较容易地捕捉和吸取日本文 化的精华,被称作是“知日派”作家。日本著名作家谷崎润一朗认为周作人“最能够真 正理解日本民族的长处”[7],学者山田敬三甚至说周作人“对日本文化的理解超出日 本人之上”[8],周作人研究专家钱理群说日本学者特别是木山英雄的周作人研究“似 乎比我们更接近周作人”[7]。如果不是因为具有“对相同的事物有相同的情感反应” ,大概就不会有周作人对日本文化的“真正理解”,同理也就不会有钱理群所谓的对周 作人的“隔”,不如日本学者“更接近周作人”的慨叹。钱理群说:“周作人不仅属于 中国,而且属于日本,属于东方文化。”[7]周作人与日本文化和日本人具有某种“相 似”,“对相同的事物有相同的情感反应”,正是他之所以痴迷和热衷日本文化的情感 依据。这必然带来周作人对日本文化的认同和对日本文化情不自禁的喜爱。在《怀东京 》中他这样写道:“东京的气候不比北京好,地震失火一直还是大威胁,山水名胜也无 馀力游玩,官费生的景况是可想而知的,自然更说不到娱乐。我就喜欢在东京的日本生 活,即日本旧式的衣食住”[1]。
需要强调的是,周作人文化性格和审美趣味与日本文化某种一致或相通,只是周作人 日本文化情结的表层,更深层的在于,周作人从日本文化所保留的中国古昔的文化风俗 和现实的相近的卑屈命运中,触摸到两个民族的共同的历史血脉,超越了民族文化界限 ,感受到了同为“东洋人的悲哀”,把中日文化视为人类文化组成部分的东方文化的一 个整体。在众多的明治时期的作家中,永井荷风是周作人最为推崇的一位,原因有很多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与永井荷风的散文随笔所流露出的“东洋人的悲哀”产生了 强烈的共振。他曾多次引用永井荷风在《江户艺术论》中的一段话,“我反省自己是什 么呢?我非威耳哈伦(verhaeren)似的比利时人而是日本人也,生来就和他们的命运及境 遇迥异的东洋人也。呜呼,我爱浮世绘。苦海十年为亲身的游女的绘姿使我泣,凭倚竹 窗茫然看着流水的艺妓的姿态使我喜,卖宵夜面的纸灯寂寞地停留着的河边的夜景使我 醉。雨夜啼月的杜鹃,阵雨中散落的秋天树叶,落花飘风的钟声,途中日暮的山路的雪 ,凡是无常无告无望的,使人无端嗟叹此世只是一梦的,这样的一切东西于我都是可亲 ,于我都是可怀。”[1]1944年在《浮世绘》中第四次引用了永井荷风的话后,写到: “这一节话我引用过恐怕不止三次了。我们因为是外国人,感想未必完全与永井氏相同 ,但一样有的是东洋人的悲哀,所以于当作风俗画看之外,也常引起怅然之感。”[1] 之所以怅然,是因为从中周作人读出了同为专制社会黑暗之中人民的“无望无告无常” 的悲哀情怀,引起了同病相怜的感触。不过,这是他对东洋人的悲哀产生了强烈共鸣的 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就在于他把“西洋人”和“西洋文化”视为拒斥和抗衡的“文 化他者”,而建立起中日共同命运的情感纽带。在《怀东京》中写到;“中国与日本现 在是立于敌国的地位,但如离开现时的关系而论永久的性质,则两者都是生来就和西洋 的命运及境遇迥异的东洋人。”[1]由此,周作人超越了民族、国家界限,从同为“东 洋人”的中日历史与现实联系中,生成了“东洋人的意识”。“东洋人的意识”构成了 周作人日本文化情结的深层部分,深化了由周作人的文化性格和审美趣味带来的对日本 文化的挚爱之情,并且二者融为一体长期制约周作人。我们认为这就是周作人之所以终 生与日本文化结缘,难舍难分的内在根源,也是他最终走向附逆,成为民族罪人的隐性 根源。
周作人的“东洋人的意识”包含着周作人的对于“中日文化共同体”的“想象”。早 在留学时他就深深感触道:“我们在日本的感觉,一半是异域,一半却是古昔,而这古 昔乃是健全地活在异域的。”[6]周作人所说的“古昔”就是“日本替我们保存好些古 代的文化”,即日本生活中保留的中国古俗、民间的原始的生活方式,也是他所向往的 生存和审美的理想境界。他说:“日本生活中多保存中国古俗”[1],所以,他认为中 国人要想了解日本的文学艺术就自然比西洋人更为容易,“就是研究本国的文物也处处 可以在日本得到参照比较的资料,有如研究希腊古文化者之于罗马。”[1]周作人从中 日文化的同中,发现了东方文化的相同的神韵,但是,不仅如此,更在于他沉重地感受 到了中日两个民族一样的现实境遇和历史命运。在附逆前的1935年,他这样写道:“日 本与中国在文化的关系上本犹罗马之于希腊,及今乃成为东方之德法,在今日而谈日本 的生活,不撒‘国难’的香料,不知有何人要看否,我亦自己怀疑。但是,我仔细思量 日本今昔的生活,现在日本‘非常时’的行动,我仍明确地看明白日本与中国毕竟同是 亚细亚人,兴衰祸福目前虽是不同,究竟的命运还是一致,亚细亚人岂终将沦于劣种乎 ,念之惘然,因谈衣食住而结论至此,实在乃真是漆黑的宿命论也。”[1]应当说,周 作人的中日“文化共同体”思想包含着多种因素,且有着漫长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在留 学时,就接受晚清反满革命中流行的泛亚洲主义思潮的影响,并在日俄战争中,因同为 东亚的日本的胜利而倍受鼓舞,信心大增;而受日本文化情结的影响,从日本文化中, 深深感触到了“东洋人的悲哀”的情感,加深了周作人“同是亚细亚人”的情感认同, 进一步推动了他的“中日文化共同体”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三
显然,周作人的日本文化情结是长时间被扭结的抹煞了民族界限和剔除了正常理性的 特殊精神—心理现象,因此,决定了在民族危亡时的民族立场的迷失和在人生道路上误 入歧途。
首先,周作人的日本文化情结直接影响到他的民族文化身份的认同,构成了他在重大 历史关头误入歧途的内在情感因素。具有留日背景的周作人本身存在着跨文化的双重民 族文化身份,对日本的怀恋“爱着”和对中国现实的悲观失望,使他在刚回国时忧郁寡 欢,虽遇辛亥革命的暴风骤雨竟至于几乎熟视无睹,当时他这样写道:“居东京六年, 今夏返越,虽归故土,弥益寂寥;追念昔游,时有怅触。宗邦为疏,而异地为亲,岂人 情乎?”[9]在1911年所作古诗中有句诗云:“远游不思归,久客恋异乡”[10],这种反 认他乡为故乡的情感,呈现了身首相异的痛苦。显然,去日归国加强、加深了周作人的 日本文化情感和双重民族文化身份认同的内在冲突,并由此滋生出复杂矛盾的“双乡心 理”。在《日本管窥》中称“日本是我所怀念的地方”,在《日本的衣食住》中,更把 东京称为“第二故乡”,这种“双乡”心理蕴含着文化身份认同的分裂心态。他说:“ 我是爱日本的,我重复地说,但我也爱中国。”[1]流露出深刻的矛盾和焦虑,其实就 潜伏着民族文化身份认同的危机,厘清和确认是迟早的事。1935年开“日本店”集中谈 论日本文化,有研究者认为是运用曲笔含蓄地否定和批判日本军国主义,我们认为这仅 仅是一个表面,其中还隐含着在民族矛盾越来越尖锐和激化之时,想努力划清民族边线 ,确认自己的文化身份和情感归属,以挣脱因双重身份所致的心理压力与痛苦。但是, 受日本文化情结的支配,使他无法战胜情感对理性的控制,即如周作人自己所说:“人 终是感情的动物,我恐怕理性有时会被感情所胜。”[1]因此,使周作人不能更加理性 和深刻地认识日本文化,不愿承认也无法理解他所至爱的日本文化何以衍生出军国主义 和侵略行径?只能用连自己也说服不了的所谓的“日本反汉文化的反动”来解释日本“ 许多离奇的对华行动”[1],这实际上正是他无法挣脱自己的双重文化身份和确立自己 的民族意识与立场的体现,使他最后不得不关闭“日本店”。
因此,面对日本军国主义赤裸裸的侵略暴行,他表现出的却仅仅是感到失望、伤心、 遗憾、难过,而不是愤恨、仇视和强烈的民族复仇心理,因为他只是觉得“伤了我为中 国人的自尊心”和“动摇了我对于日本的憧憬”[1]。中国对于周作人来讲是生身之地 ,“血缘”是无法摆脱的,尽管他对此悲观失望,日本虽然不是“原乡”,却是他的情 之系所,情怀难以割舍。所以当民族危亡之际,对于周作人来讲面临的不仅仅是民族立 场的理性抉择而且是情感归属的选择,最终还是被情感所胜。而情感选择直接影响到了 周作人的历史命运。当人们纷纷南下,周作人却留住于北京,因素固然很多,我们认为 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情感上对日本文化的亲和或亲近。他对日本文化自身的矛盾是深知 的,他不是不知道日本人残酷的一面,他曾指出:“日本人是单纯质直的国民,有他的 好性质,但是也有缺点,狭隘,暴躁。”[1]他也意识到日本帝国主义的军国欲望和对 中国的侵略野心,并对日本的军国主义和“武士道”丑行以及日本记者对中国的不友好 态度、错误谣言予以抨击与驳斥。但是对日本文化好的方面的“爱着”,遮蔽或淡化了 日本文化野蛮与丑陋的地方,反倒使他坚信现在的一切都是暂时的,只不过是“现在日 本‘非常时’的行动”。同时,他清楚自己的影响和对日本人的意义,朱光潜当时就曾 说过:“以他在日本知识界的声望,日本人到了北平,决定包围他,利用他,这是他应 该预料到的。”[9]但他知道自己为传播日本文化所作的一切,深知日本人不会把他怎 样,即如梁实秋所说:“抗战开始,周先生舍不得离开北平,也许是他自恃日人不会为 难他。”[7]所以在日寇即将打来的前夕,人们都在为他捏一把汗,而他却依然显得胸 有成竹、镇定自若的样子,这实际上就是双重文化身份和亲和心态所至,显然,正是由 于日本文化情结为他走向附逆提供了充分的心理准备和情感支持。
其次,当他一步步走向深渊时,日本文化情结所蕴含的“中日文化共同体”思想情感 与日本侵略者“大东亚主义”统一起来时,就成了他为日寇的侵略行径寻找合理性和正 义性的赤裸裸说教宣传。“中日文化共同体”的思想恰好与“大东亚文化圈”不谋而合 地统一起来,这是周作人始料不及的。可是,他后来在日伪时期为“大东亚主义”进行 的宣传说教,是自觉地把“大东亚主义”纳入“中日文化共同体”思想的框架之中。遵 循“中日文化共同体”的思想,他从三十年代中期开始到四十年代初对儒家原始思想进 行了重新解释。突出强调了“仁”与“民为贵”的中心地位,他称之为“儒家人文主义 ”,并以此提出了所谓“儒家文化中心论”,认为他的“儒家人本主义”不仅是中国文 化的固有的“中心思想”,还可以充当“大东亚文化”的“中心思想”。在《中心思想 》一文中,他这样写道:“所谓中心思想,就是大东亚主义的思想。再进一步去研究, 大东亚主义的思想的出发点,还是在儒家思想之内,即所谓儒家所提倡的‘仁’的思想 。”其动机按周作人的解释是旨在以中国文化的理性精神体现代表——儒家文化来抵御 日本的非理性文化。但实际上,是对日本侵略者鼓吹的“大东亚文化圈”的认同。在《 中国的思想问题》里,他引用《礼记》所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饮食以求 个体之生存,这本是一切生物的本能”,但人不同于其他生物,在“我自己要生存”之 外,“也要让别人生存,要互相扶助,团结合作,要共济”,“共济即是现在说的烂熟 了的共存共荣”,显然是与日本军国主义者的“大东亚共存共荣”论是同一个腔调的。 他说:我们要“深切明了在当前中日两国的百年大计上所负的使命。中日两国壤地相接 ,同文同种,无论在国情上,在共同利害上,都应当相爱相助,以定成辅车相依的任务 ”。“我想翻译介绍日本人民生活情形,希望读者从这中间感到东亚人的悲辛,发出爱 与相怜之感情,以替代一般宣传与经验所养成的敬或畏。”[1]这是和他附逆前的思想 情感是相通的,是一种合乎逻辑的延续。它为周作人最终走向罪孽,提供了情感和理论 上的支持,使日本侵略者在30年代推行的“大东亚共荣”在周作人那儿得到了响应,在 实践上对周作人的附逆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总之,从上述分析可见,周作人的日本情感对其附逆的影响是毫无疑义的,当然并不 是说是唯一的原因。周作人的附逆是一个复杂的精神现象,是一个漫长的发展的动态过 程,非突发而成,而且,是各种因素交织在一起的,不是孤立的。无论是作为一个活生 生的人也好,还是作为一代宗师和“五四”青年领袖,能置民族共同的道德价值于不顾 ,最终甘心情愿走向与民族对立的道路,其中的因素恐怕很复杂,可能远非我们想象的 那么简单。但是这其中,周作人的日本文化情结起了相当关键性的作用,忽视了它,我 们就无法彻底解开周作人的附逆之谜。
收稿日期:2004-07-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