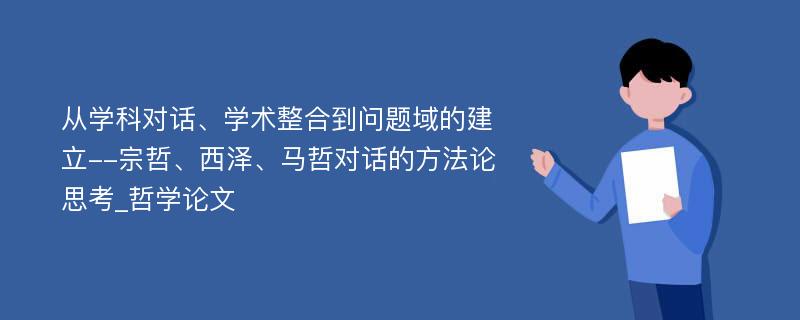
从学科对话、学术整合到问题域的确立——关于中哲、西哲、马哲对话的一个方法论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方法论论文,学科论文,学术论文,西哲论文,马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哲、西哲、马哲的对话,这是引起近年来学术界关注的一个跨学科话题。这一话题的突现,有其特定的历史与思想语境。首先是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对现行学术体制的反思,学术界越来越意识到,当下国内的这种学科划分(这里当然指哲学学科的划分)既在逻辑上很难自洽,又有悖于哲学学科的本性。要打破这种格局,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实现哲学学科内部的跨学科对话,以达哲学的本性,使哲学真正成为具有批判意识的智慧之学。其次,随着中国的发展及其在世界上的影响日益扩大,需要在学术、文化上发展自己。这三个学科之间的对话沟通,就是实现文化发展与文化自觉的一个重要因素。应该说,相比于过去这三个学科的壁垒、与简单地用传统马克思主义话语来评价西哲、中哲相比,当前的对话与沟通不仅加深了这些学科间的相互理解,而且出现了一些有分量的成果。但这并不意味着当前的研究就可以按照现有的路径走下去。
康德曾指出,在研究人的认识之前,先要考察人的认识能力。虽然这一观点遭到黑格尔的嘲笑,但在我看来,这种方法论的自觉却是学术研究的前提。回到当下的话题,我们需要追问的是:我们的对话到底意味着什么?是想获得一种新的话语体系,还是获得透视中国问题的理论构架?如果我们想达到后一种意图,那么,重要的就不是这三种话语体系之间的比较、对话,而是在更高的基础上实现对三者的整合。这时,我们需要讨论的就是:什么是整合这三者的基础?这种整合的目的又是什么?在我看来,这是当前中哲、西哲、马哲三者之间实现沟通的更为根本的问题。
一、比较与对话:前提、意义及局限性
讨论中哲、西哲、马哲的对话问题,我们面临着一个尴尬的情境:即在当下的学术界,可能只有很少的学者能够同时精通这三门学科,对于大部分哲学学者来说,我们只是某一学科的研究者或专家。在目前的学科建制下,这种分野虽然有助于学术的精细化、专业化,合乎现代学科发展的特点与要求,但是它显然有碍于我们从总体上把握国内哲学学科的发展以及未来中国应有的精神状态。要打破这种学科壁垒,就需要比较研究与学科对话,这是我们走出学科限制的重要一步。
两个不同学科要实现真正的对话,至少需要三个前提:一是每一门学科研究的成熟性。这种成熟性指的是它的研究应该在许多方面成为一个整体,对它所要追问的问题有着深入的解剖与应答,比如就中哲与西哲对话来说,我们首先需要对中国哲学的根本精神与价值理念、西方哲学的根本精神与价值理念都有着真切的理解,它们各自的思想逻辑有着深入的把握。
二是理解这些思想与特定历史情境之间的联系。哲学思想虽然具有一种形而上的特征,追问的常是一些带有普遍性的、根本性的问题,但其具体的表现形式往往带有特定时代的历史印记。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第一卷第九章论家庭获得财产技术的方式中指出:“我们所有的财物,每一件都可以有两种用途。财物是同一财物,但应用的方式有别,其一就是按照每一种财物的本分而作正当的使用,另一则是不正当的使用。”①从思想逻辑的层面来说,这里涉及商品二重性问题,即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问题。虽然亚里士多德也提到“价值”概念,但他所理解的“价值”只是交换中的量的关系,而没有把它看作抽象的劳动。根据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讨论,“价值”是以劳动的抽象化为基础的,而劳动的抽象化又意味着商品生产与交换的普遍化。商品生产的普遍化在人与人的关系维度上,又有一个前提即一切人在形式上都是平等的。这是现代历史的情境。而在亚里士多德时代,这种一切人的平等是不可能的,虽然智者学派认为奴隶与主人在自然本性上是平等的,但亚里士多德认为,这种奴役关系是人的自然本性的显现。可以说,亚里士多德无法理解“价值”或“交换价值”,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的思想无法超越他生活时代的历史情境。按照我的理解,思想史研究中最需要的就是这种历史性的方法,这是我们真正激活思想,能够推动传统与现代、中国思想与西方思想之间对话的重要条件。
在此基础上,我们进入第三环节,即比较与对话,这是取得不同学科之间的理解与沟通的途径。通过比较与对话,我们可以将问题细化,可以得出不同思想间的一致与差异。这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但也正是在这里,问题也就产生了。两个不同的事物之间,我们可以找到很多相同的地方,也可以找到无限多不同的地方,特别是当两种不同的文化理念之间进行比较时,更是如此。可以说,这种比较与对话工作,可以无限期地进行下去。这虽然有意义,但这种无限的比较与对话,也容易陷入一种“恶的无限性”(套用黑格尔的话)之中。黑格尔是这样解释“恶的无限性”的:“某物成为一个别物,而别物自身也是一个某物,因此它也同样成为一个别物,如此递推,以至无限”。“这种无限进展乃是互相转化的某物与别物这两个规定彼此交互往复的无穷进展”②。这种比较与对话仍是一种知性思维,虽然有助于对一些问题的澄清,但如何在这个基础上实现一种创造性的理论转换,并不是通过对话就可以实现的。
二、从对话到整合:问题域的界定
学术研究往往体现为两个层面:一是注重对前人思想的“客观”描述,力求揭示某一思想家的所有生活细节,以示精确;二是在新的历史情境中,通过发掘前人思想,而实现新的理论建构。从思想史的视角来看,后一层面更为重要。对现有思想的精确阐释或发挥,都不是想简单地“回到某处”,而是力图在新的历史情境中实现理论的创造,接着前人的思想往下说。结合本文的论题,那就是要实现从比较、对话到学术整合、学术重构的转变。这样一种重构,固然可以从思想逻辑上寻找生长点,但更为重要的是在思想逻辑与历史情境之间的内在关系中去重新规划。这是通过双重诊断而实现问题域的转换,是学术整合与创造的基础。
从历史性的视角来看,思想史的问题转换虽然常常表现为思想逻辑的演变,但这种逻辑转变往往受到历史情境的影响,可以说,特定的历史情境有其相应的学术问题。因此,对于学术研究来说,如何揭示过去的学术与历史情境之间的关系,把曾经的历史作为一个总体,在此基础上透视当下的历史,从而确定新的问题域,这是学术重构的前提。思想史上的大家,实际上都是在这个维度上实现了对传统思想的继承,并在此基础上完成了新的学术建构,从而将思想史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在这个意义上,对特定时代的历史问题进行提炼与划界,并在此基础上实现思想型的转变,这是学术发展中的根本问题。
如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我们可以从思想逻辑层面来确立其与思想史的关系,确立其学术的意义,或者它在黑格尔思想中的意义。但如果只是停留于这个层面,对《法哲学原理》的历史意义就无法理解。当黑格尔从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分离、并以国家理性作为法哲学的最高标准时,一方面固然是其哲学逻辑的体现,另一方面也是黑格尔对德国历史问题的诊断与批评,他力图寻求解决问题的出路。黑格尔以自由为前提,但这里的自由是人与人之间相互承认基础上的自由,而不简单地是个体自由。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这是个体与他人、个体与共同体或社会的同时自由。按照这个原则,熟悉古典经济学与英国、法国历史的黑格尔看到,现代意义上的市民社会,虽然在一定的意义上能促进个人能力的发展,增加财富,但并不能真正地实现上述自由。即使就经济学方面来说,也很难实现普遍人的福利。那么怎样改变这一状态呢?只有国家理性实现了对市民社会的规制,同时又充分吸收市民社会的成就时,才能真正地实现法的原则与理想。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黑格尔批判了卢梭的契约论以及康德的法权思想。前者聚焦于个体自由,后者只是确立了一种“应当”的理想。黑格尔的法哲学当然与其哲学理念是一致的,是其哲学理念在具体领域的表现。而这一具体化却又与对历史课题的思考结合在了一起。
如果从历史视角来看,黑格尔的讨论又是对德国发展道路的哲学探索。当英国与法国已经进入资本主义社会时,德国还处于封建城邦林立的状态。要想发展自己,德国首先需要实现民族国家的统一;同时又不能简单地按照英国、法国的方式来规划自己。如果从社会政治的角度来说,德国古典哲学对英国、法国哲学的继承与反思,就具有了为德国的现实与政治建构奠定思想基础的意义。由此黑格尔对国家理性及其与市民社会关系的讨论,就具有了直接的历史意义。从这个意义上可以看出,黑格尔的哲学就不简单地是对德国古典哲学内在逻辑问题的解答,同时也是对历史问题的探索,并很好地将两者统一了起来。这正是黑格尔的“问题域”。这一问题域实现了思想问题与历史问题的沟通,并在此基础上探寻新的哲学理念,进行哲学规划。在这里,哲学问题同时是经济学、政治学与法的问题,它们之间形成了内在的统一。显然黑格尔是在更高的问题域中实现了对这些问题的把握。
黑格尔生活的时代,学科分化还不够明显,还可以出现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到了19世纪后期,随着资本主义的长足发展以及科学技术的进步,学科分化日益加剧,先是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分离,后是每一门类中又进一步划分出诸多的学科,一直延续到当代。每个学者都很难说自己能够精通所有学科,即使在人文学科内部,学科分化使得学者们越来越成为专家,学科之间的对话也显得越来越困难。在这种情况下,确立学术研究的社会历史课题显得越来越重要,学术的融合与重新建构往往是在新的历史性课题中形成的。在这方面,法兰克福学派提供了一个学科整合的例证。早期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面临的问题是法西斯主义的兴起,他们确立的主题是“批判理论”,即一种不同于当时流行的实证分析的哲学,强调哲学的批判意义,并将之指向法西斯主义。在这个问题域内,他们整合了哲学、经济学、政治学、心理学等学科,在学科对话与沟通中,通过历史性的课题完成学术理念的重构。在哲学的内部,应该说,他们最先实现了我们国内意义上的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话与沟通。在研究所移驻美国之后,面对日益兴起的技术控制与支配,他们对工具理性的批评与对西方文化根源的批判结合起来,使批判理论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在这里,并不只有学科间简单的对话关系,而是一种新的整合与建构。
又如海德格尔,虽然在学术的思辨层面,他是针对过去哲学忘记存在而只关注存在者的起诉,但这种重新探讨存在的哲学同样是对历史的追问与反思,这种历史是关注存在者意义上的历史,也是存在丧失的历史。虽然海德格尔与纳粹的关系一直争论不休,但我还是认为,海德格尔从哲学立场对历史情境的判断以及他对历史课题的规划,还是直接影响到了他的政治行动。可以说,一种问题域的确立,直接影响到学术研究的结果,也直接影响到学术研究中学科间的整合与沟通。
从思想史的发展来看,也正是根据历史课题并通过思想史的规划而发展起来的学术,才真正构成了思想史发展中的环节。学术的分化与整合也只有在这种情境中,才能真正地展现自己的生命力。
三、中国问题:在现代性的视野中
按照本文的讨论思路,真正的学术最后或者一开始都是要面对历史课题的。这种面对并不是用现成的理论去解释、论证现实,简单地为其合法性辩护,而是借助于思想史和历史,实现对当下历史情境的透视。因此,当下中国的哲学研究,在深入探讨思想史与人物思想的同时,面临的是如何判断中国当下情境的问题。实际上,不同的哲学家都是在对历史情境的不同判断中来建构自己哲学的。
囿于笔者的学科限制,本文只从自己专业的视角来面对这一问题,确立判断问题的外部情境,作为面对中国问题的一个标尺。当然这本身就是有局限的。按照我的理解,在西方现代性产生与发展中,存在着三个维度:即资本逻辑的确立、形而上学的建构以及民族—国家的形成。这三者同体而生,共同支撑着西方现代性的发展。
资本逻辑是西方现代社会结构的核心。随着商品生产与交换的普遍化,资本逻辑取得了支配社会生活的地位,追求剩余价值成为生产的原则。正是资本逻辑的确立,改变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与交往模式,引起了社会生活的结构性转变。马克思曾对此进行了较为细致的描述。也正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人类生活的一般物质生产被资本生产所统摄,这使得资本虽然从头到脚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但它同时又是人类社会生存与发展的基础。资本逻辑的直接活动境域是市民社会,但市民社会要想成为资本逻辑的舞台,又需要另外一个重要条件,即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在亚当·斯密看来,国家与自由市场的发展无关,国家干预只会破坏自由市场的良性发展。在这个意义上,似乎资本逻辑与统一的民族—国家无关。李斯特通过考察英国的发展过程指出,英国经济的发展首先有赖于英国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早期英国正是借助于国家主权,通过贸易保护而发展起来的。所以他批评斯密说:“亚当·斯密对于政治力量、生产力量与财富之间的交互作用与反作用这个规律视若无睹,即敢贸然断言,从商业观点来看,麦修恩条约与航海条例对英国并无好处。”③李斯特虽然谈的是商业保护政策,但这种政策出台的前提是独立自主的民族—国家。意大利较早地走上了现代自由贸易的道路,但它最终衰落了,“它所缺少的是国家统一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力量。意大利的许多城市和统治势力并不是作为一个团体中的成员而存在着的,而是像独立的国家那样”④。这种统一的民族—国家,正是当时德国所缺少的。理解了这一点,我们才更能理解黑格尔为什么赋予国家理性以很高的地位,也理解了他为什么会大力称赞马基雅维里在《君主论》中所表达的思想:“这本书时常被人认为是满纸胡说,徒然替虐政张目,所以厌弃不读;而不知道这位作者实在深刻地意识到了当时有成立一个‘国家’的必要,因此才提出在当时环境下非得这样就不能成立国家的各种原则。”⑤可见,资本逻辑与民族—国家之间存在着内在制约关系。这是我们过去研究时所忽视的内容。进一步说,这里的民族—国家不只是国家权力的独立自主,而且也包括国家权力的组织形式与结构,这是民族—国家对内对外的不同表现层面。当民族—国家的独立自主实现之后,后者的合理化结构就日益重要。
与资本逻辑、民族—国家相一致的,就是人们的思想信仰上的变化,这就是现代以来的形而上学的奠基。中世纪的上帝合乎自然经济的理念,市场经济打破了传统社会的生活方式及相应的思想与价值观念,就需要重新确立人们的思想坐标。近代以来的哲学就是这一过程的展开,并以此直接影响到人们对政治、经济的看法,以及对未来社会的构想。虽然在西方哲学史上,我们过去常讲经验论与唯理论是对立的,但实际上两者都是对资本逻辑合法性的确证。英国的经验论构成了古典经济学的基础,这是从经验事实归纳出经济规律的基础,当经济学家从经济规律出发并得出自由市场经济才是合乎自然的经济样态时(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这是最不合乎自然本性的),哲学与经济的同构完成了。唯理论强调个人思想的独立与自由,在社会历史的意义上,这正是市场中所需要的个人。但那个决定社会市场运行的总体结构是个人所无法知道的,它就像“物自体”一样处于幕后。卢卡奇认为,康德的“物自体”学说,正好表现出学者们对资本主义社会总体认识的失败。而哲学的发展过程,正是要认识这个整体,所以形而上学的奠基也就不断地被提出。这种形而上学,在黑格尔那里,也是国家学说的基础。
现代性的发展从根基上来说,都得益于资本逻辑、形而上学与民族—国家三者的同构,当然在不同的国家,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不同的。这些不同也就形成了西方国家在走向现代性时的不同样态,或者说构成了它们各自发展中的“特色”。特别是对于后发展国家来说,它们也只有在“特色”式的发展中,才可能真正地实现富国强民的理想。当中国迈入现代性发展规划时,它们构成了我们讨论的参考系。
但在这里,我认为真正需要关注的是中国的独特性问题。中国已然走上了现代性的道路,但这同样不能直接复制西方发达国家的路径,我们需要的是“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中国特色”构成了当前学术研究需要关注的“总问题”,如何对这个问题进行探讨,透视当下中国现实,真正地探索中国发展的良性轨道,在我看来,这才是当前学术需要关注的核心。这并不意味着只需要将现成的理论直接套用到中国现实,或者只是将外来理论中国化就可以了,也不是复兴传统文化就可以解决的。我们需要的是对这一问题的透视并在此基础上实现真正的理论创造。上述现代性的结构也只有在这种理论创造的高度才成为讨论中国问题的参照系。
四、总体性:面对中国问题的理论方法
从社会发展的过程来看,如果以西方为参照系,可将西方视为一个线性的进程,虽然实际上并不这么简单,而中国的当下则可看成一个复杂性的过程,这种复杂性就是学术界已经取得共识的多重社会形态叠加的发展状态。这决定了审视中国当下发展的过程需要一种“总体性”的视野与方法,我们今天的对话、沟通与整合,实际上也是想获得面对哲学问题时的“总体性”视野与方法。
强调总体性的方法首先是因为当下中国问题的结构复杂性。在中国,经济问题并不简单地表现为经济发展,政治问题又不简单地是单纯的政治管理,文化问题同样不具有完全独立的特征,它们都交织在一起,这意味着任何一个问题往往都是与其他问题联系着,或者一些不同的问题浓缩在同一个构架中,就像弗洛伊德所描述的压缩的“梦”一样。问题的这种复杂性与整合性,要求我们必须将之看作一个总体。问题的总体性要求我们具有总体性的意识,即任何一个问题的解决并不是单个学科就能完成的,这正是总体性方法的第二个层面。比如中国的经济问题常常就是政治问题,而政治问题又常常与道德问题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说,如何面对这些问题,就需要学科之间的整合。当然,这种解决方案一方面虽然是就事论事,但另一方面,所有这些意识都必须以中国面临的总问题为根据。这才是运用总体性方法的根本要求。
在现代社会,任何一个个体都很难成为百科全书式的学者,要真正实现总体性的方法,就需要一个真正的学术团体,以团体的力量真正地推动理论的发展。我想,今天对话的意义,正在于此。
注释:
①亚里士多德认为,获得财产的技术有两种:一是以自然的方式,家主要熟悉以自然方式取得家族所必需的各种物品,如狩猎或农耕等;一是“获得金钱(货币)的技术”,这是违反交易的自然本性的。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25页。
②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06、207页。
③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陈万煦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47页。
④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第11页。
⑤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第41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