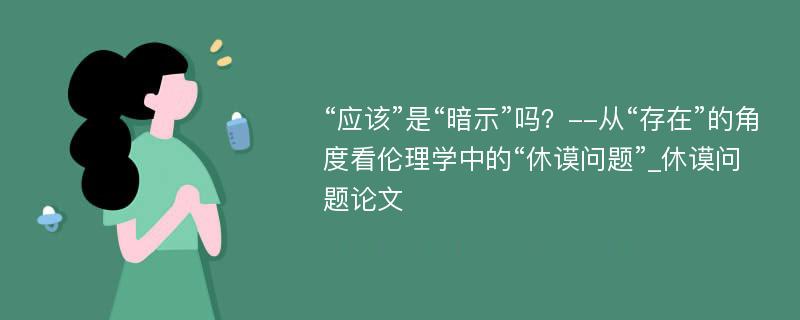
“是”蕴涵“应该”吗?——从“Being”的考察看伦理学中的“休谟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蕴涵论文,伦理论文,学中论文,休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53(2007)06-0106-04
所谓“休谟问题”在哲学史上有两种涵义:一是指认识论和逻辑学中的“归纳问题”,一是指伦理学中“是(be)”与“应该(ought to be)”的区分。后一问题一直是休谟研究的热点之一,国内外学术界对此的共识是此处所论乃事实与价值的关系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展开了持续的讨论。但是休谟的本意是否如此,想当然的研究者们却不再追问,结果竟致其蔽而不明。本文立足于休谟的文本本身,通过对传统伦理精神演进之内在逻辑的梳理,借助于目前国内外对“Being”研究的最新成果,试图解答这一区分的真正内涵及其价值所在。
一
休谟是在《人性论》第三卷提到这一问题的:“在我所遇到的每一个道德学体系中,我一向注意到,作者在一个时期中是照平常的推理方式进行的,确定了上帝的存在,或是对人事作了一番议论;可是突然之间,我却大吃一惊地发现,我所遇到的不再是命题中通常的‘是(is)’与‘不是(is not)’等联系词,而是没有一个命题不是由一个‘应该(ought)’或一个‘不应该(ought not)’联系起来。这个变化虽是不知不觉的,却是有极其重大的关系的。因为这个应该或不应该既然表示一种新的关系或肯定,所以就必须加以论述和说明;同时对于这种似乎完全不可思议的事情,即这个新关系如何能由完全不同的另外一些关系推出来的,也应当举出理由加以说明。”[1]“是”与“应该”的区分是休谟在批判传统道德观时提出的一个基本观点,他指责以往的伦理体系总是混淆这两者。因此,欲辨明休谟在此的确切所指,就要先弄清涉及“Being”的传统伦理学之本真意蕴。
对“Being”的探讨在西方哲学史上源远流长,据海德格尔考证,早期希腊哲学家对此皆有论述。最早将其作为哲学核心范畴的是巴门尼德。他一反以前自然哲学寻求万物生成性本原的传统,转而探求事物的逻辑本质,第一次将希腊文的esti和on(相当于英文的being)作为其哲学的核心范畴。Esti是希腊文中主动语态现在陈述式单数第三人称,相当于英文的is,einai是其不定式,相当于to be,eon是on的早期写法,是第一人称单数eimi的中性分词。据汪子嵩、王太庆先生考证,在此esti有“依靠自己的力量起作用”[2]之意。笔者认为,其意即指事物因其本质的恒定性而成其自身。与赫拉克里特相反,巴门尼德认为不确定的感官只能认识流幻的现象,只有理性思维才能把握事物实在之“是”。作为超越于虚浮表象与世俗感受之上的事物之内在规定性,“是”不仅是事物应然之本质,而且是理性之应识。在此,“是”已具有逻辑上、认识上和价值上应该的意味。“真理之路”的称谓已表明巴门尼德的态度所向。可以说,在理性形而上学的发端处,理智世界对感性世界的优先性已得到强调,“Being”已内涵“Ought to be”之意。
柏拉图沿着巴门尼德的思维方式继续探讨事物的最后根据,系统地提出了具有浓厚价值意蕴的理念论。理念是事物的终极原因,而作为最高理念的善不但是“关于宇宙和变动事物起源的最高原则”[3],而且是“每个灵魂的行为目的”[3]。正是因为理念,一个事物才能是什么,因而理念是“根本之是”(Being),是人们在价值上应该趋向(ought to be)的目标。柏拉图由此将目的论纳入体系中,体现了某种终极关怀的精神。
柏拉图的伦理学以其宇宙论为背景。在《蒂迈欧篇》中柏拉图提到,范型世界中的任一范型可被可见世界中的诸多事物所分有,而范型世界却只能被一个可见世界所摹仿或分有。“为了这个世界在单一性上像完美的生物,创造者没有创造二个世界,更没有造无穷数的世界。”[3]这一带有伦理意义的理由体现了普遍的目的因素,柏拉图认为,在社会生活中与之对应的就应是他所描绘的理想国的图景。在此,他的分析完全是超验主义的:理想国产生的合理性不在于现实,而在于其理念,因为“应该”存在而“必然”存在。在这幅乌托邦的蓝图中,柏拉图主张社会分为三个阶层,这三个阶层分别由金、银、铜形成,因而天生有别。每个阶层都有其天赋的职能和德性。统治者必须有智慧,卫士必须勇敢,而民众则应当节制,这三者各司其职,国家与社会处于最佳状态,即为正义。其实,这种整体主义理论与价值取向在整个传统伦理学中是具有普遍性的。在柏拉图看来,这样一种社会状态就显现了“在制度和法律中的美”。每个人均应以善的理念为最高行为之光,摆脱肉欲的束缚,使自己的人生境界不断攀升。这样一种状态的实现即是人类的目的趋向。显然,其伦理学的核心是一种以抽象理性人性论为基础的目的论。这样一种先验的思维模式与价值信念对后世伦理学的发展影响深远。这在中世纪神学和黑格尔那里表现得最为明显。在这种理论中,人的自由仅仅在于服从既定的必然,而非理性的情感欲望充其量只是理性实现其狡计的手段。可见,对天赋价值原则的设定是传统理性主义伦理学之基本理论特征,包含着对事物的应是追求。
由于理念论本身的困难,柏拉图在后期对其做了进一步的修正。在《巴门尼德篇》中,柏拉图不再主要从与现实相对的意义上来规定理念世界,而是试图寻求理念之间的相互规定。他通过分析“一”与“是”(on,英文being)的分有与否,来考察理念的存在方式。通过那八组著名的推论,柏拉图得出结论:一个理念如要是其所是,必须从其与其他理念的关系中去规定,如果不参照与其他理念的关系,这一理念本身亦不能成立。
在此需注意的是:一,“是”(being)作为一个基本范畴被正式提了出来。由于理念间的相互分有,以及理念对现实事物的逻辑在先性,因而一切东西都可以称为“是”的东西,即“所是”(beings)。这样,一个由系词“是”连结的句子也就获得了新的意义,它表示“是”这个理念与同样作为理念来看的主词与宾词之间的结合。那么,使得一切东西得以“是”的“是”本身又是什么呢?这样,由to be转化而来的动名词being逐渐获得了实质性的内涵,成为拥有独特地位的Being,“这个词作为词构成可寻觅的过渡,这个词作为词不再单纯是词了,这个词用神秘的超语言方式指出了从语言走到它所标示的现实客体的道路,简而言之,这个词要在一切词中起一种和救世主—圣子在人们中所起的基督教幻想的作用一样的作用。”[4]到了中世纪,Being被用来指称上帝,成为最高最普遍的范畴。二,由于理念脱离经验,是纯粹的先天概念,要展示理念之间的逻辑次序及理念系统与现象世界的逻辑派生关系,就需要从这一最高前提Being出发进行有序的演绎。这一过程,即为to be(Being将beings规定为是……),亦即Being自身逻辑运动、自我显现的过程。托马斯·阿奎那就此指出:“是”首先“表示被感知的现实性的绝对状态,因为‘是’的纯粹定义是‘在行动’,因而才表现出动词形态。”[5]在此初显形而上学伦理学的方法论特征,即以“Being”为最高范畴的逻辑演绎法。这是由其内容决定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这套原理系统的普遍必然性。这对后世影响深远,黑格尔的逻辑学就是从最基本的范畴“Being”展开的。由于这一演绎过程囊括一切真理,所以“应是”(ought to be)的价值原则也能从中导出。用海德格尔的话就是:“这个是本身,在确定地被阐释为理念的情况下,就随身把与可作模式的事与应当做的事的关涉带来了。”[6](熊伟先生将Being译为“在”,今改译为“是”)由之就将价值判断归于纯粹逻辑判断,将应然纳入预定的因果必然中。这样,理性的力量就突出出来,求善隶属于求真的知识系统。理性占据了对情感欲望的绝对统治地位。在此尤需注意的是,“理性”是一个超验的范畴,既指至高至善的目的论实体,又指超验的理性能力,而其对于感性欲望则有绝对的至上性。由以上分析可见,传统理性主义伦理学的实质内涵在柏拉图哲学中已被决定性地展示出来。
到了中世纪,“Being”作为认识与价值的最高原则,在思辨中被等同为上帝。面对摩西对自己身份的询问,上帝的回答是:我是我所是。虽然我们在描述上帝的属性时可以说上帝如何(God is great),但上帝自身只能被描述为“Being(是)”,而不能被描述为本质上是什么,否则的话就是规定,而规定就是限制,限制就是不完满,这既与上帝的本性相违,也非人所能识。安瑟伦所谓“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就是从“上帝是最完满的Being”这一前提出发的。休谟在《自然宗教对话录》中借第美亚之口也指出,上帝“是一无限完善的Being(He is a Being infinitely perfect)。”“他的真名是‘他是’,或者说,无限制的‘是’,‘全是’,无限而普遍的‘是’(That his true name is,He that is; or,in other words,Beingwithout restriction,All Being,the Being infinite and universal)。”[7]由于万物皆依于上帝,所以价值原则也须由对上帝仁慈之性的认识中演绎而出,至善实体的存在是人类伦理原则的标准和道德生活可能性的基础。实际上,这仍是一种形而上的理性主义伦理学。
二
休谟所面对的不仅是这一伦理学中源自古希腊而经中世纪的悠远的形而上传统,其批判的矛头更直接指向近代的理性主义伦理学。此学说的代表在大陆是以笛卡尔、斯宾诺莎、莱布尼茨为代表的唯理论,在英国则是以克拉克、库德渥兹为代表的道德理性主义者。近代理性伦理学以上帝至善作为自明的前提,以逻辑演绎为基本方法,寻求一种普遍主义的价值原则,而对情感欲望则采取排斥与否定态度。这与以休谟为代表的情感主义伦理学派形成了鲜明的对立。
休谟清楚地看到这一争论的分歧所在:“新近,出现了一种非常值得审查的争论,是关于道德的一般根据的问题:道德是来自理性还是来自情感;我们有关道德的知识是通过一系列的论证和归纳得到的,还是通过直接的感受和更为灵敏的内在感得到的;它们是像一切有关真理和谬误的正确判断一样,对于每一个有理性能力的人都应当是相同的,还是像人们感知美和丑那样,完全依赖于人类的特殊结构和气质。”[8]将这两种观点的对立放在整个西方哲学史的视域中来加以审视,实际上是发轫于柏拉图的理性主义传统与肇始于古希腊以善罗泰戈拉为代表的经验主义传统在当时伦理学领域的体现。由于理性主义伦理学以上帝这一最完满的“Being”为悬设,所以说上帝如何(God is benevolent,上帝是仁慈的),虽然用的是“is”(be),但实际上却也是一种价值陈述,包含一种对人们行为应然的设定(Ought to be)。比如克拉克就认为,因为上帝比人无限优越,所以人应当遵从上帝。上帝使万物普遍向善、让好人得福,这比让万物遭受苦难更合适。效法于此,人更应当努力促进他人的善和幸福,避免对他人福祉的破坏。正如康德所指出的,这是一种宾词蕴涵在主词之中的先天判断。黑格尔在谈到经验论与形而上学的原则对立时也指出:“在经验主义里包含着一条伟大的原则,即凡是真的东西都必定存在于现实世界里,而且必定是在那里为知觉而存在着。这条原则是与应当对立的,而反思则依靠应当的原则,趾高气扬,抱着轻蔑的态度,用一个彼岸世界去反对现实世界和当代世界。”[9]
本文开始的引文中,休谟直接批判的正是这种道德学说。仔细分析,可以发现,在这一段中,休谟提到了“上帝的存在”及“照……推理方式进行”,显然这里所指的是形而上学的理性主义伦理学。正如上述,在传统伦理学的目的论演绎体系中,说某物在理念上是什么,实际上就蕴涵着某物所应趋向的理想本质,“是”本身作为目的因表现为应然的价值趋向。休谟所指的实际上就是这种情况,由之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命题中的“是”与“不是”转变成了“应该”与“不应该”。他极其敏锐地察觉出“是”对“应该”的蕴含是传统理性伦理学的关键所在,并指出:“这个变化虽是不知不觉的,却是有极其重大的关系的。”也正是由此,他才会认为这条附论“相当重要”,并且指出,“这样一点点的注意就会推翻一切通俗的道德学体系”。
三
既然抓住了要害就可以深入地对其展开批判。休谟认为,道德中的决定性因素既不是理性也不是单纯的感觉,而是情感,最终成为道德的根源并为道德判断提供标准的是人内在固有的道德感。这种道德感是从对原始苦乐印象的反省中产生出来的次生印象。“根据自然的原始结构,某些性格和情感在一经观察和思维之下,就产生了痛苦,而另外一些的性格和情感则在同样方式下刺激起快乐来。不快和愉快不但和恶和德是分不开的,而且就构成了两者的本性和本质。”[1]道德感不但具有价值评价的意义,还有伦理规范的意义,行为的应该与否就看行动中产生的感觉是乐还是苦。
对于理性,休谟则完全是以此岸的眼光看待之,取消了它形而上学的神秘性并将其完全置入经验论的视域之中。依他看来,传统的理性实体既不可知,人也无超越的理性能力。关于“是”的命题只能是对经验事物及事态的非思辨、纯描述的关乎真假的知识命题。在行为领域,理性只有通过弄清事实和选择手段、借助判断和推理才能对道德行为起一定积极作用。这样:“理性是,并且也应该是情感的奴隶,除了服务和服从情感之外,再不能有任何其他的职务。”[1]立足于经验,休谟自然认为传统的思辨推理似乎是“完全不可思议的事情”。他之所以指出“这个新关系如何能由完全不同的另外一些关系推出来,也应当举出理由加以说明”,是因为他不承认这一推理的有效性。
基于以上分析,笔者以为所谓“休谟问题”并非如研究者通常所认为的仅仅是指对事实与价值的区分,而是有针对传统形而上学的特定内涵。其首先应指休谟对传统理性伦理学中“是”对“应该”蕴含关系的批判。至于伦理学界一直争论的所谓“事实”与“价值”的区分,也是顺理成章的,因为在休谟经验论的视域中,关于观念或事实的“是”之判断本身确实只关乎认知,而与德性无涉。
休谟对传统理性主义伦理学的批判破中有立,意义深远。他从其经验主义原则出发,对以往道德学说的独断性、盲目性和思辨性展开了系统而深刻的批判。“盲目接受的原理,由此而推出来的残缺的理论,各个部分之间的不相调和,整个体系的缺乏证据;这种情况在著名哲学家们的体系中到处可以遇到,而且为哲学本身带来了耻辱。”[1]休谟的批判表明,传统的至善实体由于超越经验因而是不可理解的,根本无法为人类生存价值奠基,而人类通达实体的超验能力只不过是非法的人性设定。以往道德学说作为指路明灯的价值理性已丧失了为人类制定普适规范的特权,而沦为本能的奴隶,让位于道德感与想象力。而认为有天赋的道德真理只是“狂妄自大的轻浮”。传统伦理学的合理性在休谟这里受到了根本的质疑。正如赖欣巴哈所指出的,只有休谟“摆脱了那些为了要替道德找一基础而不得不引入一个综合先天真理的人的错误,因此能够不带着道德论者的成见来研究知识。”[10]
由于只有批判了理性独断的权力话语,才能为价值问题的解决开辟新的方向,因而可以说休谟的批判实际上预示着伦理学范式的更替,其学说本身即构成范式转换的最初一环。就其建构性而言,休谟哲学反对超验性,而为感性正名。人的自由价值的寻求应充分肯定世俗情感的合理性。在此,休谟实际上表达了一条哲学的真理:任何理论都不应忽视经验。“哲学要是不同于健全人的感觉和以这种感觉为依据的理智,是不可能存在的。”[11]由之休谟将伦理学的探讨由实体主义的思考方式转化为关于主体的情感机制和心理根源的问题,为后人的研究开辟了新的方向。
我国哲学界之所以对休谟问题的原初涵义及深远影响一直没有深刻理解,一方面是由于对西方的伦理传统、尤其是对这一传统与西方语词文化的内在关系缺乏真正的的把握和透彻的参悟,因为在我们汉语中没有这一现象。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无批判地接受西方伦理学界的观点所致。而西方学界之所以长期对此亦无明确阐述,恐怕一者是因为一种传统的流变本身会掩盖自身的某些特质,另一方面可能是因为“事实”与“价值”区分在其看来更具实质意义。
“是”与“应该”的区分是休谟伦理学的难点,笔者所论只是一家之言,相信随着研究的深入,这一问题必将得到更为合理的认识。
[收稿日期]2007-06-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