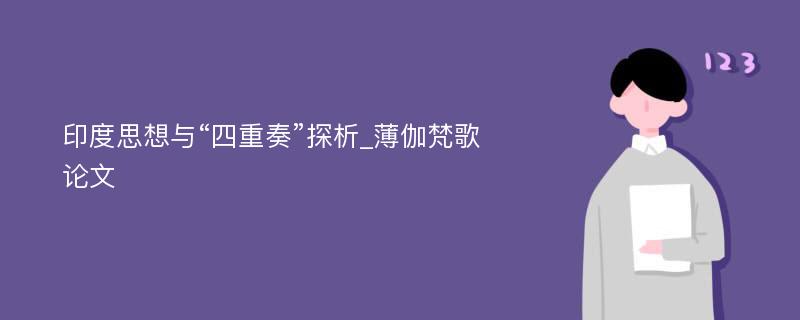
印度思想与《四个四重奏》探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印度论文,四重奏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托·史·艾略特曾经说过:“亚洲文学中有伟大诗篇,亚洲也有深刻的智慧和某些非常深刻的玄思……许久以前,我学习了古印度语言,而那时我感兴趣的主要是哲学,我也读了一些诗,我知道自己的诗歌表现出印度的思想和感觉。”[①]诚如他所言,他的代表作《四个四重奏》正是一部融东西方文化为一体的经典诗作。在这部诗歌中,印度思想的智慧与基督教思想,穿越时空,挪移随采,觑巧通变,精心构造,相互辉映,使得这部作品更加气势磅礴,博大精深。艾略特自己在《批评的功能》一文中指出:“当时我想到文学,想到世界文学、欧洲文学、某一个国家的文学,正象现在一样,并不把它当作某些个人写下的作品的总和来看,而是把它当作‘有机整体’,当作个别文学作品、个别作家的作品与之紧密联系,而且必须发生联系才有意义的那种体系来看。”[②]后来他在接受诺贝尔文学奖的演说中说道:“我认为诺贝尔文学奖——当她奖给一个诗人时——主要是对诗的国际价值表示肯定。”[③]《四个四重奏》无疑是具有国际价值的,艾略特正是运用这种具有东西方文化的“有机整体”来共同探索,“追求一个痛苦、寻求拯救的主题”,这部诗歌以其深邃的思想意蕴和独特的艺术结构而彪炳现代英美诗坛。笔者在本文中不揣简陋,参考诸家的观点,对该诗包含的印度思想影响试作钩玄发隐,以期抛砖引玉。
一、题解及其他
目前对《四个四重奏》的标题解释不一,各有其理。下面列举几家较有代表性的观点:
第一,许多人认为这四首诗分别代表空气、土、水、火四大元素,都以作者及其家族所住过、去过的地方做标题,好像是在做一生的回顾和总结。典型代表如伊丽莎白·朱在《托·史·艾略特:他的诗歌的设计》中认为,“整个结构是四合为一(a four—in—one),它把宇宙世界分为气、土、水、火四大元素,并用来象征性地表达人的本性成份,人成为宏观中的微观,人的抽象思维能力是气,人体的化学构造为土,人血中的生命流为水,人的灵魂是火。而每一首诗则具体强调四元素之一。”[④]
第二,有人认为《四个四重奏》是以探索时间与永恒为主题的,这四首诗分别代表一年中的春、夏、秋、冬四季。[⑤]
第三,艾略特将标题以四重奏命名,有其用意,且全诗的结构借鉴了奏鸣曲的格式。海伦·加德纳在《艾略特的艺术》[⑥]一书中作了较为详细的探讨,她认为,每个四重奏都有五个乐章,相应部分长度大致相等,结构类似,第一乐章通常是显示部,包含陈述与反陈述,相当于奏鸣曲的第一主题与第二主题;第二乐章比较抒情,用两种不同方式来表达同一主题,效果听起来像是用不同的乐器演奏同一曲子;第三乐章是每首四重奏的核心,冲突达到高潮,然后出现和谐与转折,令人联想起贝多芬的两个乐章之间的铺垫和连接段落;第四乐章是简短的抒情乐章;第五乐章概括了全诗的主题,回应与协调第一乐章的对立面。
吉廷德拉·库玛·莎曼在《时间与T.S.艾略特》[⑦]一书中从印度文化的角度对《四个四重奏》的标题与结构进行了探幽索隐,吉廷德拉认为某些印度经典的结构与《四个四重奏》有些类似,两者相互映照,可以平行阐发,下面请看几例。
印度的最早婆罗门教和印度教的经典——吠陀(Veda)包含着:吠陀本集、梵书、森林书、奥义书。这是指从广义上看用吠陀梵文写作的一些古代西北印度文献的总汇。对吠陀的狭义了解是单纯指吠陀本集。吠陀本集共有四部:(1)《梨俱吠陀》(《赞诵明论》);(2)《夜柔吠陀》(《祭祀明论》);(3)《娑摩吠陀》(《歌咏明论》);(4)《阿闼婆吠陀》(《禳灾明论》)。
根据印度传统,可以从四方面探求“人间的目的”(purushartha):达摩(Dharma,涉及人的责任与美德),财宝(Artha,财富的获得),爱欲(Kama,快感的获得),解脱(Moksha,从尘世中解脱出来)。所有这四种行为是个人的完整人生。
古代婆罗门教法典把种姓分为四种瓦尔那(原有“颜色”的意思):婆罗门(祭司),刹帝利(武士、贵族),吠舍(农民和手工业者)和首陀罗(奴隶)。
佛教中的基本内容有“四谛”(四种真理),四谛就是苦、集、灭、道。苦谛是讲现世存在的种种痛苦现象;集谛是讲造成痛苦的各种原因;灭谛是讲最终理想的无苦境界涅盘;道谛是讲为实现理想所应遵循的道路与方法。
达马扬·蒂·戈希在《T.S.艾略特的印度思想》[⑧]一书发现《四个四重奏》可以从印度的《薄伽梵歌》的四个重要瑜伽找到平行关系。虽然《薄伽梵歌》是分为十八诗章,但从中可以总结出四个基本的法则或者瑜伽供人们遵循:禅定瑜伽,智慧瑜伽,有为瑜伽,信仰瑜伽。《四个四重奏》中的四元素与这四种瑜伽有异曲同工之妙:空气(焚毁的诺顿)与禅有关,土(东库克)与行为有关,水(干赛尔维吉斯)与智慧有关,火(小吉丁)与信仰有关。《四个四重奏》正如《薄伽梵歌》的不同瑜伽,既各自独立成章,又合为一体来探索最高真实。
鲁迅先生说:“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⑨]艾略特本人在1917年写道:“一个作家的成长取决于前二十一年的积累的感觉。”[⑩]艾略特对印度文化的兴趣由来已久,他从小博览群书,那时读到有关印度的书籍颇感兴趣,且印象深刻,例如埃德加·阿诺德的《印度之光》是其中之一。后来上了哈佛大学正赶上哈佛的“黄金时代”,哈佛的师生当时正处于东方文化热的浪潮中,艾略特遇上一些当时杰出的学者。一位是诗人、哲学家乔治·桑塔耶那,艾略特向他学习过“历史发展进程中的社会理想、宗教、艺术与科学”。另一位是著名的人文主义者欧文·巴比特,虽然以后艾略特与巴比特的人文主义思想颇有分歧,但是巴比特要建立秩序的思想给艾略特打上了深深的烙印,此外,他还把艾的兴趣引向梵文与佛教。艾略特在研究生阶段,他选修了有关古印度语言和文学的三门课程,在当时有名的印度学教授查尔斯·洛克威尔·兰门指导下学习梵文和巴利语,又从师于詹姆士·霍顿·伍兹教授学习一年的钵颠阇梨的玄学,艾略特后来回忆这三年的东方语言和哲学的学习使他“处于一种豁然开朗的神秘境界。”[(12)]与此同时,他阅读了大量的印度经典,特别是对《奥义书》和《薄伽梵歌》,他是熟记于心。这对他以后的创作是受益无穷的,因此,我们从《荒原》到《四个四重奏》都可以发现印度文化的影响,这也是情理之中的。
二、回响在玫瑰园中
“焚毁的诺顿”的第一段中开始对时间进行哲学上的沉思,然后用具体的意象进行描述。“沿着我们不曾走过的那条走廊/朝着我们的从未打开的那扇门/进入玫瑰园。”诗中的叙述者进入玫瑰园所想到和见到的情景丰富多彩:玫瑰花,鸫鸟、第一道门、灌木丛、一圈杨木丛、水池。对艾略特这段玫瑰园的精采描述,评论家们各有阐释,他们都能从西方文学作品中找到类似的玫瑰园的情景描写[(13)]。有人说这与童话故事《阿丽丝漫游奇境》的玫瑰园情景相似,旨在回忆童年的世界;有人说这与纪尧姆、德·洛赫思的寓言诗《玫瑰的罗曼司》的花园类似,旨在引起读者联想到中世纪的爱情传奇,因为从这本书起玫瑰常用来象征爱情(在西方文学传统中);还有人说玫瑰园在此处有宗教的含义,暗指《圣经》中的伊甸园。笔者认为艾略特的玫瑰园在此处一喻多柄,可能含有多层象征意义,如上几层联想意义在全诗的上、下文都可以找到连接点。因限于篇幅,暂不做细论。
艾略特在玫瑰园中提到另一个中心点,“干的水池,干的水泥,褐色的池边缘,/池子里充满了阳光中流出来的水,/荷花在静静地,静静地,升高。”此处的“荷花”是借用于印度和中国文化的象征。在中国“荷花”亦称莲花,宋朝的理学家周敦颐的《爱莲说》传颂至今,濂溪先生对莲花着力赞扬,并借喻君子的品节:“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溢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14)]在印度的《恒多罗方法》(The Tantric Way)谈到“荷花”的象征意义:“正如荷花长于‘泥的黑暗’中,在水的表面开花,出污泥而不染。由此观之,内在的自我超越物体的局限,超越自身,这样就不受幻象与无知的污染。”[(15)]因此,“荷花”在印度思想中不仅意味着纯洁与完美,而且意味着沉思与觉悟。此外,评论家P.S.斯里(P.S.Sri)在《T.S.艾略特:吠檀多和佛教》一书认为,艾略特对玫瑰园的情景描绘与恒多罗的坛场(mandala)的结构相似,艾略特在“焚毁的诺顿”中写道:诗人通过“第一道门”后进入玫瑰园,走进“一圈黄杨树丛”,俯观“干涸的水池”,水池里神秘地充满了“阳光中流出来的水”,“荷花正长在池子里”。[(16)]在《恒多罗经》是这样描述坛场结构的:[(17)]“主要的形状是圆形,或是同一中心的多层圆,外有方形包围,四门可进入……坛场的中心指向宇宙,由一圈荷花围成宝库,象征着最高智慧。”因此,坛场在这里不仅是一个几何图形,而且充满着精神意蕴,《恒多罗方法》进一步解释说:“坛场是整体的浓缩,类似宇宙,它反映了宇宙形成的过程,元素的循环,以及其内部的对立面:尘世的和非人间的,静态和动态的之间的融合。”[(18)]另外,《恒多罗方法》指出运动的整个过程是“通向中心”,这是象征性地表示各种冲突在中心得到缓解与平衡。当人们看见坛场,自然陷入沉思,得到精神上的升华。诗人正是这样一步步地向“玫瑰园中心”走去,思考人与时间,生与死,痛苦与行为之间的关系,并且逐渐产生对最高真实的短暂领悟。玫瑰园在《四个四重奏》的整体设计中是非常重要的,全诗前后回照,“焚毁的诺顿”中的情景与“小吉丁”前后呼应,在“焚毁的诺顿”中的鸟、玫瑰、荷花,到“小吉丁”中出现了鸽子、火与光中的玫瑰,灵魂逐步得到升华。推而言之,通过玫瑰园的象征意义,整个《四个四重奏》亦可以象征地看作“坛场”,引导诗人和读者一步步地意识到各种矛盾的和谐统一。
三、在旋转的世界的静点
“轮子”是艾略特诗歌中用得较多的意象,这是从印度传统文化中借来的。在佛教中,“轮子”用来寓指轮回,有生命的东西在灭、人、阿修罗、饿鬼、畜生、地狱等六道迷界中生死相续,永无穷尽,犹如车轮没有始终地转着,所以叫轮回。轮回是与“涅盘”相对称,人只有中断轮回,才能抵达涅盘的彼岸。在吠檀多中用“轮子”的意象来表示不断变化与痛苦中的人类困境,如在《白骡奥义书》中写道:
“这广袤的宇宙是个大轮,万物在其上生息繁衍,围绕它不停地旋转。它是梵之轮,只要个人认为自己与梵分离,他就围绕轮子旋转,隶属于生息繁衍的规律,但是当通过神圣的梵时,他就意识到梵与他同在,他就不再随轮旋转,那它就达到了永恒。”[(19)]
在《薄伽梵歌》中克里希那(krishna)谈到生死的痛苦之轮时,将个人束缚到时间与环境的现象世界中:
“人的精神当在本质上感到自然不停变化状况,当他将自己束缚到不断变化事情上,好或坏的命运通过死中生围绕他旋转。”[(20)]
“轮子”的意象,艾略特在《荒原》中借用了,在《荒原》中“死者葬仪”这一章中借“梭斯脱里斯夫人”的口说,“这是带着三根杖的人,这是“转轮”……,接下来又说“我看到一群人,绕着圈子走”,这象征着伦敦人的生息繁衍的单调循环生活。艾略特本来在《荒原》的草稿中写了“伦敦,你的人民系在轮子上”,[(21)],还写了“汉普斯蒂德的居民永远系在轮子上。”[(22)]后来由于庞德的建议,艾略特在正式诗稿中将这两行删掉了,但这说明艾略特想借“轮子”来象征伦敦人虽生犹死的绝境。
在《四个四重奏》中,艾略特没有用“轮子”(wheel)这个具体的词,但是他很有技巧地用了相关的词和语境来表达这种意义。在“焚毁的诺顿”Ⅱ中的第二段开头写道:“泥土里的蓝宝石和石莲花/拥塞在陷进地里的车轴旁。”根据评论家格罗弗·史密斯的解释说,[(23)],蓝宝石和石莲花象征着“暴饮和贪婪的弥天大罪”,“泥”又象征着肉体的污秽与尘土,“车轴”是轮的中心,是与“静点中心”的意象相关,代表着人与上帝之间的连接点。当这种中心轴陷入不洁的肉体中,车轮的运转受到了阻碍,人世的罪恶与贪婪阻碍了轮子的自由运转,人生变得毫无意义。
人只有在伟大的模式中,才能克服自身的局限,他的存在的各种矛盾才能得到调和。在“焚毁的诺顿”Ⅱ的第二段中:
在旋转的世界的静点。既无众生也无非众生;既无来亦无去;在静点上,那里是舞蹈,然而既非止也非动。别称它是固定,过去和将来在此相聚。既非从哪里来也非朝哪里去的运动,既不上升也不下降,除了这一点,这个静点,别无其它的舞蹈,只有这种舞蹈。
这些诗行使人联想到旋转之轮的中心是中心轴,这个意象有多种含义,此处它强调不动者(上帝)和他的创造物之间循环运动的对立与协调。“舞蹈”在这里多次提及,它与印度文化中湿婆主(Lord Siva)宇宙之舞极为相似,这种“既非此又非彼”的句式结构在《广林奥义》中用来描述永恒的梵:
智者(灵魂,阿特曼,自我)
既未生,亦未死。
这个智者未从何处来,
亦未变成任何人。[(24)]
由此说来,“梵既非此又非彼”,使用排除法来肯定宇宙世界唯有梵作为最高境界而存在。艾略特在这里用“既非此又非彼”的否定结构来描述“静点”,这显然是受了印度思想的影响。
当人克服了自身的贪欲,获得了对静点中心的瞬间领悟,他就会有一种直接的启示:
新世界和旧世界,
在获得其部分的惊喜里,
在克服其部分的恐惧里,
变得明确,得到理解。
这种惊喜的瞬间与上、下文中的痛苦并不矛盾,是让人们对尘世的无常与痛苦增强新的认识,人们在对静点的领悟之中看待永恒中的瞬间,学会与本体的和谐相处,这样,现象世界的无常与痛苦就不会造成人的精神痛苦,轮子就可以不受人的不完美的阻碍,围绕中心轴自动运转。这种和谐生活在“东库克”Ⅰ的乡民围绕篝火舞蹈的场景中进一步表现出来:
绕着,绕着篝火,
跳过火焰,或者又汇合成几圈,
质朴的庄严,质朴的欢笑,
抬起穿着粗陋鞋子的沉重脚,
大地的脚,沃土的脚,
满怀着田园的快乐抬起脚,那是
很早以前在田里种植谷物的人的快乐。
这幅乡间舞蹈图是多么的质朴!多么地和谐!这与《荒原》和《空心人》中绕圈走大不一样。在《荒原》中,“我看到一群人,绕着圈子行走”,荒原人惶惶不可终日,在《空心人》中,“这里我们围着多刺的梨树走/多刺的梨树,多刺的梨树/这里我们绕着多刺的梨树走/在早晨五点钟。”空心人精神空虚,毫无人生目的。在《灰星期三》中开始出现了一种新的声音,“光照耀在黑暗中/这个不平静的世界依然旋转着抵抗那道/围绕这个寂静的道的中心。”在这里,叙述者虽然对他背叛的诱惑有依恋之情,但道出了叙述者人生观方向的改变。有的评论家说艾略特写《灰星期三》时也许是受了兰斯洛斯·安德鲁(Lancelot Andrews)一篇训诫中旋转之轮的影响,安德鲁写道:
此时是一年的转折点……现在万事在旋转,我们应该转向上帝……有两种旋转方向……一种是我们转向上帝,全心全意地转向他;另一种是我们偏离上帝时我们要反省自己的罪过……[(25)]
在《四个四重奏》中的篝火舞蹈象征着阴阳交合,丰收季节,象征着万物和谐,天地一体。艾略特正是运用这些若隐若现的意象来暗指轮子,轮子不停地运转,象征着存在的不停流动,天地万物都围绕轮子旋转,并在轮子旋转的高低弧线上找各自的位置。
四、难以置信的结合
《四个四重奏》在创作上是很受印度经典《薄伽梵歌》的影响,艾略特本人对《薄伽梵歌》评价很高,他说:“我们从但丁或者《薄伽梵歌》或者其他宗教诗那里学到了很多,这些诗让人觉得去相信那种宗教,《薄伽梵歌》就我所知是仅次于《天堂篇》的最伟大的哲理诗。”[(26)]现在让我们通过《四个四重奏》这部作品,来欣赏艾略特是如何借鉴《薄伽梵歌》及其如何与他的基督教思想相结合的。
首先,在时间的探索上,《四个四重奏》的开头就说:
现在的时间与过去的时间
两者也许存在于未来之中,
而未来的时间包含在时间过去里。
如果所有的时间永远是现在,
所有的时间都无法赎回。
艾略特这种历史和时间的循环观点从《薄伽梵歌》中找到了印证,从《薄伽梵歌》中我们得到了绝对时间的全面观点,诗中的黑天大神克里希那(krishna)综合了各个层次的时间:
我们在这里永久:我,你与诸王也是同样,我们将在此永久,我们将会永远。
往昔和现在的万有,
阿周那!我全都知晓,
我也知道将来的万有,
然而,对我却无人明了。[(27)]
克里希那督促阿周那(Arjuna)意识到:
阿周那!我是一切
创造物的始、末、中
我是无尽无休的时间,
我是形貌遍宇的载持。[(28)]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印度的时间概念是循环的,印度教的时间观是重复性,这种时间循环的观点与重生的原则有着逻辑的联系,艾略特在此是明显地受了印度时间观念的影响。同时作为基督教徒,艾略特在《四个四重奏》中未忘记在基督教的语境中探索时间,克劳德·德雷斯蒙坦(Claude Tresmontant)指出:“据说基督教时间是线性的……但是在这不幸的术语中仍然正确的一点是,基督教时间测度着一种创造,它不可避免地指向独特而确定的终极。基督教的时间是矢量性的”[(29)]。纵观《四个四重奏》,艾略特始终指向无时间瞬间的目标运动,全诗“不断以基督教术语,以基督圣徒、受难日、领报节和圣灵降临节等意象来表现。它力图表现时间除了朝向永恒运动之外,只是空虚和无意义。”[(30)]
其次,如何达到永恒呢?艾略特结合基督教思想与印度思想做了进一步的探索。在《干赛尔维吉斯》Ⅴ中:
然而,了解时间有限与无限的交叉点
是圣人的天职——
又不是天职,是他一生在
爱、热情、无私和自我屈从的牺牲中的一种给予和领受。
在该段诗中时间的有限与无限的交叉点指的是静点,它是所有运动与形式的源泉,是对永恒性瞬间的肯定。从基督教的观点看,世人一出生都是有罪的,这种罪是世代相传的(称为原罪),世上的一切苦难就是人类自己犯罪的结果,因此,人们必须要忍受一切苦难,唯有信靠一个救世主耶稣为人类赎罪,才能求得死后永生。作为基督徒,艾略特是信奉基督教义的,所以他在“干赛尔维吾斯”Ⅴ中进一步写道:“猜到一半的暗示,即了解到其中一半的馈赠,是化身。”化身一词在原诗中,他特地大写Incarnation,并未加冠词,这表明耶稣是上帝的唯一化身。但这两行诗与“干赛尔维吉斯”Ⅲ中的“我有时不知道那是否是克里希那的本意——尤其是——或者是表达同一事物的一种方法。”这样,克里希那与基督化身——耶稣前后呼应,有的评论家认为这是艾略特的一处败笔,因为“基督教与印度教的时间观与历史观不一样”,[(31)]基督教义的唯一化身与吠檀多中的多重化身(克里希那是化身之一)是相互矛盾的。但是又有的评论家认为这是对基督教的时间观与历史观的进一步充实,也许是暗示基督的降临。[(32)]笔者以为诗歌的艺术创造性有时可以突破教义的条文,通过读者的想象将它们神奇地结合一体,既然克里希那和基督都是永恒的化身,艾略特在诗歌中为其所用,大大地丰富了该诗的内涵。正如他在该诗中所言:
在这里确实有
几种存在范畴的难以置信的结合,
在这里过去与未来
得到了克服与统一,
艾略特曾说,“我不是佛教徒,但是早期佛经的某些部分对我的影响就如《旧约》一样。”[(33)]由此可见,艾的基督教观有时是可以与印度教和佛教相互协调与补充的。因此,有的评论家说,如果艾的诗歌中没有印度思想的影响,艾略特照样是个好诗人,但是他的诗歌不可能如此博大精深。笔者以为此言是有道理的。
注释:
① T.S.Eliot:Notes Towards the Definition of Culture,London,1948,p.113.
② 《艾略特诗学文集》,王恩衷编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p.61。
③ 《四个四重奏》,裘小龙译,漓江人民出版社,1991,p.287。
④ Elizabeth Drew:T.S.Eliot:The Design of ltis Poetry,New york,1949,p.146.
⑤ 江先春:“诗的音乐结构”,见《国外文学》1987年1期。
⑥(31)Helen Gardner:The Art of T.S.Eliot,New york,1950,p.36-56,173.
⑦
Jitendra Kumar Sharma:Time and T.S.Eliot,New Derhi,1985,p.69-70.并参阅黄心川著《印度哲学史》p.32,商务印书馆,1989。
⑧(12)(24)Damayanti Ghosh:Indian Thought in T.S.Eliot Calcutta,1978,p.56,24,92.
⑨ 《鲁迅全集》,第6卷,第425页。
⑩ Egoist,Ⅳ,2(Dec,1917).
(13)(32)Staffan Bergstan:Time and Eternity Stockholm,1960,p.164,p.288.
(14)《中国历代散文选》下册,刘盼遂主编,北京出版社,1981,第228页。
(15)(16)(17)(18)(19)(25)P.S.Sri:T.S.Eliot,Vedanta and Buddhism,Vancouver,1985,p.102,103,103,104,34,48.
(20)The Bhagavad Gita,tr.,Juan Mascaro,Harmondsworth Penguin,1962,p.101.
(21)(22) T.S.Eliot,The Waste Land,(a facsimile and transcript of the original drafts including the annotation of Ezra Pound),ed,Valerie Eliot,London,p.31,103.
(23)Grover Smith:T.S.Eliot's Poetry and plays,p.261.
(26)T.S.Eliot,"Dante",Selected Essays,London,1958,p.258.
(27)(28)《薄伽梵歌》,张保胜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p.91,123。
(29)(30)史成芳:“无常与永恒之间”,见《外国文学》,1993,2。
(33)T.S.Eliot,The Use of Poetry and the Use of criticism,London,1933,p.9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