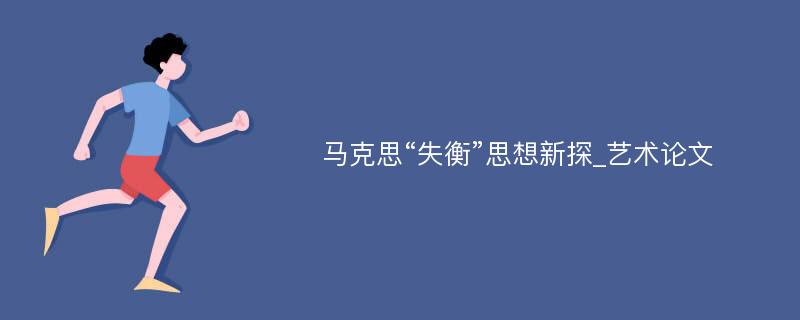
马克思“不平衡”思想新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不平衡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766(2000)02—0069—04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提出了著名的关于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发展的不平衡关系的论断。这是他对文艺学所作出的一个重大理论贡献。
我国文论界对马克思的“不平衡”思想, 在1951 年、 1959 年和1978年曾有过三次规模较大的讨论。这三次讨论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在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上均有所拓展,但总的看来,都还停留在一般地把艺术的发展同社会物质生产的发展从现象层次上作分析比较的水平上,没有意识到艺术随社会所发生的深层次的现代转型,因而也就不能从艺术作为社会生产形式和部类这一新的视点上去分析和比较它与社会物质生产发展的关系。所以,它们的局限性也是很明显的。
现在,我们已经越来越清楚地看到,马克思的“不平衡”思想乃是运用辩证、发展和深层次转型这样一种相当深刻和超前的眼光、方法对艺术发展作思想和宏观把握的结果。它包含着三个基本的命题。
第一个是关于“在艺术本身的领域内部的不同种类的关系中”的不平衡命题:
当艺术生产一旦作为艺术生产出现,它们就再不能以那种在世界史上划时代的、古典的形式创造出来;因此,在艺术本身的领域内,某些有重大意义的艺术形式只有在艺术发展的不发达阶段上才是可能的[ 1](48页)。
第二个命题是关于“在整个艺术领域同社会一般发展的关系上”的不平衡的命题:
希腊人是正常的儿童。他们的艺术对我们所产生的魅力,同这种艺术在其中生长的那个不发达的社会阶段并不矛盾。这种艺术倒是这个社会阶段的结果,并且是同这种艺术在其中产生而且只能在其中产生的那些未成熟的社会条件永远不能复返这一点分不开的[1](50页)。
第三个命题则是在《剩余价值理论》中提出的。针对俄国经济学家施托尔希对精神生产问题的荒谬解释,马克思在强调了必须在以历史的观点看待物质生产的基础上去理解与之相适应的精神生产这一原则之后指出:
而且,这种关系本身也完全不像他原先设想的那样简单,例如资本主义生产就同某些精神生产部门如艺术和诗歌相敌对。不考虑这些,就会坠入莱辛巧妙地嘲笑过的十八世纪法国人的幻想。既然我们在力学等方面已经远远超过了古代人,为什么我们不能也创作出自己的史诗来呢?于是出现了《亨利亚特》来代替《伊利亚特》[2](295—296页)。
在这里,第一个命题和第二个命题都是就艺术本身尚未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社会生产部类,它还只是一种纯粹的精神创造活动这样一个历史阶段,也即“艺术发展的不发达阶段”而言的。在这个历史阶段上,一些“有重大意义”的艺术形式,例如史诗和神话等,是由无数的创作者、传播者和接受者一起,在创作、传播和接受并无明确严格的划分的情况下,经历了漫长悠远的时代所共同创造出来的。它们不但是无数人智慧的结晶,而且是某种类型的文化累积叠加的结果,包含着这一阶段物质、精神文化多方面多层次的成果,其广阔深厚有如浩瀚的海洋,远非后世所说的那种艺术所能囊括和包容,更不是近现代“艺术生产”的独立或小群体操作方式所能创造出来的。它非个人所能及,主要也不靠艺术的才力,而是靠世世代代的非自觉的积淀和叠加。所以,当我们说连但丁、莎士比亚、托尔斯泰等大师们也无法创造出这样的艺术形式和作品时,这并不是在贬低大师,而只是指出了两种不同的艺术创造方式的区别。人类历史的进程总是这样,每一种进步也往往意味着某种丧失。当我们用进步的“艺术生产”的方式推动着艺术的进步和发展,把“艺术发展的不发达阶段”远远抛在身后之时,我们也就永远失去了只有用那种不发达的方式才能创造出来的艺术奇观,那种“就某方面说还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这就是艺术的辩证法。
因此,结论就应该是,像史诗和神话这种“有重大意义”的艺术形式,它们与产生它们的那个不发达的社会阶段并不矛盾。“这种艺术倒是这个社会阶段的结果,并且是同这种艺术在其中产生而且只能在其中产生的那些未成熟的社会条件永远不能复返这一点分不开的。”
这不是明明在说相适应、相平衡吗?那么,为什么又说它们是“不平衡”的命题呢?
这里的关键是在“发展”二字上。就是说,正是由于这些艺术形式与产生它们的社会阶段是适应的、平衡的,甚至是“分不开的”,是这一特定的社会阶段的历史和审美的规定性的积淀及抽象化凝结,打着深刻的时代的烙印。因此,一旦社会发生巨大变化,则这些艺术形式便会因其与旧的时代的过于紧密的内在联系而难以改造、不堪改造,从而陷于停滞、衰落甚至于消亡的境地。当年伏尔泰不是曾殚精竭虑地创作出史诗《亨利亚特》,想要救活这种早已死亡的远古的艺术形式吗?结果不但未能挽狂澜于既倒,反而在文学史上落下了一个“不识时务”的笑柄。
所以,过于平衡、过于适应是会反过来造成发展的不平衡的。综观中外文学史,可以发现,如果一种艺术形式的时代特点越是突出和明显,则其命运也就往往越是短暂。除了马克思所指出的远古神话和史诗而外,像西欧中世纪的英雄史诗、骑士文学、宗教剧,我国古典文学中的汉赋、唐诗、宋词、元曲等等,都曾盛极一时,但随着时代的变化不也是或消亡,或停滞衰落,都呈现出“不平衡”的景观吗?
由此看来,马克思所说的“不平衡”,决非偶然,而是带有普遍性和规律性的现象。
但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马克思并不认为“不平衡”是艺术发展过程中的基本规律。他明确地指出:“必须把这种物质生产本身不是当作一般范畴来考察,而是从一定的历史的形式来考察。例如,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精神生产,就和与中世纪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精神生产不同。如果物质生产本身不从它的特殊的历史形式来看,那就不可能理解与它相适应的精神生产的特征以及这两种生产的相互作用。”[2] (296页)
可见,在马克思看来,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的关系在总体上还是相平衡、相适应的,而所谓“不平衡”仅仅是限定在“某些有重大意义的艺术形式”这样一个范围之内的。因此,总体上的相平衡、相适应和局部的不平衡、不适应的辩证统一,相对的平衡中包含着绝对的不平衡,这才是马克思对艺术与物质生产、艺术与社会生活关系的全部理解,它构成了马克思的艺术发展理论的基本观点和思路,成为我们解开艺术发展之谜的钥匙,并在具体的实践中不断得到证明。
至于马克思所提出的第三个命题,也就是通常被称作“相敌对”的命题,其所针对的则是艺术的“资本主义”阶段,亦即在“艺术发展的不发达阶段”之后的、真正意义上的“艺术生产”阶段。在这个阶段上,艺术已由一种纯粹的精神创造活动转型为图书出版业这一社会生产部类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兼具工业、商业、科技和文化等多重性质的“文化工业”。因此,“诗歌”——马克思在此明确是指“史诗”——与“资本主义生产”的“相敌对”实属必然。其理由如前所述,兹不赘言。事实上,史诗对于今天的人们而言,它的意义犹如史前的恐龙化石,只在于它保留下了一段早已消逝的历史。
那么,“艺术”,包括绘画、雕塑、音乐等等,为什么也会与“资本主义生产”“相敌对”呢?
这首先是因为当“资本主义生产”把艺术纳入自己的轨道,使之成为一种社会生产形式和部类,对之进行彻底的改造之时,它也就强化了艺术的异化状态,使艺术家成为了一种工具化、机器化的“非人”。
艺术是天才和灵感的领域,它靠的是深厚的生活积累,精湛的艺术修养、技巧,以及精神上的高度自由和激情。
但“艺术生产”却把艺术家变成了像工人一样的由资本家“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变成了按市场的需要和资本家的指令去进行工艺式操作的匠人。于是,自由、激情、灵感没有了,独创性没有了。原来是表现和丰富人性的天地变成了对人性自由的严重束缚和扼杀。
这不是“相敌对”又是什么呢?
而且,艺术的作品,包括绘画、雕塑、音乐的演奏、演唱等,都是一次性的,不可重复的。但“艺术生产”的印刷出版术及其他技术,如石印、照相、铸模、录相、录音等把它们统统变成了复制品,使之永远失去了其独一无二的韵味、气氛、圣洁性。因此,艺术大贬值、大沦落了。从这个意义看,艺术与资本主义生产也确是“相敌对”的。
但这种“相敌对”状况的出现是否完全悲观的、纯粹否定意义上的呢?
要正确地回答这个问题,回顾一下本雅明的有关论述,可以得到很大的启发。
本世纪30年代中期,本雅明曾在他名噪一时的《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作为生产者的作家》等著作中对他自己所提出的关于“艺术是一种社会生产形式”这一基本观点作了深入的探讨。他从追溯“艺术作品的机械复制”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敏锐而深刻地发现了一场艺术的“伟大革新”的到来。他指出,随着印刷术、石印术、照相术等的发明和推广,“技术复制已达到了这样一个水准,它不仅能复制一切传世的艺术作品并由此对公众施加影响,引起极为深刻的变化,而且还在艺术的制作领域里为自己攫取了一块地盘。”[3](243页)于是,“艺术的神学”被击碎了,“机械复制在世界上开天辟地第一次把艺术作品从它对仪式的寄生性依附中解放出来”,使之由少数人的工具和玩物一变而为群众的生活方式,回归到“现代的群众运动”之中[3](241页)。从此“艺术的功能就颠倒过来了,它就不再建立在仪式的基础之上,而开始建立在另一种实践——政治的基础之上了。”[3](248页)
本雅明的独创性的贡献在于,他抓住了生产工具这一生产力要素,从其变化发展中发现并阐明了艺术的现代性质——社会生产、商品生产性质。伊格尔顿在评介本雅明时正确地指出,本氏的这一发现来自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中的“相敌对”命题,但又有所发挥和深化,是对马克思思想的很有价值的重大发展。
因此,马克思的“相敌对”的命题,所揭示和阐明的只是艺术成为一种社会生产的形式和部类这一现代性转型所引起的巨大而深刻的冲击。正是在此冲击下,出现了巨大的进步与巨大的丧失并存,大普及之中又有大沦落,伟大的天才同时又是异化了的非人等矛盾现象,使人们产生种种困惑。但是,只要我们用辩证发展的眼光,并不简单化地把艺术的发展理解为一个一浪永远高过一浪的直线上升过程,更不把它看成是一个不断抛弃负面因素,向至善至美境界进发的辉煌的历程,那么,我们便能清醒地意识到,“相敌对”命题正是对“艺术生产”发展规律的深刻的发现和揭示。
对马克思的“不平衡”思想,本文的研究还只能说是粗浅的,但即便如此,我们仍然可以明显地感受到这一思想的巨大理论魅力。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是迄今为止对艺术发展问题作出的最具深度、最具全面性和启发性的阐释,而对它的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则必将开拓出一个全新的理论领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