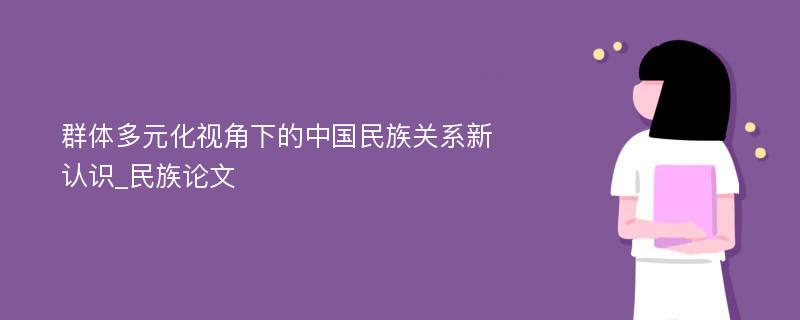
从团体多元主义的角度重新理解中国的民族和民族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族论文,中国论文,团体论文,角度论文,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G95/G5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09)06-0104-03
在拉萨“3·14”事件和乌鲁木齐“7·5”事件发生之后,出现了一种怀疑甚至否定中国的民族政策乃至“民族”概念和民族识别、认为中国民族关系出现危机的言论。事实果真如此吗?
我们先从民族—国家的建构和世界上多民族国家解决民族问题经验背景下审视中国的“民族”和民族识别。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为多民族国家,单一民族国家的数量非常有限且往往并非真正意义的单一民族国家。纵观世界历史和多民族国家民族关系模式,各国处理民族或族群关系的模式主要有以下四种:第一种是种族主义,其极端的典型是德国在纳粹时期对犹太人的排斥与杀戮;第二种是民族同化,其代表性例子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前的美国;第三种是自由的多元主义(liberal pluralism),即民族性或族群性的选择是个人选择而非集体规则,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后的美国民族政策是其代表;第四种是团体的多元主义(corporate pluralism),民族或族群得到国家的正式认可,并采取政策给予保护。在这四种模式中,第一种被唾弃,无须多言;第二种遭到多元文化主义的强烈批评,在此也不必赘述;第三种采取自由选择的路径,国家不进行民族或族群识别,即本国究竟划分为多少族群或民族,国家不做统一规定,个人归属于哪个族群完全自主选择,其优长之处是赋予个人以充分的选择权,其弊病是无法真正实现各族群或民族平等且公平地参与国家事务和经济体系,在“优胜劣汰”的自由竞争规则下那些不具备人口数量、经济资本、政治资源优势的族群往往被政治和经济边缘化;第四种实现的条件是国家必须对公民进行以文化为标准的群体划分即民族识别,使之成为被国家认定的具有边界和法律地位的群体,国家据此从民族的群体划分角度对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资源进行分配与调整,其优势在于国家能够按照民族身份分配与调控资源,让组成国家的各个民族都有表达其诉求的正常渠道,一定程度上较完整地体现了“民族—国家”的真正含义,其劣势在于一定程度抑制了公民自由选择与变换民族身份的空间。
从这个意义上看,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体和国家结构的设计者尚无“文化多元主义”的理念,但自鸦片战争以后,抵御外族侵略的民族解放一直是动员革命运动的旗帜,如孙中山的“五族共华”思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故而让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各民族能够平等参与国家治理和利益分配的思想无疑会深刻地影响着国体和国家结构的设计者及其设计过程。如何保证各民族平等地参与国家政治事务和利益分配呢?前提是确定各民族的群体边界和法律地位,否则国家无法按民族身份进行政治和经济的制度安排。民族识别的重要目标就是确定公民的民族群体身份。族群和民族都是以历史形成的文化传统为标准划分出的社会群体,但两者具有明显的区别:前者未经国家制度的确认,其身份具有任意性和流动性,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具有法律规定性的稳定的社会群体,国家难以对其权益进行制度性安排;后者却是经过国家确认的具有法律规定性的稳定的社会群体,其获得平等、公平的权益分配具有制度化实现的基础和条件。因此,从国家制度和法律的角度看,中国的“民族”与西方的“族群”具有根本性的区别,无法互相替换,更不能用“族群”替代;中国的民族识别,无论划分的具体标准是否准确,也无论划分的结果是否完全恰当,但都是体现“民族—国家”体制的实质、保障各民族群体平等参与国家治理和权益分配、实现“团体多元主义”的必备条件。
我们再从世界民族/族群关系的演变历程和中国社会转型的角度来评估目前中国民族关系的状况。许多国家的民族/族群关系经历了封闭→接触→竞争→或同化或消灭或分离或多元文化平等共荣的过程。在封闭阶段,各个民族/族群社会处于封闭循环的状态,与他族几乎没有联系,偶尔会因争夺土地、人口等资源而爆发战争,其结果往往是败者退避三舍、远遁他乡,随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各民族/族群社会又回归到自我循环的状态,日常生活圈主要在民族/族群内运行;在接触阶段,民族/族群社会之间开始互动,但主要限于人员往来、交换有无以及偶然的婚姻关系等范围,大体上属于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所说的“机械团结”的阶段,联系较为松散、利益相关性较弱、互动程度较低,因而产生摩擦、冲突的机会和可能性较少;进入竞争阶段后,民族/族群社会之间进入频繁互动、全面互渗的“有机团结”阶段,“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社会网络和文化表征无处不在、无时不在,联系日益密切、利益关系交织,由表层性互动深入到深层性互动和结构性互动,接触的常规性和频繁化必然造成个体之间摩擦的可能性,其中有些就有上升为群体之间摩擦甚至冲突的可能性,同时,许多民族/族群之间的互动或直接或间接地涉及权益竞争因素,而竞争不可避免地产生输赢、得失的结果,既涉及客观现实上的权益分配有无和多少问题,又涉及主观评判上的是否平等、公平、公正问题,倘若制度安排、政策调整、文化建设和心理调适等不能做到及时有效,就为以民族/族群为单位的群体性摩擦与冲突的爆发留下了可能性。由此可以说,作为由国家所确认的社会群体,民族本身必然带有政治性;作为以历史形成的文化传统为标准划分的社会群体,文化是确立民族边界的依据和基础,但既然是社会群体,无论是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关系还是民族与国家的关系,都不可避免地含有政治的内容,“政治化”拂之难去。
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由封闭走向开放、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农民由固定的土地和农村转向自由流动,各民族之间由原来的较少接触发展到频繁接触、由简单联系(如民族间的个人交往)到复杂联系(如不同民族在生产、交换、分配等经济过程中的分工)、由表层互动(如物品交换)到深层互动(如在企事业单位内多民族共事)等,加之各民族维护自身权益的意识、竞争意识和能力的增强,中国的民族关系开始由接触阶段进入了竞争阶段。从世界民族/族群关系演变过程来看,近年来中国出现的一些民族矛盾和民族问题乃竞争阶段难以避免的现象,绝非中国有关民族的制度安排和政策设计所致,而且从总体上看属于程度较轻、范围较小、处置较好的。放眼世界,多民族国家中几乎找不到没有民族/族群矛盾的,从前苏联、南斯拉夫等东欧国家,到所谓“民主国家”,民族矛盾均在所难免,如加拿大的魁北克问题、英国的北爱尔兰问题、西班牙的巴斯克人问题等。就连被视为世界解决民族关系问题典范的“族群天堂”比利时在2007年10月也出现法语区与荷语区的对立。当然,这并不等于说,对于业已存在的和可能出现的民族矛盾可以视而不见、听之任之,只不过不能妄自菲薄与悲观评判当前中国的民族关系,而应从国际的视野和历史的角度做出理性、客观、准确的判断。同时,我们也应该认识到,中国民族关系开始进入关键时期,步入多种可能性的“岔路口”:或同化,或消灭,或分离,或多元文化平等共荣。此时,需要从维护各族人民利益、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国家利益出发,更为重视民族问题,更为有效地调整民族关系,更为谨慎地处理民族矛盾,使中国的民族关系朝着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方向发展。
最后,从世界多民族国家有关民族/族群问题的实施结果来评判中国处理民族问题的制度安排和政策措施。多民族国家的国家结构设计存在三种模式。第一种是不体现多民族/族群的模式,即多民族/族群的特性在国家结构设计上被忽略不计,如美国的联邦制。民族/族群的存在需要以一定的空间为载体,如国家不赋予民族/族群的存在空间以特定行政区划建制和权力,那么事实上民族性/族群性就会被漠视与同化,故而美国的文化多元主义无法走向团体多元主义的道路,其结果必将导致主流文化同化少数族裔的文化。第二种是民族/族群自治,即赋予民族存在的空间以具有次级国家权能的地方行政区划,如前苏联的加盟共和国。这一模式存在着明显的民族独立的潜在危险性,国家控制力略有弱化便会导致国家分裂,前苏联的解体与其国家结构设计的缺陷具有密切的关联性。每个民族都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从而形成单一民族国家的现实性是不存在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解构与分裂是社会破坏性非常严重的灾难性事件,受益者只有政治集团特别是少数人物,所带来的灾难让各民族/族群大众承受。第三种是民族区域自治,这是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和国家结构设计,其特征是赋予少数民族集中居住的区域以特殊的行政区划建制和民族事务自治权力,此项制度设计的基点是平衡少数民族的自治权与国家统一的完整主权。为了保障少数民族文化多样性权益,赋予民族自治地方不同于非自治地方的特殊立法权和行政权力;自治地方不具有像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次级国家权力,为了维护国家统一和主权完整,其自治权限定在不妨碍、不危及国家统一的范围之内。同时,针对少数民族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现状,中国政府制定与实施了一系列的经济、教育、干部等方面的扶持优惠政策,以求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构建平等团结的民族关系。尽管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及民族政策有待于进一步完善,但实现了既保证少数民族文化多样性又保障国家统一性的基本目标,极大地改善了少数民族的生存条件和发展条件,有力地推动了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