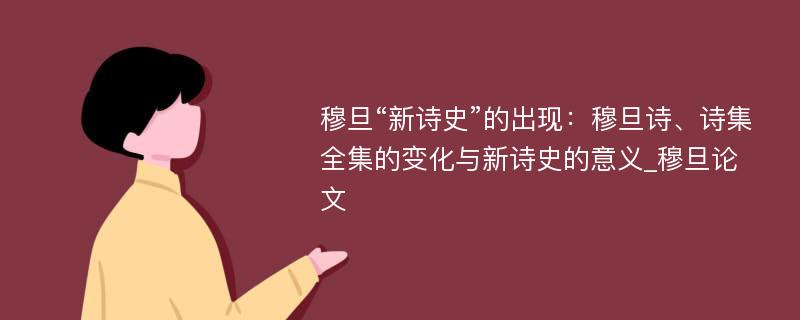
穆旦的新诗史状貌——《穆旦诗全集》、《穆旦诗文集》的变动及新诗史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诗史论文,穆旦论文,状貌论文,诗文集论文,变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28X(2007)020023-06
历史犹如遥远而模糊的景象,而关于历史的叙述一方面是时间进程中人类生活经验的总体呈现与记忆,一方面则是史家根据自己对过往资料的理解而拼贴重组出的图像。然而不管文学史家能否复现历史的原貌和真实,我们都会注意到史料在文学史研究以及具体文学史写作过程中的重要性。而对于曾长期在新诗史写作与研究中被忽视的穆旦而言,由李方编选的《穆旦诗全集》(1996)和《穆旦诗文集》(2005)对穆旦的研究而言无疑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推动作用。
从1996年《穆旦诗全集》编定,到2005年《穆旦诗文集》重编,不觉又近十年过去。其间世纪交替,社会转型,时尚与落伍相反相成,起伏变幻,令人目眩。然而,作为中国现代诗史上堪称奇崛的“穆旦现象”,却始终未如某些聪明的臆测那样“热”起来。显然,编纂这部诗文集并非想要什么“风行”与“火爆”,因为诗意这个终难界定清楚的东西,似乎生就并在更多时候是同沉寂与沉郁相伴[1]393-394。
《穆旦诗全集》和《穆旦诗文集》的史料是有增删和变动的,尤其是穆旦在不同时期改动诗作的情况对于研究诗人的写作是很有裨益的,版本研究在新诗史写作中应该受到重视。穆旦日记和书信则使穆旦的新诗史形象更为丰富和复杂,这对于考察穆旦在建国后特殊的诗人心态、诗学观念和特殊的新诗传播方式都相当重要。
史料挖掘与文本的变动情况
在穆旦和“九叶诗派”逐渐受到研究者倚重并几已成为新诗史经典的今天,需要注意的是穆旦诗歌的不同版本及变动情况。李方在《穆旦诗全集·编后》中谈到所收诗作除个别文字错讹核改外,均以诗人的正式发表稿或手稿为准,“不同时间或不同版本发表的同一作品,文字若存差异,则以作者的修订稿或最后版本为准”[2]420。考察穆旦不同时期诗的手稿、诗集、报刊就会发现这些诗在标点和字句上有改动情况,有的变动甚至是相当大的。这些诗作之间的变动与差异应该引起研究者的注意。而通过考察《穆旦诗全集》和《穆旦诗文集》的史料的变动,则可以相当有力地呈现出一个特殊时代的诗人的写作史与多难的灵魂挣扎史,并且呈现出穆旦修改诗作的大致情况。
在当下的新诗史写作实践与研究中,“文革”时期的“地下诗歌”写作随着80年代中后期以来相关史料的挖掘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和“青睐”。在洪子诚看来,“地下诗歌”史料的挖掘在80年代以来“经历了因服从于某种意图,而在叙述上不断累积的‘清晰化’过程。”[3]109洪子诚所说的“服从于某种意图”的叙述的“清晰化”的过程显然指涉诗歌史家在新的历史语境下的整体走向,即研究者更情愿追随和挖掘与“现代主义”相关的诗歌史线索,这条线索在许多当代新诗史实践和新诗研究论著中都有着相近的处理。而在这一发掘与“构造”过程当中,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就是文本的写作时间与发表时间相互龃龉的问题。对于特殊时期内的“非主流”诗歌的叙述以及构造,研究者往往遇到难题。一是在“文革”期间采取特殊的传播方式在不同范围内秘密传抄和流传的作品,如穆旦、食指、多多、芒克、北岛、舒婷、顾城等人的早期诗作。这些作品一般是迟至“文革”结束之后才得以在正式刊物发表。另一种情况就是在50年代至70年代的一些由于在思想艺术上与当时的主流文学规范相抵触,不被认可因而也不可能公开发表的作品。由于写作时间和发表时间处于两个差异很大的时期,显然写于“文革”和写于“文革”后的文本的文学史意义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所以洪子诚在研究中很注意这些文本的时间问题。“确定作品的写作、特别是发表的年代,是文学史研究(包括与此相关的作品编选)的一项基础性工作;这对所有的文学史写作来说都是这样。不过,中国‘当代’诗史在这个方面有它的特殊问题”[4]。既然如此我们是否可以根据公开发表时篇末注明的时间来确定作品的写作年代?这些文本在从写作到发表过程中是否经过了修改?
对于读者而言,一首诗写在什么年代可能并不重要,读者也往往是从美学角度来评判一首诗的优劣,而对于新诗史研究而言,有时时间界限对判定一首诗的文学史价值就不是无关紧要的。而且对于诗史写作来说“它还承担了考察诗歌文体沿革,诗歌精神流脉的任务。所以,时间的确定就不是可有可无的工作”[4]379。如《妖女的歌》一诗的写作时间问题,在《穆旦诗全集》中该诗的写作时间注明是1956年,而在《穆旦诗文集》中则更改为1975年,而对于建国后的新诗研究而言,一首写于相对宽松的1956年和写于严苛的“文革”时期的诗作其新诗史意义肯定是有区别的。
作品系年的认定工作也是相当复杂的,对作品语境的确认也历来是文学史最基本的工作。按照福柯的观点重要的不是话语讲述的年代,而是讲述话语的年代。
作品的系年在许多情形里,都可借印有书名的书页上所附的刊印日期,或借当时出版、印刷方面的证据来确定。但这些明显的外在证据常常缺失,例如,许多伊丽莎白时期的剧本和中世纪的手抄本都有这种缺失的情形。一个伊丽莎白时期的剧本很可能是在首次演出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才刊印出来的;中世纪的手抄本可能是抄自原作写成后数百年的另一个抄本。因此,外在的证据必须由本文里的内在证据来补充,如从同时代一些相关的事件找到暗示,或从别的可查考的日期的事件引出的线索等都是这类内在的证据。但这种能补充说明外在证据的内在证据,只能确定该作品与那些外在事件有关的部分的写作日期。[5]59
值得注意的是《穆旦诗文集》收入了以往穆旦各种诗集包括《穆旦诗全集》在内未收入的一些诗作,如《法律像爱情》和《伤害》,这对于穆旦研究尤其是“文革”诗歌而言其意义是不言自明的。
法律是太阳,园丁说,/法律是一种规格/一切园丁都得遵守/昨天,今天,以至永久。∥法律是古老的智慧,/曾被无力的祖父尖声责备;/孙儿吐舌发出最高音:/法律是年青人的理性。"法律,教士以教士的神情,/对一群没有教士派的人解释/法律是,我的传教书里的文字,/法律是我的讲坛和教堂的尖顶。"法律,法官以视线一扫鼻尖/最严厉而又清楚地说,/法律是,我曾告诉你们过,/法律是我想对你们很明显,/法律是,让我对你们再解释一遍/法律就是法律。∥可是守法的学者书写:/法律不是什么对和错/法律只是一些罪恶/受到时间和地点的惩处,/法律是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人们所穿的衣服,/法律是早安和晚安。∥又有人说,法律是我们的宿命/又有人说,法律是我们的国家/又有人说,又有人说/法律不再存在,/法律已经走开。∥那总是声势汹汹的人群,/非常愤怒而高喊着说:/法律是“我们”,/还是那总是轻柔的白痴的“是我”。∥假如我们知道,亲爱的/我们不比他们更懂得法律,/假如我不比你更懂得/我们该做和不该做什么,∥只知一切人都同意/也许高兴也许悲哀地[6]368-370
穆旦在《法律像爱情》这首诗中相当理性地呈现出“文革”中法律的搁置、人性的扭曲、自由的无望。在强大的无主体性的“汹汹”的对“权力”膜拜的绝对服从的人群(“我们”)中,诗人感到了作为个体的“我”的无助的“白痴”状态。
首次在《穆旦诗文集》中露面的《伤害》一诗最初是发表在1942年2月27日的《贵州日报·革命军诗刊》上,全诗如下:
这样的感情澎湃又澎湃:/酸涩,是的。因为你们底自尊心/践踏了我底;你们底目光/含蓄,把我底世界包围;/你们底偏见随着冷淡底武器要在/我无防而反复的心上开垦,/你们,你们,你们,/即使你们全是地面,我是海水。”你们是施与者/注来沉郁和外界底影——不,/独立从愉快中伸出来,愉快/把我漂浮。我是拒绝反映的/液体,是抱紧你们的波涛,/我将要笑过嘴里的剑锋,/无形的网,热带和寒带:/没有你们底存在能够拦阻,/我将向自己底偏见奔跑。/以我底热血和恐怖/那里,把它塑成一个神,/一个神永远潜伏在海底,/一个神发光,统治,复仇。"我将要歌唱/生底威胁,生底严密;/说我是狭窄的,谁肯/永远忍耐着,等死后的判断和遗忘?/我不愿意存在像不动的真理,/平衡,解说,甚至怜悯/一切胜利和失败底错综,/这一切是吸力,我是海水。/我不愿意你们善良,像贼,/送来歉意,和我妥协,/因为现在是这样真实而孤单的/我拒绝的痛苦:我底记忆![6]217-218
实际上,穆旦在“文革”后期,在他生命的暮年集中爆发和闪现的诗歌写作的光辉并不只是呈现为我们目前所见的近30首诗作。李方根据穆旦家属提供的穆旦遗存手稿辑录成的《穆旦晚期诗作遗目》共列诗人晚期诗作59首,其中有一部分收入到了《穆旦诗全集》和《穆旦诗文集》中,但其余的则已散佚。
《穆旦诗文集》由于增加了大量的图片、手稿从而将遥远发黄的历史拉近到当下,在与历史的对话中相当真切而直观地呈现出历史的现场感。相当有意味的是穆旦这些诗作手稿的新诗史意义在于呈现和证明了穆旦在不同时期修改诗作的大致状况。这些诗作手稿是《自然底梦》手迹(1942年11月),《智慧底来临》手迹(1944年1月30日),《冬》、《友谊》、《秋》(1976)等手迹。《怀恋》是1940年1月应同学赵瑞蕻(阿虹)之邀抄在赵瑞蕻给杨苡的书后面,未收入到以往的穆旦诗集和各种相关诗选中,此次由于种种原因也没能收入到《穆旦诗文集》中来。
比照穆旦的这些诗作手稿、抄件和《穆旦诗全集》和《穆旦诗文集》以及各种诗歌选本会发现这些诗作存在不同程度的改动情况,如《自然底梦》:
我曾经迷误在自然底梦中,/我底身体由白云和花草做成,/我是吹过林木的叹息,早晨底颜色,/当太阳染给我刹那的年轻,∥那不常在的是我们拥抱的情怀,/它让我甜甜的睡:一个少女底热情,/使我这样骄傲又这样的柔顺。/我们谈话,自然底朦胧的呓语,"美丽的呓语把它自己说醒,/而将我暴露在密密的人群中,/我知道它醒了正无端地哭泣,/鸟底歌,水底歌,正绵绵地回忆,"因为我曾年轻的一无所有,/施与者领向人世的智慧皈依,/而过多的忧思现在才刻露了/我是有过蓝色的血,星球底世系。[6]
我曾经迷误在自然底梦中,/我底身体由白云和花草做成,/我是吹过林木的叹息,早晨底颜色,/当太阳染给我刹那的年青,"一个少女它底思想底化身,/呵,为了我毒害的,诱人的热情,/是这样的骄傲又这样的柔驯。/我们谈话,自然底朦胧的呓语——/美丽的呓语把它自己说醒,/而将我逐出了在密密的人群中,/我知道它醒了正无端地哭泣,/鸟底歌,水底歌,正绵绵地回忆,/因为我曾年轻的一无所有,/施与者领向人世的智慧皈依,/而过多的忧思现在才刻露了/我是有过蓝色的血,贵族底世系。
——穆旦手迹
此外,《智慧的来临》、《冬》、《秋》、《友谊》、《停电之后》等都有改动情况。
成熟的葵花朝着阳光转移,/太阳走去时他还有感情,/在被遗留的地方忽然是黑夜,"对着永恒的相片和来信,/破产者回忆到可爱的债主,/刹那的欢乐是他一生的偿付,∥然而渐渐看到了运行的星体,/向自己微笑,为了旅行的兴趣,/和他们一握手自己是主人,∥从此便残酷地望着前面,/送人上车,掉回头来背弃了/动人的忠诚,不断分裂的个体"稍一沉思会听见失去的生命,/落在时间的激流里,向他呼救。[6]
盛开的葵花朝着阳光转移,/太阳走去时他还有感情,/在被遗留的地方忽然是黑夜,"对着永恒的像片和来信,/破产者回忆到可爱的债主,/刹那的欢乐是他一生的偿付,∥然而渐渐看见运行的星体/孤独的在各自的轨道上,/和他们一握手自己是主人,"于是便残酷地从他们走过,/稍一沉思会听见过去的生命,/在时间的激流里,向他呼救。
——穆旦手迹
《冬》在“文革”结束后发表于《诗刊》1980年第2期,刊出时每节的最后一行均为“人生本来是一个严酷的冬天”。而1976年的该诗手迹则是受了诗友杜运燮的意见而进行了一些改动,全诗4节的最后一行分别改为“多么快,人生已到严酷的冬天”,“呵,生命也跳动在严酷的冬天”,“人生的乐趣也在严酷的冬天”,“来温暖人生的这严酷的冬天”[6]371-372。《友谊》的手稿与后来发表于《诗刊》1980年第2期时的文本也有改动,“细致的雕琢”改为“细致的雕塑”,“冷冻”改为“冰冻”,“留下破产的我,面对严厉的岁月,/梦想那丧失的财富,丧失的自己”改为“留下贫穷的我,面对严厉的岁月,/独自回顾那已丧失的财富和自己”。
穆旦在不同时期对诗作的改动一方面说明诗人在不断追求诗的完美,另一方面也为新诗的版本研究设置了一些难题,比如在新诗史写作中究竟以哪一版本作为参照都不能不让新诗史家谨慎从之。
穆旦日记和书信:特殊境遇下的诗人心态、诗学观念及新诗传播
当代新诗的史料工作成了重要问题不能不与当代长期的外在力量对新诗发展的戕害和规训有关。频繁而激烈的政治运动使得史料以及相关的新诗史叙述在不同时期都处于相当大的变动当中,对同一个诗人和诗歌史往往会出现完全肯定或完全否定的奇怪现象,甚至会为了政治的需要而不惜篡改历史、涂抹历史。在这样的时代语境下,每当政治运动袭来的时候,诗人在因一首诗就可能罹难的状况下而不得不亲手烧掉那些诗稿、信件,而大量珍贵的史料就这样在一次又一次的政治大火中而灰飞烟灭,这种现象在“文革”时期则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应该说,《穆旦诗全集》和《穆旦诗文集》的编选和出版的意义正是体现了新诗史料研究工作的成果,尤其是《穆旦诗文集》中关于穆旦的71封书信和首次结集的穆旦建国后的日记为穆旦研究提供了不无广阔的空间。
透过《穆旦诗文集》所呈现的部分书信和日记,我们可以从中窥视一段特殊岁月中诗人特殊的交流方式和新诗的传播方式,而穆旦在书信和日记中所呈现的心态和诗学观念则呈现了那段历史的“丰富的痛苦”。
尽管从1957后穆旦失去了在报刊公开发表诗作的机会,但是穆旦仍在频繁的运动中冷静而清醒地观察文坛的走向和状况。“听说袁水拍正在挨批,因为他是文化副部长。大概为四人帮污染了,很可惜。”[7]138在“四五”天安门诗歌运动后穆旦问郭保卫“传抄作品盛行吗?”[8]222无不呈现了诗人作为知识分子对时局和诗坛的关注和隐忧。
穆旦对新诗传统、建国后狭隘、僵化而低下的新诗写作和审美水平进行了批评,这在诗人众口一声的顺役时代是弥足珍贵的。“你谈到你的学生看你的‘冬与春’而‘不易懂’,欣赏的水平如此之低,真是哭笑不得。所以如此,因为他光喝过白水,没有尝过酒味。国内的诗,就是标语口号、分行社论,与诗的距离远而又远。”[7]149-150“中文白话诗有什么可读呢?历来不多,白话诗找不到祖先,也许它自己该作未来的祖先,所以是一片空白。现在流行的,是想以民歌和旧诗为其营养”[7]183。而在穆旦看来,要改变这种新诗写作和审美的“哭笑不得”的状态就必须吸收外国诗的传统,“在这种情况下,把外国诗变为中文诗就有点作用了。读者会看到:原来诗可以如此写。这可以给他打开眼界,慢慢提高欣赏水平。只有广大水平提高了,诗创作的水平才可望提高。”[7]150穆旦对新诗与古诗的关系的体认是相当深入的,杜运燮曾希望穆旦多看看旧诗,吸收一下旧诗的传统,穆旦对此是持保留意见的。
你提到我该多看看旧诗,这一点我接受。的确我在这方面缺少接触,可是马上拿些旧诗来读,却又觉得吸收不了什么。总的说来,我写的东西,自己觉得不够诗意。即传统的诗意很少,这在自己心中有时产生了怀疑。有时觉得抽象而枯燥。有时又觉得这正是我所要的:要排除传统的陈词滥调和模糊不清的浪漫诗意,给诗以hard and clear front。[7]145
在穆旦看来古典诗学已经与现代人复杂的生活经验不相适宜,“现代生活能否成为诗歌形象的来源?西洋诗在二十世纪来一个大转变,就是使诗的形象现代生活化,这在中国诗里还是看不到的”[7]183。
即使是在与公开诗坛渐渐远隔的情况下,穆旦仍坚持可贵的诗歌观念,在穆旦看来,从文体上讲诗是不同于散文的,诗“实在和写散文不一样,要把普通的事奇奇怪怪地说出来,没有一点‘奇’才是办不到的。我说你可以写就是这个意思,因为把诗仅仅写成分行散文,无论如何是没有味道的”[7]181。正是因为当代新诗写作忽视了新诗的本体性并将诗沦为分行的政论文和阶级斗争口号,所以穆旦对当代诗坛是相当失望。“听说何其芳等老诗人都有作品发表了,我没有看到,反正多半老一套吧。现在时兴的,还是小靳庄之类的诗,如果能改变成三四十年代的新诗,那就很不易了,标语口号一时不易(也许永远得存在)。”[7]223
穆旦认为从诗与现实的关系来看,当代新诗不仅没能有力而深刻的揭示现实生活,相反倒是因为一元的、狭隘的诗歌观念的限制和主流诗学的规训而遮蔽了现实并留下诸多缺憾和“空白”。
谈到文学写作,过去的文学题材内容既窄而又不符合许多现实现象。因此留下生活上的一大片空白没有得到反映。这是我感到值得注意的。平平常常的人,每日看到周围一些人,他们想的是什么?他们的问题和忧喜是什么?写出这些来变得非常需要了,因为太缺乏了。还有,从什么角度看一切现象?仅仅使用一个角度,放弃了其他许多角度,这也留下空白。[7]209
值得注意的是,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一直就是禁忌的话题,即使提到这个话题也是认为文学要为政治服务,而有意味的是穆旦在写给郭保卫的信中引用了鲁迅在1927年所写的谈论文艺与政治关系的文章《文艺与政治的歧途》,借鲁迅之口对歌颂文学和革命文学进行了反思。
为什么穆旦在“文革”后期仍在坚持秘密写作?穆旦的书信提供了答案。在写给杜运燮的信中穆旦提到“写诗恐怕更是如此。可能是一焚了之,又何必绞脑汁?但活着本身就是白费力气,最后白白回到泥土了事。所以明知其为傻事而还可以兴致勃勃。”[7]150穆旦在“文革”后期如此集中的写下大量的诗作也能说明穆旦对当时的政治环境是相当敏感也是怀有相当清醒的认识的。穆旦在“文革”刚刚结束的时候对新时代的诗坛还是充满了乐观的期望的,他还是希望自己的诗作能够发表的,尽管穆旦仍对政治的发展心存疑虑,但这对于沉寂20年的诗人来说肯定是长期郁积内心的夙愿。
今天忽动诗思,写了一首“退稿信”,是由于看到对“创业”的批示而有感。想到今后对百花齐放也许开放一些了吧。前十多天,在听到“大批判组”的垮台后,写了一首“黑笔杆颂”,这两首看来是可以发表的,但我自己已无意发表东西,想把它们送给你,由你去修改和处理,如果愿送诗刊,(我想是可以送诗刊)那就更好,那就是你的东西,由你出名字,绝不要提我。[7]215
不久,穆旦在写给郭保卫的信中再次提到了《退稿信》和《黑笔杆颂》是否发表的问题。“你看情况吧,如把握不定,等些时再寄也好。像‘退稿信’,现在也许太早,等一等看,杂志上提倡百花时,再拿出也不晚。凡有点新鲜意见的东西,都会惹麻烦,人家都不太喜欢的。”[7]218根据穆旦1976年12月2日写给郭保卫的信中可以知道郭保卫将《退稿信》和《黑笔杆颂》投寄给了杂志社,但是这两首诗并没能发表,可见像穆旦这两首充满了批判色彩和良知的诗作在“文革”刚刚结束的语境中还是属于不被接受的“另类”或“异端”。
通过考察1959年至1977年的日记,我们会发现穆旦在对知识分子的改造运动中也不得不不时的检讨自己、批判自己。在1959年日记的开头穆旦即明确说明写作日记的主要内容和目的就是表现自己“思想斗争的过程,反省到的自身错误,自勉的决心及计画。”[7]255这位现在看来深受奥登等西方现代主义诗人影响的诗人也不得不在主流诗学的规训面前放弃了写作。值得注意的是穆旦在1969年1月8日的日记中抄录了毛泽东诗词13首。
从1970年2月开始,穆旦的日记已经不像此前的日记而变得相当俭省,基本是每天只写短短的一句话就匆匆收笔。而在这些相当繁琐的日常叙述中,有意味的是穆旦提到最多的内容就是收到了谁的来信并复信。在写作被限制并基本上失去了文学自由的时代,通信成了穆旦最为特殊的对话方式,也许正是在与家属、亲戚尤其是与诗友的通信使穆旦的文学冲动不至于泯灭并在“文革”的后期爆发出写作的高潮。与穆旦在文学上通信最多的就是杜运燮、郭保卫和萧珊。而在这些与文学和新诗相关的通信中,穆旦在特殊年代所写下的诗作通过这种不无特殊的方式得以存留下来,这也是特殊时代的新诗的传播方式。穆旦在给好友杜运燮、郭保卫、江瑞熙、董言声等人的信中抄录的诗有《冬》、《秋》、《友谊》、《苍蝇》、《还原作用》、《老年》、《演出》、《退稿信》、《黑笔杆颂》等此外穆旦还给诗友们抄录(译)了《两人的结婚》(路易士)、《葡萄》(普希金)、《暗藏的法律》(奥登)、《太亲热,太含糊了》(奥登)等诗。需要强调的是穆旦在1976年12月29日写给杜运燮的信中提到了郭小川的《囚人之歌》。穆旦说:“郭小川咱们和他见过,你记得吧?他在73(?)年写过一首纪念主席横渡长江的诗,被内部通报为‘大毒草’,大概又下放回干校了。这是四人帮乱扣帽子乱害人。他最近逝世是因为高兴多喝了酒,引起火,听说是如此。你看到他的诗‘囚人之歌’吗?我只听说而未见。”[71148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郭小川全集》并没有穆旦所提到的这首《囚人之歌》,这可能是《秋之歌》之误。
考察《穆旦诗全集》和《穆旦诗文集》中的一些史料的增补和变动,不仅可约略看出穆旦诗文的改动情况,而且在他留下的日记、书信和诗作中,特殊年代的诗人心态、新诗观念和新诗传播方式都为考察建国后的诗人写作提供了崭新而宽远的视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