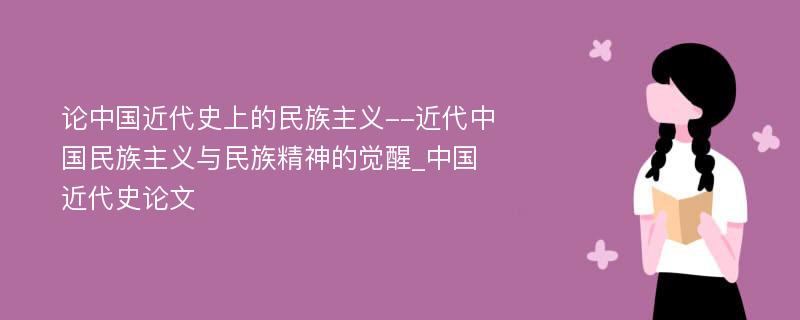
“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笔谈——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与民族精神的觉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族主义论文,中国近代论文,笔谈论文,史上论文,民族精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民族”难以准确的定义,有如“文化”。斯大林的民族观着眼于欧洲资本主义初期的情况,强调经济的要素,并不完全适用于中国近代社会的情形。费孝通的民族观强调文化的要素,注意到中国民族现象的特殊性。我认为,民族与人类相对而言。民族是人类的组成单位,有如家庭是社会的组成单位。社会不可能成为单一的家庭,人类也不可能成为单一民族。除非另有一个星球向人类挑战,迫使人类成为一个社会共同体来应对这种挑战。
“主义”一词有两种用法。一是指有主语的学说,如马克思主义、凯恩斯主义等等;一是指无主语的思想倾向,如科学主义、个人主义、恐怖主义等等。民族主义属于后者。“主义”是一个连接率很高的词汇,有些词一旦与主义连接,便有了负面的含义。如科学主义,表示一种把科学当成崇拜对象的错误的思想倾向。《辞海》的编纂者就在这种意思上解释“民族主义”一词。《辞海》关于“民族主义”的释义是:“资产阶级对民族的看法及其处理民族问题的纲领和原则。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国家起着不同的作用。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民族运动中,在现代殖民地、半殖民地和民族独立国家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它有一定的进步作用,但以符合资产阶级的利益为限。资产阶级巩固政权以后,就加紧压迫和奴役本民族人民和其他民族,或者侵略其他国家,实行扩张主义。当资产阶级统治受到外国资本的压力或本民族人民的反抗时,资产阶级又往往出卖民族利益,企图保存其阶级利益和阶级统治。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以后,垄断资产阶级更加利用民族主义,实行对内的阶级压迫和对外的侵略。在民族问题上,无产阶级政党的世界观是国际主义,不是民族主义。在革命斗争中,无产阶级政党支持进步的民族主义,反对反动的民族主义。任何时候,无产阶级政党都必须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划清界限。”我不同意《辞海》对“民族主义”所做的释义,因为这个词语不一定在负面的意义上使用,也可以在正面的意义上或中性的意义上使用。我在中性的意义上使用“民族主义”一词,在负面的意义上使用“狭隘民族主义”一词。至于“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我认为是一个正面的语汇,是指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观念逐渐形成全民族共识的发展历程,是指促使中华民族精神觉醒的社会思潮。
由于中国所处的地理位置比较特殊,东南临海,西为高山,北有大漠,形成相对独立的地理环境。自古以来,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就生息繁衍在这块土地上,造就出一个在全世界闻名的文明古国。由于中国的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凭借天然屏障的保护,总的来看,在古代并没有真正受到来自外部的强有力的威胁。亚历山大远征没有威胁到中国,奥斯曼帝国也没能威胁到中国。在中国历史上,夏夷之别仅仅是中华民族内部的差异。中华民族内部各民族之间固然存在着差异和矛盾,也发生过战事,但不能看成是异族入侵。在中国古代曾出现少数民族掌握全国政权的情形,如蒙古族建立的元朝、满族建立的清朝,但并没有因此而改变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例如,元朝的“元”,就是取义于《易传》中的“大哉乾元”。明清两朝实行的政治制度、礼义规范、行政区划、科举,取士等,与其他朝代相比,也没有根本的区别。在这种情况下,中华民族很难形成自觉的民族自我意识。汉族作为中华民族的主体,虽然人口众多,但民族自我意识比起少数民族来,更为淡薄。汉族没有共同的宗教信仰,不看重血缘关系,在婚姻上几乎没有任何限制,心态宽容,随遇而安,与人为善,民族溶解力强,适应环境的能力强,几乎在任何一个少数民族地区都可以看到汉族人的身影。实际上,汉族本身就是民族融合的产物,历史上许多少数民族(如匈奴人、契丹人、慕容人、乌桓人)都融合到汉族当中,成为汉族的组成部分。在古代,由于中华民族没有自觉的民族自我意识,当然以中华民族为主语的民族主义也就无从谈起。
中华民族的民族自我意识的自觉是在近代实现的。西方列强凭借坚船利炮撞开中国的大门,这才是真正的异族入侵。为了抗击侵略者,挽救民族危亡,中华民族团结起来,共同对敌,强烈地意识到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是一个休戚与共的人们共同体。梁启超说:“凡遇一他族而立刻有‘我是中国人’之一概念浮于其脑际者,此人即中华民族一员也。”(《梁任公近著》第1辑下卷,第43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23版)“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这激越的旋律扣动每个有良知的中国人的心扉。我国著名的民族学家费孝通经过多年的研究,得出的结论是:“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的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费孝通等著:《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第 1页,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版)事实证明,这一结论是正确的。
“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是中华民族自我意识走向自觉的理论升华,对于促进中华民族的觉醒、对于克服民族自卑感、对于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起到积极的作用,应当予以充分的肯定。除了少数的民族败类以外,每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可以说是这种意义上的民族主义者。孙中山先生把民族主义纳入三民主义体系之中,举起民族主义的大旗。中国共产党人也多次申明鲜明的民族主义立场。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号召共产党人动员全民族一切生动力量,为克服困难、战胜敌人、建设新中国而奋斗。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采取统一战线政策,理论依据之一就是这种意义上的民族主义。有良知的中国人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的民族主义的指引下,赢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达到“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伟大目标,使全世界人民都对中华民族刮目相看。
“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觉醒的前提,并且推动了中华民族精神的觉醒。
首先,它促进了爱国精神的觉醒。鸦片战争的惨败激起了中国人强烈的民族自我意识,“志切同仇,恨声载道,若不灭尽尔畜,誓不具生”,这是有良知的中国人的共同心声。中华民族精神的觉醒首先表现为爱国主义热情的空前高涨。虎门销烟,向全世界表明了中国人民维护民族尊严和反抗外国侵略的坚强决心,弘扬了伟大爱国主义的精神。中国各族人民在团结御侮、救国救民的斗争中,增强了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尤其是地处于边疆的少数民族人民,更值得称道。他们勇敢地投入抵御外辱的斗争中,自觉地意识到自己是中华民族的成员,粉碎了列强肢解中国的图谋。“多难兴邦”的古训在近代中国得到充分的体现:面对突如其来的剧变,为了民族的振兴、国家的富强,优秀的中华儿女前赴后继,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开启了近代中华民族精神的反省历程。中华民族精神的近代觉醒,首先表现为民族自我意识的自觉和爱国主义精神的高扬。尽管中华民族事实上早就存在,但中国人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整体的自觉意识,却出现在近代。因为只有到了近代,中华民族才真正与“非我族类”的外国人发生冲突,才有可能使民族自我意识从自在走向自觉,意识到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共同的生存空间、共同的文化、共同的生活方式的人们共同体。于是,民族主义在近代首先表现为爱国主义热情的空前高涨。
其次,它促进了改革精神的觉醒。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每一次对外抵抗的失败,都强烈地刺激先进的中国人,促使中华民族精神的进一步觉醒。甲午战败给中华大地带来新一轮的冲击波,上自光绪皇帝,下至普通民众,无不强烈地意识到严重的民族危机。普遍的危机意识为积蓄已久的“求变”、“求新”观念的出台,提供了适宜的条件。甲午战后,维新变法思想迅猛发展,只短短三年,便发展为戊戌百日维新政治改革运动。正如梁启超所说:“中国维新之萌孽,自中日战争产生。”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戊戌变法的领袖们,都是直接受甲午战败的刺激而走上政治舞台的。在他们的周围和身后,是大批要求变法的举人、士大夫。甲午之前,只有少数上层知识分子主张变法,并且局限在“中体西用”、“师夷长技”的范围内。到甲午战后,以中下层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改良派迅速崛起,他们主张向西方学习政治制度,走君主立宪的道路。“于是慷慨爱国之士渐起,谋保国之策者所在多有。”有人甚至主张效法美法革命,推翻清朝封建专制,实现民主共和,以图振兴中华。由于甲午战争的失败,才使人们意识到,必须对祖宗传下来的典章制度、纲常礼教进行有近代性质的改造和重构,中国才有自存自立的希望。此时中华民族精神觉醒,主要表现在民族主体对自身历史使命的自觉。
再次,它促进了革命精神的觉醒。近代中华民族的觉醒过程中,辛亥革命是一块醒目的界碑,标志着民族危机意识、救亡图存意识、民主共和意识的积聚和彰显。从民族主义出发,先进的中国人突破了“忠君报国”的传统观念,投身于具有近代意义的民族解放运动。辛亥革命把反对帝国主义与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结合起来,揭示出20世纪中国历史的两大主题。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人民为反对外来侵略和封建主义的压迫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但却没有冲破君主政体这个藩篱。孙中山破天荒地举起了推翻君主专制政权的旗帜,认为“非推翻专制,彻底改革,无以拯救祖国于危亡”,主张在中国必须实行民主革命。孙中山把反对外来侵略同反对本国的反动统治结合起来,把争取民族独立与实现民主自由统一起来,指明了中华民族的历史使命。辛亥革命的领袖们认识到:要救国必须革命,明确提出推翻皇权、平均地权、建立民国、振兴中华的民族民主革命纲领。他们一面歌颂历史上民族英雄们的民族气节,以鼓舞当前的斗争;一面又明确指出国家不是君主的私产,一姓王朝的灭亡不等于国家和民族的灭亡,愚昧的忠君观念不是爱国而是害国。邹容在《革命军》中以青年人特有的激情歌颂革命、歌颂共和,大张旗鼓地宣传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思想,在青年学生及新军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辛亥革命作为一次重要的思想解放运动,其标志性成果是从改良救国转向革命救国。这是中华民族精神近代觉醒的一次飞跃。这一觉醒所释放出的能量,把自鸦片战争以来形成的民族民主运动推向高潮,在中国进行了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民族民主革命。
最后,它促进了启蒙精神的觉醒。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华民族启蒙精神近代觉醒的集中展现,它高扬以科学和民主为主要内容的启蒙精神,为中国社会发展迈入现代提供了精神动力。在这场运动中,新文化的倡导者明确地提出了民主的口号,在政治上反对封建专制,要求平等自由;在思想上反对封建伦理道德,要求个性解放。李大钊号召青年要彻底解放自己的思想,“冲破过去历史之罗网,破除陈旧学说之囹圄”,担负起“孕育青春中国之再生”的责任。提倡民主必然要高扬科学,科学是反对迷信盲从、反对偶像崇拜、高扬理性的最有力的武器。五四运动作为反帝爱国的救亡运动,给新文化的启蒙思想拓展了空间广度,赋予民主和科学以新的历史意义,使反帝、爱国、民主、科学融为一体。五四的启蒙精神的觉醒与救亡图强是统一的。一方面,启蒙思想家鞭策国民劣根性,启迪国民认识自己落后和面临的生存危机,唤起人们的救亡意识;另一方面,他们以启蒙为手段,探寻救亡之道。他们深知,近代中国的民族生存是第一位的,只有救亡问题基本解决了,现代化的目标才有可能实现。这样,五四启蒙精神的觉醒就直接与社会危机和民族危机相联系,直接反映了救亡的要求和民族的希望。在五四时期,救亡仍然是压倒一切的任务,启蒙只是完成这一任务的手段,是服务服从于救亡的。
由上述,我的看法是:不能把“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与“狭隘的民族主义”混为一谈,也不能用《辞海》的“民族主义”释义看待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是以中华民族为主语的新的社会思潮。这是一种健全的民族主义,并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
收稿日期 2006-01-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