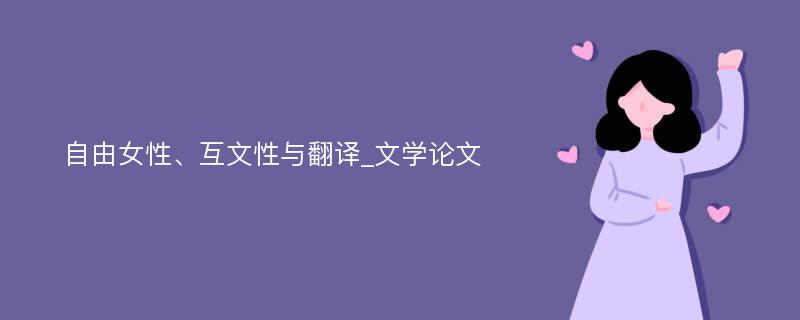
自由女性、互文关系和翻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关系论文,自由论文,女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朵丽丝·莱辛( Doris Lessing)1919年出生于波斯(现伊朗),父母亲为英国人,1925年随家人迁往南罗德西亚(现津巴布韦)。莱辛在首都索利斯伯上学,14岁辍学,之后不再接受正式教育,但她博览群书充实自己。
莱辛1939年和法兰克·惠斯顿结婚,生一男一女,于1943年离婚。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莱辛对政治产生浓厚兴趣,参加一马克思组织,与一来自德国的难民葛提弗烈德·莱辛相识,并于1945年结婚,生下儿子彼德,但婚姻关系维持不久,两人于1949年离婚,莱辛自此不再结婚。
莱辛离婚后携子彼德离开罗德西亚前往英国定居,并于次年1950年出版了第一部小说《青草高歌》(The Grass Is Singing),开始了数十载的写作生涯。莱辛作品十分丰富,计有10数部长篇小说,70多部短篇小说,2部剧本,1本诗集,多本论文集和回忆录。长篇小说包括两组小说系列:《暴力下的孩子》(Children of Violence,1952—1969 )和《南船星座的老人星》(Conopus in Argos,1979—1983),各有5部。另有2部以笔名珍·萨姆斯(Jane Sommers)出版,1984 年身份揭露时,引起传媒极大的反响。作品中,最富盛名的则是《金色的笔记本》(The Golden Notebooks,1962)。
莱辛的作品广受学术界注视,早在1971年现代语言学会(MLA )的年会上已有专题研讨会讨论她的作品。1976年出现了第一部以她的作品为题的博士论文。1975年狄·斯陵民创办朵丽丝·莱辛专刊。到了70年代末,在美国已有35 篇博士论文研讨她的作品。 (注:有关资料取自Sprague,C:Reading Doris Lessing,Chapel Hill & London: theUniversity of North Cnrolina Press,1987,p79。按目前电脑网络上的资料,仅美、加两地,与莱辛作品有关的博士论文,已超过60篇。)
莱辛关心社会、政治问题,对人的问题——个人身份的认定和人的结合,乃至人类的命运,尤其关心。她作品中的主题包括殖民主义、种族歧视、女性主义、政治、战争、社会福利、医疗、教育、艺术、成长过程、精神分裂、疯狂、梦、宗教神秘思想等。她曾热心研究马克思主义,研习伊斯兰教苏非(Sufi)教义,亲身经历荣格的心理治疗,甚且亲尝数日不眠不食陷入狂乱的滋味。(注:见Ingersoll.E. G.( ed)Doris Lessing Conrersations,Prineeton:Ontario Review Press,1994.p49。)20世纪的重要政治运动和学术思想如弗洛伊德、荣格心理学、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神秘主义、社会生物学,或多或少都反映在她的作品之中,但她极不喜欢评论者将她的作品分门别类,归为女性主义、荣格派等等。(注:莱辛对评论家的反应,散见其访问谈话中。)她注重的是人类整体的问题, 而不是分割片断的世界。 ( 注:见Pickering, Understanding Doris Lessing,University of SouthCamlina Press,1986,p6。)她的小说种类繁多,有悲剧、社会写实、寓言、神话、成长故事,也有科幻小说,但一如她作品中的主题,她的小说技巧也不是一元化的,她不喜欢两分化(either/or )的创作形式,总是写实中带有幻想,现实中有梦幻;清醒与狂乱难分,真实与梦境难辨。而对于她的一系列以太空为背景的小说,她也不喜欢称之为科幻小说(science fiction),而称之为太空(space fiction)小说。她之所以采用太空小说的技巧,是为了能够更自由地探讨人性的问题。(注:见Ingersoll.E.G.(ed) Doris Lessing Conrersations,Prineeton:Ontario Review Press,1994.p107。)
莱辛的另一个特色是她总走在时代的前面,不论是种族隔离的问题,女性的问题,还是梦、疯狂、无意识的问题,以至核武器、地球的命运等等,她的作品远在人们热烈地讨论这些问题之前就早已反映了问题的种种。有论者认为,她作品中预言的口吻是她最具创意的特质,她对地球的悲观看法因而尤为令人担忧。(注:见Whittaker, R. DorisLessing,London:Macmillan,1988,p13。)
本集收录的14 篇短篇小说选自莱辛的《小说集》(Stories),1980年出版。这14篇小说大多写于五六十年代,属于她较早期的作品,当中除了《天堂里的上帝之眼》(The Eye of God in Paradise)和《危城纪实》(Report on the Threalened City), 主要都是讲述女人和男人的故事。
作品的解读和诠释因人而异,不同的读者有不同的诠释本是自然之事。莱辛最富盛名的长篇小说《金色的笔记本》,有人从中只看到了男女两性之间的争斗;有人只看到了政治的一面;也有人只看到了疯狂这一主题。(注:见莱辛“The Golden Notebook”序言。 )这和盲人摸象的情况类似,每人只摸到了象的一部分。而莱辛的作品不但主题多元,且写作技巧变化多端,读者要摸索这种活力和动力兼具的“飞象”更是困难重重。而文化背景不同的译文读者透过译文如何探索这种异国“飞象”更是一大问题。就译者来说,能够做到不把“飞象”翻译成“飞牛”或“飞虎”已不容易,译文读者要如何理解和诠释,实非译者所能主导。何况就如莱辛所说,只有具有生命力的作品才能刺激读者的思考和探讨,而作品的生命力在于其结构、形式和意图。作品有如活生生的有机体,本不应解开,一旦解开,作品就失去其刺激之处。(注:见莱辛“The Golden Notebook”序言。)但在跨语言、 跨文化的翻译中,读者由于文化、历史、知识背景的差异,信息流失的情况可能较为严重,甚至容易产生歧解或误解。下面就莱辛这14篇小说,选择信息流失情况可能较为严重的几个问题,加以分析讨论。
莱辛虽不喜欢自己的作品给标上女性主义的标签,但女性的问题无疑是她作品的重要主题之一。只是她讨论的不只是女性所遭受的不平等、男性的粗暴、不忠而已,她的作品也探讨爱情的真义;女人与事业、家庭、婚姻的关系,女人与女人以及女人与男人的关系,尤其是女性的成长和醒悟,以及最终的“自由”。
近代欧洲自从法国大革命之后,人们追求自由和平等,但女性在法律上获得和男性平等的地位只是近年之事。欧美女性主义从历史、社会、政治、经济、语言各种角度探讨男女不平等的问题,提倡妇女解放运动。70年代的美国妇女运动分子将莱辛的作品,尤其是《金色的笔记本》视为妇女运动的先驱。但莱辛说她虽绝不会不支持妇女运动,也十分理解妇解分子所采取的激烈手段,但她的作品并不是妇解的号角。(注:见莱辛“The Golden Notebook”序言。)换句话说, 她探讨的虽是女性的问题,但她的主人公并不声嘶力竭高呼女性的不平等地位,也不是和男性开战。本集故事中的女主人公虽有遭男人遗弃的怨妇(《男人间》),有遇人“不淑”的痴情女(《二奶》),有无故遭人骚扰的妇人(《天台上的女人》),但也有让男人神魂颠倒的贵妇人(《女人》)和弃绝男人的女人(《我如何最终把心给丢了》)。此外,故事中虽有遭家人遗弃的老妇人(《老妇人和她的猫》),有遭小男孩强暴的老太太(《佛特斯球太太》),有因家庭、子女、婚姻丧失创作力、甚至生命的妇人(《一个男人和两个女人》、《十九号房》),但也有最终勇敢表达自我的妇人(《爱的习惯》),或自始至终都保持独立自主的女性(《吾友茱蒂丝》)。在这些故事中,有高高在上的男人,有朝三暮四的男人,也有暴跳如雷毫无涵养的男人,但他们不一定都是站在女性敌对的位置上。女性固然身受种种压力和苦恼,男性何尝不是,问题在于人人都想把自身的烦恼与创伤扔给对方(例如《我如何最终把心给丢了》)中的女主人公手中握着的心),谁也不会想到主动去接取别人手中握着的心(烦恼与创伤)。有人认为,《金色的笔记本》中的男人都十分可恶,莱辛则说他们都很好(terrifie)。(注:见 Ingersoll.E.G,(ed) Doris Lessing Conrersations,Prineeton:Ontario ReviewPress,1994.p49。)问题可能不在于好、坏那么简单,分辨好坏也不是问题的重点,重要的是人在现实社会的压力下如何寻找自我,如何认定自己的身份(有别于妻子、母亲、情妇),乃至如何走出自我,找寻“自由”。而女性和男性也可合作无间,在创作上达至完美的结合(《爱的习惯》中的男女街童)。
莱辛这些有关女性的问题,个人寻求自由的主题,也出现在她的许多其他作品中,以及英国文学史上某些作家的作品之中,构成茱莉·克丽丝蒂瓦(J.Kristiva)所说的“互文关系”。文本(text )可单指某一作品,也可泛指一切文化结构。文本与文本之间构成千丝万缕的关系,隐含了许多信息,产生信息的空隙现象。例如,《十九号房》和《我如何最终把心给丢了》都出现了疯女人:前者的女主人公苏珊在镜中看到的疯女人和后者的女主人公“我”在火车上看到的。这种“疯狂”的主题在英国文学中并不罕见,如勃朗特的《简爱》。而这也是文学批评上所谓的“他者”:人将自己投射到无意识之中,两者互动。苏珊和镜中的疯女人,以及《我如何最终把心给丢了》的“我”和火车上的疯女人可以视为一个人的两面。对具有英国文学背景知识的读者来说,这种关联并不难理解。但读者如缺乏此种互文关系的知识,就无法掌握其中所隐含的意义。至于有关女性的基本观点,与莱辛的作品关系较明显的英国文学史上其他的女性作家有乔治·艾略特( George Elliot)、夏绿蒂·勃朗特(Charlotte Bronte)、维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Woolf),尤其是伍尔夫。
女性主义按其基本理论可粗分两种:男女同体主义(androgyny )与实质主义(essentialism)。前者主张不管男性或女性,每个人的生理、心理结构、语言都含有阴阳两种成份,完美的人格在于两性完美合作无间。后者强调男女生理上实质的不同,以及为男性所主导的社会,甚至历史对女性所造成的种种不公。(注:参见周英雄《小说·历史·心理·人物》,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9年,第189—208页。)就男女同体合作无间,以及女性争取空间、争取机会表达自我这两点来看,莱辛的作品即使不是一脉相承伍尔夫,相似之处也是有迹可寻的。
《爱的习惯》中夫妻老少配,女主人公不论年龄、学养、社会地位、经济条件都和男主义公乔治有一大段距离,两人的生活从新婚蜜月开始即出现不调和。但另一方面,她在歌舞表演上,却找到了她的另一半,两人合作无间,一男一女,或说半男半女,或说不男不女,两人甚至男女角色对调,完成美满的演出。当然,这只是舞台上的演出,在现实生活中,两人由于种种的原因,并不能如伍尔夫笔下一同进入计程车的男女,让观者分割为二的心顿然化为一体。(注:伍尔夫原文的译文是:毫无疑问,我一看到一男一女进入一部计程车,我的心本来是分割为二的,这下显然融合为一体。最明显的原因不外:男女合作是最自然不过的事。参见周英雄《小说·历史·心理·人物》,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9年,第199页。)另外, 在莱辛的《一封未投邮的情书》中,女主角说,她大可告诉人家,“我是艺术家,因此是男女同体。”或是,“我在身体里创造了个男人,和我的女人配对。”她在偶然间见到情书中的假想情人之后,想象自己是一张帐篷、一块天空、一个房间、一池水、一个世界、一片空间,两人共处其中,融为一体。而她第二天的表演将再创艺术高峰,达到男女同体的最高境界。
男女同体并不是伍尔夫作品中男女关系的唯一看法,她的作品也反映实质主义女性受屈的一面。 例如, 《自己的房间》(A Room
ofOne's Own)当中一篇《莎士比亚的妹妹》(Shakespeare's Sister ),叙述女性即使才华出众,在男性为主的社会里,也没有表现的机会和条件。而女性要想写作,最基本的条件是拥有属于自己的房间和每年固定的收入。伍尔夫这个房间和固定收入的观念,在莱辛的作品中并不罕见,较为突出的是《十九号房》和《吾友茱蒂丝》。《十九号房》的苏珊在“妈妈的房间”有名无实地变成另一个家庭起居室,以及在花园的整个房子给她越来越大的压迫感之后,终于选择了一间又旧又脏的旅馆房间,逃避外面世界的压迫,也逃避自己心中的恶魔(devil), 以取得内心的平静,但在房间的秘密被揭穿之后,竟赔上了一条性命。相对来说,《吾友茱蒂丝》拥有自己的房子,每年有一笔固定的收入,写诗之外,也教书补贴家用。她不结婚,不但生活独立,思想、创作也都独立,她那两个拜倒在她石榴裙下的老作家非但影响不了她,连他们题赠的两书架作品,她也翻都没翻过。茱蒂丝,这位和《莎士比亚的妹妹》中的妹妹同名的女性,有论者认为,是现代女性的英雄,她找到了“自己的房间”。(注:见Gardiner,J.K.Rhys,Stead, Lessing
andthe Poctics of Empathy,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9,p99.)
《十九号房》的苏珊婚前是广告画画家,婚后怀孕之后为了家庭辞去工作,成为专职的妻子和母亲。表面上,她婚姻美满,丈夫收入高,经济条件好,住宅豪华漂亮,子女健康活泼,她即使感到生活“无聊”,(注:见Ingersoll.E.G,( ed) Doris Lessing Conrersations,Prineeton:Ontario Review Press,1994.p49。)秘密被揭发, 似乎也无足够的理由自杀。她的死,引起许多的讨论和诠释。从现代女性主义的观点来看,苏珊处身西方中产阶级以男性为主的社会,在社会的约束之下,死是必然的结果。(注:见Knapp,M.Dotis
Lessing, NewYork:Ungat,1984,p80。)苏珊的死固然和她经济不独立有关:她得每个星期伸手向丈夫要五镑支付旅馆房间费用,也正因此才泄露了房间的秘密。此外,她最后打开煤气开关也是因为她丈夫向她承认不忠,甚至逼迫她捏造婚外情的故事所造成的。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苏珊的死也是必然的,是作者早就作出的安排。故事一开始,作者就说“这是一个理智发挥不了作用的故事”。理智(intelligence)是故事中罗林夫妻做人做事的原则,故事中一共出现了十数次,另有十数个类似的词语。在一个表面几乎是完美的婚姻中,女主人公和花园中的魔鬼,镜子中的疯女人斗争,最后投降自绝。这可以说是对现代分崩离析的社会的一种反讽。但另一方面,这和莱辛的长篇小说《金色的笔记本》的主题不无相似之处:个人经由疯狂、神经崩溃之后,和他人融合成一片,达到最终的结合。只是苏珊单独崩溃,也没有从疯狂中解脱,获得精神上的提升。套用弗洛伊德的用语:死亡是欲望的最后目标。(注:转引自Tiger,V."Taking Hands and Dancing in (Dis)unity:"Story toStoried in Doris Lessing's "To Room Nineteen" and "A Room",Modern Fiction Studies,Vol.36,No.3,1996,p421—434。)
假如说《吾友茱蒂丝》的茱蒂丝是找到“自己房间”的自由女性,《十九号房》的苏珊无疑是找不到“房间”的不幸女性,并以昂贵的代价——生命,消极地换取最终的自由。本集故事中的其他女性,也有经过漫长的心路历程,最终毅然与男人分手以寻求自立的女性(《二奶》),或摒弃女人标记,穿上男装宣布“新生”的女性(《爱的习惯》)。而做得最彻底或最特别的则是《我如何最终把心给丢了》的女主人公。这位女主人公经过两次的婚姻,无数次的“爱情”经验之后,终于把心交给车厢里一个遭男人遗弃、自怨自艾的疯女人。疯女人满心欢喜,而没有了心的女主人公则感到“幸福”、“自由”。她本来和《爱的习惯》中的乔治一样,养成了爱的习惯,交往的男人连名字都没有,以字母、数字或其他符号代替。但她终于决定抛弃一个接一个的爱的习惯而换取自由。只是没有了心,是否就是自由? (注:见 Barzilai, S.'Unmaking in Words That Make Us:Doris Lessing's "How I FinallyLost My Heart" ' Style,Vol.22,No.4,1988, p595—611。)
自由的定义,和许许多多其他的词语一样,因人、因时、因地而异。莱辛虽使用“自由女性”(free women),相信也不是要向读者交待什么是自由,而正如她自己所说,“自由女性”是个十分反讽的词语。(注:见莱辛“The Golden Notebook”序言。 )女性穿上男性化的衣服(《爱的习惯》),离开男人(《二奶》),甚至把心丢了(《我如何最终把心给丢了》),这些是否就等于“自由”,相信莱辛并没有答案。但这不应是她作品的重点,重要的是女性追求自由的过程。而这个过程所涉及的历史、社会、个人心理因素,以及莱辛个人的艺术表现,则是缺乏互文关系知识的读者,尤其是译文读者,容易产生理解和诠释困难之处。一个词语可能包涵一段历史,反映一个文化。“自由女性”所包涵的西方历史和文化,经过翻译后难免造成信息流失的现象,但这也是翻译的本质,在所难免。下面再举数例,说明互文关系中所隐含的信息,在跨文化翻译上可能产生的流失情况。
在《天堂里的上帝之眼》故事中,两个英国人听到德国医生克洛勒称希特勒为“窜发的杂种”(mongrel upstart)时, 心中涌起一股不自在的情绪。“mongrel upstart”隐含了些什么意义? 两个英国人为什么会觉得不自在?“mongrel”虽带贬义, 但有别于一般骂人的词语,应是有所指。按未经证实的传言,希特勒具有犹太人的血统,(注:见《大美百科全书》,台北光复书局1990年。)这应是那位德国医生称他为杂种的原因。但在战争结束不久的德国,犹太人仍是个敏感的话题,而且两个英国人各和犹太人有深厚的关系:一个带有犹太人血统;另一个的太太是犹太人。他们听到那“杂种”的称呼,难免产生不自在之情。此外,根据记载,希特勒出身寒微,父亲是私生子,属贫农阶级,希特勒本人只完成中学学业。在注重阶级地位的英国社会,非出身名门或望族而成功的人,被贬为窜发(upstart), 这含有浓厚的社会意义。但在无皇室、社会阶级区分不明显的德国,两个思想开放而前进的英国人,听到那位他们本来甚有好感的德国人,使用英国的社会阶层标准来形容希特勒,于是感到不安。
在《吾友茱蒂丝》中,作者描述茱蒂丝时,刻意描绘她穿上一件直身连衣裙(dress)的情形, 说她穿上那件衣服产生一种古典的形象,像希腊(罗马)女神黛安娜或山林仙女(nvmph)。 黛安娜是野生生命之母兼保护人,喜爱狩猎。山林仙女栖居在树林、树丛中,具有美丽的容貌,自由自在地在树林中追逐、歌唱、舞蹈。莱辛用希腊女神、仙女来比喻茱蒂丝穿上那件连衣裙所产生的形象,除了证实她的美丽之外,还暗指她和女神、仙女相似之处:自由自在、超俗、独立。而那件宽宽松松的直身连衣裙更包涵无拘无束的象征意义,以及潇洒脱凡的联想意义:图书中的希腊女神和仙女都身披直身的宽松长袍。
最后再举一例。在《爱的习惯》故事中,乔治生病时请芭比当他的看护。他看到她照顾他,以及应对客人的举止——冷淡、漠然,甚至有点懒洋洋的美态:这种冷漠无情的举止是显示涵养的极端表现。乔治起初看了心中一阵寒颤,但后来他看穿了,明白那不过是她模仿出来的,不论她的血统、出身是什么,她不会是她的举止所代表的那个英国社会阶层。英国人的性格一般都较内向,而社会阶层越高,涵养越好,举止就越含蓄,感情越不外露,几至冷漠无情的程度。乔治是个新派艺术家,政治取向是工党中间偏左,看到芭比这种上流社会般的表现和具有高度涵养的举止,感到的不是认同或欣赏,而是心寒。在上面这三个例子中,从“窜发的杂种”一个词语到听者坐立不安的反应;从一件宽松的连衣裙到旁观者产生仙女自由自在的联想;从冷漠的举止到观察者心寒的感受,中间包涵了许多作品之间,以及文化结构上的社会和历史意义。
除了互文关系之外,作者使用语言的叛逆(subversive)策略,亦造成翻译的困难,产生信息流失的情况。下举一例说明:
《我如何最终把心给丢了》(“How I Finally Lost My Heart ”), 英语“to lose one's heart”的惯用意思是“爱上(某人)”。莱辛舍弃习惯用法,取其字面意义,即丢弃。惯用语(idiom )常用比喻的说法,包涵一个意象,例如英语用“丢失”或“献出”自己的心这一个意象来比喻爱上某一个人。莱辛的女主人公丢失了自己的心,却不是和对方擦出火花,献上自己,快乐地度过余生,而是丢弃那充满感情、怦怦跳动、活生生的心脏器官,一了百了。就翻译来说,包涵意象的惯用语通常是一种两难的情形:取意象则丧失喻意;取喻意则丧失意象。在莱辛的这个故事中,“to lose one's heart ”既然不是一种比喻的说法,翻译其字而意义本不困难,但原文的叛逆意义则丧失殆尽,产生另一种两难的情形。
由互文关系和作者的语言叛逆策略,以及其他修辞方式所造成的信息间隙,是理解上的一大障碍,对译文读者来说,情况可能更加严重。译者常采用各种策略将隐含的信息显现,注解即是一种方法。但注解,尤其是脚注或后注,容易分散读者的阅读集中力,减低兴趣,故通常并不适合小说一类的文艺作品。此外,要将一切不熟悉的概念,例如人名、地名、物名、事件等等全部加注,也不切实际。本集译文完全不采用脚注或后注,只将关键性的重要隐含信息,采用插注的方式使之显现。例如,在《天台上的女人》故事中,史丹利——那位满怀怒气的工人,称那个近乎赤裸地在天台上晒太阳的女人为“葛黛娃夫人”(LadyGodiva),并且说大厦中另一个女人不像葛黛娃夫人,因为她会跟他们聊两句,展露笑容。("Not like Lady Godiva," said Stanley."Shecan give us a bit of a chat and smile.")葛黛娃夫人、 天台上裸体的女人,以及展露笑容的女人三者之间有何关联?葛黛娃夫人是11世纪的英国贵妇,相传曾为了为民请愿而裸体骑马穿过市区,但不准百姓窥视。《天台上的女人》中的女人,对那几个男人的叫嚣采取不理不睬的态度,使得史丹利暴跳如雷。他将她比喻为葛黛娃夫人,两者相似之处除了裸体之外,还有冷淡的态度。而天台上女人的态度,以及史丹利的反应是故事中的重要主题,因此译者在处理葛黛娃夫人这一比喻时,将隐含的两个相似点——裸体和冷漠,加以显现。(将“not likeLady Godiva”译为“不像那一位冷冰冰、赤裸裸的葛黛娃夫人”。)
互文关系的产生是语言的自然现象,但艺术性越高的作品,如文学作品,作者常利用间接、隐含的方式创造特殊的效果,互文关系因而可能越复杂。而文化色彩越浓的作品,在跨文化翻译中信息间隙也越大。但小说翻译,毕竟不是注解作品,而解读作品也是一种乐趣,读者应享有解读隐含信息的乐趣,译者不应一一加以注解,过于“越俎代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