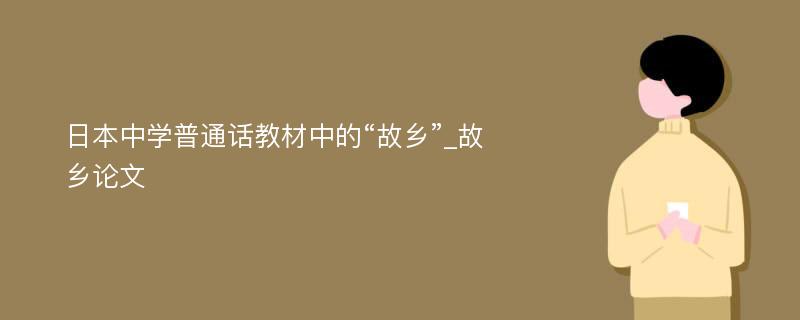
日本中学国语课本里的《故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本论文,课本论文,故乡论文,国语论文,中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日本,除一些私立中学外,初中三年级的学生一般都学过鲁迅的《故乡》①。因此日本教育学研究也有很多关于鲁迅的论文②。他们主要研究的是如何讲授鲁迅作品。例如,足立悦男在第59届日本文学协会国语教育部会夏期研究集会(2007年8月11,12日)上,提议不需要通过作品中的“我”来看《故乡》,应该把《故乡》看作闰土或杨二嫂的故事。因为在对日本初中生的问卷调查中,问到《故乡》里印象最深的人物时,学生们的回答,第一是闰土,第二是杨二嫂,第四才是小说中的“我”。对日本初中生来说,“我”不算有魅力的人物。由此可见,日本教育学家一直摸索讲授鲁迅《故乡》的方法以及重读的方法。 实际上,很多日本人对为什么要学习鲁迅的《故乡》持有疑问。例如在杂志《文学界》(2002年6月号)上,四方田犬彦、武藤康史、川村凑等作家和评论家就对此提出了疑问。一位在补习班教“国语(语文)”的老师在网上指出,“国语”课本上的文章大都是保守的,几乎没有又新又先进的文章。自己小学、初中时代课本上的文学作品现在还保留着,鲁迅的《故乡》等是最典型的。他认为《故乡》虽是名作,但是不了解中国当时的社会背景就无法理解原文。他认为这样的作品不应收入课本③。 然而鲁迅的《故乡》一直都被收入中学课本,中西达治把鲁迅的《故乡》叫做“安定教材(稳定教材)”④。为什么在日本初级中学“国语”课上要学习鲁迅的《故乡》?《故乡》为何被称作“安定教材”?日本课堂上如何看待此现象,是否存在问题?本论文将以这些问题为中心,考察日本初中课堂如何看待鲁迅的《故乡》。 一、《故乡》在日本的授课实践史 首先透过中西一彦(2010)在《〈故乡〉(鲁迅)的授课实践史》(「『故郷』(鲁迅)の授業実践史」田中宏幸·坂口京子编《文学课教学指南·第四卷》[『文学の授業づくりハンドブック』第4卷、中·高等学校编],渓水社,2010)了解《故乡》在日本的授课实践过程。 中西首先介绍鲁迅的生平和《故乡》的创作背景。在“作品简介”中他对日本发表《故乡》的过程做了如下介绍:1927年在武者小路实笃主办的月刊杂志《大调和》10月号⑤上第一次刊载了鲁迅的《故乡》。但这篇《故乡》是由谁译成的日文,至今不详。1932年佐藤春夫翻译的《故乡》登载于《中央公论》1月号,可以说,在《故乡》翻译史上,佐藤的译作对之后的翻译影响很大。佐藤在翻译时,先阅读了英文版的《故乡》,之后与原文对照,再翻译成日文。1956年,竹内好翻译的《故乡》收录于《鲁迅选集》(岩波书店)。此外,增田涉、高桥和巳也翻译了《故乡》。至今竹内好的译本为更多人阅读,日本国语课本采用的也是竹内好的译本。 中西在“作品评价”部分介绍,在日本,1956年一家初中“国语”课本出版社选入了鲁迅《故乡》,1972年中日邦交恢复后至今,所有出版社都选入了《故乡》。但据足立悦男考证,首次选入鲁迅的《故乡》是1953年教育出版的课本⑥。藤井省三也表示,1953年教育出版社版的初三“国语”课本首次收录了鲁迅的《故乡》⑦。因此中西所说的1956年首次选入课本值得商榷。据三村孝志(2010)介绍,2010年,日本的学校图书、教育出版、三省堂、东京书籍、光村图书五家出版社出版的初中“国语”课本都选入了《故乡》⑧。这五家是目前出版国语课本的出版社,因此可以说,日本初三的国语课本全部选入了《故乡》。 中西认为,《故乡》与赫尔曼·黑塞的《回忆少年时》、太宰治的《奔跑吧梅勒斯》一样,一直被选入初中课本,因此被称为“安定教材”。日本人几乎都读过《故乡》。就是说,“自古文学作品就常描写对‘故乡’的怀念和回忆,但在日本的文学教材中几乎见不到通过故乡来展现社会或国家现状问题、具有广阔视野的作品。虽说鲁迅是外国人,但可以说他是近乎日本的国民作家。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故乡》作为世界文学也具有珍贵的意义。”⑨ 中西指出,授课时大多要把握作品的主题,但授课实践者在贴近主题的过程中感到焦躁且不易把握。他介绍了田中美也子(1986)、大冢敏久(1994)和菅野圭昭(1989)的看法⑩。前两者都提到小说中的“我”的问题。他们认为,作品里没有介绍“我”的背景,日本初中生不明白当时中国的社会情况,所以对初中生来说,他们很难把握小说的内容,而老师要求他们找到小说的主题。菅野(1989)认为,《故乡》发表以后,日本侵略中国,折磨中国民众。我们日本人不能忘记这个事实。所以应该从中国近现代的历史逻辑中看待《故乡》,这样就形成一条中日交流之“路”。 中西还介绍,山田文雄(1987)(11)建议要关注描写和“视点人物”(小说中采用特定视角讲述故事的人物)。这里所说的“视点人物”就是小说中的“我”。因此在理解《故乡》时,先要理解这篇小说是从“我”的视角来讲述的故事。之后归纳了飞田多喜雄(1987)(12)、宇佐美宽(1986)(13)和鹤田清司(1995)(14)的看法。飞田同意了山田的意见,宇佐美则提出在注意同化“我”的同时,也要异化“我”(对象化)。鹤田部分同意宇佐美的意见,他认为这个观点在《故乡》的教材研究史中是缺乏的。一直以来,在授课中,与小说中的“我”产生“共鸣”是主流的解读方式,但还需要“评论(批评)”式的解读。 中西还介绍了授课的历史——以朗读为中心的教学法(村上正子)、尝试指导和评价一体化的教学法(花田修一)、选择课题和设定课题的教学法(中岛阳子)及分析性的教学法(门岛伸佳)这四种教学实践方法(15)。 在最后的部分是今后的课题及授课的启示中,他指出,《故乡》是可以多次阐释从而不断出现新课题的作品,国语课的老师尽管多次阅读,但是最危险的是满足当下的理解,简单地重复讲授同一内容。他特别提醒,包括教员在内的所有学习者应带着疑问来阅读这部作品。他认为,每次授课内容都应超过上次。作为结语他强调:“《故乡》是永远的教材”(p.114)。 二、作为“安定教材”的《故乡》 日本初中一年共有1015课时,其中一、二年级的“国语”课时为140节,三年级为105节,每节课五十分钟。讲授《故乡》一般需要6-10课时。中国的初中课,除预习外,需要讲授3课时(16),每节四十分钟。与此相比,日本初中生学习《故乡》的时间要多出两三倍。 石原千秋指出,日本国语课的特征是“国语等于道德”(17)。所以,“在学校这一空间,不知为何‘正确的答案’被确定为只有一个”(18)。这正是因为日本国语教育是道德教育之故。日本文部科学省也清楚,当下迫切的问题是需要培养学生的读解力和能记述自己思考的能力。于是文科省2008年开始修订学习指导要领。但是从文部科学省出版的学习指导要领可见,国语课与道德课仍未分开。虽然是“国语编”,但附录里仍有“道德”课的学习指导要领。 那么“国语等于道德”的日本国语课的课本里,为何入选鲁迅的《故乡》?且被称作“安定教材”? 蔡栅栅(2015)认为,“《故乡》得以入选教科书,是日本战后教育政策修正的结果,是人们追求教育民主化和国家化的结果。另一个理由则是鲁迅的留日背景——众所周知,鲁迅曾在日本留学七年。这一背景让日本国民觉得很亲切。第三个理由是鲁迅本人在新文学(或说现代文学)里的地位。我们知道,鲁迅不但发表了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还是现代文学的主将。他的文章在生前就已经扬名四海,何况是邻国。”(19) 也许确有这些原因,但由此还不能说明为何是《故乡》而非鲁迅的其它作品入选。石原(2005)解释说,实际上,国语课本隐藏着思想。被选作日本国语课本的“定番教材”(固定的教材,等于安定教材)的原因是,作品中包含“利己主义是不对的”等内含道德的信息。(20)那么,《故乡》里隐含的思想是什么呢? 石原在《国语教科书的思想》里分析了小学国语课的思想倾向。笔者认为这个分析与中学国语课本选入鲁迅的《故乡》有关,为此对石原的分析结果作简要介绍。 石原分析了2004年采用的一年级到六年级的十二本光村图书的教科书。根据2002年的调查,光村图书的课本被60%以上的学校采用(21)。通过他的分析明确了教材的以下几个特征。 特征之一是倡导“回归大自然(自然に帰ろう)”(p.76)与“动物化(動物に戻ろう)”(p.84),其二是倡导“乡村好”的理念(p.93),这体现出对现代文明和城市的强烈嫌恶之感,由此也可以说是一种“批判文明的教材”(p.93)。他指出,小学国语课本对所谓“动物化”的追求,传递出这样一种信息:这类作品对培养“被动地、对所赋予的环境顺从型的‘人格’可能会起到作用。”(22)这样的“人格”对“当权者”而言更方便。由此可见,国语教育“正是发挥着温和的意识形态装备的作用”(23)。 通过这些分析,他发现教材里几乎没有以城市为题材的作品。如今日本城市化普及,却没有描写城市生活的作品入选教材,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他还指出,为了强化“乡村好,城市恶”这一意识形态,需要“批判文明的教材”。他还发现,课本中很多文学作品没有父亲的存在,倡导和平的“和平教材”最为明显。他用多篇作品证明了父亲的缺失。父亲“缺失”的后面隐藏着“弑父”的思想。他的结论是,“无非是这本国语课本隐藏着‘母亲=大自然/父亲=文明’的图式。而且这一图式还与‘乡村好,城市恶’这个思想有所关联。”(24) 笔者以为,鲁迅的《故乡》也可算作这个思想体系里的作品。因为《故乡》里描写了乡村,而且“我”只有母亲,父亲已经不在了。“我”一回到故乡,就感觉到“悲凉”。然而,“我”记忆中的故乡是“好得多了”、是“美丽”的,特别是有着跟少年闰土的乡村画面象征着“乡村的美丽”。然而眼下的故乡是“荒村”“没有一些活气”,闰土的变化也让“我”心中的图画褪色。但对于读者来说,印象最深的还是少年闰土向“我”讲述的活生生的乡下生活。“我”还说:“似乎看到了我的美丽的故乡了。”(25) 在《故乡》这篇小说中,如果“我”的父亲还活着,故事就无法成立。在小说中,“我”是以家长身份回乡整理家里的东西。因此是以“我”跟母亲谈话为中心展开故事。《故乡》里描写了闰土父亲对儿子闰土的关爱、闰土对儿子水生的关爱,但没有描写“我”和“我”的父亲的关系。而且,小说中的“我”是先进文明社会的代表。最终,“我”与故乡(乡下)诀别,也没有发现闰土作为父亲对水生的关爱(26)。 《故乡》入选日本国语课本时,无疑是没有意识到上述的内容。但从石原的分析看,却隐藏着上述的信息。照此分析,鲁迅的《故乡》也符合“乡村好”“父亲不存在”这个选题范畴。因此,可以说,正是因为该作品的思想内容符合课本选材的需求,才被选入日本国语课教材。 三、翻译作品的教材化 日本中学国语课的课本中收入的《故乡》均采用竹内好的译本(27)。 鲁迅的《故乡》多次被翻译成日文。最早的日文译本是1927年发表,但译者为何人尚不明确。1932年佐藤春夫进行了翻译,此后井上红梅、田中清一郎、增田涉、高桥和巳、松枝茂夫、丸山升、驹田信二、小田岳夫、宇野木洋、藤井省三都曾译过。 那么,为何所有教材都选用竹内好的译本呢?实际上已经有很多人指出竹内翻译的《故乡》存在的问题。例如中西(1985)曾指出,竹内好把“这正是一个廿年前的闰土(28)的“廿年前”改成“三十年”,批评了他的翻译(29)。但竹内好认为,“二千余里”“二十余年”“廿年前”都是概数,而且“我”和闰土见面正是三十年前,所以他把“廿年前”修改为“三十年前”(30)。 田中实关注到这个问题,将其称作“三十年二十年问题”(31)。他批评道:“由于旧有的‘解读’方法,现在所有出版社的初中国语课本都对《故乡》的文本进行了不自觉的‘窜改’。”(32)田中介绍,2010年8月召开的“发掘《故乡》的‘文章脉络’座谈会”上,藤井省三把田中所说的“三十年二十年问题”看成“鲁迅的战略”。之后,田中(2014)解释道,这个“廿年前”的逻辑表明“相对于外界,‘我’所生活的‘空白的十年’”(33)。他认为,这就是鲁迅把三十年前改作“廿年前”的原因。其实,这个“廿年”也表示“我”在外界一直想念闰土的“二十年”。 再次回到鲁迅《故乡》的翻译问题上来,竹内翻译的《故乡》存在诸多问题,但日本初中课本都采用他的译本。藤井省三指出,“可以说,几乎所有国语课本中都采用由竹内好(1907-1977)的翻译,这是本土化·日语化的典型例子。与鲁迅的原文相比,竹内译文用了超出原文几倍的句号‘。’,将原本数行的长句断成很多短句,把在传统和近代的缝隙中艰苦奋斗的鲁迅的曲折的文体,进行了适合当代日本人喜好的意译。”(34)总之,竹内在翻译时,为了迎合日本人的喜好改变了鲁迅的文体。而纳入课本的作品又进行了更改,改为适用课本的形式,可以说是一种“再译”。因此日本初中学生在课堂上读到的鲁迅的《故乡》比竹内的译本更容易看懂,可称之为更加日本化的作品。 在此举出一例。1970年,青柳隆发表了一篇文章(35),在谈到通过竹内和增田涉译文的比较以加深作品理解时,他举出这样一例。只有九节课,时间不算长,他注重让学生考虑和讨论作品的内容。在第五节课时,他示范朗读竹内和增田两篇译文的开头部分。当时很多学生的反应是“教科书的文章响彻着沉闷的‘寂寥’(按:=悲凉,竹内翻译为‘寂寥’,与‘悲凉’相近。)感,从较抽象化的字面能展开自由的联想。但也因此,有些地方很难抓住大意;增田涉的译文更容易理解,但贯串整个作品的‘寂寥感’在增田涉的译文中明显消失,且少了沉重感。总觉得在自己的心中有与教科书中的作品产生共鸣的东西。”(36)据说教科书的译文引起了当时大约80%的学生的共鸣。笔者认为,这是由于1970年代的影响,如果同样的问题问现在的学生,或许很多学生会支持易懂的增田译文。如果考虑到选定教材的那一代人的时代特征,上述的1970年代学生的反应对理解为何教材采用竹内译文是一个启示。 由此可见,日本人大多是在初中三年通过国语课本阅读了鲁迅的《故乡》,且第一次读到的鲁迅作品就是竹内的译文。很多日本人通过国语课本,已经习惯了竹内的译文。正如藤井省三指出的那样,竹内的译文是本土化和日语化的文章。国语课学习的正是作为“语言”的日语,因此像竹内译文这种日语化的作品选入国语教材,也是可以理解的。 因此,可以说大多日本人是通过竹内好这个滤光镜来接受鲁迅的《故乡》及其他作品的。 四、日本国语课的《故乡》 如上所述,日本人一般通过竹内好的译文阅读鲁迅的《故乡》。因此会在《故乡》开头部分感到“寂寥感”(37)。日语“寂寥”一词为竹内译文中的词汇,而非鲁迅所写。鲁迅文中的“悲凉”一词与日语“寂寥”意思相近,但对初中生来说,“寂寥”一词比较难懂。尽管如此,在授课过程中仍会用“寂寥”一词解释《故乡》的开头部分(38)。这也是受了竹内译文的影响。 蔡栅栅介绍,“以光村图书版《国语3教学指导用书》里《故乡》的教学过程为例,中日教科书在‘主题’的提炼上有很大差别。在我国,《故乡》通常是被作为一个‘启蒙主义’文本,或是‘反封建’文本来看待的,教学理念上也比较重视‘政治思想’等宏观主题的构建。比如对《故乡》主题的提炼,有的认为,‘小说通过“我”的主客观矛盾的急剧冲突,反映了辛亥革命后在帝国主义掠夺、军阀混战、地主官僚的压榨和连年自然灾害的摧残下,中国农村破产、凋敝的真实面貌,描述了故乡人民在半封建半殖民地制度下身受的剥削、压迫,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精神损害。’有的认为,‘《故乡》是采用第一人称,以一个知识分子“我”的自叙的形式写出的。它以“我”回到故乡的经历为线索,以现实和回忆的矛盾作为情节的基础,通过“我”的回忆与见闻,刻画了农民闰土的鲜明形象,并以“我”的思想认识的深化,逐步表达出必须推翻旧社会,创造新社会,以便改变农民的命运,改变知识分子与劳动人民的关系的主题。’”(39) 她还指出:“我们的教学往往有主题先行的习惯,在这样的‘主题’灌输下,《故乡》被当作揭露旧社会黑暗的一个‘启蒙主义文本’:‘闰土’是被旧社会迫害的农民,他在政治上不觉悟,需要被启蒙;‘杨二嫂’是落后的小市民,也需要被解放头脑;故事中的‘我’是‘革命民主主义’的知识分子,头脑是清醒的,但对现实认识还不清,所以彷徨。在这样的教学方式下,一代又一代的学生接受了既定的‘鲁迅印象’:旧社会的揭露者,会写投枪和匕首式的文章,对旧中国子民的态度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这个印象随着年代的久远不断被固化,以至于一提起鲁迅,就是上述的那套‘标准答案’。这样的已经偶像化的鲁迅,也难怪学生没有新鲜感了。”(40) 那么,日本初中的国语课是如何讲授《故乡》,中日的讲解有哪些区别呢?接下来将以下三点展开论述。 (一)“希望的文学” 陈漱渝主编《教材中的鲁迅》“第四章鲁迅作品在中学教材中的阐释”中谈到,在中国,关于作品的主题,长期以来有诸多说法,其中代表性的观点有“隔膜说”“农民问题说”“批判辛亥革命说”这三种。其中,“‘批判辛亥革命说’是受了极左思想的影响。‘隔膜说’和‘农民问题说’有道理的,在小说中也能找到可靠而充分的根据。”(41)这里提出了三种主题。 在日本课堂上较多采用学生通过讨论自己寻找作品的主题的授课方式。日本的讲授方式如前野昭人(1977)所说“国语课的授课,以语言为媒体,尤其注重对读解的指导,说教师对教材的解释是决定性的手段也不为过。”(42)可以说,对主题是由教师决定的。佐藤佐敏把《故乡》的主题设定为“希望自己首先要实现并努力的,而非期待他者、从他者处获得的事物。首先自己向希望迈出步伐非常重要,与自己的想法产生共鸣的伙伴增加的话,那么那个希望一定会实现。”(43) 实际,在日本初中的课堂上,很多教师在讲解时都将《故乡》作为“希望”的文本,关注“希望”。须贝千里在《作为教材的〈故乡〉》(足立悦男等《座谈会作为教材的〈故乡〉》,《日本文学》483,1993年)中指出,从1953年至今,教学第一线的教师一般把《故乡》诠释为“希望的文学”。他还指出,作为一个“希望的文学”看待,更易于贴近引发“道德主义的”“德目主义的”(44)的教学理念。这些都说明,“希望的文学”这一解释也与“国语教育等同道德教育”相关。 吉原英夫(1997)也提到日本教育界的情况,指出在课堂上“将《故乡》作为‘希望的文学’的倾向很强。”(45)他还指出,这个解读方法与日本鲁迅研究家的理解有所不同。他提及四位中国文学研究家——丸山升、桧山久雄、片山智行、藤井省三的看法是“青春梦的彻底崩溃”、与上述的“隔膜说”类似的“与民众隔绝”、瞿秋白的“僵尸支配”出发的“‘吃人’社会里的民众心中的凄惨”及“希望伦理的破产”,这几点与“希望的文学”的解读全然不同(46)。 吉原指出,“希望的文学”这一读解方式很容易将“教员的愿望”涵盖其中。他还指出,“研究者将作品与该作家的其它作品联系起来,并结合作者的一生和他生活的时代展开论述。而在课堂上,往往将作品本身作为独立的文本来阅读。”(47)因此,他分析日本教育界所做的“希望的文学”的解读是受了竹内好译文的影响,也可以说是一种“误读”。这与鲁迅文中的“只是他的愿望切近,我的愿望茫远罢了”(48)的译文有关。竹内1976年的译文把“茫远罢了”翻译成「手に入りにくいだけだ(很难得到罢了)」(49),从而让人觉得这是一种“被理解为只要努力就能得到的说法”“竹内好或许在重新翻译里将自身的希望也包含在内了。”(50)因此,可以说,将《故乡》作为“希望的文学”来解读也是受制于竹内的译文。 对此,日本的汉学研究者与日本国语教育界的理解不同,其原因正如田春娟(2006)指出的——与中国的教育方式有关。田(2006)介绍,中国初中语文课在学习外国文学时,“给学生介绍作者的一生、作者的作品风格(作品的写作风格)、作品的成立时期、写作品时的社会背景及作家的国家大概文化。”(51)但上述的佐藤佐敏教师讲解时,“虽然把鲁迅的生平及当时中国的社会现状等相关资料简单的整理成年谱印成学习资料,也简要介绍了作品的时代背景,但关于文豪鲁迅的作品风格完全没给学生介绍。”(52)与田指出的中国教学方式不同,日本课堂对《故乡》的阐释如吉原所说具有“将作品本身作为独立的文本来阅读”(53)的倾向。 (二)小说中的“我”是否等于鲁迅? 中西达治(1985)把《故乡》叫做“安定教材”,这个“安定”性,是根据“我”读书时的“容易讲授”产生的(中西:1985,p.31)。中西指出,“自传性、私小说的作品,往往从中可以看出其中描写的‘我’,即作家本身”(54),《故乡》也在此例。 日本五家国语课本出版社都收入了《故乡》,在1985年,四家出版社将《故乡》选入初三的课本,一家选入初二的课本。中西谈到:教师在给初中三年级的学生讲授时感觉很难,但给初中二年级讲授却没有这种感觉。所以,在考虑《故乡》的难点时,提出了三个问题:“我”和故乡的关系、“我”到底是谁、在此基础上再思考“我”和闰土的关系这三个要点(55)。这些问题都与“我”的人物形象有关。他说,如果仅限于作品的内容,初二学生的阅读水平也没问题。要解决上述的三个问题,就要补充小说中没有描写的内容——中国当时的社会状况、阶级问题、鲁迅的思想及行为等。如果将作品内容同鲁迅及当时的时代关联起来,讲解就变得很难。因此,可以说,讲解《故乡》的难点都源于对“我”这个人物情况把握不清。 日本国语教育界对“‘我’=鲁迅”这种解读方法也再三发出警告。森山重雄(1967)说:“这里首先说明的是,‘我’并非作家鲁迅。这是自传性色彩很浓的作品,虽然‘我’常常被混同于作者鲁迅(中国的教科书也是一例),但从小说鉴赏上来说这两者还是必须严加区别的。虽然确实‘我’是作者的分身,但并非原封不动的作者像。”(56)他还指出,“在这篇小说中,一句也没有提及一九一八年以《狂人日记》而开始从事文学活动的作者、作为文学家的形象。作者为了展现构由这次归乡经历获得的故乡印象,给予了‘我’独特的设定。总觉得‘我’完全是个孤独的人。不仅如此,‘我’还被设定为属于‘旧时代’的孤独知识人。”(57) 田中实(2014)也指出:正是这个没直接叙述的“叙事方法”,才是鲁迅特有的“叙事模式”(58)。他将读者作为听众,要求听众(读者)想像闰土的内心及以自己的“美”为骄傲的杨二嫂的内心(小说中,“我”没看出她是谁时,伤害了她的自尊心)。 如上所述,很多人指出小说中的“我”不是鲁迅。但日本国语课本是如何设定呢? 三村孝志(2010)(59)采用2006年版的所有教科书及光村教育出版(光村图书)的各个时代的五种课本进行比较和分析。他指出,各个课本的学习指南书中,提出的问题很多都与“我”有关,而且这些问题的提出都基于“我”是主人公的这一前提。总之,“我”=主人公之外的解读方式都被排除了。他还指出,从课本上的作者的简介、版面设计及插图导致“我”=主人公=鲁迅这种解读结果。 光村图书从1966年开始选入《故乡》,到1969年,都是以“我”=主人公=鲁迅为前提的,1972年是以“我”=主人公为前提。1981年,第一次提出“主题”,但补充了“我”是“活在社会和历史的动荡之中”,以及“苦难的时代里良心地活着的作者自身的形象”这样的描述。为此,三村指出了在解读上会造成混乱的可能性。可见,自1986年以后,出现了重视主题和“自己的想法”的变化,同时“也反映出学生自己总结就好的倾向。”(60) 三村还指出,教科书中的《故乡》与竹内好的译文不同。例如,所有教科书都删掉原作标注的“一九二一年一月”。他说,删掉日期后,学生不清楚这篇作品的写作时间。但这种删减也使得教科书中的《故乡》不再是鲁迅的原文了。所以三村指出,不该删掉“一九二一年一月”这个日期。 (三)究竟是谁在灰堆里埋碗碟? “究竟是谁在灰堆里埋碗碟”这个问题,中日双方的解释不同。而且,据藤井省三《鲁迅〈故乡〉的读书史》(1997)介绍,中国各个时代的解释也不同。其实,在日本国语课上并不讨论这个问题,任由学生各人自由的想像。本来“谁”埋的完全没有关系,重要的是“我”的想法。所以笔者认为,这个问题始终是教师乃至学者关注的问题。 其实,一般都认为是“闰土”把碗碟埋在灰堆中的。这些看法不胜枚举。仅举下述几例。 森山重雄(1967)在了解中国语文课的读解方法后说到:“闰土的这种懦弱态度与将碟碗藏在灰堆里偷偷搬走的行为是一致的(也有看法认为是杨二嫂的诬告,但笔者不认可这个观点)。”(61) 中西达治(1985)也说:“尽管说出来就能得到,但还是将一些想要的东西藏在灰堆里”(62)。他也认为是闰土把碗碟藏在灰堆里的。 在西乡竹彦与竹内实的谈话中,西乡说道:“闰土就是闰土,灰堆里‘十多个碗碟’虽然不算什么,但还是打算之后搬回去的吧?”(63)竹内实则谈到:“对鲁迅来说,隐藏碗碟这件事是很悲哀的。如果说要,就能得到。那些东西就算卖到旧器具店也不值多少钱,给亲友分赠东西也是理所当然的。为什么不跟我说自己想要呢,这便是鲁迅的心情。仅此而已。但是,从鲁迅对闰土的关系来说,闰土不是说不出口,而是闰土的生活习惯所致,将自己(鲁迅)看做旧时代中国的‘老爷’,闰土看到了在说出来之前逆来顺受的自己。我认为这里也有着悲哀。闰土与我的关系本不应该这样,但为什么不说呢,比起令人着急,更多的是些许的悲哀。”(64)可以看出,竹内实把将小说中的“我”视作鲁迅,而且他没有怀疑把碗碟藏在灰堆里的是闰土。对于西乡与竹内的对谈,笔者感兴趣的不在于闰土是否埋了碗碟,而在于他们的对谈中说到杨二嫂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偷窃”行为,而是根据当时社会的习俗,将其看作是一种施舍。就像少年闰土说的:“走路的人口渴了摘一个瓜吃,我们这里是不算偷的。”(65)如果是这样的话,杨二嫂的行为也不算“偷”,而是当时社会的一种感觉——从富人那儿获取没有价值的东西不算“偷”。 中西一彦(2010)在谈到授课实践中发给学生的“课文要点问题表”里,也有这样的字样:“虽说‘凡是不必搬走的东西,尽可以送他’,但还是把碟碗藏在了灰堆里”(66),这是“象征闰土的卑屈的情节”。 田中实(2014)肯定地说:“犯人当然是闰土,就像杨二嫂也有强烈的自尊心一样,看似木偶人的闰土也有自尊心。他能说出想要香炉和烛台那样高价的东西,但说不出想要碗碟那样的小小的日用品。这就是佃农闰土的悲哀又悲惨之处。但就算偷了东西,在拜访旧主人之时还是带了干青豆作为问候。他并非没有自尊或分寸,反而,就算只能见到闰土自我瓦解,身体变成木偶人,也不逊于地主出身的知识分子“我”,想到自己的孩子水生的未来,为了不让水生和宏儿变成迅哥儿和自己一样,九天后在送别时闰土没有带水生来,这是作为父亲的心情。蕴含着从‘我’这里看不到的闰土的人物形象,‘我’与闰土人物的形象意外地有着相似之处。”(67) 除竹内实之外,许多日本文学家或教育学家均持有同样的观点。因此,日本普遍的解读方法都认为是闰土把碗碟埋在灰堆里的。三宝政美(1994)(68)也指出了这一点,但她提及:中国的看法则是杨二嫂。 那么,学生是如何看的呢?对这一问题,丁秋娜(2009)进行了问卷调查。她2007年进行的调查(69)显示,日本初中学生中,54%的学生认为是闰土、34%是杨二嫂、12%是其他人。丁指出,日本的解读方式有变化。同时她也对中国的初中学生进行了调查,中国的初中生中,92%的学生认为是杨二嫂、5%是闰土、3%是其他人。而且,认为是“闰土”的中国初中生说:如果能读懂后面的文章,就能判断是闰土埋的(70)。丁指出,日本学生有“要有想要阅读人物内心的感情和想法的心情阅读”和“贴近人物、表现感激和感情的感性阅读”(71)的倾向。而中国的初中学生的解读方式是理性的和教训的。而且,依照文章的逻辑性和内容理解的倾向很强。丁还说:日本学生的解读方式各式各样,是多元性的。与之相反,中国学生的解读方式是统一的,有统一意见的倾向。 通过丁的调查,我们可以看出,日本初中学生并不都认为是闰土埋藏的碗碟。这个看法与上述的研究者与教师不太一致。因此可以说:日本国语课并不重视对这一点的解释。 日本中学讲授鲁迅的《故乡》已有四十年以上(从1953年算起,有六十年以上)的历史,日本国语教科书均收入了鲁迅的《故乡》,且被称之“安定教材”。因为鲁迅的《故乡》是“近代小说(现代文学)”的代表,且日本文学中尚无《故乡》那样既描写怀念故乡的情感,又通过故乡的现状反映社会问题之类的作品。因此可以说,鲁迅的《故乡》是独一无二的以故乡为题材的作品,一直为日本教科书所采用也就可以理解了。 然而,在日本国语课堂上读到的并非是鲁迅的原文,而是竹内好的译文。中国的中学生能欣赏到鲁迅的原文,但日本初中学生却无法做到。实际,鲁迅《故乡》的日文译本有很多种,但国语课本都采用竹内好的译本。藤井省三指出,竹内好的译文是本土化、日语化了的。所以,以学习语言(日语)为目的的日本国语课上,自然会选择与日语水乳交融的竹内的译文。尽管很多人指出竹内译文存在许多问题,然而日本教育界依然选择竹内的译文以凝练对《故乡》的解读。例如:把《故乡》看做“希望的文学”并加以诠释也源自竹内译文。因而,日本初中学生接受的《故乡》,并非是真正意义上的鲁迅的《故乡》,可以说是竹内“鲁迅”的《故乡》。正如是吉原(1997)所说,“希望的文学”包含了竹内的愿望。 一直以来,日本国语课都发挥着道德教育的作用。事实上,“希望的文学”这种解读方式也被看做是道德主义式的,很多教师通过这一“希望的文学”对初中学生寄予期望。但有些人向这种道德主义式的解读方式敲了警钟。但三村(2010)提出:“我认为,在‘希望’一词让人感到空虚的时代里,必须讨论要怎样阅读《故乡》。”(72)他以这句话结束了文章。三村分析了初三所有的国语教科书。通过分析,我们知道并不是每个教科书都强调“希望”。但看他的结束语,会觉得他心中也感觉是“希望的文学”。总之,我们看到日本国语教育界还有“希望的文学”这个阐释,也可以说“国语就是道德”的理念尚存。 最后,顺便介绍一下日本初中学生对鲁迅的《故乡》的读后感。市毛胜雄(1986)整理了当时日本学生的读后感。他说:“虽然觉得一点儿也没有趣,但说‘能够理解’这样的初中生多了起来。”(73)据丁(2009)进行的问卷调查(74),很喜欢或喜欢《故乡》的日本初中生为4%/64%,一共有68%;中国初中生是30%/67%,一共有97%。答不太喜欢或不喜欢的:日本初中生是30%/2%;中国初中生是3%/0%。从她的调查还可以看出,不能表达自己看法的日本初中生比较多。 此外,笔者在教授大学生阅读鲁迅作品时,发现连鲁迅的名字都不会写的大学生也很多。所以笔者认为,他们在初中时对鲁迅或《故乡》的印象并不深,这与藤井省三《鲁迅〈故乡〉的读书史》中介绍的1930年前后的初中生的反应——印象不太深(75)一样。 虽然日本初中生接受的《故乡》不是鲁迅的原文,而是竹内“鲁迅”的《故乡》,且受到竹内译本的诸多影响。但鲁迅的《故乡》在日本称得上是独特的作品,对其作品的解读也在日本独特地发展着,因而呈现出与中国初中学生不同的解读。 ①1980年代也有初二的学生学习鲁迅的《故乡》,现在一部分私立高中也为高中生讲授《故乡》。因此可以说日本学生几乎全都学过《故乡》。 ②吉原英夫:《〈故乡〉(鲁迅)是“希望的文学”吗?——附〈故乡〉研究·实践文献目录》(「故郷」(魯迅)は〈希望の文学〉か——附「故郷」研究·実践文献目録——),《北海道教育大学纪要(第1部C)》第47卷第2号,1997年》。此资料目录截至1996年。目录包括翻译、著作和论文。 ③《初中3年级国语教科书中上的〈故乡〉》(中3の国語の教科書にある「故郷」),2014-10-01,http://ameblo.jp/g-kobo-takashi/entry-11932895485.html.2015.04.20。 ④《关于〈故乡〉(鲁迅/竹内好译)》(「『故郷』(魯迅/竹内好訳)について」),名古屋市立女子短大《研究纪要34》,1985年。收录《课堂上的“文学”阅读》(『教室で「文学」を読む』),三省堂,1991年。 ⑤《大调和》1卷7号,1927年10月。中西一彦只写《大调和》10月号。 ⑥足立悦男:《以〈故乡〉(鲁迅)为中心的问题史》(「『故郷』(魯迅)をめぐる問题史」),《研究纪要》第45号,教育調查研究所,1992年。 ⑦(75)藤井省三:《鲁迅〈故乡〉阅读史》(『魯迅「故郷」の読書史』),日本:创文社,1997年,p.7、p.80-81参考。 ⑧三村孝志:《鲁迅〈故乡〉载入教科书方法的探讨——为让教师新鲜地阅读〈故乡〉》(「魯迅『故郷』の教科書揭載方法の検討——教師が『故郷』を新鮮に読むために——」),《全国大学国语教育学会発表要旨集》118,2010年。 ⑨中西:2010,p.100。 ⑩田中美也子:《采用“变容”视点的读法》(「『変容』という視点でとらえた読み」),《教育科学国语教育》1986年10月号,日本:明治图书。大冢敏久:《摆脱安定教材》(「「安定教材」からの脱却を」),《月刊国语教育》1994年11月号,日本:东京法令。菅野圭昭:《谈谈新生活》(「新しい生活について語り合う」),《教育科学国语教育》1989年6月号,日本:明治图书。 (11)山田文雄:《用视点人物“我”来阅读》(「視点人物『わたし』で読む」),《教育科学国语教育》1987年9月号,日本:明治图书。 (12)飞田多喜雄:《故乡教材分析的读后感》(「故郷教材分析を読んでの感想」),《教育科学国语教育》1987年9月号,日本:明治图书。 (13)宇佐美宽:《国语科授课批判》(『国語科授業批判』),日本:明治图书,1986年。 (14)鹤田清司:《叙述者和视点的分析技术》(「話者と視点を分析する技術」),《月刊国语教育》1995年12月号,日本:东京法令。 (15)村田正子:《朗读中心场面》(「中心場面を音読で」),《教育科学国语教育》1996年10月号,日本:明治图书。花田修一:《谋求〈故乡〉一体化》(「『故郷』で一体化を図る」),《教育科学国语教育》1993年3月号,日本:明治图书。中岛阳子:《选择〈故乡〉中的课题的学法》(「『故郷』における課题選択学習——T·Tを活用して——」),《月刊国语教育》1997年12月号,日本:东京法令。门岛伸佳在第十届日本教育技术学会鹿儿岛大会上发表,《教育科学国语教育》1999年8月号,日本:明治图书。 (16)丁秋娜:《〈故乡〉(鲁迅)学习指导的中日比较研究》(「『故郷』(魯迅)における学習指導の日中比較研究」),《早稻田大学院教育学研究科纪要别册》16号-2,2009年,参考。她用的是《语文教学参考书九年上》(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17)(18)(20)(21)(22)(23)(24)石原千秋:《国语教科书的思想》(『国語教科書の思想』),日本:筑摩新书,2005年,p.28、pp.27-28、p.25、p.75、p.84、p.84、p.103。 (19)(39)(40)蔡栅栅:《日本教科书中的〈故乡〉》,《中华读书报》2015年7月22日。 (25)(28)(48)(65)鲁迅:《故乡》,杨义选评:《鲁迅作品精华(选评本)第一卷小说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52、55、57、51页。 (26)田中实:《续〈主体〉的构筑——鲁迅《故乡》再论——》(「続〈主体〉の構築——魯迅の『故郷』再々論——」),国语教育思想研究会《国语教育思想研究》8号,2014,指出。 (27)竹内好的译文有两种。以前国语科教科书使用的是《鲁迅作品集》(日本:筑摩书房,1953年)收入的译文,1976年修改后,使用《鲁迅文集第一卷》(日本:筑摩书房,1976年)收入的修订版译文。本论文也采用后者。 (29)(54)(55)(62)同注释④,p.36、p.31、p.35、pp.44-45。 (30)(49)鲁迅:《阿Q正传·狂人日记外十二篇》,竹内好译,日本:岩波书店,1981年修改,pp.222-224、p98。 (31)(32)(33)(58)(67)同注释(26),p.23、p.20、p.25、p.25、p.26。 (34)藤井省三:《译者后语》(「訳者あとがき」),鲁迅:《在酒楼上/非攻》,光文社古典新译文库,2010年,pp.281-282。 (35)(37)青柳隆:《以〈故乡〉(鲁迅)为例》(「『故郷』(魯迅)を例に」),《教育科学国语教育》,1970年9月号。这篇文章是《在文学授课的哪个阶段教员模范朗读》(「文学の授業のどの段階で範読したか」)中的一篇。 (38)参照注释(15)。花田修一的例子正是用“寂寥之感”指导的例子。 (41)陈漱渝主编:《教材中的鲁迅》,福建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第311-312页。 (42)前野昭人:《能不能成为多么游学的丰富授课?》(「どれほど血と肉のある豊かな授業になり得たか」),《教育科学国语教育》,1977年9月号,p.46。 (43)佐藤佐敏:《使用阅读形象的技巧,深化解释的授课》(「形象を読むスキルを使い、解釈を深める授業——井関型分析批評による無指名討論の協働学習を通して——」),《在与教课专任教师共同努力下的佐藤佐敏教喻〈故乡〉(鲁迅)的多元研究》(「教科専門教員との協働による佐藤佐敏教諭「故郷」(魯迅)実践の多角的研究」),《新潟大学教育人间科学部附属教育实践综合中心研究纪要教育实践综合研究》第5号,2006年,p.41。佐藤佐敏当时是新潟大学教育人间科学部附属新潟中学校的教员。 (44)“德目“主义是将道德进行分类的名目。如正义、勇气、善意等,通过对这些德目的逐一传授,便可形成“道德性”。 (45)(46)(47)(50)(53)同注释②,p.177、pp.178-179、p.179、p.179、p.179。 (51)(52)田春娟:《中日外国文学作品学习指导的不同》(「日中における外国文学作品学習指導の相違点」),《在与教课专任教师共同努力下的佐藤佐敏教喻〈故乡〉(鲁迅)的多元研究》(「教科専門教員との協働による佐藤佐敏教諭「故郷」(魯迅)実践の多角的研究」),《新潟大学教育人间科学部附属教育实践综合中心研究纪要教育实践综合研究》第5号,2006年,pp.44,45、p.44。 (56)(57)(61)森山重雄:《中国鲁迅〈故乡〉》,日本文学协会《文学教育的理论与教材的再评价》,日本:明治图书,1967年,pp.122-123、p.123、p.122。 (59)参照注释⑧。当时,三村是佐渡市立内海府中学校的教员。 (60)(72)同注释⑧,p.218、p.218。 (63)(64)《民众的思想与文学》(「民衆の思想と文学」),《西乡竹彦文艺·教育全集·第31卷》,日本:恒文社,1998年,p.251、p.255。 (66)参照注释⑩。中西:2010,p.107。 (68)三宝政美:《教材〈故乡〉论——中日比较》(「教材『故郷』論——日中の比較」),《月刊国语教育》,153,1994年。 (69)丁2007年12月在日本东京都中野区立第三中学进行调查,2008年2月在日本学习院中等科也进行调查。在中国,2007年7月在江苏省如皋市江安中学和沈阳市第二十四中学进行调查。(参照注释(16)) (70)(71)(74)参照注释(16),p.290、p.294、p.288。 (73)市毛胜雄:《描写的学习指导——以〈故乡〉为例·二》(「描写の学習指導——『故郷』を例に·その二」),《教育科学国语教育》,1986年1月号,p.102。标签:故乡论文; 鲁迅论文; 鲁迅的作品论文; 国语论文; 翻译文学论文; 文学论文; 读书论文; 语言翻译论文; 闰土论文; 鲁迅中学论文; 日本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