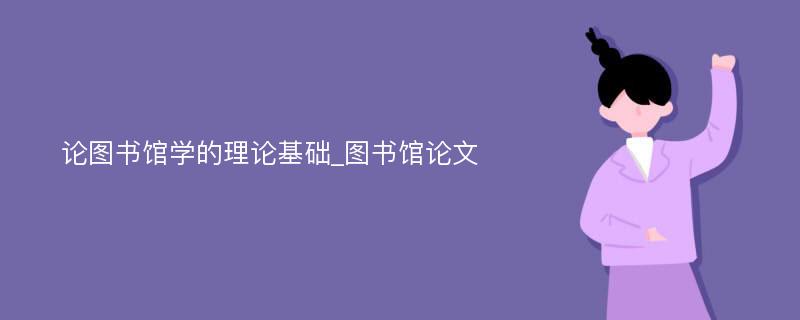
论图书馆学的理论基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图书馆学论文,理论基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类号]G250
1 理论基础的涵义及作用
1.1 理论基础的涵义
任何一门学科的建立与发展,都必然得到某种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的支持,图书馆学也不例外。我国图书馆学理论基础的概念,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初,此前叫做“指导思想”,一般指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80年代以来,有关理论基础的文章逐渐增多,然而什么是理论基础,其内涵、外延至今还存在着一定的模糊性。归纳众说之长,笔者认为,图书馆学理论基础是图书馆学理论建立的根基,它是由一些抽象、具体的理论观点组成的图书馆学先导思想。理论基础的涵义应包括以下内容:①是图书馆学理论创发的根本或起点,即发生学意义上的逻辑起点。逻辑起点一旦给定,图书馆学的原理、体系等便可演绎而成。②是哲学与图书馆学沟通的桥梁,起着哲学与图书馆学相互联接与沟通的作用。③是一些可辨析的、陈述的思想学说或理论观点,它们生成于哲学或具有抽象思维性质的某些学科(如数学、系统科学)之中。④这些思想学说或理论观点不仅对图书馆学具有启发、指导作用,而且具有很强的解释力。
1.2 理论基础的作用
把理论基础视为图书馆学的逻辑起点、哲学与图书馆学沟通的桥梁,应该说既阐明了其地位,也论及了其作用。不过,理论基础在图书馆学研究中的具体作用还未进一步明确。卿家康曾撰文涉及此问题,他说理论基础的具体作用有三方面:“第一,深刻地揭示研究对象类现象的本质,并正确地反映对象事物的客观规律;第二,正确地指引学科发展的基本途径与方向,为对象学科奠定认识论基础;第三,有效地指导科学研究全过程”[1]。此观点的提出者最早是沈继武, 他将这三方面内容表述为构成理论基础的条件[2]。不过, 卿家康将其视为“具体作用”似乎更为合理。
2 理论基础与其相关概念
2.1 理论基础与基础理论
理论基础与基础理论是两个不同的概念。黄宗忠认为:一方面,“理论基础大于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因为它可以是多个学科的共同理论,“既可是某一种单一理论,也可能是多种理论的集合,是一个群体。如图书馆学的理论基础就包含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哲学、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教育学、心理学等”。另一方面,理论基础又“处于图书馆学体系之外,不是图书馆学的必然组成部分”,而“基础理论属于图书馆学体系之内,是图书馆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图书馆学的基石”,“在图书馆学体系中处于第一层次”[3]。
对于黄先生的观点笔者有不同看法,理由在于:①理论基础是图书馆学理论的逻辑起点,如果把理论基础排除在外,不属于图书馆学,也就等于说图书馆学没有逻辑起点。没有逻辑起点,怎么可能演绎出其基础理论来呢?所以,理论基础应属于图书馆学范畴,是基础理论的第一层次,它是图书馆学的根基。②黄先生把哲学、信息论、教育学等学科或学科群视为图书馆学的理论基础,理所当然它们是处于图书馆学之外,且又大于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但笔者认为,理论基础是由一些具体理论观点、思想学说乃至某学科中的个别原理、概念构成的,它们只是自身所属学科的组分,而非其整体。它们被吸收、化约、融合至图书馆学中已经成了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一部分,对图书馆学肩负着启发、阐释、指导的作用,不应再看成图书馆学以外的东西。
2.2 理论基础与图书馆学哲学
什么是图书馆哲学?目前说法有异。1996年周文骏先生倡议“建立图书馆哲学”时说:“图书馆哲学是关于图书馆本质规律和方法论的学科。它一方面是图书馆实践和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的总结、概括和升华;另一方面也是一般哲学原理在图书馆领域的应用。”此外,他对图书馆哲学的地位归属也作了阐释:“多年来关于‘理论基础’的探索,假如其目的是追求把握图书馆的本质规律,那么也可以认其为图书馆哲学的近义语或同义语”。图书馆哲学“既是应用哲学的一个分支,又是图书馆学的一门基础理论学科”[4]。
图书馆哲学是哲学对图书馆、图书馆学的关照,它与图书馆学理论基础有某种等义关系,二者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语义互换。这些认识是应当首肯的。然而,图书馆学理论基础的内容不仅仅是哲学的,它在发展中还能够吸收、借鉴其他具有抽象思维性质的学科(如系统科学、数学)的理论观点,并用其阐释图书馆学的一些元问题。因此,从内容范畴来说,理论基础较之图书馆哲学更为宽泛。
此外,我们提倡图书馆学要加强哲学研究,但是否把图书馆哲学建成一门学科,则应持谨慎态度。因为图书馆哲学是生动的、鲜活的、深邃的、灵敏的抽象思维活动,它通过深刻的分析与见解为图书馆实践、图书馆学理论提供启示与感悟,只要它有效达到此目的就可以了,不必一定要具备什么体系,成为一个学科。理论基础就不是以独立学科面貌出现的。事物总有两面性,图书馆哲学一旦成为一种体系、一门学科,它就具有了模式、规则、框架、结构,这对哲学思维的活力无疑会形成一种限定。而且,哲学对图书馆、图书馆学探索的成果,最终也要分归于图书馆学理论各自的组成部分之中,那么图书馆哲学想建立自己哪些新的内容体系呢?
2.3 理论基础与图书馆学方法论
图书馆学方法体系是由哲学方法、一般科学方法及图书馆学专门方法组成的。从内容角度看,图书馆学方法论与理论基础都具有其他学科“渗入”图书馆学,被图书馆学借鉴、吸收的共同特征。但是二者还是有区别的:①理论基础的内容是一些对图书馆学可解释的、可陈述的概念、观点、道理,而方法论讲的都是一些思维方法、分析方法,它不提供具体的、可陈述的概念、观点、道理等。②理论基础的宗旨是使图书馆学更具有价值和意义,而方法论的目的却是使图书馆学更为科学和具有效率。
当然,此处讲二者的区别,仅就理论基础与方法论涵盖的内容及功能而言,并非关涉科学与方法有何区别。科学与方法从来都是同生共长的,没有科学方法就没有科学成就。例如,数学对图书馆学的影响是深刻的。印度图书馆学家阮冈纳赞曾是一位数学博士,正因其具有深厚的数学素养,他才经过苦思冥想,利用数学的公理法演绎出了“图书馆学五定律”,并以此而享誉全世界。从方法论的角度看,这是数学方法应用于图书馆学的一个杰出范例。公理法是科学方法,虽然可以成功运用于图书馆学中,但它不是理论基础;“图书馆学五定律”才能称得上是理论基础。
3 理论基础的几种重要思想
80年代以来,理论基础的研究一度成为热门。一方面,国外图书馆学界某些理论基础观点先后引入国内,如美国谢拉的“社会认识论”,前苏联米哈依洛夫的“交流系统论”,德国卡尔施泰特的“图书馆社会学”,英国布鲁克斯的“知识基础论”等,都是从形而上层面对图书情报活动长期思考的结果;另一方面,国内学者也先后提出了引起人们关注的理论见解,如彭修义的“知识学”,赵红州的“中介世界论”,周文骏的“情报交流论”,宓浩的“知识交流论”,以及90年代以后的“信息资源论”、“知识组织论”等。人们力图寻找到一种有效的思想理论,使其能成为图书馆学的理论基石,并对图书馆学起到统摄、定向的作用。其中,波普尔的“世界3”理论曾因引起纷争而广为人知。 这些思想、理论从各自不同的角度显示出了宝贵的认识价值。
3.1 波普尔的“世界3”理论
英国哲学家波普尔的“世界3 ”理论广为图书馆学情报学界所熟知,其内容不必赘述。本文仅想提示的是,波普尔把客观物质世界称“世界1”,主观精神世界称为“世界2”,客观知识世界称为“世界3”, 其意义不仅在于突破了哲学上的一元论、二元论,关键还在于阐释了“世界3”独立存在的意义,强调“世界3”的实在性、自主性与永恒性,努力赋予“世界3”以充分本体论的地位。“世界3”所以能够成为图书馆学的理论基础,理由至少有两方面:
第一,“世界3”理论揭示出了客观知识世界独立存在的意义, 从而为图书馆学划定了研究对象的从属领域。波普尔认为人类主观知识一旦社会化、公开化、客观化,即“世界3”一经产生, 就具有客观自主性,成了独立于人类之外的自主世界。例如那些自然数、乘法法则等,虽是人为产生的,而且每代人都要学习它,但它并不因是否有人在学习或运用而决定其存在还是消失[5]。波普尔还数次提及了图书馆, 认为人类创造图书馆就是为了保存、积累“世界3”, 使客观知识得以继承与扩展。而且人类的进化恰恰也是建立在客观知识的不断继承与拓展之上的。可以说,“世界3”为图书馆学提供了科学的理论基础, 它启示建立在数千年图书馆发展史上的图书馆学,应该把其研究对象定位于客观知识世界这个层面上。“知识”包括主观知识与客观知识两大部分。主观知识的产生、发展、变化,有哲学、教育学、心理学等对其研究,而图书馆学研究的则是客观知识及其存在状态。
第二,“世界3”理论明确了文献的终极归属, 它为图书馆学提供了合理的逻辑起点。波普尔说:“我认为,书籍、杂志和书信都是典型的第三世界客体,……书籍的物理形状是无关紧要的,甚至物理的不存在也并不损害第三世界的存在;只要想一想所有‘佚失’的书籍、它们的影响及寻找它们的努力”[6]。波普尔认为,世界上所有图书馆、 资料系统保存的客观知识,它们只有极少部分被“世界2”所掌握, 从个人与私有意义说,大部分不是人们都“知道”的,亦即“谁也不能掌握这个世界的哪怕小小的一角”[7]。事实上,就是一个著作等身的人, 他也无法一一详述其著作中所写的内容。这一观点提示我们图书馆学,必须把那些文献记载的多如恒河沙数的知识内容,看成是人类拥有的大部分知识。这一部分客观知识是散乱的、无序的,如何将它们汇集、整序,从而为人们提供检索、利用,这就成为图书馆学研究的主要内容。个体文献表现的是客观知识的“单元”,它是组成图书馆的最小元素,也是初始起点,而对文献(客观知识单元)的研究,无疑就会成为图书馆学的逻辑起点。
波普尔“世界3”理论从1982 年由青年学者刘迅率先引入图书情报学界之后[8],曾引起图书情报学界的一场争论。随着争论的深入, 支持“世界3”成为图书馆学理论基础的观点, 遭到了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理论基础观点的人们的坚决反对。最终前者因处于劣势主动偃旗息鼓而使这场讨论落下帷幕。这场理论基础的大讨论留给我们可待深思的东西很多,而且这场讨论的结局也有欠公正,因为我们选取某种哲学思想作为理论基础时,应该看这种哲学思想能否转换成图书馆学理论的一部分。换言之,这种哲学思想在“内容”上与图书馆学之间应该具有可以化约、借用、融渗的逻辑对接关系。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成为图书馆学指导思想有其历史必然性,但应看到它更多的是为图书馆学提供方法(如唯物辩证法)指导,具有方法论意义,本身并未给图书馆学提供可化约、借用、融渗的“内容”。再说,任何一种理论思想如果是真正科学的,它不应该排斥其他的科学思想。
3.2 信息科学中“信息”的观点
信息科学是在70年代末传入我国的,仅数年时间,它就从学术界蔓延至社会各领域。80年代前期,“信息科学”、“信息技术”、“经济信息”、“市场信息”、“信息社会”、“信息时代”等概念纷至沓来,“信息热”席卷全国。图书馆学研究者从80年代初就对信息科学给予了极大关注,他们敏感到:信息科学的两大部分内容,即信息理论与信息技术,必将对图书馆学和图书馆实践产生深刻的影响与推动作用。而且事实发展证明,信息科学作为一门新兴的横断学科,它的许多理论观点对图书馆学都发生了重要启示与引导作用,被图书馆学界引入本学科充当自己的理论基础。
第一,信息科学对信息的阐释动摇了图书馆学的某些传统理论范式,图书馆学不得不用信息理论来重新审视自己原有的理论体系。信息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信息。信息理论创始人申农把信息看作用来消除随机事件形式的不定性的东西,控制论创始人维纳称“信息就是信息,不是物质也不是能量”[9]。 我国学者则认为:“信息是事物运动的状态和方式”[10],材料、能量、信息是物质的3个基本方面,三位一体, 是现代文明社会的三大资源。材料提供物质基础,是形体;能量提供做功潜力,是活力;信息提供知识智慧,是灵魂[11]。可以说,从本体论高度对信息进行如此深刻的探究与揭示,这在信息科学之前是绝无可能的。这些观点给予图书馆学极大震动。1979年,美国图书馆学家谢拉说:“我经常提出这样的反诘:‘人可以理解的书籍是什么?可以理解书籍的人又是什么?’这个问题看起来很简单,但实际含义非常深刻。这就是信息这个最基本的问题,也是图书馆学家的研究任务[12]”。因而,当我国图书馆学者开始将以往停留在书籍、图书馆表面上的目光穿透至书籍内容中去的时候,一种新的理论就开始出现了。
1984年,况能富发表文章建议图书馆学界关注并使用“文献信息”这一概念,他说:“文献信息是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识的精华,它是人类认识世界所获全部信息中的核心部分。只要抓住了文献信息,我们就抓住了人类认识的结晶,抓住了人类的思维果实”[13]。此后,“文献信息”成为图书馆学论文中高频使用的词汇。1992年,黄宗忠、朱建亮分别出版了自己的学术专著《文献信息学》与《文献信息学引论》,两书都认为应该建立一门能够覆盖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图书发行学的综合性学科“文献信息学”,“文献信息学”属于信息科学的一个分支。他们的理论根据是:图书、情报、档案等,本质是“文献信息”[14—15]。如果说波普尔的“世界3 ”理论把图书馆学研究对象从“图书馆”拉移至“客观知识”,其力量尚且不足的话,信息科学有关“信息”的理论,则大大助其以一臂之力。
第二,不仅信息科学关于“信息”的概念对图书馆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信息科学关于信息过程的学说,如1948年申农在《通信的数学理论》一文中提出的信源、编码、信道、噪声、解码、信宿的理论,也对图书馆学有启示作用。图书馆工作与信息过程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信息过程的学说对图书馆学自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因此,早在1983年,美国图书馆学者斯.J.高尔文就曾说过, 信息科学这一新兴学科对加强和扩大图书馆学理论基础所作的贡献,“使人们相信图书馆学像其他所有专业一样也需要广泛、 坚实的理论基础用以指导专业实践”[16]。1985年,吴慰慈也认为,建立在信息科学基础之上的文献信息理论,应该成为图书馆学、目录学、情报学共同的理论基础[17]。
3.3 系统科学有关“系统”的学说
系统科学几乎是同时与信息科学传入中国的,当时与信息论、控制论合称“三论”,也曾广为人知。何为系统,系统科学创始人贝塔兰菲认为,“系统可以定义为相互关联的元素的集”,它是一切事物的存在方式之一,无论在物理世界还是精神世界,“处处有系统”。因此,系统科学的原理是具有普适性的,贝氏本人就称系统科学为“一般系统论”[18]。系统科学的这一论断,受到图书馆学者们的普遍认同。他们借用“系统”的观点,把图书馆看成是一个系统。如1981年郭星寿就提出,图书馆是一种人造的、开放的和可适应的系统。理由是:①任何系统都具有本身功能,图书馆有储存与传播知识的功能,也有系统功能这一普遍特征;②任何系统都具有本身的层次结构,图书馆由文献收集、整理、保藏、服务等子系统构成,它们是并列关系,也具有系统的层次结构特征;③图书馆具有开放系统必然与外界环境进行物质、能量、信息交换这一普遍特征。因此,系统科学可以成为“图书馆管理的理论基础”。
此后,某些学者不满足于把图书馆仅视为一个系统的见解,他们结合信息科学关于信息过程的理论,将图书馆看成一端有“信源”输入,另一端有“信宿”接收的一个开放的信息系统,提出了图书馆是“文献信息系统”的观点。如1987年陈源蒸提出图书馆“属于文献信息系统”,他认为作出这样的认定,图书馆的属性就明确了,“图书馆学的属性也就得到了揭示,图书馆学是文献信息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他进一步陈述道:“信息论揭示了图书馆学属性,系统论为图书馆学找到了应有的位置”[19]。1992年,黄宗忠把图书馆、档案馆、情报机构等归属于文献信息系统。他认为,文献信息系统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实体,是一个整体,是一个不断发展和变化的动态系统[20]。至此,我国图书馆学界对图书馆本质的认识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准。
系统科学观点的加盟,充实、强化了图书馆学理论基础的建设。80年代以来,形成于理论基础层面的、广有影响的一些观点,都与之有密切关系。如1982年赵红州的“中介世界论”,他借助“世界3 ”理论把图书、情报界定为既有别于物质世界,又有别于精神世界的“中介世界”,在分析论证中,就使用了“系统”观点,认为图书是特殊的科学结构、知识系统,它们与精神世界有着重要的区别[21]。1984年宓浩提出“知识交流论”,其中对图书馆结构的分析与知识交流三层次的论述,都借助了“系统”观点,正如他本人所言:“无疑,用系统论、信息论以及耗散结构理论等原理和方法来解释和揭示图书馆工作机理是一个正确的方向,如何使图书馆系统成为一个动态稳定的有序结构是图书馆生机勃发,充分发挥其社会效益的核心问题”[22]。进入90年代,“信息资源论”、“知识组织论”的提出,更是对“系统”观点进行了纯熟的运用,如果说80年代“信息”、“系统”的观点与图书馆学对接时,“拼合”痕迹还较明显的话,90年代它们则融通圆化,浑然一体,“拼合”痕迹已经消失。
当然,上面所列举的“世界3”、信息科学、 系统科学等理论观点,还不能代替理论基础的全部与整体。之所以在这里将其重点提出,是因为它们至今还对图书馆学研究起着有效的指导作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20年来图书馆学研究的发展充分显示出了它们的价值和意义。另外,80年代以来图书馆学者们提出的各种理论基础层面的观点,可以说没有一种观点是以单一理论为基础的,它们往往综合了哲学、信息科学、系统科学、数学等等理论,其中甚至对国外学说也有直接继承关系。它们呈现出的多样性、整体性、综合性,正是我国图书馆学理论基础的一大特点。
4 理论基础的开拓建设
4.1 强化对哲学等抽象思维科学的研究
一种新的哲学思想或横断学科理论的出现,立刻受到图书馆学界的关注与研究,这既反映出图书馆学研究者具有较强的学术敏感,也反映出图书馆学理论基础的匮乏。1980年,英国情报学家布鲁克斯曾说,理论基础最初是由一些不言而喻的基本假说集合而成的。新的理论核心一旦形成,一是可以在初始基础上发展上部结构,扩大理论体系,一是可以深化、强化其自身所在的基础。当上部结构的生长失去了初期的坚定步伐时,人们才开始对处于隐含状态的基本假说产生疑问。他认为情报学无论外显的、内隐的基本假说均不存在,“情报学还处于被哲学遗忘的角落里,没有什么理论基础”[23]。其实岂止是情报学,作为历史较其远为悠久的图书馆学,尽管一段时间宣称自己有理论基础,但在80年代以前,可以作为理论基础的可陈述的内容有些什么呢?其内隐的基本假说在哪里?因此,时间与事实表明,当我们努力构建理论基础时,也正是理论基础薄弱、匮乏之际。近年图书馆学界对图书馆哲学的呼唤,也恰恰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一点。
建立能够指导图书馆学健康发展的理论基础,必须抓紧对哲学及其他抽象思维科学的研究。过去那些有效的,可以称之为理论基础的思想观点,大多是西方为顺应社会时代发展而产生的新学说,虽然我们不可以忽视,应积极引入、借鉴、消化,但这是一种被动的学术创获方式,即“人家有了我们才有”。它使理论基础的建设受到外力、时间等因素的制约,从而丧失自创性与自主性。因此,我们强调对哲学的研究,对一切科学思想的研究,最终是想主动地从中寻找到适合图书馆学实际的指导思想,摆脱外力、时间的制约。例如,经过认真研究,我们发现数学集合论对图书馆学就很有说服力。集合论是德国数学家康托尔提出的,他把具有某种共同属性的事物的全体称为“集合”,组成集合的个体事物称为该集合的元素。集合有集、全集、子集,有限集、无限集,有序集、无序集,交集、并集等等各种概念。他还提出了无限集的势、序型,建立了超限数理论。集合论不仅对数学的影响是巨大的,对其他科学(如哲学)的影响也是深刻的。系统论事实上也受到了集合论的启发,如前述贝塔兰菲给系统下的定义,就是借用了集合的概念。用“集合”的观点来分析图书馆,我们能深刻地揭示出图书馆的本质实际就是“知识集合”。如果将“知识集合”作为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以集合论、系统论原理阐释其元素、结构、组织、功能、环境等问题,也许图书馆学中的一些元问题会得到很好的解答。
4.2 理论基础的评价标准
80年代关于波普尔“世界3”的一场大讨论, 说明当时图书馆学界对什么是理论基础、什么是理论基础的评价标准还缺乏明确的共识。缺乏这样的共识,就会使讨论陷入混乱或者出现僵局。因此,我们不仅要对理论基础作出定义性解释,还应建立起一个评价标准,以便于对某种思想学说能否成为有效的理论基础作出恰当的评价。什么是理论基础的评价标准?笔者认为它有两个方面,一是理论评价标准,一是实践评价标准。
理论评价标准是指从合理性上对一种思想学说进行的理论评价。 1986年郑奋曾提出,一种理论能否成为一门学科的理论基础,应该考虑是否具有如下条件:“①这种理论本身是否具有科学性;②这种理论本身是否比较成熟;③这种理论能否给指定的学科以理论与方法上的指导”[24]。这是国内较早阐述理论基础标准的一种见解。笔者认为,理论基础的理论评价标准实际上只有一条,即看其能否对图书馆及图书馆学中的元问题作出合理的、深刻的预设与解释。因为,凡能给予合理、深刻预设与解释的思想学说,必定是科学的、成熟的理论。
实践评价标准是指从实用上对一种思想学说进行的实践评价。某一思想学说对图书馆学能否起到指导作用,最后不是靠理论证明,而是要靠图书馆学研究实践来验证。当我们要想否定某种思想学说时,最终要看它是否背离了客观实际,是否背离了社会实践。因此,凡是被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那它就是科学的、合理的、实用的理论基础。在实践面前,任何争论、辩白都是乏力的。虽然实践受时空因素局限,总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即有些理论问题在某一具体时代还不能用实践给予检验,但从历史延长的角度看,最终实践将给予回答。
总之,理论基础的评价标准虽然有两个方面,但它们之间不是割离的,它们共同形成了一个评价标准结构。其中实践标准是最根本的标准,因为有些思想学说作为理论基础出现问题时,如果不能在思维范围内解决,不能靠理论争论解决,那么最后只能靠实践来解决。这不仅仅是图书馆学应遵循的学术原则,也是任何一门学科发展所应遵循的学术原则。
收稿日期:2000—07—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