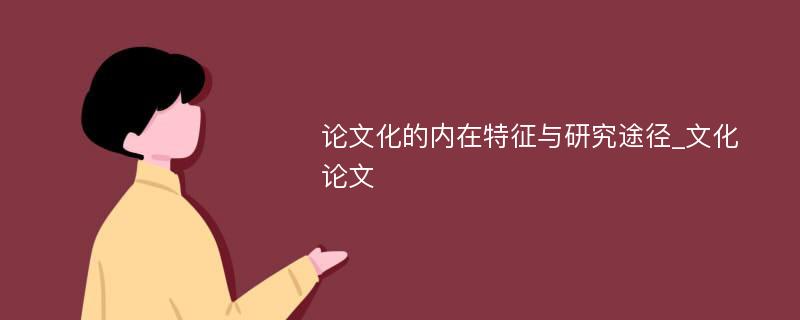
论文化的固有特征和研究进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进路论文,特征论文,论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什么是文化?
英语中的“文化”一词culture源于拉丁语cultura,其本意是:耕耘、耕作土地,种植、栽培庄稼,培育、饲养家畜等。这种涵义今天在“农业”(agriculture)和“园艺”(horticulture)两词中仍然保留下来。西塞罗(注:西塞罗(M.T.Cicero,公元前106~前43)是古罗马时期的政治家、律师、古典学者、作家。)在他的拉丁语著作中使用cultura时,有转义或比喻的意义——他言及“耕耘智慧”(culture mentis),其义与“哲学”一词同义,不过这种用法在当时的拉丁语中也是罕见的。culture在16世纪(《牛津词典》说在1510年)进入英语,已经具有为增进某种东西的质量而做的审慎的努力之义。例如,人们可以说“麦子的改良”(the culture of wheat)、“工艺的改进”(the culture of arts),可是不能单独说culture(“改良”或“改进”)。晚至1852年,清教徒纽曼(注:纽曼(J.H.Newman,1801~1890)是英国基督教圣公会内部牛津运动的领袖,后改奉天主教,成为天主教会领导人。)开始使用“精神耕耘”(mental culture)或“智力培育”(intellectual culture),而仍然不单独在此意义上使用culture——当今我们更乐意使用“教养、培养”(cultivation)来表述同样的意思。直到18世纪,像沃夫纳格侯爵(注:沃夫纳格(Vauvenargues,1715~1747)侯爵是法国道德学家和散文家。他和伏尔泰是朋友。)和伏尔泰这样的学者,开始在法语中以全新的意义使用“文化”(culture)一词。对他们来说,culture意指训练和修炼心智(或思想、或趣味)的结果与状态而非过程。很快地,这个词就被用来形容受过教育的人的实际成就。人们称良好的风度、文学、艺术和科学等为“文化”,并认为文化是通过教育能够获得的东西。从《牛津词典》得知,在1805年之前,英语中的culture还未出现这个意思。是马修·阿诺德(注: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1822~1888)是英国维多利亚时代优秀的诗人、评论家。)在他的重要著作《文化和无政府状态》(1869)中,把这个用法加以推广,作为文化一词的通常书面用法存留至今。至于文化一词在现代人类学的专门用法,只是在18世纪末的德国,出现在赫尔德(注:赫尔德(J.G.von Herder,1744~1803)是德国批评家、哲学家和路德派神学家,浪漫主义运动的先驱。)和他的同时代人的著作中(注:巴格比(P.Bagby):《文化:历史的投影》第87~89、191、143页,夏克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至于中文“文化”一词的渊源,在《易·贲》“观乎天文以察事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一语中,虽然业已可以窥见其端倪,但是作为一个连贯的名词则出现在西汉刘向的《说苑·指武》:“圣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当然,这里的“文化”是指文治和教化,是与“武力”相对应的“文德”,与现代意义上所谓的文化还相距甚远。
现代意义上的文化是什么呢?
文化可以说是与人的出现相伴而生的。但是,直到19世纪中叶以降,只是随着社会学、人类学、文化学的兴起,文化问题才引起人们的关注和研究。在20世纪,文化概念经历了重要的变化。据说,在1920年之前只有6种文化定义,可是到1952年,文化的定义已经多达160余个。在那些林林总总的定义中,大概没有一个是令人满意的——否则就不可能有那么多的定义了。可见,对像“文化”这样内涵极其丰富、外延十分广泛的大概念,要下一个严格、准确的定义,确实是不容易的。不过,我们在这里还是想简要地罗列一些文化定义,这是前人和今人从各个角度——例如从描述、功能、结构、规范、心理、历史、传承等角度——所下的定义,以便尽可能多地把握文化的涵义和精神实质。
人类学家泰勒和马林诺斯基的经典性的定义分别是:
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乃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任何人作为一名社会成员而获得的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杂整体(注:泰勒(Sir E.B.Tylor):“文化之定义”,载庄锡昌等编:《多维视野中的文化理论》第99~100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文化显然是一个有机整体,包括工具和消费品、各种社会群体的制度宪纲、人们的观念和记忆、信仰和习俗。无论考察的是简单原始的文化,抑或是极为复杂发达的文化,我们面对的都是一个部分由物质、部分由人群、部分由精神构成的庞大装置。人借此应付其面对的各种具体而实际的难题(注:马林诺斯基(B.Malinnowski):《科学的文化理论》第52~53、132、53、56、56页,黄建波等译,[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一些西方学者是这样给文化下定义的:
克罗伯:文化是一种产物;是历史的产物;包括观念、生活模式和价值观;是可以选择的;是习得的;是建立在符号基础上的;是一种来自行为或行为产物的抽象(注:威尔逊:《论契合——知识的统合》第185~186页,第190页,第180~181、192~195、223~224、219页,田洺译,[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版。)。
克鲁柯亨:文化是历史上所创造的生存式样的系统,既包含显型式样又包含隐型式样。它具有为整个群体共享的倾向,或是在一定时期中为群体的特定部分所共享(注:克鲁柯亨(C.Kluckhohn):“文化概念”,载庄锡昌等编:《多维视野中的文化理论》第119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沃斯诺尔:文化是用符号表现人类行为的方面,这个定义十分宽泛,足以考虑到口语、姿势、仪式行为、意识形态、宗教以及一般和文化这个术语相关联的哲学体系(注:沃斯诺尔(R.Wuthnow):《文化分析》第3页,李卫民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赫勒:文化在某种程度上是比人的价值更广泛的概念,因为它除了人的价值之外,分解为更为客观的成分,例如知识、语言、文学、艺术以及涉及到社会的表达的和符号的维度。于是,文化包括在给定的人中的习惯以及人工制品、观念和行为的抽象的共同特性的整体。它曾被定义为包括知识、信念、艺术、道德、法、习俗和作为社会成员的人获得的任何其他能力和习惯(注:Peter B.Heller,Technology Transfer and Human Values,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n,1985,Chapter 2.)。
布什:文化是由对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和寓居于其中的人的广泛了解构成;他们的历史,他们的希望和抱负,他们的欢乐和悲痛。它包括对工业的、艺术的、政治的、社会的舞台的广泛理解。它包括科学的进程,科学对我们的生活方式和对我们藉以思维的方式的影响。它就其本性而言是诠释的、疑问的、分析的。一句话,它是智慧的真正基础(注:V.Bush,Science Is Not Enough,New York:William Morrow & Company,Inc.,1967,pp.45~46.)。
赫斯:关于文化,我像大多数文化人类学家一样,我不把该词的范围局限于观念、宗教、艺术、文学、语言、电影、口述传说——简言之人的理智生活——的无形领域。更恰当地讲,在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概念与人的群体的总和知识和生活方式有关:有意识的和无意识的、隐含的和明显的。它是人群习得的一切,因此最好不与社会对照定义它,而代之与自然对照定义,与人的物理环境(虽然对自然的理解本身被文化地构造)和他们的生物学遗传(这通过生物学家的构造而传达)而定义。因此,文化不仅包括人的无形的信念,而且也包括社会行为领域:仪式、工作、职业、政治建制、家庭和亲属关系等(注:D.J.Hess,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a Multicultural World,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5,p.10.)。
我手头的有关辞书如下写道: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文化由思想和行为的习惯模式组成,文化包括价值、信仰、行为规范、政治组织、经济活动等等,这些是通过学习而不是通过生物的遗传代代相传的。文化概念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因为它产生了一整套解释和理解人类行为的原则(注:亚当·库珀、杰西卡·库珀:《社会科学百科全书》第161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
文化的中心意思是表征不同历史的人类群体的生活方式、工具、符号、习俗和信仰等等……文化也涉及到某一社会特有的价值体系与思维方式。这便等于“对某一社会的认识”。在广义上,文化是指人类思想、行为与人类活动产品的总和。在此意义上,文化与生物本性截然不同,并且一直用来区别人类与动物,因此属于哲学人类学研究的主题。在狭义上,文化包括艺术、体育、娱乐和其他休闲活动……文化也指通过教育和培训而获得的个人修养(注:布宁、余纪元编著:《西方哲学英汉对照辞典》第222~223页,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中国学者也对诠释文化概念甚感兴趣。梁漱溟说:“文化是人类生活的样子,文明是人类生活的成绩。”任鸿隽对此评论道:单说人类生活的样子还不能尽文化两字的涵义,还要加入“人类生活的态度”来包举思想方面的情形,文化两个字的意思才得以完备(注:任鸿隽:“科学与近世文化”,原载《科学》,第7卷(1922年),第7期。)。胡适认为:“文明是一个民族应付他的环境的总成绩,文化是一种文明所形成的生活的方式。”(注:胡适:“我们对于西洋文明的态度”,原载《东方杂志》,第23卷(1926年),第17号。)孙本文的定义是:“文化实在是一种复杂体,包括一切有形的实物,如衣服、宫室等,与无形的事项的知识、信仰、艺术、法律、风俗及其余从社会上所学得的种种做事的能力与习惯。”(注:朱谦之:《文化哲学》第3、7、8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
由文化的定义不难看出,作为一个整体,文化是有结构的,或者说是分层次的。最简单的,是把文化分为一般文化和高级文化,或称通俗文化和高雅文化。前者指一般人的生活方式,后者特指宗教、哲学、科学、艺术之类的文化形式。
马林诺斯基认为文化有三个维度。他说,处于文化过程中的人类是组织化的,使用人工制品,并通过语言和其他符号类型进行交流。人工制品、组织化群体和象征符号是文化过程的三个相互紧密联系的维度(注:马林诺斯基(B.Malinnowski):《科学的文化理论》第52~53、132、53、56、56页,黄建波等译,[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怀特把文化区分为三个亚系统:技术的系统(物质的、机械的、物理的、化学的器械)、社会学的系统(人际关系)及意识形态的系统(思想、信仰、知识,以语言或其他符号表现)。或者把文化系统分为三个层次:底层是技术的层次,上层是哲学的层次,社会学的层次居中。技术的系统是基本的和首要的,是整个文化系统的决定性因素。社会系统从属于技术系统,是技术的功能。哲学系统在表达技术力量的同时反映社会系统,并由前二者决定其内容和方向(注:怀特(L.A.White):《文化科学——人和文明的研究》第349~351页,第21、80页,第353、358页,第110~114、389页,曹锦清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让·拉特利尔采用的是四分法:一个共同体的文化可以认为是它的表达系统、规范系统、表现系统和行为系统的总和。表达系统包括构成共同体的各个群体用以解释自身以及他们生活于其间的世界的概念和符号之集合,还包括社会借此扩展其知识与技艺的方法;规范系统包括与价值观念有关的一切,这些价值构成了评价行为与情境的基础,必要时也为实践活动的辩护提供基础,同时提供与特殊规则相关的一切,行为系统则以这些规则组织起来;表现系统包括物态的方式和形态的方式,表达和规范系统由此得到体现,通过情感使更深层的东西外化为有意义的形式,并在无穷的诠释中发挥作用;行为系统既包括某些技术手段,这些手段使合理地适当地控制社会环境成为可能,也包括严格意义上的社会手段,一个以掌握自身命运为己任的共同体即由此组织起来(注:拉特利尔(Jean Ladriére):《科学和技术对文化的挑战》第4、5页,吕乃基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我觉得,殷海光先生的分类方法(他恐怕是有所参照的)是蛮不错的。在他看来,文化有四个层次:器物层次、制度层次、行为规范层次、价值观念层次。前二者处于文化系统结构的外围,后二者则处于文化系统结构的核心(注:李汉林:《科学社会学》第236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我认为,行为规范这个层次其实可以消去。关于行为的体制性的或成文的规范(如法律、政令等)可以列进制度层次,非制度性的或不成文的规范(例如道德、习俗等)可以计入价值观念层次。至于人的行为本身,也可以上推下移:属于制度约束的行为计入制度层次,属于观念支配的行为计入观念层次,因为正常人的行为总不会是无缘无故的。于是,文化只有三个层次——器物层次、制度层次、观念层次。这也是一种人们比较认可的见解。
在汲取前人思想的基础上,我在数年前给文化斗胆下了一个定义(注:李醒民:“弘扬科学精神,撒播人文情怀”,载[北京]《民主与科学》2002年第3期。)。我的指导原则是,既要尽可能地囊括文化的内涵和外延,又要尽可能地简明扼要。我不揣简陋,愿在这里和盘托出:
文化是种族的、宗教的或社会的群体的生活形式。文化由思想和行为的惯常模式组成,是建立在符号基础上的,它包括价值、信仰、习俗、目标、态度、规范等无形生活形式,以及与之相关的体制化的、仪式化的和物质化的有形生活形式。文化是进化的、历史的、社会的产物,是通过后天习得以及先天遗传代代相继的(基因-文化协同进化)(注:李醒民:《纵一苇之所如》第2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在这里,我们顺便涉及一下文化与文明概念的区别和联系问题。
文明是人类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过程和结果之总和。大约在1850年左右,“文化”和“文明”(civilization)概念获得了某种现代意义,它们有时被当作同义词,有时被当作反义词使用。20世纪许多学者对这两个概念已经不加区别,因为广义的文化概念也包括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个方面。
然而,一些学者还是在力图寻找二者之间的某些差异。例如,西方学者巴斯希望将文化限定为技术方面,即“人对自然在支配”。文明则用来指社会对人的本能的制约,即“人对其自身的支配”。汤尼斯和阿尔弗雷德·韦伯(A.Weber)却做出了恰恰相反的区分:文明是“一个实践的和理论的知识实体以及控制自然的技术手段的总和”,而文化则被限定为“价值、规范的原则以及观念的结构”。斯宾格勒(O.Spengler)指出,文明之于文化,正如存在(being)之于演化(becoming),智力之于灵魂(注:巴格比(P.Bagby):《文化:历史的投影》第87~89、191、143页,夏克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中国学者朱谦之认为,德国人所谓的Kultur(文化)概念实为精神的文化概念(宗教、哲学、科学、艺术等知识生活),英美人所谓的civilization(文明)概念实为社会的文化概念(如政治、法律、经济、教育等社会生活)。含混起来固然可如一般学者把两者区别置之不论,若精细考察起来,则此实际代表人类之两方面的表现。也就是,一方面表现为人类之知识生活的文化,一方面表现为人类之社会生活的文化(注:朱谦之:《文化哲学》第3、7、8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胡适在对文明和文化各下了定义——“文明是一个民族应付他的环境的总成绩,文化是一种文明所形成的生活的方式”——之后进而表明:
凡一种文明的造成,必有两个因子:一是物质的,包括种种自然界的势力和质料;一是精神的,包括一个民族的聪明才智、感情和理想。凡文明都是人的心思智力运用自然界的质与力的作品;没有一种文明是精神的,也没有一种文明单是物质的(注:胡适:“我们对于西洋文明的态度”,原载《东方杂志》,第23卷(1926),第17号。)。
即使从以上这些区分尝试和努力来看,文化与文明的差别也是不显著的。更何况,如何区分,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如果非要找出二者的微妙差异,文化似乎偏重精神的风范和风貌,而文明仿佛侧重社会的风范和风貌。其实,civilization一词本来就源于拉丁语civilis,其意是公民的、国家的、社会的,用以表示社会和国家的进步状态。不过,话说回来,就是这种微妙的差异也不是明显的和绝对的。事实上,英语词典就是用culture解释civilization的:文明是文化和技术发展的相对高的水平,尤其是文化发展达到书写和保持书写记载的阶段;文明是特定时间和地点的文化特征(注:Merriam-Webster's Collegiate Dictionary,Tenth Edition,Merrian-Webster Inc.,Publishers Springfield Massachusetts,U.S.A.,1993,p.210.)。
二、文化的固有特征
从文化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结构和要素以及对我们生活于其中的文化的观察和感悟中,我们可以窥见文化的诸多固有特征。
1.文化是人独有的,是人超越于动物的本质特征
动物是依靠本能和被动地适应自然而生存(并非生活)的,不像人那样依赖文化并在文化中生存,也不像人那样具有主动改造自然的能力以便更好地生存——这样的生存才是名副其实的生活。文化是人的生活形式和符号化的东西,这仅为人所拥有。文化使人有别于动物。让·拉特利尔一语中的:
正是在一个人的文化之中并且通过这一文化,他的生活才真正称之为人的生活,他才能升华超越他的纯粹生物的存在水平。他的文化向他提供“生活形式”,在这种生活形式中并由这种方式,他作为个体彻底存在方才得以实现。只有在这种生活形式的联系中,他才得以安身立命(注:拉特利尔(Jean Ladriére):《科学和技术对文化的挑战》第4、5页,吕乃基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斯诺也指出:文化表征人性的本质和人的才能,因为对自然界的好奇心和对思维符号的系统运用,正是最珍贵、最人性的两类人类本性(注:斯诺(C.P.Snow):《两种文化》第60页,纪树立译,[北京]三联书店1994年版。)。文化使“人类行为的支配原则不再只是物种的生存,也是我们称之为思想的生存”(注:韦斯科夫(V.F.Weisskopf):“科学的界限”,敬克兴译,载[上海]《世界科学》1990年第10期。)。
2.自然而然的东西不是文化,文化就其本性而言是非自然的或反自然的
文化不是自然而然地从自然中产生的,文化是自然界以外的由人另创造出来的东西。李凯尔特说得不错:自然产物是自然而然地由土地里生长出来的东西,文化产物是人们播种之后才从土地生长出来的,或者虽然是现成的,但至少是由于它的固有价值而为人们特意保留的(注:李凯尔特(H.Rickert):《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第20页,涂纪亮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例如,天然水不属于文化之列,但是经过提取、净化、消毒、输运而利用的自来水却打上了文化的烙印。在干旱地区把雨水收集、存贮在水窖中,以供饮用和浇灌,这样的水也包含文化因素。
自然是集柔美和凶暴于一身的。人类为了生存,为了解决安全、温饱、营养、生殖、卫生等需求难题,就不得不与自然抗争,建造新的人工环境或人工自然,以便利用自然的柔美,抵御自然的凶暴,使自然环境尽可能与人为友而不是与人为敌。也就是说,文化这种表达人的创造性的手段,是人积极地适应其整个环境的工具。文化中的技术系统明显是非自然的或反自然的,例如为防洪和灌溉而使用的水利技术和工程。文化的非自然的或反自然的因素,也或多或少体现在社会学系统和意识形态系统中。
3.文化产生的最低前提是人的机体需要之满足,但是随着人类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超体性文化的意义越来越凸显出来
不难理解,“个人和种族的机体或基本需求之满足,是强加于各种文化之上的一组最低条件”(注:马林诺斯基(B.Malinnowski):《科学的文化理论》第52~53、132、53、56、56页,黄建波等译,[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但是,在机体的需求逐渐满足的过程中,人的精神需求也会变得愈来愈强烈,加之人本身具有较高的智力和心理功能,这便为超体性文化(exosomatic culture)(注:林德塞(R.B.Lindsay):《科学与文化》第9章,方祖同译,[台北]协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76年第2版。)——和身体反应没有直接关系而和心智活动有关的文化——凸显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和坚实的基础。就文化本身而言,随着人类社会的进化,超体性文化的数量和权重急剧增加,而作为一个整体的文化的认知和审美特征越发突出,其认知和审美功能也愈加显著。布洛克(A.Bullock)所谓的文化主要指的就是超体性文化:
在自然世界之外还有一个人类参与的第二维度。用人类学的笼统术语来说,叫人类文化世界,也就是思想的、价值的、信仰的、艺术的、语言的、象征的、制度的、历史的(包括科学史)世界(注:布洛克:《西方人文主义传统》第251页,董乐山译,[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
4.文化是一个整体,它的构成要素只能在理论上加以分析研究,而在实践中则难以分割
马林诺斯基说,文化是由部分自主、部分协调的制度构成的整合体。它依据一系列原则而整合,例如血缘共同体通过生育,空间相临通过合作,活动中的专门分工,尤其是政治组织通过权力的运用来整合。每个文化的完备性和自足性都归因于一个事实:满足基本的、实用的及整合化的全部需求(注:马林诺斯基(B.Malinnowski):《科学的文化理论》第52~53、132、53、56、56页,黄建波等译,[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在对一个共同体的文化进行研究时,我们完全可以运用分析方法,在思想上把它加以分割。但是,我们在实践中则无法分割它,因为它的各个要素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且,在研究结束时,我们只有再用综合方法,把它整合起来,才能够全面、深刻地认识它。对于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类文化来说也是如此。文化的器物、制度、观念三个层次是难以在实践中分割的,作为文化的人的日常生活形式(ordinary form of life)和超体生活形式(exosomatic form of life)在实践中也是无法分离的。
5.文化是模式化和符号化的,因而是有规律可寻和可循的
文化是模式化的存在,不同的共同体或群落拥有不同的文化模式。文化模式既构造了行为和仪式,也构造了感知和思想,乃至塑造了个人的心理和群体的“地方性”“民族性”和“国民性”——这往往以“集体无意识”的形式显示出来。人是唯一地拥有文化和使用符号的动物,这本身就隐含着符号是文化的表征,或文化是符号的运用。正如怀特所说,符号是整个人类行为和文明或文化的基本单位。全部人类行为起源于符号的使用,人类行为是符号行为,符号行为是人类行为。正是符号使类人猿变成人,使人类的所有文化得以产生和流传不绝。文化是以社会符号为媒介的行为总和(注:怀特(L.A.White):《文化科学——人和文明的研究》第349~351页,第21、80页,第353、358页,第110~114、389页,曹锦清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在众多的符号中,语言符号占有特殊的地位。语言这种心智能力是人类独有的,是真正的文化产生的前提(注:威尔逊:《论契合——知识的统合》第185~186页,第190页,第180~181、192~195、223~224、219页,田洺译,[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版。)。语言(包括书面语言)的出现和使用,使文化得以广泛交流、迅速传播、有效保存和积极创新。由于文化是模式化的和符号化的存在,它就有可能呈现出某些规律性,从而可以借助经验方法加以考察,借助理性方法加以分析,借助人类学方法加以体味。
6.文化是经验的和理性的,也是历史的和多样的
文化的发生和发展既源于生活经验的总结,也源于理性的思考和创造。因此,文化是经验的和理性的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尤其是在文化达到较高的阶段即形成知识体系之后。小李克特的见解是有道理的:文化知识体系一般倾向于具有某种理性的和经验的特征——理性强调逻辑的重要性,经验强调观测的重要性。但是,在大多数前科学的文化体系中,这样特征在某些方面可能是相当有限的(注:李克特(Jr M.N.Lichter):《科学是一种文化过程》第96~101、89、81~83页,顾昕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版。)。
文化也具有历史性和多样性的特征。文化的历史性体现在巴格比的下述说法中:
文化是众人行事的方法。因为历史本身就是众人所作所为的结果。所以我们就能够知道,文化就是模式化的和反复地出现在历史中的因素……是历史的可理解的方面(注:巴格比(P.Bagby):《文化:历史的投影》第87~89、191、143页,夏克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无论从全球看(比如东方文化、西方文化等),还是从国家和地区(阿拉伯文化、中国文化及中原文化、岭南文化等)、部门(人文文化、科学文化等)、层次(通俗文化、精英文化等)看,文化都是多样性的。像生物多样性有利于生物的竞争和进化一样,文化的多样性也有利于文化的创造与昌盛。拉兹洛说得好:“只有在文化上是多样的,才可能是可行的:一致性在人类领域里可能像在自然领域里一样是极其有害的。”(注:拉兹洛(E.Laszlo):《决定命运的选择》第121页,李吟波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
7.使用和转换能量的水平是文化进步的标志
人类为了生存和发展,就必须使用和转换自然界的能量,为自己创造一个适于生活的具有人工痕迹的环境。如何使用和转换能量,标志着人类文化和文明的发展水准。起初,先民只会赤手空拳使用自己的体力,直接与自然搏斗;后来学会使用石器和弓箭,也只是转换为机械能的体力而已;再往后,人类逐渐学会使用直接的自然能(畜力、水力、风力等)、化学能(木材、煤、天然气、石油等)、电能、原子能——这实际上是从物质表层深入物质深层获取能量的过程。而且,也发明出便于利用能量的能量转换装置,比如蒸汽机、内燃机、发电机、电动机、核电站等等。德国哲人科学家、能量学和能量论(注:李醒民:“奥斯特瓦尔德的能量学和唯能论”,载[北京]《自然辩证法研究》第5卷(1989年),第6期。)的创始人奥斯特瓦尔德就是从能量论的角度解读文化的:
有助于人类社会进步的一切东西都被恰当地称为文明或文化,进步的客观特征在于改善为人的意图获取和利用自然界中的天然状态的能量之方法(注:奥斯特瓦尔德(W.Ostwald):《自然哲学概论》第125页,李醒民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
怀特赞同奥斯特瓦尔德的观点,他也依据能量论阐明文化演进的基本规律:在其他因素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当每人每年消耗的能量的数量增加时,或者使能量产生作用的工具的效能不断提高时,文化逐渐发展,即文化发展的水平同工具的效率成正比(注:怀特(L.A.White):《文化科学——人和文明的研究》第349~351页,第21、80页,第353、358页,第110~114、389页,曹锦清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8.文化的欣赏或消费不仅不会造成文化的匮乏,反而会促进文化的创造和繁荣
人的衣食住行之类的物质产品,是随着消费量的增加而减少的。如果它们的数量有限,一个人的消费则妨碍或剥夺另一个人的消费。也就是说,物质产品的消费是递减的和互斥的。与之相对照,文化成果或产品具有大异其趣的效果:对它的欣赏或消费反倒会激励文化的创造,刺激文化的繁荣。也就是说,文化成果或产品的欣赏和消费具有递增性和互惠性。比如一篇美文,你越是与其他人分享,或者欣赏(消费)它的人越多,它的意义和价值就会越大,每一个人都会从中受惠得益,并且有可能在交流和讨论中激发出新的灵感和思想,而不会对美文本身有丝毫的损耗。即使对器物类的文化成果的消费,在某些方面也是如此,比如我们到博物馆欣赏那些精美的青铜器,或者到茂陵汉墓欣赏那些粗犷、古朴的石雕。波兰尼注意到这一点,他说:
与原欲的满足适成对照,文化的欣赏不会造成提供满意感的物品的匮乏,而是保证并不断扩大这些物品对别人的供给。那些得到这些货物的人们增加了它们的普遍供给,并通过实践他们被教会的东西的方法教其他人学会欣赏它们(注:波兰尼(Michael Polanyi):《个人知识——迈向后批判哲学》第267页,许泽民译,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9.文化进化速度远快于生物进化的速度
根据现有的资料大致推知,地球的年龄有46亿年,最原始的生命也有38亿年。但是,人类所属的灵长目大概产生于白垩纪(约7000万~6500万年之前)的后期,在始新世(约5400万~3500万年)出现现代外表的灵长目,直至渐新世(3500万~2400万年之前)属于现代猴、猿的群体才得以问世。从类人猿到人的进化,又花费了千百万年,早期人类与动物揖别只不过数百万年。自从人类有了最初的文化之后,特别是在新石器时代(距今约1万年)有了农业和畜牧业文明或文化之后,尤其是有了文化的载体和思想的工具书面语言即文字(仅仅有5000年左右的历史)之后,文化的进化可谓一日千里。尤其是科学这种文化形式,在诞生之后的300多年间更是突飞猛进地发展。情况正如小李克特所言:“即使在前科学时代,与生物进化比较起来,文化的发展也是非常非常急剧的。”(注:李克特(Jr M.N.Lichter):《科学是一种文化过程》第96~101、89、81~83页,顾昕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版。)
李克特对这一现象做了这样的解释:坎贝尔(D.T.Campbell)把进化描述为包括变异,连贯地选择标准,保存、复制或扩散经过选择的变异。这个模型适用于生物现象,也适用于文化现象。把这个模型应用到文化现象上去,需要假设:在一类特定的文化客体中存在变异;某些变异在选择下生存并扩展;把经过选择的变异作为属于已建立的文化的一部分保持下来,成为以后的变异的一个起始点。但是,文化进化有不同于生物进化之处。第一,生育和成熟的长时间间隔限制了生物进化的速度,文化进化是通过学习产生的,学习可能具有的速度并不受类似的限制。第二,生物有机体具有很高程度的结合,从而形成强有力的稳定性力量,这阻止了急剧性的变化,因为这种进化变革往往是毁灭性的。与此相反,文化体系只有相对小的结合,这样便容许较大的变化在文化的某一局部出现,其他部分至少在短时间内可以原封不动,以致不会影响整个文化的生存。第三,在生物进化中,最初的变异相对于进化发展的方向而言是随机的,在其后的选择过程本身还要受到随机性的显著影响,致使变异在进化发展方向上所带来的优点非常微小。在文化进化中,随机性在最初的变异和选择过程中都相对较小,创新者的预见和计划有助于产生较大的连贯性。这样一来,文化进化相对于生物进化具有潜在的速度上的优越性,这在科学的进化中得到充分的展示(注:李克特(Jr M.N.Lichter):《科学是一种文化过程》第96~101、89、81~83页,顾昕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版。)。
10.文化是后天习得的,但是也不能完全排除某种先天的遗传因素,生物进化和文化进化是相辅相成的
一般认为,文化——无论知识型文化还是心理型文化——都是通过后天学习和仿效获取的,而不是通过先天性的生物遗传而自然而然地拥有的。也就是说,文化是学而知之,而非生而知之。这种观点现在受到某些挑战。近几十年的研究表明,基因遗传因素也在某种程度上介入文化的传承之中。这个问题比较新颖,也很有意思,我们不妨多花些笔墨讨论一下。
作为进化认识论的思想先驱,奥地利哲人科学家马赫早就注意到,遗传与文化(认知的和心理的文化)是相互影响的。马赫不同意洛克的“白板说”,认为人具有天生的倾向和“观念”,比如因果性观念、空间和时间观念,都具有某种先天性。在他看来,这种先天性是就个人而言的,其实它是种族长期的生物进化结果之积淀(注:李醒民:“进化认识论和自然主义的先驱”,载[北京]《自然辩证法通讯》第17卷(1995年),第6期。)。马赫这样写道:
不仅人类,而且每一个达到充分意识的个体,在他自身都会发现他并非深思熟虑地做了一份贡献的世界观。他接受这个作为自然和文明的赠品的世界观:每一个人都必须从这里开始。思想者只不过从这种观点出发,扩展和校正它,利用他的祖先的经验,尽最大可能地避免他们的错误,一句话:审慎地再次独立走相同的路径。
马赫这里所谓的“自然和文明的赠品”,实际上说明了文化在人身上的某种先天遗传性——这是作为一个种族的人类漫长自然进化的结果。难怪他说:“遗传、本能之类的东西,可以说是达到超越个体的记忆。”(注:马赫(E.Mach):《认识与谬误》第11、51页,李醒民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
进化认识论的公设包括先天性存在公设、先天性产生机制公设和认知载体公设。福尔迈是进化认识论的著名学者,当然具有这些见解。“精神”属性是否可以遗传?他对此明确做了肯定的回答。我们知道,智力是与文化密切相关的,是创造文化的工具;语言既是文化的一部分,也是文化发展的催化剂。福尔迈认为:“诸如智力或语言这些复合与综合的能力,恰恰以好些基因为条件。”即是说,就人的语言和理智能力而言,遗传传递起着某种作用。他探讨了文化的遗传传递的原因:
文化的每一次进步,又都增强了更好地适应和利用文化环境的必然性。凭借这种方式,文化给予人的遗传进化以强有力的选择压力。这样,文化能力,也就成了用来适应和支配环境的一种手段(注:福尔迈(G.Vollmer):《进化认识论》第135~137、122页,舒远招译,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因此,生物进化和文化进化是统一的,二者之间存在某种正反馈的关系。
美国当代著名的社会生物学家威尔逊提出基因—文化协同进化的理论概要。该理论认为,人类谱系的遗传进化推动了人类文化发生相平行的进化,这两种进化是有联系的。他把该理论的大致原则陈述如下:
文化是由众人的智力创造出来的,而每个人的智力又是人类大脑遗传结构的产物。因此,基因与文化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但是这种联系又不是僵硬的,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无法测量这种联系。这种联系并不简单,基因限定了预成规则,这种规则没有什么倾向性,而且受个人智力所具备的认知能力的调节。人的智力在人从生到死的发展过程,吸收了所能获得的部分文化,在这个过程中,选择引导了个人大脑所遗传的预成规则。
威尔逊进而解释了文化的基因遗传机制:文化的天然要素就是呈阶层体系排列的语义记忆成分,这些语义成分由不同的神经回路编辑,形成最终和大脑活动联系起来的节点。这些节点就是与语词关联的概念或符号,节点之间的联系便组成具有复杂含义的信息。数量众多的基因指令大脑、感觉系统和所有其他与外界物质和社会环境相互作用的生理过程,从而产生出心智和文化的综合性质。通过自然选择,环境最终选择了那些行使这种指令的基因。就这样,基因决定渐成规则,渐成规则调节感觉的接受和心理发育,而次成规则又推进和疏通文化的获得。文化帮助决定哪一种指令基因可以从一代到另一代幸存下去,并表现出更大的活力。成功的新基因改变群体中的渐成规则。变化了的渐成规则改变文化获得途径的方向和效力。他强调指出:“遗传学家利用高超的统计手段,已经能够计算出基因在多大比例上影响了感觉生理、脑功能、个性和智力等特征。他们得出重要的结论:人类行为几乎所有方面的变异在某种程度上都具有可遗传性,因此人类当中的基因差别以某种方式影响了人类的行为。”(注:威尔逊:《论契合——知识的统合》第185~186页,第190页,第180~181、192~195、223~224、219页,田洺译,[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版。)
一些当代作者也持有类似的观点。拉德尼茨基坚持,人的生物的和智力的构成——能使他应付物理环境——是生物的和文化的进化结合起来的结果。人的感官和大脑是长期进化的产物,适应所谓的中等宇宙(mescosmos),即客体、距离、速度等在大小上是中等维度的世界。设想人的认知感觉装备是由硬件(生物结构)和系统软件(假定、预期、假设、理论)组成的,不管软件以不可言传的知识形式存在,还是以语言上阐明的假设形式存在。即使在观察、感知某事物像某东西的最简单的行为中,我们由于做关于被感知的事物像什么的假设而超越了即时经验。不过,我们是在先前的经验上做这些假设的,并在任何感知行为中检验这些假设。这些假设被某些潜意识地持有的期望或阐明的理论构造。这种广义的“理论”在本体论上是先验的,但是在发生学上不完全是先验的,而是种族在长期进化中获得的种系发生的遗产。我们不妨称这种理论为“主理论”或“原始理论”(primary theories),它们是人的认知感觉设备的系统软件,对于所有文化是共同的,是人普遍具有的文化特征。由于主理论说明能力有限,需要另一种理论即“副理论”或“辅助理论”(secondary theories)。副理论是力图说明下述现象的理论类别:这些现象无法用局限于我们感官的理论来说明,而不管它们是包括超自然的实体,还是在经验上可检验的理论。宗教教义形成副理论类别的重要子集。这些教义不仅尝试说明事物,而且具有像提供内聚力和维持秩序的社会功能。副理论不归因于生物进化,而唯一地是文化进化的产物,从而它们从一种文化到另一种文化是广泛变化的。与主理论对照,由于它们对人的幸存而言没有什么价值,所以它们承担得起包括显然荒谬的断言后果(注:G.Radnitzky,Science As a Particular Mode of Thinking and the“Taming of the State”.F.D Agodtino & I.C.Jarvia,Freedom and Rationality:Essays in Honor of John Watkins,the Netheland: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1989,pp.163~181.)。韦斯科夫则一言以蔽之曰:“人的文化是基因差异和通过经验获得的差异的放大器。”(注:V.F.Weisskopf,Art and Science,F.D Agodtino & I.C.Jarvia,Freedom and Rationality:Essays in Honor of,JohnWatkins,the Netheland:KluwerAcademic Publishers,1989,p 105.)
三、文化研究的进路
在大体把握了文化的定义和固有特征之后,我们讨论文化研究的进路就比较方便了。研究文化的学科被人称为“文化学”,奥斯特瓦尔德似乎是使用该术语的第一人。他在1915年所做的“科学的体系”的讲演中,清楚地认识到人类的独特之处不是社会而是文化或文明。因此,对这一特征的科学研究应该叫做文化学而非社会学。他把文化学置于科学金字塔的顶端,他说:
很久以前,我就提议把这一正在讨论的领域称之为文明的科学或文化学(Kulturology)(注:怀特(L.A.White):《文化科学——人和文明的研究》第349~351页,第21、80页,第353、358页,第110~114、389页,曹锦清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尽管“文化学”这一学科并未得到学术界的公认——不过有“文化科学”(cultural science)的提法——但还是有人探讨了它的研究领域或子学科。例如,朱谦之说,可以把文化学分为两大部门:研究知识的文化生活者是文化哲学,研究社会的文化生活者是文化社会学(注:朱谦之:《文化哲学》第3、7、8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文化史(cultural history)不用说属于文化学之列,其中研究人类文化的起源、发展、功能等的分支往往叫做文化人类学(cultural anthropology),它也是人类学的子学科。现在,人们认为文化哲学(cultural philosophy)是从哲学的视野、运用哲学的方法,以文化为研究对象,探索文化以及人的本性、特征和发展规律的学科。文化社会学(cultural sociology)是研究人类社会中的行为、信仰、习惯和社会组织的学科,它有时也被称为社会人类学(social anthropology)。不过,也有人主张必须把文化系统与社会系统分开,把文化系统作为内部紧密结合的整体来分析。他们的工作离开了跨文化的比较研究,而转向对文化做解释学和符号学的研究——这种研究方向有时被叫做“符号人类学”或“认知人类学”。
关于文化研究的方法,马林诺斯基重视功能和制度两类分析方法,认为这将能够更加具体、精确和彻底地界定文化(注:马林诺斯基(B.Malinnowski):《科学的文化理论》第52~53、132、53、56、56页,黄建波等译,[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沃斯诺尔则指明了文化研究的四种方式。他说,在20世纪第三个四分之一时期,人们怀着日益增长的兴趣采取四种方式研究文化,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功。这些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处于社会科学主流之外,主要面向意义、符号、语言和话语的领域。每一种方式都植根于深刻的哲学传统。这四种研究方式是现象学、文化人类学、结构主义和批判理论,它们分别基于四门不同的学科——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和哲学。四种研究方式的差异是明显的,其假设和关注的现象大异其趣。但是,它们也有不少相似之处:十分强调语言和交际、分类体系、符号表现,显示出走向综合或者至少是借鉴的可能性,关注文化的可观察的、客观的、共有的方面,并探求其中的模式(注:沃斯诺尔:《文化分析》第8~22页,李卫民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有趣的是,施韦默尔从科学与文化的关系的角度,以文化作为科学的研究对象,探讨了文化理论的逻辑。他列举了九个命题。(1)在科学哲学借以描述科学的基本概念的关系的逻辑诠释中,科学和理性的特定特征一般被提升到指导形象和模型的地位,这既没有公平对待在科学中知识获得的过程,又没有公平对待我们在我们生活世界的文化中认识它的过程。(2)我们需要修正我们基本的逻辑概念,以便批判地反思和系统地理解作为一个过程的文化。这种修正能够由对象的同一和概念的普遍性这两个概念开始。(3)当行为的结果一起进入一种形式,而且它们本身出现在正在行动的人中,以便把这种形式理解为他们自己生活的表达,即作为他们自己的生活史的插曲,此时行为的结果作为行动获得了它的统一性。(4)对某一事物的每一个描述总是富有想象力的成就,某一事物不是用它参照对象或事实,而宁可说是用它与其他想象力的关联或诉诸这些成就辩护的,而这些成就本身又要求其他成就。(5)描述的富有想象力的继续只能够在文化符号化的媒介中达到——尤其是在语言符号化中达到——这个体间地(interindividually)在存在的特殊形式中发展。(6)属于符号化的个体间结构使个体表达的形式如此均一化,以致它们对其他人来说变成个体表达的潜在形式。以这种形式,其他人的表达能够作为我自己的自我的可能表达被领悟和理解。(7)处在个体中间的符号化的固定结构容许表达和言说(discourse)的公式呈现,这种公式如此传达了表达和与他人交换的可能性,以致它们可以被诠释为普遍概念,即以消除外部语境和使内部语法图式化的方式描述概念。(8)文化研究不应当提出某种普适的、从而封闭的文化事实的体系,而应该分析在文化过程中是有效的事实的无限制的、从而部分的集成。(9)文化科学必须把文化理解为一个过程。这个过程能够通过它的因素和要素概括其特征。表达形式的个体化和这些形式通过符号化的结构在个体之间的均一、个体化的“侧面的”超越和文化普遍性在表达交换中的兴起都属于这些因素和要素(注:O.Schwemmer,Science and Culture:On the Logic of the Theory of Culture.D.Anapolitanos et.ed.,Philosophy and the Many Facts of Science,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1997,pp.223~231.)。这些命题可以启发研究者的思路,从而在跨学科的研究和多维度的透视中揭示文化的内隐奥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