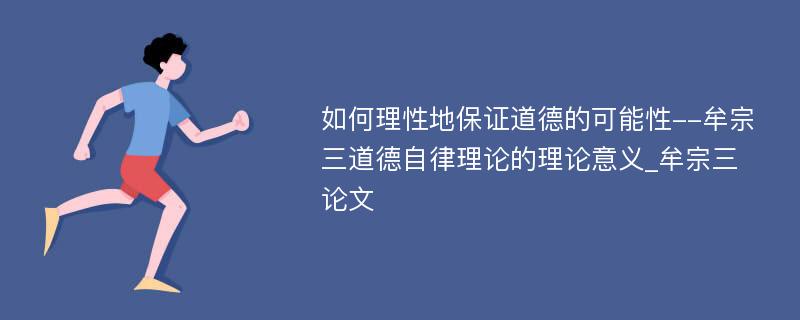
理性如何保证道德成为可能——牟宗三道德自律学说的理论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道德论文,学说论文,理性论文,意义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笔者认为牟宗三儒学思想标志之一的道德自律学说,在理论建构方面存在着很大的问题,而这些问题限于牟宗三感性、理性的两分思维方式,又很难解决[1]。但是,这并不是要完全否认牟宗三的道德自律学说,与此相反,我认为牟宗三这一思想隐含的理论意义是非常深刻的,它向人们提出了这样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理性如何才能保证道德成为可能?以下就这个问题谈一点个人理解。
一
牟宗三道德自律学说是其“三系论”的一个理论标准。依据这一标准,牟宗三将孟子、象山定为正宗,将伊川、朱子定为旁出。牟宗三为朱子之学定性,是有严密逻辑根据的:定其为旁出是因为朱子之学属于道德他律,之所以为道德他律是因为朱子之学只能顺取,之所以只能顺取是因为理不能活动。在这个过程中,本体能不能活动,有没有活动义,即所谓“即存有即活动”还是“只存有不活动”,为牟宗三判定朱子为旁出的核心理由,最为重要。正如其所说,这对概念“为吾书诠表此期学术之中心观念”[2]。
按照一般的理解,人既有理性,又有感性,理性代表人的价值,感性不代表人的价值,人具有了理性也就具有了成就道德的可能,只要时时处处按照理性的要求行事,就可以使道德成为可能了。不过,人们这样思考的时候,往往没有进一步考虑这样一个重要问题:理性本身是否具有活动能力呢?也就是说,作为道德根据的理性本身是否具有一种力量,能够直接决定道德呢?如果理性有这种能力,能够直接决定道德,那么这种道德就是由理性本身决定的,是对理性的服从,这就是自律;反之,如果理性没有这种能力,不能直接决定道德,那么这种道德就不是由理性本身决定的,不是对理性的服从,这就是他律。牟宗三提出问题的重要意义正在这里。
牟宗三认为,“义理、道理所意指的天理不只是静态的道德法则,亦不只是属于‘本体论的存有’之静态的实理,亦不只是那‘平铺放着’之静态的百理之多相,乃实是本体宇宙论的、即存有即活动的实理(实体),粲然明著之百理之一起皆统摄于寂感真几而为诚体之神之所显发,是这样的一多不二,存有活动不二,心理不二,神理不二的实体,此即综名之曰天理。”[3]
牟宗三常常将义理、道理上升到上天的高度,直接称其为天理。这些说法用词虽有不同,但无本质的区别,都是指一种本体宇宙论的存有。这个存有不是静态的道德法则,也不是平铺放着的理之多相,而是心理不二、神理不二、存有活动不二的实理,故总名曰天理。这里牟宗三明确反对两种倾向,一是将天理视为静态的道德活动,二是将天理视为一种共相(即所谓“理之多相”)。这两种倾向之所以不对,一个共同点,就是没有活动义。既然没有活动义,天理如何能够创生万物,创造道德呢?所以讲天理必须讲活动,不讲活动就无法讲天理。
恰恰在这个问题上,朱子没有做到。牟宗三指出:“(朱子)所不透之一点,说起来亦甚简单,即在:对于形而上的真体只理解为:‘存有’而不活动者。但在先秦旧义以及濂溪、横渠、明道之所体悟者,此形而上的实体(散开说,天命不已之体、易体、中体、太极、太虚、诚体、神体、心体、性体、仁体)乃是‘即存有即活动’者。(在朱子,诚体、神体、心体即不能言。)此是差别之所由成,亦是系统之所以分。”[4]
朱子对于形而上的实体理解为只存有而不活动,与先秦旧义以及濂溪、横渠、明道之所体悟者完全不同。既然理不能活动,那它如何能产生道德呢?结果,朱子只能从外面绕出去,大讲格物致知,以存在之然求其所以然,最终走上以知识决定道德的道路上去。
由此可知,牟宗三由理是否有活动义出发,最后判定朱子为旁出,思路是非常明确的。在他看来,天命流行之体是一创生的实体,这个创生的实体是理也是心,有其活动性;由其所发,就是善行,就是道德。既然道德是由理、由心直接决定的,而不是由外在的因素(如物质的因素,知识的因素)决定的,所以这种由理、由心直接产生的道德即为道德自律。但在朱子的学理中,理不是心,没有活动义,本身无法直接产生道德;要成就道德必须以格物穷理的方法,以存在之然求其所以然。这种方法对于成就道德当然也有所助益,但并不是直截了当地以理、以心决定道德,只是在道德何以可能的问题外面绕圈子,显然不如承认理本身即有活动义,本身即能决定道德的方法直接明了。这种以知道之是非决定道德的路子,按照牟宗三的理解,就是康德所说的道德他律,所以牟宗三将朱子判定为旁出。
牟宗三这些说法所包含的理论意义是极其深刻的,它迫使我们必须思考这样一个理论问题:理性本身究竟有没有活动性?或如何才能保证理性具有活动性?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如果理性有活动性,就可以保证道德成为可能;否则,将无法保证道德成为可能。
二
在西方哲学史上有人也曾提出过类似的问题,其代表人物就是休谟。休谟之时,西方哲学史上关于何者为道德根据有一场激烈的论战,有的认为是理性,有的则主张是情感。休谟参与了这场论战,认为“我们只须考究,我们是否能够单是根据理性来区别道德上的善恶,或者还是有其他一些原则的协助,才使我们能够作出这种区别”[5]。经过深入思考,休谟得出了一个重要的结论:善与恶的行为不是由理性决定的,理性不是道德的源泉。休谟之所以得出这种结论,最重要的理由就是:理性是完全无力的。
休谟以理性完全无力为理由,认定理性不是道德的源泉,这一观点值得我们注意。休谟有关的论述很多,为了说明问题,择其要者引述如下:
“道德准则刺激情感,产生或制止行为。理性自身在这一点上是完全无力的,因此道德规则并不是我们理性的结论。”[6]
“理性是完全没有主动力的,永远不能阻止或产生任何行为或感情。”[7]
“我们只要承认理性对于我们的情感或行为没有影响,那么我们如果妄称道德只是被理性的推断所发现的,那完全是白费的。一个主动的原则永远不能建立在一个不主动的原则上;而且如果理性本身不是主动的,它在它的一切形象和现象中,也都必然永远如此,不论它是从事研究自然的或道德的问题,不论它是在考虑外界物体的能力或是有理性存在者的行为。”[8]
“单是理性既然不足以产生任何行为,或是引起意志作用,所以我就推断说,这个官能(理性)同样也不能制止意志作用,或与任何情感或情绪争夺优先权。”[9]
休谟非常强调理性本身是否具有主动性的问题,认为德与恶的行为是受情感支配的,道德善恶判断只是性质不同的知觉,知觉中的感性印象是主动的、有力的,而理性则是被动的、无力的。理性的作用只在于发现义务,但在刺激情感、产生和制止行为方面,却是“完全没有主动力的”。一个主动的原则不能建立在一个不主动的原则上,所以理性不可能成为道德的源泉。
因为理性完全没有主动力,不能成为道德的源泉,所以休谟提出了“是”与“应该”的矛盾问题。在《人性论》第三卷附论中,休谟写道:他在考察道德理论时发现,事实判断和道德判断是两类完全不同的判断,事实判断的系词为“是”与“不是”,道德判断的系词为“应该”与“不应该”,可是人们在按照常规进行道德推理的时候,总是不知不觉改变判断的性质。“这个变化虽是不知不觉的,却是有极其重大的关系的。为这个应该或不应该既然表示一种新的关系或肯定,所以就必须加以论述和说明;同时对于这种似乎完全不可思议的事情,即这个新关系如何能由完全不同的另外一些关系推出来的,也应当举出理由加以说明。”[10]就是说,由于理性“完全没有主动力”,不能成为道德的根据,所以,“是”如何过渡到“应该”也就成了一个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
至此,我们不能不承认,虽然出发点和理论背景不完全相同,但休谟和牟宗三在这一点上,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休谟非常重视理性本身是否具有主动性的问题,认为一个主动的原则不能建立在一个不主动的原则上。理性的作用只在于发现义务,但在产生和制止行为方面,却是“完全没有主动力的”。牟宗三同样非常强调天理是否活动性的问题,认为天理本身就是心义,就有活动义,即存有即活动,如果取消了天理中的心义,就是取消了天理的活动性,天理就成了“只是理”,失去了活动义,成为死理,也就没有办法产生善的行为,决定具体的道德了。
当然,休谟和牟宗三的结论并不一致。休谟看到理性不具有活动力,不能成为道德的源泉,于是将道德的根据置于情感之上。牟宗三并没有放弃理性,依然认为理性是道德的根据,只不过认为不能活动的“只是理”无法决定道德,要使道德成为可能,必须通过别的办法使理活动起来,具有活动力。
三
那么,如何才能保证理能活动呢?牟宗三根据儒家心学的传统,强调要做到这一点,理中必须有心的位置,即必须有心义:
大抵濂溪、横渠、明道,皆是如此体会道体,故天地之心亦是直通於穆不已之天命诚体而为实体性的心也。就阳动言,实并无实体性的心义。而就一阳来复生于下之象征义,象征於穆不已之天命诚体,则天地之心乃是实说,即直通“於穆不已”之天命诚体而为一实体性之天心。天命诚体不只是理,亦是心,亦是神。天命诚体是实,则心、神亦是实,故曰心体、神体。[11]
牟宗三认为,“天命流行之体”是一创生实体,在这种实体中含有“心”义。“天命流行之体”作为一创生实体,实际起创生作用的不能是别的,只能是心,“天命流行之体”的真实意义,也只是说心是“创生之实体”。为了突出心的这个作用,保证天命流行之体是活物,牟宗三甚至还将这个心说成是“天心”、“天地之心”,意思是说,有心就有活动性,就有创生性,无心就无活动性,无创生性。
理有了心义,能够活动了,也就是有神义:
此天理不是脱落了神的“只是理”,故它是理、是道是诚、是心,亦是神。不然,何以能说寂感?何以能说生物不测,妙用无方?父子君臣乃至随事而见之种种理,所谓百理、众理或万理,俱浑完于寂体之中,而复随感而显于万事之为实事。如对父便显现为孝以成孝行,对子便显现为慈以成慈行,对君便显现为忠以成忠义,对臣便显现为恕以成敬恕。其他例然,皆有定理。此皆寂感真几、诚体之神之所显发,故无一少欠也。[12]
天理有活动义,也就是有神义,所以天理本身就是神体。反之,如果认为天理不能活动,就是失去了理的神义,失去了神义的“只是理”是不能活动的,即为死理。
有了心义和神义的理,就可以称为“寂感真几”了:
此虚灵虚明之体即由神以实之,或由心以实之。心即天心也。唯神与心始可说寂感。说“天命流行之体”,乃至说“创生之实体”,是形式地说,客观地说,说心说神寂感是实际地说,内容地说,亦是主观地说。此即明此“於穆不已”之实体不只是理,亦是心,亦是神,总之亦可曰“寂感真几”(Creative Reality=Creative Feeling)。此是此实体在本体宇宙论处为心理合一、是一之模型。若道德自觉地言之,便是孟子所说之本心或良心。心即理,此是那心理是一之模型之实践彰著。[13]
“寂感真几”是牟宗三非常喜欢用的一个说法,意思是说,作为天地万物总根源的天命流行之体即是心,又是神,是一个生动活泼的创生实体,既能感通天地,创生万物,又能滋生道德,产生善行,一句话,是万事万物的总根源。
这里最关键的一点就是看理是否有心义。如果理有心义,理就能够活动就是道德自律,就是正宗;如果理没有心义,理就不能活动,道德必然为其他条件所决定,就是道德他律,就是旁出。这样一来,牟宗三提出的理性是否具有活动性的意义越来越显现出来了:理性必须有其他因素作为保证,才能使其具有活动力、兴发力,才能直接决定道德;反之,如果只是单一的理性,没有其他因素的指导或辅助,那么它就不可能有活动力、兴发力,也无法决定道德。这个所谓的“其他因素”,在牟宗三看来,就是儒家心学传统的道德本心,所以他一再强调在理性之中必须有心的位置,必须有心义,强调心与理必须为一,不能析而为二。
如果认为这样讲还不足以使牟宗三这一思想的重要性显现出来的话,那么不妨再将牟宗三与麦金太尔结合起来加以比较。在西方,自从休谟提出伦理难题之后,不断有人试图解决这个难题,其中以麦金太尔借助亚里士多德的目的论体系的解决方案最值得重视。麦金太尔认为,亚里士多德伦理学是一个目的论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存在着一种‘偶然成为的人’,‘一旦认识到自身基本本性后可能成为的人’之间的重要对照”[14]。伦理学就是一门使人们懂得如何从前一种状态转化到后一种状态的科学。在这个重要对照中,有三个基本的要素:一是未受教化偶然形成的人性;二是认识到自身目的后可能形成的人性;三是作为从前者向后者转化的合理的伦理戒律。这三个要素中第二个要素特别重要,没有它就没有办法保证由第一个要素转化为第三个要素。但是启蒙运动和理性主义时代之后,人们放弃了亚里士多德的学说,特别是取消了亚里士多德理论中的第二个要素,使得三大要素不再完整:一方面是一组光秃秃的道德律令,另一方面是未受教化的人性,其间没有任何的“教导者”。这个变化是致命的,正是这个变化决定了启蒙运动和理性主义一开始就必须要陷入失败。休谟伦理难题的产生正是这种失败的结果。
既然休谟伦理难题是由于拒斥亚里士多德道德传统造成的,那么要解决这一难题,就必须重新回到亚里士多德的理论上来。麦金太尔认为,要解决休谟伦理难题必须借助亚里士多德的目的论体系。在亚里士多德传统中,目的论概念是非常重要的。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生的目的就是追求“幸福”。“幸福”一词希腊原文为ludamacma,包含“很好”(1u)、“精神”(damacma)等意义,另外也含有“繁荣昌盛”的意思。亚里士多德认为,幸福就是至善。这种学说的意义是非常深远的,它直接决定了人们不必询问为什么,则自然乐善行善。麦金太尔写道:“在亚里士多德传统中,说X是好的(这个X可以意指多种事件,其中包括人、动物、政策或事态),也就是说想要把具有X所具特性的事物作为自己目的人都会选择X类事物。”[15]显然,在当时的传统中,说某物是好的,已经包含了我要以某物为自己的目的。这个关系是非常直接的,其间几乎没有任何形式的过渡。亚里士多德以幸福作为人生目的,其理论的重要意义也正在这里。
有了目的论的基础,也就有了行善的动力,这种动力在逻辑关系上就表现为,道德判断的形式既是假言的,又是直言的。麦金太尔指出:“就其表达了什么行为对一个人的目的是恰当的这种判断来说,它们是假言的;‘如果且因为你的目的是某某,你就应该做某某行为’,或‘如果你不想使自己的最基本欲望受到阻挠,就应该做某某行为’。就其表述了神的命令的普遍法则的内容来说,它们又是直言的,‘你应该做某某行为,这是神的法则所命令的’。”[16]在这个关系当中,确定判断有一个假言的前提是非常重要的,只有保证了假言的这个前提,才能保证行为者的目的,也才能保证道德判断有内在的动力。因此,要解决“是”与“应该”的矛盾,必须恢复亚里士多德的目的论概念。麦金太尔尖锐指出:“我已指出,除非有一个目的(telos),一个借助构成整体生活的善(good),即把一个人的生活看成是一个统一体的善,而超越了实践的有限利益的目的,否则就将是这两种情形:某种破坏性的专横将侵犯道德生活;我们将不能够适当地说明某些德性的背景条件。这两种问题由于第三种问题而更为严重;至少有一种为传统所认识到的德性,它除了依据个人生活的整体。根本不能得到说明——这就是完善的或坚贞的德性,”[17]很明显,没有一个目的论就不可能有完善的道德生活,也就不可能真正解决休谟伦理难题。
通过上面的比较,我们很容易注意到,牟宗三和麦金太尔两人之间有着许多共同点。牟宗三指出,如果在理之中没有心义,即所谓“只是理”,这种理一定没有神义,没有活动性,不可能完成道德的自律。只有在理中加入心义,这种理才是活的,才能保证道德成为可能。麦金太尔借助亚里士多德的目的论概念,强调在理性之上,必须有一个目的论作为指导,人才能产生道德,跨越“是”与“应该”的鸿沟。牟宗三和麦金太尔解决问题的方案从具体处说虽然有很大的不同,但却强调作为道德的根据,理性不能是单一的,还必须有其他东西作为保证,否则,单一的理性不可能成为道德的根据。这种变化是巨大的,它告诉人们,在传统的道德哲学中一场彻底的革命已经不可避免了。
牟宗三通过阐发道德自律学说,明确提出理性是否有活动性的问题,将传统儒学家提升到理性如何保证道德成为可能的理论高度,使人明了单一的理性无法使道德成为可能这一深刻道理,在现代新儒家中,尚无第二人可与其比肩。我想,这就是牟宗三道德自律学说给我们带来的启发,也是其学说的理论意义之所在。[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