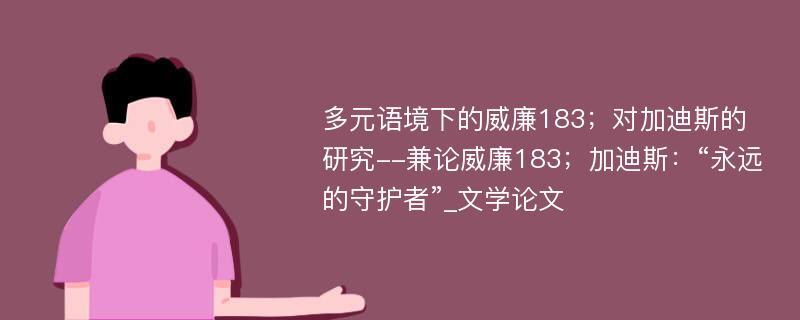
多元语境中的威廉#183;加迪斯研究——评《威廉#183;加迪斯:“永远的后卫”》,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威廉论文,迪斯论文,语境论文,后卫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威廉·加迪斯(William Gaddis,1922-1998)在战后美国小说家中占有重要地位。他一共发表了四部长篇小说——《承认》(The Recognitions,1955)、《小大亨》(JR,1975)、《木匠的哥特式古屋》(Carpenter's Gothic,1985)以及《诉讼游戏》(A Frolic of His Own,1994),其中《小大亨》和《诉讼游戏》分别获得1976年和1994年的美国国家图书奖。他的这四部小说成了了解战后美国社会各个层面的指南,对战后混乱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切实威胁表现出极大的关注。尽管加迪斯对战后美国文学的贡献巨大,但是正如评论家斯蒂芬·穆尔(Steyen Moore)所说:“在当代美国文学中,他是一位评价最高,但读者最少的小说家”(1),我们不得不承认由于他的作品阅读难度比较大,加上他独特的文艺观不容易被理解,加迪斯长期以来被读者和评论家所忽视。
随着美国后现代派小说逐渐走进研究者的视野,加迪斯最终凭借其对战后美国社会关注的主题思想和艺术创新获得了文学界的认可,赢得了美国后现代派小说先驱者和巨匠的称号。近年来美国本土出版了多部相关的研究专著,①这些专著都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深入探讨了加迪斯作品的主题思想、表现技巧和语言风格。我们可以看到自从20世纪末以来,加迪斯越来越受到评论界的重视,他的遗作《爱筵开裂》(Agapé Agape)2002年出版。2010年,为了纪念加迪斯的第一部小说《承认》出版50周年,美国学界又推出了由克里斯特尔·阿尔贝茨(Crystal Alberts)等主编的加迪斯研究论文集《威廉·加迪斯:“永远的后卫”》(William Gaddis,“The Last of Something”:Critical Essays)。论文集的题目引自加迪斯在一次访谈时所说的话,“我永远是后卫:队伍中的最后一个”(qtd.in Walker 18)。正如前言所指出的:“所有这些论文都从不同的语境研究了加迪斯的小说创作,包括哲学、文学、地理学、艺术、经济、政治和神学。这些论文试图用多重视角而不是单一视角审视加迪斯的作品”(7),②本论文集最突出的特色是把加迪斯的作品放置在小说赖于生成的多元文化语境下考察,把历史分析、文化研究同具体的叙事结构与话语分析相结合,综合评价加迪斯作为小说家、社会文化批评家和艺术评论家的地位。
克里斯特尔·阿尔贝茨在论文集中的首篇论文“威廉·加迪斯地图:本人、《承认》和他的时代”一文中,从考察小说中的地理维度出发,运用地理信息系统(Geography Information System)绘制加迪斯和小说的主要人物的旅游路线,结合小说创作的时代背景分析,探讨了西班牙之旅在《承认》中的重要意义(9-25)。文体学家和批评家威廉·加斯(William Gass)在论文“抱怨、痛骂、牢骚”中,称他多年的好友加迪斯为一位“具有创造力的抱怨者”(4),他从语言修辞学角度出发,以《木匠的哥特式古屋》为例,将小说人物各种形式的痛骂归入“抱怨、痛骂、牢骚”这三类,研究这三类修辞格所隐含和指涉的不同内容,并探究了这三种痛骂形式背后的创作动机(27-35)。
克里斯托夫·莱斯(Christopher Leise)运用美国数学家、控制论创始人诺伯特·维纳控制论中的第一和第二原理,也就是科学和信息交流理论的话语解读了加迪斯的作品,在论文“巴别塔的力量:艺术、熵与迷阵”中指出加迪斯的语言在信息传递方面是戏谑性的严肃和严肃性的戏谑。莱斯从另一个角度审视作品所具有的认识论的价值,认为加迪斯的小说犹如希腊的室内游戏“迷阵”,提出问题而却没有给答案,他以“含混、悖论、和迷阵”有效地改写了《圣经》中的巴别塔故事,让巴别塔发挥创作力,告诉读者不仅要与不确定性共生,而且要为含混的正面影响叫好,因为读者会被迫独立思考,而不是用陈词滥调和空洞的习语,因此也就避免陷入一种毫无思想的趋同一致(38-40)。克里斯托夫·奈特(Christopher Knight)从迷阵转自对否定神学的讨论。他在“变否定为肯定:加迪斯与否定神学”一文中,探讨加迪斯给读者暗示,让读者猜测的写作方法。他认为加迪斯在小说中敬重信仰与怀疑,他在作品中为自己所提出的问题,尤其是音乐、宗教或作者地位给予的含混的回答恰恰是一种变否定为肯定的否定神学。奈特不仅探讨了加迪斯个人的独特创作力,而且将加迪斯的创作与更广阔的新英格兰文学传统联系起来(从爱默生到艾略特),乃至欧洲的文学传统(从莎士比亚到柯勒律治再到伊夫林·沃)联系起来(66-68)。
伯格·凡温森比克(Birger Vanwesenbeeck)从宗教语境出发,分析了加迪斯小说中体现的基督教精神。凡温森比克遗作《爱筵开裂》也是延续加迪斯孜孜以求的对艺术与社团关系的探索。西方传统将同社团的认同等同于同圣体的认同,然而,加迪斯在小说中同时强调艺术家在创作过程中与众不同的个性对这种圣体模式进行再次定义,超越这种圣体认同模式(98-99)。在“《承认》与《木匠的哥特式古屋》:反保罗的小说”中,约翰·苏特(John Soutter)不仅将加迪斯的作品放在他既沿袭又质疑的基督教传统进行研究,而且结合哲学语境解读加迪斯的作品。他认为德国现代哲学家汉斯·费英格(Hans Vaihinger)的《仿佛哲学:人类理论、实践和宗教虚构系统》(The Philosophy of“As If”,1966)的影响贯穿加迪斯的创作始终。苏特运用费英格所发现的一种宗教创始人的原始的教义,(在这一情况下,就是指基督)被他的信徒尤其是保罗变成了一种教条,这种“仿佛”的假设虚构在加迪斯作品中变成了一种“真实”(115-116)。
加迪斯的《小大亨》被普遍认为是对上世纪下半叶自由资本主义的最愤怒的讽刺,在“这个小神童步入市场了:《小大亨》的教育意义”里,蒂姆·康利(Tim Conley)通过细读文本提出教育模式是小说的主题和形式。他认为《小大亨》可被当成一部关于教育的哲学专著来阅读。《小大亨》隐含加迪斯的人文教育思想和对“人性与教养”之间关系的探讨(126-128)。在论文“加迪斯之后:资料存储和小说”中,斯蒂芬·伯恩(Stephen J.Burn)思考了加迪斯作品中“百科知识”所起的作用,加迪斯的小说实际上是运用广博的文本知识探索被裂变的知识整体模式,以及永无止境的信息增殖给人类带来的负面影响,他的观点同后现代主义的哲学基质是相符合的。伯恩进一步以详细的文本比较分析指出了加迪斯对信息的运用影响了一批当代的美国小说家,包括唐·德里罗(Don DeLillo)、理查德·鲍尔斯(Richard Powers)和戴维·华莱士(David Wallace),因此加迪斯作为美国后现代派小说先驱者的地位得到进一步确立,这预示着加迪斯将继续受到美国学者的关注(164-165)。
读罢掩卷,不禁思考这部由阿尔贝茨等主编的加迪斯评论集何以能在众多已经出版的加迪斯研究专著中独辟蹊径,发出独树一格的声音?这些美国学者的研究方法能给我们国内的外国文学研究者什么启示呢?该论文集有何特色值得我们借鉴呢?笔者看来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在透视文本和文本之外相关的史学、哲学的基础上,坚守批评者的主体意识,而不是公式化地套用某种理论,才能产生真正的批评。本论文集其实就是在批评者占有新材料的基础上与前批评进行对话,指出前批评的误读,为加迪斯研究开启崭新的视窗。阿尔贝茨就是在细读了加迪斯遗留下来的书信文集、访谈录和他在真实生活中现场记录下来的凌乱笔记,在占用大量新材料的基础上指出了前批评的误读,对把《承认》归入“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提出了质疑。阿尔贝茨驳斥了约翰斯顿认为加迪斯文本中语言没有稳定性的观点,她认为加迪斯运用一致的语言来描述的地理场景是小说稳定的框架和结构的基础。她把《承认》中的地点与艾略特《四个四重奏》中“干燥的赛尔维吉斯”相比较,发现加迪斯在小说中也运用地理营造出一种“统一性、一种模式、一种平静的移动”(18)。阿尔贝茨强调加迪斯试图走出二战后无意义的平面,探求过去与现在之间的联系,小说中西班牙修道院堪称为文本结构的中心,起着唤醒记忆的作用,引领读者去识别那反复出现的人物、地点和象征(19-20)。
又如在“失败的批评:《承认》”中,约瑟夫·康韦(Joseph Conway)指出前批评家对《承认》的误读,因为太多的学者曲解加迪斯的文本去适应某种单一线性透视,或把作品当成某种时髦的批评的对象,把作品简化成对某种理论的阐释。如彼得·沃尔夫的弗洛伊德生平批评的方法忽略了小说中加迪斯对骗人的弗洛伊德主义的尖锐的讽刺,莫尔用的荣格批评忽略了文本潜在的叙述者对荒诞的点金术学说的讽刺,约翰斯顿的后现代主义反再现的理论忽略了作品中与艾略特的圣杯一样的现代主义象征性的表现,科姆在专著《不确定性的准则》把加迪斯的小说当成后现代文化形式的表现。康韦引用《承认》中画家瓦特说的话说明加迪斯作品是多元的,拒绝任何单一的透视,必须使用多重透视的方法才能更客观、更辩证地审视加迪斯作品丰富的时空(70-71)。
第二,在认真阅读文本的基础上,重视小说创作的社会历史,采用新的视角和新理论展开新的研究。本论文集不乏跨学科的研究以及将文学、史学、哲学融会贯通产生新意的研究。马修·都普莱(Mathieu Duplay)关注加迪斯作品中因为殖民冲动所引发的宗教的腐败。在“等待收割的熟地:《木匠的哥特式古屋》、非洲和生命政治控制”一文中,他将加迪斯在小说中表现的主题放置在古典哲学的背景下和西方人文主义历史的语境中进行考察,运用吉奥乔·阿甘本、本雅明、卡尔·施密特、福柯、阿伦特等当代思想家所阐发的关于政治伦理的理论思考加迪斯在小说中对于现代国家主权与个人生命的反思(146-152)。我们可以看到,以生命政治的哲学思想关照加迪斯的作品能够摆脱单纯将小说创作当成艺术创新的实践,挖掘作品深奥的寓意。
第三,运用比较分析,于细微处见精神拓展批评的思维空间。我们知道真正伟大的作家是在细节处下功夫,因此成熟的批评家也应该着眼细节处进行研究。约瑟夫·康韦就是从细节出发,比较海明威与加迪斯的文体风格,对加迪斯的文体风格提出了富有洞见的看法。他认为加迪斯的小说是以亘古永恒的神话为基石,而海明威的作品显示出一位前新闻记者如实再现世界、感知世界的方式(75)。然而加迪斯作品中的象征性价值并不是意味着每一个神秘的能指都有神秘的所指,当然也不能完全把加迪斯的风格完完全全跟海明威对立起来,只是在某个视角方面,他可能跟海明威完全不同,比如加迪斯的复杂文体是为了使时间神圣化(hallow time),而海明威的简洁文体只是为了掏空时间(hollow time)(75)。与海明威不同的是,加迪斯情愿产生词汇过度与浪费,以影射消费社会的大批量生产,加迪斯的语言呈现了一种在再现(representational)与反基础理论的倾向(anti-foundational)之间的一种张力(76)。
第四,在各种文学批评术语充斥文学评论的情况下,从伦理和道德的角度出发,可以挖掘作品深层次的人文精神和美学批判。蒂姆·康利发现把《小大亨》当成后现代史诗和信息系统论的小说时会忽略了小说隐含的人文教育思想。他发现让·雅克·卢梭的《爱弥儿》其实是小说重要的潜文本,也是加迪斯重要的创作思想来源(132-133)。《小大亨》中的一些情节与《爱弥儿》相似。《小大亨》(JR)其实就是让·雅克·卢梭名字的首写字母,康利的这种推断是从伦理和道德角度解读作品的新发现。在“一种自律的怀旧:加迪斯与现代艺术作品”中,丽莎·斯拉甘里安(Lisa Siraganian)注意到加迪斯对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纽约艺术运动的关注以及他在小说中所表现的美学旨趣被许多评论家所忽略(102-103)。《承认》中的瓦特宁愿通过摹仿古典画师的赝品式画作向世人表达真实的艺术。加迪斯以元小说的方式告诉读者:优秀的艺术家并不按照批评家的规则走,而是创造自己的规则。加迪斯的四部长篇小说可以说是十年磨一剑的精品。通过对文本所蕴含的道德和美学价值的批评,我们认识到作为重要作家的加迪斯被忽略的人文艺术精神。加迪斯的作品不只是对美国后现代生活和文化的批评,也是对他所熟悉的20世纪中期的艺术审美的批判,当我们认识到加迪斯作为“永远的后卫”所要固守的濒临破产的艺术精神时,更能深刻体会到加迪斯如何在小说中实现形式创新与意义深度的完美统一。
加迪斯作品的博大精深为评论家提供了无限解读的可能,多种不同的解读赋予其作品丰富的意义差异。然而,多种解读之间的差异并不是相互否定和排斥的,而是互相补充和参照,正如本书的前言所说:“读者要超越文本的表面,追随加迪斯那些百科全书似的典故,当找到新的批评立场时,情愿认为自己的先前批评失败了,但却是有创造性地失败”(6)。那些愿意为加迪斯庞大的、迷宫般的作品投入时间的读者和评论家定能够在这本论文集的基础上进一步形成和发展自己的见解,再次发现加迪斯作品的魅力,挖掘其中为人所忽略的宝藏。我们期待着加迪斯这位“永远的后卫”越来越受到更多学者和读者的重视和理解,他的影响将不断扩大。
注释:
①相关专著主要包括斯蒂芬·莫尔(Steven Moore)的《威廉·加迪斯》(William Gaddis,1989)、莫尔和约翰·库恩(Moore and John Kuehl)主编的《承认威廉·加迪斯》(In Recognitions of William Gaddis,1984)、约翰·约翰斯顿(John Johnston)的《重复的狂欢》(Carnival of Repetition,1990)、格里高利·康姆(Gregory
Comnes)的《威廉·加迪斯小说中的不确定性》(The Ethics of Indeterminacy in the Novels of William Gaddis,1994)、彼得·沃尔夫(Peter Wolfe)的《他自己的视野:威廉·加迪斯的思想和艺术》(A Vision of His Own:The Mind and the Art of William Gaddis,1997)以及克里斯托弗·奈特(Christopher Knight)的《暗示与猜想:威廉·加迪斯的渴望之书》(Hints and Guesses:William Gaddis’s Fiction of Longing,1997)等。
②See Crystal Alberts,“Preface”,William Gaddis,“The Last of Something”:Critical Essays.Eds.Crystal Al berts,Christopher Leise,and Birger Vanwesenbeeck(Jefferson,NC:McFarland & Co.,2010).本文相关引文均出自该论文集,以下只标出具体页码,不再一一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