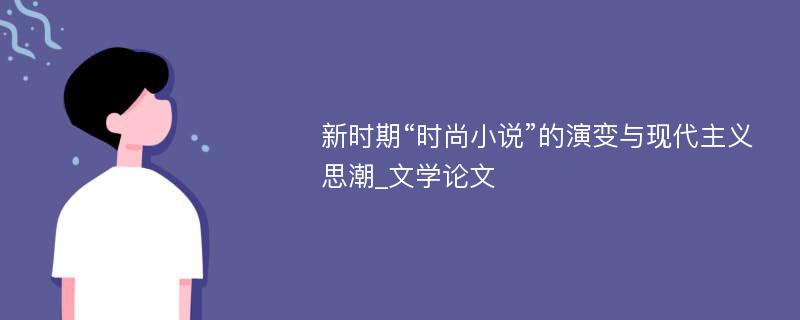
新时期“新潮小说”的流变与现代派思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潮论文,现代派论文,思潮论文,新时期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853(2003)01-112-07
新时期“新潮小说”的源头,在“文革”“地下文学”中。赵振开(北岛)写于1974年的中篇小说《波动》,已经透露出愤世嫉俗的虚无主义情绪和具有存在主义意味的荒诞感(例如作品主人公肖凌的叹息“咱们这代人的梦太苦了,也太久了,总是醒不了,即使醒了,你会发现准有另一场梦在等着你”,“哼,伟大的二十世纪,疯狂、混乱,毫无理性的世纪,没有信仰的世纪……”)。小说以人物内心独白、回忆的组接作为叙事 的框架,也突破了现实主义的叙事模式。虽然作者在创作之前是否接触过西方“意识流 ”小说尚有待披露,但作品本身已经具有了“意识流”小说的特质(依据表现人物心理 活动的需要展开叙事)是显而易见的事实。小说曾经以“手抄本”在社会上流传,到198 1年才在《长江丛刊》公开发表。值得注意的是,新时期另一部呼唤人道主义复归、感 悟政治运动的荒诞、流露出虚无主义气息的长篇小说《人啊,人》(戴厚英),也是以人 物的内心独白的组接作为小说的结构框架的。小说出版于1980年。戴厚英在《人啊,人 》的“后记”中明确申述了自己离开现实主义道路,学习“严肃的现代派艺术家”,“ 吸收了‘意识流’的某些表现方法,如写人物的感觉、幻想、联想和梦境”,“调动一 切艺术手段表现作家主观世界”,“让一切思想、逻辑都自由地活动”,为催生“一个 中国的、现代的文学新流派”的努力和追求。[1](P355-358)小说既展示了一个饱经苦 难、真诚依然、为人道主义的回归大声疾呼的思想者何荆夫的崇高精神世界,也真切刻 画了饱受政治运动捉弄、看破了历史的荒诞的知识分子许恒忠、李宜宁、游若水的复杂 内心世界。许恒忠关于“全部历史可以用四个字概括:颠来倒去。……我算看透了”的 叹息,关于“政治斗争中的正确和错误,在于机会,而不在于一个人是否真诚”的醒悟 ,李宜宁关于“历史也可以像废旧物资一样,捆捆扎扎,掼到一个角落里就算啦!像打 毛线,打坏了,拆了从头打,换一个针法,就完全是一件新衣服,谁也看不出它原来的 样子”的感慨,都揭示了“文革”的荒诞给当代人留下的深刻刺激。《人啊,人》中理 想主义激情与虚无主义寒雾的交织,对政治、历史、人性的深刻反思,都使得它不同于 地道的西方“意识流”作品。
而王蒙,则是新时期“意识流”小说的代表作家。从1979年发表中篇小说《布礼》、短篇小说《夜的眼》开始,他连续发表了一大批“意识流”风格的中、短篇小说——《春之声》、《海之梦》、《风筝飘带》、《蝴蝶》、《杂色》、《深的湖》、《相见时难》等等。在这些作品中,除了《夜的眼》是描写一个人对都市的陌生感以外,其余的都集中表达了作家对革命理想与历史悲剧、政治运动与人的命运的深刻反思。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他被公认为新时期中国“意识流”小说的代表作家,他自己却是有意识在借 鉴“意识流”手法的同时努力超越着西方“意识流”小说的天地的。他在三个方面作出了可贵的努力:第一,清醒的反对非理性主义立场。他坦言:“我反对非理性主义,我肯定并深深体会到世界观对于创作的指导作用。”[2](P203)从一个当年的“少年布尔什维克”到后来的共青团干部、中共中央委员、文化部长,俄苏文学的理想主义精神、浪漫主义气质,参加中国革命的激动体验、理性思考,都不可避免地在他的世界观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以至于在饱经政治磨难以后,他仍然认真地思考着革命和理想的价值,一面反省“很可能我们的爱戴当中包含着痴呆,我们的忠诚里边也还有盲目,我们的信任过于天真,我们的追求不切实际,我们的热情里带有虚妄,我们的崇敬里埋下了 被愚弄的种子”(《布礼》),一面也真诚讴歌了“革命的必然,革命的神圣和伟大”。 [3](P909)一直到晚年,他的多卷本长篇小说“季节系列”仍然体现出鲜明的“革命情 结”。因此,不同于西方“意识流”小说的非理性色彩,王蒙的“意识流”小说具有很 强的“反思性”。第二,深厚的中国古典文化底蕴。作家自道:“小时候我就爱读古典 诗词。”他喜欢李白、苏东坡的洒脱与豪迈,也喜欢李商隐的神秘、白居易的自然,因 此,他“重视小说中的诗情词意”,“往往是以写诗的心情来写小说的”。[2](P222-2 24)他也因此“不能接受和照搬(西方“意识流”小说)那种病态的、变态的、神秘的或 者是孤独的心理状态”。他的“意识流”不是一种叫人们逃避现实走向内心的意识流, 而是一种叫人们既面向客观世界也面向主观世界,既爱生活也爱人的心灵的健康而又充 实的自我感觉。在他看来,李商隐的无题诗、鲁迅《野草》中的《秋夜》、《好的故事 》、《雪》都可以说是优美的“意识流”作品[4](P71-74)这样,他就在“意识流”小 说的文体中融入了古典诗词的温柔敦厚、明丽流畅,而去除了西方“意识流”小说中常 见的尖刻、晦涩、阴暗因子。他的“意识流”小说因此而被称为“东方化意识流”。[5 ]第三,不拘一格、杂糅多种文学、艺术手法的尝试。王蒙曾经说过:为了创作,他“ 不准备视任何一种手法为禁区”——“如实的白描,浮雕式的刻画,寓意深远的比兴和 象征,主观感受与夸张变形,幽默讽刺滑稽,杂文式的嬉笑怒骂,……民间故事(例如 维吾尔民间故事)里大故事套小故事的方法……各式各样的心理描写(我认为,意识流只 是心理描写的手段之一)……散文作品中的诗意与音韵节奏,相声式的垫包袱与抖包袱 ……”,等等。[2](P202-203)写实的白描、诗歌的比兴、杂文的泼辣、散文的抒情、 民间故事的技巧、相声的俏皮,一切都在他自由心态的驱遣下,一切都包容在他汪洋恣 肆的作品中。他喜欢俄苏的普希金和艾特玛托夫(他的系列小说《在伊犁》就带有艾特 玛托夫式的异域风情,长篇小说《恋爱的季节》也富于抒情的格调),也倾心于美国作 家海明威和约翰·契佛(他曾经写过《我为什么喜爱契佛》一文,自道“是因为他的迷 人的叙述方式与叙述语言”——“相当幽默”,“风度优雅”,“娓娓道来,亲切随意 ”,“仅止于讲述故事而已,他绝不把分析故事、解答故事、表演故事、总结故事的沉 重负担置于自己的肩上”),[4](P438-439)他还表达过对德国作家伯尔的崇敬,因为“ 他恰恰主张要对社会起作用”。[6](P479)而且,伯尔也是擅长将写实的风格与内心独 白、象征、怪诞风格熔于一炉的作家。在王蒙的“寓言体”小说《风息浪止》、《冬天 的话题》、《活动变人形》、《坚硬的稀粥》中,都可以使人感受到写实笔触与漫画意 味、批判锋芒与调侃口吻的水乳交融。这样,他也就将他受到的世界文学影响融化为一 体了。王蒙的小说风格多变,与兼容并包各种文学手法、各国文学影响的博大胸怀密不 可分。
谈到新时期的“新潮小说”成就,1985年被普遍认为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年。在那一年里,一批年轻的作家发表了一批产生了深广影响的现代派作品,标志着文学多元化格局的进一步扩大: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明显受到美国作家约瑟夫·赫勒的“黑色幽默”名著《第二十二条军规》的影响;徐星的《无主题变奏》颇得法国作家加缪的《局外人》的神韵,表达了对存在主义人生观的认同;韩少功的《爸爸爸》深受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的影响,是“魔幻现实主义”的中国版;马原的《冈底斯的诱惑》得益于美国作家霍桑的神秘主义的影响,显示了对宿命的深刻体悟;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郑万隆的《异乡异闻》系列都显示了学习美国作家福克纳“追求事物背后某种‘超感觉’的东西”[7]的成绩……正是在这一批作品产生的“轰动 效应”中,西方现代派小说的许多流派都在新时期文坛上开花、结果了。虽然其中有的 作品模仿的痕迹太显著,以至于到了1987年还产生了“伪现代派”的争论,但许多作家 在学习、借鉴西方现代派小说技巧的同时念念不忘寻找中、西文学与文化的契合点,并 在自己的创作中予以成功地表现的努力,仍然为“中国的现代派”文学的发展积累了可 贵的经验。
同样是深受福克纳和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启迪,韩少功笔下的“湘西故事”就与莫言营造的“高密东北乡世界”、郑万隆创造的“黑龙江故事”呈现出不同的风采:“湘西故事”融入了作家对“楚辞中那种神秘、奇丽、狂放、孤愤的境界”的追求。[8]作家 有时将“楚文化的主观浪漫主义精神”看作“整个人类超时间超空间的一种生存状态, 一种生存精神”,[9]有时则更强调巫楚文化的民间性,指认其“非正统非规范”,“ 至今也没有典籍化和学者化,主要蓄藏于民间”的特质,并认为“一切原始或半原始的 文化都是值得作家和艺术家注意的”。这样,他就将楚文化看作了人类精神文化的一个 重要组成部分,从一个独特的角度超越了中、西文化对峙的流行见解。值得注意的是, 《爸爸爸》、《女女女》中奇丽的色彩并不鲜明,神秘、孤愤的情绪则相当突出。“《 爸爸爸》的着眼点是社会历史,是透视巫楚文化背景下一个种族的衰落,理性和非理性 都成了荒诞,新党和旧党都无力救世。《女女女》的着眼点则是个人行为,是善与恶互 为表里,是禁锢与自由的双变质,对人类生存的威胁。”[10]于是,作者便对传统文化 中的荒诞因子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在这方面,他又实现了对“五四”批判精神的认可。 韩少功特别将“文化精神”和“社会机制”区别开来。在《文学的“根”》一文中,他 格外强调了“尤其是在文学艺术方面,在民族的深厚精神和文化物质方面,我们有民族 的自我”。而在另一次访谈中,他也表示了对老庄、禅宗智慧的认同。在他看来,“中 国有很好的思想,然而,它的机制上如果有毛病就会变成很坏的东西”。[9]这种对中 国传统文化的复杂性认识有助于我们理解作者在“寻根”思潮中的矛盾心态:一方面呼 唤绚丽楚魂的回归,另一方面对楚文化的衰亡谱写了无情的挽歌。也正是由于这一矛盾 心态,使作者成功地将楚文化的神秘、狂放、孤愤遗风与西方现代派的变形、夸张、象 征手法融合在了一起。而莫言虽然从加西亚·马尔克斯和福克纳那里接受了悲观主义的 世界观(诸如“世界是一个轮回,在广阔无垠的宇宙中,人的位置十分渺小”,等等[11 ]),并写下了《枯河》、《爆炸》、《金发婴儿》等风格悲凉的小说,但《透明的红萝 卜》却放射出朦胧而温馨的光芒。在谈及这部作品的追求时,莫言提到了中国古典诗歌 的朦胧美给他的影响:“生活中原本就有的模糊、含蓄,决定了文艺作品的朦胧美。我 觉得朦胧美在我们中国是有传统的,像李商隐的诗,这种朦胧美是不是中国的蓬勃潇洒 的哲学在文艺作品中的表现呢?文艺作品能写得像水中月镜中花一样,是一个很高的美 学境界。”他还谈到了对老庄传统的认同:“我看鲁迅先生的《铸剑》时,就觉得那里 边有老庄的那种潇洒旷达,空珑飘逸的灵气。”[12]由此可见,他是努力将西方现代派 的悲凉感与中国古典诗歌中的朦胧美熔于一炉的。此外,莫言还曾经谈到《秋千架》的 创作“得力于川端康成”。并坦言自己“读外国的作品太杂了。我喜欢的作家是因着年 代和我个人心绪的变化而异的,开始我喜欢苏联的,后来是拉美是马尔克斯,再后来是 英国的劳伦斯,再后来又喜欢起法国的小说来,我看了他们喜欢了他们,又否定他们否 定了喜欢过他们的我自己。你看我钦佩福克纳又为他把自己固定在一个地域一个语言系 统中而遗憾”。[13]他的作品因此而给人以天马行空的感觉。而郑万隆也是一面接受着 外国文学的启迪(他告诉我们:《异乡异闻》受到了博尔赫斯和马尔克斯的影响,《地 穴》受到过胡安·鲁尔弗《佩德罗·巴拉莫》的启发),一面思考着如何从西方文学的 影响下走出来的问题,认为“当代艺术一个极为重要的特征就是多种文化融汇”。[14] 他清醒地认识到“我的根是东方。东方有东方的文化”。“极浓的山林色彩、粗犷旋律 和寒冷的感觉”,充满了“神话、传说、梦幻”的人生——这一切,使《异乡异闻》神 秘又苍凉,朦胧也豪放,既具有浓郁的地域文化异彩,又闪烁着对于“人怎样创造自己 ”和“生与死、人性与非人性、欲望与机会、爱与性、痛苦和期待以及一种来自自然的 神秘力量”的现代之思。[7]
由此可见,韩少功、莫言、郑万隆不约而同地都在对乡土民间文化资源的开掘中发现了具有人类感的文学主题,都在将本土的神话传说、民间故事、审美传统与西方的文化观念、叙事技巧、创新意识融合的尝试中作出了积极的探索。他们都深受福克纳(他是美国“南方文学”的经典作家)和加西亚·马尔克斯(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大师)的影响。他们从地域文化中汲取创作灵感的做法既得益于福克纳和加西亚·马尔克斯创作的启迪,也与中国的“地域文学”传统(从古代的《楚辞》、“边塞诗”到现代的“京 派”、“海派”、当代的“山药蛋派”、“荷花淀派”,等等)一脉相承。他们是“寻 根文学”的代表人物,又是“新潮小说”的重要作家。
马原也是“新潮小说”的重要作家。他的“西藏故事”也具有浓郁的地域文化色彩。但他在新时期小说中的独特意义在于:他打破了“虚构”与“真实”的传统界限,将自己的名字和经历与“信不信由你”的叙事口吻引入了小说创作中,从而造成了似真似幻的奇特效果。这样,他就深刻揭示了“神秘不是一种氛围,不是可以由人制造或渲染的某样东西。神秘是抽象的也是结结实实的存在,是人类理念之外的实体”这样的哲理,[15]表达了对“生活不是逻辑的”的理解。[16]他的“西藏故事”(如《拉萨河女神》、《冈底斯的诱惑》、《西海的无帆船》、《虚构》、《拉萨生活的三种时间》、《游神》等等)和“知青小说”(如《海边也是一个世界》、《错误》、《上下都很平坦》等)都因此而赋有了“哲理小说”的意味。在谈到自己所受到的外国文学的影响时,他开出了一串二十世纪作家的名字:“加缪、纪德、圣埃克絮佩里、迪伦马特、贝克特、赫 勒、吉卜林、海明威、卡夫卡、福克纳”,还有霍桑、拉格洛孚。其中,既有以浓郁的 异域文化风貌取胜的作家(如纪德、吉卜林、海明威、福克纳),也有以哲理风格见长的 作家(如加缪、贝克特、赫勒、卡夫卡、霍桑),还有以情节的扣人心弦著称的作家(如 迪伦马特)。[17]此外,他还深受博尔赫斯(这位作家十分擅长在扣人心弦的故事中揭示 神秘主义的哲理,也很喜欢在“真实”与“虚构”之间自由出入)的影响。他在《游神 》、《黑道》的开篇都以博尔赫斯作品中的句子作题记,就是证明。这样,他就在兼收 并蓄外国文学的影响,熔神秘性、哲理性、情节性于一炉方面作出了可贵的贡献。不过 ,马原在提及外国文学的影响时常常不忘强调民族文化传统的深刻影响。他不止一次谈 到庄子的影响:“《庄子》也是我最爱读的故事。”[15]“我骨子里是汉人,尽管我读 了几千本洋人写的书,我的观念还是汉人的。没法子的事。信庄子和爱因斯坦先生共有 的那个相对论认识论”。[15]这样,他就以对庄子哲学的认同使自己神秘主义世界观和 文学观平添了一层东方文化的色彩。除此而外,他也坦言了对本土民间神秘文化的倾心 :“我比较迷信。信骨血,信宿命,信神信鬼信上帝,该信的别人信的我都信。泛神— —一个简单而有概括力的概括。”[17]作者的这一文化背景显示了民间萨满教的深刻影 响,披露了作家神秘主义世界观的思想之源。作者还曾自道“自幼喜欢民间故事”。[1 8]综而观之,庄子的哲学、民间的泛神论信仰和民间故事,成了马原选择外国文学、接 受外国作家影响的文化心理基础,也是作家融汇中、西文化观念和文学风格的思维定势。
以韩少功、莫言、郑万隆和马原为代表的“新潮小说”在1985年产生的巨大影响不仅出色地延展了由“朦胧诗”、王蒙的“意识流”小说开辟的新时期“中国的现代派文学”的道路,而且极大地丰富了融合中、西文化与文学的经验。他们的成功表明:无论是古代的经典哲学、文学,还是古今相续的民间信仰、故事,都可以通过作家创造性的解释与写作,与西方现代派哲学与文学的文化观念、思维方式、创作手法融合在一起。
此后,以苏童、余华、格非、陈染、林白、韩东、朱文、毕飞宇为代表的更年轻的一代作家的紧紧跟上,进一步推动了“中国的现代派文学”的发展。其中,苏童的“枫杨树故乡”系列小说(如《1934年的逃亡》、《罂粟之家》、《飞越我的枫杨树故乡》等)、毕飞宇的“家族故事”(如《叙事》、《楚水》)、林白的“沙街故事”(如《青苔》、《同心爱者不能分手》、《沙街的花与影》等)都足以使人联想起韩少功、莫言、郑万隆和马原营造的地域文化世界,想起福克纳创造的“约克纳帕塌法县”和马尔克斯笔 下的“马孔多镇”;而余华、陈染、韩东对卡夫卡的一致推崇也足以解释为什么他们的 作品中充满了解剖人性的深刻力量和表达“纯粹个人化”感受的奇特风格。余华心中的 卡夫卡是一个“内心异常脆弱过敏的作家”,“他的思想和时代格格不入”,“他的思 维异常锋利,可以轻而易举地直达人类的痛处”。[19]而陈染则“喜欢卡夫卡的生活方 式和态度”,“感到在个性及思想上的极为贴近”。[20]在韩东喜欢的外国作家名单上 ,卡夫卡也排在首位。[21]如果说,苏童、林白、毕飞宇的故乡记忆在消解了“故乡” 一词的传统诗意的同时也丰富了我们对历史的混浊性和文化、人性的脆弱性的认识(在 这一点上,他们更多继承的,是韩少功的《爸爸爸》、莫言的《红蝗》、郑万隆的《黄 烟》等作品中一脉贯通的文化批判与人性批判精神,而不是莫言的《红高粱》、郑万隆的《老棒子酒馆》、《我的光》等作品中显示的弘扬民族魂的精神),是将“现代派手 法与‘寻根’情结、地域文化氛围”融化于一体的成功尝试,那么,余华、陈染、韩东 在学习卡夫卡的同时也兼收并蓄其他外国作家的影响,也就为超越卡夫卡打下了良好的 基础。余华在卡夫卡之外,还喜欢川端康成、普鲁斯特、曼斯菲尔德、福克纳这样一些 “多愁善感的作家”,[19]使他既能写出《往事如烟》、《河边的错误》、《一九八六 年》那样无情解剖人性、深刻揭示人生的荒诞的力作,又能写出《活着》、《细雨与呼 喊》、《许三观卖血记》那样具有悲悯情怀、感伤意蕴的佳篇。陈染将卡夫卡的影响与 沃尔夫、尤瑟纳尔那样“把男性与女性的优秀品质这两股力量融合起来”的女权主义作 家的影响和博尔赫斯、爱伦坡、乔伊斯那样具有神秘主义倾向和“病态的美”的作家的 影响熔于一炉,[20]才成为当代女性写作的代表作家。她的《与往事干杯》、《凡墙都 是门》、《私人生活》都将女性隐秘心理的展示与对人生哲理的感悟、对人的命运的思 考揉在一起,并因此而为人瞩目。韩东除了卡夫卡以外,还喜欢辛格、纳博科夫、博尔 赫斯和“鲁尔弗、索尔仁尼琴、海明威、卡尔维诺、杜拉的一些篇目和章节”,[21]这 份驳杂的名单能够揭示韩东创作的驳杂风格——他既在《反标》、《西天上》、《农具 厂回忆》等作品中记录了自己的“文革”记忆,又在《助教的夜晚》、《单杠·香蕉· 电视机》、《西安故事》、《同窗共读》那样的校园生活故事中揭示了当代青年知识分 子的委琐与无奈,还在《房间与风景》、《障碍》那样别具一格的“性文学”中探讨了 性心理与命运的命题。他善于在平淡的生活琐事中开掘出玄妙的人心之谜。
在建设中国现代派文学的进程中,贾平凹的创作具有独特的意义。在谈及自己所受到的外国文学影响时,他提到过:“泰戈尔,川端康成,海明威”,[22](P565)还说过“我对美国文学较感兴趣……像福克纳、海明威这种老作家”。[23]但他常常谈得很简略、笼统。他作品中常常流露的唯美主义倾向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川端康成,而他对“商州世界”的经营也与福克纳的小说世界十分相似。他一面承认“西方现代派的东西给我影响很大”,一面“主张在作品的境界、内涵上一定要借鉴西方现代意识,而形式上又坚持民族的”。[24]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爱使他那些具有魔幻风格的小说创作更加具有传统“志怪”的意味:从《瘪家沟》、《龙卷风》、《太白山记》那样的当代“志怪”到《白朗》、《晚雨》、《怀念狼》那样的当代“传奇”,还有《烟》那样的“佛理寓言”,都表现了作家致力于描绘中国民间神秘文化,表现神秘文化“恍兮惚兮”的奇异境界的成果。他的上述作品与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文学有异曲同工之妙,也是他有意将中国古典文学遗产发扬光大的结晶。他不断追求着文学的“中国味、民族气派”。在他看来,这种民族气派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中国的古典哲学对古典文学的影响。例如 他曾经谈到“自觉地认识东方的重整体感应”的思维方式,[25](P146)并在自己的创作 中追求“更多混茫,更多蕴藉”的艺术境界。他的《浮躁》就体现了他对道家哲学的认 同;他的《烟》则充分展现了他对佛家“古赖耶识”哲学的悠然心会。而他“有意识地 ”借写作“修我的性和练我的笔”[26]的态度也是富于古典的文人气质的。二是对中国 古典文学传统的继承与发扬。一方面,他看重古典文学的“空灵”,认为“中国几千年 的文学,陶渊明、司马迁、韩愈、白居易、苏轼、柳宗元、曹雪芹、蒲松龄,尽管他们 的风格有异,但反映的自然、社会、人生、心灵之空与灵,这是一脉相承的。空与灵, 这是中国文学的一项大财富。……在以中国的传统的美的表现方法来真实地表现当今中 国人的生活、情绪的过程中,我总感觉到作品里可以不可以有一种‘旨远’的味道?”[ 27]他的“商州世界”通过描绘商州人的生存状态、历史沿革、风土人情,表达了作家 对“中国农村的历史发展,社会变革,生活变化”的认识与思考,达到了“以一个角度 来反映这个大千世界和人对这个大千世界的心声”[28](P3)的目的。另一方面,他“崇 拜大汉之风而鄙视清末景泰蓝一类的玩意儿”,[27]因此,他喜欢“放达、旷达”的文 风,从早期创作的清新渐渐走向古朴、苍劲、神奇。[23]三是对传统艺术的综合修养。 他说过:“我喜欢国画……工笔而写意,含蓄而夸张……在有限之中唤起了无限的思想 和情趣。”他还说:“我喜欢戏曲,融语言、诗词、音乐、舞蹈、绘画、雕塑、工艺、 建筑、武术、杂技为一体,表演的不是生活的真实幻觉,而通过表演,又让人感到了是 生活的幻觉。”[29]四是对神秘文化的浸染。他说过:在故乡,在西安,“神秘现象和 怪人特别多,这也是一种文化”,“我自己也爱这些,佛、道、禅、气功、周易、算卦 、相面,我也有一套呢”[8]。这一切,在他的创作中交融在一起,成为当代文坛的一 个奇观。贾平凹在新时期“新笔记小说”(如《商州三录》)、“新志怪小说”(如《太 白山记》)创作中的积极探索使他成为“中国的魔幻小说”的代表作家。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中国的现代派文学是在兼收并蓄西方现代派文学的驳杂影响中发展起来的,这种兼收并蓄本身便是对于模仿的超越——它使得中国作家的现代派创作更具有不拘一格的杂糅品格和多变的色彩。同时,中国的作家们在兼收并蓄西方现代派新观念、新技巧、新流派的过程中常常自觉地将自己的中国古典哲学、古典诗词、古典小说以及地域文化和神秘文化修养融入了创作的实践中,从而使他们的现代派创作赋有了浓郁的传统文化底蕴。应该说,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派文学”不仅是中、西文化交融的结晶,也是世界现代派文学格局中具有独特风采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在许多中国作家念念不忘的“中国味、民族气派”上,我们不难感受到中国作家根深蒂固的民族自尊心。从革命年代里的中国作家对“民族化、大众化”风格的追求到新时期的中国现代派作家对“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派文学”的追求,我们可以看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蜕变中那条深深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作家的建设民族新文化的思想线索。另一方面,革命年代里那些“民族化、大众化”的成功之作(如“山药蛋派”、“荷花淀派”那样的小说流派和《王贵与李香香》、《天山牧歌》那样的民歌体佳作)和新时期“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派文学”的成功之作(从“东方意识流”到“新志怪小说”),不是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显示了“民族文学”更新的丰富形态吗?
“万端变化中,中国还是中国,尤其是在文学艺术方面,在民族的深厚精神和文化物质方面,我们有民族的自我。我们的责任是释放现代观念的热能,来重铸和镀亮这种自我”。诚哉斯言。
收稿日期:2002-11-19
标签:文学论文; 福克纳论文; 意识流论文; 小说论文; 莫言作品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外国文化论文; 艺术论文; 文化论文; 西方世界论文; 读书论文; 韩少功论文; 作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