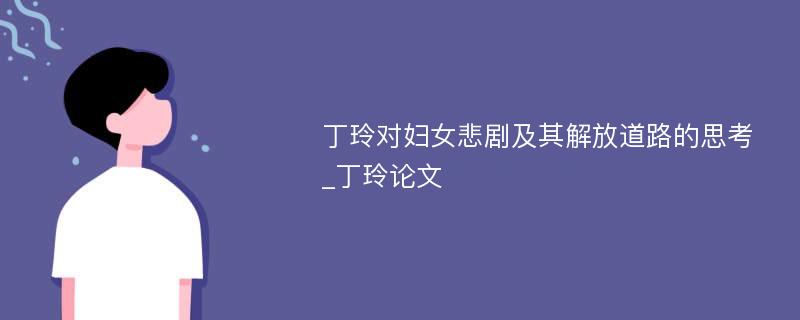
丁玲关于女性悲剧及其解放之路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之路论文,悲剧论文,女性论文,丁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5587(2009)04-0078-06
“丁玲一生都以女性的姿态在自己的作品中探索中国女性的生存、地位、价值等问题”[1],她的人生记录了她寻求的轨迹,她的作品是她解放思想的生动印证。作为一个灵动敏感、心智超卓的女性,她从自己的生活和感受中体味女性的丰富复杂,同时以敏锐的性别意识感悟自己所生存的这个男女世界,观察和思考着她所体味和感悟的女性生活与命运。她描摹千姿百态的女性生存本相,探求思考女性命运的根源,她笔下的女性从梦珂、莎菲、阿毛、阿英、贞贞、陆萍到杜晚香,个个都热爱生命,个个都呈现出女性生命的独特色彩,然而她们都没有自己理想的人生,她们或生不逢时,被时代与社会的大潮所裹挟和抛弃;或被传统的思想观念逼压于男权社会的狭窄空间;或者她们被看不见的体制和制度绳索所束缚;或者局限于自身的软弱与识见的逼仄。多样的女性悲剧引起了她对女性的命运的思考和对女性解放道路的寻求。笔者在此试作分析。
一
其一,社会与时代的悲剧。
丁玲早期的作品主要描绘了被时代与社会大潮所裹挟和抛弃的年轻女性:“莎菲女士是心灵上负着时代苦闷的创伤的青年女性的叛逆的绝叫者,是‘五四’以后解放的青年女子在性爱矛盾心理上的代表者”[2],这绝叫和苦闷是对生不逢时、走投无路的人生处境和百无聊赖、无所事事的生活状态的绝望和控诉,于是她逃离,到无人的地方去浪费生命的余剩。而梦珂在社会遭遇了求学悲剧、爱情悲剧、求职悲剧后,陷入了纯肉感的社会沉沦为靠出卖肉体为生的色相明星。这个社会从内与外即爱情婚姻和职业上斩断了她体面的生存之路。而阿毛由于生活环境的变化,自我意识觉醒萌发,可是她周围的生存环境跟不上她思想意识的变化,她与周围的人事格格不入,她选择了死亡以实现对时代社会的逃避。《自杀日记》里的伊萨,觉得生活“毫无乐处,永无乐处”,连死的价值也找不到,因而焦躁、厌烦、什么事也不能做。《日》中的伊赛所看到的是“谁都是那么一天一天的毫无意味,毫无用处的把时日送走”[3](P467)。自己感觉“在一种固定的、成为定型的无聊的空气中,她更证实了一切的无望”[3](P469)。生活无意义以及自我的无所适从正是人与时代背离而产生的孤独与被抛弃感,是女性在社会寻找出路而不得的社会的悲哀。《在暑假中》的女性们试图组成自己的女性王国,然而这个“王国”也为时代和男性所不容,最终她们解散了。丁玲早期作品所塑造的女性的悲剧,是觉醒了女性在其生存的时代社会找不到出路的悲剧。这一时期的女性苏醒了自我意识,开始了自我价值和人生命运的主体思考,但时代社会在发展,人们的思想观念还停留在封建专制的思想文化意识层面,于是,这些先知先觉的女性必然在她们所处的时代和社会中走投无路。
其二,传统男权思想意识与性别观念的悲剧。
丁玲文本揭示了传统男权思想意识给女性造成的伤害,这种意识以男尊女卑为核心内涵,以男主外女主内为社会角色分工,以男主女从为家庭角色定位,以色相和性的工具作为女性的价值存在。《梦珂》摹写女性在男权社会被欲望化的生存图景:即“女人的社会位置始终由男人来指定,她从未实施过自己的法律,唯一适合她们的就是做个纯粹的肉体,作为一个被欣赏的对象”[4];而《夜》建构了一个异化的性别世界,这个世界一切以男性(何华明)的要求为准则,三个女性在何华明的眼中只是有色、欲、工具的价值存在,而完全没有人的价值的彰显[5]。《我在霞村的时候》贞贞的悲剧是身为女人而要为男人守贞节的性别悲剧,即便失贞为革命带来了既得利益[6];在《三八节有感》里,即使在革命政权内部,妇女虽然经济上独立了,并获得了政治上的男女平等,可实际上她们在爱情、婚姻、家庭、工作等日常与实际生活中仍面临着种种不公平的“非议”和“指责”。在这里,传统的男女有别的思想依然存在,女性的社会活动空间还是受到限制:“她们平时不能同一个男同志比较接近,更不能同几个男同志接近”[7](P3)。其次,女性的婚姻不能自主,男性潜意识里的性别优越感和对女性的歧视暴露无遗:女同志拒绝了老干部的求婚就会遭到这样的训斥:“他妈的,瞧不起我们老干部,说是土包子,要不是土包子,你想来延安吃小米”[7](P4);而提出离婚的女人会认为“那一定有更不道德的事,那完全该女人受诅咒”[7](P5)。再次,女性依然是“是非”的中心和传统家庭义务的承担者:“女同志若不结婚她将会成为制造谣言的对象,结了婚后则是被逼着做了操劳的回到了家庭的娜拉”[7](P4)。然而,即便这样,“他们(男人)常常心安理得地看待女人为革命和家庭所作出的牺牲,认为这一切是很正常的,无须大惊小怪”[8]。然而这一切“在旧社会里,她们或许会被称为可怜、薄命,然而在今天却是自作孽、活该”[7](P5)。由此,“在延安,尽管妇女的社会保障有了提高,但性别意识和性别观念却仍没有多大的改观,而这种现象同一切的理论都无关,同一切主义思想也无关,同一切开会演说也无关。但这种‘无关’正是性别观念和性别秩序的‘盲区’的存在状态,这表明传统的旧观念依然根深蒂固地存在于人们的思想观念中”[9]。这种旧的观念、这种“盲区”的存在状态表明作为社会主流话语层性别意识的整体缺失,这就必然遮蔽由性别而带来的有形无形的悲剧,因而女性的悲剧依然是深层的,是社会、主流话语的人们还没有意识到的性别观念的悲剧。
其三,不合理的体制和制度的悲剧。
丁玲一生都以女性的姿态在自己的作品中探索中国女性的生存、地位、价值等问题,并且思考不断地走向深入、全面、现实。从梦珂的沉沦,到莎菲觉醒独立后依然无路可走的思考;从关注乡村女性阿毛到《在暑假中》女性联盟的破产;从贞贞的被贞节观念所煎熬到《三八节有感》女性群体的被漠视,丁玲发现了女性被时代和社会遮蔽的严峻事实,发现了传统男权观念对女性的弱化和歧视。她的思考没有停留,“一九四一年二月在川口农村作短篇小说《夜》,它与那一时期的其他作品(《我在霞村的时候》1940年,《在医院中》1941年,《三八节有感》1942年等等)构成了一种深刻不安的历史气氛”①。这种“深刻不安”正是对女性问题的深入思考,她发现新体制下,自由独立、有了自己政治经济权利、甚至掌握了知识话语权的女性依然不见容于新的环境,而这种情况与“体制”有关。贞贞即便在革命组织内部,也没有赢得真正的价值认定,革命内部的同志关心的也是她在那边的所谓的“材料”,即有关贞贞失节的隐私,细节。在这里,即便是为革命献了身也尽了力的贞贞在革命阵营内部没有获得制度层面的保障,革命内部对女性价值的界定依然是两套标准,依然挣脱不了传统贞节观念的阴魂。革命虽然给她指定了一条出路,那就是到延安去,但去了延安以后的贞贞怎样呢?答案可以在陆萍那里找到。掌握了科学话语权利,完成了现代性转换的新女性陆萍在表征着新体制的解放区命运怎样呢?种田出身的外行院长、有着“一副八路军里青年队队长的神气”整天思考着怎样对付负责医生的指导员以及虚伪的应付的产科主任构成的官僚体制,不仅“以一种对女同志并不需要尊重和客气的态度接见陆萍”[10](P614),而且在随之而来的日子里,对她所有的热情与参与进行了无声的回避,有意的冷漠。她的陈述、意见、辩论,她所看到的不合理的事情,她对医院制度的看法,所有有关她的表达成了院长、指导员指责她的借口。而那个没脚的人在陆萍感叹“我实在呆不下去了。我们这个医院像个什么东西”[10](P627)时告诉她,现在还算好的了,早前自己住院,整个人都喂了虱子。而他的脚就是因为医务工作不好,没有人才,冤枉锯掉的。更可悲的是他告诉她:这里的人都不行,要换人,可是,他们上边的人也就是这一套。至此,陆萍与体制的严重对立正表征了“解放了的知识妇女与未给女性留下地位的革命阵营或统领着那一阵营的意识形态初次相遇时发生的摩擦”[11]。这摩擦正说明了革命体制对知识女性的排拒和挤压。而没脚的人的话意味深长地说明了这种体制的腐朽森严、由来已久、根深蒂固。正是体制的打压,扼杀了她所有的热情与努力,折断了她爱飞的梦,她也不得不在延安出走。这种被剥夺话语权的情况在《三八节有感》附言中更直接明显地呈现出来,“有些话假如是一个首长在大会中说来,或许有人认为痛快。然而却写在一个女人的笔底下,是很可以取消的”[7](P7)。首长才有话语权利与女性即便发出了声也是没有作用的对比,正是体制对女性性别压抑的显在证据。但正如周可所说:“如果一种先进的体制,不能有效地使包含在其中的性别成分得到合理的配置,并使不同性别的利益得到平等的分享,那么,长期处于‘第二性’地位的女性为社会所付出的代价也就永远得不到补偿”[8]。女性自然也就成了不合理体制之下悲剧的承受者。
其四,女性主体人格阙如的悲剧。
丁玲既从历史文化的纵深角度思考女性,对女性的悲剧进行了社会文化的探源,又着眼女性自己,从女性自身寻找悲剧的因素。从莎菲的孤傲、倔强到阿毛的无知、简单,从承淑、嘉英们的脱离社会到丽嘉、玛丽们的对男人的爱情沉迷和依附;从贞贞的自轻自卑到陆萍的神经过敏、好冲动、沉迷于幻想之中,丁玲从女性自身出发对女性的个性人格进行了无情的解剖。而在《在医院中》,作者塑造的女性群像更生动地印证女性是自己悲剧的重要责任者。
跪在草地上的、浑身都是草屑,剪短的头发乱蓬得像个孵蛋的小鸡,破布片似的苍白的脸,和两个大而无神的眼睛的女人,连串地熟悉地骂着那些极其粗鲁的话的张医生的老婆,眼光里含着“敌意”,语调“又显得傲慢”的化验室里的林莎,庸俗平板的脸孔,最会糊涂涂懒惰地打发日子的张芳子,让人感到有说不出的压抑的产科主任王梭华的太太,以及对看护工作既没有兴趣,也没有认识的产科室的看护。从作者描绘的这群懒惰、糊涂、粗鲁、庸俗、百无聊赖的女性群像来看,她们还远没有成为一个“独立”的人,受历史文化、自我修养、社会实践的制约,她们脆弱、自恋、眼光狭窄、依赖性较强。她们对自我的感知局限在狭隘的个人感觉与经验;她们无从清醒地决断自我的存在,更无从从群体的角度去把握作为类的存在的女人对人生与社会的责任,她们是一群主体人格被阉割的人。由于主体人格的阙如,她们的自我处于混沌不明的状态,她们无从在生活和实践中成长属于自己的力量,更无从感知类的力量,因而,她们也就无从把握自己改造世界的命运。因此,她们自身也是自己悲剧命运的制造者。
二
丁玲在揭示了女性悲剧命运的时候开始了对女性解放之路的探寻,她通过刻画生动的艺术形象向我们展示了她对妇女问题的看法:妇女的解放不仅意味着经济和政治的解放,还应包括妇女本人以及社会对她们存在的意义和价值的认识。丁玲的这一妇女观包含着两层意思:第一,妇女仅仅获得政治和经济的解放还不能算是最后的解放,妇女的最终解放在于妇女自身价值的全部实现。第二,要达到这最终的解放,既需要妇女本身的独立自强,同时,也需要社会为此创造有利的环境[12](P54~63)。
首先,改革社会,更新制度。
正如马克思所说:“社会的进步可以用女性(丑的也包括在内)的社会地位来精确地衡量。”[13](P571)当社会不能给人类一半的女性以应有的社会地位,不能让女性的生命价值得到充分实现的时候,那么这个社会的进步性就值得质疑,这个社会就是一个需要改造和改进的社会。与西方伴随着女权运动的妇女解放不同,中国的妇女解放一直是由男人提倡,男人指导并伴随着阶级解放和民族解放的搭车解放。这种不是针对以男权中心为前提的解放造成了女性性别压迫的被遮蔽。而且由于“五四”提倡的人的解放并没有深入到女性作为“女”人的解放,以致“30年代,大多数女作家不仅将做人置于首位,而且几乎视为唯一。在她们看来,阶级、民族所遭受的灾难浩劫涵盖了女子由于个人由于性别而遭受的压迫奴役,阶级的、民族的抗争包容了女性寻找个性解放的奋斗”[14](P11)。但丁玲常常逸出界定,不仅在政治、经济话语的罅隙流露出自己深沉的忧思,而且在阶级解放和民族解放的话语遮蔽中敏感地意识到“妇女解放虽同民族与阶级解放相联系,但并不能为其所取代”[15]。争取到了经济独立的莎菲、梦珂、伊萨们,她们在时代和社会大潮中依然苦闷彷徨、走投无路;美林、丽嘉投身革命而遭到的革命与恋爱的矛盾,贞贞、陆萍们献身社会却也为自己的社会所不容,以及黑妮的吊诡处境,直到新社会的杜晚香失去了作为女性性别的特殊存在,女性自身的价值不是毫无施展的空间就是被时代和社会更大的命题所遮蔽,女性成了一枚棋子,唯独失去了自己的“为人”、“为女”的本质存在。丁玲以其近一个世纪的写作告诉我们,女性生命价值得到全面实现的时代和社会还没有来到。而人类一半的女性的生命价值得不到实现,这不仅是女性生命的悲哀,也严重限制了男性生命的发展。基于此,丁玲发出了“妇女要真得到解放,得到自由,得到平等,必须整个社会整个制度彻底改变,否则是不行的”[16](P155)的呼吁,并热切期盼当权者“少发空议论,多谈实际的问题”[7](P5),不要只满足于表面形式的开会、讲演、发文章。这不仅在当时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时至今日仍然发人深省,值得借鉴。
其次,投身社会实践、进行文化改造。
丁玲的作品,多以女性为主角,并将对女性生存的关注投入到对社会实践的关注。从《黑暗中》的女性在社会上的走投无路,她想到了隐忍、逃避、自杀、取名字,她们以自己的方式实施着对社会的反抗和对自己生命之路的寻求。但个人的力量无力抗拒沉沉的黑暗,而时代的大潮又将新的选择带给了她们。丽嘉、美林们在恋爱与矛盾的漩涡中,既用恋爱来滋养自己,又投身革命获得生命的新感受,丽嘉爱的力量使韦护“在有了新信仰之后一直处于理性控制与压抑状态的生命需要找到突破口”,而丽嘉在革命实践中,她开始感觉不能“单单用梦想来慰藉自己的懈怠,总要着手干起来才好”[17](P71),进而要“凭自己的力找条出路”。她的心灵一步步成长,以至韦护离开她时,她并没有因此而沉沦,而是确立起自己“好好做点事业,慢慢来支撑”[17](P121)的新的生活目标。美林投身到革命的洪流中,并思考她还要“在社会上占一个地位,她要同其他的人,许许多多的人发生关系”[18](P261)。她们在投身社会实践中,成长了自己,对生活有了自己的理解和选择,有了自我的意识。而到了贞贞,虽然贞节的绳索从各个方面套向她,但她自己却超然,她以自己的理解与方式实现了对传统贞节观的超越,显示了对自身价值的主体认同,这是实践带给女性的新质素。而到了陆萍,思想的先进与现代技术的掌握,使她对自己的力量充满自信,她觉得她能担当一切,她努力用自己所拥有的思想和技术来改造她所处的环境,她内心充满了作为主体的女人对自己命运的创造之情。以致“在历史的舞台上一直没有停止探索的是丁玲式的女性们,她们的精神追求有一个明显的上升轨迹:即不断地否定‘旧我’,重塑‘新我’,且这些重塑中带有明显的时代色彩”[19]。丁玲正是通过女性的不断投入社会实践的描写,揭示了投身社会实践的女性不断扩大的心灵世界和日益增长的生活空间,从而启示女性,投身社会实践是女性解放的一条可行的道路。
投身社会的丁玲以自身的行动实践着女性的解放之途,并在实践中不断增长着对于女性解放的新认识。“女性的解放不仅仅是争取政治上的平等、经济上的独立,而是要在以上社会的、自然的(性别特点的)、文化的不同层面获得完全的解放”[20]。她意识到女性的悲剧无论是时代社会的悲剧,体制制度的悲剧以及自身的悲剧,其深层的根源在于文化的悲剧。从莎菲对现实中男人的无情否定到对贞贞生存尴尬的思考与揭示;从阿毛生命意识觉醒后的走投无路到陆萍“革命既是为着广大的人类,为什么连最亲近的同志却这样缺少爱”[10](P626)的对革命的质疑,丁玲的思考实际上已越过阶级民族的思考而触及到了社会文化的层面。她发现女性解放的社会文化环境远没有到来,莎菲生长的文化环境成长不出心身和人格健康的男人;而贞贞的逼仄处境也无不是文化思想观念的沉沉压力带来的;阿毛的死也与周围人的文化隔膜不无关联;陆萍的动摇源于先进理念与落后现实的文化落差。而要解决这个悲剧,实现妇女的真正解放“有待整个人类思想意识的进步,尤其是妇女自身的自立和自强意识的壮大和发展”[21]。这人类思想意识的进步即是整个社会文化呈现出一种顺乎人类天性又提升人性精神素质的发展态势,而这种思想意识“只能靠来自人的内心世界的精神革命”[22](P54~63)。而这种内心世界的精神革命除了主体的人通过各种途径广泛吸纳人类宝贵的精神财富并加以实践的强化而内化为建设自身的一种生产力外,我觉得人类的精神领袖应不辱使命,从人类精神宝库中精选出人类所需要的精神营养,对广大的民众进行精神导引,以减少个体探索的时间和精力花费。其次,社会应将思想意识的进步作为一种精神产业纳入体制,这是比任何其他的生产更为关键的生产。只有人类主体与社会意识形态呈现出一种整体向上的发展态势,整个社会的文化氛围才能适应人的不断解放的需要。而从丁玲对女性解放的思考来看,她认为必须有文化层面的人类思想意识的整体提升,亦即必须清算男权意识,必须突破传统两性价值观念,必须营造有利女性发展的人文环境等等。
第三,建构女性主体,树立强己意识。
当丁玲对女性解放的外在因素作了细致而诚恳的探求后,她反观女性,进而从女性自身寻求解放的内在动力。强己意识是她个性人格的核心,而她的强已基于她对女性的了解和对女性力量的自信。从莎菲、微底、玛丽对自己欲望的认知、肯定到贞贞对千百年来压在妇女心理上的种种耻辱观、道德观的颠覆;从三小姐的勇毅、觉悟到陆萍的改造现实,到杜晚香对生命的无限的包容,丁玲认识到了女性的力量,肯定女性在了解和掌握自己生存现状基础上对自己命运的主动抉择。在《三八节有感》里,她将这种强己意识发挥到了极致,她将“强己”的要求具体化,即“爱自己的生命、把自己铸造成一个健康的、乐观的、有恒心的、有理性的人”[23]。同时,她通过一系列的女性形象有力地寄托着自己对女性自身解放的期望与设想:“世界上从没有无能的人……女人要取得平等,得首先强己”,“幸福是暴风雨中的搏斗,而不是在月下弹琴,花前吟诗”[7](P7),“人是要经过千锤百炼而不消溶才能真正有用。人是在艰苦中生长”[10](P629)。形象地说明着女性的解放不能靠别人的恩赐,只能靠自己自尊、自信、自强不息,这是女性求得自身解放的前提。她在文本中刻画了因“强自己”而具有独特生命光辉的一群女性:莎菲的“强自己”把千百年来神圣的男人形象颠覆,冷傲地宣布她对男人的失望、轻视;梦珂“强自己”,在纯肉感的社会里对自己将要沦为玩物的命运保持理性的警觉,她在隐忍中活着,企图突破历史必然性的制约;阿毛的“自我意识的苏醒”使她认清了无前途的生存环境,选择了对自己命运的主动了断;阿英本能意识的觉醒,洋溢着“女性自组织的生态智慧”[24];丽嘉、美林的“强自己”,使她们在社会的风浪中谋得了自己生存的一个位置;贞贞的“强自己”使她超越了传统的贞节枷锁,以自己的方式实现了对生存价值的突破;陆萍的“强自己”使她萌发了拯救社会的雄心壮志,并在自己可能的范围内对周围环境进行了现代化氛围的营造。杜晚香的“强自己”使她成为了一个对社会完全奉献的楷模。丁玲为这些“强自己”的女性树碑立传,在对她们的人生命运寄予着深深的理解和同情的同时,她又告诫广大的女性要以她们为人生的借鉴,吸取经验和教训,以有效的方式“强自己”,从而走向新的希望和新的解放。
综上,丁玲对妇女问题的关注和思考倾注了她一生的心力,她描摹千姿百态的女性生存本相,探求思考女性悲剧命运的根源,她认为女性的悲剧是时代社会的悲剧,是传统思想意识与性别观念的悲剧,是体制制度的悲剧,是女性自身的悲剧。面对多样的女性悲剧,她进而思考女性的命运、寻求多样的女性解放的道路。她认为要改变女性的悲剧命运,必须改革社会,更新制度;必须投身社会实践,进行文化改造;女性还必须“强自己”。
收稿日期:2009-03-25
注释:
① 黄子平《病的隐喻与文学产生——丁玲的〈在医院中〉及其他》,转引自王晓明主编《批评空间的开创——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