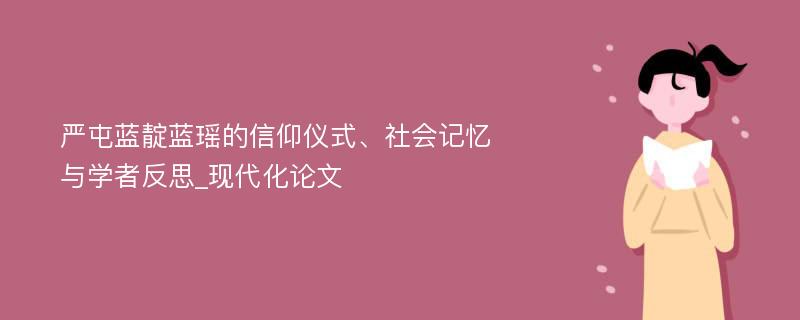
各烟屯蓝靛瑶的信仰仪式、社会记忆和学者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蓝靛论文,仪式论文,学者论文,记忆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7年5月13日至8月22日,我作为由翁乃群博士主持的福特基金会资助项目《南昆铁路建设与沿线少数民族社会文化变迁研究》课题组的成员,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田林县潞城乡各烟屯进行了累计近5 个多月的田野调查。
各烟屯位于广西西北部,有62户,311人,其中男性140 人, 女性171人。人口中绝大部分是瑶族(蓝靛瑶),有293人;其余少数为壮族,有18人。各烟屯是各烟村村公所所在地,在潞城乡政府以南15公里处。各烟屯位于群山怀抱中,居家分布在半山腰上。周围多土山,海拔在900~1100米之间。这里气候凉爽,日照充足,土地肥沃,森林茂密。在本地,由于坪坝地区气温低,只种早稻,不种晚稻;另外种山谷、玉米。山谷分粳米和糯米两种。
各烟屯的蓝靛瑶至今信仰祖灵和鬼魂,他们举行的仪式充满了道教色彩。这种以道教为基础的灵魂信仰,渗透在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从盖房子、造牛栏到生病、丧葬,都伴随着一定的禁忌和仪式。在各烟屯,在“现代化”的背后总会出现地方化的道教的影子,物质的“现代化”并不影响由师公和道公执掌的道教的力量,就像西方社会中的许多科学家仍然信仰宗教一样。各烟屯的道教及其精神文化是一种“语法”,它控制着人们怎样“说话”。现代化的物质“暴力”并不能使他们感到非常惊讶,他们以一种平常之心看待变化着的一切,好像一切都是“玉帝”、“三清”安排的。他们不怕金钱,不怕电视,不怕城里人,因为金钱、电视、城里人早已经在他们的文化格局中有了位置,放到那里“说话”就是了。他们不像城里人那样怕死,生与死是按照自然的节律来出现的。他们没有城里人那种“怒气冲天”,惩罚与宣判似乎是在平静中进行。保罗·康纳顿(Paul Connerton)在谈到社会记忆的时候注意到,过去的形象能使现在的社会秩序合法化,而任何社会成员都会有一个建立在肢体性仪式上的共同记忆。“但是,纪念仪式只有在它们是操演的时候,它们才能被证明是纪念性的。没有一个有关习惯的概念,操演性是不可思议的;没有一个有关肢体自动化的观念,习惯是不可思议的。 ”(注:Paul Connerton.How Societies Remember,p. 4.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9.)各烟屯蓝靛瑶的习俗具有一系列观念基础,也具有用肢体来操演的民间仪式。思维观念和肢体仪式共存互生,成为社会记忆的一部分,通过一次又一次的操演,和经济理性对话,使传统在表层蜕变的同时,保持底层的沿续。
各烟屯人在盖新房之前要拜被称为piao[35]man[55]的梁神, 他能托梦告诉恶兆。建房时要在柱子下面埋月份牌、铜钱等,两个柱子下面都有。月份牌上有二十八星宿,瑶话称tson[35]on[35]man[55]。 管三代人的神叫做tju[213]pu[55]man[55]火神叫做kru[22]man[55]; 畜神叫做bwtei[23]man[55];坟神叫做dbeu[213]man[55];神台上的神叫做pjao[35]man[55]。
在各烟屯的北面矗立着他们草木繁盛的神山,山顶上有一处用石头堆成的神位,形状如微缩的“敖包”,高约60公分,宽1米多, 正中是凹进去的神龛,里面的石板上放着一个碗,碗里有香灰,祭祀的时候可以插香;神龛旁可以置放酒瓶。每年清明节都要有师公来这里举行仪式,安慰祖灵,祈祷幸福。在一般情况下,各烟屯的人不到这里来,因为这里是鬼魂出没的地方;即便来到这里也有很多禁忌,例如不能折断树枝,不能大小便等。离神位不远,在神山北面的那座山里曾经埋葬着盘家、李家等族人的祖先。这样的神山在田林地区的蓝靛瑶聚居区普遍存在,也普遍受到敬奉。大年初一和三十、农历七月十四和正月十五,都要拜神山,一般是由文书的五叔主持,另外找两个帮手,一个“读经书”,一个“搞动作”。然后,全屯的人都要到五叔家里来拜神。
八月的一天,各烟屯的调查合作人之一小李带我去山上看一看。从他家房后的半山腰走小路,路过梁结家的新房的背后、旧房的背后,从这条路可以去山那面的岩才屯。神山上树叶铺地,蚊虫成群,不像别的山林那样有那么多的人的痕迹(小路、近几年栽种的桐果、八角、山地、水田等等),这里到处是野生杂木,到处是不见阳光的树荫,所有这些再配上小李讲述有关“神灵”的“地方性知识”的缓缓而似乎遥远的话语,也就更加证明了这座神山的特殊地位的“合法性”。然而,我们先去的并不是神山,而是神山旁边那座山上的“坟山”。李家和盘家的祖坟先是埋在那里,后来迁走准备二次葬,不过,原来放骨殖的瓦罐和坟坑,还可以看得到。这里草木茂密得难以通行,可知很少有人来。在我们来这里的前一天,梁结的两个女儿就领着我上北面这座山拍摄各烟屯的全景照,拍照的地方离现在这块坟地不远,那时她们告诉我说那边有坟。我让她们领我去,可她们不去,还问我怕不怕。也许去坟地是有社会性别的规定的,即女人不能随便去。神山崇拜及其禁忌,是南昆铁路沿线诸少数民族中比较多见的现象。
在各烟屯,风水是一种表象的空间配置,是社会记忆的再生产,是“神圣地理”的一部分。从盖新房、造马厩到丧葬活动及其相关的观念,可以说是各烟屯瑶族信仰的核心部分。各烟屯的住宅,不分新旧,都要请师公看风水,择吉日营造。所以,许多前几年盖新房的人家至今大梁上还悬挂着一些与风水吉相有关的红色纸幅。各烟屯的文书要建一座马厩,他上山伐木,肩扛马驮,用个把月时间才把木料备齐。但是,在开工之前,还需要请他的三叔看风水、定吉日。三叔住在各烟屯南面的那来屯,对两个屯来说他都是一个重要的师公。可是一连等了好几天,三叔也没能来,这样,马厩也只能放着以后建,而文书一家却并没有什么怨言。似乎请师公看风水的人家,首先要学会随遇而安,任其自然。
表面上看,各烟屯的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互为表里,似乎自然地理是人文地理的“载体”,神圣地理是自然地理的意义。其实不然。只要到那里生活一段就会发现,这两种地理是互相渗透、互相生成的。当然,我们并不想就此说它是一种原始思维的互渗规律,(注:根据法国学者列维·布留尔的观点,在原始人的集体表象中,客体、存在物、现象可以使它们自身,也可以使其他东西。它们也可以发出和接受那些在它们之外被感觉、同时又留在它们里面的神秘的力量、能力、性质、作用。参见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中文第1版,丁由译, 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69~70页。)说它是各烟屯的一种思维方式就足够了。各烟屯的社会实践并非完全杂乱无章,随机应变,而是具有和其他人类学模型一样的结构。只是这种结构是流动的、变化的,与社会实践保持辩证统一的关系。
风水观念支配着各烟屯瑶族的日常生活,造房的时候要选风水好的地方,办事不顺利是因为坟头方向不对,等等。丧葬活动及其相关的观念可以说是各烟屯瑶族信仰的核心部分。人死后,要给他洗澡、剃头,请健康的中年妇女做寿衣。洗澡的水要加香水;做寿衣的妇女最好是不曾生育并且已经过了生育年龄的人。也可以请寡妇来做寿衣。死者的寿衣是白色的,穿上以后,再用一条白布盖脸;死者入棺之后,身上还要盖一层白布,表示阴阳相隔;他的两手里要放糯米饭,嘴里要放半块“法光”,免得他在阴曹不顺利的时候回来找儿孙的麻烦;放了“法光”之后,死者有了好事才找儿孙们,坏事不找他们。把棺材放在大堂里,不让猫狗进来。子孙们要围着棺材坐下,儿子们身披孝服守灵。棺材底下、头上各点油灯1盏;杀1只鸡摆放在棺材上,旁边放3个酒盅, 点上香;香不断,灯不灭。此外,还要把一块“法光”分割成6条,分3个一组钉在相当于死者头部和北部的棺材处。找一个男孩请师公,请的时候要提一壶用白布缠紧的酒壶。中间人引着小孩到师公家门口跪下。中间人是一个能说会道者。小孩身穿孝服,跪在那里,请人传话,把拿来的酒壶放在门口。师公接他进去时,小孩要爬行。师公用白布打结挂在神台下。师公每念一本书,小孩就手拿短棍爬地一圈,膝盖都会被磨破。还要请师公算命,选入葬的时辰和入葬的地方,与神灵商量能否“买”一块地。选好坟地之后,师公还要做法事,用三角旗在坟地四面插定,叫做“催魂旗”。“催魂旗”有红、绿、浅红、白、黄等5色, 其中黄旗插在中央;五色旗象征东西南北中。死者家门前还要插白色“引魂旗”,树立1、3、5、7面数目不等、以单数计算的幡,一面幡有两三掰长。孝男孝女跪在那里挖坟坑,这时师公在灵位处悬一块白布上面打一个结,象征把鬼魂捕入阴曹,不准乱动。白布结要拿回来保留3年, 表示判它3年徒刑;3年之后开结刑满释放。从此,死者魂灵进入受祭拜者的行列。白布结在打开之后,与孝服一道烧掉。蓝靛瑶一般实行二次葬,人死入葬3年之后,打开棺材,取出骨殖,放入瓮中, 另找风水好的地方埋葬;同时要请人造纸房子,造灵台。埋葬的地方有坟头,坟头前面立1块小碑,一年培土两次:一次是二月二, 一次是立冬后的任何一天。聋哑人死后,当即请师公下葬,不做许多法事。
在我调查的时候,各烟屯来了两位德宝县的木匠,是叔侄俩。我的合作人之一盘志金的祖先给他留下了一棵高23米多,直径70多公分的椿树,是寿材。他告诉我,他的三叔给他算过命,说他只能活30岁。他想着要赶紧准备,就请这两个从德宝来的木匠上山伐木,再加工成9 块寿板,7个横条,4个方条,一共花了280多元。他说这9块寿板已经足够做一付棺材了。听说屯里其他人也要让这两个木匠伐木做寿材。瑶族对死亡泰然处之,认为来去都是前定。文书倒并不急着准备寿材,因为他算的命可以活到70岁,所以50岁以后再考虑也不迟,反正他的寿木在山上长着。按照当时的价格,加工一块寿板12元,1个横条7元,1根方条4元,一共合起来要付木匠286元。盘队长一时拿不出这么多钱, 就只能贷款。德宝木匠老一点的属鸡,和我同岁,当时是40岁。他有两个儿子,老大在德宝上师专,老二在那儿上完小。侄子是他的徒弟,是他哥哥的孩子,先是上了中学,后来因为没钱初二就退了学,出来谋生。7 月的一天早晨,我和他们上山,看他们伐木、破木材。他们的工作点在接近山顶的地方,要走1个多小时,走过一段山路之后,就没了路, 径直攀援而上,不时要用手扒开茂密的杂木林,绕过一棵棵栽种的桐果树,驱散那些试图“剥削”我们的蚊虫,在一片山野朦胧中到达目的地。本来我是来看他们伐木和破木的,可是,等我到那儿一看,那棵老椿树已经被伐倒,展展地横在一片草木丛中,上面的枝叶基本被清理得干干净净。前天他们砍了一些杂木搭起一个工作架,被伐倒的椿树有218 公分长的一段横放在工作架的两根木头上,用藤条捆死,年长的木匠在上面把握锯子的走向和力度,他的侄子在下面拉锯,大约1 个小时能破开1 块218×5×50公分的板子。这是他们第三天干活儿,今天能干完。他们俩是从福达乡那边转过来的,出家门已经一个多月了。盘队长家是雇他们做工的第三户人家,另外还有四五家人等他们去破木材。根据木材量的大小,有的人家出60元,有的人家出300元,让他们做工。 两位木匠晚饭在盘队长家吃,午饭从他家拿米、拿油,再从他家菜地里摘些瓜秧,到山上去做饭菜——他们在山上准备了做饭和炒菜的锅。
葬俗中的禁忌是最典型的信仰对社会行为的控制形式。人死之后,死者的家人不能待在高于死者的地方,不能坐板凳,不能睡床,吃素,不喝水,三天三夜守在棺材旁。母亲死了,120天不能剪头发; 父亲死了,90天不能剪头发。此外还不能拔青草,不能做工;见到蚂蚁和蚊子也不能打死。据说有一家迁到各烟屯的壮族,他们家死了人没有请瑶族师公,而是请了一个弄读村的壮族师公。瑶族做法事的时候,师公和死者家里的人都要吃素,不能吃肉、喝酒、喝水,可他们来了以后就不忌讳这些,随便吃喝。扛尸体出门的时候,瑶族是用引魂旗领路,一路上撒一些纸钱;可他们按照壮族习惯,打一个火把引路。结果那死者的尸体很快腐烂发臭,这在各烟屯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屯里人去帮他们的时候,都不进他们家,往外扛棺材的时候,臭气熏天,人们很恼火,说应该让那些师公来扛。结果,那些师公的法术失灵了。那天晚上,潘队长陪着他死了阿婆的朋友过夜,正好赶上那阿婆的鬼魂回来闹腾:明明关了门,门被打开;灯也被吹熄了,就听见她老人家的脚步声。他们俩吓得用被子捂上头,听见他爸爸说:“我们白天做工,你晚上来闹,我们睡不着觉,有本事给我们做饭吧。”就听见她又出去了,门也吱呀一声关上了。后来,人们都不从他们门前过了,没办法就请一个瑶族师公重新做法事。
有一次,屯上梁远良的母亲病了,就请文书的五叔用巫法做药。五叔在离开他家不远的路上用1个畚箕放1个碗、1双筷子、1颗鸡蛋、3 个装满酒的酒盅、3个芭蕉心。五叔用一把刀竖插在畚箕旁边, 开始念念有词地做巫法。大约过了半个小时,五叔的药做成了。其实,做法祛病只是五叔的“小术”,他真正的用武之地在每逢节日或者葬礼所举行的仪式之上。例如,七月十四那一天晚上,文书潘志光请他的五叔做巫法。潘志光先替五叔摆好一张小桌子,上面放一个碗,碗上横放3根香;再横排放3个酒盅;酒盅之前再撒一些稻谷。 他的法器包括一对用竹子制作的“告”、一沓纸钱和一把刀。他点燃一盏茶油灯,左手部位放一沓纸钱,把小砍刀插在桌子下面的地上。做这种巫法的目的是请祖宗和家人一道享福,保佑他的后代。五叔让潘志光给酒盅斟满酒。他忙跑到小卖部买了两个用塑料袋装的“土茅台”,把酒盅斟满。他又在桌子下放了一把没有把的铁锹,准备烧纸用。他把横放在碗上的3 柱香点燃,然后在桌上左上角放两条用芭蕉叶裹上的粽粑;在这两条粽粑中间插 1柱香并把它点燃。潘志光又用草纸做了一些纸钱放在桌角上。与此同时,1位从能良乡来为潘志光帮工的小黄正在帮着剥豆角、煮鸡, 他的爱人在泡粉条。梁远良也过来和五叔攀谈,并送他一盒烟,好像是要感谢上次为他母亲的病做的巫法。
五叔头戴一项军帽,记得我给文书在那来屯的三叔照相时,他大热天也戴了一顶棉帽,而他也是一位师公。显然,这些军帽和棉帽都具有法帽的功能。
过了20多分钟,那只刚煮熟的鸡被放到那张法桌上, 另外还放有9个鸡蛋、1块猪肉和一些鸡肠子。
五叔用酒桶的盖子装酒,又给那3个已经斟了酒的酒盅加酒, 还不时默念一段咒语,然后把桌子上的稻米撒向酒盅和已经放到下面的草纸上。
五叔前后转动“告”,然后把它们放到帽子里,抄起砍刀,扎在一张铺在地上的纸上。他始终默念咒语。他又从帽子里取出“告”,边敲边念祝词。过了一些时候,他又抄起刀,前后转动,再一次扎纸,念祝词击“告”。此时他拔起刀,把纸钱揉做一团,走到火塘前,用刀比划着扔进火中。
他用草纸条做捻子,蘸茶油点燃,手里拿着站起来,走到祖灵牌位前,默祝。默祝完毕,转回来把纸扔在锹头里烧了。
又用草纸做了4个捻子,把其中3个放在锹头上,再覆盖一些纸钱。用第4根捻子蘸茶油点燃,用右手拿着,左手拿一张纸钱, 摇动右手的火捻,默默念诵祝语。然后吹熄火捻,把纸钱(左手那张)撕成几块,放在左面的地上烧了。
把锹头拿起来,凑到油灯前面把里面的纸钱烧掉。原地绕两圈,举着拿燃烧的纸钱暗祝。
把锹头放下,再点燃一些纸钱,击“告”。把刀又插在原来那沓纸钱上。把“告”随机投在地上。
再次给那3个酒盅加酒。撒米。
把剩下的纸钱放回到桌子的左手部位。又开始击“告”。起立。原地转两圈。投“告”。右手持纸钱点燃,压在右面地上放着的那沓纸钱上。击“告”。左手持刀,翻动纸钱,使之充分燃烧。
击“告”,投之。
再次加酒。
放下“告”,撒米。
击“告”。
起立,撮米,默念。合掌上下翻动。
以上动作(撮米、撒米、合掌上下翻动)反复9次。
取香投地上。
潘志光把右手那盅酒放好,以便全家喝。
经过1个小时左右,仪式结束。
在仪式期间,五叔让潘志光拿些香出去,放在各个门口、牛棚、猪栏和鸡窝处;祖先牌位前也要放。牛棚、猪栏和鸡窝处各放1根香, 每个门口放2根香,祖先牌位前放3根香。一共用去12根香(门是3个)。
各烟屯的瑶族在信仰方面与壮族和汉族有许多接近的地方。例如,他们也在门上贴关羽、张飞之类神像;同时,他们也在祖先牌位处用红纸写类似于下面的词句:
旺兴畜六 手应心得 利万本一 意胜事万 安平落上 旺两财丁
芳流德祖
亲 祖
之 德
神 南 位 门 灶 九 神
恩 母 唐 堂 皇 天 功
圣 娘 六 上 府 东 昭
德 娘 国 历 君 厨 百
福 之 花 代 之 司 代
千 位 皇 远 位 命
秋 圣 近
各烟屯的社会记忆在信仰仪式中延续,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中调整,在生人看来是“杂语”,(注:“……巴赫金青年时代的维尔纽斯,正是‘杂语’现象的一个样板,那种现象后来成了他的理论基石。‘杂语’现象即不同的语言、文化和阶级彼此交融,这在巴赫金看来是一种理想状态,它确保了语言和思想的不断革命,提防着现有社会中任何‘单一的真理语言’或‘官方语言’的霸权统治,以及思想的僵化和停滞。”凯特琳娜·克拉克·迈克尔·霍奎斯特:《米哈伊尔·巴赫金》,中文第1版,语冰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2页。 )在他们自己看来是“自然”。他们按照自己的“菜单”,用各种原有调料和新来的“料理”烹制“风味小吃”。各烟屯在地理上属于山区,但是,它的社会文化却处于山野和城镇之间,其社会文化结构正在发生变化,正在受到来自国内外流动的知识、资金、人员和其他各种资源的影响。不过,结构的变化不等于失去结构,而是说结构内部的各种成分及其互相之间的关系,正在出现变异和重组。这是一种流动的结构。
1996年各烟屯靠集资通了高压电,迄今全屯已经有15台电视,其中3台是彩电。距离潞城河不远,在各烟屯这面, 有广东南方集团公司桂北分公司的厂房,它是一个主要生产和加工板材的现代化企业,属于国家对口扶贫“光彩事业”的一部分。南方集团也投资建设了横跨潞城河的那座大桥,各烟人再也不用为在雨季渡潞城河担忧了。随着南昆铁路全线通车,山里的物产大量流通出来,各烟屯和其他沿线屯子与厂子之间的联系,随之增加。有趣的是,当你登上南山集团这边的山往下望时,会看见潞城那边的南昆铁路的铁轨和桥梁,看见试运行的火车;你的脚下就是具有象征意义的机器轰鸣的现代化厂家;在你的背后,有农民在烧荒锄地,给人留下刀耕火种的一丝联想。各烟人隔三差五要路过这里,我们这些“做田野的”,也不止一次地光顾此地。他们也许刚刚操演完信仰仪式路过这里,而我们也出于对自己学科的信仰与他们共度朝夕,我们都以各自的操演方式,延续自己的社会记忆。
克利福德·格尔兹(Clifford Geertz )强调文化是“表演的文件”,即操演的文本,反对把观念和物质分割开来,试图超越“主客观”之争。(注:《深描:迈向文化的阐释理论》,载《文化的解释》,纳日碧力戈等译,中文第1版,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36页。)这无疑是“新的综合”,或者勿宁说是“旧的综合”,因为要突破以往的“二元对立”的争论,只能采用1+1=2的作法。 我们自己受到语言和思维的限制,总要继承过去的窠臼,只有继承才能打破,这是一个怪圈。文化的存在形式是什么?是复制。文化被不断地复制,在复制中存在,在复制中保持价值和意义。所谓“原汁原味”的文化,从严格意义上说,是不存在的:文化经历了一代人又一代的派生,要找到它的客观实在源头,几乎是不可能。我们所说的文化或者文明的源头,是一种根据某些现存实物或者话语形式的推理,在很大程度上靠说服和信奉来得到认可。如形成文字的权威观点、“国家标准”的定义、民间传说、公众信仰等等。各烟屯的信仰仪式和社会记忆,使我们想到“反相对论”和“反反相对论”之争,到底文化是相对的,还是有一个全人类共有的“语法”?(注:《国外社会学》,1999年第1期。 )恐怕这样的争论要永远持续下去。人类学的“看家本事”在于田野工作,就是长期跟踪调查一个社区,深入发掘。当然,现在也有广泛“打钻”,“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做法。无论哪一种做法,其精髓在于“一小见大”,它是一种全息论。起初,弗雷泽、泰勒等奉行普世主义,追求普遍原则,把“原始文化”看作是人类文化的原型,是“活化石”。但是,从美国人类学者波厄斯开始,文化相对主义成为主流。文化相对主义强调文化之间的不可通约性,一个文化有一个文化的独特价值,不能用另一种文化强为比拟。但是,极端相对主义最终会否定人类学者自己,因为他总是来自一定的文化背景,既然文化之间难以沟通,那他也就失去了理解、描述和解释其他文化的资格。同样不能否认的是,许多欧洲中心主义者往往打着普世主义的旗帜,把自己的偏见强加于人。这就需要有一个辩证的态度,需要区分不同的抽象程度,例如在“人是高等动物”这一个命题是普遍适用的,而“泸沽湖畔的摩梭人实行走访婚”则是一种相对的说法。社会文化人类学者的魅力不在于他们的雄辩,而在于他们的“田野”,在于“行行重行行”。(注:费孝通:《行行重行行》,第1版,宁夏人民出版社,1992 年版。费孝通教授用亲身常年实地考察,建立了自己独特的学术风格。他“到农村里、城镇里去观察,去思考”。)他们不是没有理论,只是他们的理论用“田野”来表述。社会文化人类学者总是习惯于肢体的操演,总要在面对面时才感到舒适。他们的“社会记忆”体现在他们自己的“信仰仪式”(各种仪式性学术活动)中,而这种“信仰仪式”少不了用“肢体语言”来表述。他们和各烟人有共同之处,但毕竟是个独特群体。
1949年以来,中国一直在探索农民和国家之间的生产经营单位,从个体经济、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又回到以家庭经营为主要形式的经营承包制。国家在探索,农民在实践。这种探索和实践不仅仅是生产经营形式的探索和实践,而是政治理想和生存方式的对话;不仅仅是一场社会主义的国民运动,也是一场历史与文化的复制或者改写。无疑,各烟屯的农民也经历了这场从个体经济又回到个体经济的大轮回,只是他们并没有成佛,也没有想过成佛,而是像他们的祖先一样,以诚实的劳动生息繁衍,永远是普通的生灵。在各烟屯,家庭之间的互助一直没有断过,在大山的怀抱里,在河流的阻隔下,这是生存的本能。面对文字的历史,回想实践的经历,按下突兀的心绪,陷入深深的思考。
标签:现代化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