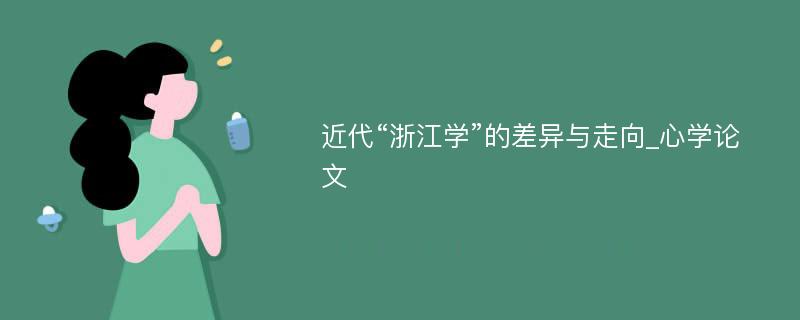
近世“浙学”的东西之分及其走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近世论文,之分论文,走向论文,东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现代浙江的行政区域是到明代才形成的。明初把元代的浙江行中书省领两浙九府改为浙江承宣布政使司领两浙十一府,嘉兴、湖州二府始自直隶来属浙江。故乾隆《浙江通志》有“(杭、嘉、湖)凡三府,在大江之右,是为浙西”;“(宁、绍、台、金、衢、严、温、处)凡八府,皆大江之左,是为浙东”的说法。所谓“大江”,即钱塘江。江左浙东八府,历代变化不大,而江右浙西的自然区域,则变迁离合频繁。尽管明廷为便于控制,而人为地划分行政区域,于是“合浙东、浙西为一,而钱塘之险失”(魏源:《圣武记》),但从总体上看,“吴下”的浙西地区与“吴中”、“吴上”的苏南地区①,无论在自然地理上还是在人文地理上都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地缘文化联系。而近世以来浙西在行政区划上属于浙省的历史事实,则丝毫不影响其在学术风格和文化型态上明显接近于苏南而远离浙东的趋向和特质。
从自然地理的角度看,“浙江十一府,以秦置会稽郡之封计之,西虽缩而东则赢”(《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中册,第1822页),即浙西面积小而浙东面积大。但从人文地理的视角看,明清时期吴的核心区域就是狭义的江浙,这必然包括浙江的湖州和嘉兴。浙省的吴地自古就有“吴根越角”之说,并且表现出与苏省的吴地天然亲近而与越地则因钱塘江和杭州湾的阻隔而相对疏远的特征。由于吴地属于浙江的太少,更由于江苏的吴地太过显耀,于是浙江向来以越自称。这不仅促成了江苏以吴自居而把吴、越等同于广义的江、浙,也影响了浙江人地域观念的转变。湖、嘉地区甚至有被边缘化的趋向。因为苏南的吴地太正宗,因而不管从实惠上还是情感血缘上,越才是浙江的灵魂。换言之,浙西不仅“缩”于地域,而且“缩”于文化与观念;在吴文化的强势渗透下,“浙学”自古以来就有“东”强“西”弱的特点。不过所谓浙东、浙西,在学术上亦非铁板一块,浙东的宁、绍与金、衢、温、台就有明显不同,浙西的杭州更显得相对独立,而与周边的嘉、湖、严、绍均有差异。总之,两浙、三吴中的浙西与苏吴,吴越以后就比较亲近,而与钱江以南的浙东地区和长江以北的苏北地区,在地域文化上逐渐显示出独有的个性。所以我们不能以现今的地域概念来笼统地指称“浙学”或“吴学”。
尽管吴、越两地自古以来就有“同气共俗”的文化渊源关系,但比较而言,吴、越两地包括浙东、浙西,在各个方面都存有差异②。所以浙之东西的学者文人,一直以来就有彼此瞧不起的思维定势,这种观念甚至还影响到从学于阳明的浙西弟子及其后学。比如出生于吴兴的顾应祥,少受业于阳明,对吴中地区之文风颇有微辞:“苏州人惯作小说而事多不实,盖苏人好文,往往以传闻之言文饰而成书故也。”(《静虚斋惜阴录》卷十二,《杂论三》)而同样出生于吴兴的管志道在述及自己身处吴中、孤独无友时,竟伤感道:“吴中士习,大概在诗文、势利两途。趋诗文则为诗文之有力者收去,趋势利则为势利之有力者收去。方今两途之有力者,孰有过于我吴者哉?弟孑然一身,其谁与侣?即有侣,亦衰耄之朋、方外之士耳。人方欲竦我讪我以自明,而我又不忍舍斯人以为与,且欲以绵薄之力,障两途之狂澜,以待后进中之良心未丧者……假我数年,脚跟立得稍稳,而风俗倘难力廻,亦不难抽身,就贵境之仁贤矣。”(《惕若斋集》卷二,《寄邓太史定宇年兄书》)管氏甚至断言浙西吴中地区“非振铎之地”,进而为自己遁入禅门寻找借口:“故权修檀度于禅门,此愿学孔子之变局也。”(同上,《寄涂光禄念东年兄书》)浙西、吴中与浙东及其周边地区的人文环境差异之大并引起士人不满之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正因为近世以来的“浙学”中心一直在浙东,故常有浙东学者前往浙西讲学或者浙西学者跨江来求学的,如董澐、董穀父子乃王阳明的浙西高足,陈确、张履祥等为刘宗周之蕺山学派在浙西的主要传人③。所以尽管浙西在思想原创性上难以与浙东比肩,但在学术传承上,却仍有与浙东一脉相承的学派源流。仍以阳明学为例,除董澐父子外,尚有倾心阳明的徐孚远、蔡汝楠以及为韩贞遗稿作序的余尚友等。徐孚远对浙西地区民风颓靡、学术潦倒的情形感触极深,而对好友绍兴人张元忭为中兴学术事业所做的努力则赞许备至,曰:“吾乡习俗颓靡,朋友寥落,莫有甚于此时。如吾兄挺然卓立,逈出尘表,真弟所敬服,弟所倚赖也。”(《敬和堂集》卷五,《简张阳和年兄》)而余尚友则干脆自称是阳明的“浙西后学”(《颜钧集》,第167页)。故陶望龄代左景贤写的《潜学编序》称:“夫文成之后,驾其说以行浙之东西者多矣。”(《歇庵集》卷三)又谓:“当正、嘉间……先生之教始于乡而盛于大江以西。”(同上卷六,《修会稽县儒学碑记》)此处所说的“大江以西”乃取广义的“浙西”概念,包括安徽的宁国地区。而若就广义概念而言,阳明学在浙西的传播也许并不亚于浙东④。即使就狭义概念来说,阳明学在浙西也有不少传播的机会与运动,如嘉靖十六年,阳明后学沈谧曾在嘉兴文湖建书院,祀阳明,“同志与祭天真者俱趋文湖,于今益盛”(《王阳明全集》,第1333页)。文中所说的“祭天真者”,即在杭州天真书院参与讲会活动的阳明学者。如果把天真书院的讲会活动也算作浙西的话,那么甚至可以说,阳明去世后的浙江学术中心,不在浙东,而在浙西。但即便如此,“浙学”所表现出的“东”强“西”弱之特点,仍是无法回避的事实,这在其宋以后的学术流脉中反映得尤为显著。
众所周知,秦汉以前的浙江学术在整个中华文明史上并不占主导地位。东汉以降,浙江学术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涌现出一批著名的思想家和独具风格的学术流派,不过这在不少学者眼里都只能算作“浙学”的萌芽期。“浙学”的真正形成,当在北宋,南宋以后趋于繁荣,明清时期则可谓“浙学”的鼎盛期。
北宋中期的庆历、皇祐年间,浙江学者与北方传来的理学发生了首次碰撞。这一时期的浙江地区先有以明州“杨杜五子”为代表的一批学者与理学先驱之一的胡瑗及其“湖学”在学术和教育上互相呼应,继有永嘉学者林石等人对“湖学”的积极追随和传播。正是由于后者的努力,才在很大程度上为稍后“洛学”、“关学”在永嘉地区的广泛传播奠定了基础。把理学思潮全面而广泛地引入浙江的是继林石等人而起的“永嘉九先生”。他们是“洛学”、“关学”在浙江的主要传播者。由于九先生在接受“洛学”的同时,还受到“关学”甚至王安石“新学”的影响,加之浙东地区原本就有的十分浓厚的求实致用学风,所以使得他们并不满足于对师说的简单因袭和传承,而是在某些方面表现出与正统“洛学”的明显差异。他们的这种既传承师说又不拘泥师说,既传播一学又不局限一说的学术理念,对后世“浙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从一定意义上说,南宋乃至明清时期浙江地区各种学术思想的风涌而起,均导源于此。
南宋中期,“浙学”进入全盛阶段,在短短的几十年中,涌现出一大批著名学者,形成了诸多各具特色的学术流派,如温州地区有“郑氏之学”、“平阳之学”、“永嘉事功之学”,婺州地区有“吕学”、“永康之学”、唐氏“经制之学”,明州地区有“四明之学”,等等。这些“浙学”之分支与理学的关系,可谓形态各异,质地纷呈。它们有的受到理学思潮的影响,有的成为理学的主要派别,有的则以强烈的反理学姿崭露头角。因此这一时期的“浙学”与理学之间是既全面融合又互相冲突的局面,而且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南宋后期,甚至影响了“浙学”在元代及明初的走向。
一方面,那些一度与理学分庭抗礼的学派在南宋后期走向衰微,使得“浙学”在总体上呈现出向理学尤其是逐渐占统治地位的程朱理学全面会归的态势,以至在众多的朱子后学中,不少所谓“醇正”的支流都出现在浙中。诚如《宋元学案》所言:“晦庵生平不喜浙学,而端平以后,闽中、江右诸弟子,支离、舛戾、固陋无不有之,其能中振之者,北山师弟为一支,东发为一支,皆浙产也。”(卷八十六,《东发学案》)所谓“北山一支”,是指南宋后期至元初兴起于婺州地区的“金华朱学”,又称“北山四先生”。因其较多地保留了正统朱学的色彩,故被后世视为朱学嫡脉、理学正宗。所谓“东发一支”,是指明州学者黄震,他既是宋末朱学在浙东地区的主要传人,又以修正程朱理学而著称。无论“北山”还是“东发”,在传承程朱之学的同时,都有创新与发展。除了金华朱学和东发之学外,在南宋后期,永嘉地区的学者也逐渐背离了叶适的事功之学,而走上了追随程朱理学的道路,如这一时期永嘉最著名的两位学者叶味道和陈埴都先后接受了朱学,并以积极传播朱学为己任。
另一方面,活跃于明州地区的“四明四先生”却高举“陆学”的旗帜,与程朱之学相抗衡。四先生虽总体上都属心学之范畴,但对心学的理解和发挥却存有差异,由此而显示出他们的不同思想特质。如杨简公开引进佛家思想,并把心学进一步推向极端化的“唯我论”路径;袁燮积极吸收婺州、温州等地事功之学,侧重于政治伦理的挖掘与发挥,而把心学向“笃实”的方向引进;舒麟在竭力调和朱、陆学说的同时,将玄虚的心学移向平实的日常生活;沈焕则“辨论古今”,力求心学能开物成务,已初显出心学化之史学的思维向度。从心学演变的轨迹看,四先生不仅运用各自的影响力把浙江心学朝着不同的方向引进,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为后来的王阳明对心学的全面而彻底的改造创造了条件、奠定了基础,并且为明中后期浙中王门的展开提供了可以利用的思想资源。
在南宋“浙学”发展过程中,吕祖谦曾发挥过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与陈亮、朱熹、张栻、陆九渊等讲学论道、往复辩难,共同营造了浙中良好的学术氛围。吕学有兼摄朱、陆之特点,其融入朱学的大致情形,大致可分为二:一传于金华,一入于宁波;前者经“北山四先生”而至明初宋濂、王袆、方孝孺,后者经王应麟、胡三省而至明初郑真。而其融入陆学的基本脉络,则可从“四明四先生”那里找到衍变的轨迹。四先生与吕氏兄弟的关系均甚为密切,他们的心学理念与其说是直接传承于江西陆学,倒不如说是通过吕学而与陆学相链接。从这一意义上说,浙东心学实际上从一开始就整合了浙东史学的思想因子。盖“浙学”之初兴实由经而入史,及其衰也,又往往由史而人文;而心学之兴盛,则实开其中兴之局面矣。
明代中叶的王阳明学说,便产生于宋代以来浙东丰厚的文化土壤之中。邵廷采说:“浙东承金华数君子后,名儒接出;正德、嘉靖之际,道统萃于阳明。”(《思复堂文集》,第52页)尽管阳明心学具有很大的原创性,与南宋浙东心学派之间并无任何可以考索的渊源关系,但就某种学术的本质精神而言,王学之起亦可谓承浙东心学派之余烈,因此在某种意义上亦可视之为浙东心学派的复兴。阳明以后,浙江学术基本上是由王学或同属心学系统的湛学一统天下,然其走向在浙东与浙西又有区别。
浙东可分为王学极端派、王学稳健派和王学修正派。极端派有王畿、万表、周汝登及陶望龄兄弟,浙西的董澐父子、管志道甚至袁璜亦属此派。其时“俗学宗传注,王学宗‘四无’”(同上,第126页)。而“四无”说的首创者王畿,不仅在浙东地区讲学传道,而且还在浙西地区广授门徒,就连张履祥亦受过其影响。稳健派有徐爱、季本、钱德洪、孙应奎、程松溪、王宗沐等。其中永康人程松溪“早受文成之教,晚及湛翁之门”,“用功有实地”,而与乡里先哲陈亮相链接(庐屏等编:《明礼部尚书程文德文史选》,第9-14页)。修正派有黄绾、张元忭、刘宗周、毛奇龄、潘平格、陈确、黄宗羲等,其中除潘平格、陈确属浙西籍外,大都为浙东籍。该派的特点是立足于阳明而批判王学末流,进而修正阳明本身,使心学化的史学实学倾向更加凸显。他们批判王学末流的武器不是朱学,而多为浙东固有的实学之传统;其“务崇躬行,砥实践”,较之稳健派又有“更多发明”(《思复堂文集》,第48页)。
浙西可分为湛王折中派和王学反对派。湛王折中派有蔡汝楠、许孚远、唐枢、钱薇等⑤。这些人组成了甘泉学派的重要分支,使岭南心学与浙中心学相衔接。王学反对派又可分为两支:一是刘宗周在浙西的传人如张履祥、吕留良、陈确等。该派与湛王折中派联系紧密。宗周曾从学许孚远,“侍杖屦蔡月余,终身守师说不变”(同上,第18页)。二是站在朱学立场上批判王学的顾应祥⑥、陆陇其、陆世仪、顾炎武等。比较而言,宗周传人大都由王学摄取朱学,故对阳明本人尚多加肯定;而顾应祥等人则立足于朱学,不仅批判阳明后学,而且直指阳明本人。
概而言之,阳明以后的浙江学术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浙东心学从修正王学而走向实学与史学,而浙西心学则是从折中王湛而走向朱学。二是越靠近吴地,朱学的影响力就越大,吴中东林学派虽亦有调和朱王之倾向,但较之浙西的王湛折中论者在王学倾向上已大为逊色。三是作为介于浙东、浙西间的关键性人物刘宗周,其影响力曾横跨钱江两岸,对提升浙西的学术地位功不可没。四是杭州作为浙东之学与浙西之学的缓冲地,是两边学者聚会讲学的重要场所,故在学术性格上,浙东学风与浙西学风兼而有之。五是如果说明代以后的“吴学”是以放弃宋学而返诸汉学为趣向,“皖学”是以宋、汉同弃而寻归传统儒学为诉求,那么“浙学”便可以说是以明学为基点而融会宋学与汉学。
注释:
①“三吴”之称,历代所指不一。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浙水》:“汉高帝十二年,一吴也,后分为三,世号‘三吴’。吴兴(治今湖州)、吴郡、会稽其一焉。”唐指吴兴、吴郡、丹阳。宋以后则指常州(吴上)、苏州(吴中)和湖州(吴下)。其中浙西之湖州一直属“三吴”之一,然称“吴下”,则在宋明时期。
②详见拙稿《“浙学”的东西异质及其互动关系》,《杭州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
③据董玚《蕺山弟子籍·学人》,刘宗周不同时期弟子学人有姓名籍贯可考者共计145人,其中浙东籍的约占五分之三,而浙西籍的也不算少,共有38人(《刘宗周全集》第5册,台北,中央研究院文哲所1997年,第719-721页)。
④据清人赵绍祖《赤山会约跋》:“自姚江之学盛于水西,而吾泾各乡慕而兴起,莫不各建书屋,以为延纳友朋、启迪族党之所,其在台泉则有云龙书屋,麻溪则有考溪书屋,赤山则有赤麓书院,蓝岑则有蓝山书院。一时讲学水西诸前辈,会讲之暇,地主延之,更互往来,聚族开讲。”(《丛书集成初编·证人社约及其他五条》,民国二十五年刊)如此讲学之盛况,在当时的浙东地区并不多见。
⑤浙西儒者尤好甘泉学(如沈佳的《宋明四子书》,合濂溪《通书》、明道《定性书》、白沙《自然书》、甘泉《心性书》于一体,嘉靖三十四年张淙刻于浙西,廖宪刻于增城,张潮为之序〔《性命圣理学汇函》,《中国子学名著集成》,台北,1978年〕),并通过甘泉学而与程朱相链接。
⑥顾应祥虽“少受业于阳明”,但他不仅批评王阳明、王畿,还批评湛若水、黄绾,其所著的《惜阴录》,属于浙西阳明学者最重要的理论著作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