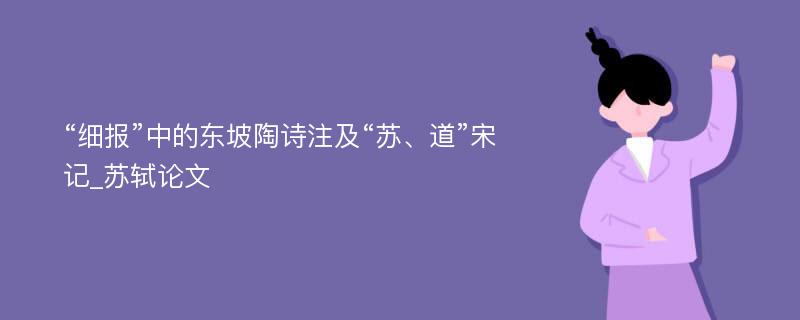
《精刊补注东坡和陶诗话》与苏轼和陶诗的宋代注本,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坡论文,诗话论文,宋代论文,苏轼论文,补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的提出 苏轼创作的和陶诗不但强化了陶渊明在中国文学史上的经典地位,而且也开创了一种新文类,自此之后,和陶诗的创作连绵不绝,成为中国文学、文化史上的独特景致。东坡和陶诗在宋代就已单独成集并刊行于世,苏辙《子瞻和陶渊明诗集引》载东坡语云:“吾前后和其诗凡百数十篇,至其得意,自谓不甚愧渊明。今将集而并录之,以遗后之君子,子为我志之。”①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又载:“公诗本似李、杜,晚喜陶渊明,追和之者几遍,凡四卷。”②此集现仍存,即宋黄州刊本《东坡先生和陶渊明诗集》四卷,③保存了宋代东坡和陶诗的原貌。千百年来,对东坡和陶诗的评论与研究蔚为大观,但鲜有学者论及宋代的东坡和陶诗注本,这可能缘于资料的缺失。但随着域外汉籍研究的推进,这一点目前得到了解决。 南宋施元之、顾禧、施宿所著《注东坡先生诗》(下简称施顾注)卷四十一、四十二所载东坡和陶诗注,是目前存世最完整的宋代和陶诗注。一段时间以来,人们也一直以为这可能是惟一保存至今的宋人和陶诗注本。不过,最近由宋元之际遗民蔡正孙所编的《精刊补注东坡和陶诗话》(下简称《诗话》),在韩国被发现,这极大地改变了学界对宋代和陶诗注本的认知。这部书保存了三种宋人的和陶诗注本,即傅共《东坡和陶诗解》、蔡梦弼《东坡和陶诗集注》,以及蔡正孙本人的评注。现在可见的宋人所编的和陶诗注本达到了四种。这四部注本,除施顾注文本比较完整外,其余三部皆为残本,但蕴含着极大的学术与文献价值。同时,这四部注本都是所谓的宋人注宋诗,体现出本朝人对苏轼和陶诗的见解与研究。 二、施元之、顾禧、施宿《注东坡先生诗》中的和陶诗注 宋黄州刊本《东坡和陶诗》共收和陶诗109首,书前所载苏辙《子瞻和陶渊明诗集引》引苏轼语亦云:“吾前后和其诗,凡一百有九篇。”可见苏轼本人编定的和陶集有109首,而施顾注收和陶诗107首,较宋刊《东坡和陶诗》少2首。施顾注和陶诗采用了与宋代苏轼和陶诗单行本(施顾注中称为“集本”)不同的底本,大量利用了当时所存的东坡诗的石刻文献,④保存了和陶诗的诸多异文,如卷四十一《和归园田居六首》题下注云:“东坡曾孙叔子名岘,刻所藏真迹于泉南舶司,间与集本不同。所作类多晚岁,当是集本有误,今从石本。”在注文中,也不时见到施顾用石本与集本校勘的文字,如卷四十一《和咏贫士》其四“典衣作重九”,注云:“石刻作九,集本作阳”;“徂岁惨将寒”注云:“石刻作岁,集本作暑”,“石刻作将,集本作夕”。 施顾注苏诗包括题下注与诗句注两部分。题下注主要是对诗题中牵涉到的人物生平进行考证,已有学者考证清楚,题下注为施宿所作。⑤因为是宋人所作,其史料价值也特别大,如卷四十一《和岁暮作和张常侍》,东坡自序中有“时吴远游、陆道士皆客于余”,施宿有一段比较长的注释: 吴远游,名复古,字子野,事见三十八卷《次韵子由赠吴子野先生》诗注。陆道士,名惟忠,字子厚,眉山人,始见东坡于黄州。惟忠作诗,论内外丹,自以为决不死。坡告之曰:子神清而骨寒,其清可以仙,其寒亦足以死。后十五年,复见于惠,曰:吾真坐寒而死矣。绍圣四年,卒。坡为铭其墓。坡尝以文祭张安道云:某于天下未尝志墓,独铭五人,此盛德故。如惟忠、吴远游辈于公困厄流离之中,追随不舍,如惟忠不幸而死,故独得公为铭以垂千载,是亦可谓知所托矣。这段对诗序中出现的两个人物—吴远游与陆道士—进行了扼要介绍,并对其人格也有所表彰,强调他们在东坡在“困厄流离之中,追随不舍”。通过这段注文,我们再读东坡的原诗,在诗意理解上才会更深一层,才能体会到东坡诗中所言的“二子真我客,不醉亦陶然”⑥的涵义。 有的题下注也对诗歌背景加以介绍,如《和饮酒二十首》其十一注云: 元祐七年五月,先生守扬州,上奏曰:“今大姓富家为市易所破,十无一二,其余小民大率皆有积欠。守令督吏,文符日至其门,鞭笞日加其身。虽白奎、猗顿,亦化为荜门圭窦矣。近者诏旨,凡积欠皆分为十料催纳,通计五年而足。而有司以谓有旨,倚阁者方指挥。臣亲见两浙、京西、淮南之民,皆为积欠所压,日就穷蹙。本州于理合放,而于条未有明文者,且令权住催理,听候指挥。伏望特留圣意,深诏左右大臣,早赐果决行下。”六月十六日又上奏曰:“今夏田一熟,民于百死之中,微有生意,而监司争言催欠。臣敢昧死请内降手诏,应淮南东西、浙西诸般欠负,不问新旧,特与权住催理一年。”此诗所述,盖是得请故也。原诗中出现了“积欠”一词,施顾注引用了苏轼在扬州太守任上向哲宗上的两封札子,即《论积欠六事并乞检会应诏四事一处行下状》、《再论积欠六事四事札子》来解释此诗写作的背景。读完施顾注后,不只对此诗产生的语境有所了解,亦可以看到东坡仁民济世之心,正如清人温汝能所云:“观其忠君爱民之心,蔼然溢出于言表,虽古之大臣,亦无以过也。”⑦ 诗句注采取的是李善注《文选》的方式,即注重对出典的勾稽。从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施顾注的一个特点就是引用东坡本人的作品来证其诗,再如《和己酉岁九月九日》“今日我重九”,就引东坡《杂说》中“海南气候不常,有月即中秋,有菊即重阳”来注之。施顾的诗句注有时将苏诗与当时的政治联系在一起,如《和羊长史》末句“稍欲懲荆舒”,注云:“王安石初封荆国公,后封舒王。”关于“荆舒”到底指谁,清人冯应榴认为“荆舒”指海南人,并认为施顾注“似非诗意”。⑧不过宋人施德操早已指出:“介甫既封荆公,后遂进封舒王,合之乃荆舒。故东坡诗曰:‘犹当距杨墨,稍欲懲荆舒。’”⑨纪昀评《苏文忠公诗集》卷四十二亦云:“结指半山。”如果结合此句上文“犹当距杨墨”,即可看出施顾注是准确的。 施顾注不但注解详赡,学理性强,而且还能揭示苏诗创作的背景与诗句的内涵。⑩施顾注苏轼和陶诗与其注坡诗的整体风格是一致的,清人对施顾注评价甚高,顾嗣立言其“尤得知人论世之学”,又张榕端特别表彰了题下注:“又于题下务阐诗旨,引事征诗,因诗存人,使读者得以考见当日之情事。”(11)以此来评论其注和陶诗亦不为过。 三、傅共《东坡和陶诗解》的解诗特色 傅共著《东坡和陶诗解》(下简称《诗解》)可能是最早的一部宋人所著的东坡和陶诗注本。傅共,字洪甫,号竹溪散人,仙溪(今福建仙游)人,约为两宋之际人,主要活动于南宋初年。福建仙溪傅氏家族是宋代一个专门研究苏轼的世家,同是仙溪傅氏的傅藻著有东坡的年谱《东坡纪年录》,以及傅共族子傅斡著有《注坡词》。(12)《诗解》在宋代就已刊刻并流传,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五著录:“《和陶集》十卷,苏氏兄弟追和,傅共注。”又李俊甫《莆阳比事》卷三:“傅共注释《东坡和陶诗解》。”全书虽已亡佚,但蔡正孙《诗话》大量援引了傅共的《诗解》,(13)可以从中一窥《诗解》的原貌与特色。 从蔡正孙的引录来看,《诗解》原书可能是在东坡的和陶集基础上校注而成的,不仅有二苏的和陶诗,还附有陶诗原文,甚至还有傅共对陶诗的校勘。《诗解》的主体部分是对和陶诗的注释。傅共《诗解》中的和陶诗文本可能异于当时的传本,《诗话》卷二东坡《和连雨独饮》中有“误入无何乡”一句,蔡正孙云:“傅仙溪本作‘无功乡’,注云:‘唐王绩,字无功,有《醉乡赋》。’”这些异文,保留了南宋初年东坡和陶集某个版本的面貌。 比较有特色的是,《诗解》记载了傅共本人实地考查东坡故居的行迹。《诗话》卷一《和时运》,傅共注云:“予尝游白鹤峰,公之故居旧基依然,峰颠乔木数本参天,其北下瞰长江之潭,岸傍巨石可容数人布坐。”东坡于绍圣元年(1094)十月贬谪到惠州,先住在合江楼,不久迁入嘉祐寺;绍圣三年三月,又迁于合江楼,同时开始营造白鹤峰新居,次年三月建成。但入住不久,东坡就被贬到儋州。东坡白鹤峰故居在两宋之际的战乱中并没有遭到损坏,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四十六引洪迈《夷坚志》云:“绍兴二年,虔寇谢达陷惠州,民居官舍,焚荡无遗。独留东坡白鹤峰故居,并率其徒葺治六如亭,烹羊致奠而去。”但到傅共时代,就已经只剩下“旧基”了。南宋时的宋人注唐诗或注宋诗中,开始出现注者踏访实地,以本人亲自经历注释诗文的现象,如李壁《王荆公诗注》利用出使金朝以及被贬至王安石故乡临川的经历来注释王安石诗,谢枋得《注解章泉涧泉二先生唐诗选》也多次以“余”的口吻,穿插其本人实际考察的见闻来注唐诗。(14)这是宋人集部注释的一种创新,也体现了宋人的求实精神。(15) 傅共《诗解》文字训诂的内容比较少,但也有一部分对和陶诗的语意解释或背景介绍,如《诗话》卷四《和胡西本曹示顾贼曹》中有“长春如稚女”一句,傅共注云:“长春,一名月季花,晕红如人饮酒颊。此花盛冬亦开,不畏霜雪。”按苏诗宋注,如王十朋的《集注》以及施顾注皆未解释“长春”,清查慎行《苏诗补注》卷四十二云:“长春,按《本草》,金盏草,一名长春花,言耐久也。但金盏花色深黄,今诗云‘卯酒晕玉颊,红绡卷生衣’,乃是红色,当另是一种。”此花,清人已不详,作为宋人傅共的此注,颇有参考价值。又《诗话》卷一苏辙和《劝农》,傅共注云:“海康之俗既不耕稼,而闽人多以舟载田器,寓居广南,耕田不为长久之谋,但为二三岁之计。”苏辙诗历来无注,傅共之注对苏辙之诗的背景揭示尤为重要。 《诗解》中最多的内容是对和陶诗诗意的阐释。《诗话》卷五东坡《和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渊明堕诗酒,遂与功名疏”,傅共注云:“汉末天下三分,而吴有江左。及晋室永嘉南迁,其后刘裕擅命。晋遂微弱,而裕乃兴宋,故曰‘强臣擅天衢’。渊明以刘裕移晋祚,遂不复仕,故曰‘与功名疏’。”此解深得陶苏二人之心曲。傅注和陶诗并不以旁征博引见长,其注简洁明了,但对诗意理解作用颇大。 四、蔡梦弼《东坡和陶诗集注》的苏轼和陶诗阐释 蔡梦弼,字傅卿,号三峰真逸、三峰樵隐,建安(今福建建瓯)人。据俞成《校正草堂诗笺跋》称,梦弼“生平高尚,不求闻达,潜心大学,识见超拔,尝注韩退之、柳子厚之文,了无留隐。至于少陵之诗,尤极精妙。”蔡氏著有《东坡和陶诗集注》(下简称《集注》)及《杜工部草堂诗笺》四十卷。《集注》未见著录,南宋史铸等编《百菊集谱》卷四《历代文章》注中提到“近年蔡梦弼有《注和陶诗》”,元李公焕《笺注陶渊明集》卷二《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引到“蔡注”,旧题王霆震《古文集成前集》卷七十一前癸集二录苏轼《和渊明归去来辞并引》,也提到“三峰蔡梦弼注”。引用《集注》较多的是蔡正孙的《诗话》,凡有12则。(16) 蔡梦弼生平不详,但从《集注》的注文中隐约可见其思想倾向。《诗话》卷八苏轼《和拟古九首》其二云:“有酒从孟公,慎勿从扬雄。”蔡氏注云: 此诗言隐遁之士不以名宦为贵,如竹林诸贤不数山、王二公,以其宦达故也。故我宁从孟公而不从扬雄,虽二公俱好饮者,然孟公放达,恬于势利;子云逼仄于篡逆之朝,既为之臣,又颂美之,其事皆君子所羞道,如元规之尘污人也。盖人生所贵大节,大节一丧,则其余无足观。子云之俯仰可怜,岂亦未能忘情于穷通丰约之间乎?不然,何其甘于豢养而不知退也?南宋之前,古人对扬雄基本上持正面的评价,虽然扬雄写过《剧秦美新》,投靠过王莽,但古人多能持一种同情之了解的态度。《汉书·扬雄传》载其自序云:“家产不过十金,乏无儋石之储。”后人对扬雄贫而好学,雅咏不辍,如左思《咏史》:“寂寂扬子宅,门无卿相舆。”(17)北宋人对扬雄亦多称赞,如张咏《送张及三人赴举》:“才雄扬子云,古称蜀川秀。”(18)刘攽《寄王深甫》:“昔有扬子云,著书恬势利。”(19)苏颂《七言二首奉答签判学士》:“屈指当时文学士,谁知扬子思湛深。”(20)苏轼这首和陶诗虽然对扬雄有点微词,但对其批判并未上升到道德或气节的层面,苏轼其实对扬雄并无恶感,其《复次韵谢赵景贶陈履常见和兼简欧阳叔弼兄弟》曾云:“能诗李长吉,识字扬子云。”(21)苏辙《次韵答张耒》也说:“欲学扬子云,避世天禄阁。”(22)但到南宋之后,宋人尤其是理学家对扬雄开始有了非议。朱熹在《资治通鉴纲目》卷八上特书一条“莽大夫扬雄死”。这是一种“春秋笔法”,也代表一种道德立场,从此也影响到宋人在道德层面对扬雄的判定。如刘克庄《汉儒》其一云:“执戟浮沉亦未迂,无端著颂美新都。白头所得能多少,枉被人书莽大夫。”(23)此诗亦见于于济、蔡正孙编《唐宋千家联珠诗格》卷十七,蔡正孙评此诗云:“雄作《剧秦美新》一篇以谀王莽”(24),同时也引用到朱熹《通鉴纲目》中的话。蔡梦弼生活于南宋中后期,他所言“人生所贵大节,大节一丧,则其余无足观”之语明显受到朱子学的影响,这应是《集注》特色之一。 与此相关的是,《集注》解诗亦特别注重从东坡的人格角度来阐发诗意。《诗话》卷八苏轼《和拟古九首》其八“城南有荒池,琐细谁复采。幽姿小芙蕖,香色独未改。欲为中州信,浩荡绝云海。遥知玉井莲,落蕊不相待。攀跻及少壮,已失那容悔”,蔡氏注云: 此诗因芙蕖以起兴,言海峤之外,荒僻之邦,人士所不到,而乃有此华,可以为中州之信。公盖自喻抱负芳洁,求忠于君,而隔绝云海,无路以自通也……公少年筮仕即有尘外之趣,其见于诗文者,未尝不欲归休求道,而不幸罹于世故,不早自拔,自伤迟暮,不获遂所求。纪昀《苏文忠公诗集》卷四十二评此诗云:“此首纯乎古音,绝无本色。”其意指,东坡此诗不用典实,不以学问为诗,全然用《诗经》的比兴手法,“幽姿小芙蕖,香色独未改”,分明是在自喻。蔡梦弼对此诗的解释非常准确,既看到了东坡以芙蕖“起兴”,又看到东坡以此“自喻抱负芳洁”。对照清人的解释皆执著于诗艺,而蔡氏的评释则能透过纸背,阐发东坡诗中的隐喻。这种阐释方式与他阐释杜诗非常相似,《杜工部草堂诗笺》卷一注《望岳》“会当临绝顶,一览众山小”云:“登临山之绝顶,俯视众山,其培欤?众山知尊乎?泰岳众流知宗乎?沧海当安史之乱,僣称尊号,天子蒙尘,其朝宗之义为如何?甫望岳之作末章之意,固知安史之徒乃培之细者,又何足以上抗岩岩之大者哉?”这里,蔡氏认为培是安史叛军之喻,俯视众山则隐喻着天下朝宗的忠义之心。可见蔡氏解诗比较注意揭示诗歌意象后的隐喻之意。 又《诗话》卷九苏轼《和杂诗十一首》其五“孟德黠老狐,奸言嗾鸿豫。哀哉丧乱世,枭鸾各腾翥。逝者知几人,文举独不去。天方斫汉室,岂计一郗虑。昆虫正相啮,乃比蔺相如。我知公所坐,大名难久住。细德方险微,岂有容公处。既往不可悔,庶为来者惧”,蔡氏注云: 此诗言(孔)融之遇祸,直以资性刚直,负其高气,而又有海内重名,故不容于奸雄之朝……公平生慷慨大节与其刚大不屈之气,大略似融,故每喜称道之。而一时遭罹口语,为小人怨疾构陷,以至得罪窜斥,流离岭海,其遇祸亦大略相似,故作此以自警云。这段评论亦是从东坡的性格来论诗,观察也非常准确。纪昀《苏文忠公诗集》卷四十三亦云此诗“以孔融自比”,王文诰《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卷四十三同样认为“此以孔融自慨”,蔡氏的论断则在清人之先。 蔡梦弼的注解以诗意阐发为主,文字一般都比较长,如《和陶咏荆轲》一诗的注文长约六百字,仿佛一篇小型的史论: 此诗言秦之事无异于晋,自不韦货楚、牛金生睿,统绪固已中绝,而国非其国矣。但天欲厚其毒而盈其恶,故必待其穷凶极暴而殄灭之。使始皇能早定扶苏之位,则无后日之事矣。然天欲亡人之国,其事盖有出乎意料之外者。以李斯之才,始皇用之以一天下。沙丘之崩,受遗托孤,疑若可以保子孙万世帝王之业矣。死未旋踵,乃与阉宦舍谋矫诏,杀扶苏而立胡亥,卒以亡秦,此岂人力也哉!盖天假手于斯以灭之耳。使燕丹能以一朝之忿而听其傅鞠武之方,招合贤俊,修明政事,分遣说客,阴定六国之从,如韩、魏之裂智伯,则秦可亡,燕可复,孰与驰一介之使,入不测之秦,挟尺六匕首,而欲以强燕而弱奏哉?此愚夫愚妇之所不为,而丹易行之,所以可为悲恨也。荆轲之事,固无足言。以田光之老且贤,而乃始创此谋,然则古称燕、赵多奇士,则亦徒有虚名而已,奇安在哉?夫以秦政之凶暴,杀所生父吕不韦而迁其母于雍,此岂天道之所可容?使丹能保其国家,徐以待之,则秦室覆亡之祸,不待沛公入咸阳、项羽杀子婴,而固已见其兆矣,何必信狂生之谋,捐一旦之命,而轻以社稷尝试,一掷于艰难不可必成之事也哉!且以三户之楚,尚足以亡秦,况我列城数十,岂不能有所为邪?然荆、高虽死,犹足以动秦政之惧心,而加以警卫。使后世读其书者,莫不为燕叹惋,而惜二子之无成,亦可以见天理之所在,而秦之无道,虽去之千载,而人心犹未忘也。苏轼此诗的艺术手法,宋人多有好评:“诗人咏史最难,须要在作史者不到处别生眼目,正如断案不为胥吏所欺,一两语中须能说出本情,使后人看之便是一篇史赞,此非具眼者不能。自唐以来本朝诗人最工为之,如张安道《题歌风台》,荆公咏范增、张良、扬雄,东坡《题醉眠亭》、《雪溪乘兴》、《四明狂客》、《荆轲》等诗皆其见处高远,以大议论发之于诗。”(25)也就是说,苏轼此诗之妙即在于别具只眼,“别生眼目”,立论与前人不同,甚至可以说采用了翻案手法。苏轼《和咏荆轲》与陶渊明《咏荆轲》在思想意识上明显不同,陶渊明对荆轲基本上是礼赞的态度,而苏轼则认为荆轲是“狂生”,“不足说”,持否定性意见。(26)同时,好的咏史诗亦如一篇“史赞”,寓“大议论”于诗,东坡《和咏荆轲》可谓这方面的杰作。蔡梦弼此段评论是对东坡此诗的详细阐释,将东坡要表达的意思比较透彻地表达了出来。其贯穿的逻辑是:秦之灭亡是必然的,所以必须彻底暴露其罪恶,最后天假李斯之手灭亡秦朝。燕太子丹任用“狂生”荆轲,而不是“招合贤俊,修明政事,分遣说客,阴定六国之从”,故其失败亦“天理”之必然。东坡此诗对燕赵“奇士”太子丹、荆轲进行了解构,其立论并没有历史的必然性,或“天理”的价值判断在其中,而蔡梦弼的解说则可能受到理学的影响,一直在强调“天”或“天理”的作用。 总之,蔡梦弼的和陶诗阐释受到理学影响比较大,同时又能以意逆志,从东坡的人格性格来阐发诗意。 五、蔡正孙《精刊补注东坡和陶诗话》对和陶诗的研究 蔡正孙(1239~?),字粹然,号蒙斋野逸,又号方寸翁,福建建安(今福建建瓯)人。他是宋元之际一位非常有特色的诗学批评家,著有《诗林广记》、《唐宋千家联珠诗格》、《精刊补注东坡和陶诗话》。《诗林广记》在中国流传甚广;《联珠诗格》则在中国失传,然有朝鲜及日本的翻刻本及注本;唯《诗话》仅流传于韩国。《诗话》凡十三卷,目前仅存部分目录、卷一至卷五(其中卷五亦有残缺)、卷八(残)、卷九至卷十三(卷十三缺《联句》诗及注)。卷一至卷十二皆是对陶诗及苏轼、苏辙和陶诗的注释及评论,卷十三是对苏氏昆仲未和的陶诗的评注。虽然《诗话》已非完本,但此书作为目前存世最早的和陶诗注释与评论专书,很值得研究。目前已有学者对此书的内容与文献价值作了研究,而关于蔡正孙对和陶诗的研究则未见探讨。蔡氏对和陶诗的研究略可以分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对和陶诗创作背景的介绍。 苏轼最早于扬州太守任上开始创作和陶诗,后于贬谪惠州与儋州时进行大规模创作。宋人所编的苏轼年谱已对东坡诗作初步编年,如傅藻《东坡纪年录》对部分苏轼和陶诗进行了系年,施宿所编《东坡年谱》分为纪年、时事、出处、诗四栏,最后一栏“诗”的部分即有对若干首和陶诗的系年。蔡正孙《诗话》也尽量根据诗意揭示每首诗的创作背景。施宿《东坡年谱》未系年或佚失的部分可以参考《诗话》补足,对照清人及今人的研究成果,《东坡诗话》的系年基本无误。如《和乞食》一诗,施宿《年谱》未系年,《诗话》谓“此诗在儋耳作”。按:查慎行《苏诗补注》卷四十二编此诗于元符元年、二年卷中,并谓此诗作于儋州。金甫暻《苏轼“和陶诗”系年表》(27)定在元符元年十月前后。东坡居儋时间为绍圣四年七月至元符三年六月,可见《诗话》系年是准确的。两者系年结论不同之处,参考其他文献,则可以确定《诗话》的判断是准确的,如《和九日闲居》,施宿定在绍圣三年,而《诗话》谓“此诗在儋耳作”。按:傅藻《东坡纪年录》系此诗于元符元年。查慎行《苏诗补注》云:“诗中有‘登高望云海’之句,故知此诗为海外作。”并将此诗系于绍圣四年。孔凡礼《苏轼年谱》则系于元符元年,亦作于儋州。施宿定为作于惠州,则不确。 (二)对和陶诗典故的补注。 傅共《诗解》及蔡梦弼《集注》皆有对和陶诗典故的注释,但仍有大量未注之处,《诗话》皆予以补注。施顾注和陶诗最为详尽,《诗话》多有可补施顾注之处。如《和劝农》“云举雨决”,施顾无注,《诗话》注云:“汉武帝时,赵中大夫白公,奏穿渠引泾水溉田,名白渠,人得其饶,歌之曰:‘田于何所,池阳谷口。郑国(韩人)在前,白渠起后。举锸为云,决渠为雨。泾水一石,其泥数斗。且溉且粪,长我禾黍,衣食京师,亿万之口。’”又《和形影神·影答形》“我依月灯出”,施顾无注,《诗话》注云:“按《庄子》,影答魍魉曰:‘火与日,吾屯也;阴与夜,吾代也。’‘月灯’之语,盖本诸此。” 有些施顾注比较简略,而《诗话》则非常详尽,如《和归园田居》其五“行歌《紫芝曲》”,施顾注云:“杜子美诗:松下丈人巾屦同,偶坐似是商山翁。怅望聊歌《紫芝曲》,时危惨淡来悲风。”《诗话》则云:“《高士传》云:四皓见秦政虐,乃逃入蓝田山,作歌曰:‘莫莫高山,深谷逶迤。晔晔紫芝,可以疗饥。唐虞世远,吾将安归。驷马高盖,其忧甚大。富贵之畏人,不如贫贱之肆志。’且共入商洛山,以待天下定。杜甫《洗兵马行》云:隐士休歌《紫芝曲》。”《诗话》引用的文献更为原始。 还有一些地方,《诗话》所引文献比施顾注更准确,如《和胡西曹示顾贼曹》中的“卯酒晕玉颜”,施顾注仅引用了白居易诗以明“卯酒”二字,未解释“晕玉颜”,而《诗话》引用的《太真外传》则应是东坡此诗所本,故而更为准确。再如《和移居》“暮与牛羊夕”,施顾注引用了柳宗元的《朝日说》,《诗话》则引用了《诗经·王风·君子于役》“日之夕矣,牛羊下来”,出处更早,更契合诗意。 (三)对和陶诗诗意的阐发。 施顾注和陶诗基本上是释事,而《诗话》可能受到《集注》的影响,除了释事之外,还有释意,有时以“愚谓”形式发表个人对诗歌的认识。如《诗话》卷一《和答庞参军》“功名在子,何异我躬”,蔡注云:“愚谓:此诗末语,亦相勉励之切也。”此诗前有东坡之序云:“周循州彦质,在郡二年,书问无虚日。罢归过惠,为余留半月。既别,和此诗追送之。”东坡寓惠期间,多得友人周彦质的照拂,此诗即分别之后送给周彦质的,对周彦质表示了感激。但从诗中看出,东坡的感戴给人的感觉也是一种君子之交,所以在诗的末尾才会相勉励。纪昀评《苏文忠公诗集》卷四十称此诗:“友朋之谊,君子之言。”所言甚是。其他没有用“愚谓”形式出现的诗意阐释也值得重视,如《诗话》卷三《和示周掾祖谢》“今此复何国,岂与陈蔡邻”,蔡注云:“孔子厄于陈蔡之间,七日不火食。公在儋耳,极海陋邦,忍饥谈道。谓此地岂亦近陈蔡邪?言如夫子之厄穷也。”此处大意的串讲,皆能将坡诗的意蕴解读出来,也很准确。特别是“陈蔡”之典,东坡这里并没有用两处地名,而是用了孔子之典,则知此诗将东坡在儋州生活之困厄与孔子于陈蔡之厄相类比。 与蔡梦弼长篇的诗意阐释相比,蔡正孙的阐释更为平实,以疏理大意为主,对理解东坡的诗意也多有帮助。 六、结语 在蔡正孙《诗话》发现之前,人们一直以清代温汝能《和陶合笺》为惟一的和陶诗注本,现在看来此说不准确。在宋人注宋诗之中,苏诗的注本最多,而其中独有和陶诗在宋代至少有四种注本,可见其在宋代受到的重视与欢迎。何以出现这种现象?笔者揣测可能有以下原因:其一,和陶诗是宋代的“新生事物”。苏轼自己说:“古之诗人,有拟古之作矣,未有追和古人者也。追和古人,则始于东坡。”(28)在苏轼之前或同时,也有一些诗人创作过追和古人的作品,如唐代皮日休、陆龟蒙作有《追和虎丘寺清远道士诗》及《追和幽独君诗次韵》,但诗题中的“清远道士”及“幽独君”的身份成谜;李贺亦写过《追和柳恽》,但并非次韵诗。这些追和古人的作品,一方面数量少,另一方面影响力有限,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说苏轼开创了次韵古人诗歌的传统,亦不为过。其二,与次韵诗的发展有关。宋代是次韵诗发展的高峰期,即如东坡本人二千多首诗歌中,大约三分之一是次韵诗。(29)虽然次韵诗不无文字游戏的性质,但对于以学问见长的宋代诗人来说,次韵诗可能更符合生活在书斋中、喜欢读书的宋人的口味。(30)次韵诗中,和陶诗可以作为学习的范本。蔡正孙本人就非常喜欢创作次韵诗,如他所编《联珠诗格》中收录了他本人的58首,其中标明和刘克庄《梅花百咏》的就有七八首。通过揣摩苏轼和陶诗的艺术成就,对于自己写作次韵诗亦有帮助。其三,与陶渊明在宋元之际隐士、诗人与遗民综合形象的形成有很大关系。在六朝仅以隐士形象示人的陶渊明,在宋代一跃而为六朝最伟大的作家,《逐斋闲览》云:“渊明趋向不群,词彩精拔,晋、宋之间,一人而已。”(31)曾纮亦称渊明“真诗人之冠冕”。(32)宋人甚至认为苏、黄都不如渊明:“东坡豪,山谷奇,二者有余,而于渊明则为不足,所以皆慕之。”(33)蔡正孙之所以特别倾心于陶渊明,与其本人的遗民身份也有很大的关系。(34)将陶、苏这两位文学史上最伟大诗人的诗歌加以合编并注释,具有极大的规范意义与文化意义,这可能是蔡正孙编纂《诗话》的心理动因之一。 本朝人给本朝诗人的某类诗编纂了至少四种注本,这不但在中国文学史上是罕见的现象,在世界文学史上也并不多见,这正可见苏轼和陶诗的魅力。在宋代文学注释史上,出现了多位同一注者同时注释杜甫、苏轼诗的现象,如赵次公著有《新定杜工部古诗近体诗先后解》,同时也有东坡诗注;本文讨论的蔡梦弼,也同时著有《杜工部草堂诗笺》及《东坡和陶集注》。荷兰文学理论家佛克马(Douwe W.Fokkema)认为“文学经典是精选出来的一些著名作品,很有价值,用于教育,而且起到了为文学批评提供参照系的作用”(35),故宋人同时注杜、苏,或陶、苏,也正是为了给宋人诗歌创作提供一个经典性的标的。 目前可见的四种宋人和陶诗注本的注者皆为闽浙之地人,施元之、施宿为吴兴(今浙江湖州)人,顾禧为吴郡(今江苏苏州,在宋代亦属于浙江),傅共为仙溪(今福建仙游)人,蔡梦弼为建安(今福建建瓯)人,蔡正孙亦为建安人。和陶诗注在闽浙产生,除了与两地在南宋时期文化发达,是当时的印刷业中心之外,亦与福建是南宋朱子学的重镇有很大的关系。南宋福建建阳蔡氏,四世九儒,是著名的理学世家,尽管不能确知蔡梦弼、蔡正孙是否与“蔡氏九儒”源出同族,但他们受到理学影响则是不争的事实。《诗话》不但保存了已经失传的傅共《东坡和陶诗解》及蔡梦弼《东坡和陶诗集注》,具有极大的文献价值;而且是文学史上最早的东坡和陶诗专门注本,其价值值得进一步研究。 注释: ①②苏辙:《栾城后集》卷二十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402、1422页。 ③参见刘尚荣:《宋刊本(东坡和陶诗)考》,载《苏轼著作版本论丛》,成都:巴蜀书社,1988年。 ④施宿本人也精通金石碑帖之学,曾撰《大观法帖》二卷(《宋史·艺文志》著录),因此他在注坡诗的过程中,留心石刻文献,并以之为校勘之用,也是其学术兴趣使然。 ⑤参见郑骞:《宋刊施顾注苏东坡诗提要》,载《增补足本施顾注苏诗》前,台北:艺文印书馆,1980年。又刘尚荣:《宋刊(施顾注苏诗)考》,载《苏轼著作版本论丛》。 ⑥元好问对此二句比较欣赏,《遗山先生文集》卷四十《跋东坡和渊明饮酒诗后》云:“另一诗云:‘二子真我客,不醉亦陶然。’此为佳。” ⑦温汝能:《和陶合笺》卷三,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0年,第65页。 ⑧冯应榴辑注:《苏轼诗集合注》卷四十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2179页。 ⑨《北窗炙輠录》卷上,《宋元笔记小说大观》第三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第3303~3304页。又苏轼《仇池笔记》卷上载:“王介甫先封舒公,改封荆公。《诗》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惩。’识者曰:‘宰相不学之过也。’”引《诗》出于《鲁颂·閟宫》,“稍欲懲荆舒”即用此典,可见此句指王安石无疑。唯王安石元丰元年封舒国公,元丰三年改封荆国公,当以苏轼所记为是,施顾注有误。 ⑩参见何泽棠:《施宿与“以史证诗”》,载《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 (11)以上所引见《苏轼诗集合注》,第2707、2723页。 (12)关于福建仙溪傅氏对苏轼的研究,笔者《宋代的东坡热:福建仙溪傅氏家族与宋代的苏轼研究》(《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有详细考论。 (13)杨焄已将《和陶诗话》残本所录的《东坡和陶话解》全部辑出,参见其《宋人〈东坡和陶集〉注本二种辑考》,载《中国诗学》第十七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 (14)参见卞东波:《谢枋得〈注解章泉涧泉二先生唐诗选〉与唐宋诗学》,载《南宋诗选与宋代诗学考论》第五章,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 (15)这可能与宋人“亲证其事然后知其义”(释惠洪《冷斋夜话》卷一)的风气有关,参见周裕锴:《中国古代阐释学研究》第五章《两宋文人谈禅说诗》六《亲证:存在还原》,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 (16)今有杨焄辑本,见《宋人(东坡和陶集)注本二种辑考》。杨焄认为蔡氏《东坡和陶诗集注》“从所辑佚文来看,其主体内容与傅共之注类似,主要是对陶、苏诗作内容的串讲。在此过程中,蔡氏既能联系作者生平抉发其创作初衷,又能由文本引申出相关的议论或感慨;除此之外,蔡氏注本还包括作者考辨、异文校勘、字词注音释义、征引其他文献等多项内容。”(《中国诗学》第十七辑,第9页)所论甚是。 (17)《文选》卷二十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989页。 (18)《乖崖集》卷二,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16页。 (19)《彭城集》卷五,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0)《苏魏公文集》卷九,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106页。 (21)《苏轼诗集》卷三十四,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792页。 (22)《栾城集》卷九,第205页。 (23)《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三,《四部丛刊初编》本。 (24)卞东波:《唐宋千家联珠诗格校证》,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年,第789页。 (25)费衮:《梁溪漫志》卷七,《宋元笔记小说大观》第三册,第3406~3407页。 (26)关于这一点,金甫暻《苏轼“和陶诗”考论》第三章《苏轼“和陶诗”的内容》有很好的讨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34~136页。 (27)金甫暻:《苏轼“和陶诗”系年表》,载《苏轼“和陶诗”考论》第一章,第57~58页。更详细的参见金甫暻:《宋刊〈东坡和陶诗〉编次》上下,载《苏轼“和陶诗”考论》第一章,第34~56页。 (28)苏辙:《子瞻和陶渊明诗集引》,《栾城后集》卷二十一,第1402页。 (29)王若虚《滹南诗话》卷二:“集中次韵者几三分之一。”参见内山精也:《苏轼次韵诗考》,载《传媒与真相—苏轼及其周围士大夫的文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 (30)关于东坡和陶诗与次韵诗的关系,参见金甫暻《苏轼“和陶诗”考论》第二章《苏轼“和陶诗”的创作背景》第一节《苏轼的次韵诗创作》。另外王宇根认为,次韵诗与北宋时期一种新的诗学风尚相关,即诗人的创作更多地与诗人或其他作者创作的既成文本联系在一起,见其所著《万卷:黄庭坚与北宋晚期诗学中的读与写》(Ten Thousand.Scrolls:Reading and Writing in the Poetics of.Huang Tingjian and the Late Northern Song,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1)的导论部分。 (31)蔡正孙:《诗林广记》卷一引,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4页。 (32)李公焕:《笺注陶渊明集》卷四引,《续修四库全书》集部130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1999年,第191页。 (33)吴可:《藏海诗话》,《历代诗话续编》本,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339页。 (34)参见卞东波:《韩国所藏孤本诗话〈精刊补注东坡和陶诗话〉考论》,《域外汉籍研究集刊》第五辑,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 (35)佛克马、蚁布思著,俞国强译:《文学研究与文化参与》,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5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