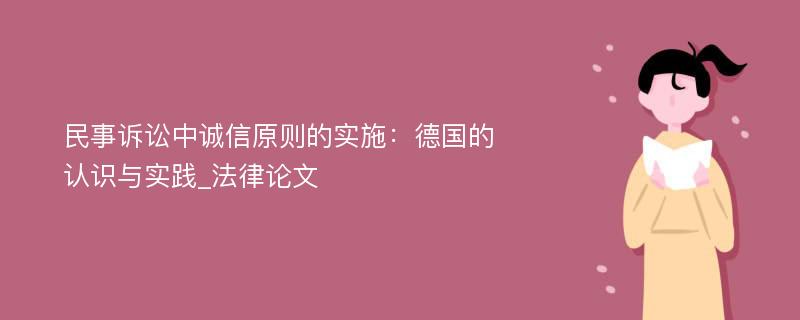
民事诉讼诚实信用原则的实施——德国的认知与实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德国论文,民事诉讼论文,认知论文,诚实信用原则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3条第1款规定:“民事诉讼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鉴于该条文的概括性和抽象性,仅仅通过语义分析难以解决诚实信用原则的具体适用问题;同时,鉴于诚实信用原则在限制当事人诉讼权利行使的同时,也会赋予法官一般裁量权,①为防止恣意裁判,有必要廓请诚实信用原则的效力范围。 诚实信用原则实施的关键,在于该原则的具体化。而我国学界过去对该原则的探讨,集中于立法论层面,着眼于诚实信用原则的历史沿革、学理分析、制度意义等理论问题,较少从解释论角度对诚实信用原则在民事诉讼中的具体适用作出回应。②在此背景下,运用比较法方法考察德国民事诉讼实务中诚实信用原则案例组,③结合我国立法与司法的特点对其进行分析不失为一种合适的做法。 与我国不同的是,德国民事诉讼法没有明文规定诚实信用原则。④但按照通说,诚实信用原则除适用于民事法律关系外,同样适用于民事诉讼法律关系,其依据是对德国《民法典》第242条⑤的类推适用。⑥德国民事诉讼诚实信用原则的具体适用规则来源于司法实务,经过长期的司法实践,法律积累了一定数量的同类裁判,学界通过总结,形成了较为稳定的案例组,来指导诉讼实践。因此,考察德国民事诉讼案例组,对我国民事诉讼诚实信用原则的具体化当有所裨益。本文以民事诉讼诚实信用原则的实施为中心,介绍基于德国司法裁判形成的四个案例组,即禁止制造恶意诉讼状态(Verbot arglistiger Prozesslagen)、禁止自相矛盾的行为(Verbot widerspruechlichen Verhalten)、诉讼失权(Verwirkung prozessualer Befugnisse)以及禁止滥用诉讼权利(Missbrauch prozessualer Befugnisse),⑦在此基础上尝试对我国民事诉讼诚实信用原则的具体化提出建言。 一、禁止制造恶意诉讼状态 何谓禁止制造恶意诉讼状态?对这一概念内涵的厘清有赖于具体案例的支持。在禁止恶意诉讼状态的案例组中,对此细分为以下四种情形: (一)规避法律 [案例1]A和B是汽车经销商,住所都位于慕尼黑市。A一向以“FA”的简称进行广告宣传。而B在《南德报》(德国著名的全国性报纸之一)以简称“Fa”做广告,并且在广告中注明经销电话以及出售汽车信息。在警告无效的情况下,A向位于埃森(德国西北部城市,属北威州,而慕尼黑位于德国东南部,属拜仁州,两个城市相距约650公里)的州法院提出了针对B的假处分(einstweilige Verfuegung)申请,要求禁止B在《南德报》及其他跨州发行的报纸上以“Fa”为简称进行广告宣传。A的代理律师知道位于埃森的州法院刚刚在类似的案件中作出过有利于申请人的裁判,因此向该法院提出申请能够获得最快的回应和保护。州法院果然很快支持了A提出的假处分申请。B向州高等法院提起上诉,州高等法院以A的假处分申请欠缺权利保护必要⑧为由予以驳回。⑨其理由大致如下:A在埃森提出申请应该被认定为规避法律的行为。因为按照管辖的一般规定,A应当在B的住所地慕尼黑进行诉讼,况且这里同时也是A的住所地。然而A舍近求远,主张按照《反不正当竞争法》第24条第2款由侵权行为地法院管辖。虽然B进行广告宣传的《南德报》是全国性的著名报纸,印有汽车广告的《南德报》也会在埃森发行,但不能据此认为埃森是《反不正当竞争法》第24条第2款所规定的侵权行为地。本条的立法目的在于更好地揭示案件事实,从而维护司法公正。然而A选择埃森进行诉讼的理由,只是该法院在之前的类似案件中作出过对申请人有利的裁判,其目的是利用当地法院的裁判习惯,正如他和他的代理律师在言词辩论中所表述的那样。但这并不符合《反不正当竞争法》第24条第2款的立法目的。诉讼法的出发点是,原则上所有的法院都是一样公正的,否则将无法保障法律秩序。在本案中,《反不正当竞争法》第24条第2款关于侵权行为地法院管辖的规定所追求的查明案件事实的考量,完全被A的选择架空了。根据诚实信用原则,滥用管辖规定的行为并不存在权利保护必要。虽然原告在选择法院时无需考虑对方的利益,而是将自己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但其只能在合理的范围内争取利益。当事人之间的诉讼法律关系,既受各种程序性规定的约束,也受诚实信用原则的制约。本案原告的选择不仅违背诚实信用,也不符合程序性规定的要求,应当认定A实施了故意规避法律的行为,其诉讼请求欠缺权利保护必要,故驳回A向位于埃森的州法院提出的假处分申请。⑩ (二)拆分请求金额(Rechtsmittelssummen) [案例2]A采用“化整为零”的方式,将2100马克的金钱请求拆分成为5个金钱给付之诉(Teilklage),分别向柏林地方法院起诉。柏林地方法院按照《民事诉讼法》第147条对5个金钱给付之诉加以合并,并驳回A提起的诉。柏林州法院支持这一裁判,认为A将诉讼请求拆分为5个部分,意在以不诚信的方式获得地方法院的管辖权。因此,部分金钱给讨之诉在地方法院缺乏权利保护必要;就诉讼要件而言,该诉是不合法的,因此A无法获得实体判决。据此,州法院判决驳回A的诉讼。(11) (三)恶意阻碍送达 [案例3]A租住在B的房屋里,双方约定如果因为A的装修使房屋升值,B应在规定期间内支付给A补偿费用。在双方的合同中,B写错了自己的地址。A按照错误地址寄去的催告信也没有被退回。在催告无果且经过约定期间后,A向州法院提起给付之诉,并按照合同中错误的地址填写了起诉状,致使邮局职员在送达时无法找到B本人,因此起诉书和开庭的传票由邮局职员以留置(Niederlegung)的方式进行了送达。A要求法院针对未出席和未被代理的B作出缺席判决。此后,A找到了B的正确通信地址并交给执行官(Vollzieher),要求其送达判决和执行判决内容。在执行官向B送达时,B谎称其不是本案被告,以此妨碍对其送达判决。继而,B又以诉状未送达给他为由,对缺席判决提出异议。州法院以B的异议不合法为由予以驳回。法院认为,自B恶意阻碍送达判决书时起,《民事诉讼法》第339条规定的异议期间开始起算,B未能在两周的不变期间内提出异议。在对执行官和邮局职员进行补充询问后,上级法院撤销原判,发回重审。理由是:虽然B存在恶意阻碍缺席判决送达的行为,但不能据此认为自此开始起算异议期间。在错误送达或者未送达的情况下,不变期间不能开始起算。毕竟,送达制度对于法律安定性以及法定听审权的保障不可或缺。即使对于诉讼中未能坚持诚信的当事人,诉讼法也应当对其提供保护。当然,因B的不诚信行为给A造成的财产损失以及由此增加的送达和执行费用,A可以要求B损害赔偿,没有必要以异议期间的起算作为制裁措施。(12) 这一判例得到了学者的支持。一方面,诚实信用原则应当适用于诉讼当事人之间;(13)另一方面,作为修正因恶意行为形成的诉讼状态的一般条款,诚实信用原则在民事诉讼中仅发挥补充和辅助作用,不能将其视为平衡当事人之间利益的特别规定而加以优先适用。(14) (四)恶意援引仲裁协议 [案例4]A向州法院起诉,要求B支付268776.41马克。B以双方当事人签订了仲裁协议为由进行抗辩。根据仲裁协议的约定,A与B之间的纠纷应当通过仲裁方式加以解决,因此州法院以诉不合法为由驳回起诉。此后,A的上诉被州高等法院驳回。A又向联邦最高法院提起上诉。联邦最高法院撤销原判,发回重审。联邦最高法院认为,虽然A与B之间的合同确实存在有效的仲裁协议,但不能据此认为诉不合法。正如A在再抗辩中主张的那样,B提出的仲裁协议抗辩是恶意的,因为B根本没有足够的资金进行仲裁程序,也无力承担仲裁的预付费用,甚至B必须申请诉讼费用救助才得以诉讼,因此A才选择向法院提起诉讼。基于以上理由,关于仲裁协议的抗辩并不导致诉不合法。(15) 二、禁止自相矛盾的行为 [案例5]A与B签订的合同中存在仲裁条款。A申请仲裁,B提出异议,主张仲裁条款无效。为此,A改向法院起诉,B却在其提交的答辩状中主张仲裁条款有效,法院对本案无管辖权。对此,联邦最高法院首先考察帝国法院时期的判例。在之前的判例中,有被告先在普通法院以存在仲裁协议为由提出抗辩,此后双方进行仲裁,仲裁庭随后作出了裁决。在仲裁裁决的执行程序中,被告却以仲裁庭没有管辖权为由阻止执行。对此,帝国法院认为被告在前诉中援引仲裁协议并据此提出了抗辩,导致原告之诉被驳回。在后续的仲裁中,被告参与了仲裁庭的组成等全部仲裁程序,如果因为仲裁庭作出了对其不利的裁决,他再以没有管辖权为由主张仲裁程序不合法,那么他的行为就是恶意的,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联邦最高法院注意到A与B之间的案件不同于帝国法院时期的判例。在本案中,仲裁程序并非在诉讼程序之后,而是在诉讼程序之前进行的。对此联邦最高法院认为,像帝国法院的其他判例一样,B的行为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因为B在诉讼程序中的行为与他在仲裁程序中的行为之间存在无法自圆其说的矛盾。如果B在仲裁程序中主张仲裁庭没有管辖权,本案应当交由法院处理,那么原则上禁止他在之后的诉讼程序中再援引仲裁协议,主张仲裁庭对本案的管辖权。B的矛盾行为将导致A既不能在仲裁庭也不能在法院获得法律保护,从而架空了A的权利。(16) [案例6]夫妻双方A和B在第二审判决作出后达成和解。和解协议约定A负有撤诉的义务。据此,B向联邦最高法院提起上诉,主张原审判决在A履行撤诉义务之前不发生既判力。联邦最高法院以B的上诉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第546条和第547条规定的上诉条件为由予以驳回。根据《民事诉讼法》第546条规定,对于非财产争议,只有州高等法院在判决中准许进行第三审时,第三审才可以被提起。第547条列举的例外情况并没有出现在本案中。基于维护法律安定性的考虑,如果第三审没有被准许,原则上判决一经宣告就产生既判力。如果允许提起第三审,那么第三审法院应该在上诉期届满后立即对第三审上诉的合法性进行判断,以免拖延判决的生效。在本案中,无论以何种理由,上诉人B都无权要求推迟既判力的产生。根据B的陈述,当事人之间只是签署了债法意义上的协议,原告依约负有撤诉的义务。这样的协议被帝国法院所准许,但其不能产生撤诉的效果。如果原告违背和解协议继续进行诉讼,被告只能提出原告为恶意的抗辩。(17)原被告之间的和解协议是在第二审程序后缔结的,性质上属于诉讼外和解,不能作为当事人提起第三审上诉的理由。(18) 三、诉讼失权 受实体法上失权制度的影响,诉讼权利也存在失权的可能,这是德国民事司法实践中诚实信用原则的具体表现之一。(19)实体法上的失权条件也被类推适用于诉讼法律关系中,(20)即一方当事人必须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以自己的行为使对方当事人合理地期待他不会再主张诉讼权利,并且据此对自己的生活作出了安排。诉讼失权要符合四个具体要件:1.经过相当长的时间;2.对方当事人对不主张诉讼权利产生期待和信赖;3.这种期待和信赖是值得法律保护的;4.对方当事人根据这种期待和信赖对自己的生活作出了其他安排。 然而,失权制度是否同样适用于受宪法保障的向法院起诉的基本权利(诉权(21)),这在德国民事诉讼中经历了由肯定到否定的发展过程。德国民事诉讼法学过去很长时间内并未将宪法意义上的诉权失效从具体诉讼权利的失效中区别出来,(22)一些文献虽然谈到二者的区分,却依然对诉权和具体诉讼权利作划一性的处理,肯定两者产生失权效的可能性。这种观点也支配了联邦最高法院及联邦劳动法院的相关判例。直到1972年,联邦宪法法院才在判例中指出,宪法层面的诉权具有与具体诉讼权利不同的法律性质。但遗憾的是,联邦宪法法院未能利用这个机会否定诉权的失效,而是依旧进行划一性处理。按照目前德国通说,诉权不受失权效和诚实信用原则的制约,联邦宪法法院的判例成为少数说。(23)这是德国民事诉讼判例中极为罕见的现象。 [案例7](24)1954年6月23日,税务局根据《税法》第445条(25)要求A因逃税行为缴纳罚款400马克。到1955年6月7日,A采用分期付款的方式缴清了罚款。1962年2月15日,A向税务局申请复核,以发现了新的事实为由主张其没有义务纳税。税务局认为申请合法,但以申请无依据为由将其驳回。对此,A提出行政复议,在复议理由中,A主张其1954年6月23日做出的放弃向法院起诉的声明因为违反《基本法》第19条第4款而无效。1963年12月5日,税务厅(Oberfinanz-direktion)以申请无依据为由驳回A的复议申请,以不合法为由驳回A要求确认其放弃向法院起诉的声明无效的请求,理由是《税法》第445条是否与《基本法》第19条第4款相违背应当由法院进行判断。此后A向法院提起诉讼,在1964年2月7日的诉状中,A申请确认1954年6月23日在税务局作出的不向法院起诉的声明无效,并且《税法》第445条违宪。科隆地方法院通过判决确认A的声明有效。A的上诉被州法院驳回。州高等法院也以无依据为由驳回A的第三审上诉。此后,A提起宪法抗告(Verfassungsbeschwerde)。联邦宪法法院最终驳回了A的抗告。宪法法院认为,按照通说,如果迟延主张请求权违反诚实信用原则时,将产生实体法和诉讼法上的失权效。诉讼法上的失权效应当受到重视,因为其不仅涉及对方当事人的信赖保护,还事关法律秩序的维护。因此,在很长时间后才向法院起诉的行为应视为不合法。就像联邦宪法法院在先前的判决中所表述的,即使没有期限限制的申请也不能由当事人随意延误为之,宪法规定的诉权也可能在具体案件中受到失权效的制约。本案中,因为A已经丧失了向法院起诉的权利,州高等法院的做法没有违背宪法原则,也没有损害A的基本权利。虽然A明知或应知自己的处境,但他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都保持不作为。州高等法院将A明知可以起诉的时间点确定在1960年末。在此期间,有众多的判例、法律出版物和新的法律规定使A重新向法院起诉成为可能。因此,A完全可以或者已经他的税务顾问进行过咨询。州高等法院的这种判断既不是随意的,也不是对A的苛求。然而,A直到1962年才要求复核,并且直到1964年才主张《税法》第445条违宪。(26) 联邦宪法法院的该裁判一经作出,就受到了激烈的批评。(27)宪法意义上的诉权应该与具体诉讼权利区别开来,套用具体诉讼权利失效的要件,来分析诉权失效,本身就存在疑问。即使认可该要件同样适用于诉权,经过分析后就会发现诉权不存在失权的可能性。首先,何谓“相当长的时间”,要过多久才能够产生否定诉权的效果,宪法法院的判例并未对此作出回应。其次,现实生活中是否存在着对某一实体权利只能在诉讼外主张,而不能去法院起诉的合理信赖也存在疑问。此外,诉权并不是争议当事人之间的关系,而是当事人与法院之间的关系,因此,对方当事人的期待和信赖在诉权失权上也没有保护的必要性。而作为相对方的法院不可能基于当事人不起诉的期待和信赖作出其他安排。可见,任何一项具体诉讼权利的失权要件都无法在诉权情形下得到满足,理论上不存在诉权失权的可能性。而且,在司法实践中也不可能出现诉权失权:在案件到达管辖法院的时候法院不知道可能存在诉权失权,并且审理本案的法官不会考虑某个案件是否需要法律保护,也不可能预计到对方当事人存在着不起诉的合理期待。由上,德国通说认为,与具体诉讼权利不同,诉权即使在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情况下也没有失权的可能性。像生命权一样,宪法保障的诉权不能由当事人自由处分,可以被当事人处分的只是具体的实体权利和诉讼权利(例如《民法典》第397条“债务免除”,《民事诉讼法》第306条“诉讼请求的放弃”)。联邦宪法法院的论证说明,其未将宪法保障的诉权理解为当事人与法院之间的公法关系,而是将其视为存在于当事人之间受当事人处分权制约的实体权利在诉讼中的投影。(28) 四、禁止滥用诉讼权利 诉讼权利滥用与权利保护之必要性是密切相关的。诉讼权利被滥用,意味着权利保护必要性的欠缺。(29)例如,和解协议存在形式瑕疵,但如果和解协议早已履行,那么再提出这些瑕疵,以主张和解协议无效,就会被视为诉讼权利的滥用。 [案例8]A与B签订了和解协议,B按照和解协议的约定向A支付了很高的金额。十个月后,B以形式瑕疵为由主张和解协议无效。州劳动法院认为A与B达成和解协议后一直肯定其效力,B已按和解协议的内容部分履行了自己的义务。此际,B以形式瑕疵为由主张和解协议无效的行为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因此B的主张欠缺权利保护必要。B此后上诉到联邦劳动法院。联邦劳动法院支持了州劳动法院的观点,认为和解协议缔结多年之后再非议形式瑕疵是不合法的。在本案中,B在之前的诉讼程序中始终没有主张和解协议的形式瑕疵,只要求法院调整和解协议的内容。B在州劳动法院才提出和解协议存在形式瑕疵。可能的解释是,起初B并不知道形式瑕疵的存在。但是这并不重要,因为失权并不以当事人明知有失权风险为要件,当事人的请求权可能在他并不知晓的情况下丧失。虽然B首次主张和解协议无效的时间是和解协议签订十个月后,但A关于诉讼失权的抗辩具有正当性。B向法院提出调整和解协议内容的请求,也恰恰说明B认可和解协议的有效性。不仅如此,B已按协议约定向A支付了高额金钱,这使A有理由相信和解协议得到了B的肯定。因此,从协议签订到B首次主张形式瑕疵的时间经过,足以产生失权的效果。 [案例9]A向家事法院提起离婚诉讼,要求法院判决其与B离婚。在言词辩论中,A与B就孩子的抚养权和房屋等财产分割达成和解协议,并被法院记录在案。B在诉讼及和解协议的缔结过程中都没有律师代理。家事法院曾两次以书面形式通知B,如果他坚持要求在明斯特或者柏林注册的律师代理的话,则只能由他本人进行诉讼。在1977年12月1日的言词辩论中,B明确表示,他知道必须由家事法院许可的律师进行代理,但自己放弃这样做。在和解协议缔结后,家事法院判决A与B离婚,孩子由A抚养,B向A支付孩子的抚养费用。到1978年春天,B断断续续地支付了孩子的部分抚养费用。因此,A要求按照和解协议强制执行。B在1979年5月11日递交的异议书中,以其在和解协议缔结时,没有被家事法院许可的律师代理为由,主张和解协议不能作为执行依据。家事法院驳回了B的异议。家事法院认为,离婚诉讼中的和解程序不受律师强制代理制度的制约,(30)这仍是新近判例中的通说。在是否只有双方律师代理的情况下达成的和解协议才能成为执行依据这一问题上,之前的判例存在较大的意见分歧。本案中B的申请违背诚实信用原则,构成了诉讼权利滥用,应予驳回。禁止诉讼权利滥用是诚实信用原则的具体表现之一。对于任何滥用权利的行为,法院可以依职权适用诚实信用原则。B对于律师代理的要求是明知的,和解协议本身构成了《民事诉讼法》第630条的要件之一。此外,在达成和解协议后的一年多时间里,B也一直认为其有效,并且支付了部分抚养费。因此,法院应当根据诚实信用原则驳回B对于形式瑕疵的抗辩。这种做法并不违背联邦最高法院在先前判例中的意见。按照联邦最高法院之前的观点,法律行为的形式瑕疵和长时间被视为有效的事实,不足以按照诚实信用原则认定法律行为有效,除非当事人对于法律行为的有效性形成了重大信赖。本案中A对和解协议有效性的信赖是重大的。A与B被判决离婚,而判决离婚的前提条件之一是双方就孩子的抚养问题达成和解协议。如果没有和解协议,则需要另行确定孩子的抚养问题,这将严重推迟离婚法律效果的产生。(31) 以上四个案例组,是诚实信用原则在德国民事诉讼中具体适用的概括。它们既是学界认识民事诉讼诚实信用原则的生动材料,也为司法实践中正确理解与适用诚实信用原则提供了相对明确和具体的指导规则;既使诚实信用原则不至沦为装饰性条款,同时也可大大降低转向纠问主义和职权主义的风险。诚实信用原则在德国民事诉讼中的具体化过程可以归纳为三个要点,相信这对我国不无有益的启示。 (一)诚实信用的规则性质和特点 德国和我国民事诉讼法律规范中都存在着若干反映诚实信用精神的规定(如德国《民事诉讼法》第138条第1款规定的真实义务),能起到促使当事人诚实守信地行使诉讼权利、法院客观公正地处理民事争议的作用。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原有法律制度无法应对所有的不诚信行为。由于德国民事诉讼法典中缺少诚实信用原则的一般性条款,因此不得已类推适用德国《民法典》第242条。而对德国《民法典》第242条的准用理由,决定了其不能被视为民事诉讼的特别规范,这也划定了诚实信用原则与其他具体法律规范之间的界限:一方面,诚实信用原则通常并不是直接适用,而是以法律解释的背景和理由出现。例如[案例1]的关键问题是如何理解德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24条第2款关于“侵权行为地法院”的内涵,A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被作为排除第24条第2款适用的重要理由之一。类似的还有[案例2]中的德国《民事诉讼法》第147条,[案例3]中的德国《民事诉讼法》第339条,[案例6](32)中的德国《民事诉讼法》第546条和547条,[案例9]中的原《民事诉讼法》第630条第1款第3项和第2款。简言之,当存在具体规范时,不应直接援引诚实信用原则。另一方面,当存在具体法律规范,并且通过文义解释、体系解释、历史解释和目的解释可以确定其内涵时,原则上也不得以违反诚实信用为由排除具体规范的适用。虽然[案例3]中B恶意阻碍送达的行为违反诚实信用原则,但不得因此突破德国《民事诉讼法》第339条对缺席判决异议期间的明确规定,即:以实际送达作为两周不变异议期间的起算点。同样,[案例6]中第三审上诉理由和既判力产生时间的明确规定也不因诚实信用原则而被改变。此外,通过[案例7],可以得出诚实信用原则不能限制德国《基本法》第19条第4款诉诸法院的基本权利的结论。 此外,民事诉讼规范的特点决定了诚实信用原则适用范围的变动性。例如,德国1933年修正民事诉讼法以前,真实义务被理解为诚实信用原则的主要内容。但随着1933年10月修正案将真实义务规定在德国《民事诉讼法》第138条第1款后,有关真实义务的案例组被理解为第138条第1款的直接适用,从而被排除出诚实信用原则案例组的范围。这体现出诚实信用原则对立法的积极作用:当存在法律空白或漏洞时以诚实信用原则进行填补,在对司法实务进行学术总结的基础上形成有针对性的案例组,再通过立法将案例组总结出的规则上升为法律的具体规范,从而形成司法、学术和立法之间的良性互动。应当说,在适用范围上,德国民事诉讼之诚实信用案例组与我国民事诉讼诚实信用原则之间也存在差异。例如,由于德国坚持严格的形式主义,因此[案例8]中“和解协议存在形式瑕疵但依然有效”的情形无法在德国法中找到直接适用的法律规范,但在我国可以考虑适用《合同法》第36条。我国《合同法》第36条使“和解协议存在形式瑕疵但依然有效”成为可能,可以成为该情形的直接适用规范,而无须援引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3条第1款。同样,在[案例2]拆分请求金额的情形下,我国民诉法没有与德国《民事诉讼法》第147条相类似的规定,因而可以构成诚实信用原则的直接适用范围。因此,最高人民法院制定诚实信用原则司法解释时要重视我国民事诉讼立法和司法实践的自身特点,逐项审视德国的案例组与我国既有法律规定之间的关联。 (二)诚实信用原则的具体操作 违反诚实信用原则的情形往往涉及诉讼当事人的恶意或不诚信行为。由于当事人的恶意是行为动机,属于主观因素,因而在认定上存在较大的困难。对此,法官能否以当事人涉嫌不诚信为由而对当事人的诚实信用进行主动和积极的调查?[案例9]中法院对该问题作出了肯定回答,但这并不意味着德国民事诉讼在诚实信用原则的适用上采取依职权探知的做法。结合[案例1]可以发现,是否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判断,只能够依赖当事人的陈述和证据证明的过程,法官原则上不能依职权提出和考虑双方当事人均未提出的事实和证据。因此[案例9]没有赋予法官依职权审查诚实信用与否的权力,而只有在当事人提出的事实和证据使法官确信一方或双方当事人存在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时(即使这并未被当事人所主张)。法官才能依职权加以考虑。这种做法与德国《民事诉讼法》第138条第1款真实义务的适用相一致。(33)与德国相比,我国民事诉讼目前依然具有较为浓重的法官职权主义色彩,因此,对引入诚实信用原则可能强化法官职权的担心并非杞人忧天。德国民事诉讼诚实信用原则在司法实践中所体现出的克制态度值得我国民事诉讼理论和实践的关注和重视。 (三)诚实信用原则的制度定位 通过考察诚实信用原则在德国民事诉讼中的规范特点与具体操作,可以发现,该原则在德国被定位为辅助性和补充性的一般条款。一方面,诚实信用原则不能替代具体规范的适用,而是作为具体规范适用的解释背景出现;另一方面,在诚实信用原则直接适用的情况下,法院依职权进行的诚实信用审查也被限定在较为有限的范围之内。这种态度固然与诚实信用原则的制度作用有关,同时也反映了德国民事诉讼对基本原则的认识。德国民事诉讼中的辩论原则和处分原则依旧被视为最重要的原则,诚实信用原则只是对传统辩论原则和处分原则的修正,而不可能成为民事诉讼中第一位的基本原则。诚实信用原则禁止当事人滥用诉讼权利,但这不意味着法院动辄以违反诚实信用为由对当事人诉讼权利的正当行使进行实质限制。(34)这些基本认识集中体现在诚实信用原则的制度定位上,并在该原则的具体适用中予以贯彻。与德国相比,诚实信用原则在我国有更广的适用范围和更大的作用空间,在此背景下,强调我国民事诉讼诚实信用原则的辅助性和补充性,在具体适用中对法官的诚实信用审查采取克制态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惟有如此,才能实现诚实信用原则在保障当事人正当行使诉讼权利的同时,有效遏制恶意诉讼和虚假诉讼等不诚信诉讼行为,发挥其填补法律空白和保障司法公正的积极作用。 ①参见张卫平:《民事诉讼中的诚实信用原则》,《法律科学》2012年第6期,第157页。 ②在诚实信用原则正式入法之前,也有文献涉及其具体化问题,如论及诚实信用原则的适用形态(参见刘荣军:《诚实信用原则在民事诉讼法中的适用》,《法学研究》1998年第4期,第126-133页)、具体表现(参见汤维建:《论民事诉讼中的诚信原则》,《法学家》2003年第3期,第92-104页)、客观范围(参见包冰锋:《民事诉讼中诚实信用原则适用之客观范围探究》,《现代法学》2009年第6期,第103-110页)、具体适用(参见董少谋:《诚实信用原则在民事诉讼中的具体适用》,载《检察日报》,2012年9月20日)。上述文章致力于民诉中诚信原则具体化问题的探讨,但在该原则的适用范围上出现不同理解。例如,将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12条、第113条等已经入法的法律制度都视为民事诉讼诚实信用原则的具体适用。然而按照德国通说,诚实信用原则只被认为具有补充作用,没有具体可适用的法律规定构成其作用的最重要的前提,否则就有架空既有法律制度和破坏程序安定性的危险。因此,一旦诚实信用原则的某一案例组被立法所采纳,严格意义上它就不再是诚实信用原则的适用范围,而成为法院直接适用的法律依据。Vgl.Rosenberg/Schwab/Gottwald,Zivilprozessrecht,Muenchen:C.H.Beck 2010,§2Rn.16 f;Stein/Jonas/Brehm,Kommentar zur ZPO,Tuebingen:Mohr Siebeck 2003,vor§ 1 Rn.223 f; Thomas Rauscher,Muenchener Kommentar zur Zivilprozessordnung,Muenchen:C.H.Beck 2013,Einl.Rn.34,35; Zoeller/Vollkommer,Zivilprozessordnung,Koeln:Dr.Otto Schmidt 2010,Einl.Rn.56; Baumbach/Lauterbach/Albers/Hartmann,Zivilprozessordnung,Munchen:C.H.Beck 2011,Einl.Rn.53 f; Gottfried Baumgaertel,Treu und Glauben im Zivilprozess,Zeitschift für Zivilprozess 86(1973),359. ③关于日本民事诉讼诚实信用原则的司法实务,参见王亚新:《我国新民事诉讼法与诚实信用原则——以日本民事诉讼立法经过及司法实务为参照》,《比较法研究》2012年第5期,第32-43页。 ④德国民事诉讼对诚实信用原则的称谓多为“诚实和信用”(Treu und Glauben),有时也称为“诚实信用原则”(Grundsatz von Treu und Glauben)。在制度性质方面,诚实信用原则被定位为一般条款(Generalklausel)。此外,德国民事诉讼对于基本原则的理解要比我国更为宽泛,只要具有一般性并对若干具体规定具有指导作用的法律制度都可以为基本原则(如真实义务原则)。因此,不能仅因文字表达方式就将诚实信用原则理解为与辩论原则和处分原则并列的民事诉讼基本原则。我国民事诉讼对基本原则的理解较为严格,其指代的是贯穿民事诉讼并对民事诉讼活动具有指导意义的根本性和指导性规则。因此,诚实信用在我国是否可以被称为基本原则也是值得反思的。参见张卫平:《民事诉讼法》,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33-35页。 ⑤德国《民法典》第242条规定:“债务人有义务照顾交易习惯,以诚实信用所要求的方式履行给付。”参见《德国民法典》,陈卫佐译,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86页。 ⑥参见注②,Rosenberg/Schwab/Gottwald书,第16页;Walter Zeiss,Die arglistige Prazesspartei,Berlin:Duncker § Humbolt 1967,S.19. ⑦参见注②,Rosenberg/Schwab/Gottwald书,第49页;Stein/Jonas/Brehm书,第227页。 ⑧权利保护必要(Rechtsschutzbeduerfnis)是诉讼要件(Prozessvoraussetzung)的子类。权利保护必要的欠缺将产生诉不合法(unzulaessig)的后果。此时法院将不再对案件实体争议进行裁判,而是以诉讼判决(Prozessurteil)的形式判决驳回起诉。我国将Prozessvoraussetzung直译为诉讼要件会产生误导,易误认为民事诉讼开始的条件,因此将其意译为实体判决要件更为恰当。参见张卫平:《起诉条件和实体判决要件》,《法学研究》2004年第6期,第58-68页;注②,Rosenberg/Schwab/Gottwald书,第89、93页。 ⑨假处分在德国适用简易审判程序,因此申请假处分必须满足诉讼要件,否则法院将以欠缺诉讼要件为由驳回申请。参见[德]穆泽拉克:《德国民事诉讼法基础教程》,周翠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27-430页。 ⑩参见哈姆州高等法院《新法学周刊》,1987年合刊,第138页(OLG Hamm NJW 1987,138)。 (11)参见柏林州法院《法学周刊》,1931年合刊,第1766页(LG Berlin JW1931,1766)。 (12)参见联邦最高法院《新法学周刊》,1988年合刊,第426页(BGH NJW 1978,426)。 (13)参见注②,Rosenberg/Schwab/Gottwald书,第16页;Stein/Jonas/Brehm书,第223页;Thomas Rauscher书,第34-35页;Zoeller/Vollkommer书,第56页;Gottfried Baumgaertel文,第86、359页;Baumbach/Lauterbach/Albers/Hartmann书,第53页。 (14)参见注②,Stein/Jonas/Brehm书,第223页;Baumgaertel文,第86、359页。 (15)参见联邦最高法院《新法学周刊》,1988年合刊,第1215页(BGH NJW 1988,1215)。十年后,联邦最高法院在类似案件中仍持相同观点(Vg1.BGH NJW 1999,647,648)。 (16)参见联邦最高法院《新法学周刊》,1968年合刊,第1928页(BGH NJW 1968,1928)。十年后,联邦最高法院在类似案件中仍持相同观点(Vg1.BGH NJW 1997,3377,3379)。 (17)但目前德国通说认为,被告可以提起的抗辩并非基于对方当事人的恶意,而是诉讼契约的处分效果或义务作用,参见注②,Rosenberg/Schwab/Gottwald书. (18)参见联邦最高法院《新司法周刊》,1964年合刊,第549页(BGH NJW 1964,549)。 (19)参见注②,Rosenberg/Schwab/Gottwald书,第51页;Stein/Jonas/Brehm书,第234页。 (20)参见注②,Stein/Jonas/Brehm书,第233页。 (21)在德语中也有诉权的对应概念,即Klagerecht,但这一表述在德国民事诉讼法学中已经被司法请求权(Justizanspruch)取代:一方面,司法请求权凸显其公权属性,是针对法院要求司法裁判的请求权,因此与私法上的请求权相区分;另一方面,司法请求权是德国宪法所保障的基本权利,强调其宪法属性是基于其能够在制度上获得宪法上的特殊保障,当普通法院拒绝裁判时可以通过宪法法院进行救济,[案例7]就是比较典型的例证。参见注②,Rosenberg/Schwab/Gottwald书,第65页。 (22)文献和判决中有多种与之相关的表达,比如诉的可能性(Klagemoeglichkeit)、诉权(Klagebefugnis或Klagerecht)以及基本法保障的向法院起诉的权利(Klagebefugnis des grundgesetzlich garantierten Wegs zum Gericht)、法律保护请求权(Rechtsschutzanspruch)、司法请求权(Justizanspruch)以及权利保护请求权(Rechtsschutzsgewaehrungsanspruch)等。对于这些概念,有必要区分哪些是宪法意义上的诉权,哪些是一般法意义上的具体诉讼权利。但这种区分并未被文献和法院裁判所重视。Vgl.Duetz,Verwirkung des Rechts auf Anrufung der Gerichte,Neue Juristische Wochenschrift 1026(1972). (23)参见注②,Rosenberg/Schwab/Gottwald书,第65页;Stein/Jonas/Brehm书,第234页。 (24)在案件性质上,[案例7]并不能归入民事诉讼范畴。但由于本案最终诉至联邦宪法法院,且联邦宪法法院就诉权是否存在失权的可能作出了判断,因此,本案同样被列入了民事诉讼诚实信用原则的案例组。 (25)第445条是1919年《税法》中的内容,按此,对于小额的违反税法的违法行为,如果当事人放弃向法院起诉,则通过罚款等方式做出终局性的处理。 (26)参见联邦宪法法院《新法学周刊》,1972年合刊,第675-676页(BVerFG NJW 1972,675,676)。 (27)参见注②,Baumgaertel文,第385页;注(22),Duez文,第1025页。 (28)参见注(22),Duetz文,第1026页。 (29)参见注②,Rosenberg/Schwab/Gottwald书,第29页。 (30)根据当时的《民事诉讼法》第630条第1款第3项和第3款的规定,法院记录的离婚财产分割和解协议(Scheidungsfolgen-vergleich)只有在双方当事人都由律师代理的情况下,才能够成为有效的执行依据(Vollstreckungstitel)。参见《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谢怀栻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162页。 (31)参见哈姆州高等法院《家庭法期刊》,1979年合刊,第848页(OLG Gamm Fam RZ 1979,848)。 (32)[案例6]同样涉及对当事人之间达成的诉讼契约效力的认识和理解问题。 (33)关于德国民事诉讼真实义务的边界问题,参见任重:《民事诉讼真实义务边界问题研究》,《比较法研究》2012年第5期,第146-154页。 (34)参见注②,Rosenberg/Schwab/Gottwald书,第76-77页。标签:法律论文; 诚实信用原则论文; 恶意诉讼论文; 法律案例论文; 驳回起诉论文; 民事诉讼当事人论文; 上诉期限论文; 法制论文; 送达方式论文; 税法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