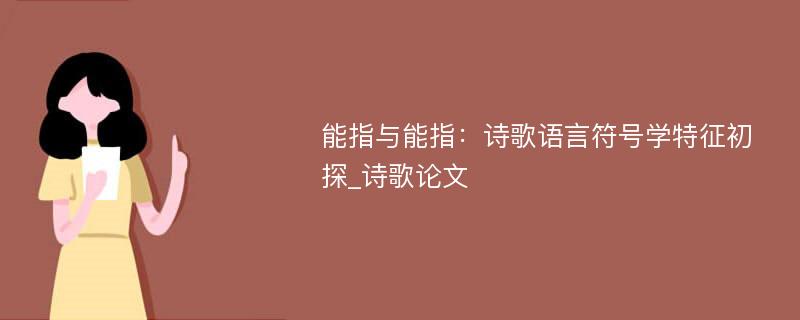
能指与所指:诗歌语言的符号学特性初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符号学论文,所指论文,诗歌论文,特性论文,语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从语用功能的角度,我们可以将人类语言的功用大致分为以下三类:第一类,也是最常见的一类,是用来传递交流信息。我们说现在是早上七点,说某某喜欢一本书,说乔治·华盛顿是美国第一任总统,这些可以分属此类,我们亦可称其为语言的实用功能,它帮助我们处理日常事务。第二类是将语言作为一种工具,例如广告、宣传布告、宣教、政治宣言等均属此类,可称为语言的工具功能。语言的第三类功用存在于小说、戏剧、诗歌等文学作品中,这些文学形式能够加深并拓展我们对生活的感受,这是语言的文学功能。
由于语言具有文学的功能,因此它能够对人类的经验进行浓缩组织,使之产生出新的意义,并通过文学作品传达这种意义。文学语言不仅能够将别人的经验传达给我们,而且能够让我们通过想象参与其中。文学语言能够让人们通过想象而获得对生活的更加完全、更加深切的感知和体认。
诗歌语言作为文学语言的一种,不仅具有文学语言的一般性质,而且还具有其他文学形式所没有的特征。其中最突出的是诗歌语言乃是文学语言中最浓缩最精炼的一种,它可以用最少的语词表达最多的含义。
关于诗歌语言的神奇特性,人们在欣赏赞叹之余却无法做出科学精确的解释。这一难题只有到了索绪尔创立现代语言学以后才获得解答。
对于文学语言的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研究始于本世纪六十年代,该研究试图将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运用于文学语言性质和功能的分析上。在索绪尔看来,一个语符的组成包括能指(signifier)和所指(signified)两个部分。能指即该语符的音像或书写形式,所指则是该语符意义或概念上的对应物。例如英语中d-o-g这三个字母的书写形式是能指,而它在一个懂英语的人头脑中唤起的狗的形象是所指。索绪尔进而指出能指与所指之间的联系是任意的:二者之间并没有内在必然的关联。例如汉语用“狗”这一形式表达同样的含义。不仅如此,整个语符(包括能指和所指)与该语符在现实中的对应物之间的联系也是任意的。例如狗这个语符与现实中那个真正的有毛四足动物之间的联系是人为的和任意的。索绪尔认为语符的意义并不存在于它自己之内,而是存在于该语符同其他语符的差别之中。dog这一语符之所以具有意义,是因为它不是dot,也不是log或dig。不论一个语符的能指如何变化,只要它仍然保留与其他语符相区别的特征,其所指意义仍旧不变。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理论对人们认识语言的本质具有极大的启发意义。虽然后来的理论家对索绪尔的语言观褒贬不一,如有学者提出索绪尔语言学只注重语言内部结构的研究,忽略了语言与思维(思维表象、想象、直觉、形象思维)之间的联系,但是索绪尔对语言本质的独到见地和精辟阐释至今仍具有重大的价值,其理论研究的方法也被包括文学研究在内的许多领域所采用。以下我们运用索绪尔理论中有关能指与所指的观点,对诗歌语言的符号学特性及其功能机制试做分析。
二
首先,索绪尔提出的结构主义语符理论使人们增加了对语言符号本身而不是符号同对应物之间关系的关注。在诗歌研究领域,研究者们已突破了传统美学理论对诗歌语言研究的束缚,转而对诗歌语言的符号学特性更加重视。俄国形式主义文学批评家雅克布森(Jakobson)认为,诗歌语言的特性首先在于语言自我意识的突出。他指出,诗歌语言的功能在于增强了语符的可触知性,使人们更加关注语符的物质特性而不是仅仅注意它们在传递交流信息中的作用和意义。在诗歌语言中,语符能够脱离对应物而独立存在:语符与对应物之间的通常联系被打破,语符从而获得了自身独立存在的价值。布拉格语言学派的理论家Mukarovsky、Vodicka等人从索绪尔的理论出发,对形式主义的诗歌语言观点进行了更为系统的阐发。他们认为,对诗歌语符的研究应当着眼于它们自身的价值(语符的内部特性和结构),而不是它们反映现实(语符与对应物之间的关系)的功能。由此可见,索绪尔对符号与对应物、语词与事物之间联系任意性的观点深深影响了诗歌语言的研究,诗歌文本也因此成为能够脱离外部现实而独立存在的自足的系统。然而这种自我意识的突出并非完全隔断了语言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形式主义诗歌语言理论认为语言依然通过陌生化的作用与外部世界相联系:诗歌语言打破了日常语言符号系统的常规,通过陌生化使读者将其注意力集中到语言的物质特性本身,因而能够更新读者的感受。俄国符号学家Lotman指出,每一种诗歌文本都是由一定数量的“系统”构成的;这些系统包括:词汇系统、词形系统、格律系统、语音系统等。诗歌作品的艺术效果正是通过这些系统之间的不断碰撞产生的。现以下诗为例:
SOUL:Oh,who shall from this dungeon raise
A soul enslaved so many ways?
With bolts of bones,that fettered stands.
In feet,and manacled in hands.
Here blinded with an eye;and there
Deaf with the drumming of an ear;
A soul hung up,as'twere,in chains
Of nerves,and arteries,and veins;
Tortured,besides each othe part,
In a vain head and double heart.
BODY:O,who shall me deliver whole
From bonds of this tyrannic soul?
Which,stretched upright,impales me so
That my own precipice I go;
And warms and moves this needless frame
(A fever could do but the same),
And,wanting where its spite to try,
Has made me to live to let me die.
A body that could never rest.
Since this ill spirit it possessed.[①]
该诗是十七世纪英国玄学派代表诗人安德鲁·马维尔的诗《灵魂与肉体的对话》中的第一、二两节。为便于分析,我们先将该诗的内容大意介绍如下:在马维尔诗作的各类主题中,宗教占据了极其重要的地位,该诗便是一首重要的代表作。这首诗通过灵魂与肉体对话的形式,生动逼真地表现了西方传统文化中灵魂肉体相分而冲突的观念。
诗的第一节显然是描述了灵魂被囚禁于肉体中的痛苦情状,诗的前两行是一问句,这里诗人使用了“dungeon”(地牢)和“enslaved”(奴役)等词,生动逼真地描绘出灵魂被囚受困而欲挣脱获得自由的图景。这一问句在下面的叙述中并未立即予以解答,而是直到最后一节读者方可找到答案。随后的描述看似怪诞离奇,实则寓意深刻;骨骼何以成为枷锁?手脚何以成为桎梏?有眼反成盲人?有耳反至失聪?神经、血管何以竟成锁链?此间意蕴非假作者之宗教背景不能辨明。从基督教的信仰来看,人由灵、魂、体三部分组成。其中灵乃出于上帝,《圣经·创世纪》记载上帝“将生气吹在他(亚当)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灵乃无形亦无限,体为有形亦有限。灵与体的矛盾永远难以调和,只有等到基督再来,众生得救,才可以得着复活后天上“灵性的身体”。再者,基督教信仰认为,人自乐园堕落以后,肉体之中便有了罪性;诸多罪性,如“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等不仅使灵眼闭塞,灵体麻木,而且引人耽于罪中之乐,走向堕落与毁灭。此外“vain head”和“double heart”也使人自然联想到《旧约·诗篇》中有关罪人特征的描述:They utter lies to each other;with flattering lips and a double heart they speak.(人人向邻舍说谎;他们说话,是嘴唇油滑,心口不一。)
在诗的第二节中,肉体对灵魂的回应同样是希求解脱的呼唤。如此看来,灵魂与肉体同样皆处于无能为力的境地,而二者彼此成为对方的桎梏。在这里,“precipice(悬崖)”一词寓意深刻,其比喻象征之涵义唯出于基督教之教训:人异于草木禽兽,乃缘于人具有灵魂;然正因人具有灵魂,才有堕落沉沦的危险;灵魂因而成为人里面的悬崖。进一步看,肉体对灵魂的怨尤同时反映出肉体的罪性及动物的本能:如果肉体因灵魂离去而失去任何约束(“stretched upright”),则其以后的景况不言而喻。恰恰因为灵魂的约束,肉体之本能不能肆意张狂,于是它抱怨说“making me live to let me die”。与第一节相类似,作者在该节末尾引用《圣经》的教训;“ill spirit”说明基督教对罪(sin)的解释:罪的危害首先是灵魂,而非肉体。奥古斯丁在他的著作《上帝之城》中说:“肉体的堕落,及其对灵魂的侵蚀,乃是人首次犯罪的惩罚,而非其犯罪的起因;并非堕落的肉体使灵魂负罪,而是负罪的灵魂使肉体堕落”。
通过仔细阅读我们就能发现,上述的各类语言系统都处在不断的相互冲撞的状态中。例如,格律形成的系统不断地被句法系统所冲撞和跨越。在这两节中,每节都是押aaaabbccdd尾韵,产生一定的韵律效果。然而每一行并不都是一个完整的句子,而是经由作者有意分割而成的句段。例如在首节的第一、二行,这样的分割就产生了特殊的艺术效果:它不仅在第一行的末尾制造了悬念,而且在第二行的开头形成强调和突出。我们对语法结构和韵律的感受在这样一种冲撞中无疑加深了对该诗主题意蕴的认识。在其后诸行中,这种系统间的相互作用也是很明显的。词与词之间可以通过谐音相联系,如“chain”和“veins”;可以通过句法位置相联系,如“dungeon”和“me”;可以通过词形对应相联系,如“manacled”和“hands”(“man”为一拉丁词根,意为hand);还可以通过头韵相联系,如“bolts”和“bones”,“fettered”和“feet”等。这些作用和联系无疑加深了读者对诗歌思想意蕴的体认,使作品的主题得以更为充分表达。
三
其次,诗歌语言的符号学特性还表现在,在语符内部的能指与所指之间存在一种非对称的关系。根据布拉格语言学派的观点,诗歌语言可被视为一种“功能结构”。诗歌文本经由“语义渗透”而比任何其他的语篇包涵更多的信息。诗歌语言将普通语言的“冗余性”减至最低限度,即在尽量减少那些仅仅是便于交流进行而非真正传达信息的语符的同时,最大限度地产生信息。在这一点上,没有任何其他的语言形式能够同诗歌语言相媲美。诗歌语言激活了整个能指的系统,使语词在诗歌语境的强大压力场中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潜力。现举实例分析如下:
The Sick Rose
O Rose,thou art sick!
The invisible worm
That flies in the night,
In the howling storm,
Has found out thy bed
Of crimson joy,
And his dark secret love
Does thy life destroy.[②]
这首由英国诗人威廉·布莱克创作的短诗具有极其丰富的内涵。在这首诗中,能指与所指间的非对称关系首先表现在“rose”(玫瑰)和“worm”(蠕虫)这两个语词的涵义上。这里的rose和worm从所指涵义上讲绝不仅仅局限于一种花卉和一种昆虫。这里的rose是大写的并且是拟人化的。从植物美学和文化学的角度来看,rose具有指涉女性美、爱情、以及肉体快感等象征意义。诗中的“bed”(床)既可以指花床,也可以指女人的床榻。“crimson joy”(绯红的喜悦)既可以指红色花朵的鲜艳美丽,又可以指充满激情的性爱所带来的强烈快感。“invisible worm”(隐身的蠕虫)和“dark secret love”(黑色的秘密的爱)当然可以指蠕虫对植物的悄悄啮食,但是指一种隐蔽的或不为常理所接受的爱情似乎更为恰当。当然,这些语词的所指范围还可以更广。对于该诗的主题,历来存在众多不同的解释,如:爱情受害于嫉妒和猜疑;天真受害于经验;人类受害于撒旦;想象受害于理性;生命受害于死亡;等等。我们无法准确地说出诗人所指的究竟是什么,事实上这也并无必要。就诗歌语言的表现功能来讲,一篇诗作往往并不着意描绘现实生活中的事物,却更多地在于表现和传达某种经验。诗歌中语符的能指也往往不只对应一个或几个所指,而是对应凡适合其象征范围的众多所指。诗歌语言的这一符号学特性是日常一般语言所不具备的。
注释:
① M.H.Abrams,et al.The Norton Anthology of English Literature,Vol 1.5th ed.New York:W.W.Norton & Company,1986,p.1383.
② Laurence.Perrine,Sound and Sense:An Introduction to Poetry,New York: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Publishers,1987,p.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