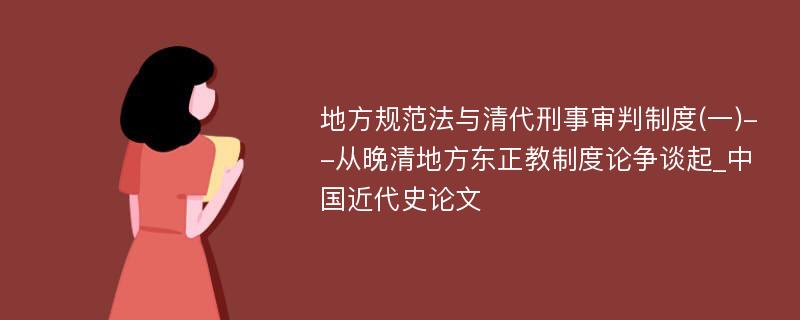
就地正法与清代刑事审判制度(之一)——从晚清就地正法之制的争论谈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就地正法论文,晚清论文,清代论文,制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问题的提出
清代刑事审判制度以其严格的死刑复核审判程序而著称,相关的法制史论著和教材大多也仅及于此。(注:有广泛影响的大学法学课程教材,如张晋藩主编的《中国法制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怀效锋主编的《中国法制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以及张晋藩主编的《清朝法制史》(中华书局1998年版)等,只介绍了清朝死刑复核审判制度,都未提及就地正法之制。)《清史稿》简略提到了另外一种情形——就地正法之制:“唯就地正法一项,始自咸丰三年。时各省军兴,地方大吏,遇土匪窃发,往往先行正法,然后奏闻。”此后,直至辛亥革命,清王朝“就地正法之制,迄未之能革”。(注:赵尔巽等撰:《清史稿》第15册,“志·刑法二”,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4202、4203页。)学界以此为依据,对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期间及战后就地正法的情况做了初步的记述和论证,一致认为就地正法之制始于镇压太平天国时期。(注:李贵连:《晚清“就地正法考”》,《中南政法学院学报》1994年第1期;邱远猷:《太平天国与晚清“就地正法之制”》,《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2期;邱远猷:《晚清政府何时何地开始实行“就地正法之制”》,《历史档案》2000年第3期;郑秦:《清代法律制度研究》,“论清代秋审制度”部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李贵连先生根据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手稿本《刑部奏案》中一道皇帝谕旨将就地正法的开始实施确定在金田起义两年后,亦即咸丰三年(1853)三月十三日:“前据四川、福建等省奏陈缉匪情形,并陈宝绶等奏遣散广东各勇沿途骚扰,先后降旨谕令该督抚等认真查办,于讯明后就地正法。并饬地方官及团练、绅民,如遇此等凶徒,随时拿获,格杀勿论。现当剿办逆匪之时,各处土匪难保不乘间纠伙抢劫滋扰。若不严行惩办,何以安戢闾阎。著各直省督抚,一体饬属随时查访,实力缉拿。如有土匪啸聚成群,肆行抢劫,该地方官于捕获讯明后,即行就地正法,以昭炯戒。并饬各属团练、绅民,合力缉拿,格杀勿论,俾凶顽皆知敛迹,地方日就乂安。至寻常盗案,仍著照例讯办,毋枉毋纵。”(注:李贵连:《沈家本传》,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61页。)
邱远猷教授认为李贵连先生的说法“不符合历史事实”。他所引用的材料是道光三十年(1850)十一月十六日,贵州巡抚乔用迁向朝廷奏报:“为黔省毗邻广西地方,遵旨饬属严防……将现获随同陈亚溃劫掠要犯”、“籍隶广西”的丁二旺等14犯“审明先行正法”。邱远猷认为,“这是第一个地方巡抚向朝廷奏报‘先行正法’的”,而道光帝对这显然与过去死刑复核审判制度迥异的“先行正法”,没有表示异议。另一方面,邱先生似乎更加强调另一件事:金田起义后不久,道光三十年十二月二十七日,钦差大臣李星沅等奏报,拿获广西庆远一带“恃众攻劫,迭抗官兵”的“贼首张晚”以及“梧州属积年巨盗邓立奇”,就近解赴李星沅行营“审明正法”,而咸丰帝对此批示是“知道了”,“无疑表示了同意”。此外,邱先生还列举了随后一系列就地正法的实例,并得出结论:“由上可见,晚清政府实行‘就地正法之制’,绝非始自‘咸丰三年’太平天国建都南京之后,而是始于金田起义后不久的1851年,始于太平天国革命首先爆发的广西省。”(注:本段引文散见于邱远猷《太平天国与晚清“就地正法之制”》,《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2期;《晚清政府何时何地开始实行“就地正法之制”》,《历史档案》2000年第3期。)
而郑秦先生则认为: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清朝统治者除了武装围剿外,“创造了有名的‘就地正法’”,以便放手地、不受任何程序限制地进行镇压。(注:郑秦:《清代法律制度研究》,第197页。)
但笔者在查阅相关史料过程中发现,从清初一直到清末,不仅有大量就地正法的实例,而且有相关的法律制度规定。为什么相关研究者,尤其是清代法制史的研究者会忽略这一明显存在的事实,在清代法制史中只字不提这一重要的死刑审判制度,仅仅局限于晚清范围内来讨论这一问题呢?这里的原因可能比较复杂:就地正法确实是在晚清才成为一个突出的司法问题;《清史稿》的影响不可忽视;以及对清代前期严格的死刑审判复核程序的确信等等。但毫无疑问,近代史时段的划分和相应研究范式的形成是其中最根本的原因。
如李贵连先生在讨论晚清就地正法之制时,首先在时段上确定:“1840年,也就是沈家本出生这一年,中国社会由古代进入近代”;然后据此判断:“就法律而言,清朝的基本法律——《大清律例》,直到法律改革前,和1840年以前没有什么不同。用中世纪的法律去规范近代社会,这就是十九世纪下半叶中国法律和社会的现状。传统法律与近代社会脱了节,《大清律例》无法规范近代社会,传统法律陷入无法解脱的困境之中。”他因此还专辟一章“吊诡时代的法律与社会”来探讨相关问题,其中之一就是“就地正法与传统司法审判制度”,并将这一问题同“领事裁判与国家法权”,以及“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异与传统法的困境”相提并论。(注:参见李贵连《沈家本传》第五章“吊诡时代的法律与社会”。)
这里的问题是,提出什么样的问题和怎样提出问题。就地正法之制的产生是否是传统司法审判制度无法规范近代社会的结果?这显然是一个未经证实的推论,而这一推理的依据就是近代社会与古代社会根本不同,且区分这两种社会的界限就是“1840年”。1840年前是传统司法审判制度,即严格的死刑审判复核制度;1840年后,变成了就地正法之制,因为传统法律无法规范近代社会。在这种问题意识之下,自然无须追溯就地正法之制在清代的起源。就地正法在清末确实有变化,但基本上是一个旧的问题,尽管搀杂着新的因素。
郑秦先生把就地正法放在“清代秋审制度”当中来讨论,而没有将就地正法与秋审制度并列作为清代刑事审判制度来讨论,他将二者作为前后关系,以秋审制度来反衬太平天国时期的就地正法之制,因而才有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清朝统治者除了武装围剿外,“创造了有名的‘就地正法’”这样的结论。(注:郑秦:《清代法律制度研究》,“论清代秋审制度”部分。)
邱远猷先生在李贵连先生的研究基础之上,更明确地把对就地正法的考察范围限制在太平天国运动时期,突出了就地正法的起始时间和太平天国与就地正法的关系,以及就地正法与晚清权力下移的关系。他所特别强调的重要问题之一是晚清权力下移,这也是晚清政治史关注的问题。邱文认为:“在全国推行十多年的就地正法之制,破坏了清王朝持续近二百年的司法审判制度,主要是死刑上报中央刑部复核、皇帝亲自裁决的制度。这就使得皇帝独揽的死刑最终审判权下移,从而削弱了皇权,增长了地方督抚、尤其是汉族督抚的权势,出现了‘内轻外重’的局面,引发了中央和地方之间、少数满族皇族亲贵与汉族地方督抚之间的权力矛盾。”李贵连先生对此有更详细的讨论,但结论相似,还是将之设定为政治史而非法制史问题来讨论,即以就地正法来印证晚清权力下移这一政治现象,对其涉及的司法问题则关注不够。
此外,对就地正法的批判也是站在近代或“农民革命”的立场,将就地正法定性为一种“防盗匪之酿成乱匪,而以治乱匪之法治盗匪”的衰世恶法,没有将就地正法作为清代法律制度来研究。这样,原则性批判就取代了具体问题分析。
以上相关研究现象给我们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当史学研究由事件史扩展到社会史时,以事件史(鸦片战争)为起始的近代史时段划分,如何适应诸如制度史这类研究?这不仅涉及研究时段划分,还与研究视野和问题意识相关。
“晚清就地正法之制始于何时”这一问题本身就值得推敲。就地正法之制作为一项司法制度的产生或始于何时,是一个制度溯源问题。但论者将其限定在“晚清”这一相对含糊的时段来讨论,甚至局限于太平天国这一事件范围内讨论,显然眼界过于狭窄。在未经溯源和论证的情况下,便断言就地正法之制产生于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期间,这是不符合制度史研究规范的。
作为就地正法之制的溯源,我们认为“清代”是一个比较合适的时段。因为每个王朝都会构成一套相对独立的制度体系,可以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单位。
就地正法是清代刑事审判的一个重要现象和制度形式,应当在清代法制史层面来探究这一制度的形式、具体实施,及其与清代死刑审判复核制度的关系,在此基础上确定晚清就地正法之争的实质和意义。
清代就地正法的制度形式
对就地正法之制的界定,李贵连先生在《晚清就地正法考》一文注释中说明“本文称其为制度,本于《清史稿·刑法志二》:‘而就地正法之制,迄未之能革’之说”。但《清史稿》对这一制度的内容或形式并无说明。邱远猷先生则从就地正法与清代死刑审判复核制度的对照,解释了就地正法的含义,即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过程中,对死刑犯改变正常的死刑复核审判制度,一面奏闻皇上,一面即行就地正法。但这只是对太平天国时期就地正法含义的解释,对就地正法之制这一司法制度并没有界定。郑秦先生则将就地正法之制看作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清政府的一项制度“创造”,但也只是一笔带过,未加说明。
(一)就地正法的法律形式
清代没有专门的刑事诉讼法,因此,就象我们归纳总结出清代刑事审判复核制度一样,就地正法制度也需要我们归纳总结。作为清代刑事审判制度的就地正法,其法律形式可以归纳为以下4类:
1.“律”定之就地正法
清初颁布的《大清律集解附例》卷第一“处决叛军”条规定:“凡边境城池,若有军人谋叛,守御官捕获到官,显迹证佐明白,鞫问招承,行移都指挥使司,委官审问无冤,随即依律处治,具由申达兵部衙门,奏闻知会。若有布政司、按察司之处,公同审问处治。如在军前临阵擒杀者,不在此限(按:事后须奏闻)。”同卷之“吏卒犯死罪”条规定:“凡在外各衙门吏典、祗候(即皂吏)、禁子,有犯死罪,从各衙门长官鞫问明白,不需申禀,依律处决。然后具由申报本管上司,转达刑部,奏闻知会。”(注:[清]沈之奇撰,怀效锋、李俊点校:《大清律辑注》(上),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00—101页。)
在清初的《大清律集解附例》中,“例”的部分尚无就地正法的规定,因为此时严格的死刑审判复核监督制度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但在“律”中这两条有关就地正法的规定非常重要,尤其是对叛军就地正法这一条一直延续下来。这不仅说明清律中有就地正法的制度规定,而且对后来就地正法之“例”和其他规定的形成与实施奠定了法理基础,即在紧急情况下可以实施就地正法。“律”是清朝的基本法,在清代的各种法规中居于主导地位,是各种法规的渊源和基础,是制定和修改“例”时所遵循的宗旨,是“例”实施的指导。因此,军法中的就地正法后来延伸到临阵脱逃、叛乱和军兴之时的盗匪案件审判处置中,前后有一定渊源关系。
2.“例”定之就地正法
在《大清律例》中,有多处有关适用就地正法的明文规定。我们以道光六年的《大清律例》为例,在“兵律”中有:
(1)“直省刁民,假地方公事强行出头逼勒平民,约会抗粮,聚众联谋,敛钱构讼及借事罢考、罢市,或果有冤抑不于上司控告,擅自聚众至四五十人,尚无哄堂塞署,并未殴官者,照光棍例,为首拟斩立决……如哄堂塞署,逞凶殴官,为首斩决枭示……若遇此等案件,该督抚先将实在情形奏闻,严饬所属,立拿正犯,速讯明确,分别究拟。如实系首恶通案渠魁,例应斩枭者,该督抚一面具题,一面将首犯于该地方即行正法。将犯事缘由及正犯人犯姓名刻示,遍贴城乡晓谕。”(注:上海大学法学院等点校:《大清律例》,天津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311页。)
(2)“派往伊犁等处换防种地之满、汉各项兵丁”,“若逃走二次及在原派处所曾经犯逃,移驻伊犁之后复行逃走者,自行投回,应俱用重枷枷号五个月,痛加责惩,折磨差使。如被拿获者,即行正法”。(注:《大清律例》,第317页。)
(3)随征兵丁在军营私自潜逃,“蒙恩免死减发者,如再由配所脱逃,请旨即行正法”(注:《大清律例》,第317页。)。
(4)“凡滇省永昌、顺宁二府以外沿边关隘,禁止私贩碧霞玺、翡翠玉、葱玉、鱼、盐、棉花等物……如有因私贩透漏消息者,审实无论人数多寡,请旨即行正法”。(注:《大清律例》,第323页。)
(5)“在番居住闽人,实系康熙五十六年以前出洋者,令各船户出具保结,准其搭船回籍,交地方官给伊亲族领回,取具保结存案。如在番回籍之入,查有捏混顶冒,显非善良者,充发烟瘴地方。至定例之后,仍有托故不归,复偷渡私回者,一经拿获,即行请旨正法。”(注:《大清律例》,第332页。)
在“刑律”中有:
(1)“粤东内河盗劫之案……如行劫伙众四十人以上,或虽不及四十人,而有拜会结盟,拒伤事主,夺犯伤差,假冒职官,或行劫三次以上,或逃脱二、三年后就获,各犯应行斩决者,均加以枭示,恭请王命先行正法。”(注:《大清律例》,第371页。)
(2)“凡拿获盗犯到案,即行严讯,如有供出行劫别案,讯明次数、赃物,取具确供。其在本省他邑者,即行通详该督抚,无论他邑有无拿获盗犯,总于赃物查起,事主认领之后提解来省,并案审理具题,将该犯即行正法。若系供出邻省之案,其伙盗已获者,应令该督抚关查明确,首、从绝无疑义者,详悉声明题请,即行正法。”(注:《大清律例》,第372页。)
(3)“凡强盗除杀死人命,奸人妻、女,烧人房屋,罪犯深重,及殴事主至折伤以上”者;“未伤人之首盗能于事未发时自首者”;“若伙盗曾经伤人,及行劫两次以上,事未发而自首”者;“窝家盗线,如有自首及闻拿投首者”;“以上各犯遇有脱逃被获,如系近边充军,加等调发,其实发云、贵、两广者,请旨即行正法”。(注:《大清律例》,第375页。)
(4)凡用药迷人得财之案,发配回城伊犁等处为奴的,“到配之后,故智复萌,将药方传授与人,及复行迷窃,并脱逃者,请旨即行正法”(注:《大清律例》,第377页。)。
(5)“谋杀期亲尊长,正犯罪应凌迟处死者……请旨即行正法。”(注:《大清律例》,第441页。)
(6)“凡杀一家三命以上凶犯,审明后依律定罪。一面奏闻,一面恭请王命,先行正法。”(注:《大清律例》,第441页。)
(7)“充军之犯,如在配无故脱逃已逾五日拿获者,无论有无行凶为匪,请旨即行正法。”(注:《大清律例》,第587页。)
(8)“由黑龙江、吉林减回内地充军、拟流,并改发云、贵、两广充军四项人犯,俱调发新疆给官兵为奴,均毋庸具奏。如再脱逃拿获,奏请即行正法。”(注:《大清律例》,第587页。)
(9)“蒙古发内地驿站当差人犯,在配脱逃……如原犯免死减等之罪,本应外遣,因系蒙古改发内地者,仍依免死遣犯逃回行凶为匪例,照原犯死罪即行正法。”(注:《大清律例》,第588页。)
(10)传习邪教人犯,拟发额鲁特为奴,各发犯曾奉有谕旨,如在配脱逃被获即行正法者,应钦遵办理。(注:《大清律例》,第589页。)
道光朝禁烟运动中实施的就地正法,依据的是《严禁鸦片章程》中制定的“新例”:“开设窑口等犯向无治罪专条。今拟沿海奸徒开设窑口,勾通外夷,潜买鸦片烟土,入口囤积,发卖图利,一经审实,首犯拟斩立决,恭请王命先行正法。仍传首海口地方悬竿示众。”(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1册,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566页。)此后,还专门制定了针对外商走私鸦片实施就地正法的专条《洋人携带鸦片入口治罪专条》。它规定,“夷人带有鸦片烟入口图卖者,为首照开设窑口例斩立决,为从同谋者绞立决。由该督抚审明,确系带卖鸦片烟,首从正犯并无替冒情弊,即交该地方官督同该夷人头目,将各犯分别正法,起获烟土全行销毁。”后来由于局势变化,这一规定没有实施。(注:《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1册,第602页。)
3.“令”定之就地正法
清代的就地正法,大多是以皇帝谕令形式针对特定情形形成的临时性“就地正法章程”。它们又可分为两类。
一类是皇帝谕令实施的就地正法。如:
康熙六十年(1721),在镇压台湾朱一贵起义中,康熙帝谕令对台湾地方失职官员“道员以下文职官员,俱著提拿,交总督满保,提督施世骠会同审明,即发往台湾正法”(注: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等编:《康雍乾时期城乡人民反抗斗争资料》下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738页。)。
乾隆三十五年(1770)三月,乾隆帝指示将福建漳浦蔡乌强“谋为不轨”一案中“已获各犯,速行审明定拟,将应行正法之犯,一面办理,一面奏闻”。(注:《康雍乾时期城乡人民反抗斗争资料》下册,第685页。)
嘉庆五年(1800)闰四月二十三日,对铁保奏报浙江绍兴水手张湖广、白文魁等抗官案的处置,上谕认为“将该犯定拟斩枭,所办尚是,但既恭请王命办理,何必再行请旨”;遂令“张湖广著即处斩,传首枭示;白文魁著即处绞,俱在犯事地方办理,以昭炯戒”。(注:《康雍乾时期城乡人民反抗斗争资料》下册,第546—547页。)
二是皇帝认可地方官员采取的就地正法措施。如:
康熙六十年(1721),台湾朱一贵起义,除起义首领被俘解京城外,“其余在军前擒抚诸贼……拟就地正法”(注:《康雍乾时期城乡人民反抗斗争资料》下册,第744页。)。
乾隆四十一年(1776),出现了“围场内偷打牲畜,砍伐木植人等胆敢拒捕”事件,因而规定:“嗣后……若有缉拿之时拒捕不肯就擒者,著加重治罪。其敢于拒捕致伤缉获之人者,拿获时著就地正法。”(注:《清高宗实录》卷1016,“乾隆四十一年九月”,中华书局1986年版。)
嘉庆十八年(1813)九月,河南天理教起义,官兵拿获崔士俊等30余人,“一面录供具奏,即一面将该犯等先行正法”(注:《康雍乾时期城乡人民反抗斗争资料》下册,第871页。)。
清代皇帝的诏令是国家最高的法律渊源,皇帝总揽全国的最高司法权。因而,由皇帝谕令形成的就地正法章程具有法律效力。
4.清末所定就地正法专项条例
太平天国战争时期,在特定情况下由皇帝谕旨形式认定的就地正法之制,在太平天国战争结束后面临合法性危机。朝廷和督抚围绕就地正法的争论正是这一危机的反应。经过各方反复争论,最终在光绪八年(1882)四月由刑部起草了一个正式的就地正法实施规范,确定“除甘肃省现有军务,广西为昔年肇乱之区,且剿办越南土匪,以及各省实系土匪、马贼、会匪、游勇,案情重大,并形同叛逆之犯,均暂准就地正法,仍随时具奏备录招供咨部核查外,其余寻常盗案,现已解勘具题者,仍令照例解勘,未经奏明解勘者,统予限一年,一律归复旧制办理。倘实系距省窎远地方,长途恐有疏虞,亦可酌照秋审事例,将人犯解赴该管巡道讯明,详由督抚分别题奏,不准援就地正法章程先行处决,以重宪典而免冤滥。得旨,如所议行。”(注:[清]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中华书局1958年版,总第1318—1319页。)刑部的草案经朝廷批准下令施行,成为新的就地正法之制的法律依据。其作用为:一是明确授权;二是限制范围,明确权限,包括实施的对象和空间范围;三是以列举具体情形表明其暂时性,从而与死刑复核程序相一致,并可留有修改余地。
宣统元年(1909)四月,当时的法部对光绪朝的就地正法之制做出修订,除剿办胡匪的东三省外,各省“土匪、马贼、会匪、游勇”,只有“啸聚薮泽,抗拒官兵,形同叛逆”时,才暂准就地正法。此修改意见由朝廷颁布施行。此后,宪政编查馆还对就地正法规定中的“抗拒官兵”做出进一步的司法解释:“抗拒官兵,自系指派兵剿办时而言,凡由军营官兵……登时于军前拿获者,暂准讯明禀请军令,立予就地正法。此外事后捕获人犯,但有拒捕情形,只能按律治罪。”(注:《法政浅说报》第17期,转引自李贵连《沈家本传》,第168页。)这是清代第一次从诉讼法的角度对就地正法做出专门的法律规定。
(二)施行就地正法的对象和范围
(1)聚众抗官个案中的就地正法。如乾隆三十七年(1772),湖北京山县严金龙“纠众不法”一案,主犯严金龙父子、施晋三和全国灿等于审明后,即恭请王命,押赴市曹处斩,传首枭示。(注:《康雍乾时期城乡人民反抗斗争资料》下册,第691—692页。)
(2)谋反个案中的就地正法。如嘉庆十八年(1813)九月,河南天理教起义,官兵拿获崔士俊等30余人,“一面录供具奏,即一面将该犯等先行正法”(注:《康雍乾时期城乡人民反抗斗争资料》下册,第871页。)。
(3)贩卖鸦片案件中的就地正法。如道光二十年(1840)八月十二日,林则徐查办邱阿长、卢文秀出洋向夷船购买烟土入口转卖案,“即于审明后恭请王命,饬委署按察使王笃、督标中军副将赵光璧,将邱阿长、卢文秀二犯绑赴市曹,先行正法,仍传首海口地方悬竿示众”。(注:《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2册,第331页。)
(4)对战俘就地正法。如鸦片战争时期对台湾第二次抓获的49名英俘,道光指示台湾总兵达洪阿进行审讯,了解英人为何来台,内中有无头目,以及中国沿海英军和汉奸情况,获取确实供词。取供之后,除头目暂行禁锢候旨办理外,其余各俘与上年所获130余名俘虏,均即行正法,以纾积忿而快人心。(注:《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5册,第263页。)
(5)对汉奸就地正法。如道光二十一年(1841)四月二十四日,道光谕令奕山,对其拿获多名汉奸,讯明枭示表示赞赏,认为此种奸匪必须尽行诛戮,剿办方可得手。他明令奕山等,严密查拿汉奸,“获到一名,即于讯明时在军前正法,慎毋姑息养奸”(注:《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3册,第489页。)。
(6)对战时滋事匪徒就地正法。如道光二十一年(1841)十二月十八日,钦差大臣怡良奏报,就在台湾堵剿英船之际,有嘉义县匪徒江见等意图乘机起事,南路同时响应。经台湾官兵剿办,“现获各犯,当在军前分别正法”。道光批示:“拿获首从各犯,分别正法,办理迅速,可嘉之至。”(注:《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4册,第568、599页。)
(7)对临阵溃逃官兵就地正法。如乍浦失陷后,道光严令奕经等,查明“是日情形究竟若何?其首先逃散弁兵,著一面即在兵营正法,一面据实奏闻,毋得稍存姑息”。同时,谕令防守吴淞口两江总督牛鉴,“恪遵纪律,并力守御,其有首先却退者,即以军法从事。一面先行正法,一面奏闻,毋得稍存姑息,致坏大局,是为至要”(注:《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5册,第308页。)。
(8)对失职官兵就地正法。如康熙六十年(1721),因在台湾朱一贵起义开始阶段当地清军镇压不力,康熙帝谕令对台湾地方失职官员审明后即行正法。(注:《康雍乾时期城乡人民反抗斗争资料》下册,第744页。)
另外,在其他一些紧急情况下,也曾施行就地正法。如道光二十七年(1847)十一月,两广总督耆英等奏报,广东民人黄竹岐等与英人发生冲突,殴毙英人6名,中国百姓也有一死一伤。英方坚持要将中方人犯即行正法。耆英等一开始认为此案系临时起意故杀,“按例应拟斩候,听候部复”,但“夷性躁急,若不酌量变通,该夷不谙中国律例,必疑为支吾迁延,不为究抵,决裂即在顷刻,事关大局,未便因此遽开边衅”。耆英等于是召集广东要员和士绅“悉心筹酌”,决定先将“情重人犯”4名先行正法。随后将梁亚来等4犯提出,在犯事地方先行正法。道光批示“办理尚属妥协”(注:《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7册,第828、832页。)。这应该视为特例。咸丰三年,署江苏巡抚许乃普上奏:“贼迹逼近地方,请将监狱重犯先行正法,以免勾结。”咸丰帝谕令:“著刑部速议具奏。”刑部表示赞同,咸丰帝即日谕令河南巡抚陆应谷:“逆匪窜扰地方开狱纵囚,勾结死党,是其惯技,是以决重囚,亦豫除逆党之一策。”要陆应谷“查明距贼较近各府州县在监狱人犯,如实系强抢重犯及火器杀人在狱待决者,即著酌量缓急,一面奏闻,一面先行正法,毋涉拘泥”(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7册,光明日报出版社1990年版,第353—355、362—363页。)。此后其他省份也采取了类似措施。咸丰四年,直隶总督桂良奏请清廷,“因直隶贼氛未靖”,“将各该州县案犯酌核犯罪情节,其谋故凶盗拒捕杀人重犯法无可贷者,即行正法”。清廷随即“降旨允行”(注:《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15册,第169页。)。
由上可见,就地正法主要是针对聚众抗官、谋反和叛国一类重犯案件及战时出现的特殊情况,实施范围一般是因时、因地、因事灵活运用。
(三)就地正法的司法程序
这方面的情况可根据按例办理与按令执行而分为两类。所谓按例办理,意即就地处决,事后上报备案。这种情况比较简单。如道光十九年(1839)十月十六日,林则徐报告对黄添化通英售卖鸦片一案,俱照新例问拟:“黄添化即黄面胜、彭亚开、邓三娣,均合依沿海奸徒勾通外夷,潜买鸦片入口发卖图利,首犯〈拟〉斩立决例,拟斩立决。”审明后,林则徐当即饬委广州府佛山同知刘开域、署水师提标右营游击王鹏年,将三犯绑赴海口,“先行正法,悬竿示众,以示昭炯。”(注:《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1册,第729页。)嗣后,钟亚二等偷运贩卖鸦片,首犯钟亚二在虎门海口被就地正法。
按令执行的情况则比较复杂,基本上可分为三种程序,一是先斩后奏,事后追认。如乾隆十七年(1752)十月,江西上犹县发生何亚四等“谋为不法”一案,朝廷谕令对俘获的“附逆伙党,当如今年办理马朝柱之例审明,即于该处一面题报,一面正法,毋得曲为开脱,使愚顽知所警惕”。随后,何亚四被拿获,“于审明后,即加以极刑”(注:《康雍乾时期城乡人民反抗斗争资料》下册,第666页。)。又如,咸丰三年,钦差杭州将军瑞昌奏报拿获奸细等8名,其办理就是依据先例:“奴才伏查从前拿获逆犯卢道谈,饬交濮州知州衙门监禁,请旨正法折内,钦奉朱批:‘即应正法,何必交地方官,太属拘泥。钦此’。钦遵在案。奴才谨遵训示,将应行正法之贼犯八名,即行正法。”(注:《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10册,第31页。)这里,多数是有以往谕令惯例作为依据的,但又非正式“条例”,故类似于上文列举的鸦片战争后处理中外纠纷中的违“例”就地正法。这类情况应属于特例。
二是遵旨执行。如乾隆十八年(1753)二月,福建漳州平和县蔡荣祖“谋为不轨案”,“其已究出从逆各兵,虽系为从,必当即行斩决,以儆戎行,不可稍为姑息。再,拿获匪徒既有二百余名,此时已觉为时稍久,若再迟时日,恐至意外,别生事端,殊为可虑。所有供证明确之犯,应处以极刑即决不待时者,此旨到日,即可一面即行正法,一面奏闻。”(注:《康雍乾时期城乡人民反抗斗争资料》下册,第668页。)又如,道光二十二年(1842)六月十三日,道光帝令两江闽浙两广督抚严拿为英人递送京报的汉奸,“将递送该逆京报之人一面正法,一面奏闻”(注:《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5册,第673页。)。
三是请旨执行。请旨执行与先斩后奏是有所区别的。如咸丰二年(1852),咸丰帝针对太平军攻入湖南,提督余万清“辄先出城引避,并将西门防兵带出,以致州城失陷”的情况,紧急谕令:“嗣后统兵大员有临阵脱逃或托病迁延,致误军机者,著该大臣督抚等,一经查明确实,即行据实参奏,请旨正法;其参游以下各员,如有逃避畏葸以致失地丧师者,著一面奏闻,一面即于军前正法,以肃军纪。”这里,对“统兵大员”是请旨正法,对“参游以下各员”是先斩后奏,二者显然有区别。(注:《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3册,第337页。)又如,镇压义和团运动中,对谭文焕一案,地方官认为谭“本系游勇……实与逆匪无异”,“既该布按二司审明不讳,应请旨正法,以昭炯戒”,即按惯例应请旨正法。“惟当洋兵入省,疏脱堪虞,谨遵便宜行事之旨,于拜折后即批饬在省正法,传首被扰地方枭示,以快人心而伸法纪。”(注: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726—727页。)就是说,地方官对谭实际施行的是先斩后奏。
请旨执行是事前报告,于批复后执行,是一种特批程序,有事前监督的作用,但与常规死刑审判复核程序有区别;遵旨执行是事先一般性授权,确定对象、范围和情形,地方遵照执行,事后上报备案;先斩后奏则是典型的事后监督,漏洞也最大。但所有的就地正法按规定都要上报朝廷,也就是说还在朝廷控制范围内。对没有上报的就地正法,则应视为违法行为。
就地正法之制与死刑审判复核制度
清代司法审判,尤其是和死刑审判相关的制度应分两个方面来概括:司法机关的相互制约和司法审判程序上的复核监督。前者包括:
1.地方的审转与题奏
刑事案件的逐级向上申报,构成了上一级审判的基础,清代的法律术语叫做“审转”。距省遥远各厅州县案件一般均“就近审转”,其程序为,徒刑以上(含徒刑)案件在州县初审后,详报上一审级复核,每一级都将不属自己权限的案件主动上报,层层审转,直至有权做出判决的审级批准后才终审。这样,徒刑至督抚,流刑至刑部,死刑最后直至皇帝,所以可以叫作逐级审转复核制。
2.刑部三法司的核拟与皇帝的裁决
各省督抚具题的死刑案件,经过内阁票拟,进呈御前,照例是奉旨“三法司核拟具奏”,于是将案件批到刑部。京师的死刑案件由刑部直接审理,题奏皇帝,而后也经三法司核拟。所谓核拟就是对案卷进行复核,根据《律例》看其量刑定罪是否准确,提出立决或监候的明确意见。核拟后,由刑部领衔,都察院、大理寺会签,以三法司名义向皇帝具题。
死刑的审判、复核监督包括:
1.死刑的审判
按清《律例》,死刑罪名有400多条,包括斩、绞两种正刑和称之为极刑的凌迟(剐),还有枭首(斩后悬首)、戳尸、株连等加重刑。枭首主要用于强盗得财,凌迟主要用来惩处谋反、大逆等严重犯罪,一经皇帝裁决,就立即执行,所谓“决不待时”。清律对于某些过失杀、误杀和职务上的犯罪应处死刑者,称为“杂犯死罪”,其死刑并不执行,照例减等改为待五年,叫作“准徒五年”,五年后再行审核,定生死。死刑中最多的是人命、强盗(包括抢夺、盗窃等)两大类,依情节分别斩绞,因而清代习惯上将死刑案件称作“命盗重罪”或“命盗斩绞重犯”。一般命盗案的斩绞又有“立决”和“监候”的区别,重者立决,轻者监候。立决则立即执行,监候则缓决,在第二年秋审时再复核,定其生死。
2.秋审制度
康熙年间,清朝的秋审所审录的都是死罪重囚,分为“情实应决”、“应缓”、“可矜”、“可疑”等项,分别入理。秋审要在天安门前举行会谳“大典”。此后秋审还有些变化,如取消“可疑”,增加“留养承祀”,但秋审制度的基本内容已经定型,一直实行了200多年。
清代死刑审判复核制度自成体系,有其内在的合理性,在统治者力图展现的法律制度形式上是完善的。因而,后世的研究者对此赞赏有加。张晋藩先生认为清代在司法制度上,“程序完备、审级严格,会审和死刑复核进一步制度化法律化”。清朝刑法在中国封建刑事法律中“最为完备,无论刑法思想、原则、内容、刑制都达到了十分严密、成熟的程度”。乾隆时,“秋审制度进一步规范化,成为饶有特色的完备的封建死刑缓刑复核制度”(注:张晋藩:《中华法制文明的演进》,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25、588、605页。)。郑秦也盛赞“清代的秋审把自古以来的录囚发展到最完备的形式,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独特的死刑缓刑复核制度”(注:郑秦:《清代司法审判制度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201页。)。“从法的发展角度看,秋审制度表明,清朝统治者的法律思想是多么成熟,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融会发展了两千多年来的法律传统思想。”(注:郑秦:《清代法律制度研究》,第203页。)基于这一认识,他们对就地正法自然加以排斥。
清代的死刑审判复核制度确实是古代法制建设的成熟形式。这种“完备”也是清代统治者在文献中试图给人留下的形象。但法制史研究不能停留在制度描述上,而要作制度分析。要作制度分析,首先就不能满足于制度形式上的“完备”,还要看制度的实施过程;此外,不能以死刑审判复核制度为标准来批判和排斥就地正法。在一个司法审判体系中出现了两种看似矛盾的司法程序时,需要弄清楚的是两者关系。而这两者的关系并不是太平天国这一事件中皇权削弱,权力下移所能解释的,这时我们便会发现这一看似完备的制度,从司法实践角度看却存在重大缺陷。
从司法机构看存在两大缺陷。一是省级以下行政司法不分。这就使地方在面对严重的刑事犯罪时首先是作政治上的考虑——维护稳定,因而倾向于选择就地正法这样的简便措施,而不是维护法律规范,确保法律的实施。就是说,刑部和地方政府是不同的执法主体,他们对法律及其实施有不同的态度。双方的差异在清末围绕就地正法的争议中表现得非常明显,地方强烈要求实施就地正法,主要就是从维护社会秩序稳定出发;而刑部则主张停止就地正法,主要是从维护常规法制的角度考虑。我们从下面一例可以更直观地看出两者的差异。
清末法制现代化的核心人物沈家本,任职刑部时,力主“申明法律,慎重刑章”。但在其担任天津知府期间,曾重建因同治九年(1870)“天津教案”而被烧毁的望海楼,楼成以后,民间流行各种传说。适在此时,又查获拐卖孩童人犯,一时民气沸腾,大有一触即发之势。为了平息民愤,沈家本迅速查清案情,将拐卖孩童人犯立即处死。当时有人提醒他说:按照《大清律例》规定,拐卖孩童没有使用迷药,不能处死刑。他回答说:这是特殊情况,不能以“常例”论处,坚持将罪犯处死。由于他的及时处理,很快就平息了民愤。因此其《墓志铭》说他“用律能与时变通也”。就是说,他不拘守死条文,能按照不同情况灵活运用法律。可见地方与中央司法机关因不同身份而对待法律有不同态度,即使在沈家本这样的法律专家身上也是如此。而许多人对沈氏行为的认同和赞赏又似乎昭示着就地正法在特定情况下有其合理性。(注:参见李贵连《沈家本传》,第73页。)
正是由于省级以下司法机构的这一缺陷,为保证法律实施的规范性,有必要建立严格的审判监督和复核制度。这一制度主要是要约束地方,即流刑以上都由中央来控制,以扩大审判监督和追加司法成本来弥补制度缺陷。这无疑增加了审判程序的复杂性和审判复核的数量,增加了司法成本。因此,这一制度设计在遇到社会动乱,重刑案件急遽增加时便难以实施,客观上只能采取就地正法措施。
行政司法不分的另一后果是地方官员法律意识淡薄和法律知识缺乏。即使有职业吏卒的协助,但其司法能力仍必然受到影响。法律意识淡薄和司法能力不足也是简便易行的就地正法受欢迎的原因。总之,地方政府是清代就地正法的主要推动力量。
清代死刑审判复核制度的另一重大漏洞就是皇权专制。由于皇帝具有更改司法制度的权力,这一制度的确定性便是相对的。就地正法之制正是专制皇权的体现,即皇帝与地方政府绕过专门的司法审判监督机关,构成一个简单的司法审判体制,由皇帝授权地方直接处理死刑案件。在清代大多数时间里,就地正法是君主授权,而非我们一般所说的“权力下移”。君主授权不仅使就地正法作为一项司法制度得以成立,而且具有“合法性”。
清代死刑审判复核制度在审判程序上也存在缺陷。“逐级审转”制度不仅是案件卷宗的转送,还包括人犯的押解转送,这不仅耗费人财物,而且不安全,也大大延长了审判周期。秋审制度更是以年为周期。考虑到当时的交通和信息传输条件,以及官僚机构的办事效率,整个司法审判效率的低下可想而知。这一方面增加了羁押人犯的数量和监狱的压力,另一方面影响了及时执法的社会效应,尤其是不能应对突发社会事件和社会动乱。因而社会一旦有大的不稳定,统治者就可能把目光转向就地正法。
可以说,清代死刑审判复核制度的缺陷派生了就地正法之制,反过来说,就地正法之制成为清代死刑审判复核制度的必要补充,两者在维护封建统治秩序方面是一致的。在现代法制意识和法律文化建立之前,基于落后的技术和条件下的法律制度,越是繁复“完备”,越难完全遵照实施。因而与其说清代死刑审判复核制度与就地正法之制是对立和冲突的,不如说两者是相伴而生的。正是相对于严格的死刑审判复核制度,才有就地正法这一概念。清初并非没有就地正法,大规模的杀戮可以说比比皆是,但几乎不见就地正法之说。在康熙朝死刑审判复核制度确立之后,就地正法才开始出现,可见两者是相对应的概念。
这里还要说明的是,清代死刑判决分“立决”和“缓决”两种。就地正法针对的主要是罪应立决的罪犯,因而把就地正法与秋审放在一起讨论是不准确的。
当然,就地正法之制与“死刑审判复核制度”是两种不同的死刑审判程序。
首先,两者在制度形式上不同。死刑审判复核制度是在平时运用的基本的司法程序,是正式的、确定的制度规定,主要由大清律和大清会典中的相关规定构成,具有概括性;其适用范围,涵盖所有的死刑案件;一直贯穿运用于清朝司法实践中,即使在实施就地正法期间,这一制度仍然直接或间接地在发挥效应,清末对就地正法的批判,就是这一制度作用的体现。而就地正法之制是自死刑审判复核制度派生的应急性特殊刑事审判制度,主要是应对叛乱和战时,因而根据具体情况而变化,且往往是临时性的,多数以谕令形式出现,比较具体。其适应范围多数是针对特定情况、特定对象和特定时段。它的实施并不排斥死刑审判复核制度,而是弥补这一制度的不足。
其次,两者立法和司法思想原则有差异。死刑审判复核制度主要体现“恤刑”、“好生”的“仁政”思想和无枉无纵,各得其平的法制精神。康熙帝便主张,以刑弼教,慎刑慎杀,适当宽宥。“朕念人命关系重大,每于无可宽待之中,亦以法外得生之路。”他经常警告官员不得滥刑:“刑罚关系人命,凡审谳用刑,理应恪守宪制,精译[绎]慎重,不得恣行酷虐,致滋冤滥……恐不肖官员,日久玩忽,乃于法外妄用重刑,有负钦恤之意。”(注:《清圣祖实录》卷98、114,转引自俞荣根主编《中国法律思想史》,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253页。)对于这个问题,乾隆帝也屡次申明:“朕临御万机,乾纲独断,宽严之用,务在得中。”“秋审为要囚重典,轻重出入生死攸关……应酌情准法,务协乎天理之至公,方能无枉无纵,各得其平……朕毫不存从宽从严之成见,所勾者必其情之不可恕,所原者必其情之有可原。”“总当按律定谳,不得预存从宽、从重之见,用昭平允。”(注:转引自郑秦《清代司法审判制度研究》,第202页。)
而就地正法的立法原则是“禁暴止奸”、“敷治戡乱”和从重从快、宁枉毋纵的法律精神。如镇压太平天国时期采取就地正法,便是“当此有事之秋”,“不复拘泥成例”,合乎“《尚书》辟以止辟之义”。(注:《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5册,第143页。)曾国藩在奏复中提出:“治一方之匪类”,必须“纯以重典,以除强暴”,“即用巡抚令旗,恭请王命,立行正法”。(注:《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5册,第140—142页。)
就地正法之制与死刑审判复核制度的关系还涉及法制史的一个基本问题——稳定与变化。
对法律与历史问题,美国学者庞德曾提出“法律必须稳定,但又不能静止不变”。“法律思想家所致力解决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将法律固定化的思想与变化、发展和制定新法的思想相协调。”(注:[美]罗思科·庞德著,曹玉堂、杨知译:《法律史解释》,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1—2页。)这实际上也是法律制度和司法实践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因而也是法制史关注的重点所在。法律史就是法律修订史,就是协调稳定和变化关系的历史过程;是法律实施和司法实践经验上升为法律的过程。而这背后主要的动力和压力是政治和社会经济的变化和要求。
清朝的主要法律《大清律例》就是由律与例构成,“律”是祖宗成宪不可改变,“例”是用来辅助补充法律的。对清朝统治者来说,“例”是一种灵活的法律形式,较之固定的“律”更能适应形势的变化,可以随时把他们的意志提升为法律,而不受法律条文的约束,因此在司法实践中广泛推行以“例”断狱。以至“律”、“例”之间前后抵触,以“例”破“律”。学界对此有深入的研究。但在程序法方面,我们却忽略了同样的稳定与变化的结构。其实,死刑审判复核制度就是保持死刑审判的稳定性,而就地正法之制则是适应形势变化的需要。这在法制史中是正常的现象。
标签:中国近代史论文; 清朝论文; 清朝历史论文; 晚清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清史稿论文; 刑事审判论文; 法律论文; 道光论文; 大清律例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