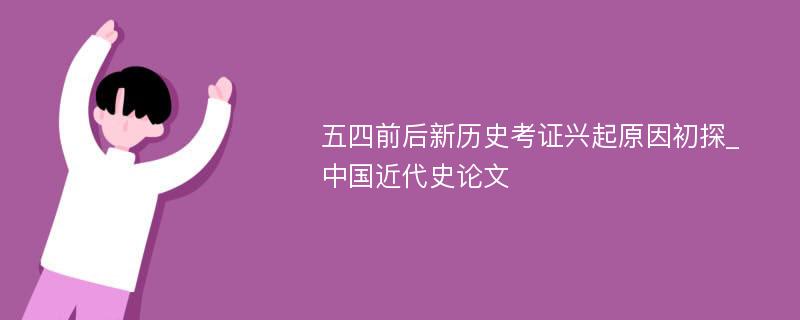
五四前后新历史考证学兴起原因初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原因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47-662X(2003)06-0115-06
纵观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史学,历史考证是史学家们使用的最为普遍的研究方式与方法,所取得的研究成果,以历史考证学的研究成果分量最为厚重,许多著名的史学家,如王国维、陈垣、陈寅恪、钱穆等人,也主要是以历史考证学的研究成果奠定了他们在国内乃至国际学术界的地位。20世纪的中国历史考证学,得益于传统的考证学所打下的坚实基础,但又与传统的考证学有着很大的区别,我们因此称之为新历史考证学。(注:白寿彝在他主编的《史学概论》中说:“‘五四’以后,在史料考订上的成绩,继承了乾嘉考据学的传统,而又大大发展了这个传统,是远非乾嘉考据学所能比的。我们可以称之为新考据学。”(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299页)林甘泉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学》一文中说:“二十世纪的上半叶,近代实证史学是中国史学的主流。”(《历史研究》1996年2期,5页)此外,还有史料派、考史派诸说。考虑到对传统考证学的继承、对西方实证史学的借鉴和与新史学的关系等因素,本文称之为新历史考证学。)新历史考证学在五四前后的历史条件和学术环境下形成并发展起来,对20世纪的中国史学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本文试对新历史考证学在五四前后兴起的原因作一初步考察。
一、清代考证学与新历史考证学的关系
考证(或称考据)是中国传统学术中的一种十分常见的研究方式。表现在史学方面,历史考证学有着悠久的历史。清代的乾嘉时期,考证学得到了充分的发展。考察20世纪新历史考证学的兴起,必须联系到其与清代考证学,特别是乾嘉考证学的承接关系。
以惠栋、戴震、钱大昕等人为代表的乾嘉考证之学,标志着以考经为主的清代考证学的极盛。囿于经学的特征和长期以来形成的神圣地位,对经学的考证总是会存在着某种局限。乾嘉时期的经学考证虽为“极盛”,却也存在着很严重的问题,譬如,经学考证的范围有限,只尊信汉人经说,“凡古必真”,“惟汉是从”,“不读汉以后书”;经学考证是以自身为标准,一切以儒家经典为是非真伪的准则,很难做到真正意义上的考证学所要求的实事求是;经学考证的极盛,客观上出现史学不振、“经精而史粗”、“经正而史杂”的局面。陈寅恪曾评价说:“往昔经学盛时,为其学者,可不读唐以后书,以求速效。声誉既易致,而利禄亦随之。于是一世才智之士,能为考据之学者,群舍史学而趋于经学之一途。其谨愿者,既止于解释文句,而不能讨论问题。其夸诞者又流于奇诡悠谬,而不可究诘。虽有研治史学之人,大抵於宦成以后休退之时,始以余力肆及,殆视为文儒老病销愁送日之具。当时史学地位之卑下若此,由今思之,诚可哀矣。此清代经学发展过甚,所以转致史学之不振也。”这番话是从史学发展的纵向角度,指出了清代经学考证的极盛对史学所造成的负面影响,结论是“有清一代经学号称极盛,而史学则远不逮宋人”。(注:陈寅恪:《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序》,《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38-239页。)这些问题有些是乾嘉学者所无法超越的,只能待之于经学的神圣地位被打破,方有可能跨出新的一步,有些问题确为乾嘉学者所意识到并努力在史学的考证上给予纠正。
钱大昕的经学考证水准在清代即属一流,但他以更多的精力涉足史学,原因之一就是他看到了经尊史卑的偏向,并力图扭转这种局面。在《廿二史考异》的序言中,钱大昕概括了史学的价值及历史考证学的宗旨:“史非一家之书,实千载之书。祛其疑,乃能坚其信,指其瑕,益以见其美”,“惟有实事求是,护惜古人之苦心,可与海内共白。”(注: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序》,《廿二史考异》,商务印书馆,1958年,第1页。)他批评了当时重经轻史的现象,认为自宋元以后,“道学诸儒,讲求心性,惧门弟子之泛滥无所归也,则有呵读史为玩物丧志者,又有谓读史令人心粗者。此特有为者言之,而空疏浅薄者托以借口,由是说经者日多,治史者日少。彼之言曰:经精而史粗也,经正而史杂也。予谓经以明伦,虚灵玄妙之论,似精而实非精也。经以致用,迂阔刻深之谈,似正而实非正也。”(注:钱大昕:《廿二史劄记·序》,《廿二史札记》下册,中华书局,1984年,第885-886页。)此段议论在经学大盛的乾嘉时期来看,不可谓不尖锐。同为经史大家的王鸣盛自述其治学经历:“予束发好谈史学,将壮辍史而治经;经既竣,乃重理史业。”“始悟读史之法,与读经小异而大同。”“治经断不敢驳经,而史则虽子长、孟坚,苟有所失,无妨箴而贬之。”(注: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序》,《十七史商榷》,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1、2页。)钱、王二人均指出了专事经学考证的某种局限。具有了这样的认识,便可知乾嘉历史考证学,立意十分深刻,而以钱大昕、王鸣盛、赵翼等人的研究成果为代表的乾嘉历史考证学的成就则更当不可忽视。柳诒徵在《中国文化史》的“考证学派”一章中明确表示:“世尊乾嘉诸儒者,以其以汉儒之家法治经学也。然吾谓乾嘉诸儒所独到者实非经学,而为考史之学。”(注:柳诒徵:《中国文化史》,《学衡》64期(1928年7月),第50页。)要言之,就清代乾嘉史学而言,并非事事“不逮”前人,其历史考证学在当时的条件下就已达到极高的水准。(注:汪荣祖在《陈寅恪与乾嘉考据学》一文中说:“陈氏曾批评清代史学的‘不振’,此一批评须与他所说清代史学不如宋代一语,合而观之,所以不如,不是考证的方法不如,而是清代缺少综合性、通论性的史学巨著与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比美。”所言甚是。见汪著《陈寅恪评传》附录一,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2年,248页。另,杜维运著《清代史学与史家》一书,对此亦有相近见解,见该书第1-14页,中华书局,1988年。)
清代历史考证学是20世纪新历史考证学的直接源头。以钱大昕为例,“钱大昕治史具有严谨的态度和严密精审的方法,与近代科学方法和理性精神相符合,他的丰富考证成果和精良的治史方法,为二十世纪考证学的崛起打开广大法门,成为传统学术向史学近代化演进之重要中介。”(注:详见陈其泰:《钱大昕:历史考证的精良方法及其影响》,《史学与民族精神》,学苑出版社,1999年,第360页。)此外,王鸣盛对于典章制度和学术史问题的考辨,赵翼对于一个时期的历史特点与历史趋势的总结和探究历代盛衰治乱的努力,崔述对于古史的考证等,不仅为20世纪新历史考证学家充分重视,而且还自觉地承袭之,使其成为新历史考证学的先导。譬如,王国维以“乾嘉之学精”而概括出的乾嘉学术的代表人物之一是以历史考证学著称的钱大昕(另一位是戴震)。(注:王国维:《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观堂集林》卷,第23,36页,《王国维遗书》第4册,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陈垣自述其治学之初,“专重考证,服膺嘉定钱氏。”(注: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302页。)顾颉刚说崔述“已经给予我们许多精详的考证了,我们对于他应该是怎样地感谢呢!”(注:顾颉刚:《自序》,《古史辨》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46页。)
王国维和陈垣是新历史考证学的两位巨擘。王国维主要采用清代考证学(主要是考经)中文字音韵训诂学的治学路数来治史。他考史的方法是二重证据法,“地下之新材料”与“纸上之材料”相互“补正”的途径,是文字音韵训诂之学。梁启超说:“小学本经学附庸,音韵学又小学附庸,但清儒向这方面用力最勤,久已‘蔚为大国’了。”(注: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329页。)清代学者把文字音韵训诂之学纯熟运用于考证之中,王国维对此深得要领,但又大加发展,用以考释新旧材料,“古史新证”。他认为:“苟考之史事与制度文物,以知其时代之情状,本之诗书以求其文之义例,考之古音,以通其义之假借,参之彝器,以验其文字之变化。由此而知彼,即甲以推乙,则于字之不可释,义之不可通者,必间有获焉。然后阙其不可知者,以俟后之君子,则庶乎其近之矣。”(注:王国维:《毛公鼎考释序》,《观堂集林》卷,第6,17页,《王国维遗书》第1册,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许冠三指出:“王学的最大建树在古史研究,古史研究的出发点在古文字学,立足点在小学。亦即由小学以通史,正如乾嘉诸老之由小学以通经。”(注: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104页。)陈垣则直接师承清代历史考证学家的方法和精神,全祖望、顾炎武、钱大昕、赵翼、王鸣盛等清代考史大家向为陈垣所推重。无论是他“竭泽而渔”地搜集材料、列举类例和归纳演绎的研究方法(注:参见牛润珍:《陈垣学术思想评传》,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第247-260页。),还是寓通史以致用、表彰民族气节于考证之中的深刻用意,均深得清代历史考证学的精髓。可见,他们的治学都以清代考证学为出发点,只是所承继的重点有所不同。
晚清以后,社会的剧变导致了学术风气的转移,最主要的是今文经学的复兴取代了古文经学的一统地位。历史考证在研究对象与研究旨趣上也发生了相应转变。王国维说:“道咸以降,涂辙稍变。言经者及今文,考史者兼辽、金、元,治地理者逮四裔,务为前人所不为,虽承乾嘉专门之学,然亦逆睹世变,有国初诸老经世之志。”(注:王国维:《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观堂集林》卷,第23,36页,《王国维遗书》第4册,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考证的方法仍在继续延用,而考证的宗旨则转变为以“经世”为要务,民族史、边疆史地等成为历史考证新的主要的研究领域。梁启超在讲到清朝末年的学术变化时认为:“清朝正统学派——即考证学,当然也继续工作。但普通经学史学的考证,多已被前人做尽,因此他们要剑走偏锋,为局部的研究。其时最流行的有几种学问:一、金石学;二、元史及西北地理学;三、诸子学。”(注: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122页。)晚清以来考证学的变化表明,历史考证仍然是学人治学的主要方法,考证之学也绝非就意味着脱离现实,相反,晚清史家究心于边疆史地、辽金元史诸领域的考证研究,都与现实有着密切关系。清代考证学的发展和变化,为20世纪新历史考证学的出现,在方法和旨趣上都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
二、新历史考证学形成的原因
20世纪新历史考证学之所以能够从传统考证学中脱胎而来,基本前提是走出经学的羁绊,区别出经学考证与历史考证间的异同,在力图摆脱经学束缚的基础上认清传统考证学的价值。钱穆指出:“晚清康廖诸人之尊经,其意惟在于疑经,在发经之伪,在臆想于时代之所需要而强经以从我。盖经学之至于是已坠地而且尽。”(注:钱穆:《经学与史学》,杜维运、黄进兴编《中国史学史论文选集》第1册,华世出版社,1976年,第136页。)晚清时候,经学自身的发展已呈穷途之势,而史学却更加受到重视。诸如王国维、梁启超等人,已将研究的主要精力转入史学。梁启超“由经师弟子转变而为新史学家。”(注:周予同:《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522页。)王国维“对于学术界最大的功绩,便是经书不当作经书(圣道)看而当作史料看,圣贤不当作圣贤(超人)看而当作凡人看。”(注:顾颉刚:《悼王静安先生》,陈平原、王枫编《追忆王国维》,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第132页。)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狂飙扫荡,经学走向终结。五四时期史家对于如何看待与处理经学的材料和研究方法极为重视,综其所论,有两点非常突出:
其一,视经学的材料为史学的材料,视经学为史学,扩大了史学的研究范围。1921年,吕思勉在《论经学今古文之别》一文中说:“吾辈今日之目的,则在藉经以考见古代之事实而已。夫如是,即‘发生今文与古文孰为可信’之问题。予谓皆可信也,皆不可信也。皆可信者,以托古改制之人,亦必有往昔之事实,以为蓝本,不能凭空臆造;皆不可信者,以其皆为改制之人所托,而非复古代之信史也。”(注:李永圻编:《吕思勉先生编年事辑》,上海书店,1992年,第106页。)这段议论颇有代表性。吕思勉已不再纠缠于今文、古文的孰是孰非,而是涵盖了今古文双方“皆可信皆不可信”,其立意在于史学,即“藉经以考见古代之事实。”顾颉刚回顾二十年代的经史关系时,也有同样的观点:“窃意董仲舒时代之治经,为开创经学,我辈生于今日,其任务则为结束经学。故至我辈之后,经学自变而为史学。惟如何必使经学消灭,如何必使经学之材料转变为史学之材料,则其中必有一段工作,在此工作中我辈之责任实重。”(注:顾颉刚:《顾颉刚读书笔记》卷5,转引自顾潮、顾洪著《顾颉刚评传》,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年,第10、11页。)其二,仍然看重经学考证的方法,强调用治经的方法治史。梁启超、顾颉刚、吕思勉等史家都极言应“有意识地”以治经之法治史,如柳诒徵列举三礼、古音、六书、舆地、金石等“一一如其法以治之”,应当是后人努力的方向。(注:柳诒徵:《中国文化史》,《学衡》64期(1928年7月),第51页。)
不过,如果仅仅是将治经的方法移植过来,并不足以形成传统考证学向新历史考证学的转型,梁启超讲得十分清楚:“凡此皆以经学考证之法,移以治史,只能谓之考证学,殆不可谓之史学。”(注: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44-45页。)金毓黻同样认为:“考证之学,本不能独立成一学科,而吾国之治经,即等于研史,不惟治经当用考证学,即就史学而论,亦无不用考证学,为其治史之方法也。”历史考证,本为史学研究的常见方法。但是,“果其所用之方法,日有进步,则旧书可变为新,否则不惟不进步,而日呈衰颓之象,则新者亦变为旧矣。是故研究之对象,不论其为新为旧,而其研治之方法,则不可拘守故常,而应日求其进步,其所谓新,亦在是矣。”(注:金毓黻:《中国史学史》,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397页。)史学走出经学羁绊的更深刻的意义,是史学得以摆脱经学思想和义例的长期束缚,有可能将追求历史真实真正作为观念和方法上的学科目标。黄进兴指出:“传统经典已不复是最后诉求的权威,史料与事实的关联方构成新史学关怀的焦点。”(注:黄进兴:《中国近代史学的双重危机:试论新史学的诞生及其所面临的困境》,《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新6期(1993年),第276页。)中国史学一直有着强调实录的“求真”精神,但这是囿于传统史学范畴之内的。现代意义上的史学“求真”,始于儒家经典神圣光环的被打破,以及对学术“独立”的追求和对学术研究自身的“尊重”。梁启超说学者应该“为学问而学问,断不以学问供学问以外之手段”,学问的价值,“在善疑,在求真,在创获”。(注: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86页。)他以“求真”、“求博”、“求通”为标准来衡量治学,其中又以“求真”为首位。(注:梁启超:《治国学的两条大路》,《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九》,中华书局,1989年,第113-114页。)顾颉刚则认为,学问“只当问真不真,不当问用不用”,“应用只是学问的自然结果,而不是着手做学问时的目的”。(注:顾颉刚:《自序》,《古史辨》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25页。)传统的历史考证学是以实事求是和无徵不信为基本准则的,这与五四前后要求为学术而学术、视学术为目的而把“求真”作为首要目标的治学宗旨基本相符合。不同的是,旧的考证学在贯彻实事求是的原则方面,在观念上和认识上均有诸多的束缚和局限,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有可能摆脱这些束缚和提高认识程度,这是新历史考证学的“新”之所在。
新历史考证学之所以“新”,还新在“科学方法”。五四时期对“科学方法”的提倡和使用,是促成新历史考证学兴起的更为直接的原因,“此为蒙受西方之影响而然。”(注:顾颉刚:《自序》,《古史辨》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25页。)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旋律是民主和科学。五四时期对民主和科学的提倡遍及当时中国的思想、文化、学术领域,对史学的影响当然也是巨大的,带来了史学从观念到方法上的更新。五四时期形成了输入西方史学理论与史学方法的热潮以及史学科学化的要求,随之而来的就是中西史学结合的问题。将“科学方法”与中国传统的考证学相联系,是当时学术界结合中西的主要呼声和趋势。
胡适、梁启超等是最主要的倡导者。胡适反复地强调这样的意思:“中国旧有的学术,只有清代的‘朴学’确有‘科学’的精神。”(注:胡适:《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胡适文存》卷2,上海亚东图书馆,1926年,第216页。)他将实验主义中的实验的方法、历史的方法、存疑的方法与清代考证学的方法相结合,提出了“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著名学术口号。这其实可以看作是他的“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号召的具体实践方针。胡适的“科学方法”不仅是借“输入学理”来“整理国故”和“再造文明”,“更重要的是,使得胡适悟出现代科学法则与古老中国的考证学在内在精神上是相通的。”(注: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90页。)胡适曾经回忆道:“杜威对有系统思想的分析帮助了我对一般科学研究的基本步骤的了解。他也帮助了我对我国近千年来—尤其是近三百年来—古典学术和史学家治学的方法,诸如‘考据学’、‘考证学’等等。[这些传统的治学方法]我把他们英译为evidential investigation(有证据的探讨),也就是根据证据的探讨,[无徵不信]。在那个时候,很少人(甚至根本没有人)曾想到现代的科学法则和我国古代的考据学、考证学,在方法上有其相通之处。我是第一个说这句话的人;我之所以能说出这话来,实得之于杜威有关思想的理论。”(注:胡适:《胡适口述自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97页。)胡适“感觉到清代的朴学与近世西洋所谓科学方法相合,遂以现代学术的眼光表扬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于清儒之中,尤特别表扬戴震、崔述,这都于当时的治学的风气发生了很大的影响。”(注:齐思和:《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燕京社会科学》2卷12期(1949年10月),第23页。)梁启超同样多次提及清代考证方法的科学意义,如他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清代学者,刻意将三千年遗产,用科学的方法大加整理,且亦确已能整理其一部分。……故清儒所遵之途径,实为科学发达之先驱,其未能一蹴即几者,时代使然耳。”(注: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四》,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76-77页。)
胡适、梁启超等强调的“科学方法”,都是从方法论的角度力图找到沟通中西学术的途径,史学从中受到的启发和影响最大。顾颉刚总结说:“过去的乾嘉汉学,诚然已具有科学精神,但是终不免为经学观念所范围,同时其方法还嫌传统,不能算是严格的科学方法。要到五四运动以后,西洋的科学的治史方法才真正输入,于是中国才有科学的史学所言。”(注: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引论》,胜利出版公司,1947年,第2-3页。)走出经学羁绊的中国史学既已认识到应将“经学考证之法移以治史”,而考证的方法又“暗合科学的方法”,这在崇尚“科学”的五四时期,是新历史考证学得以最终形成的更重要的原因。
史学“求真”,除去主观上的认识和努力之外,对史料有着很高的要求。人们已经认识到,“审定史料乃是史学家第一步根本工夫。西洋近百年来史学大进步,大半都由于审定史料的方法更严密了。”(注: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4页。)“近百年来欧美史学之进步,则彼辈能用科学的方法以审查史料,实其发轫也。”(注: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三》,中华书局,1989年,第99页。)受到西方史学理论与方法的影响,五四时期的学者对史料的搜集、鉴别和利用给予充分重视。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导言》、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等论著,都重点对史料做了理论上的阐释,区分出不同类别的史料,概括出各类史料的特点,论述了史料的搜集与鉴别的方法。这番工作不仅从理论上论证了以往被认为是不可触动的儒家经典、以往不被许多人承认的材料(如金石、甲骨)都是史学研究的有价值的资料,扩大了史料的范围,而且为以实事求是、求得历史真相为鹄地的历史考证学开辟了新发展的广阔前景。
极富机缘的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新史料的大发现又为新历史考证学的形成和发展带来了意外的生机。传统的历史考证学以文献考证为主,实物考证间或有之,但成就毕竟有限,因为对实物史料的认识和使用是与所发现的实物史料的价值和规模成正比的。乾嘉时期的金石学不可谓不盛,但是仍无法与20世纪初以来的史料大发现所产生的影响相比,很大原因就在于这次的史料发现“自来未有能比者也。”(注:王国维:《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学衡》45期(1925年9月),第1页。)新史料的发现,使得历史考证学研究豁然开拓了许多新的领域,也刺激了新历史考证学的形成和发展。因此,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首次明确地将文献史料与实物史料放在了同等重要的地位来看待。新发现的史料中,甲骨文因罗振玉、王国维等学者的整理和考证而很快显示出了其对于“茫昧无稽”的上古史的重大价值。罗、王以后,新一辈的学者如唐兰、容庚、柯昌济、商承祚等人对甲骨文的研究均对古史考证做出了贡献。“甲骨文和金文经过科学的洗礼,再加上考古学上的其他发现,便使古代文化的真相暴露了出来。”(注: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引论》,胜利出版公司,1947年,第3页。)西北简牍、敦煌文书的发现,均为新历史考证学在中古史、民族史、历史地理等多方面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有利条件。由于史学界利用新发现的史料考证中国古史收益甚多,1922年,有人以“专门旧学之进步”将这种状况总结为“昔人所谓考证之学,则于最近二十年中,为从古未有之进步。”(注:抗父:《最近二十年间中国旧学之进步》,《东方杂志》19卷3号(1922年2月10日),第33页。)十七年之后,金毓黻的《中国史学史》中“最近史学之趋势”一章,针对上述观点有所辨正:“与其谓为旧学之进步,无宁谓为国学之别辟新机,与其谓从古未有之进步者为考证学,无宁谓为史学。”(注:金毓黻:《中国史学史》,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397页。)金氏所论的依据,“悉为近三四十年间之收获”,他明显意识到了考证学与史学的密切关系。其时,历史考证学已经发展成为中国史学的主流。
具备了在沟通中西的基础上的“科学方法”的提倡,明确了在研究目的上应“揭发历史真相”,还有对史料的科学系统的认识和新发现的史料的支持,所以梁启超提出:“我们现在做这种工作,眼光又和先辈不同,所凭藉的资料也比先辈们为多,我们应该开出一派‘新考证学’。”(注:梁启超:《治国学的两条大路》,《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九》,中华书局,1989年,第113页。)
值得一提的是,五四时期开始出现的新的史学建制所逐步形成的现代史学规模对史学人才的培养,促成了新的史学考证人才辈出的局面。五四时期的北京大学、清华学校等院校纷纷设立专门的研究机构,如北大研究所国学门、清华国学研究院,目的是“研究中国高深之经史哲学。其研究之法,可以利用科学方法,并参加中国考据之法。”(注:清华大学校长曹云详于1925年致清华国学研究院开学词,载《清华周刊》350期,见齐家莹《清华人文学科年谱》,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9页。)这些专门的研究机构,虽称“国学”,实以史学研究为最主要内容,由教授专门指定和指导学生的研究范围和论题,学生的毕业论文以历史考证方面为最多。以清华国学研究院为例,第一届学生的毕业论文题目涉及历史考证学的主要有:王庸《陆象山学术》、《四海通考》,吴其昌《宋代天文地理金石算学》、《朱子著述考》,杜钢百《周秦经学考》,汪吟龙《文中子考信录》,姚名达《邵念鲁年谱》,何士骥《部曲考》,余永梁《殷虚文字考》、《金文地名考》,徐中舒《殷周民族考》、《徐奄淮夷群舒考》等。(注:见苏云峰:《清华国学研究院述略》,《清华汉学研究》2辑,清华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304-305页。)史坛新人既有着从小打下的传统学术的坚实基础,又经过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在观念上较少束缚,在思想上锐意进取,新历史考证学后劲丰实,产生了一大批有分量的研究成果。
要之,新历史考证学既得益于传统考证学所打下的坚实基础,又受到了五四时期特定的时代条件和学术环境的深刻影响。对西方学理的借鉴,对史学“求真”的重视,对“科学”的历史学的追求,都成为历史考证学的内涵,也是20世纪新历史考证学形成的主要原因,而新历史考证学的形成与迅速发展,则成为中国史学转型过程中史学科学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标签:中国近代史论文; 中国文化史论文; 清代学术概论论文; 王国维遗书论文; 读书论文; 中国史学史论文; 梁启超论文; 中国学者论文; 胡适论文; 钱大昕论文; 顾颉刚论文; 古史辨论文; 自序论文; 王国维论文; 科学论文; 历史学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