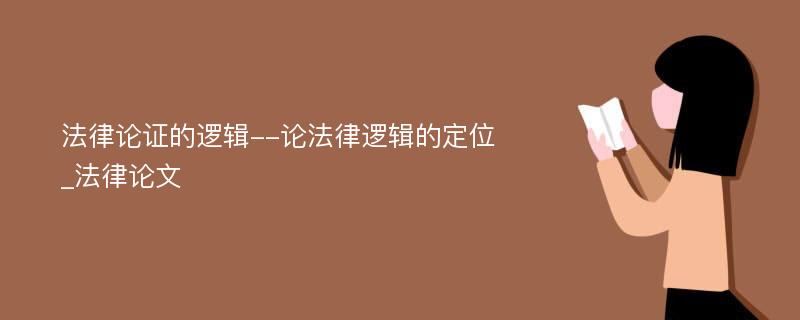
法律论证的逻辑——试论法律逻辑的定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逻辑论文,法律论文,试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924(2007)03-0042-07
法律逻辑在我国出现的时间并不长,对其定位仍存在一定的争论。现在法律逻辑作为一门学科或理论,面临多方责难,处于“逻辑学界不认同,法学界不愿看,实务界看不懂”的尴尬境地。面对这种困境,早在1997年,我国法律逻辑学界著名学者雍琦教授就已提出关于法律逻辑性质及走向的思考,他所提出的若干建议直到今天仍极具借鉴意义[1]。但法律逻辑研究的现状却未见大的改观,这由今天各类名为法律逻辑学的教材可见一斑,“逻辑”加“案例”仍为其共同特点。相比之下,我国的法哲学界对法律逻辑相关领域的探索与研究却取得了相当成就,围绕法律推理与法律论证的研究成果颇丰,有以法律推理和法律论证为中心的较有影响的张保生、解兴权、王晨光、陈锐和焦宝乾等学者的博士论文,有葛洪义、陈金钊和张琪等在这方面有较多研究的学者的各类研究成果。这些探索与研究无疑对进一步为法律逻辑定位有所助益。
法律逻辑作为一门关涉逻辑学与法学双重领域之学科,想简单地将两者“捆绑”在一起,缺乏一种将二者融合起来的进路或维度,是难以成功的,更不可能很好地满足司法实践之需。在此,我们仍不妨将目光移向欧美,近代以来,那里的法学家 (主要是法哲学家)与逻辑学家的诸多思想是我们建构中国法律逻辑的“他山之石”,他们对法与逻辑关系的探讨为我们建构适合中国司法实践之法律逻辑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也为中国法律逻辑的定位提供了极大的帮助。
1 西方法哲学界对法与逻辑关系的探讨
1.1 20世纪60~70年代以前,西方法哲学界对法与逻辑关系的探讨。这一阶段主要是指从近代资本主义制度建立到20世纪60~70年代以前这一时期。18~19世纪,是西方自由资本主义时期,亦是其法治国形成与确立时期,伴随这一时期的是形式主义的法律观,这种法律实践,是对前资本主义社会法律决定的任意性、非理性之反对,是与启蒙思想一脉相承的。在方法论上,对逻辑(主要指形式逻辑)方法情有独钟,逻辑方法甚至一度被抬高到至高无上的地位。这种方法与观点认为,法律是一个完备、一致与明确的体系,每一个案件均可以从现有法律体系中通过形式逻辑(主要为演泽的方法)获得解决方案。这种形式主义的法律观,对于清除前资本主义法制的弊端和确立近现代资本主义法治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但是,随着哲学思想的两次转向,即认识论转向和语言学转向,人们对形式主义之方法逐渐采取了怀疑主义的态度,到20世纪中期后,形式主义的思想与方法已基本被解构了。伴随着哲学思想的巨大转变,法学思想与方法也随之发生重大转变。针对形式主义法律观,在西方首先出现了现代法律思想,在美国主要有以霍姆斯为代表的实用主义,以庞德为代表的社会学法学,以卢埃林和弗兰克为代表的现实主义法学,其共同特点是对形式主义法律方法的反动。霍姆斯就提出了他的那句名言:“法律的生命始终不是逻辑,而是经验。”这里的逻辑,就是指形式主义法律观中的三段论演绎逻辑;所谓经验则包括“可感知的时代必要性、盛行的道德理论和政治理论、公共政策的直觉知识 (无论是公开宣称的还是无意识的),甚至法官及其同胞所共有的偏见等等,所有这一切在确定支配人们所应依据的规则时,比演绎推理具有更大的作用”[2]160。以庞德为代表的美国社会学法学的兴起,不仅是为了反对传统的自然权利观点,而且也是对分析法学所主张的那种形式主义观点的一种回应[2]157。美国现实主义法学主要反对的是以美国法学家兰德尔为代表的“形式主义法学”或“概念论”的。现实主义法学中,卢埃林系规则怀疑论者,弗兰克系事实怀疑论者。前者对法律规则能指引法官判决的传统观点表示怀疑,后者认为法律不确定的主要原因来自案件事实。卢埃林认为,美国法律自19世纪以来有两种不同的风格,他反对所谓的形式风格,形式风格主要是指仅仅根据法律规则判案;认为政策仅与立法部门有关,而与法院无关;判决意见是以演绎和单线形式来表述的;“原则”可以而且应该用来取消那些“异常”的案件或规则[3]324。作为事实怀疑论者,弗兰克所提出的司法判决之公式为:
R(规则)×SF(subjective fact,主观事实)=D(判决)
所谓“主观事实”是指法官、陪审官所发现的事实,并不是初审以前在特定时间、地点发生的实际的“客观事实”[3]341。弗兰克认为,法官也是人。人在正常的思维过程中(除了有限的简单情况),并不是遵循形式逻辑的三段论推理路线作出判断[4]372-373。
因此,这一阶段主要是形式主义法律观由顶峰逐渐走向衰落的历史时期。但逻辑(主要指形式逻辑)作为证立法律结论的理性标准之一和工具价值往往被贬低甚至抛弃了。
1.2 20世纪60~70年代以后,西方法哲学界对法与逻辑关系的探讨。20世纪60~70年代以后,受哲学的语言学转向与后现代主义思想之影响,西方法哲学界中出现了一些新的思想派别或学说,它们对法与逻辑的关系有了更深入的探讨。主要有美国波斯纳的新实用主义法学派、比利时佩雷尔曼的“新修辞学”法律思想、美国博登海默的综合法学、德国乌尔弗里德·诺伊曼的法律逻辑学、荷兰以爱默伦和荷罗顿道斯特为代表的阿姆斯特丹学派的语用-辩证的法律论证理论和德国阿列克西的法律论证理论,等等。波斯纳在其《法理学问题》(1990)一书中,提出了“实践理性”的新经验推理说。他认为,演绎逻辑的三段论推理对于维护法律的确定性和法治原则起着重要作用。然而,逻辑推理的作用有限,它只能解决简单案件中的法律问题,对于疑难案件和一些涉及伦理问题的案件,逻辑推理就无能为力了。在法庭辩论的场合,仅凭逻辑演绎不能决定对立的议论中的哪一种主张是正确的。所以,他主张用实践理性的推理方法对逻辑推理加以补充。实践理性被理解为逻辑方法用尽时人们所使用的多种推理方法。是囊括了常识、想象、反思、共感、先例、类推、隐喻、逸闻、经验、发言者的权威、动机的归责、记忆等推理方法的集合体[5]40。波斯纳反对的是法律形式主义,但并未完全否定形式逻辑在法方法论中的作用。佩雷尔曼的新修辞学法律思想是对现代西方哲学语言学转向的一个回应。他认为,新修辞学可以解释为辩论学。它的研究对象是讨论问题的技术,主要目的在于促进人们在思想上接受向他们提出并争取他们同意的命题。新修辞学也研究得以使辩论开始和展开的条件以及这种辩论的效果。他认为,将逻辑和形式逻辑等同起来,一切非形式的推理都不属于逻辑范畴,这种看法是错误的。他认为,在推理的整体中,形式逻辑只应保留一个适当的位置;新修辞学要填补形式逻辑的不足。形式逻辑是限于根据演绎法或归纳法加以说明或证明的技术,而新修辞学增加了辩论技术。这种辩论技术的目的在于说服听众(或读者),尽可能使他们相信,争取他们同意向他们提出的观点的价值,在持有不同意见的公众中争取最大限度的支持[3]435-438。他所以认为法律逻辑不是形式逻辑,而是包括在类推推理、法律理由的辩论等供法官完成其任务之用的一些工具,方法论工具或智力手段[3]446。总的说来,他的新修辞学大大改变了关于逻辑的传统概念,即形式逻辑的概念,逻辑学不仅仅从形式方面去研究概念、判断和推理,而主要是研究它们的实质内容。作为综合法学代表人物的博登海默认为,形式逻辑在解决法律问题时具有相对有限的作用,我们已不再相信概念法理学的可能性了,因为论者创立概念法理学的目的就是为了建构一个在定义上严格而又一致的法律概念系统,并期望这种系统能够为法官审判其所受理的一切案件提供可靠的、机械的操作标准,而要使法律成一个完全的演绎制度,这是永远不会成功的[2]517。但另一方面否认或者缩小形式逻辑在法律中的作用也是不恰当的。如果我们不是完全无视道德与社会方面的考虑,也不是错误地把逻辑认为是“机械式” (clockwork)的推理行为,那么我们就一定能够得出结论说,逻辑和经验在行使司法职能过程中与其说是敌人,毋宁说是盟友[2]517-518。德国学者乌尔弗里德·诺伊曼的法律逻辑学是对法与逻辑关系的重要探讨。他指出,法律逻辑学有双重含义,因为逻辑学有广狭义之分,广义上指“方法论”,狭义上的逻辑学仅涉及形式规则,即关涉其有效性不依赖于特殊适用范围的规则。他论述了司法三段论的相关问题,如逻辑演算(包括命题演算、谓词演算),逻辑在法律中效用能力问题(包括法律命题的形式化、公理化),法学中“形式的”逻辑和“自然的”逻辑问题,论及法律逻辑与法律论证的关系,其核心思想是,法律逻辑学是可以形式化的,但所带来的问题或负面影响也很多。他指出,法律规范和法律命题的形式化存在理论和实践的保留。其一,几乎所有著名的尝试,患有令人不愉快的副作用,特别是道义逻辑在这期间,为自己的研究领域建立了许多悖论。其二,收益问题仍未解决,耗费巨大的行动明显地降低了收益。把“计算精确的”法律者,与那些习惯于用钳子来穿裤子的男人(意为脱裤子放屁)相比,显得并非全不适宜[6]315-339。
而以阿列克西为代表的法律论证理论则主要是从建构新的法律逻辑理论为其主要目标。这实际上代表了法律逻辑学的一个新的,也是更有活力和前途的发展方向。
2 法律论证理论对法与逻辑关系的积极探讨
以阿列克西的法律论证理论为代表的法律论证理思想也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法哲学界一重大思想潮流,其对法律与逻辑之关系所作的探讨影响甚大,为建构适合司法实践需要的法律逻辑提供了新的路径。从广义上看,佩雷尔曼的新修辞学法律论证理论、麦考密克的法律裁决之证立理论和阿尔尼奥的法律解释之证立理论都对法律论证理论做了深入的探究,并取得了相当的成就。法律论证理论成为法学理论和法律实践所关注的一个重心所在。
法律论证理论的最早思想渊源是来自于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古代辩证法。古代辩证法是指通过对话进行对话、商谈和论辩的技术。这种辩证法与康德、黑格尔及马克思所谓的辩证法是不同的。尽管法律论证与法律一样历史悠久,但法律论证理论成为系统理论则是在20世纪70年代。法律论证理论为什么出现在这个时期?法律论证理论的出现是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的回应,也是对现代及后现代法哲学对法律是什么和法律如何正当化问题的不同解读之回应。哲学的第一次转向,即由本体论转向认识论,确立了理性主义法律观,法治由此进入近现代阶段。但这种受启蒙理性及近代自然科学主客体二分思想影响而产生的各类法哲学,实际上并没有达到捍卫理性主体——人在法律实践中的主体地位。因为司法不可能是自动售货机,法官也不纯粹就是法律的嘴巴,法律与道德或伦理的关系或者说法律的正当性问题仍是不容回避的问题。由此,追求主体间性的法律成为解决这一难题的基本思路。同时,哲学的语言学转向也为此提供了基本工具。尽管主体对客体的认识是建立在主客两分的前提下的,但在认识过程中,作为主体的人不可能是纯粹客观的,他是受“前见”影响着的,是戴着有色眼镜来看世界的,他所看见的世界是受一套特定的制度、思想方式,甚至风俗习惯所修改过的世界。总之处于认识过程中的认识主体不是超验、先验的理性主体,而是经验的理性主体。由于语言是理性的载体,是理解的基本工具,是主体交往的基本手段。语言对于行为主体来说处于一种先验的地位,对于主体来说是一种客观存在。本体论哲学和认识论哲学局限于语形和语义分析层次,而语言哲学则延伸到语用分析的层次,通过分析语词在具体语境中的用法,获得相关的知识。这种语言哲学深刻影响到法哲学,法哲学界也出现了语言学转向,如英国哈特的新分析法学。但德国法哲学的语言学转向最为彻底与直接[7]。哈贝马斯作为捍卫现代性的学者就是将其理论建构在以语言沟通为基础的交往行为理论上。他指出,如果从言语行为对命题知识的交往运用出发,就会做出有利于另一种和古代逻各斯观念有着密切联系的理性概念的预断。这种交往理性概念的内涵最终可以还原为论证话语在不受强制的前提下达成共识这样一种核心经验,其中,不同的参与者克服掉了他们最初的那些纯粹主观的观念,同时,为了共同的合理性概念而确立起了客观世界的同一性及其生活语境的主体间性[8]10。而在法律论证理论方面颇有影响的阿列克西同样是将其理论建立在语言学研究的基础之上。他所建立的法律论证的理性论证程序的主要内容就是法律论证所要遵守的语言交流规则。阿列克西的理论是在对实践论辩中的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规范证立的各种理论批判借鉴基础上建立的,这些理论涉及到语言哲学(语用学)、现代逻辑和对话商谈理论。涉及的主要理论大家与派系有维特根斯坦(语言游戏概念)、约翰·奥斯汀(言语行为理论)、黑尔 (道德语言理论与道德论证理论)、图尔敏(道德论辩分析和一般论证理论)、拜尔(道德论证分析)、哈贝马斯(真理共识论)、埃尔朗根学派的实践商谈理论与佩雷尔曼的新修辞学论证理论等。阿列克西正确地指出了法律论辩与普遍实践论辩的一致与区别,他们在正确性要求上有局部一致性,在规则、形式方面存在着结构上的一致性。区别是法律论辩是在现行有效法约束的条件下进行的,其正确性是要求在有效法秩序框架内能被理性的加以证立即可,法律论辩必须有一个最终清楚的结论。另外,法律论辩中双方角色不是对等分配的、程序有时效限制,等等[9]355-356。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自己的法论证理论,其法律判断的证成分为两个层面:内部证成和外部证成。所谓内部证成处理的问题是:法律判断是否从为了证立而引述的前提中逻辑地推导出来,外部证成的对象是这个前提本身的正确性问题[9]274。内部证成主要是形式逻辑之操作,而外部证成才是核心,即法律论证理论之主题,外部证成分为对实在法规则、经验命题、既非经验命题亦非实在法规则的前提的证成。阿列克西的理论虽不尽善尽美,但他一反后现代解构之倾向,以建构新理论为己任,这作为一个成功的尝试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为我们构建法律逻辑学提供了一个极有前途的路径。法律逻辑不应将自己局限于形式逻辑之操作,而应当走法律论证的方向,法律逻辑应是一种法律论证逻辑。
法律逻辑学要想确立学科合法性,必须有自己准确的定位,要与传统逻辑有所不同。若仅将法律逻辑作为传统逻辑在法律领域中的应用,法律逻辑学就无从获得学科合法性,对法律实践也难有大的助益。国内外都有不少学者主张,法律逻辑学的研究对象应当是法律推理,但国内和国外学者所指的法律推理却并非完全一致。说到法律推理,我们就不可避免的要涉及推理的含义。国内学者对推理的含义,一般界定为,推理是由已知判断引出新判断的思维形式[10]144。考察推理的两个方面分别是,一是前提真实,这是由实践和各门具体科学解决的问题,另一个是推理形式正确,这是形式逻辑着重研究的问题[10]148。因此,就国内学者的观点而言,推理和论证的区别主要表现为,两者对前提的要求不同,论证要求前提是真实的或可接受的,而推理并不要求前提真或可接受。假命题之间完全可以进行合乎逻辑的推理[11]8。因此,推理只断定前提与结论间的逻辑联系,它并不要求断定前提(也包括结论)本身的真实性或可接受性,也就是说,推理并不关注思维的内容。论证则不仅要关注思维的形式,而且还要关注思维的内容。由于论证要关注思维形式,所以,论证要借助推理来进行,论证的过程就是运用推理的过程,但推理不一定都是论证。另外,论证是有目标导向的,即,论证的目标是对论题的肯定或否定(可接受或不可接受),而推理一般并不强调这种目的性,因为它只关注从前提到结论的思维形式,至于结论的肯定与否定(可接受或不可接受)并非其关注的重心。但是,在涉及法律推理时,这种推理的含义在国内学者中似乎又和上述关于推理和论证的区别不相协调和一致。如解兴权认为,法律推理是特定法律工作者利用法律理由权威性地推导和论证司法判决的证成过程或证成手段[12]6。张保生认为,法律推理是特定主体在法律实践中,从已知的法律和事实材料合乎逻辑地推想和论证新法律理由的思维活动[13]84。从这两个典型的关于法律推理的定义来看,其中都包含一个共同的概念“论证”,这里似可得出这样的结论,国内学者事实上是将法律推理和法律论证等同起来,或者是在同一意义上使用的。这样,国内学者关于法律推理的含义有意无意地又与国外学者关于法律推理的含义相一致了。如史蒂文·伯顿就认为,法律推理可视为在法律论证中运用法律理由的过程[14]110。Kent Sinclair认为,法律推理可以被分析为不是自然或社会过程的一个阶段,但作为过程本身,它是论证(argument或辩论)过程。一般而言,论证(辩论)所描述的是形成理由、得出结论以及将它们应用于一种正在思考的情况的活动或过程[13]821。国内只有极个别学者对法律推理从道义逻辑角度即推理的角度来进行研究。①由此,国内对法律推理的研究实际上可大致分为两大类别,一类是法律逻辑教科书中将法律推理视为传统逻辑推理在法律领域中的具体应用,一类是将名为法律推理而实为法律论证作为研究对象的研究。②
需要注意的是,国外学者往往将法律推理和法律论证作为同一意义使用,也就是说,如果考虑到法律推理所处的法律实践的语境,则区别法律推理与法律论证也就没有多少实际的价值,因为此时法律推理中的推理很难也可以说是不可能脱离法律实践这种语用因素的纯语形和语义的行为了。因此,仅从术语的使用来看,在法律领域特别是法律逻辑领域里,使用法律论证较之于使用法律推理也更有其合理性。
3 非形式逻辑思想对法律逻辑定位的影响
西方逻辑学界在20世纪后半叶所兴起的非形式逻辑思想对法律逻辑的定位从另一个侧面产生了相当重要的影响。非形式逻辑可以而且应当成为法律逻辑理论与实践的重要方法与工具,其涉及的3个主要研究方向是论证(或论辩)理论、修辞学和谬误理论。但是,非形式逻辑在我国尚未被主流逻辑学界所承认,在大学逻辑教学中更无一席之地。非形式逻辑在20世纪后半叶产生与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为了解决形式逻辑在面对自然语言中的“非形式”推理之困境而应运而生的一种识别、分析和评估论证的逻辑。尽管现代形式逻辑在20世纪前半叶日趋成熟,取得了相当高的成就,但这种形式化逻辑在面对自然语言中的“非形式”推理时其效用大受限制,时常捉襟见肘。大学里的逻辑学课程离生活实践越来越远,它不能为学生提供分析诸如法庭论辩、政治论辩、日常生活论辩及论文写作等过程中所出现的论证的结构、重建、解释和评估的问题。由此,逻辑在人文学科中的地位与作用被贬低甚至误解。西方大学中兴起了对逻辑教学进行改革的浪潮,出现了所谓的批判性思维、论证或论辩逻辑、谬误及非形式逻辑等教材,现在通称为非形式逻辑,这些逻辑教材一改往日形式逻辑一统天下的局面,形式逻辑在其中往往只占很小的部分且是为非形式逻辑服务的。这些教材改变了往日逻辑教材中人造例证的情形,其所举例证紧贴生活,如在报刊、法庭和政治生活中所出现的论辩中的论证实例。非形式逻辑3个主要研究方向或领域的研究成果在欧美已极其丰富,我国的逻辑学界与法理学界理应重视这个方面的研究,并做出回应,这对我们的逻辑观与法律观足以产生强烈的冲击。
传统形式逻辑和数理逻辑主要是基于语形和语义的研究,而非形式逻辑主要是基于语用的研究,亦即从语境及语言的使用角度所进行的研究。形式逻辑和非形式逻辑的主要区别在于,形式逻辑是一种证明的逻辑,而非形式逻辑是一种论证的逻辑。以论证研究为基础的谬误理论、论辩理论、新辩证法、新修辞学及批判性思维都被划入非形式逻辑领域中,其中,谬误研究在论证理论中一直占有重要地位。亚里士多德就是把谬误分析作为其论证理论的组成部分,他研究谬误的专文《辩谬篇》被认为是研究论证的《论题篇》的第九卷。谬误研究在逻辑史上一直得以延续,特别是随着非形式逻辑的兴起与发展,谬误研究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从一个侧面促进了论证理论的成熟。以荷兰爱默伦和荷罗顿道斯特为代表的阿姆斯特丹学派的语用—辩证的论辩理论对论证的探讨是在对话语境中展开的,论辩关注的重点是论辩的种类、结构和理性讨论的规则。由加拿大学者沃尔顿提出的新辩证法也是将论证放在论辩的语境中加以理解,即把论证视为在共同推理的双方之间进行的一种对话性交流。以佩雷尔曼为代表的新修辞学注重论证的内容以及论证对于听众的可接受性向度。批判性思维对论证的关注是多角度和批判性的。
非形式逻辑尚未发展到如现代形式逻辑即数理逻辑那样成熟的理论体系,同时,对其性质和地位仍存在不同的意见,但这并不妨碍它作为法律逻辑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的作用,以研究论证为主旨的非形式逻辑对法律逻辑的定位产生了相当重要的影响。非形式逻辑以研究论证为己任,法律论证一般也是非形式逻辑领域内的学者所关注的一个重点。那些著名的非形式逻辑学者往往也是法律论证研究的专家。不少非形式逻辑学者甚至将法律论证(或论辩)作为其研究论证的典范,其著作中常涉及法律论证的实例,不少著作甚至以专章研究法律论证,研究法律论证或论辩的专著也不少见。如佩雷尔曼著有《法律逻辑:新修辞学》(1976)、《法律和辩论》(1980)和《正义、法律和辩论——道德和法律推理论文集》(1980)等,沃尔顿著有《法律论辩和证据》(2002)。③
我们用非形式逻辑来分析司法实践中法律思维与法律方法问题,主要涉及以下方面:法律论证的评价标准问题,法律论证的结构问题,诉讼主张的要求问题,庭审论辩规则,证据负担与证据确认规则问题,案件事实认定标准与规则问题,等等。非形式逻辑尽管试图提出分析和评估论证的一般工具,而不是分析和评估特殊类型论证的工具,但其理想理论将包含论证的一般理论和将它应用于推理的具体实例程序。将司法实践作为非形式逻辑基本原理应用的一个特殊且重要的领域,但不能将非形式逻辑的基本原理简单地应用于司法实践,而应致力于两者的一致与差别上做细致入微的研究。例如,通过论证图示的研究,以期对法律论证有更准确的评估,通过对论证评估标准的分析,以期对法律论证的评估更切合实际,通过对非形式谬误的研究,以期对法律论证的分析更具针对性和批判性(如诉诸权威的论证与诉诸权威的谬误,人身攻击与人身攻击谬误在法律论证中的鉴别问题)。等等。非形式逻辑主要是研究论证的目的、结构、规则、程序及评估问题,试图给出论证研究的一般原理。以非形式逻辑为工具来分析法律论证,法律逻辑学因此可以获得新的发展空间。
4 结束语
对西方近现代逻辑学界和法哲学界对法律与逻辑关系的较为系统的回顾,我们可以尝试性地得出结论说,法律是逻辑所关注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领域,逻辑在法律中的地位与作用随着哲学思想之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谈到法律逻辑的定位我们需要关注这些思想因素的影响。但不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对于“法律”与“逻辑”各自的性质与范围的认定均有较大的差异。对于“法律是什么?”和“逻辑是什么?”的回答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法律逻辑的定位。西方18至19世纪的形式主义法学认为法律就是或主要是立法者所制定公布的法律文件或法官判决的先例,而逻辑指的就是形式逻辑,在此情况下的法律逻辑,只能是以形式逻辑来解决法律适用中由大前提法律规则与小前提案件事实到判决结论之过程中的方法问题。这种法律逻辑观已经受到19世纪末以来众多法学流派的批判,这种批判成为西方法哲学进入现代与后现代阶段的一大契机。但对形式主义法律观的批判往往走向另一个极端,投入了相对主义与怀疑主义的泥沼中,未能提出合适的替代方法,因而不能完全替代形式主义而成为主导的法律逻辑观。这种解构或曰后现代倾向对于尚未历经近代法治的当代中国法治实践来说,其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可能是致命的。因为,对法治建构尚不成熟的社会中的法治进行解构将对法治的基础构成严重威胁。因此,我们在对法律逻辑进行定位的时候,将面临解构与建构,即批判与重建的双重任务。
通过以上论述,笔者以为,中国的法律逻辑应定位为法律论证的逻辑,其理论与实践的路径应为非形式逻辑。
注释:
①如陈锐所著《道义逻辑研究——法律规范推理论》,南开大学2001年博士论文。
②焦宝乾所著《法律论证导论》(山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3月版)是国内较早的一部研究法律论证的专著。
③相关内容可参考:[荷]伊芙琳·T.菲特丽丝著《法律论证原理——司法裁决之证立理论概览》(张其山等译,商务印书馆, 2005年9月版);沈宗灵著《现代西方法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2年6月版);Douglas N.Walton:Legal Argumentation and Evidence.University Park,Pa.:Pennsyly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2002.
标签:法律论文; 逻辑分析法论文; 法律规则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逻辑谬误论文; 关系逻辑论文; 形式逻辑论文; 逻辑学论文; 推理论文; 修辞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