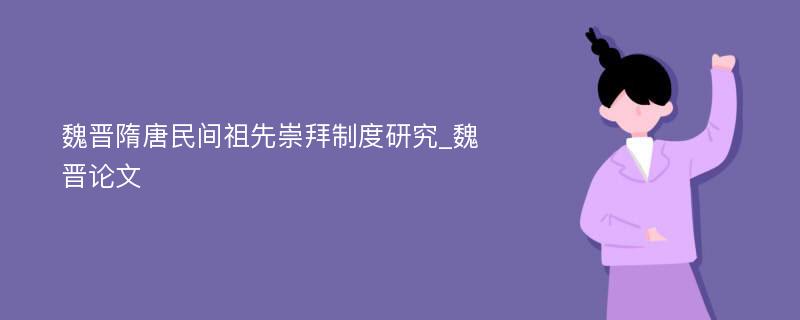
魏晋隋唐时期民间祭祖制度略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魏晋论文,隋唐论文,时期论文,民间论文,制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古代社会的祭祖,既是宗族中的大事,又是国家政治制度的重要一环。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祭祖之制,正处在中国古代社会祭祖制度的转折期,它上承汉代墓祀之制,下启宋明祭祖活动的民间化。深入研究其演化轨迹,对于把握中国古代政治与社会的实质,具有重要意义。
一、厚葬的转变与墓祀的式微
汉代民间的祭祖方式主要是墓祀,它包括两大基本内容:一是墓前祭祀,即洒扫、祭酹、植树、筑祠、立碑等活动;二是墓内祭祀,即墓内祭祀空间的开拓和祭奠。这是一种盛行于汉代的独具特色的祭祖形式。
墓祀之盛行有其深厚的社会背景,它与这一时代的厚葬之风互为表里。墓祀之盛既是厚葬的重要体现,又是厚葬之风的重要动因;而厚葬之风既助长着墓祀的盛行,又延伸着墓祀的功能与价值。就其发展而言,墓祀与厚葬的去路也是完全一致的,都是成于斯、败于斯。就墓祀而言,它所引起的一系列墓前设施及祭仪葬式,已远远超出了一般民众所能承受的能力。如《后汉书·崔骃附崔寔传》载,崔氏家族因竭力建坟茔、修碑祠而倾其所有,导致家业败落,贫困如洗。其传曰:
寔父卒,剽卖田宅,起冢茔,立碑颂。葬讫,资产竭尽,因贫困,以酤酿贩鬻为业。……(寔)建宁中病卒,家徒四壁立,无从殡殓。又如《许安国祠堂题记》所记祠主许安国仅为掾属秩百石,官小位卑,其卒后,父母及三个弟弟“以其余财,造立此堂”,“作治连月,功扶无亟,贾钱二万七千”,而且修得比较讲究。①以许安国的家境,耗资二万七千钱,历经数月修造此祠,可能要倾其所有,甚至部分资金要举贷大家。即便是中家的经济条件,也往往要倾囊而出。如《汉从事武梁碑》碑文就记道:
孝子孝孙躬修子道,竭家所有,选择名石南山之阳,擢取妙好色无斑黄,前设坛墠,后建祠堂,良匠卫改,雕文刻画,罗列成行,摅骋技巧,逶迤有章。②当时人对修筑祠堂之重视可见一斑。所以,当时民间“众庶葬埋,皆虚地上以实地下”③;“人力单于郦墓,玩好穷于粪土,技巧费于窀穸”④,不惜“发屋卖业”⑤,倾家荡产。王符《潜夫论·浮侈》对此也抨击道:
今百姓送终之制,竞为奢糜。主者无担石之储,而财力尽于坟土,伏腊无糟糠,而牲牢兼于一奠。麋破积世之业,以供终朝之费。
这样,盛极一时的汉代墓祀必然会走向其反面。
东汉末年,政局动荡,战乱不息,经济凋敝,流民无数,使民间社会的厚葬之风难以为继。至曹操时代,为恢复经济、兼并诸侯,力倡俭约。建安二十三年(218),曹操更是一反汉代的寝陵制度,提出对自己的陵墓“不封不树”:“古之葬者,必居瘠薄之地。其规西门豹西原上为寿陵,因高为基,不封不树。”⑥此后,他又进一步强调其西原高陵“禁立碑”⑦,反对厚葬。《晋书·礼志中》载:
魏武以礼送终之制,袭称之数,繁而无益,俗又过之,豫自制送终衣服四箧,题识其上,春秋冬夏,日有不讳,随时以敛,金珥珠玉铜铁之物,一不得送。文帝遵奉,无所增加。……汉礼明器甚多,自是皆省矣。
当然,曹操死后实际上还是遵循的汉制。这从后来魏文帝时“亲祠谯陵”和将“先帝高陵殿皆毁坏”之举及曹操遗嘱家人“时时登铜雀台,望吾西陵墓田”之语可以看出。只是受财力限制,规模不及两汉诸帝陵而已。尽管如此,也是开了魏晋薄葬的先河。
魏文帝时,继续提倡薄葬,并将两汉时期的陵寝制度予以废除。黄初三年(222)诏曰:
先帝躬履节俭,遗诏省约。……古不墓祭,皆设于庙。高陵上殿皆毁坏,车马还厩,衣服葬府,以从先帝俭德之志。⑧东汉以来的上陵礼遂被革除。魏文帝在营建自己的寿陵时,又进一步规定:
封树之制,非上古也,吾无取焉。寿陵因山为体,无为封树,无立寝殿,造园邑,通神道。夫葬也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见也。骨无痛痒之知,冢非栖神之宅,礼不墓祭,欲存亡之不黩也,为棺椁足以朽骨,衣衾足以朽肉而已。故吾营此丘墟不食之地,欲使易代之后不知其处。无施苇炭,无藏金银铜铁,一以瓦器,合古涂车、刍灵之义。棺但漆际会三过,饭含无以珠玉,无施珠襦玉匣,诸愚俗所为也。⑨
这样,魏文帝以“古不墓祭”为借口,将曹操陵墓上的陵殿及其设施全部毁掉,把祭祀活动都安排在宗庙进行,还力主自己死后薄葬。陵寝制度由是衰微,“自后园邑寝殿遂绝……终于魏世”⑩。而且,曹魏帝陵墓前设施一律不置,诸如寝殿、便殿、园省甚至墓表、碑碣,一概取消;墓圹多依山傍水而建;而且规定不得墓祭。另外曹魏时期的上陵活动亦十分稀疏,仅有的一次上陵还发生了司马氏诛曹爽的高平陵事变,此后更无上陵之制。故沈约说:“自后至今,陵寝遂绝。”(11)有的学者对此总结道:“三国时期,秦汉盛行数百年的礼仪繁缛,建筑豪华奢侈的陵寝制度衰落了。取而代之的是地面‘不封不树’,地下‘敛以时服’,随葬瓦器的薄葬制度。”(12)
曹操父子的薄葬主张和行为对当时的社会上下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对东汉以来的厚葬之风无疑是有力的否定和约束。从此,厚葬之风锐减。
晋代承袭曹魏遗风。《晋书·礼志中》载:晋宣帝“于首阳山为土藏,不坟不树,作《顾命终制》,敛以时服,不设明器”;“景帝崩,丧事制度又依宣帝故事”;到东晋时,又依然如此:“江左初,元、明崇俭,且百度草创,山陵奉终,省约备矣。”明帝、成帝等即是如此。在统治者的倡导下,上下皆以薄葬为尚,并逐渐成为社会风气。如东晋桓温的坟墓则“平坟不为封域”(13);另外像颜含、庾冰、孔愉、杜夷等死后均行薄葬之礼。南北朝时期同魏晋一脉相承,薄葬风气依然。著名者如刘宋时王微,南齐张荣,梁人顾宪之、王敬胤、刘杳、刘歊等,他们不但身体力行,而且还著书立说,遗命后代薄葬。(14)
另外,自魏文帝废除上陵制度后,后代基本上沿袭了这种做法。如晋宣帝遗诏“子弟群官皆不得谒陵”(15)。这样,从此直到南北朝时期,除个别皇帝进行过此类活动外,谒陵制度一直废而不用,陵园设施也自然不置。《通典》卷五二《礼十二·沿革十二》“上陵”条载唐太常博士彭景直上疏云:
自魏三祖以下,不于陵寝致祭。……至于江左,亦不崇园寝。及宋、齐、梁、陈,其祭无闻。
在皇室废除寝陵及谒陵制度的同时,也废除了王公大臣及民间在墓前列置石刻的制度。西晋以来诸朝均承魏制,如西晋即明文规定:“诸葬者,不得作祠堂、碑、石表、石兽。”(16)十六国石勒时期又进一步下令:“禁州郡诸祠堂非正典者皆除之。”(17)与此同时,一些地方官员、儒者,也在乡间不懈地做这方面的工作。譬如,《北史·苏琼传》言其“每年春,总集大儒卫凯隆、田元凤等讲于郡学……禁断淫祠,婚姻丧葬,皆教令俭而衷礼”。一些士大夫、官员也教令子孙从简而葬,不得修筑墓前设施。如《晋书·皇甫谧传》载皇甫谧著《笃终》云:
故吾欲朝死夕葬,夕死朝葬,不设棺椁,不加缠敛,不修沐浴,不造新服,殡唅之物,一皆绝之。又如《南史·顾宪之传》载其临死前诫子孙曰:
……不须常施灵筵,可止设香灯,使致哀者有凭耳。朔望祥忌,可权安小床,暂施几席,唯下素馔,勿用牲牢。蒸尝之祠,贵贱罔替,备物难办,多至疎怠。祠先自有旧典,不可有阙,自吾已下,止用蔬食时果,勿同于上世,示令子孙四时不忘其亲耳。
士大夫这种不修筑墓前设施的行为,对民间社会产生了明显的影响。
在这种氛围下,汉代曾经盛行一时的墓前建祠、树碑、立石人兽等习俗受到了空前的遏制。检魏晋南北朝诸史,虽然也有修筑墓祠、碑、兽的事例,但规模与数量远不及汉代。要么是个别人想借机沽名钓誉之为。如《宋书·孝义·郭原平传》记其“父丧既终,自起两间小屋,以为祠堂。每至节岁蒸尝,于此数日中,哀思,绝饮粥”。要么是皇帝所赐或是少数世家豪族所为。如《南史·吴明彻传》载:“秦郡降,宣帝以明彻旧邑,诏具太牢,令拜祠上冢,文武羽仪甚盛,乡里荣之。”又,《北史·司马裔传》载,裔为司马休之曾孙,其死后,“诏为起祠堂焉”。再如,《南史·齐宣孝陈皇后传》载:“后尝归宁,遇家奉祠,尔日隐晦失晓,举家狼狈共营祭食。”也有一些是民间百姓出于对某个官员的爱戴、怀念所立。如《北史·张华原传》载:“(张华原)卒官,州人大小莫不号慕,为树碑立祠,四时祭焉。”实际上,这类祠堂已脱离了汉代宗族墓祠的本意。
随着法律对墓前建祠堂的禁止,墓祀之风也告衰歇。这一时期,南北诸史中虽有一些墓侧居丧的记载,但率族墓祭的事例已较为少见,民间一些人甚至根本不去墓前祭拜。如《北史·孝行·吴悉达传》载:
(悉达)昆弟同居四十余载,闺门和睦……刺史以悉达兄弟行著乡里,板赠悉达父勃海太守。悉达后欲改葬,亡失坟墓,推寻弗获。号哭之声,昼夜不止,叫诉神祇。忽于悉达足下地陷,得父铭记,因迁葬曾祖已下三世九丧。倾尽资业,不假于人,哀感毁悴,有过初丧。
从以上悉达欲迁族墓却找不到墓地所在之事,说明民间百姓对墓祭的忽视。需要说明的是,在汉代繁缛的墓祭衰歇的同时,前往先人坟茔扫墓、谒墓之俗渐渐流行。如《魏书·高阳王传》载:“任事之官,吉凶请假,定省扫拜,动历十旬。”《北史·来护儿传》载来护儿富贵后,“谒先人墓,宴乡里父老”;樊子盖也“谒坟墓,宴故老”。(18)这一点被隋、唐两朝承袭下来。另外,墓前设施的禁令到南北朝后期也有所恢复,一般在墓前设置一对或多对石兽。学界有人就此指出:
北魏迁洛以后,迄北齐、北周之世,东汉在墓前树立神道碑、石人、石兽以及兴建高大坟冢,布置家族墓地的做法又渐渐恢复发展起来,磁县北朝墓群中就多次发现墓前石刻,如石人、石羊、石虎等等,尤其是这次司马兴龙墓前石羊的发现,更证明东魏北齐之世墓前神道石刻正处在恢复发展时期。(19)但是,宗族祠堂直到宋代才真正得以复兴,然已大不同于汉代了。
二、家庙与家祭
自魏晋以来,由于统治者对薄葬的倡兴以及对墓前设施的禁止,民间社会对祖先的祭拜地点及其方式渐渐发生转变:那些有权势的官僚贵族多将墓前祭祀改由家庙进行;一般民众则将墓前祭拜改为在家中寝堂进行。晋人卢谌《祭法》谈到:
凡祭法,有庙者置之于座;未遑立庙,祭于厅事可也。(20)南朝宋崔凯论祔庙时也讲道:
祔祭于祖庙,祭于祖父,以今亡者祔祀之也。以卒哭明日,其辞曰:“……用荐祔事,适尔皇祖某甫以隮祔。……今代皆无庙堂,于客堂设其祖座。”(21)这表明这一时期的祭祖主要是庙祭与家祭两种方式。
庙祭就是祭祖于家庙。晋代规定,诸侯王及各品级官僚均可设立家庙,“宗庙之设,各有品秩”(22)。其标准尚无严格规定,大多参照先秦宗庙之礼;祭祀时间、次数也无严格规定。以设立宗庙为例,比如晋武帝时,中山王司马睦与其兄司马逊并为诸侯,依先秦之礼,司马睦只能以其兄立为大宗,但司马睦却希望能立祢庙。结果引起争论。虞喜在论及此事时说:“今士庶始封之君,尚得上祭四代,不拘于嫡,以贵异之,况已尊同五等,更嫌不得其均用丰礼,并祭四代,所以宠之。”(23)西晋太尉荀觊也因“秩尊,其统宜远”,故“亲庙有四”(24)。看来设庙往往因事、因人、因时随机而变,没有一定之规。
一般来说,那些无官无品的平民百姓不得立庙,当然也无法祭先祖于庙堂,只能将家中的厅堂作为祭祖的地点,这也就是所谓的家祭。《晋书·皇甫谧传》载皇甫谧著《笃终》,其中涉及家祭时云:
故吾欲朝死夕葬,夕死朝葬,不设棺椁,不加缠敛,不修沐浴,不造新服,殡含之物,一皆绝之。……礼不墓祭,但月朔于家设席以祭,百日而止。临必昏明,不得以夜。制服常居,不得墓次。夫古不崇墓,智也。今之封树,愚也。若不从此,是戮尸地下,死而重伤。魂而有灵,则冤悲没世,长为恨鬼。王孙之子,可以为诫。死誓难违,幸无改焉!该文否定了汉代以来的墓前祭祖,主张“于家设席以祭”,“不得墓次”;做法是“百日而止。临必昏明,不得以夜。制服常居”。不过,对家祭的方式没有更为详细的陈述。
东晋贺循比较详细地论述了当时家祭的情况。其曰:
今无庙,其仪:于客室设亡者祖座,东向;又为亡者座于北,少退。平明持馔具设及主人之节,皆如卒哭仪。先向祖座拜,次向祔座拜,讫,西面南上伏哭。主人进酌祖座,祝曰:……又酌亡者座,祝曰:……皆起再拜,伏哭尽哀,复各再拜,以次出。妻妾妇女以次向神座再拜,讫,南向东上,异等少退,哭尽哀,各再拜还房。遂彻之。自祔之后,唯朔日月半殷奠而已,其馔如来时仪,即日彻之。(25)由上可见一般百姓多无庙,无法祭祖先于庙堂。所以祭祖之日,须将祖先牌位置于客室,祭拜完毕再撤去。前引卢谌《祭法》及崔凯之论也说到在“厅事”、“客堂”进行家祭之语。一些虽有官爵尚未立庙者,祭祖之礼也在厅堂进行。如《通典》卷五二《礼十二·沿革十二》“未立庙祭议”条云:
晋安昌公荀氏《祠制》云:“荀氏进封大国,今祭六代,暂以厅事为祭室。”
殷仲堪问庾叡:“……依《礼》,祭皆于宗子之家,支子每往助祭耳。又如吾家五等封,乃应有庙。今既无庙,而共家常以厅事为烝尝之所。”自晋以后,大体遵循以品秩尊贵制定祭祖的权力的做法。“自后齐、后周及隋,其典大抵多依晋仪,然亦时有损益矣。”(26)如北齐武帝河清三年(564)所制定的祭祖制度:
王及五等开国,执事官、散官从三品已上,皆祀五世。五等散品及执事官、散官正三品从五品已上,祭三世。三品已上,牲用一太牢,五品以下,少牢。执事官正六品已下,从七品已上,祭二世,用特牲。正八品已下,达于庶人,祭于寝,特用特肫。(27)北齐规定,从七品以上官员可以立庙祭祖;正八品以下乃至庶人,祭祖于寝堂。较之晋代更加严密、规范。隋代在北周基础上稍有更改:“新制……一品已下,五品已上,自制于家,祭其私庙。”(28)进一步将家庙的设置下限定在五品。
唐代基本继承了隋代的做法,但比前代更为缜密、完善。按照唐《开元礼》的规定,五品以上的文武官员得以祠家庙,官品不同,家庙的数量、规模也各不相同;六品以至庶民不得立庙,祭祖的场所只能在家中寝堂进行,即“祭祖祢于寝”。《通典》卷四八《礼八·沿革八》“诸侯大夫士宗庙”条云:
大唐制,凡文武官二品以上,祠四庙;三品以上须兼爵;四品外有始封者,通祠五庙。
五品以上,祠三庙……六品以下,达于庶人,祭祖祢于正寝。
从有关史料看,这一规定也确实得到实施。官品不达者,民间社会未见立家庙者。《太平广记》卷一八二《颜摽》载:
郑侍郎薰主文,举人中有颜摽者,薰误谓是鲁公之后。时徐方未宁,志在激劝忠烈,即以摽为状元。及谢恩日,从容问及庙院,摽曰:“摽寒进也,未尝有庙院。”“庙院”,即家庙。颜摽“未尝有庙院”,恰恰说明民间社会对这一规定的遵循。
如果官员晋升后达到了立庙标准即可依制立庙,申请核准。(29)如李绅立家庙,其家庙碑曰:“斋戒沐祇慄,拜章上言,请立先庙,以奉常祀。于是得请于天子,承式于有司。”(30)又如王涯立家庙,其家庙碑曰:“上章曰,臣涯官秩印绶,品俱第三,请如式以奉宗庙,制曰:可。”(31)
至于建庙的样式、规模也有规定,但是从目前所能掌握的史料看,除了《新唐书·礼乐志三》针对三品官员的规定外,其他尚不清楚,我们只能从中窥其大概。其云:
庙之制,三品以上九架,厦两旁。三庙者五间,中为三室,左右厦一间,前后虚之,无重拱、藻井。室皆为石室一,于西墉三之一近南,距地四尺,容二主。庙垣周之,为南门、东门,门屋三室,而上间以庙,增建神厨于庙东之少南,斋院于东门之外少北,制勿逾于庙。官品达到了立庙之制,一般来说就必须依制设庙祭祖,否则,会遭世讽甚至被罪。《新唐书·王珪传》记王珪“独不作家庙,四时祭于寝,为有司所劾,帝为立庙愧之,不罪也”。
家庙的设置由于受地位的限制,只能五品以上官员设置,民间百姓无权立庙,而唐代规定朝廷命官均不能在故乡做官,所以,唐代的家庙大多设于官员的治所,亦即都市。据甘怀真先生对唐代42例家庙地点的分析,其中38例设于长安和洛阳,4例设于故乡兼治所。(32)常建华先生对这两种立庙情况也进行了研究分析,认为:前一种所设置家庙的官员,从唐初起,已渐渐离开其原有郡望所在的族居地,在长安、洛阳立家庙。因京城土地狭小,人口居多,家庙多不与居处相连。在长安,一般设于皇城南六坊、朱雀街、沿街两旁以及曲江等显要地区,他们视立家庙于京城为荣耀。后一种情形的家庙与宗族有很大的关系。家庙所祀主人必是其宗族的始祖,一般来说,立庙的后代多在家庙附近繁衍。如《游城南记》云,杨瑒在长安城南立家庙,“杨氏苗裔,太和年间尚盛,人呼‘庙坡杨’”。(33)
在墓祀转化为庙祭与家祭的同时,这一时期的祭祖方式也在发生着变化。一般来说,宗族的祭祖要由族统的继承者为之。汉代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中对此也有明确规定。但是,汉代的后子继承的总原则虽然张扬的是血缘亲等关系,重视的是嫡亲,但它又不排斥庶亲。在墓祀之制下,嫡子并不能专擅祭祖,庶子同样可以行墓祀之礼。到魏晋时期,宗子对祭祖的专擅已较为普遍。如前引《通典》卷五二“未立庙祭议”条载:
殷仲堪问庾叡:“依礼,祭皆于宗子之家,支子每往助祭耳。……今既无庙,而共家常以厅事为烝尝之所。”依晋制,祭祖时,由宗子率领进行,支子要到宗子家去“助祭”。殷仲堪为长子,所以其以下诸弟要至仲堪家祭祖,“共家常以厅事为烝尝之所”。
到唐代,祭祖中的传统宗法礼制进一步被打乱,率领宗族祭祖的主祭者不一定非要嫡亲的宗子为之,而以尊贵者为之。如果宗子官秩不如支子,那么由支子主祭,兄陪于位;若兄弟同尊为官,则各自祭祖于寝。《新唐书·礼乐志三》:
凡祭之在庙、在寝,既毕,皆亲宾子孙慰。主人以常服见。若宗子有故,庶子摄祭,则祝曰:“孝子某使介子某执其常事。”通祭三代,而宗子卑,则以上牲祭宗子家,祝曰:“孝子某为其介子某荐其常事。”庶子官尊而立庙,其主祭则以支庶封官依大宗主祭,兄陪于位。以庙由弟立,己不得延神也。或兄弟分官,则各祭考妣于正寝。
因立庙取决于官品,故即使为官者在家中为庶子,也可以立庙,拥有大宗地位,率族人祭祖,处于主祭之位,兄长只能居于陪位。对此,唐后期的吕温曾说道:“近世祭多及旁亲,虽近爱而无义。”(34)这一点与汉魏时期有很大的差别。这样,“唐代的嫡子并没有绝对的政治地位保障,所以,在可考的立家庙诸例中,多是庶子立庙。立庙后,立庙者的家内须实行宗法制,严格分别宗子与支庶”(35)。
另外,祭祖的时间与程式也已固定化。前已述及,汉代的祭祖方式多是墓祀,所以祭祀时间呈现出不固定的特点。而在魏晋时期,随着墓祀的衰微,祭祀时间趋于固定。四时祭祀,魏晋时期已成风俗。《颜氏家训·终制》云:“四时祭祀,周、孔所教,欲人勿死其亲,不忘孝道也。”《北史·崔士谦传》:“卒于州,阖境痛惜之,立祠堂,四时祭飨。”《北史·崔浩传》也有“朝夕养姑舅,四时供祭祀”之语。《南史·顾宪之传》载其临死前所诫子孙曰:“祠先自有旧典,不可有阙,自吾以下,止用蔬食时果,勿同于上世。示令子孙四时不忘其亲耳。”至唐代,则将四时之祭进一步规范化、制度化。《新唐书·礼乐志三》载:
祭寝者,春、秋以分,冬、夏以至日。若祭春分,则废元日。然元正,岁之始;冬至,阳之复,二节最重。祭不欲数,乃废春分,通为四。这样,元日、夏至、仲秋、冬至为祭祖日,也就是祭祀四次。
与之相应,有关祭祖的规范与要求也形之于文字,层出不穷。诸如王肃的《祭法》、贺循的《祭仪》、卢谌的《杂祭法》(又称《祭法》、《杂祭注》)、《家祭礼》、范汪的《祭典》,以及后来傅隆的《祭法》、崔浩的《家祭法》、释僧祐的《杂祭文》、卢辩的《祀典》、徐爰的《家祭》、孟诜的《家祭仪》、徐闰的《家祭仪》、范传式的《寝堂时飨仪》、贾顼的《家荐仪》、卢弘宣的《家祭仪》、周元阳的《祭录》,等等,都对当时民间的祭祖方式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三、墓祭的异化
庙祭与家祭取代了墓祀的祭祖功能,但不能完全满足人们对祖先们的缅怀与纪念,因而,墓前的追思与祭扫在魏晋以来一直存在。对于民间社会而言,低品官员与普通百姓无权设置家庙,许多百姓在寝堂祭祖往往受场所所限,难以寄托哀思,因而墓前的扫祭仍是乡村百姓祭奠先祖、凝聚族人的最好方式。所以民间社会一直不能断其俗。在陈、隋之间,民间已相对固定在寒食节进行墓祭活动。到唐代,对这一既成事实的风俗予以承认,在法律上规定寒食节为拜祖扫墓日期。《唐会要》卷二三《寒食拜扫》载:
开元二十年四月二十四日敕:寒食上墓,礼经无文,近世相传,浸以成俗。士庶有不合庙享,何以用展孝思?宜许上墓,用拜扫礼,于茔南门外奠祭撤馔讫,泣辞,食馀于他处,不得作乐,仍编入礼典,永为常式。此诏一方面“因俗制礼”,将寒食上墓这一来自民间的风俗加以肯定,并把它纳入礼教的范围,“永为常式”;另一方面,又将这一风俗制度化、礼仪化,比如规定“不得作乐”。后来,历玄宗、穆宗、文宗等又进一步完善了这一制度。《唐会要》卷二三《寒食拜扫》载:
(开元)二十九年正月十五日敕:凡庶之中,情礼多阙,寒食上墓,便为燕乐者。见任官与不考前资,殿三年。白身人决一顿。
长庆三年正月敕:寒食扫墓,著在令文,比来妄有妨阻。朕欲令群下皆随私诚,自今以后,文武百官,有墓茔域在城外,并京畿内者,任往拜扫。但假内往来,不限日数,有因此出城,假开不到者,委御史台勾当,仍自今以后,内外官要觐亲于外州,及拜扫,并任准令式年限请假。
太和三年敕:文武常参官拜扫,据令式。五年一给假,宜本司准令式处分。如登朝未经五年,不在给假限。……《唐会要》卷八十二《休假》对寒食扫墓休假制度也有明确记载:
(开元)二十四年二月十一日敕:寒食清明,四日为假。至大历十三年二月十五日敕:自今已后,寒食通清明休假五日。至贞元六年三月九日敕:寒食清明,宜准元日节,前后各给三天。官员可以“五年一给假”,日期由最初的四日升至六日。由此可见唐人对于寒食节的重视。官方对寒食节的肯定和扶持,使这一祭祖习俗空前兴盛。《新唐书·柳宗元传》曾描述民间寒食节扫墓之情形:
近世礼重拜扫,今阙者四年矣。每遇寒食,则北向长号,以首顿地。想田野道路,士女遍满,皂隶庸丐,皆得上父母丘墓,马医、夏畦之鬼,无不受子孙追养者。寒食扫墓的具体程式,《通典》卷一二一《礼八一》“王公以下拜扫(寒食附)”条有一段描述:
先期卜日如常。
前一日,掌事者设次于茔南百步道东,西向北上。备芟剪草木之器。赞礼者设主人以下位茔门外之东,西面,以北为上。
其日,主人到次,改服公服,无者常服。赞礼者曰:“再拜。”主人以下俱再拜。礼赞者引主人以下入,奉行坟茔,至于封树内外,环绕哀省三周。其荆棘虑与荒草连接者,皆随即芟剪,不令火田得及。扫除讫,礼赞者引主人以下复门外位。礼赞者曰:“再拜。”主人以下皆再拜。礼赞者引之次,遂还第。
若解满或远行辞墓,若外官解满或京官辞墓,哭而后行。
其寒食上墓礼如前拜扫仪,唯不占日。(注:……即今之上墓,义或有凭,然神道尚幽,不可逼黩茔域,宜于茔南山门之外,设净席为位,遥祭以时馔,如平生所嗜。若一茔数墓,每墓各设位席,昭穆异列,以西为上。主人盥手奠爵,三献而止。彻馔讫,主人以下泣辞茔。食馀馔者可于他僻处,不见坟所,孝子之情也。)文中“主人”是率领全家或全族祭祖者,当是家长或族长,此仪式基本与开元诏的规定相一致。由文中所述可知,寒食祭祖仪式比较简单,恐怕“泣辞茔”后的“食馀馔”是其主体活动,而且在先人墓前“复为快乐,坐对松槚,曾无戚容”(36)。上引开元二十年四月二十四日敕令规定“泣辞,食馀于他处,不得作乐”以及开元二十九年正月十五日敕令所说“凡庶之中,情礼多阙,寒食上墓,便为燕乐”,即说明这一现象的普遍性。官方之所以采取禁断的态度,仅是从礼仪教化而言的。实际上,当时即使在宫中,寒食节拜扫之余的娱乐活动也十分盛行。如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卷三载:
天宝宫中至寒食节,竞立竖秋千。令宫嫔辈嬉笑,以为宴乐。帝呼为半仙之戏。都中士民相与仿之。民间百姓在拜扫后宴乐歌舞、郊游踏青、击球走马、荡秋千、镂鸡子……更是不亦乐乎。段成式《酉阳杂俎·续集》卷三《支诺皋下》云:
荆州百姓郝惟谅……武宗会昌二年寒食日,与其徒游于郊外,蹴鞠角力,因醉于墦间。在唐代诗歌中也有不少反映寒食拜扫情形的,如白居易的《和春深》诗:
何处春深好,春深寒食家。玲珑镂鸡子,宛转彩球花。
碧草追游骑,红尘拜扫车。秋千细腰女,摇曳逐风斜。可谓写尽寒食节的娱乐风光。
后世沿袭这一风俗。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十四云:“五代礼坏,寒食野祭而焚纸钱。”《欧阳修集》卷一五三《书简》:“今因寒食,遣人力去上坟……为地远,只附钱去,与买香、纸、酒等浇奠。”《金史·董师中传》:“以寒食,乞过家上冢。”明范成大《吴郡志》卷三:“寒食则拜扫坟墓。”
另外,从上引《通典》卷一二一《礼八一》“王公以下拜扫”条中“若解满或远行辞墓,若解满或京官辞墓,哭而后行”一句,可看到,除寒食节的拜扫墓祀外,离家远行者也可拜墓。
总之,一度衰微的墓祭风俗到唐代以后又得以复兴,但这已不是对汉代墓祀的简单回复。唐人将上墓这种敬终追远十分严肃的大事与一系列娱乐活动结合在一起,所谓“今年寒食好风流,此日一家同出游”;“拜扫无过亲骨肉,一年唯此两三辰”(37)。宋庄季裕《鸡肋篇》卷上云:
寒食日上冢,亦不设香火,纸钱挂于茔树。其去乡里者,皆登山望祭,裂冥帛于空中,谓之掰钱。而京师四方因缘拜扫,遂设酒馔,携家春游。(38)这就是说,寒食扫墓祭祖的旨归已不再是虔诚、虚无的祭拜,而更多的是一种世俗的、功利的要求。当然,唐人的这种张扬个性、注重现实享乐的态度,要比汉人一味追求名声、仕途的铺张做法更容易使人接受。从唐代以后,扫墓祭祖成了民间社会生活的一种文化需要,因而同时也具有了一种娱乐意义。由此看来,寒食祭墓不仅能给人们追念先人、禳灾祈福的心理安慰,而且还通过祭祖之余的宴乐、游玩,使人们的精神世界得到释放。
由于清明节在寒食后三天,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逐渐将二节合而为一,当然寒食节的一些习俗尤其是上墓祭祖之俗也移植于清明节中。这样,清明节遂由原来单纯的农业节气演变成为中国古代的一个重要节日。
四、外来佛教对传统祭祖风俗的影响
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佛教的传播和深入,中国古代的传统祭祖丧葬习俗中吸纳了一些佛教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种:
“七七斋”,佛法中又称为“斋七”、“七七斋”、“累七斋”,缘自佛法的轮回观念。即丧家亲属从人死之日起,每隔七日都要为其营斋作法,要斋僧、诵经、超度,进行祭奠,到七七四十九日止,共为七七,故称“七七斋”。《北史·外戚·胡国珍传》载其死后,其女(北魏胡太后)“诏自始薨至七七,皆为设千僧斋,斋令七人出家;百日设万人斋,二七人出家”。《北齐书·儒林·孙灵晖传》亦云:“(南阳王)绰死后,每至七日及百日终,灵晖恒为绰请僧设斋,转经行道。”到隋唐时期,成为乡间风俗。
“盂兰盆节”。佛家的《盂兰盆经》的目连孝母之事与中国古代的孝道相结合,因而被引以为祭祖的日子。“盂兰盆”为梵语Uilambana的音译,意为“救倒悬”。最早见于西晋竺法护译《佛说盂兰盆经》。据载:
大目乾始得六通,欲度父母,报乳哺之恩。即以道眼观视世间,见其亡母生饿鬼中,不见饮食,皮骨连立。目连悲哀,即以钵盛饭,往饷其母,母得钵饭,即以左手障钵,右手搏食,食未入口,化成火炭,遂不得食。目莲大叫,悲号啼泣,驰还白佛。……佛告目连:“十方众僧,于七月十五日,僧自恣时,当为七世父母及现在父母厄难中者,具饭、百味五果、汲灌盆器、香油锭烛、床敷卧具,尽世甘美以著盆中,供养十方大德众僧。……行慈孝者,皆应先为所生现在父母,过去七世父母,于七月十五日,佛欢喜日,僧自恣日,以百味 饭食,安盂兰盆中,施十方自恣僧,愿使现在父母,寿命百年无病,无一切苦恼之患,乃至七世父母离恶鬼苦,升入天中,福乐无极。”(39)
所以,宋人志磐《佛祖统纪》卷三二解释道:“盂兰此翻解倒悬,言奉盆供于三宝福田,用以解饥虚倒悬之急。”佛教的目莲救母故事以及这种鼓励报答父母养育之恩的主张一入中国本土,即与中国传统孝道结合起来,被中国人所接受,并经过加工、改造,成为中国祭祀祖先、追荐亡灵的日子。据《盂兰盆经》所言,在七月十五日,以百味饭食,安盂兰盆中,供奉佛僧,而在南北朝时则改为供奉死去的父母(40)等。如《颜氏家训·终制》云:
四时祭祀,周、孔所教,欲人勿死其亲,不忘孝道也。求诸内典,则无益焉。杀生为之,翻增罪累。若报罔极之德,霜露之悲,有时斋供,及七月半盂兰盆,望于汝也。供奉品也由素食而改为鸡鸭鱼肉等。(41)
到唐宋以后,盂兰盆节与中元节合而为一,成为民间节日,而且祭祖活动成为其主要内容。如唐代杨炯《盂兰盆赋》云:“上可以荐于七庙,下可以纳群动于三事。”《太平御览》卷三二亦载,代宗大历元年(766)“七月望日于(宫)内道场造盂兰盆,饰以金翠,所费百万。又设高祖以下七圣神座,备幡节龙伞裳之制,各书尊号于幡上以识之”。地点设在宫内。宋陈元靓《岁时广记》卷三○引韩琦《家祭式》云:“近俗七月十五日有盂兰斋者,盖出释氏之教,孝子之心,不忍违众而忘亲,今定为斋享。”又云:“律院多依经教作盂兰盆斋,人家大率享祭父母祖先。”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七云:“故者残暑,不过七月中旬,俗以望日素馔享先,织竹为盆盎状,储纸钱,乘以一竹焚之。”这一习俗一直沿袭到清朝。如清乾隆《辉县志》云:“俗于是日,祭先祠,祭墓,或放路灯、放河灯以照孤魂,亦古人设‘盂兰盆’之意。”另外,像二月八日“佛浴节”、四月八日“佛诞节”也都为成为追悼先人、祭祖祈福的节日。
当然,因佛教传播的影响而出现的佛教式祭祖习俗往往流行于特定的时期和特定的人群中,与寒食清明这种举国一体的祭祖之俗相比,具有较大的局限性。
综上所述,汉代的祭祖方式是墓祀,墓祀又是当时社会各阶层祭祖的通式。魏晋以降以至隋唐,随着墓祀的衰歇,祭祖之式一分为三:一是朝廷所设定的庙祭与家祭;二是兴起于民间的寒食扫墓;三是因佛教传入而引发的佛教式祭祖。在此后的发展中,庙祭与家祭汇合,演化为宗祠祭祖,寒食扫墓与佛教式祭祖继续流行。这一演化过程的总趋势就是祭祖的官方色彩不断减弱,民间色彩逐渐强化。这既是中国古代社会宗法血缘关系变迁的直接反映,又是中国古代政治与社会发展的重要标志。
注释:
①济宁文物组、嘉祥县文管会:《山东嘉祥宋山1980年出土的汉画像石》,《文物》1982年第5期;宫衍兴编著:《济宁全汉碑》,齐鲁书社,1990年,第12~13页。
②洪适:《隶释》卷六。
③《汉书·贡禹传》。
④《后汉书·赵咨传》。
⑤桓宽:《盐铁论·散不足》。
⑥《三国志·魏志·武帝纪》。
⑦《三国会要》卷一二《礼中》引《宋志》。
⑧《晋书·礼志中》。
⑨《三国志·魏志·文帝纪》。
⑩《晋书·礼志中》。
(11)《宋书·礼志三》。
(12)刘炜:《三国时期陵寝制度的衰落及其根源》,《四川文物》1986年第1期。
(13)《太平御览》卷五五六引谢绰《宋拾遗》。
(14)以上薄葬人物转引张承宗《六朝民俗》,南京出版社,2002年,第265页。
(15)《晋书·礼志中》。
(16)《太平御览》卷五八九引《晋令》。又见程树德《九朝律考》卷三《晋律考下·丧葬令》,中华书局,1963年,第304页。
(17)《晋书·石勒载记》。
(18)均见《北史》本传。
(19)司小青:《司马兴龙、司马遵业墓志铭考》,《文物春秋》1993年第3期。
(20)《太平御览》卷一八五《厅事》。
(21)《通典》卷八七《礼四七·沿革四七》“祔祭”条。
(22)《晋书·范宁传》。
(23)《通典》卷五一《礼十一·沿革十一》“兄弟俱封各得立祢庙议”条。常建华先生由此条得出结论:“当时异姓诸侯不论嫡庶,皆可上祭四代。”(常建华《中华文化通志·宗族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68页)亦即设立四庙。此说虽然没有更多史料的支持,但在目前情况下,还是可信的。
(24)《通典》卷八一《礼四一·沿革四一》“孙为祖持重议”条。
(25)《通典》卷八七《礼四七·沿革四七》“附祭”条。
(26)《隋书·礼仪志二》。
(27)《隋书·礼仪志二》。
(28)《隋书·礼仪志二》。
(29)参见常建华《中华文化通志·宗族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73页。
(30)《全唐文》卷六七八,白居易《淮南节度使检校尚书右仆射赵郡李公家庙碑铭》。
(31)《刘梦得文集》卷二八《代郡开国公王氏先庙碑》
(32)转引自常建华《中华文化通志·宗族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76页。
(33)参见常建华《中华文化通志·宗族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76~77页。
(34)《全唐文》卷六三○。
(35)常建华:《中华文化通志·宗族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81页。
(36)《唐会要》卷二三《寒食拜扫》,中华书局,1955年。
(37)《全唐诗》卷四七六,熊孺登《寒食野望》。
(38)《元氏长庆集》卷二○,元稹《寒食日》。
(39)《大藏经》卷十六。
(40)有人认为当在唐代宗以后(见谢婉若:《浅析盂兰盆会在中国的民俗化》,《株洲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4年第6期),笔者认为不妥。
(41)参见谢婉若:《浅析盂兰盆会在中国的民俗化》,《株洲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4年第6期。
标签:魏晋论文; 中国古代史论文; 汉代建筑论文; 汉朝论文; 历史论文; 文化论文; 通典论文; 祭祀论文; 寒食论文; 唐会要论文; 上陵论文; 魏晋时代论文; 祠堂论文; 清朝历史论文; 中国历史论文; 东汉论文; 晋朝论文; 魏晋南北朝论文; 文化史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