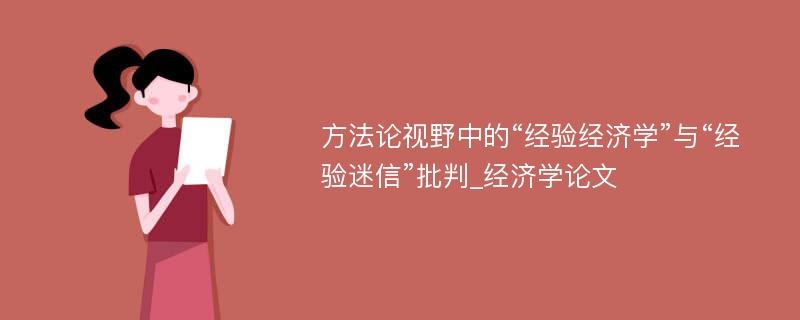
“实证经济学”与“实证迷信”——基于方法论视角的批判,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实证论文,方法论论文,迷信论文,视角论文,经济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07 )05—0077—07
一、经济学家们为何格外钟情于“实证经济学”?
经济学研究人的经济行为,但经济行为从来都是“嵌入”于复杂的社会关系中,并受人的行为目的和动机所驱使。这些复杂的社会关系以及行为的目的和动机总是与人的价值观念相关联,而这些价值观念总是与伦理的、心理的乃至社会文化传统的因素纠缠在一起。因此,经济行为从来都不是“纯洁的”经济行为,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尽管经济学家们也并不否认这一事实,但他们似乎有一个强烈愿望,即试图彻底摆脱那些复杂的社会关系及价值观念的纠缠,将经济学打造成一门能够“鹤立”于其他社会科学(尤其是伦理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的“纯洁的”经验科学,一门甚至可以与自然科学领域的其他经验科学并驾齐驱的学科。为此,经济学家们的基本做法是区分实证经济学与规范经济学,前者只涉及“实然”问题,而后者被划定为研究“应然”问题。在此区分的基础之上,经济学家们再把经济学的主体确定为实证经济学,据说如此便可以将有关价值问题从经济学主体研究领域中驱逐出去,将之推给伦理学、心理学和社会学。换言之,实证经济学成了经济学家们心目中的“纯洁的”经济学。
一个追根究底的问题是:经济学家们为何会有上述这种强烈愿望,亦即格外钟情于实证经济学呢?这个问题与近代以来人们对“科学”的性质的认识有着直接的关系。自弗兰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以来,近代自然科学在性质上被界定为经验科学,这一点几乎已成为共识。经验科学有两个基本特性:其一,理论来自于经验观察;其二,事实与价值严格分开。对于自然科学来说,这两个特性一般被认为是能够具备的;但对于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的经济学来说,即便具备了第一个特性,也难以具备第二个特性。因此,经济学在近代一直被视为至少属于“不纯洁的”科学,它跟伦理学等其他社会科学门类纠缠不清。一个典型事例是,被尊为现代经济学之父的亚当·斯密当初在格拉斯哥大学的教职并非“经济学教授”,而是“道德哲学教授”。如此说来,经济学似乎无望成为“科学”,至少与伦理学一样都成不了“公认的”经验科学。经济学家们显然不愿意接受这样的命运,因而,他们要建立实证经济学的强烈愿望也就可想而知了。试想:倘若这一愿望可以实现,那么,经济学就变成了“真正的”科学,而经济学家们也就随之而变成“真正的”科学家了。
由于上述缘故,经济学家们坚持要区分实证经济学与规范经济学,这种努力可说是由来已久,至少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上半叶的纳骚·西尼尔(Nassau William Senior)和约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19世纪后期的约翰·内维尔·凯恩斯(John Neville Keynes),以及20世纪中叶的弥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虽然这种区分实际上只是纯属问题的重复,但绝大多数从事经济学研究的人似乎仍然认为,这种区分乃是不言自明的,至少是不言而喻的,似乎没有人会怀疑实证经济学乃是经济学之主体,而他们所从事的“实证”研究理所当然地属于“科学研究”。
二、“实证经济学”是如何实现“价值中立”的?
为摆脱人的经济行为中必然涉及到的那些复杂的社会关系及价值观念的纠缠而区分实证经济学与规范经济学,这当然纯属问题的重复,而非问题的答案。实质性问题在于,在这种区分之下,被视为经济学之主体的实证经济学究竟如何摆脱那些复杂的社会关系及价值观念的纠缠呢?
对于这个问题,现在不少专业经济学者或许都会援引“价值中立”这个时髦用语。的确,“价值中立”原先是由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提出的,也是逻辑实证主义者常挂在嘴边的,但它最初渊源于大卫·休谟(David Hume)提出的一个著名命题,即不能从“是”中推论出“应该是”。也就是说,纯事实的、描述性的论述本身只能赋予或暗示着其他事实的、描述性的论述,但永远不可能得出标准、伦理见解或做某些事情的规范。这个命题后来被十分恰当地称为“休谟的铡刀”,其含义无非是在经验事实领域和价值评判领域之间作了一刀切的逻辑区分。“价值中立”概念无非只是对“休谟的铡刀”的某种意义的推广而已。专业经济学者所说的“价值中立”大致也就是如此。
然而,问题还在于:在经济学研究领域果真能做到“价值中立”吗?笔者认为,专业经济学者在求助于“价值中立”时,时常混淆了两个不同性质的含义:一是研究对象本身的“价值中立”;另一是研究者本身的“价值中立”。前者是说研究对象本身并不包含任何价值观念,后者则是研究者本身避开了自身的价值观念,对理论思考和叙述的影响。显然,后者对于任何科学研究来说都是适用的,亦即研究者本身主观上应该尽可能避开价值观念的干扰,尽管客观上他未必完全能够做到这一点;但前者却并非如此,它对于自然科学而言是适用的,因为自然科学领域的研究对象本身确实可以与价值无关,但对于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的经济学而言就不适用了,因为无论如何我们都不能讲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本身也与价值无关。如此说来,经济学家们所说的“价值中立”只能是针对后者,而不能针对前者①。然而,进一步的推断是,如果研究对象本身并不是与价值无关的,只是研究者本身意欲自觉地避开自身的价值观念对理论思考和叙述的影响,在这种情形下还能否做到所谓“价值中立”呢?笔者认为,客观上根本不可能,至多只是主观上宣布为可能。所谓“主观上宣布为可能”,并非是指研究者本身主观上是否可能避开价值观念的干扰,而是说人为地将研究对象中所包含的价值观念排除出研究领域。事实上,主流经济学在建立实证经济学的努力中也正是这么做的。
从经济学说史看,第一个这么做的人就是莱昂内尔·罗宾斯(Lionel Robbins),其做法就是通过对经济学研究的性质和范围加以狭窄界定, 试图以此而将包含在人的经济行为中的一切复杂的社会关系的内容驱逐出经济学研究领域。在《经济科学的性质与意义》一文中,罗宾斯将经济学研究的性质界定为:“这样一门科学,它把人类行为看作是目的与具有各种用途的稀缺手段之间的一种关系来研究”,同时又基于他的“目的—手段”之认识构架,把经济学研究的范围限定于所谓资源配置问题,他说:“给定的资源在不同用途上的分配才是真正的经济问题”(Robbins,1935,p.16)。所谓“资源配置中心论”正是由此而来,它把经济学研究引入了解决人的需求与资源稀缺性之间关系的狭窄领域。应该说,罗宾斯的观点影响深远,因为,此后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始终都没有摆脱肇端于此的“资源配置中心论”的窠臼。但是,他的观点也包含着显而易见的缺陷和不彻底性。这是因为,他所说的“目的—手段”关系中的“目的”,无论如何都无法摆脱价值观念——比如伦理价值观念方面的纠缠。
比罗宾斯做得更为彻底的是新古典经济学。其基本做法是通过设置“理性经济人”这一高度简略化(或简化)的基本行为假设,将包含在人的经济行为中的一切复杂的社会关系及价值观念彻底排除在外。在新古典世界里,“人”被简化为两种类型的“原子式”个体——消费者和生产者;这两种“原子式”个体的行为中所蕴涵的一切社会的和历史的内涵被全部撇开,只留下两个行为属性——“理性”和“自利”。这两个属性的结合便是所谓的“理性经济人”,亦即具有“理性”行为能力且以“自利”为行为之唯一动机的人。在此基础上,再通过设置一些必要的简化假设(如“二元关系”、“可传递性”、“完备性”),便可以从“理性经济人”逻辑地推导出“最大化行为”。“理性经济人”作为一个基本行为假设,乃是新古典理论体系的基础和逻辑出发点,这一理论体系的各个组成部分(消费者理论、厂商理论、市场均衡理论等)无不逻辑地建立在这一基本行为假设的基础之上。通过这样一个基本行为假设,便可以轻而易举地撇开人在实际经济行为中所必然涉及的一切社会关系及价值观念,而把一切经济行为都归结为纯粹技术性关系下的“最大化行为”。如此一来,经济学似乎便摆脱了各种复杂社会关系以及价值观念的纠缠,从而变得“纯洁”起来了。
由此可见,所谓“价值中立”,从而所谓建立实证经济学,其实归根结底只是通过人为地限定经济学研究领域,或者人为地通过设置“理性经济人”这一高度简化的基本行为假设,而将研究对象中所包含的价值观念人为地排除在经济学研究范围之外。我们完全有理由质疑:这么做“合法”吗?
的确,肇始于新古典经济学,“理性经济人”已成为现代西方主流经济理论共同的基本行为假设和共同的逻辑出发点。事实上,绝大多数的专业经济学者们在“实证研究”的名义之下,至今还在沿用这一基本行为假设。然而,由于“理性经济人”这一高度简略化(或简化)的基本行为假设本身具有明显的“非现实性”乃至“虚构性”,因此,其“合法性”便总是遭到质疑,批判者总是可以这样质问:如此简单而不切实际的行为假设何以能够确保经济理论的正确性呢?事实上,在经济学说史上,有关“理性经济人”的争论可谓源远流长,至少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中叶亨利·凯里(Henry Charles Carey)对约翰·穆勒关于“经济人”观点的猛烈抨击,19世纪后期的德国历史学派与奥地利学派之间的“经济人”之争,此后,还有20世纪40—50年代关于“利润最大化”问题的争论,以及20世纪后半叶关于“理性行为”问题的争论。这些争论至少表明,虽然“理性经济人”乃是现代西方主流经济理论的一个基础性概念,但它也是长期争论不休却始终悬而未决的概念。换言之,经济学者为建立实证经济学而宣称所谓“价值中立”,这本身仍是值得怀疑的。
三、“假设不相关性”能成为“救命稻草”吗?
笔者认为,关于“理性经济人”之争,其实质性问题在于经济理论中的假设问题,亦即假设是否应具有现实性问题。如果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那么,“理性经济人”假设因其具有明显的“非现实性”乃至“虚构性”,便属于不恰当的假设,而以此为基础和逻辑出发点所建立的现代西方主流经济理论便不具有坚实的基础;反之,如果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那么,“理性经济人”假设便是合理或“合法”的了。然而,在20世纪中叶以前有关“理性经济人”的争论中,这个实质性问题却始终未被明确和正面地论及,直到弥尔顿·弗里德曼在其著名论文《实证经济学的方法论》② 中才首次提出了这个问题。
弗里德曼在这篇文章中明确指出,如“利润最大化”(或“理性经济人”)等都只是经济理论的假设,而假设毋须是“现实的”,亦即假设不需要与实际经验观察相一致;他甚至还要刻意地反过来极端地说,经济理论中的假设不仅不需要是“现实的”,反而甚至应该是“虚构的”,他说:“一般说来,某一理论越是杰出,那么它的‘假设’就越是超脱现实。”其所以如此认为,是因为在他看来,理论之正确与否并不在于其假设之“现实”与否,而在于理论之“实用”与否,而“实用”则体现于理论对所要解释现象的预测之正确与否,而预测之正确与否又是与理论假设之“现实”与否互不相关的。这就是弗里德曼在文章中提出的著名观点,也是一个相当惊人的观点。这个观点,后来被马克·布劳格称为“假设不相关性”(Blaug,1992)。
这个观点之所以是惊人的,是因为:第一,如果这个观点可以成立的话,那么,主流经济学便可以高枕无忧地继续以“理性经济人”这一基本行为假设作为其理论体系之基础和逻辑出发点,不必担忧其理论大厦会由于这一行为假设所具有的明显的“非现实性”而存在倾覆之虞。换言之,弗里德曼以“假设不相关性”观点,试图轻而易举地化解针对“理性经济人”假设之“非现实性”乃至“虚构性”的一切攻击。第二,如果这个观点可以成立的话,那么,主流经济学不仅不再需要顾虑其理论假设之现实与否问题,甚至可以基于弗里德曼的这一观点而任意地给理论设置假设条件,因为无论如何设置假设都不至于危及理论之正确性。概而言之,弗里德曼的“假设不相关性”观点之所以是惊人的,是因为在某种意义上,这一大胆观点为实证经济学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方法论基础。也正因为这一缘故,他的文章才格外引人瞩目,马克·布劳格称之为“战后经济学方法论的中心著作”(Blaug,1992)。
笔者认为,这篇文章的学术意义在于,它在经济学方法论史上首次提出了经济理论中的假设问题。但是,弗里德曼只是提出了问题,却未能解决问题。事实上,弗里德曼的“假设不相关性”观点也招来了诸多的批判③。笔者也认为,这个观点是难以成立的,主要理由是:首先,虽然弗里德曼在文章中反复提到经济理论中假设的“非现实性”这一观点,可是,他除了给出诸如“自由落体”、“树叶生长”等自然科学方面的例子之外,始终都没有对“假设不相关性”作出正面的论证。究竟在何种意义上以及在多大程度上经济理论的假设可以是不相关的呢?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在弗里德曼的论文中找不到明确的答案。
其次,该文另一个更为明显的缺陷还在于:虽然“假设不相关性”是这篇文章的核心观点,可是弗里德曼始终都是笼统地使用“假设”一词,而且还莫名其妙地给这个词添加上引号。关于假设,他反复强调的只是作为理论的假设的两个基本标准,即所谓的“简洁性”与“成效性”。然而,稍具逻辑知识者大概都知道,理论的假设本身并不是单一的,而是存在各种不同的具体情形,它们与理论系统之间的关系也并非是单一的,不同情形的假设对理论系统的影响作用是不同的,绝非用“不相关”一词便能涵盖。笼统地谈论假设和“假设不相关性”,难免具有误导性。
再次,最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弗里德曼一方面未曾对“假设不相关性”观点作出正面的论证,另一方面他却把读者的注意力引到另一个观点上去了,即理论的“实用性”观点。颇具意味的是,他似乎是企图用后一个观点去为前一个观点辩解,也就是说,在弗里德曼那里,“假设不相关性”观点在相当程度上乃基于他对理论之正确与否所持有的特殊的评判标准——“实用性”。所谓“实用性”,在他那里又被狭隘地理解为“预测”。他说:“实证科学的终极目的就是要发展这样一种‘理论’或‘假说’,使之能够对尚未观察到的现象作出合理的、有意义的(而不是老生常谈的)预测。”他还说:“理论应该通过其对它意在加以‘解释’的那一类现象的预测能力来检验。……对某一假说的合理性的唯一有效的检验,是将其预测与实际情况进行比较。”由此可见,弗里德曼的思想逻辑大致是这样的:既然理论之正确与否唯一地取决于其“预测”,而并不取决于理论的假设,如此说来假设当然便成为“不相关”的了。这样一种对理论、从而对理论的假设的看法,常被称为“方法论工具主义”。方法论工具主义渊源于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约翰·杜威的“工具主义”,其大致含义可概括为一句话:有用的便是正确的。依笔者理解,方法论工具主义之所以总是有“市场”,原因再简单不过:我们永远都不能反过来说“有用的便一定是不正确的”。对于经济学这样一门以“学以致用”称道的学科来说,情况尤其如此。然而,正如劳伦斯·博兰所指出的,关键问题还在于:“预测”之正确与否的“成功的标准是什么呢?谁来决定它们应是什么呢?”④ 弗里德曼的论文并没有涉及到这些关键问题。笔者需要强调指出的是:且不说方法论工具主义本身之似是而非,弗里德曼以这种基于方法论工具主义的所谓“实用性”(读作“预测”)去为他的“假设不相关性”观点辩解,这种做法本身在逻辑上就属于偷换论题,因而应属于无效的辩解。
上述分析表明,“假设不相关性”观点本身是站不住脚的,它并不能为主流经济学继续沿用“理性经济人”这一基本行为假设之合理性提供任何有效辩护,也并不能成为拯救实证经济学之方法论基础的一根“救命稻草”。
四、究竟在何种意义和多大程度上可以“实证”?
上述分析无非可以归结为这样一点,即,尽管经济学家们一直致力于打造一门“纯洁的”经济学——实证经济学,但迄今为止他们的努力尚未能够给这样一门“纯洁的”经济学提供一个坚实可靠的方法论基础。然而,尽管如此,那些格外钟情于实证经济学的学者们似乎仍然可以对此保持不屑一顾的心态。在这种貌似傲慢的心态背后,或许至少还有一点可作为支撑这种心态的“底气”,那就是他们始终都认定自己所做的工作是“实证的”;在他们的心目中,“实证的”便意味着他们的经济理论总是面对经验检验的,因而他们所做的工作仍旧还是属于“经验科学”的范围之内。应该说,这种心态还是相当普遍的,尤其是那些只知摆弄数学模型和计量工具,却根本不知为何要做这种摆弄的专业经济学者。针对这种心态,实质性问题是:究竟在何种意义上和多大程度上可以“实证”?
针对这个问题,我们尚且不想将话题引到太远,如引到了诸如“归纳逻辑难题”,“杜恒—奎因论题”(the Duhem-Quine thesis)、 “非充分决定性论题”(the thesis of under determination)等知识论上的一些众所周知的难题, 虽然这些难题中的任何一个都足以对所谓的“实证”构成致命的挑战。这里只需指出的是,对经济理论的评判只谈“实证”,而“实证”又被理解为经验验证,这种认识本身就是极其狭隘的。一般地说,一种理论是由假设和命题所构成的一个具有某种逻辑结构的知识系统,因此,应该确切地称一种理论为一个理论系统,而那些命题通常是以假说、定理及推论等形式出现在理论系统中的。对一种理论或一个理论系统的评判,大体可以分为对单个命题的评判和对理论系统整体的评判。所谓经验验证,只能适用于对单个命题的评判,但并不适用于对理论系统整体的评判。仅就针对单个命题的经验验证而言,它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经验检验,亦即经济学者们所津津乐道的“实证”。经验验证大致包括三种形式:(1)经验一致性检验, 亦即拿命题(通常是单纯的事实性或描述性命题)与经验事实直接相对照,验证其是否一致,结果或是证实或是证伪。(2)经验解释, 亦即针对命题所揭示的某种特定关系(主要是因果、相关等),用经验事实去验证这种关系的存在性及存在的条件。(3)经验预测,它与经验解释是关系密切的,一般是指以命题所揭示的特定关系,去推断将来可能出现的某种可经验观察的现象。
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将经验验证分为直接验证和间接验证。所谓直接验证,就是直接用已观察到的经验事实去验证原命题。应该说,直接验证仅适用于为数不多的单纯的事实性命题,绝大多数命题都是无法直接检验的。所谓间接验证,是指原命题原本是不可经验检验的,但通过某种必要的转换而变得可检验了。这种转换往往需要某种辅助性假设。辅助性假设的作用在于,或是人为地缩小了理论中原命题所涵盖的范围(scope), 或是人为地大幅度减少了原命题所针对的经济现象的维度(dimensions);通过这种缩小范围或减少维度,辅助性假设使得原命题发生了转换,从而为经验验证创造了可操作性条件。需要强调指出的是,辅助性假设的使用对理论系统的评判显然是有影响的;换言之,理论命题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被经验事实所验证,显然依赖于这种辅助性假设是如何设置的。
一般地说,单个理论命题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适合上述一种或多种形式的经验验证,不仅受到该命题本身的性质的限制,还要受到种种客观条件(如数据的可获性和可靠性及分析工具的局限性等)的制约。绝对没有任何根据可以断定所有的单个命题都是可经验验证的。就经济学而言,经济理论中的大多数的单个命题都是未经经验验证的,更确切地说,大多数命题是无法被经验验证的,至少无法直接地被经验验证。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却往往被那些沉迷于“实证迷信”者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了。经济理论中只有少数命题可以被经验验证,而在这些少数可验证命题中,又多数只能进行间接验证,而间接验证本身还要受到辅助性假设的影响。
与单个命题相比,对理论系统整体的评判并不适用于所谓经验验证,或者说经验验证对理论系统整体的评判是无能为力的。这种评判主要是通过两种途径:一是逻辑推证,一是社会评价。所谓逻辑推证,就是运用逻辑去推导或证明理论系统内部是否具有内在一致性,亦即通常所说的内洽性逻辑检验。实际上,这也正是爱因斯坦所说的科学理论的“内部的完美”标准⑤。但必须明白的是,这种逻辑推证至多只能确定逻辑上的真或假,并不能确保经验上的真或假,而这两种真或假并不是一回事。所谓社会评价,即以社会对理论的接受状况为核心的评判。社会评价并不能验证或推证理论本身之正确与否,但它可以决定理论之去留,从而也就决定了理论对现实生活(包括思想)的实际影响。一个本身正确的理论有可能因社会广泛不接受它而处于“休眠”状态;反之,一个本身并不正确的理论则有可能因被社会所广为接受而存续下去。社会评价本质上乃是一个社会过程,但并非是一个科学过程,它所体现的是人的认识之主体性。社会评价意味着:在社会科学领域内没有任何一种理论可以被彻底驳回推翻,实际所能看到的只是某种理论被社会所“遗弃”,从而进入了“休眠”状态,不再对社会实践活动产生任何实际影响作用。
综上所述,所谓“实证”并不适用于对经济理论整体的评判,而只能适用于对理论中的单个命题的评判;即便仅就单个命题而言,“实证”真正所能做的也是极其有限的。可见,那些打着“实证经济学”旗号的所谓专业经济学者,虽然自以为自己所做的工作是“实证”的“经验科学”,但支撑着他们习以为常的傲慢心态的那种“底气”,其实也是相当有限的。
五、结语:“实证迷信”何以表现为数理“自助游戏”?
实证经济学并不具备一个坚实可靠的方法论基础,但在实证经济学旗号下却活跃着一个专业经济学者群体。值得关注的一个有趣现象是,这个致力于“实证”的群体非但没有因为实证经济学缺乏一个坚实可靠的方法论基础而趋于衰落,反而在过去数十年间愈来愈处于主导地位,俨然以主流自居,乃至于几乎垄断了经济学的“话语权”了。如何去解释这个有趣现象呢?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这个群体中只有极少数人愿意去接触经济学方法论,如前文所述的弗里德曼等;这个群体中绝大多数人实际上对方法论问题是毫无自觉意识的,他们只是叫喊着“实证”,也热衷于“实证”。我把后者称为“实证迷信”者,专门针对那些对“实证”深信不疑,却又对“实证”所涉及的方法论基础缺乏基本的自觉意识的人。我们这里所关心的是这样一个问题:“实证迷信”何以可能呢?换言之,其根源何在?
撇开那些属于社会学乃至心理学的根源不谈⑥,“实证迷信”之所以能够盛行于当今西方主流经济学界,这种现象与过去数十年来经济学的数学化是有直接关联的。如今,数学化已成为现代西方主流经济理论的一个显而易见的基本特征。有国外学者写道:“在这种年代里,唯一能使学生从美国式的经济学研究生教学计划中退学的理由,是怀疑其缺乏对数学工具的熟练掌握。”⑦ 为了分析经济学数学化趋势与“实证迷信”盛行这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也为了避免这种分析可能引起的误解,笔者认为,有必要谈谈数学化对经济学究竟意味着什么。
客观地说,对几乎所有的学科来说,数学总是一种有用的工具。对经济学来说,数学的主要用处在于对经济思想加以形式化,使之变成具有某种逻辑结构的理论系统;经济学的数学化本质上是对经济思想加以形式化的一种特定的方式(当然不是唯一的方式)。这种方式当然具有其自身所固有的长处,如理论在逻辑上的严谨和内洽,亦即通常所说的“前后一贯”(coherency )和“内在一致”(consistency)。但是,这种方式自身所固有的缺陷却常被人忽视了, 那就是形式化过程中思想内容的丧失。众所周知,为了能够采用数学表达,亦即把某一思想转化为数量关系,总是需要对思想内容作某些简化处理。这种简化处理往往都是通过某些人为的简化性质的假设来实现的。在这种简化处理中,某些思想内容将不可避免地丧失了。可见,采用数学方式的形式化一般地总是意味着有利亦有弊、有得亦有失。本质上讲,这种利与弊、得与失的对立,所反映的是内容与形式之间的矛盾,而这种矛盾虽然并非是经济学的数学化所特有的,但它常常被专业经济学者们忽视了。我们既不能全盘否定数学工具,也不能将它视为十全十美。真正的问题在于:在这种内容与形式之间的矛盾中,如果偏执于强调理论的数学化,那么,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丧失或牺牲了思想内容呢?比如,当新古典经济学的厂商理论采用数学工具将一切生产活动都形式化为生产函数时,究竟丧失了多少有关生产活动的其他思想内容呢?如此说来,关于经济学的形式化和数学化,问题不在于数学工具的运用,而在于不惜一切思想内容代价的数学化,或者说为数学化而数学化、为形式化而形式化,具体体现为毫无思想内容和理论基础的数学模型及其推导,也表现为统计和计量工具的滥用。
那些“实证迷信”者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沉湎于经济学的数学化。但由于对方法论缺乏基本的自觉意识,他们显然并不知道在这种数学化背后,实际所奉行的方法论基础——方法论形式主义。方法论形式主义的基本观点大致可以归结为这样一个命题:逻辑上的真必定也是经验上的真。所谓逻辑上的真,一般被理解为经济理论在逻辑上的“内洽”。数学几乎是理所当然地被视为能够确保经济理论在逻辑上内洽的最为理想的工具,因为据说“数学是纯粹的不像假的逻辑学”⑧。按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的说法,数学乃作为逻辑的延伸,这是因为数学所给出的各种定理无非就是逻辑上的“永真式”。所谓“永真式”,说得客气一点就是“同义反复”(tautology),说得通俗一点则是“套套逻辑”。如果说,在纯数学领域内“套套逻辑”尚具其固有之合理性的话,那么,在作为一种经验学科的经济学领域内,“套套逻辑”式的命题便几乎等同于“废话”——永远都“合乎逻辑”的“废话”。宣称逻辑上的真必定也是经验上的真,这与其说是一种观点,毋宁说它只是一种观念,一种延续了千年的对“数”的崇拜所形成的观念。在近代,这种观念的一个典型例证,便是常被“数”的崇拜者引用的所谓“伽利略的惊奇”——大自然这部百科全书是用数学语言写成的!那些“实证迷信”者实际上所奉行的方法论形式主义,说穿了也就是这么一个观念而已。
方法论形式主义的最大危害在于,它为这种为数学化而数学化或为形式化而形式化大开方便之门。之所以如此认为,理由在于这种方法论使得为数学化而数学化在方法论上成为可能。既然数学本身在逻辑上永远都是“内洽”的,那么便不难想象,即便是毫无经济思想内容的数学化经济理论,研究者至少在“纯技术”意义上也还是有可能进行大篇幅的数学推导论证,因而单纯的为形式化而形式化或为数学化而数学化完全是可能的,也是可行的。或许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劳伦斯·博兰把这种为形式化而形式化叫作数理“自助游戏”,应该说这一形容还是颇为生动传神的。纵观当今主流经济学界,数理“自助游戏”已经成为活跃在实证经济学旗号下的专业经济学者群体的基本特征。实际情况是,这个群体在西方国家已经基本上垄断了经济学的“话语权”了,因为“许多主流经济学领域已被形式主义所统治,……在许多杂志中,现实性和实用性实际上已不再受到关注,它们将其篇幅的大部分致力于数理经济学。”⑨ 中国读者应该不难看出, 这种情况在中国经济学界目前正处于方兴未艾之中。
注释:
① 当樊纲“理直气壮地宣称:经济学家就是‘不讲道德’”时,我想他实际上所指涉的应是后一种含义上的“价值中立”,但他的文章表明他实际上也混淆了上述两种不同性质的“价值中立”含义[樊纲:《“不道德”的经济学》,载《读书》,1998(6)]。
② 该文完成于1947年,并作为他的《实证经济学论文集》的“前言”而公开发表于1953年,现已被辑入中文版的《弗里德曼文萃》,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2001年版,第191—235页。以下凡引用该文均不再注明出处和页码。
③④ 参见劳伦斯·博兰:《批判的经济学方法论》,第Ⅰ部分,第47页,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
⑤ 爱因斯坦:《自述》(1946年),见《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
⑥ 参阅:Frey,Bruno S.:Why economists disregard economic methodology,Journal of Economic Methodology,8(1)2001,pp.41—47。
⑦⑧ 转引自罗杰·E.巴克豪斯:《经济学方法论的新趋势》,第82、82页,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
⑨ 参见劳伦斯·博兰:《批判的经济学方法论》,第78页。
标签:经济学论文; 弗里德曼论文; 科学论文; 实证经济学论文; 理性经济人论文; 理论经济学论文; 迷信活动论文; 命题的否定论文; 经济论文; 社会经济学论文; 命题逻辑论文; 基础数学论文; 关系逻辑论文; 数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