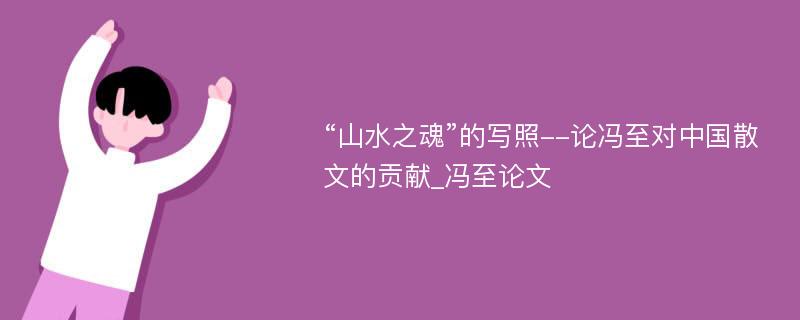
“灵魂里的山川”之写照——论冯至对中国散文的贡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山川论文,写照论文,中国论文,散文论文,灵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冯至一生所写散文不少,但其“文名”却长期不彰。事实上,到20世纪80年代,冯至的新诗、小说、学术与翻译成就,都得到了一致肯定,唯一尚未得到学界公认的,乃是他的散文成就。迨至1990年,季羡林发表《诗人兼学者的冯至先生》一文,尤为推崇冯至的散文成就。他认为在近现代散文史上,“冯先生卓然成家,同他比肩的散文作家没有几个”,并强调冯至“是继承了中国优秀散文传统的”,所以“冯先生的散文实际上就是抒情诗,是同他的抒情诗一脉相通的”①。季羡林如此论断,当时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那时,我的博士论文也涉及冯至的散文,心里很喜欢,但限于论题,散文只是作为资料而未能展开论述。 不过坦率地说,我虽然很赞同季羡林对冯至散文艺术价值的评价,但他其余的判断,比如冯至主要继承中国古代散文的传统,其散文是诗意盎然的抒情诗等,却与我的阅读体会不相合。而自季羡林的文章之后,学界对冯至散文的研究明显加强了,但或别有旨趣而意不在文,或局限于具体篇章的赏析,迄今未见对冯至散文的整体性探究。冯至散文的特点、成就及其对中国散文的贡献究竟何在,仍是一个有待探讨的问题。本文就对这一问题略述笔者的一些体会。我的讨论将集中于冯至20世纪30、40年代的散文,那是他的散文写作的黄金时期,主要作品有《山水》集和“鼎室随笔”系列散文。 一、反山水诗文传统的《山水》集 冯至也写过“抒情诗”般的散文,就在他开始发表诗作的1923年,类似的散文随之问世,此后亦与诗俱进、新作不断。到了1930年前后,冯至已发表此类散文三十余篇,数量不少。而所有这些早年散文都体现出与他早年诗作同样的特点——浪漫中略带唯美的抒情诗格调。冯至早年抒情诗般的散文,一方面借鉴了西方浪漫抒情的诗文传统,深受世纪末唯美主义、颓废派等现代主义文学的感染,另一方面则继承了自魏晋到明清的名士抒情诗文的传统,并且自觉不自觉地受到郁达夫借景抒情的情调散文、徐志摩的诗意抒情散文以及周作人的小品文之影响。换言之,年轻的冯至也走了一条借山水风物、田园故居等发抒幽情别绪的抒情散文之路,所不同的只是其散文中多了一点所谓“早岁感慨恕中晚”②(指中晚唐以来抒情寄怀的婉约诗词——引者按)的幽婉风致。不过,由于散文便于自由抒情,所以冯至的这些散文往往失去了其“幽婉的”③抒情诗里的恳切、节制和含蓄,给人以肤浅、感伤过甚之感,所以也便“不幸”地湮没在抒情散文的大潮中不为人知。而真正值得反省的,正是曾经盛行的现代抒情散文之得与失。 对“五四”以来的抒情散文的成就,新文学的先驱者早就肯定有加。如胡适在1923年2月发表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即以确信不疑的口气断言:“这几年来,散文最可注意的发展乃是周作人等提倡的‘小品散文’。这一类的小品,用平淡的谈话,包含着深刻的意味;有时很像笨拙,其实却是滑稽。这一类作品的成功,就可彻底打破那‘美文不能用白话’的迷信了。”④1933年8月,鲁迅在回顾初期新文学的成就时,也不胜欣慰地说:“到五四运动的时候,才又来了一个展开,散文小品的成功,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这之中,自然含着挣扎和战斗,但因为常常取法于英国的随笔(Essay),所以也带一点幽默和雍容;写法也有漂亮和缜密的,这是为了对于旧文学的示威,在表示旧文学之自以为特长者,白话文学也并非做不到。”⑤这些著名论断后来成为主导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权威判断。于是,所谓新散文之成功更在新小说、新诗、新戏剧之上,便成了无可置疑的文学史定论。就我所知,似乎唯一提出异议的是李健吾。1936年2月,李健吾在一篇诗评中顺便质疑新散文的现代性之不足:“通常以为新文学运动,诗的成效不如散文,但是就‘现代’一名词而观,散文恐怕要落后多了。”⑥ 现在看来,无论是胡适、鲁迅,还是李健吾,都说对了现代抒情散文之一面。可以理解,胡适和鲁迅为了肯定新文学,自然会更看重新散文成功的一面。在各种新文体中,散文的确以个性鲜明的抒情叙事、漂亮有味的语言率先获得文学上的成功,表明白话新文学也可以做到旧文学自以为特长者,所以胡适和鲁迅都乐于肯定它。而作为新锐批评家的李健吾则看到了事情的另一面,即新散文其实是中外对接、新旧妥协的产物。“五四”以后,来自西方的以浪漫主义、个性主义为基础的个性化抒情随笔,和源于中国名士才子之性灵主义、抒情主义的小品文,融会而成现代中国的抒情散文。它往往在外来的新面目之下表现着中国固有的名士趣味和才子情趣。这些趣味和情趣要在新诗里表达得恰切是较为困难的,但当把它们位移到格式自由、更便于自我表现的新散文中,立刻就显得像模像样、颇有味道和美感了。而李健吾则洞见到它的“失”,认为那不过是熟门旧路之翻修,其现代性远比不上真正从头做起的新诗。 这个迅速崛起的散文新潮,显然更偏重抒情一路。用梁遇春的话来说,便是“国人因为厌恶策论文章,做小品文时常是偏于情调”⑦,其抒情模式其实袭用自传统名士最偏爱的“借景抒情、托物言志”之套路。这是一条早被证明富有诗意抒情效果和中国文章格调的路,所以喜欢抒情的新散文家们纷纷走上这条路。到了20世纪30年代,这条借景抒情、托物言志的路日渐显现出其狭窄和肤浅:它的一目了然的寄托、“卒章显其志”的造作、沾沾自喜的情调、夸张过甚的感伤、拿腔拿调的修辞,都说明这条轻车熟路其实是一条似深实浅的林间小径,并非可致深广的文章大道,可许多新散文家却被它牢牢地束缚住了。当然,我无意全盘否定现代抒情散文的艺术成就,此处只说说它尚未被人言说的局限和弊病。 冯至的散文集《山水》,就是他反思此种抒情套路之弊而独自探索、深造自得之结晶⑧。《山水》此名很容易让人想到古代文人别有感怀的山水诗文和现代文人寄情山水的抒情散文,如《钓台的春昼》、《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等。其实《山水》恰是反山水诗文传统的,展现出一种原始朴素的山水观、存在观和美学观。 《山水》第一篇《蒙古的歌》就显示出从浪漫抒情到严肃朴素的转变。冯至写道,他年轻时曾经从一篇苏联小说里读到关于蒙古的浪漫传说。所以,他一直对蒙古的自然与人抱着一种浪漫的奇情异想。可是后来听到一个接近过蒙古人的俄国人唱了一首蒙古民歌,那歌曲朴质之至,毫不浪漫。于是,冯至向那个俄国人询问这首蒙古民歌的意义,二人遂有下述对话: “意义是很悲哀的,他们的马死了,他们在荒原里埋葬这匹马,围着死马哭泣:老人说,亲爱的儿子,你不等我你就死去了;壮年说,弟弟呀你再也不同我一起打猎了;小孩子叫声叔叔,几时才能驮我上库伦呢;最后来了一个妙龄的女子,她哭它像是哭她的爱人。” “就意义说,这是一首很好的哀歌呀,真想不到他们也有这样好的歌。但是声调怎么这样沉闷呢?我只觉得蒙古是一个野兽,无愉快的。就是蝴蝶也想咬人呢。像你们的一位作家所说的一样。” 俄国人似乎是在笑我幼稚,他说: “那不过是片面的观察罢了。什么地方没有好的歌呢。无论什么地方的人都有少男少女的心呀。不过我们文明人总爱用感情来传染人,像一种病似的。至于那鲁钝而又朴质的蒙古人,他们把他们的爱情与悲哀害羞似地紧紧地抱着,从生抱到死,我们是不大容易了解,不大容易发现的。”⑨ 所谓“文明人总爱用感情来传染人,像一种病似的”,就含蓄地表达了冯至对“借景抒情、托物言志”这个古今一脉相承的抒情传统之反省。紧接着在第二篇《赤塔以西——一段通信》里,冯至就记述了自己赴德留学途径苏联的赤塔市,看到淳朴健康的人民和新鲜到近乎原始的自然,觉得再也不能像传统士人那样移情自高了: 今天,已经不是昨天。白杨、赤杨、榆树、各样松柏一类的长青树,有的很高,有的小学生一般排成队依附在大树的旁边。血红的,阴绿的,焦黄的,色彩斑斓的叶子,没有风也是响着,飞舞着。很少行人,也少牲畜,令人想到原始的世界。色彩太鲜艳了,停车坐爱枫林晚,在这里车却无须停,因为这伟大的,很少经人道破的,美丽的树林是一望无有边涯的。⑩ 写过这两篇文章之后,冯至就来到德国就读于海德堡大学。1931年的春天,冯至深深地被里尔克所吸引,购买了后者的全集并开始学习和翻译。从冯至这一时期所翻译的《给一个青年诗人的十封信》、《马尔特·劳利兹·布里格随笔》(选译)以及《山水》,和他后来所写的纪念里尔克的文章《里尔克——为十周年祭日作》、《工作而等待》、《给一个青年诗人的十封信·译者后记》以及《山水·后记》里,可以看出里尔克独特的存在观、创作观和山水观多么深刻地影响了冯至此后的为人与为文。 里尔克反复倡言要谦虚朴素地接近自然、严肃诚恳地承担万物。他说:“你接近自然,你要像一个原人似地练习去说你所见、所体验、所爱,以及所遗失的事物。”(11)又谓:“啊,人们要更谦虚地去接受、更严肃地负担这充满大地一直到极小的物体的神秘,并且去承受和感觉,它是怎样重大地艰难。”(12)因为在里尔克看来:“自然是较为恒久而伟大,其中的一切运动更为宽广,一切静息也更为单纯而寂寞……人沉潜在万物的伟大的静息中,他感到,它们的存在是怎样在规律中消隐,没有期待,没有急躁。并且在它们中间有动物静默地行走,同它们一样担负着日夜的轮替,都合乎规律。”(13)由此,里尔克发展出了一种独特的“山水观”,它与中国从古到今相沿不衰的“山水之人化”、“山水之诗化”的传统迥然有别,主张还山水以自然的本来面目,进而主张人的世界也应该“山水化”: 在这“山水艺术”生长为一种缓慢的“世界的山水化”的过程中,有一个辽远的人的发展。这不知不觉从观看与工作中发生的绘画内容告诉我们,在我们时代的中间一个“未来”已经开始了:人不再是在他的同类中保持平衡的伙伴,也不再是那样的人,为了他而有晨昏和远近。他有如一个物置身于万物之中,无限地单独,一切物与人的结合都退至共同的深处,那里浸润着一切生长者的根。(14) 冯至显然深受里尔克的这种“山水观”的启发,所以他在《山水》集《后记》里这样写道: 对于山水,我们还给它们本来的面目吧。我们不应该把些人事掺杂在自然里面:宋、元以来的山水画家就很理解这种态度。在人事里,我们尽可以怀念过去;在自然里,我们却愿意万古长新。最使人不能忍耐的是杭州的西湖,人们既不顾虑到适宜不适宜,也不顾虑这有限的一湖湖水能有多少容量,把些历史的糟粕尽其可能地堆在湖的周围,一片完美的湖山变得支离破裂,成为一堆东拼西凑的杂景。——我是怎样爱慕那些还没有被人类的历史所点染过的自然:带有原始气氛的树林,只有樵夫和猎人所攀登的山坡,船渐渐远离了剩下的一片湖水,这里,自然才在我们面前矗立起来,我们同时也会感到我们应该怎样生长。(15) 同样感人至深的,是里尔克那种关怀世间万物、体验一切存在的存在观和诗学主张。在这种存在观及其诗学视野里,不再有人与物、主与客的分别,而是对一切都一视同仁,达到浑融无间之境界。如里尔克在《布里格随笔》里恳切地说道: 我们必须观看许多城市,观看人和物,我们必须认识动物,我们必须去感觉鸟是怎么飞翔,知道小小的花朵在早晨开放时的姿态。我们必须能够回想:异乡的路途,不期的相遇,逐渐临近的分离;——回想那还不清楚的童年岁月;想到父母……想到儿童的疾病,病状离奇地发作,这么多深沉的变化;想到寂静、沉闷的小屋内的白昼和海滨的早晨,想到海的一般,想到许多的海,想到旅途之夜,在这些夜里万籁齐鸣,群星飞舞,——可是这还不够,如果这一切都能想得到。我们必须回忆许多爱情的夜,一夜与一夜不同。要记住分娩者痛苦的呼喊和轻轻睡眠着、翕止了的白衣产妇。但是我们还要陪伴过临死的人,坐在死者的身边,在窗子开着的小屋里有些突如其来的声息。我们有回忆,也还不够。如果回忆很多,我们必须能够忘记,我们要有大的忍耐力等着它们再来。因为只是回忆还不算数。等到它们成为我们身内的血、我们的目光和姿态,无名地和我们自己再也不能区分,那才能以实现,在一个很稀有的时刻有一行诗的第一个字在它们的中心形成,脱颖而出。(16) 冯至早在1932年就翻译了里尔克的这段名言,1936年又在《里尔克——为十周年祭日作》一文里作了充分的阐发,认为“这是里尔克诗的告白,同时他也这样生活着”(17),并强调在里尔克的诗学里,深广地关怀万事万物的经验和体验取代了浪漫诗学的情感中心论。 应该说,来自里尔克的启示正适合冯至本人谦虚朴实的性格,所以对其创作产生非常显著的推动作用:不仅深刻地启发了他此后的诗歌创作,也深刻地校正了其散文写作方式。就散文写作而言,只要稍微留心研读即不难发现,冯至正是在认真吸收了里尔克的山水观和存在观的营养后,才赋予其《山水》集三个迥异于人的特点和优点。 其一,与中国的传统山水诗文及现代山水散文之瞩目于名山胜水不同,冯至的《山水》集力戒相沿成习的人化自然、别有寄托的抒情态度,而将着眼点放在那些无名的自然风物上,努力还原它们朴素的本来面目,着力抒写它们无形中给予自己的感动和启示。这种观察和写作的姿态正是反山水抒情传统的,在中国山水诗文史上可说是一个创举。对此,冯至在《山水·后记》里有恳切的说明: 十几年来,走过许多地方……都交织在记忆里,成为我灵魂里的山川。我爱惜它们,无异于爱惜自己的生命。 至于这小册子里所写的,都不是世人所谓的名胜……自然本身不晓得夸张,人又何必把夸张传染给自然呢。我爱树下水滨明心见性的思想者,却不爱访奇探胜的奇士。因为自然里无所谓奇,无所谓胜,纵使有些异乎寻常的现象,但在永恒的美中并不能显出什么特殊的意义。(18) 其二,冯至的山水散文当然不会忽视人的存在,但他笔下的人物不再是指点江山的英雄,也并非寄情山水的才子,而是同自然一样朴素的农民、市民、樵夫或猎人等小人物,显示出作者对普通人的关怀和尊重。在一向被名士才子独占的中国山水诗文中,冯至的这类作品殊为难得。然则,冯至为什么要关怀这些小人物呢?他在《山水·后记》里有这样写道:“山水越是无名,给我们的影响也越大;因此这些风景里出现的少数的人物也多半是无名的:但愿他们都谦虚,山上也好,水边也好,一个大都会附近的新村里也好,他们的生与死都像一棵树似的,不曾玷污了或是破坏了自然。”(19)我们读到《山水》集中小人物朴素自然的为人与处事,会生出由衷的感动和尊敬,获得深切的人生启示。 比如《忆平乐》里那个无名裁缝的故事。1938年10月的一天,冯至和妻子随内迁的同济大学辗转路过广西平乐,他想给妻子做一件夹衣,但因为第二天一早就要出发,裁缝们怕时间来不及,都不敢接活。在冯至的恳求下,终于有一个裁缝同意帮忙赶做,且表示工钱无须增加。当天午夜,那位裁缝送来夹衣。冯至这样描写当时的场景:“我拿出一张一元的纸币交给那个裁缝,他找回我两角钱,说一声‘一件夹袍八角钱’,回头就走了。我走上楼,把夹袍放在箱子里,又躺在床上,听着楼下的钟正打十二点。”(20)这样一个无名的小人物、这样一件普通的小事,却像广西的山水一样清正可爱。这篇散文朴素无华,却委实是极好的文章,让人读了自然而然地增进对民族和人类的信心。 其三,与山水的自然和人物的朴质一致,冯至的《山水》集力避传统山水诗文惯有的夸张渲染之笔墨,凡所叙之事都以严肃朴素的笔法出之、凡所抒之情皆以谦虚诚恳的笔调节制之,给人凝重简练而又朴厚深远之美感。以《山村的墓碣》为例,冯至笔下那些德国、瑞士交界处的山村居民过着与世无争的生活,对生老病死持自然而通达的态度。因此,他们会给无名死者的墓碑刻上生动有趣的墓碣。比如: 一个过路人,不知为什么, 走到这里就死了。 一切过路人,从这里经过, 请给他作个祈祷。 我生于波登湖畔, 我死于肚子痛。(21) 像这些简朴有味的乡村墓碣一样,冯至的这篇散文也写得简朴而隽永。文章凝练节制,绝无显山露水之态,既克制了借题发挥的议论、也省去了借景乘势的抒情,而语短情长、意味无穷,绝非中国传统山水诗文惯有的蓄意拿捏之含蓄风或有意为之的言外意。这样的文章是地地道道的好文章,它们乃是冯至虚心观照、深造自得的艺术结晶。所以,《山水》集丰富和发展了汉语散文的传统,就其独特贡献而言,只有此前鲁迅的《朝花夕拾》堪与比肩。 二、严肃思考人之存在的“鼎室随笔” 很可惜,如此沉静精美的山水散文,冯至后来未能继续写下去,因为“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的社会不容许……写这样的散文”(22)。当然,他并没有停止散文写作,而是因应着现实的要求转变了方向。从1943年起,昆明涌现出几种小型周刊,先有《生活导报》、《春秋导报》,后有《自由论坛》、《独立周报》等,冯至应约给这些刊物写文章,“一发不可收拾”(23),开始了散文写作的新阶段。晚年的冯至曾称这类文章为“杂文”,但当年他却称之为“鼎室随笔”。现在看来,还是“随笔”更为恰切。然则,冯至的“鼎室随笔”与“杂文”区别何在?作为“随笔”,它与人们熟知的英国随笔又有什么差异?或许通过辨析这些差异,正可以说明冯至随笔的特色。 诚然,冯至的“鼎室随笔”与一般所见杂文颇有相似之处。在这些写于战时的随笔中,读者不难发现批判现实、议论时事以至驳难时论的内容。在这方面,冯至未尝不受他很赞赏的论战家尼采、克尔凯廓尔以及鲁迅的影响。然而,冯至生性不是好胜之人,而严肃诚恳的为人、为文态度,也使他无意把自己的批评性随笔写成尼采、鲁迅那样自信满满、所向披靡的论战性杂文,更无等而下之的“骂人”杂文。冯至所要力戒的,正是从《语丝》派到左翼杂文家的嬉笑怒骂之流气、道德自高之霸气和政治上的诛心之论。因此,他在“鼎室随笔”中对时事的批评,始终坚持诚恳商榷的论议态度、对事不对人的严肃界限和就事论事的写作伦理,这恰与西方近现代批评性随笔在伦理和论理上的严肃性相一致。 1944年,冯至曾分别著文批评过陈寅恪和梁漱溟的言论。抗战时期的陈寅恪已是学界公认的史学泰斗,可这位史学大家同样也有盲点和缺点。除了在学术上时有钻牛角尖的执拗外,过重的旧世家子弟之积习使他颇多自矜自怜的遗少气,而博学往往成了沉重的历史包袱,反而使他看不清抗战的前途,以至于作出以古例今甚至以古乱今的悲观预言。于是,冯至对他给予严肃恳切的批评: 什么是以古乱今呢?一个现象的演成有种种复杂的因素,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自然也短不了历史的。过去的一件事与现在的一件事,无论如何类似,可是彼此组成的因素绝不能完全相同。若是把两件事只就表面的相似并论,而不顾及它们组成的因素,则很容易使人戴上历史的眼镜观看现在,模糊了现在的本来面目。一位著名的史学家,他“读史早疑今日事”,由于东晋与南宋都没有能够恢复中原,便写出“南渡自应思往事,北归端恐待来生”这样没有希望的诗句。这位史学家,在当前的史学界是有杰出的贡献的,但是这两句诗所表达的看法却很不妥切。(24) 文中所说的那位慨叹“读史早疑今日事”的史学家就是陈寅恪。而冯至主张“我们对于现在的种种现象,最好就事论事,才不至失之支离。援引古事以推论现在,与复古主义者援引古事以支持一个日趋腐朽的势力,不管二者的出发点是怎样不同,却都是同样容易犯张冠李戴的时代错误”(25),无疑是中肯之论。冯至在文末更援引小学时读过的一则故事,对那些执迷于以古例今的人发出了恰切而且中肯的提醒: 一个商人坐在一只海船上,商人问船上的水手,你的父亲是怎样死的呢?水手回答,父亲是水手,在水里淹死了。商人又问,你的祖父是怎样死的呢?水手又回答,祖父也是水手,在水里淹死了。商人惊讶地说,那么你为什么还当水手呢?水手不回答,只是反过来问商人,你的祖父与父亲是在什么地方死的呢?商人回答,都是在床上。水手也同样惊讶地说,那么你为什么还敢在床上睡眠呢? 祖父与父亲都在水里淹死了,在这商人的眼里可以说是历史的教训。但是这教训并不能阻止他们的子孙充当水手继续在海上奋斗。一个民族也应该像这个勇敢的水手似地看待过去的历史的教训。(26) 至于梁漱溟,青年时代的冯至对他很尊敬,但也有质疑。他曾这样回忆梁漱溟:“我在大学时,听过他的讲演,那时觉得他态度诚恳,言行一致,使人钦佩。但是他谈到西洋的文化或西洋人的人生态度时,却给人以一种‘强不知以为知’的印象。”(27)梁漱溟的这种“强不知以为知”的习气后来更加严重,而他的《三种人生态度》一文更是引发了冯至的批评。梁漱溟在该文中把人生态度分为三种:逐求、厌离、郑重。第一种是西洋人的,第二种是印度人的,而第三种是中国人的。冯至说: 我读到这里,不觉发生了疑问:这真是西洋人的吗?广泛言之,可以说一切人都是这样,但是一比较,却更是中国人的…… 可是,我也不否认西洋人的人生态度是逐求的,不过跟梁先生所列的那些项目有些不同。他们逐求的是什么呢?我们在他们历史上看得清楚:真理、人权,他们为了这些不惜牺牲生命,而我们这里却有不少人为了吃,为了色,为了金钱,不惜牺牲生命。(28) 这是批评性随笔所应有的恳切说理之风度,而非论战性杂文常见的嬉笑怒骂之做派。冯至曾为文专论“批评”与“论战”之区别,最后的结论是: “平理若衡,照辞如镜”,是批评家应有的风度,“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是论战家在自身内感到的不能推脱的职责;批评家辨别是非得失,论战家则争取胜利;前者多虚怀若谷,后者则自信坚强;前者并不一定要树立敌人,后者往往要寻找敌人;前者需要智力的修养,后者则于此之外更需要一个牢不可破的道德:正直;批评如果失当,只显露出批评者的浮浅与不称职,若是一个论战家在他良心前无法回答那些问题,他便会从崇高的地位翻一个筋斗落下来,成为一个无聊而丑恶的人。(29) 这辨析切中肯綮,尤其是对论战杂文的危险之警告——若一心克敌制胜因而道德自高、师心自用、任性而为,往往会走向反面、跌入丑恶——是值得杂文家思索的。 至于冯至的“鼎室随笔”与英国随笔之异同,则需要略作解释。自18世纪初斯梯尔和艾迪生主编《闲话者》和《旁观者》以来,致力于社会道德和文化政治批评的报章文字,就成为英国随笔的主要趋向。“五四”以来中国报刊上的随感录杂文,其直接的文化渊源就是英语报刊里的批评性随笔,而并非所谓中国古代“杂文”(30)之复兴。只是那些随感录杂文往往因现实的恶劣和传统的沉重而偏多愤懑极端之论,因而大多偏离了英国随笔的温和、节制与善意的态度。冯至的“鼎室随笔”却态度诚恳、分寸严谨,与英国随笔的批评态度相近。不过推究起来,冯至的诚恳与严谨首先根源于他的性格和修养,而并非来自英语随笔的启发。真正给冯至以启发的,乃是克尔凯廓尔、雅斯丕斯和里尔克的思想与文章。因此,“鼎室随笔”虽然缺少了英国随笔的幽默风趣,但冯至于随笔中深入反思国人的生存状态,并进而提点在世为人的存在之道,这种思想深度却是英国随笔所欠缺的。 诚如冯至在晚年所坦承的,他的这些战时随笔“也是我个人当时的思想记录,其中有不少主观的不切实际的议论,西方资产阶级文学哲学的影响随处可见,但也不能完全否定,个别地方不无可取之处”(31)。所谓“主观的不切实际的议论”自然是谦词,而“资产阶级文学哲学的影响”,主要就是存在主义和现代派文学的影响,尤其是来自克尔凯廓尔、雅斯丕斯和里尔克等存在主义哲人及诗人的影响。正是在他们的启发下,冯至对国人消极不健康的生存状态有了深刻的洞见,于是著文予以严肃恳切的批评。 如在《忘形》和《自慰》二文中,冯至对国人的两种人格类型——“忘形者”(包括“得意忘形者”和“失意忘形者”)和“自慰者”作了通俗的存在分析。不论是“忘形者”还是“自慰者”都在逃避自我应该承担的责任,让自己陷于自欺妄为的状态里不能自拔。尤其是“忘形的失意者”,可说是冯至对国人生存状态的过人发现。他精辟地指出:“忘形的失意者爱把自己当作一个世上最不幸的人,可以例外看待,一般人行为里的节制他也无须遵守;同时他并不自省,他的失意是否这样深,纵使这样深,他更不了解应该怎样担当这样的失意。因此自己的不幸就被看作是人间最大的不幸,在这最大的不幸的笼罩下,他就为所欲为了。”(32)这种自欺妄为的生活做派自古以来就相传不绝,尤其是知识分子中有不少人都习惯以“失意”为由而“忘形”到任性妄为。有鉴于此,冯至转而倡导自我担当的存在之道:“人之可贵,不在于任情地哭笑,而在于怎样能加深自己的快乐,担当自己的痛苦,那些临死时还能保持优越姿态的人,有如嵇叔夜最后一曲的《广陵散》,我们只有景仰赞叹。”(33)至于冯至所批评的“自慰者”,其可悲之处乃在于“看见人家有什么长处,便说自己曾经有过……看见自己有什么短处,便说人家也有”(34)。这大略相当于鲁迅所揭示的“精神胜利法”,乃是国人的精神痼疾,所以冯至既严肃地痛下针砭,同时也恳切地提出救济之道:“消极的自慰只能使人苟且偷生,积极的自责却能使人活得更像样子。在‘民族复兴’成为盛极一时的口号的时代中,我希望大家自责能多于自慰。”(35) 应该说,冯至的“鼎室随笔”之过人的思想深度确实缘于存在主义哲学的启发,但由于冯至运用随笔这种平易近人的文体,使它们与议论滔滔的杂文和抽象推论的论文判然有别,显示出深入浅出的文章艺术。如在《认真》一文中,冯至先从不认真的日常现象谈起,接着以严肃而诚恳的态度对中国人中很普遍的马虎习惯进行批判,最后水到渠成,提倡一种认真负责的生存态度。而这种态度其实带有存在主义的意味: 科学教给我们,事事不容有一点含糊……我们为什么不把那点科学精神运用在我们的生活上边呢?我爱慕那些认真的人……《檀弓》里曾子易箦的故事是很感动人的,这故事常常使我联想到一个法国诗人临死时的一件事:那是Felix Arvers,他卧在医院里的床上,他正在平静地死着,看护他的修女以为他已经死去了,便大声向外边叫喊,寻找一些东西;但她不是受过教育的女子,有些字音说不准确,把corridor(走廊),说成collidor了。这诗人于是把他的死亡往后推迟了片刻,他认为是必要的,就是向那个修女讲明,并且纠正她,说这个字中间有两个字母是两个“r”,而不是两个“l”。里尔克在他的小说《布里格随笔》里记载了这段故事,他说:“他是一个诗人,他憎恨‘差不多’;或者这事对于他只是真理攸关,或者这使他不安,最后带走这个印象,世界是这样继续着敷衍下去。”……现代哲学家雅斯丕斯曾对此说过这样的话:“任其自然,觉得事体不关重要,是走向虚无,走向世界从内心里破碎的道路。”——在事事不求认真的社会,真使人担心要走向这条可怕的道路。(36) 冯至就这样由浅入深地将“认真”上升到存在哲学的高度(所引雅斯丕斯、里尔克就是存在主义哲人或诗人),但又没有一点玄虚,对“认真”的生存态度给予了明白晓畅的解说。 批评性的随笔当然也有破有立,但与论战性杂文之不容稍让的凌厉态度不同,冯至的“鼎室随笔”之破与立均诉诸人的感性经验和知性的理解力,所以立意虽然严肃,在表达上则力求通过生动的事例,让读者自然而然地达致存在意识之自觉。如在《“这中间”》一文中,冯至要破除的是那种企望仙境、自足自了的幻念,张扬分担共在、相互关情的生存态度。然而冯至并不从说理入手,而是叙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在18世纪中叶的瑞士法隆,有一位青年矿工因事故被压在矿井之中,五十多年后人们无意中发现了他的尸体,由于一种防腐性矿水的浸润,这矿工的尸体保存完好,宛然如生。有人很歆羡这位青年沉睡了五十年,免遭人间的苦难,可问题是免去了这一切,这五十年对青年来说岂不是个空白!在这里,冯至实际上触及到个体存在与人类“共在”之关系的问题,旨在强调个人要想获得充实的生命和真实的存在,只有在“在世”中、在与他人的“共在”中才能实现,而非自私的互不关心就可达成。由于冯至对这个“存在之道”的揭示并不是通过雄辩的议论来完成,而是借助于生动有味的故事委婉提点,因此更为亲切、感人。这个例子表明,冯至的“鼎室随笔”虽以深切的存在之思取胜,但仍葆有足够的艺术魅力。 与深切的存在之思相契合,“鼎室随笔”的语言力戒华美,不求洒脱,没有幽默,而一例表现出平和恳切、庄重肃穆之美。这种语言特点,除了是冯至沉静内向的性格使然,也与他长期从事中欧与北欧文学的译介和研究有关,尤其与来自克尔凯廓尔、雅斯丕斯和里尔克等人思深文庄的随笔有很大的关系。这里不妨举《决断》一文为例。此文先从画家米勒在困苦的生活与艺术的坚守之间做出决断、王羲之和陶渊明毅然解印去官的决断说起,接着引出存在主义哲人克尔凯廓尔关于决断的名言: 我在从先的一封信里说:爱,给一个人的本质一种谐合,这谐和是永久不会完全失却的。现在我要说,选择赋予一个人的本质一种庄严,一种永久不会完全失却的寂静的尊荣。有些人把一个非常的价值放在这上边,即是有一次面对面看见过一个伟大的人物。他们永久忘不了这个印象,这印象给他们的灵魂一个理想的图像,使他们的本质高贵化;然而就是看见伟大人物的那瞬间,不管它怎样富有意义,但比起在选择的瞬间还是毫无意义的。如果在人的四围一切都是寂静的,庄严的,像一个星光历历的夜,如果这灵魂在全世界中单独地与自己为伴,这时迎面而来的不是一个杰出的人,却是那永久的力,这好像天敞开了,并且这个自我选择他自己,或者说,这个自我在迎接他自己。这时灵魂看见了最上的崇高,绝不是庸俗的眼睛所能看见的,却也是永久不会被忘却的,这时这个人格接受了骑士受勋礼,使他永久高贵化。(37) 然后冯至发挥道: 生,需要决断,不生,也需要决断。一个人从事一个事业,一个民族从事一个战争,若是走到最艰难的段落上,便会发生一个严重的问题:继续奋斗呢,还是断念?继续奋斗需要决断,断念也需要决断。前者的决断固然是坚毅的,后者的决断也未必完全是怯懦的。决断前或许会使人有一度陷入难以担当的苦恼,但生命往往非经过这个苦恼不能得到新的发展。——孟轲曾经以他伦理家的口吻用鱼与熊掌的取舍比喻生与义的取舍,事实上这个比喻是不很恰当的,因为生与义的取舍绝没有鱼与熊掌的取舍那样轻易:换句话说,越是艰难的决断,其中含有的意义也越重大。(38) 看得出来,冯至的散文语言显然受到他敬仰的克尔凯廓尔的熏陶,但却没有令人讨厌的欧化气,而是成功地转化为朴素、优雅、庄重的汉语,与文章的内容相得益彰。这样的语言造诣,在中国现代散文中是很少见的,既给人亲切恳切之感,又让人肃然起敬。 正如《决断》所表明的,冯至写于20世纪40年代的随笔往往从不显著处反思国人的生存状态、提点积极健康的存在之道。这样的文学行为绝非无所谓的“纯文学”笔墨,它们其实都包含着严肃崇高的志愿,即通过对中华民族的存在方式之批判,唤醒个人的生命活力和存在的自觉,并经由个人的自觉达到“民族的自觉”和“民族的复兴”。 从中国现代散文史的角度看,冯至的“鼎室随笔”系列散文显然属于在20世纪40年代的艰难时世中崛起的知性散文之列。此前,我曾在一部现代文学史著作里概述过中国现代知性散文的总体特征(39),同时也简略论及冯至的知性散文的独特性: 冯至的知性散文颇富生命—存在哲学的意蕴,却并不表现为抽象的说理,而始终不离日常生活的经验,谈说具体恳切,没有一点玄虚,给读者的是生动可感的印象和深入浅出的启发,其引人入胜之美与耐人咀嚼之味,远非装模作样的“哲理散文”可比,也与驳难论战的杂文及纯然论事说理的议论文有别。(40) 在此想略作补充的是:“论议”在中国古典散文中一直绵延不绝、号为大宗。自庄、孟以来,文便尚气,到曹丕乃自觉“文以气为主”,后来韩愈更有“气盛言宜”之论。然而,正因“气盛”,古人的论议便难免有过甚之词以至过情之论。而冯至的“鼎室随笔”,因为抱有谦虚的知性态度,所以旨趣严肃、不为意气之论,立言恳切、力戒过甚之辞,也可说为中国的论议文章开拓了平心静气、诚恳深切的新境界。 ①季羡林:《诗人兼学者的冯至先生》,载《外国文学评论》1990年第3期。 ②冯至:《杂诗九首·自遣》,《冯至全集》第2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06页。 ③“幽婉的”是鲁迅在20世纪30年代对冯至早年诗作的评语(参见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43页)。 ④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60页。 ⑤鲁迅:《南腔北调集·小品文的危机》,《鲁迅全集》第4卷,第576页。 ⑥刘西渭(李健吾):《〈鱼目集〉》,《咀华集》,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年版,第133页。 ⑦梁遇春:《〈小品文续选〉序》,《梁遇春散文全编》,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555页。 ⑧《山水》出过两版,第一版由重庆国民出版社于1943年9月出版,此版收文过少,且出版仓促,连作者的跋语都漏排了。抗战胜利后,冯至又在上海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刊行《山水》第二版,增收了四篇文章,共收文十三篇,写作时间则跨越了1930年到1944年的整整十四个年头。平均每年还不到一篇,足见作者写作态度之严肃认真。 ⑨冯至:《蒙古的歌》,《冯至全集》第3卷,第12页。 ⑩冯至:《赤塔以西——一段通信》,《冯至全集》第3卷,第14页。 (11)(12)里尔克:《给一个青年诗人的十封信》,冯至译,《冯至全集》第11卷,第288页,第300页。 (13)(14)里尔克:《山水》,冯至译,《冯至全集》第11卷,第330页,第330页。 (15)(18)(19)冯至:《山水·后记》,《冯至全集》第3卷,第72—73页,第71—72页,第73页。 (16)里尔克:《马尔特·劳利兹·布里格随笔》,冯至摘译,《冯至全集》第11卷,第331—332页。 (17)冯至:《里尔克——为十周年祭日作》,载《新诗》第1卷第3期(1936年12月10日)。 (20)冯至:《忆平乐》,《冯至全集》第3卷,第69页。 (21)冯至:《山村的墓碣》,《冯至全集》第3卷,第57—59页。 (22)(23)(31)冯至:《诗文自选琐记》,《冯至全集》第2卷,第182页,第182页,第183页。 (24)(25)(26)冯至:《论历史的教训》,《冯至全集》第4卷,第103页,第103页,第104—105页。 (27)(28)冯至:《逐求》,《冯至全集》第4卷,第42页,第43—44页。 (29)冯至:《批评与论战》,《冯至全集》第4卷,第128页。 (30)在古代中国,杂文乃是一个分类名称而非文类概念——古人往往把一些无法归类的文章归入“杂文”,如《文心雕龙》将“七”、“对问”、“连珠”等总称为“杂文”。后来文章样式日益繁多,无法归类者日盛,纳入“杂文”者也就日益芜杂。至于所谓古代“杂文”或“小品”之典范,如皮日休的《皮子文薮》、陆龟蒙的《甫里集》、罗隐的《谗书》等,那不过是现代人的追认。其实皮日休、陆龟蒙和罗隐的文集都属集部,它们在文章体制上追随的乃是诸子文系统论说的传统,与现代杂文或小品并不相同。 (32)(33)冯至:《忘形》,《冯至全集》第4卷,第15页,第15—16页。 (34)(35)冯至:《自慰》,《冯至全集》第4卷,第32页,第32页。 (36)冯至:《认真》,《冯至全集》第4卷,第6—7页。 (37)(38)冯至:《决断》,载《文学杂志》第2卷第3期(1947年8月)。 (39)参见严家炎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中册,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312—313页。 (40)严家炎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中册,第3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