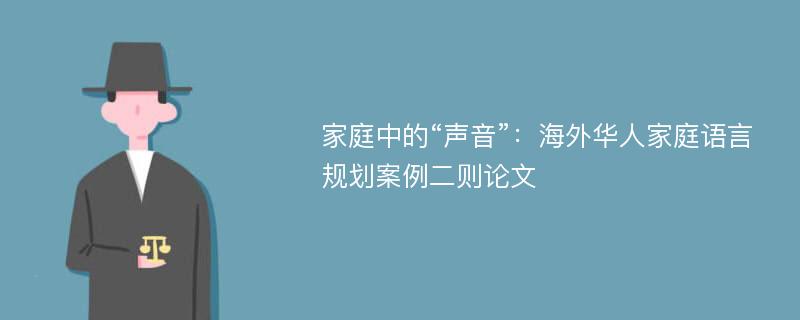
家庭中的“声音”:海外华人家庭语言规划案例二则
董 洁
(清华大学 外文系 北京 100084)
提 要 本文使用Hymes的声音理论,对两则民族志语料进行分析,探讨海外华人家庭的语言规划和家庭语言使用状况。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全球化程度加深,海外华人的全球移动轨迹愈加复杂。许多人由于工作原因或商业需要,频繁往来于移入国和移出国之间,其语言资源更加丰富、语言使用更加复杂、社会影响力也更大。新的语言和社会现象要求我们不仅要对宏观状况进行把握,更要对微观情况进行全面、深入和细致的分析。本文采用民族志研究方法,对两个华人移民家庭进行长期跟踪研究,讨论他们的家庭语言规划。研究显示,两个移民家庭处于不同的移民阶段(一个是第一代移民,一个是第三代移民),子女处于不同成长阶段(一个家庭的子女未成年,一个已经成年),家庭语言规划方式不同(一个是显性规划,一个是隐性规划),但是两个家庭对语言的规划类似,即英语和移民目国语言为公共空间语言,鼓励子女使用普通话,而家乡方言则在家长之间使用。
关键词 声音理论;家庭语言政策;语言意识形态;元语用话语;民族志研究
一、引 言
中国的语言资源非常丰富,随着全球化进程不断加深,人们的语言生活状况也呈现出更加多样化的趋势。每个家庭都是一个小型的语言生态系统(李国芳,孙茁2017)。处在全球化之中的家庭,多种语言a 为引文方便,本文“语言”亦可指方言。 可能混杂并用。这些语言之间可能存在互补或者竞争关系,也会与家庭之外的社区和社会产生不同程度的相互影响,因此家庭语言生态系统愈加复杂。当有多种语言可供选择时,应该在家庭中使用哪种语言?选择这种语言将会对儿童语言发展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能否增加第二代移民的社会竞争力?是否会导致祖语(heritage language)最终消失?这些问题以及其他许多相关问题,都属于家庭语言规划的研究范畴。家庭语言规划,或称家庭语言政策、家庭语言政策与规划,是指家庭内部对其成员之间的语言使用进行的显性或者隐性的规划(Schiffman 1996;Shohamy 2006;King et al. 2008)。家庭语言规划是语言政策研究的一部分。语言政策研究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与当时西方殖民体系崩溃、民族国家兴起、发展中国家加快现代化进程等时代大背景息息相关。早期的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注重解决语言问题,并将对语言的规划看作是语言专家使用技术手段对语言资源进行分配,进而从国家政策层面解决后殖民时代国家独立运动中遇到的语言问题(Nekvapil 2006)。近年来,随着国际学界进入“后问题”时代(不再把社会现象看作是问题),语言政策研究从解决语言问题,转而关注在动态的社会、文化、意识形态体系内语言政策是如何发生变化的(King et al. 2008)。一批采用自下而上模式的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不断涌现(如Wiley & Wright 2004;Ricento 2006;Robinson et al.2006;Cooper 1989)。这些研究主要关注行政机构、学校、工作场所等公共空间范畴内的语言使用,而家庭语言政策和规划研究相对较少。但是,家庭等私人空间中语言使用状况在儿童语言习得、双语发展、身份认同、家庭及社会关系、民族语言传承等方面都有重要意义,因此越来越多的学者将注意力转向家庭语言规划研究。
本文使用声音理论(voice)对得自两个家庭的访谈语料进行分析,探讨海外华人移民家庭语言规划。声音理论传统上有巴赫金的声音理论和海姆斯的声音理论(Dong & Dong 2013)。巴赫金(Bakhtin 1931/1981)将声音与特定的人物个性或社会角色联系起来,并将声音区分为个人声音(individual voice)和社会声音(social voice)。海姆斯(Hymes 1996)提出当人们发出声音,他们不因为自己的语言而失去机会,同时可以自由地使用自己的语言而满足其交际需求。本文先对家庭语言规划研究和声音理论进行回顾和讨论,之后主要使用海姆斯的声音理论进行语料分析,探讨海外华人家庭对多种语言资源的选择和运用,以及家庭语言规划对子女全球移动能力的影响。
大学生对外卖的便利性、卫生安全、价格、口味、服务态度和种类等方面有很高的关注度.其中,促进外卖发展的主要因素为便利性、口味、服务态度和种类,阻碍外卖发展的主要因素为卫生安全和价格.
二、家庭语言规划研究
King(2016)将对家庭语言的研究分为4个阶段,前两个阶段偏重于认识研究:(1)第一阶段是20世纪初以经典的日志研究为基础,观察和分析研究者自己小孩的语言发展状况,代表性成果是“一人一语言”模式(One-Person-One-Language,简称OPOL)(如Ronjat 1913,转引自King 2016)。(2)第二阶段在心理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框架下,以儿童双语发展研究为主,关注单语儿童和双语儿童不同的发展轨迹、语言迁移(linguistic transfer)的本质,以及双语现象与认知特征之间的关系等。比如:De Houwer(1990)对荷兰语-英语双语儿童进行调查后,认为儿童早期句法发展与具体语言相关,而且语言之间缺乏迁移。Lanza(1997)通过社会语言学和语篇分析方法回答了一个经典的心理语言学问题,即儿童语言区分能力是在3岁以前还是3岁以后形成的。通过对家长和儿童之间语言互动的深入分析,Lanza认为3岁以前的儿童有能力进行语码转换。(3)第三阶段开始在社会语言学框架下对家庭语言规划研究进行定义,并形成了这一领域中的两个主要分支,即家长语言意识形态研究和儿童语言发展研究。在这一阶段,家庭语言规划研究的短板也逐渐显露出来。比如:传统的家庭语言规划注重典型家庭(如两家长、中产阶级、欧洲语言等)研究,而对非典型家庭(如单亲、非欧洲语言、移民家庭等)尚缺乏研究。另外,关于儿童在家庭语言规划中的主体性、身份认同、家庭(重)构建等方面的研究也很不足。(4)第四阶段,也就是当前阶段,研究重点不再是家庭语言规划的结果,而转为在跨国移民家庭、非典型家庭,以及多语环境中家长和孩子如何通过家庭语言定义自己和他们各自的家庭角色,以及语言规划对家庭生活的影响等(如Zhu & Li 2016;Curdt-Christansen 2009,2016)。
四是加强信息手段监管。依托“数字政府”建设全省一体化信息平台,建立全过程留痕管理机制,实现全省预算管理动态联网监督,将各级全口径财政资金纳入实时监控范围。财政部门依法落实向省人大及其常委会报批、报告和备案等规定,配合省人大推进预算联网监督工作。
华人学者对家庭语言规划研究的贡献令人瞩目。例如:Zhu和Li(2016)对3个情况各异的英国华人移民家庭(一个朝鲜族家庭、一个香港家庭、一对退休夫妇)的语言规划进行了深入研究。他们没有讨论汉语或者朝鲜语能否得到传承,而是关注这些家庭的未来发展、身份认同、社会网络与语言使用之间的关系。Curdt-Christansen(2009,2014,2016)对加拿大、新加坡华裔家庭等的研究认为,家庭成员对语言的看法很多元,这些不同的看法来自他们对民族身份和文化实践的不同态度;这些态度和看法又与移民国家的语言政策和教育政策交织在一起,使得移民家庭在语言选择上尤其纠结,常常以减少母语的使用为代价解决这些存在于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层面的多语选择问题。Li(2002,2006a,2006b,2006c)对华人移民家庭的双文双语教育进行研究,强调少数族裔社区环境和子女能动性在家庭语言政策中的重要影响。Zhao和Liu(2008)对新加坡华人家庭及儿童的语言使用进行研究,认为汉语已经逐渐让位于英语,并且失去了相应的语言资本。此外,《语言战略研究》2017年的家庭语言规划专题也在国内学界引发了很大地研究热情,国内多家期刊不断涌现对这一领域的理论探讨和实证研究。
三、声音理论
巴赫金的著作自从20世纪70年代末被西方学术界重新发现以来,对文学批评、语言研究、历史、哲学、社会学、人类学和心理学等多个学科领域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巴赫金的声音是指“个性的言语表达,即说话的意识。声音背后总有某种意志或欲望,有它自己的音色和弦外之音”(Bakhtin 1931/1981:434)。巴赫金(1931/1981,1930/1984)区分个人声音和社会声音,并强调声音的社会维度。个人声音与特定的、独特的、情境化的人物有关;社会声音则指社会认可的、典型的语言区别,如阶级话语、性别话语和职业话语。诸如“他(说话)真像个大老板”“我(在你的话里)听到了他的声音”,或者“你为什么说话像个小女孩”这样的话语属于社会声音。Agha发展了巴赫金的声音理论,认为声音是人物形象,与社会声音接触就是与真实或想象的人接触。人们在这些实践中接触声音,识别与其相关的人物形象,并对有关的人物形象进行角色定位(Agha 2005)。
声音理论的另一个主要来源是海姆斯的著作《民族志、语言学、叙事不平等性:对声音的理解》。海姆斯(Hymes 1996:64)提出:“[声音]的两个因素由来已久。一种是负面自由,即人们拥有不会因为其语言而失去机会的自由,不论是说话、阅读,还是书写中使用的语言。另一种是正面自由,即人们使用语言得到满足……我用‘声音’把这两种自由结合起来,即人们有发出自己声音的自由,以及自己的声音得到倾听的自由。”海姆斯想象了这样一个社会:人们不会因为他们说话的方式而失去机会;不会因为他们使用的语言而被污名化;人们敢于发出声音,并且知道他们的话语会得到倾听。Blommaert(2005)发展了海姆斯的声音理论,认为声音是人们通过调动可用的符号资源来实现预期沟通效果的过程,是语言形式与预期功能之间能否形成对应关系的能力。语言形式与功能之间的关系与该语言是否可以作为移动资源有关(Blommaert 2010)。一些语言资源,如普通话,是较好的移动资源并具有较高社会声望,人们凭借普通话可以去中国各个省市,与那里的人们沟通交流;而另一些语言则只有较低的移动能力,比如有些方言可能只在某些特定的地区使用,离开这个地区就难以以之沟通了。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的语言形式与他们所期望达到的交际效果不能匹配,就会产生“失声”的现象,即他们的话语没有达到预期效果,没有实现预期功能,或没有被倾听。
(2)配备护航拖轮“云港十六”(在航线熟悉以及确保天气良好的情况下可以不配备),其职责主要是担任引航及护航任务。遇到恶劣气候,如雾天可在半潜驳近旁鸣雾号,随时观测半潜驳的吃水及灯标情况;在天气正常情况下,又可作为主拖轮的助拖,以增加拖航速度;在海域情况较复杂区域,如养殖区渔船、渔网多等情况,提前探清航行前方的碍航设施,提醒主拖轮避让;遇异常情况时,积极参与抢险。
四、家庭中的“声音”
本文中的两则案例都取自海外华人移民社群的民族志田野调查。海外华人通常掌握多种语言,具有较高的移动能力。早期劳动力移民倾向于在移民目的国定居下来,努力工作,以期融入主流社会,并实现社会上向流动;新一代移民由于受教育程度更高,可调动的社会资本更多,同时也由于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发展前景广阔,他们在移民目的地和家乡之间的移动轨迹更加复杂,完全打破了“一生漂泊海外,老来落叶归根”的传统模式。案例一的访谈对象王先生是笔者居住的一座荷兰中型城市的中餐馆厨师,属于传统的劳动力移民。我们起初在王先生工作的餐馆进行调查,之后王先生邀请我们为他的孩子辅导汉语拼音。经过一段时间的参与式观察后,我们对王先生进行深度访谈。案例二的访谈对象吕先生是笔者的学生,大学四年修过笔者两门专业课。毕业后我们仍然追踪他的语言状况、个人发展和全球移动轨迹。经过长时间的参与式观察后,我们对吕先生进行深度访谈。
早期海外华人移民以使用粤方言、闽南话、客家话为主,移民社区中通常广泛使用粤方言;近年来使用普通话的留学生、高技术移民、投资移民越来越多。除了普通话和汉语方言以外,英语和移民国当地语言也是华人家庭重要的语言资源。本案例中的王先生40多岁,20多年前从福建移民荷兰,此后一直在中餐馆打工。由于当时的餐馆老板多数是来自香港和其他东南亚地区的移民,餐馆里的工作语言是粤方言。为了工作需要,王先生首先学习粤方言,因此尽管他来荷兰已经20多年了,荷兰语水平还是较低,需要妻子帮忙翻译。他的妻子是同一家中餐馆的服务员,可以熟练使用粤方言、闽方言、普通话和荷兰语。他们有两个儿子。大儿子9岁,在荷兰当地一所公立学校上学,周六在一所中文学校学习中文。中文学校提供粤方言和普通话课程,王先生为儿子选了普通话课程。小儿子3岁,之前一直在福建老家由亲戚照看,近期才接来荷兰,因此小儿子在来荷兰之前大部分时间接触到的是福建方言。田野调查期间,王先生请我们每周给他的大儿子辅导汉语拼音,因此我们对他家庭内部的语言使用状况有比较深入的了解。在一次交谈中,王先生说他只允许孩子们在家说普通话,不允许说方言、荷兰语或者英语。于是我们就其家庭语言规划对王先生做了访谈。访谈是用普通话进行的。
案例一:“如果他说方言,我们就不理他……”a 此案例中的部分语料和分析发表在Dong, J. and Dong Y. 2013. Voicing as an essential problem of communication:Language and education of Chinese immigrant children in globalization. Anthropolgy & Education Quarterly 44(2), 161–176。
全国层面,房地产开发企业商品房销售额整体不断提升,由1987年的110.1亿元逐步增长至2017年的133 701.3亿元。如图6所示。
语料一:
近期,学者们还研究了当产品市场是垄断时的情形。Cabon-Dhersin[9]比较了完全合作和完全竞争两种极端情形的研发投资。前者是指企业不仅合作研发,而且在产品市场上达成合谋;后者是指企业既在研发市场又在产品市场竞争。Cabon-Dhersin最后惊奇地发现,当产品差异度很大或是技术溢出水平较高时,完全合作能激发更多的研发投资。
(1)董岩:你儿子是在哪里长大的?
(2)王先生:他在福建长大,我的家乡,他的姑姑照顾他。
(9)董岩:你在家教他荷兰语吗?
(4)王先生:他快3岁了,很快要上学了。所以我们把他带回来。
(5)董岩:你觉得他在这里上学比在中国好吗?
(6)王先生:是的。他现在应该开始学荷兰语了。他会在荷兰学校学习荷兰语。
(7)董岩:他现在会说荷兰语吗?
(10)王先生:不。他去荷兰学校,很快就学会了。
(3)董岩:你为什么把他带回荷兰?
在古希腊,城邦就是人开启公共生活的公共空间,人以此为契机在一个公共、开放的环境中交流与行动,人的文化和精神诉求得到满足,人的意识和肉体发展在城邦的孕育下呈现勃勃生机。亚里士多德称:“人是天生的城邦动物”。人的生命存在离不开社会活动的参与,人的生存发展始终与城邦紧密相连。人在城邦生活中自由地发表言论,积极追求至善的德性。在古希腊,长期的战争环境要求每一个公民必须具备强健的体魄,能加入到保卫城邦的战争中,斯巴达的儿童从七岁起就由国家抚养,每一个人都进行体育教育和军事训练。也正因如此,公民意志得以凝结成强大的力量,保护自身,保护家园,人的日常生活得以有序地进行。
(8)王先生:不会,基本不会。
(11)董岩:你们在家和他讲什么语言?
(12)王先生:我们在家和他讲中文。
(13)董岩:你们不和他讲福建方言吗?
(14)王先生:不。他在中国时,讲福建方言。我家里没人讲普通话。我妈妈只会讲方言。她不识字。我儿子在国内上过半年的幼儿园,学了普通话。但是他只能听(普通话),他不会讲(普通话)。
短暂性脑缺血是可逆性神经功能障碍疾病,该疾病在老年群体中发病率比较高,发病突然,没有征兆,病情持续数分钟,反复发作[1]。发病后,如果不进行科学有效的治疗,则会引起脑梗死和高血压等并发症[2]。药物治疗时目前的主要方式,不同药物的治疗效果存在差异性[3,4]。短暂性脑缺血的临床发病原因不明确,和脑血管痉挛以及微栓塞有直接联系,抗血小板药物是对短暂性脑缺血进行治疗的有效方式,阿司匹林是比较多见的抗血小板药物,能够清热去痛,抑制血小板聚集。此次我院就双联抗血小板药物进行短暂性脑缺血的治疗效果开展分析研究,现进行以下报道。
(15)董岩:现在怎么样了?
刘莉想起前不久车站搞的一次集中灭鼠活动,肯定是死老鼠什么的死在角落里了。这时正是早上,又正值出行淡季,没什么人来寄存行李,她有些无聊地翻出寄存流水台帐清理到期又无人认领的行李。这是一项例行工作,火车站寄存处总是有一些逾期无人认领的行李,为了避免挤占行李间,他们会定期把逾期无人认领的行李清理一次送到仓库,如果在仓库过了三个月还无人认领,他们就可以随便处理了。
(16)王先生:现在他好多了。我们只和他讲普通话。
(17)董岩:他有什么进步吗?
(18)王先生:是的。他必须讲(普通话)。如果他讲方言,我们就不理他,装作没听见。所以他必须和我们讲普通话。
当我们从生命的角度看一个课堂时,不如意可能是大多数。我们可能更多地看到学生没有那么投入,没有跟着教师的思路走,没有学到教师希望他们学到的东西,会有许多的矛盾和冲突。但是,如果教师不去关注,那么我们就看不到这些课堂隐藏的、微不足道的冲突,看到的只是教学步骤一步一步地推进。但当我们看到这些潜在的或外显的冲突时,课堂就会丰富起来,像一场戏一样,或者就像我们的人生。有时可能谈不上矛盾、冲突,而像杜威所说的“经验的断裂而不是连续”。比如,当其他学生非常配合教师时,一个学生撇撇嘴的表情;当自己的回答没有得到预期的来自教师的点评时,学生失落的表情等。
(20)王先生:不。现在普通话最重要,连香港人也开始学(普通话)。粤语已经不重要了,这几年在荷兰也是这样。你看,这两个孩子(老板的儿子),他们的普通话非常好。
这则语料是一则元语用话语(meta-discourse),即关于人们怎样使用语言的话语(Dong 2010)。在这则元语用话语中,王先生谈到他对家庭语言的显性规划:虽然有多种语言和方言可选择,但是他规定孩子们在家只讲普通话。从第1话轮到第10话轮,他指出把小儿子接来荷兰的最重要原因是他到了上学年龄,而在荷兰当地学校学习荷兰语是最便捷有效的方式。因此他不需要在家中教孩子们荷兰语,而且他本人的荷兰语也不足以教孩子们。这种在荷兰工作生活多年却不会荷兰语的现象在老一代华人移民中非常普遍,主要是因为早期的劳动力移民通常到荷兰后很快会加入中餐的餐饮行业,可以不需要和荷兰主流社会过多接触就能够工作和生活。近年来留学生和高技术移民普遍英语水平较高,而英语在高校等公共空间内相当普及,所以他们也没有学习荷兰语的迫切要求。这也呼应了之前对荷兰华人的研究发现(如Blommaert & Huang 2010;Li & Juffermans 2011)。不过对于早期劳动力移民来说,不会荷兰语(同时也不会英语)仍然限制了他们的空间移动能力以及社会上升空间。由于不懂荷兰语,又不能熟练使用英文,他们的生活局限在华人社区,尤其是餐饮行业中。比起自身发展,他们通常更重视子女能否在本地学校学地道的荷兰语,期望子女融入荷兰主流社会,从而有更好的前途。对这些移民家庭来说,荷兰语是一种公共空间语言,这种语言可以让他们今后在荷兰社会有更大的话语权,让他们的“声音”被听见。
虽然王先生认为孩子们学习荷兰语非常重要,但是他并不打算让他们在家里练习荷兰语。他的家庭语言规划是:每个人在家都必须说普通话(T11~T18)。考虑到在荷兰并没有说普通话的社会大环境,王先生完全可以继续使用福建方言,毕竟这是每位家庭成员都可以熟练使用的语言。但是王先生和太太非常坚定地选择了普通话,“他(小儿子)必须讲(普通话)。如果他讲方言,我们就不理他,装作没听见。所以他必须和我们讲普通话。”(T18)小儿子才到荷兰不久,所以更习惯说福建话。但是如果坚持说福建方言,他就会“失声”(Blommaert 2005),也就是他的话语会被忽略,他的语言形式与预期功能不匹配。这里我们看到海姆斯的声音理论,即为了使自己的声音被倾听并得到应有的反馈,小儿子必须说普通话,因此普通话成为家庭中唯一有用的语言。
王先生和太太的语言规划的确有些超前于孩子的认知水平,但是他们这样做也不是没有道理。首先,普通话在国内是通用语言,具有重要的沟通功能;其次,王先生的语言规划也指向全球层面的语言秩序的转变,即在海外华人社区普通话不仅是家庭语言之一,而且与粤方言一起(或者正在超过粤方言)成为华人社区的通用语。王先生的老板、一个多年前来荷兰开餐馆的香港人,也要求他的孩子们学普通话。普通话赶超粤方言的一个原因是来自中国大陆的移民越来越多,但是更重要的原因是这些新移民多数是留学生、高技术移民、知识移民等,他们更加富裕,也更有影响力,因此他们使用的语言也更有影响力。这些移民人口结构的变化是全球化进程的一部分,而微观层面的语言变化会指向宏观层面的结构性变化。
案例二:“他们切换到温州话,我就听不懂了”
案例二中的访谈对象吕先生30岁左右,是西班牙华裔,祖辈移民海外,在西班牙开餐馆,父辈开始投资其他领域。吕先生和弟弟在本科和硕士期间到中国读书,之后留在中国从事投资工作,准备积累一些工作经验,以便将来接手家族企业。由于吕先生的家族来自浙江温州,后移居安徽黄山,所以除了西班牙语和英语以外,他日常接触到的语言有温州话、安徽话和普通话。就家庭语言规划来说,他的父母没有像案例一中王先生那样明确规定家庭语言,但是在实际的家庭语言使用中,不同语言的使用范畴很明确。首先,西班牙语和英语是公共场合语言,在家里较少使用这两种语言。到中国以前,吕先生和弟弟之间有时候会用西班牙语和英语交流,但是由于18岁以后两个人先后来到中国,所以普通话就逐渐成为他们之间的主要沟通语言了。其次,虽然家庭可选择的方言较多,但是吕先生的父亲和孩子们交流时很少使用方言,而是使用普通话;父母之间、父亲和叔叔们之间交流时通常使用方言。
虽然学者们通常只使用这两个声音理论之中的一个,但是这两者却不是相互排斥的。声音在不同层面呈现出不同的形态:在其原始意义的层面上,人们能分辨出声音的音量、音色、旋律等性质;在巴赫金的理论层面上,人们可以在话语中识别出多种声音,如个人声音、社会声音、性别声音等;在语言形式与功能层面上,海姆斯的理论可以衡量人们的声音会不会被倾听,能否实现预期功能,在交谈中是包括所有在场者,还是排除一些人。因此,对同一段话语进行不同层面的分析时,可以使用不同的声音理论,二者之间并不互相排斥,本文着重使用海姆斯的声音理论对语料进行分析。
语料二:
根据数字新媒体时代的背景,有效更新教学方法是对视觉传达设计教学的必然要求。由于我国长期以来形成的重理论、轻实践的教学背景,当实践教学的要求越来越高时,教师往往表现出对现实束手无策的状态。首先,教师不能有效地学习和借鉴国外先进的教学方法;其次,教师不能根据具体教学问题对教学方法进行必要的创新和改进;最后,数字新媒体对视觉传达教学形成的巨大冲击,使不少教师盲目照搬国外的教学方法,完全摒弃了传统教学方法的精华,这种做法也是不可取的。
(1)吕先生:温州话或者安徽话用不上。
(19)董岩:你不教他讲粤语吗?
(2)董洁:嗯嗯,用不上,用不上指的是,就是比如说温州话或者安徽话没有特别广泛的用途,所以没有让你说?
晓眉和家人听说宝宝越大越健康,所以孕期一直海补,最后分娩前发现宝宝过大,阴道试产失败,不得不剖宫产掏出了重达4.5千克的宝宝,诊为“巨大胎儿”。宝宝半岁时,晓眉与其他新妈妈交流发现,自己的“大宝宝”长得还不如那些六七斤的“小宝宝”,体重被反超,体质也没比别人好。
(3)吕先生:因为教育方面我父亲对我影响很大,他本人语言说得很好,会说西语、英语,会说普通话、温州话、安徽话,但是他从来不和我说方言。他要么说普通话,要么说英语。因为,就是,谈吐这一块很重要,因为方言说多了,是英语还是中文,口音上自然而然就会带一些当地的腔调进去,他希望我(的口音)更纯净一点儿吧,不是很多mixed。
从语料二我们可以看到,吕先生的父亲认为方言“没有用”,并不是指方言的用途不广泛(T1、T2),而是指方言和他为孩子们设计的教育目标不相匹配(T3)。他认为孩子们的谈吐是重要的教育内容之一,而使用方言会使他们的口音不够“纯正”,进而产生语言混杂现象。语言本身是一种交际工具,并不存在哪个好、哪个不好的分别;而且在现实生活中,语言混杂是常态,正如吕先生在话轮3中也使用了英文mixed一词,这本身也是语言混杂的一种表现。但是当语言在社会中使用时,就难免被赋予社会意义和社会价值。人们给语言贴上标签,比如哪种语言优雅,哪种语言洋气,甚至是哪种语言更科学,以及口音是否纯正,都与人们的家庭背景、教育程度、社会层次乃至身份构建直接相关。当人们认为这样的标签是自然而然、理所应当的时候,他们就已经接受了语言被额外赋予的社会意义和社会价值。当绝大多数人都接受时,这种社会意义和社会价值因而上升成为语言意识形态(Dong 2009,2010;Bourdieu 1991;Silverstein 1996;Blommaert 2006)。语言意识形态就像我们赖以生存的空气那样充斥在我们的周边,我们却很少想到它,更少反思它。
语料三:
(1)吕先生:他们谈和我不相关的事情的时候,可能会说(温州话或者安徽话);跟我聊和我有关系的事情的时候,就会用普通话说。生意上的事情他们就不会告诉我,他们还希望我再练几年,所以有时候过节或者碰面的时候,他和我母亲、和家里的亲戚就会切换到温州话,我就听不懂了。
(2)董洁:你是说他们这种语言之间的切换是有意的?
(3)吕先生:对,是有意的选择,就是涉及一些我现在不应该听到的事情的时候,他们会(使用方言)。
为了满足学生就业的需要和行业的要求,旅游管理专业学生的普通话水平测试成绩尽量通过二级甲等水平。一方面注重普通话发音基础的训练,另一方面注重培训学生的行业用语和服务用语。每个学生必须自拟导游词并练习准确发音,情景教学法进行角色扮演,练习普通话服务语言。教师针对方言的发音特点,讲解普通话的发音特点,进行辩证性的学习。这种教学方法较大地提高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经过一学年的改革,旅游管理专业的学生普通话测试成绩二甲通过率达到了93.8%。
语料三显示,吕先生的父母对家庭语言的规划不仅与孩子们的教育有关,而且与家族生意和对未来的规划有关。当交谈内容和吕先生有关时,父母会使用普通话;无关时,则使用方言(T1)。可见这一语言选择与交谈对象、交谈内容等因素相关。什么是有关的内容,什么是无关的内容呢?吕先生列举说,家族生意方面的内容就(暂时)和吕先生无关,因此父母和亲戚们讨论生意上的话题时,就会改用方言交流。根据交谈对象、交谈内容切换语码本来是很常见的语码转换现象,人们都会下意识地根据对话发生的环境、对象、话题等因素进行语码转换,以期更好地进行交流。但不同的是,吕先生的父母是有意识地选择吕先生不能熟练掌握的语言进行交流,以达到中断与他交流的目的(T2、T3)。这就与案例一中的“失声”现象相反,也就是说,并不是让没掌握方言的子女失去发出自己声音的机会,而是使用他们不懂的方言以达到自己的声音不被听见、将他们排除在外的效果。这种排除现象虽然在表面形式上与海姆斯的声音理论不尽相同,但是回顾海姆斯的理论不难发现,海姆斯(Hymes 1996)认为人们应该拥有“免于因为语言失去机会的自由和使用语言得到满足的自由”,语料三中吕先生恰恰是因为语言而“失去”了参与家族生意的讨论。这也印证了Blommaert(2005)的看法,即声音是语言形式与预期功能之间的对应关系,是人们通过调动可用的符号资源来实现预期的沟通效果。在本案例中吕先生的父母调动他们可用的符号资源,实现排除吕先生的沟通效果。
五、结 语
本文两个海外华人移民家庭中,父母均表现出对家庭语言的规划。案例一中的家庭语言规划更为显性,案例二中的相对隐性。同时两个家庭都表现出对普通话的重视以及在家庭中使用普通话的语言实践。与多数前期研究结果不同,本文案例显示普通话在二代移民乃至三代移民中都得到保持。不过,本文案例有其特殊性:案例一中王先生的孩子们年纪尚小,普通话在他们中间的保持情况有待长期观察;案例二中的吕先生和弟弟在18岁左右相继回国,因此普通话的使用得到加强。不过,两个家庭都认为子女应该在正规教育中学习英语和移入国语言(在这里是荷兰语和西班牙语),而在家庭环境中则以普通话为主,目的是保证子女将来能够使用普通话进行交流。这样的语言规划和选择在海外华人移民家庭中非常普遍,实践效果因家庭具体情况和家庭未来发展规划不同而有所差异。
两个家庭的子女都有方式各异但本质相同的“失声”经历。在案例一中,王先生的小儿子如果不用普通话交谈就会被忽略,他的声音不被倾听,也得不到相应的反馈。先不论王先生和太太的做法是否得当,就家庭语言规划来说,这是一则非常突出的显性规划案例。这种做法也不罕见。笔者曾对中国中产阶层家庭做过田野调查(如Dong 2017,2018),其中有多个案例都是家庭为了培养子女英语能力而规定在家庭中只说英语的案例。案例二中声音不被倾听的情况看似与案例一相反,即家长发出的声音不能被子女听到;但其本质可以看作是一种“逆向的声音过程”,即不是使交谈对方的话语不被听见,而是使自己的话语不被听见,在这一过程中语言形式与其预期功能相匹配,家长达到了将子女排除在家族生意之外的交际目的。这种或有意、或无意的以排除为目的的交际事件在实际生活中也很常见。
总之,海外华人移民家庭可调动多种语言资源,这些语言资源使他们具有了较强的全球移动能力。英语和移民目的国语言是移民家庭的主要语言资源。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长,汉语普通话与汉语方言不同,不是海外移民寄托乡愁的语言,随着中国经济增长,普通话更具实用价值,使海外华人不仅可以在移民社区进行交际互动,而且为他们以及他们的子女提供了了解国内动态、参与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的机会,因此也越来越为华人移民家庭所重视。由本文案例可见,微观的家庭语言常常可以反映宏观层面语言秩序的变化和全球政治经济秩序的变化,是语言政策研究中不可或缺的基本领域和研究方向。
参考文献
李国芳,孙 茁 2017 《加拿大华人家庭语言政策类型及成因》,《语言战略研究》第6期。
Agha, Asif. 2005. Voice, footing, enregisterment. Journal of Linguistic Anthropology 15(1), 38–59.
Bakhtin, M. M. 1930/1984. Problems of Dostoevksy’s Poetic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Bakhtin, M. M. 1931/1981. The Dialogic Imagination: Four Essays.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Blommaert, J. 2005. Discours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lommaert, J. 2006. Language ideology. In Keith Brown (ed.), Encyclopedia of Language & Linguistics (Second Edition) . Oxford: Elsevier.
Blommaert, J. and April Huang. 2010. Semiotic and spatial scope: Towards a materialist semiotics. Working Papers in Urban Language & Literacies Paper 62.
Bourdieu, P. 1991. Language and Symbolic Power . Cambridge: Polity Press.
Cooper, Ralph. 1989. Language Planning and Social Change .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urdt-Christiansen, X. L. 2009. Invisible and visible language planning: Ideological factors in the family language policy of Chinese immigrant families in Quebec. Language Policy 8(4), 351–375.
Curdt-Christiansen, X. L. 2014. Family language policy: Is learning Chinese at odds with learning English. In Xiao Lan Curdt-Christiansen and Andy Hancock (eds.), Learning Chinese in Diasporic Communities: Many Pathways to Being Chinese.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Curdt-Christiansen, X. L. 2016. Con fl icting language ideologies and contradictory language practices in Singaporean multilin-gual families. Journal of Multilingual and Multicultural Development 37(7), 694–709.
De Houwer, A. 1990. The Acquisition of Two Languages From Birth: A Case Stud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Dong, J. 2009. “Isn’t it enough to be a Chinese speaker”: Language ideology and migrant identity construction in a public primary school in Beijing. Language & Communication 29(2), 115–126.
Dong, J. 2010. The enregisterment of Putonghua in practice. Language & Communication 30(4), 265–275.
Dong, J. 2017. Chinese elite migrants and formation of new communities in a changing society: An online-of fl ine ethnography.Ethnography 18(2), 221–239.
Dong, J. 2018. Taste, global mobility, and elite identity construction: How Chinese new urban migrants construct elite identities with lifestyle discourses. Journal of Sociolinguistics 22(4), 432–453.
Dong, J. and Dong Y. 2013. Voicing as an essential problem of communication: Language and education of Chinese immigrant children in globalization. Anthropology & Education Quarterly 44(2), 161–176.
Hymes, D. 1996. Ethnography, Linguistics, Narrative Inequality: Toward an Understanding of Voice . London: Taylor & Francis Group.
King, K. A. 2016. Language policy, multilingual encounters, and transnational families. Journal of Multilingual and Multicultural Development 37(7), 726–733.
King, K. A., L. Fogle, and A. Logan-Terry. 2008. Family language policy.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Compass 2(5), 907–922.
Lanza, E. 1997. Language Mixing in Infant Bilingualism: A Sociolinguistic Perspective .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Li, G. 2002. East Is East, West Is West?: Home Literacy, Culture, and Schooling . New York: Peter Lang.
Li, G. 2006a. What do parents think? Middle-class Chinese immigrant parents’ perspectives on literacy learning, homework,and school-home communication. The School Community Journal 16(2), 27–46.
Li, G. 2006b. Biliteracy and trilingual practices in the home context: Case studies of Chinese-Canadian children. Journal of Early Childhood Literacy 6(3), 355–381.
Li, G. 2006c. Culturally Contested Pedagogy: Battles of Literacy and Schooling between Mainstream Teachers and Asian Immigrant Parents .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Li, J. and Kasper Juffermans. 2011. On learning a language in transformation: Two fi nal year students’ experiences in Chinese complementary education. Tilburg Papers in Culture Studies 7 .
Nekvapil, J. 2006. From language planning to language management. Sociolinguistica 20(1), 92–104.
Ricento, T. 2006. Language policy: Theory and practice—An introduction. In T. Ricento (ed.), An Introduction to Language Policy: Theory and Method .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Robinson, J., William Rivers, and Richard Brecht. 2006. Demographic and sociopolitical predictors of American attitudes towards foreign language policy. Language Policy 5(4), 421–442.
Ronjat, J. 1913. Le Développement du langage observé chez un enfant bilingue. Paris: Champion.
Schiffman, H. 1996. Linguistic Culture and Language Policy . New York: Routledge.
Shohamy, E. 2006. Language Policy: Hidden Agendas and New Approaches . New York: Routledge.
Silverstein, M. 1996. Monoglot standard in America: Standardization and metaphors of linguistic hegemony. In Brenneis, D.and R. Macaulay (eds.), The Matrix of Language . Boulder: Westview.
Wiley, T. G. and Wayne E. Wright. 2004. Against the undertow: Language minority educational policy and politics in the age of accountability. Educational Policy 18(1), 142–168.
Zhao Shouhui and Liu Yongbing. 2008. Home language shift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language planning in Singapo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estige planning. The Asia-Paci fi c Education Researcher 16(2), 111–126.
Zhu Hua and Li Wei. 2016. Transnational experience, aspiration and family language policy. Journal of Multilingual and Multicultural Development 37(7), 655–666.
Voice in Family: An Ethnography of Overseas Chinese Family Language Planning
Dong Jie
Abstract This article uses Hymes’ notion of voice to analyze ethnographic data and to discuss language planning in two overseas Chinese families. As China’s economic growth and increasing global involvement, Chinese immigrants demonstrate more complex global movement trajectories than their earlier counterparts; many of them travel frequently between China and their immigration destinations for work or business purposes, bringing them more linguistic resources and making them more active on a global scale. The new and complex phenomena press us to employ a nuanced method in order to study the migrants in a holistic and comprehensive way. This ethnographic study fi nds that the two families demonstrate similar family language planning strategies, i.e. they use English and other immigration destination languages in the public domain, Putonghua as a preferred language in the home, and other Chinese dialects only among parents and older relatives, although the two families are of different immigration stages (the fi rst generation vs. the third generation immigrants), and the children are of different age groups.
Key words voice; family language planning; language ideology; meta-discourse; ethnography
中图分类号 H0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1014(2019)02-0051-09
DOI 10.19689/j.cnki.cn10-1361/h.20190205
作者简介: 董洁,女,清华大学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语言学、语言人类学、语言身份认同、移民研究、民族志研究方法论、语言与教育、语言与新媒体。电子邮箱:dong-jie@mail.tsinghua.edu.cn。
责任编辑:丁海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