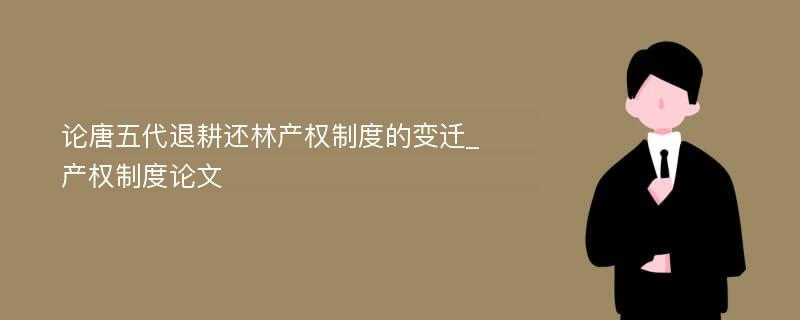
论唐五代逃田产权制度变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田产论文,唐五代论文,制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9;F1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8-0460(2004)04-0059-09
唐朝及五代时期由于种种原因一直存在着为数不少的“逃田”。所谓逃田,通常是指民户全家逃离本籍之后留下的私有田地。官方用语还有逃人“桑产”、“逃人田地”、“逃人田宅”等。
唐五代政府的逃田产权政策发生过重大变化。学术界于此似尚未有专论,但或已从户口检括、土地制度等角度有所涉及。如有的学者从唐朝前期“括户”政策演变的角度论及逃田处置,其中较重要的成果,有杨际平先生的《隋唐均田、租庸调制下的逃户问题》[1],陈国灿先生的《武周时期的勘田检籍活动》[2]等;郑学檬先生则在《五代十国研究》第三章从土地政策的角度述及五代“处理逃户庄田政策”。[3](P128-130)
关于产权的概念,学术界有几种侧重点不同的表述。我们比较赞同这样的界定:“产权即财产权,是法权的一种,即生产关系的法律表现,是包括所有权、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索取权、继承权等在内的权利束,这些权利既可以统一,又可以分离;同时,产权又是一种社会激励的约束机制,具有优化资源配置的功能。”[4]本文拟从唐五代政府如何处理逃田的所有权、使用权和收益权,政府制定和调整逃田产权制度的预期激励作用,地方政府对逃田产权的管理职能等方面,分三个历史阶段,对唐五代逃田产权制度的变迁试加论述。
一、唐朝前期的逃田产权制度
1.政府限期保护逃户对逃田的所有权,逾期则收归国有
唐朝前期,出于赋役繁重、吏治苛暴或者自然灾害等原因,一直存在着户口逃亡现象,有的时期十分严重,如武周时期朝臣竟有“天下户口,亡逃过半”[5]之说。即使在旧史誉为盛世的开元天宝时期,逃户问题依然严重,如开元九年至开元十二年(721-724),宇文融主持括户,结果“诸道括得客户凡八十余万”[6],约占当时在籍户口的十分之一。因此,如何制定和调整逃户政策,是唐朝前期朝廷相当关注的政务,由此带来逃田产权制度的变化。
唐朝前期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实行不允许逃户就地入籍,要求他们自动归回原籍,或者由官府把检括出的逃户强制遣送回原籍的逃户政策。制定这种政策主要是出于维护赋役制度的需要。因为唐前期的赋役征调是以户籍资料为基础的,即租庸调以户籍登录的丁男(课口见输)数量计征定额税,户税以户籍标注的户等高低征收差额税,地税以户籍登录的现耕地亩数计征定额税,加上在府兵制下唐朝规定“有军府州不得住无军府州”[7],因此,强制逃户必须返乡复业就是要将他们重新纳入这一赋役征调体系之中。
为了配合这种逃户政策,招引逃户自动返乡,或者让检括遣回的逃户有一定的生产条件和居住场所,尽快安定下来,唐朝采取在一定期限之内保留逃户的土地所有权的产权政策。唐朝颁令禁止非法买卖逃田。如睿宗唐隆元年(710)七月十九日敕:“诸州百姓,多有逃亡,……逃人田宅,因被贼卖,宜令州县招携复业。其逃人田宅,不得辄容卖买。”[8]玄宗天宝十四载(755)八月制:“天下诸郡逃户有田宅产业,妄被人破除,并缘欠负税庸,先以亲邻买卖,及其归复,无所依投,永言至此,须加安辑,应有复业者,宜并却还。纵已代出租税,亦不在征赔之限。”[9]但是,逃田作为一种农业生产资源,出于财政经济的收益考虑,唐朝又不能听任它们长期荒闲,为此又规定逃户的土地所有权只能保留一定的年限。源自唐《令》的日本《养老令》规定:“凡户逃走者,令五保追访,三周不获,除账,其地还公,未还之间,五保及三等以上亲,均分佃食,租调代输,(三等以上亲,谓同里居住者),户内口逃者,同户代输,六年不获,除账,地准上法。”[10]这一法令对整户或非整户逃亡所留下的田地何时充公有三年和六年两种不同的时限。陈国灿先生认为:“这恐怕是初唐以来对逃户田土的令文。”他还引用敦煌文书抄录的睿宗唐隆元年的一段敕文为据,该敕称:“逃人田宅,不得辄容卖买。其地任依乡原价,租充课役,有剩官收。若逃人三年内归者,还其剩物。其无田宅,逃经三年以上不还者,不得更令邻保代出租课。”另外,吐鲁番出土文书《唐神龙三年高昌崇化乡点籍样》有如下内容:
户主康迦卫年五十七 卫士
右件户逃满十年田宅并退入还公
陈国灿先生认为:“康迦卫的逃亡,至神龙三年(707)已是逃亡十年未归,如以检籍的长安三年(703)推算,则已逃经六年,他的田宅还未收归官府,只是由于‘逃满十年’,才按规定令其‘田宅并退入还公’,这可能是武后朝新的统一规定。……比之于原来逃满三年,其地还公的规定,显然是一种放宽。”[2]
尽管有关资料不多,但我们仍可以肯定唐朝前期允许逃户保留土地所有权是有年限的。这种规定或有所变通。如玄宗开元二十四年(736)正月《听逃户归首敕》称:“天下逃户,所在特听归首。容至今年十二月三十日内首尽。其本贯旧有产业者,一切令还。”[11]“一切令还”当包括以往逾限不归的逃户的逃田在内。这可能只是一时的放宽政策。
总之,尽管存在特例,唐朝前期实行允许逃户在一定的年限内保留土地所有权的产权政策,旨在对逃户的归籍复业有所激励。这一产权政策为唐后期、五代乃至宋朝所沿用。
2.政府对逃田的使用权和收益权的处置
无论是逃户在政府规定的期限内回归还是逾期不归,政府都面临着如何处置逃田的使用权和收益权的问题。如果逃户逾期不归,逃田充公,拥有土地所有权的政府对其经营权和收益权可自由处置。若拨充官员职田[12],则经营权和收益权在一定期限内归属官员个人;若出佃收租,则使用权交付租佃人,收益权在官府和租佃人之间分配。兹可不赘。
比较复杂的当属在允许逃户保留土地所有权的期限内的处理政策。即使是在三五年内让逃田荒废,既不利于社会经济,也有损于国家的税收利益,因此唐朝前期中央制定有关产权政策的同时,要求地方政府介入对逃田的使用权和收益权的管理。从现有的资料来看,唐朝前期地方政府对逃田的使用权和收益权的管理形式有两种。
一是官府直接“差户营种”或称“付户助营”,然后根据不同情况分配其收益。敦煌出土文书《长安三年三月十六日括逃使牒并敦煌县牒》写道:“……承前逃户田业,差户出子营种,所收苗子,将充租赋。假有余剩,便入助人。今奉明敕,逃人括还,无问户第高下,给复二年。又今年逃户所有田业,官贷种子,付户助营。逃人若归,苗稼见在,课役俱免,复得田苗。”[13](P342)
据此可知,早在长安三年(703)之前,就有由政府出面,“差户出子营种”逃田的做法,对其收益的分配,首先用于交纳租赋(即逃户的欠税),有余才给营种人。收益权的这种分配,说明国家把赋税收益摆在既出种子又要耕作的营种户的收益之上,这对调动民间营种逃田的生产积极性不太有利。长安三年,朝廷作出政策调整,一是由政府贷给种子,以减轻营种户的生产垫支;二是规定在耕种期间如果逃人归还,苗稼即归其所有,并蠲免赋役。但未提及在这种情况下营种户的生产投入是否能得到补偿。从上引唐朝对卖买逃田而逃人归复应无条件归还原主的敕令看来,我们倾向于推测直至长安年间唐朝处理逃田使用权和收益权的政策取向,仍是将营种户的收益权置于末尾。而营种户之所以愿意冒一定的赔本风险承种逃田,可能是实际上当时逃人自动复业者很少。由此也可知“差户营种”逃田不属于官府出租逃田、营种者交纳地租的租佃形式。
敦煌文书《长安四年二月敦煌县史阎迢帖》是关于把“逃人郭武生田改配马行僧、马行感等营(种)”的文书,陈国灿先生分析说:“文称‘配’,未言‘授’,还是属于‘付户助营’的范畴”,改配“经过县丞同意,并将情状通知‘知营田’官,通知到日,‘准状营种,不得失时’。这就是将逃人田地配人代为营种的一套手续。”[2]
可知若采用“付户营种”方式,地方政府对逃田的生产负有“差户”、“改配”,并且督耕的职责,在收益分配方面则负有抵扣逃户欠税或者当逃户在限期内归回时裁定收益权分配等职责,介入的程度较大。唐长孺先生指出,长安三年的括户是全国统一的检括活动[14],因此上述西州出土文书所揭示政府对逃田产权的处理办法,也是通用于全国的。
二是由民间自愿租佃逃田,官府着重于收益权的管理。上引敦煌文书抄录的睿宗唐隆元年敕文规定,逃田“任依乡原价,租充课役,有剩官收。若逃人三年内归者,还其剩物”。同年睿宗《诫励风俗敕》敕:“诸州百姓,多有逃亡……其地在,依乡原例纳州县仓,不得令租地人代出租课。”[8]即在逃户还乡之前,允许他人依照当地的经济习俗租种逃田并交纳田租;田租须先用于抵充逃户的欠税,若还有剩余则交官府代管,逃户若在三年之内还乡,可向官府领取这部分剩余。同时强调租地人只交田租一项,官府不得令他们既交田租又代纳逃户的欠税。显然,租种逃田的收益权要在租种人、官府和逃户三者之间实行这种分配,地方政府也必须介入逃田的租种管理,不过这种管理的重点在于分配收益权,即负责从租种者所交田租中抵扣逃户欠税以及替逃户保管部分生产物收益。
3.中央和地方政府对于民间自行处置逃田产权的不同态度
唐朝前期常见民间私自处理逃田产权的现象。民间私自处理逃田产权的流行方式有两种。一种是私自买卖,对此唐中央时有禁令。如睿宗唐隆元年七月十九日敕:“……逃人田宅,因被贼卖,宜令州县招携复业。其逃人田宅,不得辄容卖买。”[8]玄宗开元十二年(724)五月诏称:“百姓逃散,良有所由……且违亲越乡,盖非获已。暂因规避,旋被兼并,既冒刑网,复损产业……”[15]玄宗天宝十四载(755)八月制:“天下诸郡逃户有田宅产业,妄被人破除,并缘欠负税庸,先以亲邻买卖,及其归复,无所依投……应有复业者,宜并却还。纵已代出租税,亦不在征赔之限。”[9]另一种是将逃田出租。敦煌文书《垂拱三年西州高昌县杨大智租田契》[16](P406)有以下内容:
1.垂拱三年九月六日,宁戎乡杨大智交[ ]
2.小麦肆斛,于前里正史玄政边租取逃
1.走卫士和隆子新兴张寺潢口分田贰亩
2.半。其租价用充隆子兄弟二人庸叠直,
3.如到种田之时,不得田佃者,所取租价麦
4.壹罚贰入杨,有人吝护者仰史玄应当。
5.两和立契,画指为记。
6.租佃人 杨
7. 田主史玄政
8. 知见人 侯典仓
“前里正”史玄政为何以“田主”的名义出租逃田给杨某?杨际平先生认为:“史玄政自署为‘田主’,并不表明他具有该段田土的所有权,而是表示他代表着出租田土的一方。杨大智预付的租价(小麦四斛),史玄政用以充当和隆子兄弟的庸直……和隆子兄弟的田土由前里正史玄政主持出租,表明和隆子兄弟的逃亡,发生在史玄政任上。史玄政不再担任里正后,和隆子兄弟的租庸调仍由‘责任者’史玄政负责祗承。”[1]那么,史玄政所为是代表官府的招佃行为还是民间的私自处置?契约写有“如到种田之时,不得田佃者,所取租价麦壹罚贰入杨”一款,据此我推测,史玄政出租逃田当属于民间私自租赁逃田使用权的事例。
唐朝前期民间私自买卖逃田的现象为何屡禁不止?这与地方官员持放任态度相关。而地方官员之所以持放任态度,又与他们实行赋税“摊逃”直接相关。所谓摊逃,是指地方官员把逃户的欠税额,摊征于其亲邻身上。这种现象由来已久,所以玄宗天宝八载(749)正月敕称:“牧宰等,授任亲民,职在安辑,稍有逃逸,耻言减耗,籍账之间,虚存户口,调赋之际,旁及亲邻。此弊因循,其事自久。……其承前所有虚挂丁户应赋租庸课税,令近亲、邻保代输者,宜一切并停,应令除削。各委本道采访使,与外州相知,审细检覆,申牒所由处分。其有逃还复业者,务令优恤,使得安存,纵先为代输租庸,不在酬还之限。”[9]
对于赋税摊逃之弊的长期存在,论者一般归咎于吏治腐败。我则曾指出:这“既与预算管理制度有关,更与官吏考课制度以及人口管理制度直接相关”。[17](P51-52)后来,我又试图从纳税手续方面寻找原因,指出唐朝前期官府尚未实行发给纳税人完税凭证的制度,故受摊逃者无法据以拒绝。[18]现在我认为还应该从民间私自处理逃田产权这一角度加以补充解释。上引唐玄宗的诏令已经明白指出,地方官员“摊逃”的对象是逃户的“近亲”与“邻保”,唐朝官方文献有时统称为“亲邻”。而比较能够方便地私自处理逃户遗留的田宅的,无疑主要就是这些亲邻。这些亲邻既然已经变卖或者占用(包括出租)了逃户的田宅,获得一定的经济利益,而逃户未被削除的租庸调之类的赋税,地方官员强迫他们代纳,从权利与义务的关系来看,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也正因为如此,地方官员“摊逃”赋税与逃户的亲邻私自处置逃田产权,二者互为因果,形成恶性循环,租庸调的“摊逃”对象甚至包括无田产的逃户的邻保,(注:敦煌文书抄录的唐隆元年敕文有“其无田宅,逃经三年以上不还者,不得更令邻保代出租课”之句,说明即使逃户全无田地,邻保也要承担“摊逃”。参见前揭杨际平:《隋唐均田、租庸调制下的逃户问题》,《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4期。)这对于招引逃户还乡以及防止更多的户口逃亡是不利的,因此我们看到唐朝官方禁令常把这两者联系在一起。
概括上述,唐朝前期中央在制定和调整逃田产权制度时,其激励机制的预期重点在于保障两方面的利益:一方面是逃户的利益,即通过限期保护逃户土地所有权与部分收益权,以招诱他们还乡。另一方面是国家赋役利益,即或者让逃户限期归还,重新承担以户籍资料为基础的租庸调、户税、地税、徭役等,或者通过出让逃田的使用权,让营种者填补逃户的欠税。至于如何激励他人营种逃田的积极性,保护佃种者的经济利益,从而恢复和发展农业经济等考虑,在唐朝前期的逃田产权政策中被置于次要地位。这种逃田产权激励机制的设定,当与唐朝前期的税制以人头税性质的租庸调制为主有关。
与此同时,许多地方官员出于赋税征调职责、政绩考课等考虑,置中央的逃田产权政策于不顾,在默认逃户亲邻私自出卖或出佃逃田的非法行为的同时,进行赋税摊逃,以谋求自身的政绩。赋税摊逃从赋税制度上看是非法的,却可从民间对逃田产权的私自处理得到某种合理的经济解释。
二、唐后期逃田产权制度的演变
唐朝后期中央的逃田产权制度有所调整,引起调整的主要原因有四个方面。
第一,逃户这一社会经济问题日益严重。安史之乱爆发后,大量户口逃离本籍。肃宗宝应元年(762)四月敕称:“近日已来,百姓逃散,至於户口,十不半存。”[9]户口逃亡原因除了战乱的影响之外,主要还如肃宗至德二载(757)二月敕所说:“诸州百姓,多有流亡,或官吏侵渔,或盗贼驱逼,或赋敛不一,或征发过多……”[9]及至建中元年(780),政府为实行两税法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户口检括,结果检括得留在本籍的“主户”仅180余万户,而客居他乡的“客户”高达130余万户[19],主客户比为1.4:1。尽管“客户”包括部分有田产的“寄住户”、“寄庄户”,但主要还是抛弃家园外逃的农民。如此之多的客户必然带来大量的逃田产权处理问题。唐朝中央在考虑如何招绥逃户复业时,仍然有意识地要利用产权政策的激励机制,如武宗会昌元年(841)正月制称:“安土重迁,黎民之性,苟非艰窘,岂至逃亡?将欲招绥,必在赀产。”[9]
第二,田赋制度发生重大改变。众所周知,建中元年实施的两税法以“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20]为制税原则,而区分贫富的主要资产则是田地,所以唐人称:“据地出税,天下皆同。”[21]从国家税收利益考虑,调整逃田产权政策的关注点也要发生变化。
第三,中央财政困难。由于方镇割据、战争频繁等原因,唐后期中央财政经常处于窘境。中央既想减少逃户增多所带来的欠税,又要禁止地方官员的摊逃,颇有左右为难之感。如懿宗咸通十三年(872)六月,中书门下奏:“今月十七日,延英面奉圣旨,令诫约天下州府,应有逃亡户口,其赋税差科,不得摊配现在人户上者。伏以诸道州府,或兵戈之后,灾诊之余,户口逃亡,田畴荒废,天不敷佑,人多艰危。乡闾屡困于征徭,币藏因兹而耗竭,遂使从来经费色额,太半空系簿书。缓征敛则缺于供须,促期限则迫于贫苦。言念凋弊,劳乃忧勤,不降明文,孰知圣念。其逃亡户口赋税及杂差科等,须有承佃户人,方可依前应役。如将缺税课额,摊于现在人户,则转成逋债,重困黎元。”[22]可见他们认为若能通过鼓励经营逃田而填补逃户的欠税,方为纾缓财政困境和社会矛盾的两全之策。
第四,两税三分制的缺陷所致。建中元年唐朝建立诸州两税的“上供、送使、留州”三分制,采用定额管理,却没有规定逃户的欠税额从哪一级财政收入中抵扣。这种制度缺陷一方面使中央财政不肯承担税收损失,地方官员不得不继续实行摊逃,激化了社会矛盾。如陆贽所指出的:“……田里荒芜,户口减耗,牧守苟避于殿责,罕尽申闻;所司姑务于取求,莫肯矜恤,遂于逃死阙乏税额,累加见在疲氓。”[23]另一方面也使中央与地方政府不得不较为关注如何从处理逃田的使用权和收益权中弥补财政收入。
在上述背景之下,唐朝后期逃田产权政策发生了两方面的重大演变。
第一,国家财政的收益权逐渐占据首位,从而也加强了地方政府的招佃逃田并收租抵税等管理职责。如肃宗乾元三年(760)四月敕:“逃户租庸,据账征纳,或货卖田宅,或摊出邻人,展转诛求,为弊亦甚,自今已后,应有逃户田宅,并须官为租赁,取其价值,以充课税,逃人归复,宜并却还,所由亦不得称负欠租赋,别有征索。”[9]敕文要求地方政府要负责把所有逃田出租收取田租以代纳逃户欠税。又如武宗会昌元年(841)正月制:“诸道频遭灭沴,州县不为申奏,百姓输纳不办,多有逃亡。长吏惧在官之时破失人户,或恐务免正税,减克料钱,只于见在户中分外摊配,亦有破除逃户桑地,以充税钱。逃户产业已无,归还不得;见在户每年加配,流亡转多。自今已后,应州县开成五年已前,观察使、刺史差强明官就村乡,指实检会桑田屋宇等,仍勒令长加检校,租佃与人,勿令荒废。据所得与纳户内征税,有余即官为收贮,待归还给付。如欠少,即与收贮,至归还日,不须征理。”[9]唐朝法律规定官府对私人财产进行“检校”,只适用于主人犯法财产没官,或者户绝清点财产两种场合。会昌元年将逃户的田宅列入官府“检校”范围,足见地方政府对逃田产权的管理职责在加大。
第二,逐渐削弱对逃户的土地所有权的保护,同时加强对耕种逃田者的权益保障。如代宗广德二年(763)四月敕:“如有浮客情愿编附,请射逃人物业者,便准式据丁口给授。如二年以上,种植家业成者,虽本主到,不在却还限,任别给授。”[9]这是唐朝首次规定经营逃田者若种植有成二年之后即可将使用权转变为所有权,而逃户一旦回归,官府另给田地安置。这无疑削弱了逃户原有的土地所有权。代宗大历元年(766)制:“如有百姓先货卖田宅尽者,宜委本州县取逃死户田宅,量丁口充给。”[9]这一政策允许把逃田(应该是指逾限不归的逃户的逃田)另行分配,显然也是对这些逃户的所有权的一种忽略。穆宗长庆元年(821)正月敕文:“应诸道管内百姓或因水旱兵荒,流离死绝,见在桑产如无近亲承佃,委本道观察使于官健中取无庄田有人丁者,据多少给付,便与公验,任充永业。”[9]这是规定在逃田没有近亲承佃的情况下,地方政府有权把逃田的所有权和经营权都划拨给无地的士兵家庭。武宗会昌元年(841)正月制:“自今以后,二年不归复者,即仰县司,召人给付承佃,仍给公验,任为永业。”[9]会昌五年(845)朝廷进一步缩短允许逃户保持逃田所有权的时限,规定:“从今以后,应诸州县逃户,经二百日不归复者,其桑产居业,便招收承佃户输纳,其逃户纵归复者,不在论理之限。”[24]这种大大缩短逃户保留产权期限的政策,旨在激励他人经营逃田并向国家纳税的积极性。换言之,在调整逃田产权制度时,国家财政的收益权以及实际耕种逃田者的权益,被置于逃户的原有产权之上。
稍后,宣宗复将允许逃户保留土地所有权的期限延长到五年,并曾对地方基层政府保护逃户原有田宅的职责有所强调。此即大中二年(848)正月制:“所在逃户,见在桑田屋宇等,多是暂时东西,便被邻人与所由等计会,虽云代纳税钱,悉将斫伐毁折。及愿归复,多已荡尽,因致荒废,遂成闲田。从今已后,如有此色,勒乡村老人与所由并邻近等同检勘分明,分析作状,送县入案。任邻人及无田产人,且为佃事,与纳税粮。如五年内不来复业者,便任佃人为主,逃户不在论理之限。其屋宇桑田树木等权佃人,逃户未归五年内,不得辄有毁除斫伐。如有违犯者,据限日量情以科责,并科所由等不检校之罪。”[9]这一关于逃户的土地所有权可保有五年的规定,一直沿用到唐末,如懿宗咸通十一年(870)七月十九日敕曰:“诸道州府百姓承佃逃亡田地,如已经五年,须准承前赦文,便为佃主,不在伦理之限,仍令所司准此处分。”[9]总的来看,比起唐前期,唐后期逃田“权佃人”的权益显然更受到政府的重视。(注:窦仪等撰《宋刑统》卷十三《占盗侵夺公私田》引唐代宗宝应元年(762)四月十七日敕节文:“诸百姓竞田如已种者,并据见佃为主,待收了断割。”也是重视保护经营权的法律表现。制定保护逃田“权佃人”利益的规定当与此有关。)
必须指出,唐后期同样存在着地方官员将逃户的欠税摊征于其亲邻的“摊逃”之弊。中央屡禁而不止的原因也如同唐前期一样,与逃户的田地屋宇被其亲邻私自占用或出卖是互为因果的。反过来看,当时逃户的亲邻之所以要占用或出卖逃户财产,其理由也是替逃户交纳了两税,如上引大中二年(848)正月制所说的:“所在逃户,见在桑田屋宇等,多是暂时东西,便被邻人与所由等计会,虽云代纳税钱,悉将斫伐毁折。”对民间私自处理逃户的田宅产权并代纳赋税的行为,有的朝臣甚至建议可以作为政府处理逃户欠税的一种办法,如宪宗元和年间,李渤上疏曰:“乞降诏书,绝摊逃之弊。其逃亡户以其家产钱数为定,征有所欠,乞降特恩免之。”[25]他所提出处理逃户欠税的办法,是由官府将逃户遗弃的家产变卖抵充,不足部分让朝廷下令免除。尽管他的建议可能未被采纳,却可说明民间私自处理逃田产权的行为仍然是唐朝后期的一种经济习俗。这种经济习俗之所以长期存在,从地方政府管理职责的角度来看,还因为逃户不断地大量涌现,使得地方官员实际上无力履行中央赋予的检校与招佃逃田、收租抵税等一系列职责,只得采取听任亲邻私自处置逃田、同时向他们摊逃赋税的简单方式,以应付自己的财政职责。
三、五代逃田产权制度的沿革
五代时期逃户问题依然相当严重。而官员考课制度对刺史、县令“招复户口,能增加赋税”[26]的政绩多有奖擢。如后晋天福八年(943)三月十八日敕:“诸道州府令佐,在任招携户口,比初到任交领数目外,如出得百户以上,量添得租税者,县令加一阶,主簿减一选……出四百户至五百户以上,及添得租税者,县令加朝散大夫阶,超转官资,罢任后许非时参选,仍录名送中书……”[27]因此,无论从财政收益或是从官吏考绩看,五代王朝不可能对逃户放任自流。
不过,五代官方似未见像唐朝那样进行过大规模的检括逃户活动,而是寄希望于调整产权政策以收招诱逃户自动归业之效。这表现在两方面:一是五代进一步规定给逃户归业者予一定年限的赋役减免,这实际上就是许诺增加逃户对逃田的收益权。如后唐天成三年(928)十二月十日,明宗采纳李廷范的建议:“每逃户归业后,委州司各与公验,二年内放免两税差科。”[28]后晋天福八年三月十八日敕:“自灾沴以来,户口流散,切在抚安……其归业户,天福五年已前逃移者,放一年夏秋租税,并二年杂差遣……”[27]这一产权政策为宋朝所沿用。二是继续许诺对逃户的土地所有权有所保护。如后唐长兴三年(932)七月二十七日敕规定:“应诸处凡有今年为经水涝逃户,在园屋舍桑枣一物以上,并可指挥州县散下乡村,委逐村节级、邻保人分明文簿,各管现在,不得辄令毁拆房舍,斩伐树木及散失、动使什物等。俟本户归业日,却依元数,责令交付讫,具无欠少罪结状申本州县。如元数内称有物欠少,许归业户陈状诉论,所犯节级并乡邻保人等并科违敕之罪,仍勒倍偿。或至来年春入务后有逃户未归者,其桑土即许邻保人请佃,供输租税。种后本主归来,亦准上指挥,至秋收后还之。”[28]敕文要求官府责令乡村“节级”(乡官)和逃户的邻保负责清点当年因水灾而逃亡之家的所有财产,造册后加以保管,不得损坏、散失,甚至不许动用杂物,待本户归业时如数交还;如数交还时必须经过官府认证,否则要负法律责任,并加倍赔偿。
这一规定虽然只是针对当年因水灾而逃亡之家的临时性的产权保护政策,在五代逃田产权制度变迁中不具有普遍意义,但却对宋朝处理因“灾伤”而逃亡的逃户的产权有借鉴作用。
五代逃田产权制度的重大调整,更重要的是加强了对租佃逃田者的权益保护,这同时也是要为国家财政的收益提供更可靠的经济保障。在这方面具有承上启下意义的,是后周显德二年(955)五月二十五日敕文。该敕关于逃田产权处理的规定为:“应自前及今后有逃户庄田,许人请射承佃,供纳租税。如三周年后本户归来业者,其桑土不论荒熟并庄田(三分)交还一分。应已上承佃户如是自出力别盖造到屋舍,及栽种到树木、园圃,并不在交还之限。如五周年外归业者,庄田除本户坟茔外,不在交付。如有荒废桑土,承佃户自来无力佃莳,只仰交割与归业人户佃莳。”(注:王溥:《五代会要》卷二五《逃户》。按:括号中的“三分”系据同敕的下一款文增补。)这一规定对逃田的所有权、使用权与经营权的处理作出重大政策调整。它进一步削弱了政府对逃户的土地所有权的保护。逃户在三周年后归业只能取回原有庄田的1/3;五周年后复业者,只能得到本户的坟茔,以及承佃人无力耕种的荒废土地。与此同时,对经营者的权益保护则加强了,不仅规定经营逃田者获得逃田所有权的机会随着他们耕种的年月增多而增加,而且规定他们在三年的经营期间若有自己建造的房屋,新裁的树木,开辟的园圃,都不必交还归业的原主。这一规定有利鼓励经营逃田者加大生产投入,扩大生产规模,以获得较多的经济效益,这也增加了他们代纳逃户欠税的可行性,国家财政收益因此更有保障。
同时,这份敕文还强调国家财政收益权在逃田产权界定中不可或缺的地位,宣布对私自耕种逃田却不向政府纳税者,将得不到政府的产权保护,除非他们立即自首并纳税,规定为:“诸州应有冒佃逃户物业不纳租税者,其本户归业之时,不计年限并许论认。仰本县立差人检勘,交割与本户为主。如本户不来归业,亦许别户请射为主。所有冒佃人户及本县节级重行科断。如冒佃人户自来陈首承认租税者,特与免罪。”[28]敕文同时要求地方政府尽可能地对逃田进行招佃,宣布承佃人可免除赋役一年,以鼓励他们的生产和纳税的积极性。规定为:“显德二年正月二十五日已前,应有逃户抛下庄田自来全段无人承佃,曾经省司指挥开辟租税者,宜令本州县招携人户归业,及许别户请射为主,与免一年差税色役。至第二年以后,据见在桑木及租莳到见苗,诣实供通,输纳租税。”[28]
总括全篇,唐朝至五代,逃田产权制度变迁有如下特点:
第一,为招诱逃户重新回到原籍复业,政府始终实行在一定期限之内保留其土地所有权乃至增加其收益权的政策。但是,逃户问题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绝非政府制定这种产权政策就能有效解决。因此,唐五代政府预期的产权政策的激励机制收效十分有限。这一政策取向便逐渐让位于对经营逃田者的权益保护。
第二,招佃逃田并让佃种人纳税,始终是唐五代政府制定和调整逃田产权制度的基本考虑。随着唐后期、五代财政困难局势的发展,政府希冀从逃田获得税收补偿的意图更加明显地体现在其产权政策之中。
第三,随着人头税性质的租庸调为“据地出税”的两税法所取代,政府对逃田获取财政收益的预期,更多地表现在对逃田经营效益的关注之中,其逃田产权政策逐渐偏向于保护耕种逃田者的权益,包括许诺经一定的期限可将逃田的所有权全部或大部分转交给经营者,以及在分配逃田收益权时增加保护经营者的生产垫支的内容。
第四,逃户的亲邻私自占用或者出卖逃田的产权处置行为,违反了中央政府的逃田产权政策,但地方政府官员出于主客观原因,却加以默许,并以此为借口加剧赋税摊逃。换言之,唐五代的赋税“摊逃”现象之所以屡禁不止,在一定程度上是与当时民间私自处理逃田产权的情况互为因果的。
收稿日期:2004-04-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