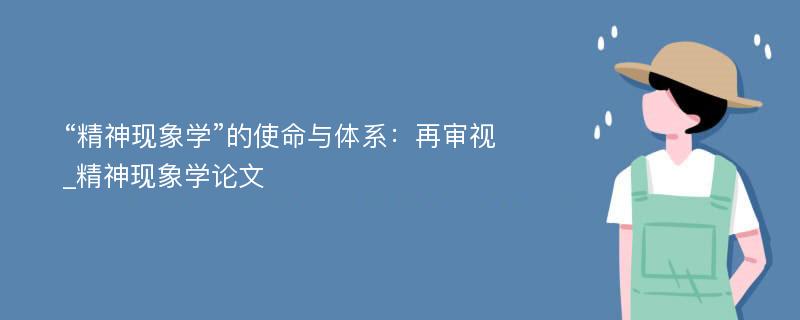
《精神现象学》的使命和体系:一个再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象学论文,使命论文,体系论文,精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精神现象学》(以下简称《现象学》)是黑格尔最杰出也是最艰深晦涩的一部著作,它的艰深晦涩固然就是青年黑格尔的才华在融入学院派传统之前表达的质朴性,但同时也折射出了其体系构制的某种混乱:作为“关于意识的经验的科学”,《现象学》原本只应是整个“科学”体系的作为“导言”的“第一部分”;但是在具体创作过程中,黑格尔不仅分析了意识发展的形式,而且提前阐述了本应在体系自身之精神哲学中才出现的思维发展的内容,即科学本身的某些部分,从而实际成为了“一个自身的整体”。正如不少学者已经看到的那样,黑格尔在《现象学》中提出的体系构想只是过渡性的(注:按照黑格尔此时的设想,《现象学》是“科学体系的第一部分”,在第二部分将论述“逻辑”、“自然”和“历史”,参见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下册273~274页,贺麟、王玖兴译,商务印书馆,1979。《逻辑学》1812年第一版序言又更明确地重申了这个计划,只不过把原先预告的“历史”部分更名为“精神”,参见黑格尔:《逻辑学》,5~6页,杨一之译,商务印书馆,1966。):“《哲学全书》的体系,这个黑格尔最终适当的体系,与《现象学》的体系相比,更强烈地显示了一种相对于较早的体系计划(这里指的是黑格尔的法兰克福体系和耶拿体系(注:法兰克福时期黑格尔计划其哲学体系由三部分组成:(一)逻辑学和形而上学;(二)自然哲学;(三)伦理学。耶拿时期,逻辑学和形而上学叫做“思辩哲学”或“先验唯心论”,而自然哲学和取代伦理学的精神哲学则合称“现实哲学”。)——引者注)的关联。”(注:Martin Heidegger:Hegel's Phenomenology of Spirit.Trans by Parvis Emad and Kenneth Maly.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8,P.8.)
那么,这个过渡性的体系之于黑格尔究竟意义何在呢?如果我们以黑格尔的成熟体系即《哲学全书》来对《现象学》进行发问,那么只能和晚年黑格尔一样得出否定性的评价,因为作为“导言”的《现象学》与《哲学全书》的真实导言相比,既不明晰更不经济:《现象学》第一版奥德塞式地漫游了800多页只是达到了后者不过三数十页就已经达成的结局,同时,后者基本上是在相当于前者“主观精神”(“意识”、“自我意识”和“理性”)的领域内就实现了自己的使命。黑格尔自己的评价从肯定到否定的变迁表明,我们更应当历史主义地在青年黑格尔的所思、所想,而不应是在因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特定论述而为国内学界所熟知的、黑格尔成熟时期的思想情境中来理解《现象学》。我们首先需要加以正确理解的就是《现象学》似乎并不存在的确定使命及其独特的体系构造,它是我们的《现象学》研究能够借以真实展开、然而却被国内学界长期忽视了的解释学基础,因为如果没有这个基础,《现象学》作为所谓“黑格尔哲学的真正诞生地和秘密”就根本无从谈起。
一、青年黑格尔的理论思考:从政治、宗教到哲学
当年轻的黑格尔1788年进入图宾根神学院的时候,在他身上我们一点也没有发现他后来能够成为伟大哲学家的征兆,因为他其时并不爱好哲学,“虽然他在法国爆发革命那一年就开始读康德的著作,但他当时还领会不了批判哲学的革命精神”(注:古留加:《黑格尔传》,12页,刘半九、伯幼译,商务印书馆,1978。)。黑格尔当时最感兴趣的是政治,他“一向对政治有种偏爱”。法国革命搅乱了黑格尔平静的书斋生活,在卢梭著作的影响下,他的政治观念变得相当激进。他不再是符腾堡君主制的幼稚的歌功颂德者,(注:黑格尔在“中学毕业的演讲”中对符腾堡专制暴君所谓重要教育和科学普及的德行进行了歌颂。参见《黑格尔早期著作集》上卷,47-48页,贺麟等译,商务印书馆,1997。)而成了古希腊特别是雅典城邦政制的热烈拥护者,在这个过程中,席勒、歌德和荷尔德林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注:参见考夫曼《黑格尔——一种新解说》,第一章“3.赫尔德林和图宾根大学”、“6.歌德的《伊菲革涅亚》”和“7.席勒的《美育书简》”的相关论述,张翼星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黑格尔和他不少同时代人相信,在古希腊社会里曾经建立过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共同体。社会实践和社会制度如宗教、道德和政治等等都紧密地交织在一起,这样就使社会制度成为纯一的东西。个别公民都能够亲自参加所有一切相互交织在一起的社会活动,因此他能够使自己的个性得到全面和完全的发展,而这种人性的完整性是近代人所得不到的。完整的希腊人格为什么会失落,以及在未来社会它怎样才能重新恢复?尼采所发现的对古希腊理想的浓重乡愁和浪漫主义正是支配青年黑格尔(甚至是他整个一生)理论思考的一个政治力源。(注:参见尼采《权力意志——重估一切价值的尝试》,166~167页,原标注419片段的相关论述,张念东、凌素心译,商务印书馆,1988。)
恩格斯在谈论19世纪三四十年代德国思想界的状况时说:“在当时的理论的德国,有实践意义的首先是两种东西:宗教和政治……但是,政治在当时是个荆棘丛生的领域,所以主要的斗争就转为反宗教的斗争。”(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选》,第4卷,220~221页。)这样的状况在黑格尔生活的时代同样存在。就黑格尔而言,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宗教问题一直在他的精神世界中占有重要地位,他是通过宗教问题的棱镜去观察其他许多世界观方面的问题的。”(注:古留加:《黑格尔的宗教哲学》,《国外黑格尔哲学新论》,37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对于自己关心的政治问题他更是如此。黑格尔写于伯尔尼时期(1793年10月至1796年秋)那些神学论著实际上都充满了明确的政治要求,或者更可以说它们本身就是政治性的:当黑格尔论述主观宗教和客观宗教、民众宗教和基督教及康德的道德主义和基督教的权威主义的对立时,他所意欲表达的不过就是古希腊城邦政制与德国当时的封建专制政体的对立。黑格尔之所以要通过对宗教的论述来表达他的政治意见绝不是因为保守,而是世界观使然:那时的黑格尔持有和法国启蒙主义相似的唯心史观,认为宗教是历史发展中的决定力量,“宗教不仅只是历史性的或者理性化的知识,而乃是一种令我们的心灵感兴趣,并深深影响我们的情和决定感,我们的意志的东西”,(注:《黑格尔早期神学著作》,3页,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88。)宗教是政治的基础。(注:在1795年4月16日致谢林的信中,黑格尔说:“宗教和政治是一丘之貉,宗教所教导的就是专制制度所向往的。”《黑格尔书信百封》,43页,苗力田编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伯尔尼时期黑格尔具体的宗教哲学思想一直处于发展之中,(注:参见赵林《黑格尔的宗教哲学》,第二章第一节的有关论述,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但他的提问方式却是相对固定的,即:他以一种鲜明的主观价值论立场去看待对立的双方,把古典的伦理共同体看做是绝对的善,德国的封建政制看做是绝对的恶;善恶之间处于绝对的不可调和的敌对之中,对立的消除就是古典理想对封建政制的彻底消灭、否定和吞噬。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康德知性哲学的深刻烙痕,不过此时让黑格尔从中受益的并不是《纯粹理性批判》,而是《实践理性批判》:“就像他的许多同时代人一样,他的目的就是运用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中所做的分析于社会历史。康德主义的影响以两种支配性的形式对他发生作用:一方面,黑格尔把社会问题初步认定为道德问题;另一方面,实践即人类自己改造社会现实的问题则持续处于他的思想的中心。”(注:Georg Lukacs:The Young Hegel,Studise in the relations between dialectics and economics.Trans by Rodney Livingstone.Merlin Press,London,1975P7-8.)前者引导黑格尔去深入领会康德哲学的实质,而后者则把黑格尔的注意力吸引到对基督教的历史考察上,使之认识到基督教的兴起和统治是一个具有必然性的历史过程。(注:参见《黑格尔早期神学著作》,240~270页的相关论述。)
如果说伯尔尼时期,哲学还是作为思考方式隐匿在黑格尔内心深处的话,那么,法兰克福时期(1797年1月至1800年底)哲学就浮现到了起码和宗教同等重要的位置上:他染上了一种“犹疑症”,对自己原先的哲学立场产生了巨大的怀疑。这种状况一方面和当时反康德的哲学潮流及谢林的影响有关,(注:因为费希特知识学的出版,学界开始反思和批判康德的道德专制主义,在1795年7月21日致黑格尔的信中,谢林明白表达了对康德的不满(参见《黑格尔通信百封》,46页)。这种情绪对把谢林当作老师看待的黑格尔一定是有影响的。)更重要的是和实践有关:“当理性一旦带着兴趣和它的希冀进入了现象的混乱之中,尽管目标一直是确定的,但还穿不透这团混乱,达不到对整体清晰而详细的了解,就会产生这种(犹疑)情绪”,(注:参见黑格尔1810年5月27日在致温迪希曼的信中的回忆,《黑格尔通信百封》,217页。)——法国大革命尚且不能完全实现自己的理想,康德的道德专制主义又能如何?对法国大革命以及德国政体的再认定,导致法兰克福时期黑格尔对康德道德主义哲学的反思和超越。
正如卢卡奇所看到的那样,黑格尔在伯尔尼时期研究基督教在晚期罗马社会的发展中,曾非常可贵地注意到“基督教社团的数量扩张和它内部社会经济差别的出现是密切相关的,也就是说,在这里,黑格尔的主要历史前提、财富的不均等扮演了一个极为重要的角色”(注:Georg Lukacs:The Young Hegel,P64.)。而在法兰克福,黑格尔则继续这种对社会历史的“唯物主义”研究,通过对英国经济学家斯图亚特《关于政治经济学原理的探究》的解读,“逐步趋向于到近代社会的经济生活中去考察适应于近代世界的那些新的整体性和共同性的发展”(注:普兰特:《黑格尔政治哲学中的经济和社会的整体性》,《国外黑格尔哲学新论》,277页。)。黑格尔在《基督教的精神及其命运》中所使用的“命运”概念,就意味着一种和康德二元论相反对的历史进化理论。同时,在摆脱康德影响的过程中,德国本土的神秘主义也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黑格尔在此时期使用的含混不清和意义不明的术语如“生命”、“爱”就体现了它们的影响。“生命”和“爱”的概念的提出,表明黑格尔日益感受到矛盾存在的客观性和矛盾难以消除的悲剧性。这些不稳定的过渡的概念实际构成了黑格尔把握历史的概念环节和批判康德伦理学的标志。(注:“在黑格尔摆脱康德的影响而实现其思想的‘重大转折’的法兰克福时期,他的思想首先就是以批判康德的伦理学、提出人的自我分裂(自我否定)和这种分裂的重新统一的问题、提出‘生命’和‘爱’的概念为标志的”。参见邓晓芒《思辨的张力——黑格尔辩证法新探》,60页,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一般说来,黑格尔在法兰克福时期所取得的哲学成果主要表现为如下两点:初步克服康德知性哲学的二元论,形成对立统一的辩证法;厘定了“绝对精神及其在世界发展过程中的显示”这一黑格尔学说的基本观念和基本主题。(注:费舍尔:《青年黑格尔的哲学思想》,61页,张世英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82。)——和刚刚开头的哲学兴趣相比,黑格尔始终关心的宗教—政治问题倒可以说基本解决了;他原先激烈反对的基督教现在处于自然宗教—犹太教—基督教这个世界宗教发展链条的顶端,它意味着世界和上帝的和解;同样,立宪君主制则代替人民主权的议会制成为后来所谓历史发展的顶点。
1801年1月,怀着绝对精神原型的黑格尔前往耶拿。黑格尔之所以去耶拿,不仅因为那是当时德国文化最活跃的地方,并且他的朋友兼“老师”谢林在那里,更重要的是,他已经不再满足于做家庭教师的现状,觉得自己具备了从事哲学研究的实力和构建自己的科学“体系”的理论冲动。(注:在1800年11月2日致谢林的信中,黑格尔表明了自己对现状的看法和对前途的期望:“我不能满足于人类低级需要的科学教育,我必须攀登科学的高峰。我必须把青年时代的理想转变为反思的形式,也就是化为一个体系。”《黑格尔通信百封》,58页。)
黑格尔一到耶拿就发表了自己第一部哲学著作《费希特和谢林哲学体系的差别》(1801年7月),在文中,他准确分析了费希特的知识学和谢林同一哲学之间的分歧,从而为两者无休止的论争做出了有利于谢林的评判。但如果认为黑格尔的立场就是谢林的立场,那就错了。事实上,黑格尔不仅反对费希特的“自我”这个“主观的主客体同一”,而且也不满意谢林的“绝对”那个“客观的主客体同一”,因为它们都是片面的,应当把它们综合或统一起来:“(主观的东西的)‘观念的秩序和联系’和(客观的东西的)‘事物的联系和秩序是一样的’。一切都只存在于一个总体之中;客观的总体和主观的总体,自然的体系和理智的体系是同一个体系;主观的规定性符合同样的客观规定性。”(注:黑格尔:《费希特和谢林哲学体系的差别》,76页,宋祖良、程志民译,商务印书馆,1994。)那个能够包容一切的总体就是黑格尔自己的绝对精神:费希特的“自我”只是缺乏客观性的主体,而谢林的“绝对同一”只是缺乏能动性的实体,绝对精神则是主体—实体,或者实体—主体。黑格尔的这篇论文标志着德国唯心主义历史中的一个转折,(注:参见克洛纳《从康德到黑格尔》,《新黑格尔主义论著选辑》上卷,570页,张世英主编,商务印书馆,1997。)它不仅直接指向黑格尔未来的哲学,(注:参见费舍尔《青年黑格尔的哲学思想》,89页。)而且还为我们具体理解黑格尔耶拿时期的研究工作提供了一条线索。黑格尔自觉地认识到,费希特哲学和谢林哲学是康德之后哲学发展的两个必然环节,两者实际上都没有超越康德主义的界限,他们“每一个都把自己和康德的不同方面相联系,《实践理性批判》为费希特提供了全部体系的发展模型,而谢林则以对《判断力批判》中的客观唯心主义精神的再解释开始其思想历程”,(注:Georg Lukacs:The Young Hegel,P245.)因此,当黑格尔使自己同费希特和谢林对立起来的时候,他最终与之面对的则是康德:对康德以及以后哲学的批判性分析构成了黑格尔耶拿时期公开发表之文献的主题。如果我们再把黑格尔公开发表之文献的批判性,同其未公开发表之耶拿“思辨哲学”、“现实哲学”手稿的建设性相比较,就不难感受到:与建构体系的激情相比,此时黑格尔首要关注的是如何使自己的绝对哲学同康德以降的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发展史相关联。这样,黑格尔从1805年起开始考虑撰写《现象学》这个整个体系的“导言”,其用意就很明白了。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黑格尔此时想要面对的绝不仅仅是康德的认识论,而是他的认识论所体现的文化意向及其政治倾向,因此,当黑格尔准备进军哲学的时候,他的新哲学就不是像康德哲学那样仅仅具有走向政治的可能性,而毋宁说就是纳政治、文化于己身之中的。
二、《现象学》的使命:文化的和认识论的
在现时代,仅仅把《现象学》视为一部“天书”而不对它的主题、观念或者说使命进行追问是很不恰当的,(注:参见肖锟焘《精神世界掠影》,江苏人民出版社,1987。)因为如果不对《现象学》贯穿全书的使命进行正确的厘定,那么,一切对它的肯定性研究其结局都将是颠覆性的:它们将证明黑格尔思维的混乱及体系构制的无计划性。这种危机主要产生于《现象学》的序言和导言在论说口径上的不同一。
与序言是在《现象学》全书完成之后才写作的不同,导言是写在全书之前的,它按照顺序讨论了三层意思:(1)康德批判哲学的实质是对真理的恐惧和对错误的恐惧;(2)现象学走的是一条怀疑和绝望之路;(3)现象学是没有先决条件的批判学说,导言的结论是:从日常意识出发,通过对“意识的经验”的考察,意识将能够达到科学的终点,在这一点上,“现象即是本质;因而恰恰在这个地点上,对意识的陈述就等于是真正的精神科学;而最后,当意识把握了它自己的这个本质时,它自身就将标示绝对知识的本性”。(注: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62页,贺麟、王玖兴译,商务印书馆,1979。)从导言中可否得出,《现象学》作为“意识自身向科学发展的一篇详细的形成史”,和序言中所规定的,《现象学》和“意识形态学”是同一的呢?有人赞同,但也有人反对(注:赞同者国内以贺麟先生为代表,参见《精神现象学》上卷《译者导言》,20~22页;反对者以Haering和Hoffmeister为代表,具体可参见Merold Westphal:History and Truth in Hegel's Phenomenology,Humanities Press,1982,P36-37 and P54,notes 38.)。反对者正确地看到,导言主要针对康德及其后继者的知性哲学,和后来《哲学全书》的导言一样,给《现象学》确定了一个认识论主题,那么,按照这种设计,《现象学》将在“理性”的某处结束自己并和《逻辑学》对接,因为到了此时,意识已经足以证明自己和自在之物的同一性了;这样,《现象学》剩下的部分就是多余的了,它们的存在说明,黑格尔在写作之前并没有一个全盘计划,《现象学》不过是一件百衲衣。
鉴于这种可能存在的解释危机,国内一些研究者对于《现象学》的整体使命问题给予了深切关注,但不论是把解释的基础归结为自由意识的发展,(注:参见肖华《自由意识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还是人性或人类关系的历史演变,(注:参见王树人《历史的哲学反思:关于〈精神现象学〉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都不能给全书的所有内容进行通贯性的合理解读。在一定程度上,正确地说明导言和序言即意识发展史或形成史和意识形态学的关系,就构成了我们解决危机的关键。为此,我们主张在篇幅上比导言大四倍的序言的背景上去理解前者所提出的认识论主题。
放在全书最前面的序言是黑格尔最后才写成的,(注:黑格尔于1806年10月8日、10日分两次寄出了手稿的大部分,并在10月13日耶拿战役前夜写完现象学最后几页,11月下旬至12月底,黑格尔在出版商那里料理出版事宜,然后,他于1807年元月寄出了《序言》,参见费舍尔《青年黑格尔的哲学思想》,70~80页,古留加《黑格尔传》,46~48页。)初读《现象学》的人如果希望它能够为理解正文提供一些启示或指导,那必定要失望。因为,我们需要整个《现象学》来理解序言,而不是相反,在这里,黑格尔像在此前写的其他著作里所表现出来的一样,并不是很清晰地表达了自己对《现象学》使命的规定。与导言只是在结尾才怯生生地标榜《现象学》作为“达到科学的道路本身已经就是科学了”不同,(注:《精神现象学》上卷,62页。)序言一开头就申明自己是“当代的科学”,而自己的使命或目的即在于“促使哲学接近于科学的形式”。(注:《精神现象学》上卷,3页。)那么,哲学为什么只是到了黑格尔时才升高为科学体系,换种方式提问就是,前科学体系的那些哲学即从康德到谢林的哲学其性质又何在呢?在“一、当代的科学任务”之“2.当代的文化”中,黑格尔对此做了某种界说。
对于直接导源于康德《纯粹理性批判》二元论的后康德哲学,即认为“真理只存在于有时称之为直观有时称之为关于绝对、宗教、存在(不是居于神圣的爱的中心的存在,而就是这爱的中心自身的存在)的直接知识的那种东西中,或者甚至于说真理就是作为直观或直接知识这样的东西而存在着的”学说,黑格尔提出要在“自觉的精神当前所处的发展阶段(实际就是黑格尔自己的哲学)来予以考察”。(注:《精神现象学》上卷,4页。)这样就发现,“自觉的精神已经超出了它通常在思想要素里所过的那种实体性生活,超出了它的信仰的这种直接性,超出了它因在意识上确信本质与本质的内在和外在普遍呈现已经得到了和解而产生的那种满足和安全。自觉的精神不仅超出了实质的生活进入另一极端:无实质的自身反映,而且也超出了这种无实质的自身反映。它不仅仅丧失了它的本质性的生活而已,它并且意识到了它的这种损失和它的内容的有限性。由于它拒绝这些空壳,由于它承认并抱怨它的恶劣处境,自觉的精神现在不是那么着重地要求从哲学那里得到关于它自己是什么的知识,而主要是要求再度通过哲学把存在所已丧失了的实体性和充实性恢复起来。”(注:《精神现象学》上卷,4~5页。)显然,想在哲学史的真实发展中理解黑格尔这里所提之问题并解答,几乎是不可能的。哲学在此只能是一种象征,接下来的论述证实了这种猜测。
黑格尔接着就在卢梭异化史观的意义上对人类精神生活史进行了一种简短的象征性的描述:“从前有一个时期,人们的上天是充满了思想和图景的无穷财富的。在那个时候,一切存在着的东西的意义都在于光线,光线把万物和上天联结起来;在光线里,人们的目光并不停滞此岸的现实存在里,而是越出它之外,瞥向神圣的东西,瞥向一个,如果我们可以这样说的话,彼岸的现实存在。那时候精神的目光必须以强制力量才能指向世俗的东西而停留此尘世;费了很长时间才把上天独具的那种光明清澈引进来照亮尘世之见的昏暗混乱,费了很长时间才使人相信被称之为经验的那种对现世事物的注意研究是有益和有效的。——而现在的当务之急却似乎恰恰相反,人的目光是过于执著于世俗事物了,以至于必须花费同样大的气力来使它高举于尘世之上。人的精神已显示出它的极端贫乏,就如同沙漠旅行者渴望获得一口饮水那样在急切盼望能对一般的神圣事物获得一点点感受。”(注:《精神现象学》上卷,5页。)以青年黑格尔思想的发展为棱镜,我们就不难理解黑格尔在这里的用意,可以说,在这里,他以一种新的方式重复了自己之前所思考的所有问题:古希腊完整人格及其丧失,人与神的和谐关系及其丧失,一句话,是人的本质生活的丧失。康德及其以后哲学的意义即在于它们理论地体现了现实生活的这种分裂,因为对它们而言,本体、自在之物、上帝是在我们之外的和我们分离的。
这样,问题就非常清楚了,“《现象学》不仅仅把自己同批判哲学相联系而且是将自己同当代的历史文化危机相联系的”,(注:Merold Westphal:History and Truth in Hegel's Phenomenology,P28.)对于《现象学》来说,导言中所提到的认识论主题仅仅是最初步的,它只是为黑格尔表述自己对人类历史及其命运的新哲学的展开提供了一个楔子,它直接指向一个非常雄心勃勃的文化即政治—宗教使命:解决时代的文化危机,恢复人的本质生活的完整性。
三、“苦恼意识”与《现象学》的体系展开
实现这个雄心勃勃的使命的道路不止一条,在《哲学全书》中,绝对精神奥德塞式的漫游所达成的正是对家的回复和对分裂与漂流的扬弃。这是在“真理之路”上对使命的肯定式完成。按照这个思路,作为体系的导引,《现象学》只需要把日常意识引导到绝对知识面前,那使命将会在“真理之路”的开展中自动得到实现。但黑格尔没有这么做,他似乎认为在日常意识的怀疑之路和绝望之路上,这个宏大的使命就有实现的必要和可能,《现象学》的体系构制体现了他的意图。
从形式上看,《现象学》体系最显著的缺陷就是它的重复:不仅重复了《精神哲学》的内容,而且在自身中许多内容总是多次出现,如苦恼意识就分别在“自我意识的自由;斯多葛主义、怀疑主义和苦恼的意识”、“信仰与纯粹识见”和“天启宗教概念的前提”中三次出现。如果我们以此为中心向《现象学》插进一根轴,那么,《现象学》就会变成一个具有相同轴心的三个平行平面的复合体:(一)主观精神(“意识”、“自我意识”、“理性”);(二)客观精神(“精神”);(三)绝对精神(“宗教”、“绝对知识”),同样,我们还可以用“个人意识”、“社会意识”和“绝对意识”来换称它们。这个轴心正是我们理解《现象学》这个独特体系构造的一个切入点。
在《现象学》中,苦恼意识的历史原型是罗马帝国末期的一些政治行动主义者。面对奴隶制崩溃的现实,他们不像斯多葛主义者和怀疑主义者那样退居灵魂深处,而是企图有所作为;但由于他们的知性思维方式“不过是无形象的钟声的沉响或一种热熏熏的香烟的缭绕,换言之,只不过是一种音乐式的思想”,(注:《精神现象学》上卷,144~145页。)因此,对于本质,他们不能把握。这样他们就不能把握命运,总感到自身处于“痛苦的分裂状态之中”,而蜕变为政治的非行政主义者。对于作为自我意识的苦恼意识,黑格尔的态度和青年黑格尔派的态度是不同的:他希望苦恼意识有所行动,但反对自我意识的主观任意,而把行动的自由狭隘地归结为对客观必然性的认识上;青年黑格尔派则赋予自我意识以客观政治行动的权利。如果说青年黑格尔派用古典自我意识哲学论证了处于上升阶段的资产阶级的政治行动的权力,那么,青年黑格尔的苦恼意识则为处于封建压制和对绝对自由的恐惧中的软弱的德国资产阶级展现了历史发展的光明性。
雅各宾专政之后的德国资产阶级对革命的心态是矛盾的,他们固然承认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的历史潮流所向:“这样,精神就作为绝对自由而呈现出来了;它现在是这样一种具有自知之明的自我意识,它知道它对它自己的确定性乃是实在世界以及超感官世界的一切精神领域的本质”,(注: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下卷,115页。)“对它而言,世界纯然是它的意志,而它的意志就是普遍的意志。更确切地说,普遍的意志并不是由默自表示或由代表表示出来的赞同所表达的那种关于意志的空洞思想,而是实在的普遍意志,换句话说,是一切个别人的意志本身。”(注: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下卷,115~116页。)但是,革命所必然伴随的恐怖却也令他们胆战心惊:“普遍的自由,既不能产生任何肯定性事业,也不能做出任何肯定性行动;它所能做的只是否定性行动;它只是制造毁灭的狂暴”;(注: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下卷,118~119页。)“普遍的自由所能做的唯一事业和行动就是死亡,而且是一种没有任何内涵、没有任何实质的死亡,……它……比劈开一棵菜头和吞下一口凉水并没有任何更多的意义”(注: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下卷,119页。)。封建主义制度无疑不利于发家致富,可法国式的前途也不见得美妙,普鲁士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因此而变得苦恼和退缩。因此,黑格尔觉得自己在阐述真理之前,完全有必要使苦恼的人们摆脱苦恼,这就要对导致苦恼的虚妄的思想根源进行揭白,即:通过对产生苦恼意识的错误思想根源的剖析,弥合知识和真实性之间的分裂,把苦恼意识引向绝对知识。因而,《现象学》的道路必然是曲折重复的,因为它只有延伸到苦恼意识的从认识论到历史观和世界观的每一个层面,才能使“虚妄的东西也不再是作为虚妄的东西而成为真理的一个环节”(注:《精神现象学》上卷,26页。)。
《现象学》这条怀疑之路不是一个人的独白而是两个人的对话:一方是黑格尔,另一方是苦恼意识。对话由表及里地从作为苦恼意识的认识论基础的知性哲学开始,逐步深入到它的历史观和世界观,最终在绝对知识的酒杯中让不得宁静的苦恼意识得到了宁静。需要说明的是,《现象学》作为“科学,它只是“达到科学的道路”意识上的科学,因此和真正的科学的展开即后来的《哲学全书》不同,它始终探讨的都是作为主体的人的意识:起先是个人意识、后来是社会意识、最终是绝对意识,它们不具备本体论意义上的客观性。所以,我们不能因为某种形式的相似性,而对《现象学》的一些内容做出本体论的解读。
(1)主观精神——个人意识。从苦恼意识自己所确定的起点即“感性确定性”出发,黑格尔和苦恼意识经过“知觉”、“力和知性”的一系列晤谈,最终使苦恼意识认识到自己所想要认识的物自体是虚假的,自己所认识的不是它物而就是自我意识本身,意识就是自我意识。(注:《精神现象学》上卷,114页。)在“意识自身确定的真理性”中,自我意识则又迫使自己向自己的客观化过渡,从而在“理性”中意识到自己原先持有的观念即个别的自我意识就是一切实在本身(注:《精神现象学》上卷,153页。)同样是虚幻的,真正真实的只是集体的自我意识“伦理的实体是自我意识的本质;而自我意识则是伦理实体的现实和实际存在,是它的自我和意志”(注:《精神现象学》上卷,290页。)。“伦理实体”的提出是“意识自身向科学发展的一篇详细的形成史”的合乎逻辑也合乎历史的结论,但《现象学》由此转入“意识形态学”的讨论却多少有些勉强。
(2)客观精神——社会意识。“精神”章似乎是一部历史哲学的删节本,但在这里,我们更应当在政治思想发展史的意义上来解读它。黑格尔从原始部落的“伦理世界”开始,对一直到法国大革命的雅各宾专政时期的“绝对自由”的政治观念进行了逻辑的推演。它一方面表明,历史的发展具有自己的内在规律,一个社会形态总是必然地从另一个社会形态内部成长起来的,就在人们为前途忧心忡忡的时候,历史总会为自己做出合理的选择,如基督教之于罗马帝国;另一方面则又表明,法国现行的资产阶级政治模式不是历史发展的顶点或对古典理想的真正回归,因为“我们称之为政府的,只是那胜利了的派别,而正是由于它是一个派别,这就直接孕育着它的倾覆的必然性;而且反过来说,它既是一个政府,这就使它成为一个派别,使它有罪过。”(注: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下卷,120页。)那什么将是历史发展的顶点呢?《现象学》对此没有做出肯定回答,它只是要人们知道,在“对其自身具有法定性的精神、道德”中答案会自己呈现出来。
(3)绝对精神——绝对意识。在客观精神中,黑格尔暗示他有所允诺的东西将在绝对精神中给出,但在这里,他的允诺同样没有兑现。他要求自己的追随者在对精神的全体的把握中自己找出答案,而他自己只对这种把握提供了一种线索,即作为对科学的概念式的理解,哲学比宗教的表象式理解要高级,这样他就曲折地实现了向计划中的“科学体系的第二部分”的引导。对于自己同样关注的国家体制问题,黑格尔的确没有给出正确的回答,不过联系他早期的政治思想的发展,以及后来《法哲学原理》中的一致思想,我们在他对宗教的热情关注中(注:作为现象学的目的和终点,“绝对知识”只占据了20页的篇幅,这还不及“宗教”80页的1/4。)再一次看到了他对国家的伦理整体性的一贯要求。
总的看来,《现象学》为了完成自己的使命而选择的否定的体系并不很成功,因为它在起承转折之间可指责的地方太多,与之相比,《哲学全书》只是在从逻辑学向自然哲学的过渡之中存在唯一难以防御的薄弱环节。我们之所以不揣浅薄地对黑格尔这一在国内并不受关注的著作的自然状况投入了异乎寻常的激情,除了它自身蕴涵的许多富于启发的不朽片断(如主奴关系、颠倒的世界等)的诱惑之外,更重要的是,在作为“黑格尔的《现象学》及其最后成果——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辩证法”中,(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选》,第42卷,163页。)我们看到了它对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及评判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某些流派的理论实质的重要性。而这一切都应当是以对《现象学》的文本状况的准确理解为基础的。
标签:精神现象学论文; 黑格尔哲学论文; 现象学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康德哲学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问题意识论文; 哲学家论文; 科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