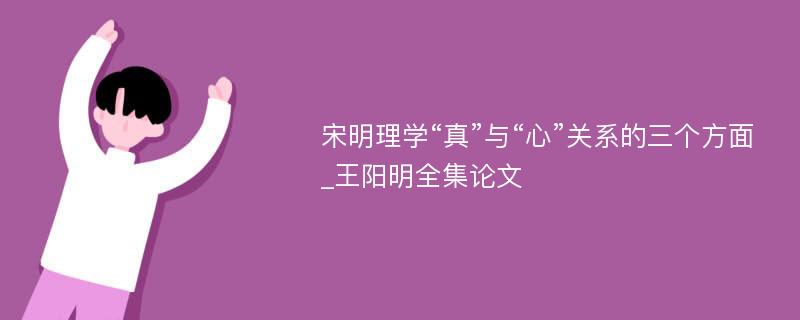
宋明理学“诚”“心”关系之三个层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学论文,层面论文,关系论文,宋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儒家在讲“诚”为“天之道”、“人之性”的同时,从来不离“心”而论“诚”,从荀子的“君子养心莫善于诚”,到朱熹的“诚以心言”,再到王夫之的“诚,心也”,莫不是将诚与心相联系,以心言诚。尤其是在宋明时期,“诚”与“心”的关系得到了更为细致的论述。但是由于宋明理学对“心”有多层次的规定,所以“诚”、“心”关系往往通过多种不同的层面表现出来。
一、从存在论而言,“心”是“诚”的寓所
“诚”有天道之诚和人性之诚之分,其中,人性之诚必须依附于人而存在,而且必须存在于人的“心”中。具有客观天理内容的“诚”以“心”为存在的寓所,展现的就是存在论上的“心理合一”。
当我们从“天道”和“人性”方面来审视“诚”时,会遇到这样一个问题:“诚”落脚于人的何处?一般而言,宋明理学家都认为“诚”具于“心”中,以“心”为存在的“寓所”(注:这里所说的“心”不是指人的有形的血肉之心,而是指人的“虚灵”之心,它无形体可言,正因无形体,所以具有包容万理的能力。)。张载就曾以“天之实”和“心之实”的合一来解释“诚”,其后,朱熹又对这一观点进行了发挥,他说:“盖诚之为言,实而已矣。……有以理之实而言者,……有以心之实而言者。”(《四书或问·中庸或问下》)“天之实”、“理之实”都是在天之诚,而“心之实”则是在人之诚,可见,在人之诚不能离心而存在。张载和朱熹通过“心之实”来说明诚在心中,陈献章则说得极为简单明了:“诚在人何所?具于一心耳。”(《论·无后论》,《陈献章集》卷一)心学的集大成者王守仁也赞成此说,只是并未明言。
虽然宋明理学家都认为“诚”存在于“心”中,但是在“诚以何种方式存在于心中”这一问题上,他们也存在着分歧。理本派和心本派的基本观点是:诚是心之体。他们认为,具于“心”中之诚决不是像物件摆放在容器中那样,与心只是空间上的包含与被包含的存储关系,而是以“心之体”的形式与心内在地结合在一起,诚就是心的本然状态。对于“诚是心之体”这一共同的命题,理学派和心学派的理解又有着些微的不同。程、朱为代表的理本派,以“理”和“性”为中介来论述诚是心之体。他们首先以诚是实理,是天理之实然,是客观的精神实体——天理的根本属性;然后人禀天理而为性,即为性理,“诚”也随之成为“性”的根本属性,而性理即具于人的心中,通过这样一系列的转换,他们建立了“诚”与“心”的联系。例如,二程认为“心具天德”(《河南程氏遗书》卷五),就是说心包涵有仁义礼智等天理,朱熹则说“理无心,则无着处”,故心与理“本来贯通”。理在心则言之为性,“性便是心之所有之理”,故性也具于心中,“心将性做馅子模样”。朱熹说“心将性做馅子模样”,并不是将心、性视为截然分割的两个事物,而只是藉此表明心与性的存属关系,因为他同时还指出:“心兼体用而言,性是心之理,情是心之用”(《性理二·性情心意等名义》,《朱子语类》卷五),所谓“心之理”就是心之体。由此可以逻辑地推出,性理为心之体,性理以心之体的方式存在。程、朱又以至善之性为心之体,而至善之性即为诚,故心之体亦为诚。
陆、王心学对“诚是心之体”有不同的论证方法。以陆九渊、王守仁为代表的心本派,他们不是将“诚”视为进入到主体心中的客观之理,而是直接将“诚”与心本体等同,使二者直接具有本体论上的统一性。陆九渊反对把“诚”视为客观精神,而是把“诚”理解为主观精神,因此他直接以心说诚,认为人的本心就是诚,“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此吾之本心也”(《书·与曾宅之》,《陆九渊集》卷一)。“本心为诚”也就是“心之体为诚”。陈献章是明代心学的开端者,他不仅明确地指出“诚”具于人的“心”中,而且以“诚”为宇宙本体,“心之所有者此诚,而为天地者此诚也。夫天地之大,万物之富,何以为之也?一诚所为也”(《论·无后论》,《陈献章集》卷一),可见,心体就是诚。王守仁则直接从心体立论,直言“诚是心之本体”(《传习录上》,《王阳明全集》卷一)。同样是以诚为心之体,同样是从存在论上论述诚是心与理的合一,理本派和心本派走的却是两条不同的道路,然而他们方向虽然不同,最终却殊途同归。
张载、王夫之等为代表的气本派,也都一致认为“诚”存在于人的心中。张载认为“诚”是天道:“天所以长久不已之道,乃所谓诚。”(《正蒙·诚明篇第六》)“诚”还是“天性”的道德内容的源泉(注:张载以气为宇宙本体,气的运行、变化、化生万物的规律和特征,即是天性,它内涵仁义礼智等道德内容。)。天地万物之性都禀赋于天性,但由于禀受程度不同,性也就千差万别。人之性由于“通而开”,故能禀受天性中仁义礼智等道德内容,而“诚”也就成为人之性的基本属性。继而,张载又提出“心统性情”说,将性和情统一于人的心中。王夫之则指出:“诚者,天之实理”(《乾称篇下》,《张子正蒙注》卷九)。而“万事万物之理无非吾心之所固有”(《四书训义》卷八),“故理者人心之实,而心者即天理之所著、所存者也”,也就是说“天下无心外之理”(《四书训义》卷六)。这样,作为天之实理的诚就随之进入了人的心中。气本派虽然认为“诚”存在于人的心中,但并没有指出“诚”是心的本体,因为在他们看来,“心”主要是认知之心、知觉之心,而较少本体论上的涵义。综上所述,宋明理学家们认为,作为“天之理”、“人之性”的诚,是不能脱离心而存在的,相反,它就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存在于人的心中,以心为存在的“寓所”。理学家们将“诚”寓于心中,一方面使“诚”具有了存在的根基,一方面又使心具有了内在的道德规定性,使儒家的心性理论以及对人的道德自觉的弘扬具有了心理根基,具有一定的伦理意义。但是,他们将“诚”视为先于人而存在的伦理属性,并以之作为“心”先天的伦理本质和道德内容,则是不科学的。他们不可能认识到,“心”中所具有的任何道德内容(包括诚)都是人们在后天的社会生活中逐渐形成的,是人社会化的产物;他们也不可能认识到,“诚”作为一种客观存在,既源于社会关系,又依赖社会关系而存在。
二、从认识论而言,“诚”需要心去体认
当我们说“诚”存在于人的心中,是对人心的道德规定时,“诚”还只是一种自在的存在,它只有被人所认识,成为主体的道德意识,才能成为一种自觉的存在,而这离不开心的认知功能的发挥。依赖心的认知功能使“诚”由潜在的存在转化为主体自觉的道德意识,体现的就是认识论上的“心理合一”。
宋明理学家在强调心为“实”、心有道德内容的同时,也都认为心是认识器官,具有认识和思维的功能。也就是说,心不仅是义理之心,而且是认知之心;不仅是本体之心,而且是功能之心(注:戴震反对把心分为认知之心与先天的道德之心,他认为,人只具有知觉运动之心,它可以使人“扩充其知至于神明”,形成道德意识。可见,道德意识并不是先天而来的,而是后天形成的。“诚”也是人的主观道德意识,因为“诚”是“实”,以智、仁、勇等德性为其内容,但却依“血气心知”而存在:“由血气心知而语于智仁勇,非血气心知之外别有智、有仁、有勇也予之也。”同时他还指出:“曰善,曰德,尽其实之谓诚。”也就是说,如果把诚视为一种德性的话,它必须通过人伦日用表现出来。戴震的这一观点完全去除了“诚”的本体论涵义,是对“诚”的比较正确的认识。)。例如他们说:
“人心莫不有知”。(《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一)
“有知觉者谓之心”。(《朱子语类》卷十四)
“心不是一块血肉,凡知觉处便是心。”(《传习录下》)
“心日生思。”(《尚书引义》卷三)
如此等等。既然心具有知觉思虑的功能(能知),那么,心的认识对象(所知)是什么?在这个问题上,宋明理学内部也存在着分歧,但在分歧中又体现出共同之处,即以仁义礼智等道德原则为内容的性理(义理)始终是心的认识对象。于是,以性理形式存在于人心中的“诚”也有待于认知之心将它发掘出来。
心本派和理本派以诚为心之体,并不否认心有认知功能,相反,他们对此也十分强调。心本派将诚与心、性、理甚至良知等同,认为人首要的就是存心,“夫此心存则一,一则诚;不存则惑,惑则伪”(《论·无后论》,《陈献章集》卷一),而要存诚,首先就要明诚,就要致良知,也就是以主体之心去认识本体之心,从而使自心之诚得以彰显。理本派也认为人首要的工夫就是明诚,但是他们所说的“明诚”不仅仅是向内认识自心之本体,而且包括格物致知,向外求物理,因为朱熹认为,穷得物理,则可豁然贯通,从而明得心中之理。由此可见,虽然同样是以诚为心之体,但识诚的方式和途径却是不尽相同的。
将“诚”理解为认知型的心理合一的代表人物主要是胡宏和王夫之。胡宏认为“诚者,天之道也”(《知言·中原》),在人即为人性,而性为心之本体,性体心用,故诚体心用。表面看来,胡宏此说似与程、朱、陆、王“诚为心之体”的观点相合,但实际上,二者之间存在着差别:胡宏认为诚并不是心的本然状态,而是心的认识对象。因为他所说的心主要是认知之心,他所说的诚体心用,是指心以诚为体,或者说是以认知之心去合诚体,故他说:“人心合乎天道,则庶几于诚乎!”(《知言·一气》)王夫之认为:“诚,心也,无定体而行其性者也。心统性,故诚贯四德,而四德分一,不足以尽诚。”(《中庸第二十五章》,《读四书大全说》卷三)但由于王夫之所理解的心主要为知觉之心,所以,诚虽然涵在心中,但心与诚却非本体的同一关系,而主要是认知与被认知的关系,故王夫之说:“实有是物则实有处是物之事,实有此事则实有成此事之理,实有此理则实有明此理行此理之心。……诚以实心行实理之谓。”(《四书训义》卷二下)以“心”“明此理”,表达的显然是一种认知关系。他所理解的“诚”就是通过心的认识功能将心中之理变为人的自觉认识,并将之付诸行动。同样是以心体诚,胡宏以心与诚为二,而王夫之明显的是以心与诚为一,只是他并不是从本体上来说明诚与心的合一,而是把诚理解为心的一种诚实无伪的状态。这样,诚就丧失了本体论的含义,而成为对人的主观意识的一种描述。其后的戴震,更是强调心的认知功能,强调“诚”作为一种道德意识的后天性③,“诚”的超越性含义越来越弱。
正是由于心具有认知和思虑的功能,内在于人心之诚才不至于成为完全自在的、潜在的存在,而是成为在人的关注下的主观意识,内在于人心之诚才具有了意义。正是由于人能够通过心对诚进行认知,认识到诚是人心所要达到的一种境界,经由尽心、知性而达天的自我修养才成为了可能,否则,作为标志“天人合一”的诚范畴,将只有从“天”到“人”的前半截,而无从“人”到“天”的后半截。应当指出的是,儒家所理解的心对诚的体认,主要实现于主体意识之内,是心的自我认识,这与我们现在所理解的对客观道德要求和道德法则的认识活动是有很大出入的。
三、从意志论而言,“诚”的实现需要“心”的主宰功能的发挥
存在于心中之诚被人所认识,转化为人的自觉意识之后,诚仍然还没有表现出它的现实性来,因为它还没有对人的情感、行为发生作用,还没有表现于外的载体。所有这一切的最后完成,还有赖于“心”的主宰功能的发挥,即一方面通过心对自身的情感等进行有效的控制、引导甚至压抑,一方面则要见善则喜,并能“择善而固执之”。发挥心的主宰功能,使自身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始终贯彻性理的要求,这就是“诚”所标志的意志论上的“心理合一”。
总体而言,在理学家看来,心并不是一团死物,它不仅具有知觉思虑的功能,而且具有一定的能动性,具有主宰功能。心的主宰功能不仅表现为心“为一身之主宰”(《张子之书一》,《朱子语类》卷第九十八),即位于人身体之中央的心能够对五脏四肢感官等进行控制(注:《说文》曰:“心,人心,土藏,在身之中,象形。”所谓“土藏”,就是指就像“土”居于五行之中一样,“心”也居于人身体的中央,而“中”在中国古人看来是统治者的位置,居中者具有统率的功能,所以“心”在人身中相对于其他的器官也处于主宰者的地位。),而且更重要的是表现为心是“万事之主”,使人在应事接物上能够始终一以贯之,因此,心为主宰就在于心不“走东走西”,能够“一而不二”,能够“命物而不命于物”。如果说前者为生理意义上的“心为主宰”,那么,后者才是真正伦理学意义上的“心为主宰”。我们则主要从后一方面来探讨“诚”向道德意志转化的过程。
在朱熹的理论中,“心”的主宰作用主要体现在“心统性情”说中。“心统性情”包括两个方面:“心兼性情”和“心主性情”。
朱熹说:“‘心统性情。’统,犹兼也。”(《张子之书一》,《朱子语类》卷九十八)“性,其理;情,其用。心者,兼性情而言;兼性情而言者,包括乎性情也。”(《论语二·学而篇上》,《朱子语类》卷二十)性和情虽然都包涵在心中,但它们的存在方式是不同的,其中,性为心之体,情为心之用;性为心之静,情为心之动;性为心之未发,情为心之已发。这说明,心不仅具有道德内容,而且可以生发出情感。既然如此,与性同为心之体的“诚”也就不可避免地与“情”发生着关系。心将性和情包含于其中,并不撒手不管,任其自生自灭,而是将其视为“客”,将自身视为“主”,并以理对性和情进行管摄和宰制。“性者,心之理;情者,性之动;心者,性情之主。”(《性理二·性情心意等名义》,《朱子语类》卷五)“心若不存,一身便无所主宰。”(《学六·持守》,《朱子语类》卷十二)这就是“心主性情”。然而朱熹认为,心只具有主宰功能,其本身并不是主宰者,心中所具之理才是真正的主宰者,也就是说,心以理为主宰。心的主宰作用是贯乎动静的。当心静时,虽是未发,亦须操存此心,时时做存心、养心的修养工夫,使“主人翁常惺惺”,因为“未感物时若无主宰,则亦不能安其静,只此便自昏了天性”(《答林择之》,《朱文公文集》卷四十三)。人的天性本善、本诚,是心之体,但如果不时常加以存养,人的天性就会丧失,从而使人失去其为人的根本。当心动时,心已发而为情,情有善恶。如恻隐、羞恶、辞逊、是非之情乃出于性,故为善;而“心所发为情,或有不善”,此乃“情之迁于物而然也”(《性理二·性情心意等名义》,《朱子语类》卷五),正因为情有流于不善的可能,所以更加需要心的主宰,控制情欲,“心宰则情得正,率乎性之常而不可以欲言矣;心不宰则情流而陷溺其性,专为人欲矣”(《答何倅》,《朱文公文集》卷六十四)。心对于性和情的这种宰制功能使人时时刻刻保持警醒,反省自身的言行,不断完善自身,实现与天理的合一,达致“诚”的境界。
王守仁也认为心具有主宰功能,但由于他以心为宇宙本体,并将理、性、良知、诚等都消解于心中,将他们视为主体精神的存在,这样,同样是认为心具有主宰功能,朱熹和王守仁之间就存在着很大的不同。首先,朱熹主要是以心来宰制性和情,王守仁则不仅强调心对性和情的宰制作用,而且强调心是天地万物的主宰。其次,朱熹主要是从功能的角度论述心的主宰作用,即心具有主宰的功能,王守仁则是从功能和主体相统一的方面,即主宰功能与主宰者相统一的方面来论述心的主宰作用,因为王守仁认为心就是理,心外根本就没有理的存在,因此主宰者就是心本身,所谓以心为主宰就是心以主体理性对自身的言、思、行进行规约和指导。王守仁言诚处并不多,但显然与朱熹有所不同。他说“诚是实理,只是一个良知。”(《传习录下》,《王阳明全集》卷三)在王守仁的道德体系中,良知本身就是判断是非、善恶的标准,具有辨别是非、善恶的能力,其对象主要是“心之所发”——“意”:心之“应物起念处,皆谓之意。意则有是有非,能知得意之是与非者,则谓之良知。”(《答魏师说》,《王阳明全集》卷六)良知对“意”还具有指导功能,促使人存善念,去恶念:“尔意念着处,他是便知是,非便知非,更瞒他一些不得。尔只不要欺他,实实落落依着他做去,善便存,恶便去。”(《传习录下》,《王阳明全集》卷三)可见,以诚为良知,就是以诚为主体的理性精神,它使人时刻注意自己一念之发动,从而保持“意”的善的性质。王守仁虽然也认为诚为实理,但由于他所说的理为主观精神的形式,所以诚也就更主要地表现为一种主体精神,从而更加带有主体意志的意味。
王夫之则主要是从道德意志的角度来理解诚。他认为诚在人即表现为心,诚心就是人的诚实无伪的精神状态,有了这种精神状态,人们就可以对自身的情、才、行为等进行有效的制约。他说:“吾立身之始,有为身之主者,心也。当物之未感,身之未应,而执持吾志使一守其正而不随情感以迷,则所以修身之理,立之有素矣,乃心素定者也。”(《四书训义》卷一)这里,之所以能“一守其正而不随情感以迷”,之所以能“定”,乃是因为心诚,心诚就使人有主心骨,就能对情感给予指导。诚心对人情感的指导必须通过人的行为表现出来,要“发而之于视、听、言、动”,如果心的主宰作用没有对人的行为产生影响,心也就不成其为主宰之心。此外,王夫之还认为,心对行为的指导和制约必须要有一贯性和稳定性,即能够持之以恒,他批评那些意志不坚定的人,缺乏坚定的信念和一以贯之的毅力,他们“得而一心,失而一心;否而一心,泰而一心;难而一心,易而一心;言而一心,行而一心;敛而一心,舒而一心”(《大雅·三十七》,《诗广传》卷四),这样根本达不到心正、身修的目的。可见,王夫之将诚与心结合,主要还是在于体现主体的道德自觉性,或者说是意在于弘扬人的道德主体性。
由朱熹发展到王守仁,诚的主体道德自觉方面的意义是在不断加强的,而在王夫之的理论中,由于他弱化了诚的本体论方面的涵义,而更主要地把诚与心理功能意义上的“心”相联系,从而使诚的道德意志、道德自觉方面的涵义得到了强化,诚更主要地是作为一种道德心理的形式出现了。
“诚”与“心”的关系虽然表现为上述三个层面,但是由于宋明理学家们都在不同程度上、或多或少地承认心是义理之心和认知之心的结合,并都强调心具有主宰功能,因此,我们也不能把某个人物关于诚是心与理的合一的理解就仅仅归结为某一种类型或层面,而应该看到每一个人物的思想都是复杂的,它往往要通过多个方面才能完全展现出来。我们在理解他们的观点时,既要看到他们思想的总体,也要看到他们在三个层面中强调的重点,而不能仅仅局限于某一个方面,忽视其他。
值得指出的是,近代以来,一方面,理的本体地位遭到瓦解,另一方面,随着西方自然科学和实验科学的发展及其向中国的传播,“心”范畴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心的不同层面和功能被逐一分化:心的认识功能与人的大脑、神经系统联系起来;心的本体性被加之于自然物质元素(以太、电等)之上(注:例如谭嗣同,他虽然以心为最高的宇宙存在,“心之力量虽天地不能比拟,虽天地之大可以由心成之、毁之、改造之,无不如意。”但是他又用以太和电来解释心的这种功能:“以太也,电也,粗浅之具也,借其名以质心力。”认为心的功能的发挥要借助以太和电等媒介。);心的道德规定性被改变为道德原则和道德观念,而心逐渐转化为与物质相对应的心理范畴。中国传统“心”范畴的这种近代转化,不仅使“诚”(道德内容)无法寓居于“心”中,再加之心的本体地位的逐步丧失,“心理合一”也就逐渐宣告结束,“诚”所标志的心理合一在近代基本上走到了终点。
标签:王阳明全集论文; 宋明理学论文; 理学论文; 读书论文; 朱熹论文; 朱子语类论文; 王守仁论文; 王夫之论文; 儒家思想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