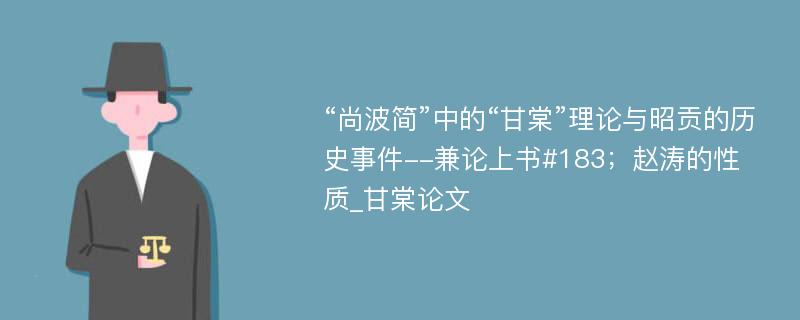
上博简《甘棠》之论与召公奭史事探析——附论《尚书#183;召诰》的性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探析论文,尚书论文,性质论文,之论论文,甘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320(2003)05-0019-07
上博简《诗论》20支竹简中有5支简提到《甘棠》一诗。《诗论》共评说诗60篇左右,对于一首诗的评论,往往是惜墨如金,有的甚至只有一字的评语,而对于《甘棠》一诗的评论,则不厌其烦地进行评说,反复申明其意。孔子对于该诗的重视由此可见一斑。《甘棠》一诗见于今《诗经·召南》,全诗3章,章3句(注:今将《诗·甘棠》具引如下:“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蔽蒂甘棠,勿翦勿败,召伯所憩。蔽芾甘棠,勿翦勿拜,召伯所说。”),本来是一篇很普通的诗作,意义明晰,训释无大障碍,然而是什么原因使孔子对它备加关注呢?孔子论此诗的背后之意何在呢?细绎《诗论》相关简文,可以发现,原来孔子对于《甘棠》诗的重视与他对于周初史事的认识颇有关系。再联系到《甘棠》一诗所歌颂的召公史事,他在周初的举足轻重的地位尚为史家认识不足,对于《尚书》中与召公直接相关的《召诰》、《君奭》等篇的一些关键问题的认识也还有再探讨的余地。今不揣浅陋,对于这些问题试作讨论如下,敬请专家教正。
一
上博简《诗论》等10、16、13、15、24号简分别载有关于《甘棠》一诗的评析[1](P139-153),现将简文依次移录如下:
《甘棠》之保(报)……害(曷)?曰:童(终)而皆臤(贤)於其初者也。
[《甘棠》之保(报),敬]召公也。
《甘[棠]》思及其人,敬爱其树,亓(其)保(报)厚矣。《甘棠》之爱,以邵(召)公[所茇也]。
吾以《甘棠》得宗庙之敬,民眚(性)古(固)然。甚贵亓(其)人,必敬开(其)立(位)。悦亓(其)人,必好亓(其)所为,亚(恶)亓(其)人者亦然。
上引首简为《诗论》第10号简,此简评析《诗》从《关雎》到《燕燕》七首诗,省略掉中间内容,即如上所引者。上引第二例见于第16号简,方括号中字原缺,据廖名春先生说拟补(注:廖名春《上海博物馆藏诗论简校释》,《中国哲学史》2002年第1期。按,《诗论》等16号简有“《绿衣》之忧,思古人也”之句,与第10号简“《绿衣》之思”句式类似。依照此例,补上“《甘棠》之报”,可谓有据。然而这其间稍有值得再商榷的地方,第16号简与第10号简关于《绿衣》一诗的评语之词一为“忧”,一为“思”,两者并不一样。所以本处是否一定补上“报、敬”二字,还有再议的余地。)。上引第三例为第13简和第15简系连而成。第13号简末尾一字为“甘”,第15号简首字为“及”,其间依廖名春先生说拟补“棠思”二字(注:《孔子家语·好生》篇载孔子评《甘棠》诗有“思其人必爱其树”之语,可证此处拟补“思”字是很可信的。),在第15号简末尾补“所茇也”三字,可以语意连贯,符合《甘棠》一诗主旨,应当是正确的。上引末例见于第24号简,其文字多有与《孔子家语·好生》篇的相关论述相似者。
关于第10号简和第13号简的“保”字的考释,马承源先生读其为褒,为褒奖之意以为是对于召伯的赞美。保通假作褒,虽然没有任何问题,但此释还是不如读为“报”为优。李学勤先生说:“‘保’读为‘报’,因思念感激召公,而敬爱召公种植的甘棠,是其报德至厚。”[2](P17)按,褒(保)字与报相通假,其例见于《礼记·乐记》,是篇谓“故礼有报”,郑注“报读曰褒”,而褒与保相通,则保可读为报矣。保字本义为襁褓之子为人所保护、包裹,并由此引伸出许多义项,比较近直的义项为保持、保有,如今语之“永葆革命青春”然。这里所用的“保”字已有报本反始之意。《韩诗外传》卷3载:“大道多容,大德多下,圣人寡为,故用物常壮也。传曰:‘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忠易为礼,诚易为辞,贤人易为民,工巧易为材。”诗曰:“政有夷之行,子孙保之。”(注:《韩诗外传》诸本多衍引诗之十一字,今据许维遹《韩诗外传集释》(中华书局1980年版)本所校。)所谓“子孙保之”,意即子孙报之,意思是说只有宽厚仁慈之政,子孙才能报本反始而长葆其美德之政。本简的“《甘棠》之保”,与此所引《诗·天作》篇的“子孙保之”的意思十分接近。《诗·烈文》亦云:“烈文辟公。锡兹祉福。惠我无疆,子孙保之。”其意亦可作如是观。
《甘棠》一诗为颂赞召伯之作,召伯即召公奭(或谓为召伯虎,似不可信)。全诗表现了人们对于召公曾经在其下休憩过的甘棠树的崇敬之情,人们不得去碰它,更不能损伤它,要做到“勿翦勿伐”、“勿翦勿败”、“勿翦勿拜(拔)”,已将其作为神树对待(注:周代有社树,如《庄子·人间世》载“匠石之齐,至於曲辕,见栎社树,其大蔽数千牛”;《墨子·耕柱》篇所载“丛社”,亦当包括有树木。《白虎通·社稷》所谓“报社祭稷”的“报社”,是汉人所记对于社神之祭,而追本资源,可能与古代对于神树的祭祀有关系。),愚以为这种树应当是周代的社树,闻一多先生曾谓:
甘棠者,盖即南国之社木,故召伯舍焉以听断其下……甘棠亦社木,当为大树,故能为召伯所舍,然则蔽芾者,木荫盛覆蔽之貌也,《传》以为“少貌”,亦失之。[3](P174)
按,闻先生此说远胜毛传,卓见灿然,但谓甘棠先为社树而后召公才休憩于其下,恐怕是将事情说颠倒了。事情本来应当是人们由敬仰召公而爱屋及乌,延及爱护甘棠之树,所以诗中才会有“蔽芾甘棠,勿翦勿伐”之语。树由于召公的原因而被保护,由此繁茂异常而被视为社神之树。《礼记·郊特牲》篇谓:“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载万物,天垂象。取财於地,取法於天。是以尊天而亲地也,故教民美报焉。家主中霤,而国主社,示本也。唯为社事,单出里。唯为社田,国人毕作。唯社,丘乘共粢盛,所以报本反始也。”可见社祭的目的即在于“报本反始”。人们祭祀召公曾经在其下休息过的甘棠树,就是对于召公功业德操的怀念。以前读诗,觉得此诗中的甘棠当为社树,苦无证据,今得此简文佐证,可以释疑。总之,简文之“保”如果读“褒”,固然不误,但不若读“报”为优。简文“保(报)”如果笼统地说是对召公的报德,固然也不误,但是具体而言,则作为报祭之“报”来理解,似又优于笼统之说。若能够进一步指出此“报”祭是对于社树的祭祀,则庶几近于实际矣。
二
一个引人注意的现象是,上博简的这几条简文可以在文献中找到旁证。由此可以考虑到《孔子家语》的两条相关材料应当是渊源有自的。过去论者多怀疑《孔子家语》为王肃伪造。《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一方面谓“其出于肃手无疑”,然而,另一方面又指出是书所载材料的价值仍不可废,“遗文轶事往往多见于其中”,此可谓持平之论。今得上博简材料,更可证其语不虚。虽然现在还没有充分的证据以否定王肃伪造之说,但可以断定其中的有些材料渊源有自,足以启发人们更为重视此书的价值。我们先来看《孔子家语·庙制》篇的记载:
子羔问曰:“祭典云:‘昔有虞氏祖颛顼而宗尧,夏后氏亦祖颛顼而宗禹,殷人祖契而宗汤,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此四祖四宗,或乃异代,或其考祖之有功德,其庙可也。若有虞宗尧,夏祖颛顼,皆异代之有功德者也,亦可以存其庙乎?”孔子曰:“善,如汝所闻也。如殷周之祖宗,其庙可以不毁,其他祖宗者,功德不殊,虽在殊代,亦可以无疑矣。《诗》云:‘蔽芾甘棠,勿翦勿伐,邵伯所憩。’周人之於邵公也,爱其人犹敬其所舍之树,况祖宗其功德而可以不尊奉其庙焉?”
这条材料所记孔子与其弟子子羔的对话,是讲古代的毁庙之制的。按照周代庙制,祖先的宗庙,天子立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庙,士一庙,庶人无庙。超出定制之庙,要择吉日将神主迁入太祖之庙,而其宗庙则被毁弃,此举称为“迁庙”,其仪节见《大戴礼记·诸侯迁庙》篇。从上面的引文可以看出,孔子所强调的在于是否迁庙虽然要依礼制而行,但是还要看祖宗的功德如何,如果有大的功德,则“其庙可以不毁”。孔子举出《甘棠》诗句为证,提出这样的反问:“周人之於邵公也,爱其人犹敬其所舍之树,况祖宗其功德而可以不尊奉其庙焉?”这里语焉不明之处在于邵(召)公是否周人所敬重的有功德的祖先呢?我们再看《孔于家语·好生》篇的一条材料,对于这个问题似乎可以理解得更多一些:
孔子常自筮其卦,得贲焉,愀然有不平之状。子张进曰:“师闻卜者得贲卦,吉也,而夫子之色有不平,何也?”孔子对曰:“以其离耶!在周易,山下有火谓之贲,非正色之卦也。夫质也黑白宜正焉,今得贲,非吾兆也。吾闻丹漆不文,白玉不雕,何也?质有余不受饰故也。”孔子曰:“吾於《甘棠》,见宗庙之敬甚矣,思其人必爱其树,尊其人必敬其位,道也。”
这条材料虽然与上一条意义大致相同,但是特别令人惊奇的是它所谓“吾於《甘棠》,见宗庙之敬甚矣,思其人必爱其树,尊其人心敬其位”与《诗论》第24号简所载的相关内容非常接近。两者的互证,无疑大大提高了《孔子家语》的真实可信程度(注:《孔子家语》的这个村料在文献中并非孤证,《说苑》卷5亦有类似的说法:“夫诗思然後积,积然後满,满然後发,发由其道而致其位焉;百姓叹其美而致其敬,甘棠之不伐也,政教恶乎不行!”孔子曰:“吾於甘棠,见宗庙之敬也。甚尊其人,必敬其位,顺安万物,古圣之道几哉!”这里所说的“尊其人,必敬其位”,与《孔子家语》完全相同,足可为证。关于这些材料的意义,朱渊清先生指出,“《孔子家语》很可能就是在《孔子诗论》之类原始本子的基础上抄撮编成,出土和传承文献相互印证,真确地反映了孔子的《诗》说思想,”(《从孔子论〈甘棠〉看孔子〈诗〉传》,见《上博馆藏战国楚竹书研究》第130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其推测是可信的。)。孔子自筮而得一般认为是吉利之卦的“贲”卦而不悦,原因是他认为贲卦为杂色之卦,贲的卦象为上艮下离,在八卦中,艮为山的象征,离为火的象征,所以孔了说它“山下有火谓之贲”,然而,离火为赤色,贲山为青色,赤、青相间是为杂色,虽然可以文饰,但却泯没了质地。在孔子看来,表示正色者乃是黑白二色,要讲求质朴须是此二色,所以说“夫质也黑白宜正焉”。本质如何就如何,不必加以文饰,孔子得贲卦失却其质朴之求,所以“愀然有不平之状”。这个记载正说明孔子重视本质的朴实无华,讲求实事求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好生》篇中,孔子引用《甘棠》之诗为证的用意何在呢?愚以为要弄清此点必须首先说明召公身份问题。
三
召公为周初重臣这是完全肯定的,历来都没有疑义,然而对于他是否文王之子这一点却有不同的记载和说法。关于召公的身份,先秦时期的文献缺载,汉朝时有两种说法,一是司马迁认为他“与周同姓”(注:《史记·燕召公世家》“召公奭与周同姓,姓姬氏”;《汉书·古今人表》取此说谓召公奭“周同姓”;《史记·燕世家》集解引谯周说谓“周之支族,食邑于召,谓之召公”。),是为普通的姬姓贵族;二是认为他是周文王之子、周公之兄。《白虎通·不臣》篇谓:“《礼·服传》曰:‘子得为父臣者,不遗善之义也。’《诗》云:‘文武受命,召公维翰。’召公,文王子也。”认为他是周文王之子而为文王臣者。《论衡·气寿》篇说:“召公,周公之兄也”,与《白虎通》的说法一致。《谷梁传》庄公三十年谓:“燕,周之分子也。”(注:清儒钟文烝《春秋谷粱经传补注》卷8引姚鼐说谓此处的“分子”,为“别子”之误。其说可信。)虽取融通说法,但却与《白虎通》、《论衡》等的说法相近。《诗·甘棠》疏引皇甫谧谓召公为“文王之庶子”,可能是比较接近实际的说法。
我们前面已经指出《孔子家语》中的与《甘棠》一诗相关的两条材料得上博简《诗论》的佐证,表明其渊源有自,是可信的,而非王肃伪造。其中特别值得重视的是讲“宗庙之敬”时以颂扬召公的《甘棠》为例,强调“尊其人必敬其位”,一个合理的推论便是,周人不仅敬受召公曾经休憩过的甘棠树,而且敬重召公在宗庙的神主牌位。既然在周的宗庙里有召公之位,那么他就应当是周文王之子,而不大可能只是周的同姓贵族。这对于我们判断关于召公身份的两种说法的是非,应当是重要证据。
召公虽然是文王之子,但却非嫡系。从他被称为别子的情况看,他很可能是与周公同父异母的庶兄(注:关于召公的身份,前人所论甚详,如左暄《三余偶笔》一曰:“《谷梁传》曰:‘燕,周之分子。’‘分子’者,犹曲礼之言‘支子’,大传之言‘别子’也。《逸周书·作雒解》:‘三叔及殷、东徐、奄及熊盈以略,周公、召公内弭父兄,外抚诸侯。’《祭公解》:‘王曰:我亦维有若文祖周公暨列祖召公。’此召公为文王子之确证。《白虎通》曰:‘子得为父臣者,不遗善之义也。’诗云:‘文、武受命,召公维翰。’召公,文王子也。则召公为文王子,汉人已明言之。皇甫谧《帝王世纪》以为文王庶子,盖本谷梁氏‘燕,周之分子’,故云然,非无据也。司马迁云:‘召公与周同姓。’按《史记》於毕公亦云‘与周同姓’,亦可谓毕公非文王子哉?”(转引自黄晖《论衡校释》卷1)按,此处举出毕公例进行论证,说服力甚强。愚以为召公身份问题似可定论于其说。)。在周代宗法制度下,庶出的召公本不仅不应有宗庙,而且也不大可能在祖庙中保存神主牌位,而从《孔子家语》的两条材料看,他却不仅曾立有庙,而且还在周人的祖庙里保存着神主牌位,受到尊敬和祭祀。这是什么原因呢?从对于子羔所问的回答之语看,孔子强调了先祖功德的重要。子羔感到“异代之有功德者”已经不在宗法体系之中,为什么还被祭祀和尊重呢?孔子强调虽然“异代”而不在宗法体系之列,但是在“功德”面前,先祖应当是平等的,“功德不殊,虽在殊代,亦可以无疑矣。”(注:汉代人曾多次举《甘棠》而论庙制。如《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论及功臣宗庙之事曰:“成王察牧野之克,顾群后之勤,知其恩结于民心,功光于王府也,故追述先父之志,录遗老之策,高其位,大其宇,爱敬饬尽,命赐备厚。大孝之隆,于是为至。至其没也,世主叹其功,无民而不思。所息之树且犹不伐,况其庙乎?是以燕、齐之祀与周并传,子继弟及,历载不堕。”可见汉代人实认为召公之庙因其有功而未被毁。西汉后期屡议宗庙之制,不少人提出,“继祖宗以下,五庙而迭毁,后虽有贤君,犹不得与祖宗并列。子孙虽欲褒大显扬而立之,鬼神不飨也。孝武皇帝虽有功烈,亲尽宜毁”,王舜、刘歆等则反驳其说,“名与实异,非尊德贵功之意也。《诗》云:‘蔽蒂甘棠,勿翦勿伐,邵伯所茇。’思其人犹爱其树,况宗其道而毁其庙乎?迭毁之礼自有常法,无殊功异德,固以亲疏相推及。至祖宗之序,多少之数,经传无明文,至尊至重,难以疑文虚说定也。”(见《汉书·韦玄成传》)王舜等所提出的“尊德贵功”的原则,合乎儒家尊祖敬宗古义,与孔子重视“功德”之论是完全一致的。)关于庙制中应当重视功德的问题,《孔丛子·论书》篇载有孔子的答问之辞,颇有参考价值:
《书》曰:“兹予大享于先王尔祖其从与享之。”季桓子问曰:“此何谓也?”孔子曰:“古之王者。臣有大功。死则必祀之於庙。所以殊有绩劝忠勤也。盘庚举其事以厉其世臣故称焉。”桓子曰:“天子之臣有大功者,则既然矣;诸侯之臣有大功者,可以如之乎?”孔子曰:“劳能定国。功加於民。大臣死难。虽食之公庙可也。”桓子曰:“其位次如何?”孔子曰:“天子诸侯之臣。生则有列於朝。死则有位於庙,其序一也。”
《书》曰:“维高宗报上甲微。”定公问曰:“此何谓也?”孔子对曰:“此谓亲尽庙毁有功而不及祖,有德而不及宗。故於每岁之大尝而报祭焉。所以昭其功德也。”
《孔丛子》此处所论祖宗若有功德者不在毁庙之列的说法,与《孔子家语》所论完全一致,都说明了孔子对于宗法庙制,持融通态度,庙制之礼固然应当遵守,但却不必拘泥。《逸周书·祭公解》称召公为“列祖”,与称为“文祖”的周公并列,召证召公必定是文王之子,所以才能有如此的称谓(注:周初宗法制粗创,嫡庶分别尚未严格,所以《逸周书·世俘解》周武王灭商以后的祭礼谓“王烈祖自大王、大伯、王季、虞公、文王邑考以列升”,顾颉刚先生指出,“此祭不分嫡庶与直系、旁系,与保定所出《两三句兵》铭文……以三世兄弟之名先后骈列,无上下贵贱之别者同,可见其时尚无宗法之制”(《〈逸周书·世俘篇〉校注》,《文史》第二辑)。按,顾先生说甚是。此时虽无严格的宗法之制,但所祭祀的对象仍是有选择原则的,那就是入选者必定是父兄之辈者,仅为同姓贵族者并不在此列。)。按照孔子所强调的“功”、“德”的原则,召公作为周王朝有巨大功德者,尽管只是文王庶子,但在周人宗庙有其神主牌位,应当是完全有可能的事情。
说到这里,可以想到我们在前面曾经指出的一个问题,那就是孔子于《诗论》中何以特别重视《甘棠》一诗,此问题的答案就在于从《孔于家语》中可以看出的他对于召公“功德”的特别强调。那么,召公有何巨大的特别值得孔子称赞不已的“功德”呢?这就需要我们认真探析《尚书·召诰》等篇的相关问题。
四
召公奭的历史功德,约略有以下三项:其一,助周武王灭商。据《逸周书·克殷解》记载,牧野之战以后“周公把大钺,召公把小钺,以夹王”进入商都,在庆祝革命成功的典礼上“召公奭赞采”,即奉币主持。后又奉周武王之命“释箕子之囚”,这些都表明他是周武王灭商大业的主要助手之一。其二,支持周公东征平叛。在武王死后“三监叛乱”十分严峻的形势下,周公曾经语重心长地对召公说了一番肺腹之言:“告汝朕允:保奭!其汝克敬以予监于殷丧大否,肆念我天威。予不允,惟若兹诺?予惟曰‘襄我’,二人汝有合哉!言曰:‘在时二人,天休滋至,惟时二人弗戡。’其汝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让後人,于丕时。呜呼!笃棐时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我咸成文王功于不怠,丕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注:《尚书·君奭》。按,是篇的著作时代,《史记·燕世家》云:“周公摄政,当国践祚,召公疑之,作《君奭》。”这是可信的说法,《书序》谓作于召公周公相成王之时,将其列于《多士》篇之后,皆不确。《君奭》篇谓,“今予小子旦,若游大川,予往暨汝奭其济。小子同(詷)未(昧)在位,诞无我责”,此时周公自称“予小子”,合于《礼记·曲礼》“天子未除丧曰予小子”之说,是时正当武王丧期,故而周公云此。“若游大川”之语,正表明形势之紧张。此篇的著作时代当定于周公甫践位当国方将平叛之时。)周公吁请召公帮助自己东征平叛,达到“海隅出日,罔不率俾”的目标。可以说,周公在召公的帮助下才能有平叛东征时的巩固后方。关于这方面的史事,《逸周书·作雒解》也提到“三叔及殷东,徐奄及熊盈以略,周公、召公,内弭父兄,外抚诸侯……作师旅,临卫政殷,殷大震溃,降辟三叔”,与《尚书·君奭》所载是吻合的。其三,参与周公成王时代的建国大业。周初诸诰表明他不仅是营建洛邑的主要策划和实施者之一,而且也是“文王之德”的最为积极的推行者之一。《诗·甘棠》就是这方面的一个明证。依《毛诗·孔疏》,可知召公之所以在甘棠树不休息,是因为他在行文王之政的途中。据《韩诗外传》卷一所言,召公之所以不愿意扰民而建筑自己的居所乃是为了实践“文王之志”(注:《韩诗外传》卷1载:“昔者,周道之盛,邵伯在朝,有司请营邵以居。邵伯曰:‘嗟!以吾一身,而劳百姓,此非吾先君文王之志也。’於是,出而就蒸庶於阡陌陇亩之间,而叩断焉。邵伯暴处远野,庐於树下,百姓大悦,耕桑者倍力以劝,於是岁大捻,民给家足。其後在位者骄奢,不恤元元,税赋繁数,百姓困乏,耕桑失时。於是诗人见召伯之所休息树下,美而歌之。诗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此之谓也。”于此可见《甘棠》之作与“文王之志”密切相关。)。
孔子之所以特别重视《甘棠》之诗,着眼点还在于他对周文王的特别肯定。上博简《诗论》表明孔子论诗并非逐篇评析,而是有自己的选择原则的。其原则之一就是颂扬文王之德的诗篇多选多论,反之则不选或少选,不论或少论。《甘棠》一诗虽然是在颂扬召公,但召公所为是在行文王之政,是在实践文王之志,所以孔子要对它青睐有加。分析上博简《诗论》的思维逻辑,可以大致看出这样一条线索,那就是《甘棠》之诗——“敬其人爱其树”——召公功业——文王之德。由此看来,孔子重视《甘棠》一诗也就不是偶然的了。
然而,问题至此并没有结束。从上博简《诗论》中我们看到孔子所说的“贵其人”、“敬其位”的原因,一如前面我们所分析过的,召公为周文王之子,所以他才能在周人宗庙里面有神主牌位而为后人所崇敬。之所以如此还有另外一个深层原因,那就是召公对于周公的谆谆告诫为孔子所赞赏。要说明这一点,我们必须先来重新认识《尚书·召诰》篇的性质。
五
《召诰》是《尚书》中详细记载营建洛邑的月、日、胐等时间的宝贵文献[4](P105),是篇的性质尚有若干问题没有解决,《书序》、孔疏及其所引郑玄说,皆以为是篇为召公通过周公而转至成王的诰辞,于省吾先生则认为“昔人以《召诰》为召公之词,今审其语意,察其文理,亦周公诰庶殷戒成王之词。史官缀叙其事以成篇也”[5](P55-57)。《尚书·召诰》孔疏所谓“召公以成王新即政,恐不顺周公之意,或将惰于政事,故因相宅以作诰也”,断定《召诰》是召公诰诫成王之辞。这可以说是迄今为止有代表性的最为流行的说法。然而,这个说法尚有不少疑问。
其一,营建洛邑是在周公摄政当国的第五年(注:洛邑营建时间,《史记》、《周本纪》和《鲁世家》一谓在“周公行政七年”,一谓在“成王七年”,其间纠葛不清处甚为明显。《尚书大传》列周公当政七年史事甚详,其中谓“五年营成周”,应当是可信的。《逸周书·作雒解》谓“作大邑成周于土中,立城方千七百二十丈,郛方七十里,南系于雒水,北因于郏山,以为天下之大凑”,成周规模之大,与考古所见是吻合的。若谓营建洛邑在周公当政七年,则从时间上似不大可能于一年之内完成。合理的推测是成周始建于周公平叛和建侯之事(《尚书大传》说“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之后的第五年,到他当政的第七年建成,方致政成王。),其时召公到洛水一带“相宅”,成王并不在这里,经文明言召公“出取币,乃复入,锡周公”,断定《召诰》为诰诫成王之辞,于篇中并无迹象可寻。
其二,在周初特殊的历史时期,周公不仅摄政,而且称王当国(注:关于周公当政称王之事,历来纠葛颇多。然而,先秦文献和彝铭中确切记载表明,周公曾经当政称王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如《尚书·康诰》“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推乃丕显考文王”,卫国始封君康叔封是“周公同母少弟”(《史记·卫世家》),《康诰》此处之“王”必定是周公,而不会是成王。因为成王不可能称其叔父康叔封为“弟”。再如20世纪60年代出土的《何尊》铭文载营建成周之事,末尾记年为“唯王五祀”。周王在位“五年营成周”,是此王之五祀,即周公在位的第五年,其称王之事,可谓又一确证。关于周公当政称王事,顾颉刚先生《周公执政称王》(《文史》第二十三辑)、王玉哲先生《周公旦的当政及其东征考》(《古史集林》第341-356页,中华书局2002年版)等所论甚详,令人信服。)。《召诰》之篇既然制作于其当政的“五年”,那么,篇中称“王”者应当是周公,而不会是成王。若谓一直支持周公的召公越过正在称“王”的周公而向尚未在王位的成王诰诫,于情理不合。
从以上两点疑问看,将《召诰》的性质定为召公诰诫成王之辞并不可取。
愚以为此篇应当是召公诰周公之辞,其时代在周公当政称王的第五年。支持这一点的最有力的证据就在于,《召诰》篇述是时正值“以庶殷攻位于洛汭”,亦即勘测成周城基址的时期,是年正是周公当政称王的第五年,所以篇中凡所称之“王”皆当是周公而非成王,更不可能是武王。如果要否定此说,那就需要证明周公没有当政称王,亦没有营建成周,而这些似乎都是不太可能做到的事情。
然而学者们之所以不敢提出此说,其原因似乎在于这其间存在着《召诰》篇中的某些词语的解释问题。今试析如下。
第一,《召诰》曰:“今冲子嗣……呜呼!有王虽小,元子哉。”作为青年人称呼的“冲子”和作为长子称谓的“元子”,似乎非成王莫属。其实,周公亦曾自称为“冲子”,《君奭》篇载:“在今予小子旦,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于我冲子。”还说:“今在予小子旦,若游大川。予往暨汝奭,其济小子。同(童)未(昧)在位,诞无我责。”是皆为其证。周公摄政称王之时年龄并不大,而召公为文王庶长子,年龄自当长于周公。他称呼周公为年轻人,并直乎其名,都是情理中事。“元子”的概念,在《召诰》的时代,亦即宗法制尚未确立的时代,并不具备宗法制下嫡长子的含义。在先秦时期的文献中,后稷、微子启、鲧、吴太伯、周康王钊等都曾被称为元子。可见只是一个泛称,并非单指嫡长子。周公被称为元子,亦无不可。
第二,经文有“旦曰:其作大邑”的说法,如果理解为召公对成王之语,似乎文从字顺。如果理解为召公对周公之语,则似乎难通。其实,西周初年宗法等级制度尚未严密,称谓也不大严格,特别是周公当政时期直呼其名、称其为“公”、称其为“王”,皆属正常,而非僭越或不尊重。周公之名“旦”多曾被人称呼,《逸周书》诸篇和其它先秦文献多有记载,可以为证。再者篇中有“旅王若公”之语,过去皆以为此处的“王”和“公”必定是两人,其实,当指周公一人,正是他当政期间天泽未严和不欲久居王位的一个表现。召公年长于周公,位高且甚有影响,称周公为王,又称其为“公”,甚至直呼周公之名,也只有召公才能如此。
如果我们消除以上两个方面的问题,那么我们也就可以顺理成章地承认《召诰》篇的性质应当就是召公向称王的周公的进言。清儒崔东璧曾经肯定召公有向周公的进言之事,谓:“召公当亦有告周公之篇,但史逸之耳。”(注:《崔东璧遗书·丰镐考信录》卷8。)我们今得对于《召诰》性质重新认识,可以说此“告周公之篇”即《召诰》也。
那么,召公进言的中心思想何在呢?
第一,充分肯定周公称“王”的合理性,表示自己拥戴周公称王的态度。此篇记载“太保以庶邦冢君出取币,乃复入,锡周公曰:‘拜手稽首,旅王若公。诰台庶殷,越自乃御事:呜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兹大国之命。惟王受命,无疆惟休,亦无疆惟恤。’”这里明言周公受命称王合乎“皇天上帝”的意旨。周公称王虽然是无尽的福祉,但也承担着巨大的责任而为天下百姓忧虑(“无疆惟休,亦无疆惟恤”)。召公自述其身份,就是“庶邦冢君”的班头,他的言辞实是天下邦国的意见,说明周公称王为天下邦国所拥护。《召诰》篇的末尾,召公再次明确表明此意:
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雠民、百君子、越友民,保受王威命明德。王天有成命,王亦显。我非敢勤,惟恭奉币、用供王,能祈天永命。
召公将自己的位置定得十分准确,对于当政称王的周公尊重有加。在周初十分复杂而严峻的政治形势下,召公的支持不仅对于周公特别重要,而且也表现了召公作为一位政治家应有的品质和气度。
第二,召公强调治理天下必须敬德保民。夏商两国皆因为不敬德而导致灭亡(“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所以建议周公汲取历史的经验,“疾敬德”。所谓“德”(注:关于德的内涵,郭沫若先生曾经指出,“德字照字面上看来是从植(古直字)从心,意思是把心思放端正,便是《大学》上所说的‘欲修其身先正其心’;但从《周书》和‘周彝’看来,德字不仅包括着主观方面的修养,同时也包括着客观方面的规格——后人所谓‘礼’”(《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1卷第337页,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指人的内心德操、精神境界。有德者,就是高尚之人,在处理人际关系中能够关心他人,为大家服务,此即《召诰》篇所说的“丕能諴于小民”、“用顾畏于民碞”之意。所以对于政治家来说“敬德”与保民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据说周文王就是典型的德操高尚的楷模。殷人不讲“德”这个概念,周人之所以大讲特讲“德”,是反思商周之际鼎革变迁的结果,是针对“敬天”思想而提出的。周人认为只有德操高尚才能够赢得天的眷顾与信任。本来,“敬德”是周公讲滥了的一个命题,召公重新提及并没有什么新意。召公讲敬德的目的只是在于表示自己对于周公“敬德”思想的拥护,表明他与周公保持一致(注:周公初当政称王之时,召公曾经不大理解,所以古书上说“武王既终,成王幼弱,周公摄天子之政。邵公不悦,四国流言”(《列子·杨朱》);《书序》亦云“召公不说,作《君奭》”,周公尽全力争取召的支持而完成了东征平叛等伟业。《召诰》之辞表明在周公当政的第五年,召公对于周公的态度已经完全转变,这对于周初政局的稳定是至关重要的事情。)。
孔子对于周公尊崇有加,赞许“周公成文武之德”(《礼记·中庸》),称赞“周公之才之美”(《论语·泰伯》)。他在晚年还曾慨叹:“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论语·述而》)召公既然是助周公完成伟业的关键人物,孔子赞美召公亦在情理中事。《诗论》之重视《甘棠》的道理,正在于此。
然而,孔子于此还与其宗法观念有一定的关系。宗法制度与宗法观念是随着周代分封制的发展而行用和完善的,如《仪礼》所反映的那样系统而完备的宗法系统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事情。这个过程大约经过了从周初到春秋这样二三百年的时间。孔子对于宗法的态度比较复杂。大略来说,孔子一方面肯定作为宗法制关键的嫡长子继承制的重要;另一方面他又不将嫡长子继承制绝对化,而是采取融通态度。例如《礼记·檀弓》篇和《孔子家语·曲礼子贡问》篇皆记载如下一个事情:
公仪仲子之丧,擅弓免焉。仲子舍其孙而立其子。檀弓曰:“何居?我未之前闻也。”趋而就子服伯子於门右,曰:“仲子舍其孙而立其子,何也?”伯子曰:“仲子亦犹行古之道也。昔者文王舍伯邑考[之子]而立武王,微子舍其孙腯而立衍也。夫仲子亦犹行古之道也。”子游问诸孔子。孔子曰:“否,立孙。”(注:引文中方括号内“之子”二字,据清儒崔东璧说补,见《崔东璧遗书·丰镐考信录》卷二。)
按照孔子所理解的“古之道”,应当立嫡,而不立庶;若无嫡子,即当立嫡孙。这显然是合乎周代宗法精神下的嫡庶之辨的说法。然而,实际上,周族在周公之前并没有严格的宗法观念,周族历史上,季历、文王、武王、周公皆非嫡长子而继位,而这些人物多为孔子特别尊敬。如果拘执于嫡长子继位的宗法精神,显然与对于这些孔子心目中的圣人的评价无法吻合,所以孔子又强调“功德”,而不着眼于嫡庶之辨。本文前引《孔丛子》和《孔子家语》的材料足可为证。在孔子看来,只要有功德于国于民,其行事可以不必过分拘泥,周公当政称王和召公被奉为“列祖”而被祭祀,皆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总之,上博简《诗论》特别重视《甘棠》一诗的事实,表明了孔子对于召公的重视和肯定。我们由此出发而分析召公史事及《尚书·召诰》的性质问题,又涉及到了孔子宗法观念的复杂性质。由此我们也可以从一个角度看到孔子人文精神的一个重要方面,那就是他完全以国家、民众的利益而转移,并不拘泥和偏执。孔子虽然十分重视体现宗法精神的祭礼,但并不拘泥于嫡庶之辨与昭穆之别。《诗论》简文所表现出的他对于召公奭的特别重视,就是一个明证。
收稿日期:2003-06-20
标签:甘棠论文; 孔子家语论文; 孔子论文; 韩诗外传论文; 国学论文; 周公论文; 白虎通论文; 绿衣论文; 儒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