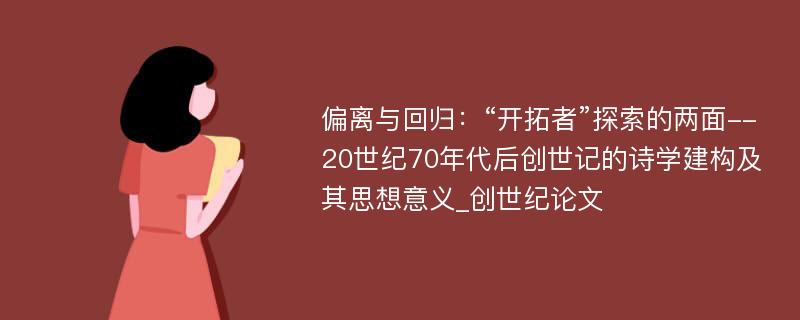
背离与回归:“先锋”探索的一体两面——20世纪70年代后《创世纪》的诗论建构及其思想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先锋论文,创世纪论文,两面论文,意义论文,年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经历了20世纪60年代狂飙突进式的“超现实主义”发展期后,《创世纪》诗刊经过短暂的调整,在复刊号中将未来的发展路向确定为:“在批判与吸收了中西文学传统之后,将努力于一种新的民族风格之塑造”①,并在七十年代后积极倡导“融合现代与传统”的新诗现代性道路。不过,尽管“超现实”时期在《创世纪》60年的发展史上仅仅占据了六分之一强的比重,而且那也是诗坛内外争议颇多的一个时期,但“超现实”时期的《创世纪》还是以巨大的光环效应使其之前之后的诗艺探索显得黯然失色。值得注意的是,“超现实”显然不能涵括《创世纪》诗人们的全部诗学特质,而且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创世纪》诗人们也曾不断地修正他们的“超现实”观念;那么,在历史视域中重新审视《创世纪》的发展历程,我们究竟应该如何认识“超现实之后”《创世纪》的理论建树及其文化价值,就是一个有必要深入探究的问题,它不仅能够重现历史现场,也在方法论意义上对当下的文化建设具有借鉴价值。 “超现实”之后:《创世纪》的文学史命运 大陆出版的文学史中,谈及20世纪50年代以后台湾文学的发展特色,都会重点评介《现代诗》《蓝星》和《创世纪》在推动现代主义诗歌运动中的诗学主张及其创作实践。讨论重点侧重思潮流派发展脉络的梳理,或是评述相关文学论争的观点,品鉴代表性诗人诗作的特征。与此相应地,同《创世纪》相关的部分,大多是浓墨重彩地评介其对超现实主义的接受与写作试验,同时作为诗艺探索发生转折的前提,提及《创世纪》早期“新民族诗型”的口号及其局限,而对其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诗论建树及创作转型则语焉不详。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些文学史著,如白少帆、王玉斌等主编的《现代台湾文学史》,吕正惠、赵遐秋主编的《台湾新文学思潮史纲》②等,都采取依照时序与文类,在某一时期中选取最突出的“文学事件”来描述文学史面貌的写作策略,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台湾文坛,自然是要由现代主义与乡土文学思潮平分秋色,因此对“超现实”之后《创世纪》诗人的观念转型只能给予少量篇幅的观照,难免给人繁华过后,归于沉寂的印象。 文学史写作近似大浪淘沙,而且受历史观、美学观等因素影响,文学历史的版图不断地被研究者以做“加法”或“减法”的方式进行修正,因此,如此呈现《创世纪》在台湾现代诗发展中的历史位置,也是著述者的一种历史态度。不过,当鲜活饱满的历史样态被挤进历史叙事的轨道,为适应轨迹的需要而不得不做出某些取舍时,我们还是需要对那个塑造过程保持反省的能力,因为“文学史叙述的症结之一就在于常常会将历史事实进行趋于本质化的概括,当我们试图梳理出一条清晰的历史发展脉络时,注定会因对共性的统筹性考察而忽略或遮蔽了某些个性化的探求。”③针对《创世纪》的研究状况,台湾研究者解昆桦也曾提出如此疑虑:“检阅目前数量庞大的《创世纪》研究论述,却可发现其中确实‘累积’了不少问题”,而其中之一便是“对《创世纪》‘超现实’的刻板印象挥之不去……其中症结点在于论者对《创世纪》20世纪70年代以来之诗社史的认识不足。”④他分析问题起因,认为“这或许是因为《创世纪》诗社所累积的资料太过庞大,使得相关论者在诗史论述上,往往以对《创世纪》概括式的刻板印象,便宜为之。连带使得当前《创世纪》诗社的研究,始终难以切中其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发展的事实。”⑤这的确是赋予洞见的思考。 不过,对于大陆研究者来说,很多时候在文学史叙述中的取舍决断却不是因为“资料太过庞大”,而恰恰是受政治因素影响造成的资料短缺。曾有文学史在论及《创世纪》诗人群时,尝试评判《创世纪》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诗学特征,如王晋民主编的《台湾当代文学史》,列专章概述了“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并列专节讨论“现代主义的第一个浪潮——现代诗运动”和“对台湾现代主义的历史评价”。考虑到此前两岸文化交流受政治历史因素影响,在资料信息渠道方面有诸多不便,著者特别详尽地引用了纪弦《现代派信条释义》和洛夫的《超现实主义与中国现代诗》两篇文章,并评价说:“《创世纪》初期提倡‘新民族诗型’。……但是,从第11期开始,《创世纪》却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高高地举起现代主义的旗帜,而且青出于蓝胜于蓝,公开地提倡和引进超现实主义。”⑥继而从思潮溯源、哲学背景和写作技巧等方面对洛夫的超现实主义诗观进行了详细评价。虽然在讨论20世纪70年代以后台湾文坛的面貌时,论述重心也转向乡土小说论战,但在后面专论《洛夫诗歌》的一章中,刻意增加了一节:《从“超现实主义”到“回归传统,拥抱现代”——洛夫的诗论》,从“接近自然”“学习‘静观’”“境界”等几个层面,阐述洛夫诗论同传统精神的相通之处,是尝试补充“超现实”之后《创世纪》诗人写作面貌的一种努力,可惜立论主要依据洛夫的《诗人之镜》《超现实主义与中国现代诗》和《回归传统,拥抱现代》等几篇理论文章阐发而成,未能透彻阐明所谓回归以后的“传统”——“已经是在‘现代’基础上的传统”⑦——究竟提供了哪些新的诗学质素?概因资料受限,未能给阐释者提供更多的考察空间。 比较而言,台湾的一些研究者因为曾见证现代诗的发展历程,在做史论时能够持有历史整体观的视野,如萧萧的文章《创世纪风云——为文学史做证·为现代诗传灯》⑧,用“《创世纪》年轻时的气质”“‘新民族诗型’的初议与检讨”“《创世纪》的性格”“草来初辟,繁花旋生”和“‘绿荫时期’的作为”“《创世纪》走进八十年代”等概述界定《创世纪》不同时期的历史特征,将“超现实”之后的《创世纪》界定为“绿荫时期”,是形象并具有历史感的观察;时隔十年之后,他在另一篇文章《〈创世纪〉风格与理论之演变——“新民族诗型”与“大中国诗观”之检讨》⑨中,将《创世纪》八十年代以后的诗论观点进行历史脉络的追溯和比较研究,是对此前研究的一种丰富和补充。杨宗翰在《台湾新诗史:书写的构图》一文中,辨析了文学史书写中面临的三个层次(文学实践史、文学史实践、文学史学)之间的关系,强调“任一部文学史(书写)要达到真正的可能,唯有先清理掉以下三个怪兽:民族国家、演化/目的论、起源迷恋”⑩,主张“把历史还原为文学本身”,“入史的准则——1.创新2.典型3.影响”(11),据此原则开列的台湾新诗史书写构图中,洛夫等人的创作被分别置于不同的历史时段中,以呈现其创作的变化及动态连续性。如此布局谋篇,当然也是为反拨文学史书写中对作家的评介重前期轻后期、顾此失彼等问题。上述两位研究者都有追踪研究台湾现代诗的经验,所提问题可谓切中肯綮,但要把设想融入具体的文学史写作实践中,显然还需要诗歌研究者们做更多的工作。 在阐释中成长的“传统”观 处在被阐释话语场中的《创世纪》诗人,如何评价和定位“超现实”之后的《创世纪》呢?其20世纪70年代以后所倡导的“现代诗归宗”理念,究竟是浪子回头意义上的迷途知返?还是繁华过后,重新出发的自主选择? 作为《创世纪》主创人之一和诗刊理论路向的重要阐释者,洛夫曾在不同的文章中谈到他对《创世纪》发展历程的评价。在《台湾现代诗的发展与风格演变》一文中,他这样谈道:“70年代在经过对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反思辩证之后,他们(《创世纪》)全力追求一种融合中国人文质素和现代精神的诗歌,但并不放弃创新求变的立场,因而为具有原创力的诗人提供一个创作实验室,历年来培植诗坛新人甚多。”(12)在另一篇文章中,他回顾《创世纪》50年的行进步履,也饱含深情地写道:“传统是智慧与时间的累积,实际上传统也就是历史,对一个像《创世纪》这样的诗刊而言,更是一段从走过荆棘,突破困境,响应改革,力主创新,以至渐趋成熟的求索过程。”(13)在他的描述中使用了“创新求变”“渐趋成熟”等评价语言,显然并未将“超现实时期”与“超现实之后”做断裂式的理解,对于将生命融入现代诗写作的《创世纪》诗人们来说,在诗艺探索的道路上他们从未停滞,从“新民族诗型”到“超现实主义”再到“现代诗归宗”,以及建立“大中国诗观”的提出,《创世纪》诗人们更愿意把方向的调整视为是诗歌观念“成长”的一个过程,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有必要认真审视“超现实”之后《创世纪》的诗论主张。 如果以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看待中外文化的关系,我们很容易将《创世纪》从“超现实主义”到“回归传统”的转型看作是一种对抗性关系的变化,而忽略了两者之间相生相克、互为促进的过程。事实上,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政治集权专治的文化场域中,借鉴西方或依托传统都是现代诗人们处理自身精神诉求与外部世界冲突的方式。标举“传统”的口号,有时并不是“复古”,却恰恰是“先锋”意识的一种呈现。《创世纪》创刊之初,在理论上尝试建树“新民族诗型”观念,意欲矫正纪弦在《现代派的信条》中提出的“新诗乃是横的移植,而非纵的继承”的偏向。“新民族诗型”强调的是“新”的“民族诗型”(14),洛夫以“艺术的——非纯理性之阐发,亦非纯情绪之直陈,而是美学上的直觉的意象的表现”,和“中国风,东方味的——运用中国语文之独特性,以表现东方民族生活之特有情趣”等阐发来界定“新民族诗型”的内涵,借以反思当时现代诗创作中出现的“泥古不化的纵的继承”和“移花接木式的横的移植之说”(15),实际是表达了一种站在潮流之外的冷静立场。 也是在求“新”的追求中,对当时而言极具先锋色彩的“超现实主义”思潮进入《创世纪》诗人的视野。“新”的“民族诗型”理论重在诗歌艺术形式的探索,而20世纪60年代提出“世界性”“超现实”“独创性”与“纯粹性”口号,则是冀望在新诗现代化的路程中,超越单纯以抗衡为目的的“破坏”,能够有所建树。洛夫在《六十年代诗选》“绪言”中论及对现代主义本质精神及形式技巧等问题的认识:“在现代主义实验阶段已渐趋尾声的今天,作为一个前卫艺术家的职责并非仅在消极地反传统,而是要创造更新的现代精神与秩序”,并从现代新诗的特质阐发说:“以作为中国现代文学艺术主流的新诗来说,它的胜利并非表现在它本身已获得事实上若干的承认上,而是它已逼着人们日渐对它的需要性加以重视,因它正在提醒人类重新认识自己,并如何使他们与包围他们周遭的外界取得新的适应。”(16)“我们深信,只要是一个了解自由意志与纯粹性在诗中的重要性的评论家或文学史家,他对于目前现代诗人所做的由破坏到建设的工作,必将予以严密的考察与慎重的评断。”(17)不能不承认,当“现代派”“蓝星”在现代主义潮流中日渐式微时,是《创世纪》诗人通过对20世纪50年代以来台湾现代诗的历史性检视,倡导“一种新的、革命的、超传统的现代意义”的新诗路向,将台湾现代诗的“先锋”实验延续了下去。 值得庆幸的是,即便在“超现实主义”创作开展得风生水起之际,《创世纪》诗人们也没有丧失自我反省的能力。《创世纪》第19期曾刊发香港同仁李英豪的文章《剖论中国现代诗的几个问题》,直陈现代诗的发展状况和症结性问题。他敏锐地意识到“近一年来的现代诗坛,显得有一种拖拖沓沓的现象,好像经过了几百米的赛跑后,已开始暗暗露出些儿‘疲态’”(18),探究其中的原因,他认为现代诗的“负荷”不是存在于外在,而在于内在本身。他从现代诗人内在的问题入手进行思考,提出一种现象:在追求前卫诗学的实践中,“现代诗人都经过一种无形的蜕变:从‘创造的我’蜕变到‘以我为中心的自我’。”这种主观意识的蜕变,落实在创作中则导致诗作从表现“创造的情绪”演变为注重表现“野蛮的主观的情绪”,因此而导致现代诗“在陷于低潮的过渡期间,蒙受了双重病害的侵寇:一为‘情绪至上论’:一为浅薄的知性主义……前者全凭情绪所支配,盲目追求兽性情绪的传达,湮没了取代了‘知性’的创造力和诗的直觉的纯粹性。后者重新跌入空洞的结构,由于过重造型的外貌和推理的方法,使诗变成失去感性的颓败躯体,甚至在文字方面玩把戏,形成堆砌或形式至上。”(19)事实上,在此前后诗社中的同仁商禽和季红都曾对现代诗发展中暴露出来的问题提出质疑,因此,即便是20世纪70年代没有政治历史等外部因素的促动,《创世纪》的诗学转型也必然会发生。 1972年9月,《创世纪》在休刊三年之后复刊。由洛夫执笔的复刊词《一颗不死的麦子》重新提出“将努力于一种新的民族风格之塑造”(20)问题。文坛内外多以“回归传统”视之,但何为“传统”、如何“回归”仍有待进一步的思考。洛夫随后在另一篇文章中表达了自己对“回归性偏误”的反思:“严格说来,我们的现代诗今天仍处于一个探索方向,塑造风格的实验与创造时期”,“无论如何,回到民族文学传统的浩浩长河中来,是一个诗人必然的归向”,但是“什么是民族性的诗”“非写‘长安洛阳’、‘古渡夕阳’不足以言中国,凡写登陆月球,巴黎铁塔,或西贡战争一概目如西化,这是我们批评界最流行而肤浅的看法。这种文学中的狭隘民族意识讲究的是魂游故国,心怀唐宋,尤其重视地域性……但一个诗人的民族意识应是全面的,时空融会,古今贯穿的整体意识。”(21)这些气势凌厉的论述显示出他在诗学观念反思中的思考,也呈现出超越同时代更多的泛泛而论者的思想深度。他反对携古语以自持、盲目复古的应景之作,“某些诗人为了刻意表示继承古典诗的余韵,凡写景必小桥栏杆,写物必风花雪月,写情则不免伤春悲秋,其遣词用句多为陈腔滥调,写出来的都是语体的旧诗,我则直指为‘假古典主义’”(22)。 对洛夫等《创世纪》诗人来说,在探索新诗现代性的进程中,无论是背离传统,还是回归传统,都同他们不肯随同流俗,决意引领时代潮流的先锋意识有关,背离与回归实为先锋探索的一体两面。正如有研究者指出的那样:“反思的现代性如果能自身包含文化寻根的需求与滋养作用,那么如何有效地开发利用文化之根的资源去为现代社会纠偏补缺,就成为最现实的课题。”(23)在大历史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单纯的背离与单纯的回归并无太大意义,问题的关键在于破坏、消解中的重建。对传统的重估,将超现实主义中国化,并探求用“超现实主义手法来表现中国古典诗中‘妙悟’,‘无理而妙’的独特美学观念的实验”(24),最终为彷徨于前路的台湾现代诗找寻到新的方向。基于此种情况,洛夫曾将《创世纪》对台湾新诗的影响概括为两点:“追求诗的独创性,重塑诗语言的秩序”和“对现代汉诗理论和批评的探索与建构”。关于后者,他特别强调了在民族与西方、现代与传统之间进行调适的必要性,“不错,‘民族’是我们的基调,但‘新’是指什么?……原来就是长时期地涉足西方现代主义,继而又长时期地对中国古典诗学做深层次的探索,然后通过审慎的选择,进而使两者做有机性的调适与整合,终而完成一个现代融合传统,中国接轨西方的全新的诗学建构。”(25)这一看似刻板中庸的论断,却是台湾现代诗人们在被迫承受文化失根之痛的历史语境中,以大胆的叛逆精神艰苦实践得来。它不仅对20世纪70年代以后台湾现代诗的发展具有引导作用,对80年代以后祖国大陆文学面临现代主义与文化寻根思潮激荡中的价值判断也具有启示意义。 “世界”文化格局中民族性转向的价值启示 在很大程度上,取火于西方“超现实主义”的诗学实验,不仅帮助《创世纪》诗人实现了对诗歌“审美现代性”的追求,也在时空观念上打开了诗人的视野,使他们获得了世界性眼光与胸襟。当《创世纪》打出“世界性”“超现实”“独创性”与“纯粹性”口号时,“世界性”并不仅仅是对应于“民族诗型”的一个概念,它更是对文化时空与世界格局的一种体认。 近代以来,被迫承受欧风美雨文化洗礼的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时常会陷入东西方文化对峙的困境中,被喻为“世界”的“西方”既是我们图强求变、开启民智的思想溯源地,也常常是造成民族文化被异化乃至处于边缘化境地的罪魁祸首。原本是“世界”空间之一员的“中国”,却总是让人产生“自外于世界”的感受,因此“走向世界”成为一个具有目标感召力的口号,并且因为恐惧被“强大”的世界所吞噬,反而更固守“民族”特色,使世界与民族的关系成为难解的问题。应当看到,在政治视野中强调民族与世界的边界是一种客观需要,但在文化领域却恰恰需要突破隔阂,将民族性与世界性有机融合。“在人类文化观之下,没有异己文化,都属于自己的文化,文化的时间性(传统与现代)、文化的空间性(民族与地域),都具有新的意义。”(26)处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历史场域中的台湾现代诗人,因为政治因素的制约被动地疏离了中国新文学传统,在“别求新声于异邦”的探索中与“超现实主义”相遇,激发了他们诗艺创新的灵感,60年代的《创世纪》大量刊登译介西方文学思潮的文章,艾略特、里尔克、保罗·梵乐希等人的诗论及创作,为他们示范了如何将个人苦痛提升为对人类命运的思考,他们通过汲取世界文化中的优秀质素而使自己获得了世界性意识。我们注意到,在东西方文化的巡礼中,痖弦由对现实的反思进入具有普泛意义的人类命运的思考,他以内涵复杂的“深渊”意象表达自己的认识,尝试“说出生存期间的一切,世界终极学,爱与死,追求与幻灭,生命的全部悸动、焦虑、空洞和悲哀”(27),其诗作在台湾文坛受到普遍好评,张默评价其诗的特点是“有其戏剧性,也有其思想性,有其乡土性,也有其世界性”(28),事实上,这也是《创世纪》代表诗人普遍具有的写作特征。“作为一个心理过程,一种特殊的思维方式,文学想象与一个作家内在的生理心理机制有关,也与该作家的人生经历,以及他所处时代的社会现实、社会风尚有关。”(29)在探索现代新诗审美现代性的过程中,尽管存在诸多争议,但《创世纪》诗人还是以引领诗歌风尚的创作,为中国传统诗歌的演进注入了新的富有活力的质素与风格。 在世界格局的意义上审视《创世纪》20世纪70年代以后向“传统”的回归,洛夫对“传统”意涵中包括的“民族意识”有所思考,他反对狭隘的民族意识,强调“一个诗人的民族意识应是全面的,时空融会,古今贯穿的整体意识”。(30)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大中国诗观”与“漂泊的天涯美学”的思想。“大中国诗观”意在倡导“消除狭隘的地域性、族群性的意识形态阴影”(31),使海峡两岸及海外华人的创作既能保留其精神上的独特性,又能在文化中国的意义上整合为完整的版图;而“漂泊的天涯美学”则着力于将个体性、民族性经验提升为具有世界意义的哲理境界,洛夫用“悲剧意识”和“宇宙境界”来描述“漂泊的天涯美学”的内涵,他认为:“广义地说,每个诗人本质上都是一个精神的浪子,心灵的漂泊者。”“我们已有很多优美的抒情诗和代表民间性的叙事诗,但诗人较少在捕捉形而上意象这方面去努力,以至他们的作品缺少哲学内涵和知性深度。这其中,是否沉溺于当下境遇,尚来不及去关照更大范围及世界性的问题?”因此,在创作长诗《漂木》时,他有意识地将其“定性为一种高蹈的、冷门的,富于超现实精神和形而上思维的精神史诗。诗中的‘漂泊者’也好,‘天涯沦落人’也罢,我要写的是他们那种寻找心灵的原乡而不可得的悲剧经验,所以我也称它为‘心灵的奥德赛’。”(32)真正伟大的作家和作品都是无国界的,正如艾略特所言:“任何一位在民族文学发展过程中能够代表一个时代的作家都应具备这两种特性——突发地表现出来的地方色彩和作品的自在的普遍意义”(33),因为有了世界性的视野,《创世纪》诗人在融会传统与现代的过程中表现出文化自信与主体自觉,而这恰恰是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在融入世界格局过程中最渴求的一种意识。 有研究者曾痛切地指出:“典律的缺席,形式范式机制的缺失,造成百年中国新诗的发展,越来越倚重于诗人个人才具的影响力和号召性,而非诗歌传统的导引。”(34)考察《创世纪》的诗路历程,至少我们可以说其在60年坚韧求新的发展过程中,始终秉持先锋意识,为建构现代诗的典律机制孜孜以求、筚路蓝缕,它的成功与偏误,在世界一体化趋势的今天,都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参考和示范价值。 注释: ①本社:《一颗不死的麦子》,《创世纪》第30期,1972年9月出版,第5页。 ②白少帆、王玉斌、张恒春、武治纯主编:《现代台湾文学史》,辽宁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吕正惠、赵遐秋主编:《台湾新文学思潮史纲》,昆仑出版社,2002年版。 ③白杨:《台湾现代诗风潮中的“痖弦”——论痖弦“新诗史料”整理工作的价值与意义》,《芒种》2013年第6期,第50页。 ④解昆桦:《隐匿的群星:八○年代后创世纪发展史与1950年世代诗人的新典律性》,《创世纪》第140-141期,2004年10月出版,第68页。 ⑤解昆桦:《隐匿的群星:八○年代后创世纪发展史与1950年世代诗人的新典律性》,《创世纪》第140-141期,2004年版,第68页。 ⑥⑦王晋民主编:《台湾当代文学史》,广西人民出版社、广西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53页,第536页。 ⑧萧萧:《创世纪风云——为文学史做证·为现代诗传灯》,《创世纪》第65期,1984年10月出版,第44-54页。 ⑨萧萧:《〈创世纪〉风格与理论之演变——“新民族诗型”与“大中国诗观”之检讨》,《创世纪》第100期,1994年9月出版。 ⑩(11)杨宗翰:《台湾新诗史:书写的构图》,《创世纪》第140-141期,2004年10月出版,第111页,第114页。 (12)洛夫:《台湾现代诗的发展与风格演变》,《台港与海外华文文学评论和研究》1995年第1期,第15页。 (13)(14)(22)(24)(25)洛夫:《创世纪的传统》,《创世纪》第140-141期,2004年版,第25页,第28页,第28-29页,第28页,第25、27、28页。 (15)本社:《建立新民族诗型之刍议》,《创世纪》第5期,1956年版,第3页。该文实际为洛夫执笔。 (16)(17)张默、痖弦主编:《六十年代诗选·绪言》,高雄大业书店,1961年版,第4页,第6页。 (18)(19)李英豪:《剖论中国现代诗的几个问题》,《创世纪》第19期,1963年出版,第24页,第24页。 (20)洛夫:《一颗不死的麦子》,《创世纪》第30期,1972年9月出版,第4页。 (21)洛夫:《请为中国诗坛保留一份纯净》,《创世纪》第37期,1974年7月出版,第7-8页。 (23)叶舒宪:《现代性危机与文化寻根》,山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219页。 (26)张福贵:《“活着”的鲁迅——鲁迅文化选择的当代意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180页。 (27)痖弦:《诗人手札》,《创世纪》第14期,1960年版,第14页。 (28)萧萧:《编者导言》,萧萧主编《诗儒的创造——痖弦诗作评论集》,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94年版,第2页。 (29)韩春燕:《文字里的村庄》,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37-38页。 (30)洛夫:《请为中国诗坛保留一份纯净》,《创世纪》第37期,1974年7月出版,第8页。 (31)(32)(34)沈奇、洛夫:《从“大中国诗观”到“天涯美学”——与洛夫对话录》,《沈奇诗学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260页,第262页,第268页。 (33)艾略特:《批评批评家》,《美国文学和美国语官》,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版,第57页。标签:创世纪论文; 中国文学史论文; 先锋文学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现代主义论文; 世界主义论文; 文学论文; 超现实主义论文; 艺术论文; 文化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中国当代文学论文; 现代诗论文; 诗歌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