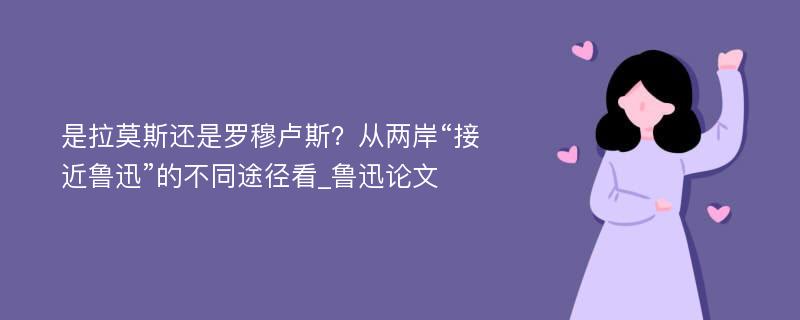
是莱谟斯,还是罗谟鲁斯?——从海峡两岸“走近鲁迅”的不同方式谈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鲁迅论文,海峡两岸论文,鲁斯论文,方式论文,是莱谟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英国有“说不完的莎士比亚”,中国则有“说不完的鲁迅”。有人把鲁迅封作“现代的圣人”,也有人把鲁迅比作“中国的高尔基”或“中国的伏尔泰”。在中国内部,还会听到“台湾的鲁迅”这样的说法。瞿秋白则说鲁迅是“莱谟斯,是野兽的奶汁所喂养大的”。但“野兽的奶汁”喂养大的不只是莱谟斯,还有他的兄弟罗谟鲁斯。不同的是,罗谟鲁斯建造了罗马城,最后还升天作了军神;而莱谟斯因敢于蔑视罗马城被自己的兄弟杀害了。1936年,好像有预感似的,鲁迅谈到了“死”和“死后”的话题。他说自己属于“随便党”,死后就“赶快收殓,埋掉,拉倒”(《死》);但他对庄子所谓“在上为乌鸢食,在下为蝼蚁食”大可随便的看法,却又似乎不以为然,说“假使我的血肉该喂动物,我情愿喂狮虎鹰隼,却一点也不给癞皮狗们吃”,因为“养肥了狮虎鹰隼,它们在天空,岩角,大漠,丛莽里是伟美的壮观,捕来放在动物园里,打死制成标本,也令人看了神旺,消去鄙吝的心”,然而若“养胖一群癞皮狗,只会乱钻,乱叫,可多么讨厌!”(《半夏小集》)鲁迅曾自称是“牛”,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不管从鲁迅那里“吃”了什么,也不管喝的是“狼奶”也好,“牛奶”也好,一代代人确实在鲁迅的喂养下成长了起来。半个多世纪以来,在中国,大概没有哪个作家像鲁迅那样获得过这样庞大、这样持久不衰的阅读群。但“同一种稻谷养百样人”,凡是“吃”过鲁迅的,有的确是狮虎鹰隼,有的却未必然。
无论如何,有了“吃”不尽的鲁迅,阅读和诠释鲁迅也就成了最富有挑战性的行为。在中国,曾像莱谟斯那样蔑视“罗马城”的鲁迅,死后却被罗谟鲁斯们建成了一个“罗马城”。“阅读”这种原本属于个人经验范畴的活动,演变成为了某种政治性的行为。我想生造“阅读政治学”这个词儿,来说明这种变化形成的原因。这本来与鲁迅没有什么关系,然而,从鲁迅生前到逝世以后,关于鲁迅的阅读史,构成了最为复杂的政治行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好像还没有哪一位作家的作品,像《鲁迅全集》那样有着最详尽的注释和索引,“鲁学”已经堪与“红学”并驾齐驱,这一点,不只说明鲁迅作品的“经典化”,也证明着阅读鲁迅也已“体制化”了。从鲁迅成为大学中文系的必读科目开始,鲁迅这位生前曾表示“我自己尚且寻不着头路,怎么指导别人”(1926年6月致李秉中信)的人,已成为莘莘学子博取学位的重要“靠山”。 说到“经典化”,我想到1925年2月10日, 鲁迅为“京报副刊”提供的“青年必读书”,“必读书”或者就是“经典”吧?鲁迅说他“从来没有留心过,所以现在说不出”。但又在附注里解释说,“中国书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华盖集》)这话即使放在今天,恐怕也仍然会伤害在名片上印着“导师”名号并倡导读中国经典的教授们的自尊心。其实,像鲁迅这样饱读中国书的人,真没有留心这个问题?据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载,鲁迅就曾为许先生的公子开列过一份书单,并做了简要的说解,他推荐的书目都是“中国书”,其中包括王充的《论衡》,刘义庆的《世说新语》,葛洪的《抱朴子外篇》等。鲁迅不愿在媒体开列“必读书”的意思,大略不过是:“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不是‘言’”。而阅读鲁迅,最初确是出于“行”的考虑,因为从他那里借点“狼奶”喝,确实令人“神旺”,但到后来,就越来越变成“言”的竞赛了。从海峡两岸的鲁迅阅读史,或者说,两岸知识者“走近鲁迅”的不同方式,是大概可以看见这样的演变的。
一
与鲁迅在大陆的情形相比,鲁迅在台湾是十分幸运的。这首先是因为鲁迅从未在台湾形成“钦定经典”,因而鲁迅才免于被神化的命运。在五十年代以后,鲁迅甚至被看作“左翼作家”的代表受到当局的禁读,因此,对鲁迅的阅读颇像二三十年代大陆的情景,更容易激发思想的活力。台湾知识界从日据时代“走近鲁迅”开始,就都出于“实用”的“启蒙主义”目的。正是在这一点上,台湾学者杨云萍认为当时的台湾知识者比大陆的更为理解鲁迅。他在《纪念鲁迅》一文中说:“我们纪念伟大人物,当然不是为满足我们个人的‘英雄崇拜欲’,更不是为假装纪念伟大人物,而来夸示我们是个伟大人物的‘理解者’。我们纪念伟大人物,当然是要继承那伟大人物的未竟之志,以尽后死者之责;以他们的决意为决意,以他们的勇气为勇气,以他们的憎恶为憎恶,以他们的行动为行动去实行,去干。不消说,我们的纪念鲁迅,也是如此!”杨云萍的文章写于鲁迅逝世十周年前一日。当时台湾刚光复后不久,台湾文化界新成立的“台湾文化协进会”于1946年9 月创办了《台湾文化》杂志,这是两岸因内战而分裂之前,由两岸知识分子共同耕耘的刊物,因此弥足珍贵。该杂志创刊伊始,就在第二期刊出“鲁迅逝世十周年特辑”。这是台湾首次也是最后一次用“特辑”的形式纪念鲁迅。这个特辑除了杨云萍的文章,还发表了许寿裳的《鲁迅的精神》,高歌翻译的《斯沫特莱记鲁迅》,陈烟桥的《鲁迅先生与中国新兴木刻艺术》,田汉的《漫忆鲁迅先生》,黄荣灿的《他是中国的第一位新思想家》以及雷石榆《在台湾首次纪念鲁迅先生感言》等文章,此外还刊登了鲁迅的最后一张相片,那是1936年10月8 日鲁迅在上海第二次全国木刻展览会中与青年木刻家们坐在一起亲密聊天的情景。特辑还特意将鲁迅的笔迹,鲁迅旧诗,鲁迅曾编辑出版的珂勒惠支的木刻《牺牲》,也一并刊出,以增加鲁迅的实感。鲁迅曾引用罗曼·罗兰的话说,珂勒惠支的作品“是现代德国的最伟大的诗歌,它照出穷人与平民的困苦和悲痛。这有丈夫气概的妇人,用了阴郁和纤秾的同情,把这些收在她的眼中,她的慈母的腕里了,这是做了牺牲的人民的沉默的声音”。对于曾沦落在日本手里五十年的台湾人民而言,当最能理解这些话所传达的苦痛吧。为此杨云萍特别谈到了鲁迅对台湾二十年代“启蒙运动”的巨大影响,《阿Q正传》就是那时(1925)转载在《台湾民报》上, 杨云萍写道:“现在我们还记忆着我们那时的兴奋。其一原因,是因为我们当时的处境;其另一原因,是因为当时的本省青年,多以日文为媒介,得和世界的最高的文学和思想相接触,获得相当程度的批判力和鉴赏力;所以对鲁迅先生的真价,比较当时的我国国内的大部分的人们,是比较的正确的切实的。”这个纪念特辑,是战后台湾走近鲁迅的特殊方式。当时他们已经感觉到台湾光复后面临的危机,因而也相信,鲁迅如果地下有知,一方面必为台湾光复而欣慰,另一方面也为光复后的政治黑暗而“变为哀痛”,“变为悲愤”了。果然,五个月后,台湾爆发了二二八事变,台湾由此进入五十年代的冷战架构下的“白色恐怖”时代,再一年之后,在台湾传播鲁迅最力的许寿裳被杀身亡,台湾知识分子对鲁迅的纪念,转入了地下,转入了内心。
在鲁迅生前,台湾就曾有许多人,特别是青年人,用种种方式试图“走近鲁迅”:阅读他的著作,慕名拜访,写信求教,从他身上吸取灵感和思想的力量,用于当时的启蒙运动的实践。与鲁迅接触的台湾青年,曾想方设法让鲁迅了解日据下的台湾的真实情况。《阿Q 正传》转载于启蒙主义报纸《台湾民报》后不久,在台湾发起“新文学运动”的主要健将张我军就到北京拜访了鲁迅,并将《台湾民报》四本送给了鲁迅(见1926年8月11日《鲁迅日记》)。1927年4月11日,鲁迅在广州为台湾青年张秀哲翻译的《劳动问题》作序,即提到他在北京遇见张我军(误写为“张我权”)时的情形,鲁迅写他当时听到张我军说“中国人似乎都忘了台湾了,谁也不大提起”时心里的痛苦:“我当时就像受了创痛似的,有点苦楚;但口上却道:‘不。那倒不至于的。只因为本国太破烂,内忧外患,非常之多,自顾不暇了,所以只能将台湾这些事情暂且放下。……’但正在困苦中的台湾的青年,却并不将中国的事情暂且放下。他们常常希望中国革命的成功,赞助中国的改革,总想尽点力,于中国的现在和将来有所裨益,即使是自己还在做学生。”鲁迅与台湾青年的相遇 , 从一开始即由启蒙与改革这些严肃的大问题联系起来。1934年,带有左翼色彩的《台湾文艺》曾用四期连载增田涉的《鲁迅传》,这是鲁迅生前就见诸台湾媒体的较早的鲁迅生平介绍。鲁迅于1936年10月去世后,杨逵主编的《台湾新文学》11月号立即刊登了两篇用日文写的悼念文章,其一是杨逵执笔的卷首语《悼念鲁迅》,左翼的杨逵将鲁迅与高尔基并列,提到蒋介石统治下中国知识分子苦斗的艰辛;其二是黄得时写的《大文豪鲁迅逝世》,回忆了他在东京开始接触鲁迅著作的经过,介绍了鲁迅文学生涯和主要作品。这是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前夕台湾最后一次介绍鲁迅。
五十年代以后,台湾文坛全面禁止阅读“鲁匪迅”的著作。然而,鲁迅仍然是有社会主义倾向的知识者吸取养料的思想资源。陈映真曾提到鲁迅的小说集《呐喊》所给予他的影响:“随着年岁的增长,这本破旧的小说集,终于成了我最亲切、最深刻的教师。我于是才知道了中国的贫穷、的愚昧、的落后,而这中国就是我的;我于是也知道:应该全心全意去爱这样的中国——苦难的母亲,而当每一个中国的儿女都能起而为中国的自由和新生献上自己,中国就充满了无限的希望和光明的前途。”他认为鲁迅的小说集使他成为一个“充满信心、理解的、且不激越的爱国者”,鲁迅使他获得了“免疫力”:“鲁迅给我的影响是命运性的。在文字上,他的语言、思考,给我很大影响。然而,我仍然认为鲁迅在艺术和思想上的成就,至今没有一位中国作家赶得上他。鲁迅的另一个影响是我对中国的认同。从鲁迅的文字,我理解了现代的、苦难的中国。和我同辈的一小部分人现在有分离主义倾向。我得以自然地免于这个‘疾病’,鲁迅是一个重要因素。”鲁迅是伟大的,鲁迅也是不易学的。学鲁迅而不得,容易失其温厚,流于刻薄。而陈映真的慧心独具之处,恰恰是他看到了鲁迅那最不易学的温厚。在创作与思想上受鲁迅影响的还不只陈映真,曾获台湾文学大奖的黄春明,他的塑造的人物,如《锣》里的憨钦仔,就被有的论者称为“台湾的阿Q”。 鲁迅的影响其实并非只在这些细枝末节上,而是融汇在他的“托尔斯泰”与“伏尔泰”精神上。
在台湾,虽然有权力的压制与阻挠,但知识者与鲁迅之间,在精神的联系上,的确是紧密而未曾间断的。对鲁迅的阅读,构成了一种民间的思想资源和“在野”的力量,因而也可以说鲁迅精神得到了“复活”。鲁迅原是属于旷野的。也许只有在现在,当所谓的“报禁”被解除,人们不再因言论获罪之后,鲁迅的自由精神才会转移到对当代社会文化的审视与批判上,而稍稍淡化它在现实政治中的“制衡”作用。
二
在大陆,由于鲁迅曾一度成为钦定的经典,对他的解读便呈现比较复杂的情形。一方面,“鲁学”获得了“合法性”;另一方面,如何在“语境”相似的状况下,对鲁迅“文本”固有的批判力量进行转移,又成为一个问题。鲁迅对“资产阶级”、“正人君子”的批判自然没有问题,何况他们有的早已“迁移”到了台湾;鲁迅对已经在掌权的当年左翼翘楚如周扬等人的批评,又当如何处置?一方面,鲁迅因有毛泽东的高度评价而身价百倍,结果很自然地也被“神化”了,以至于后来的人评价曹聚仁的《鲁迅评传》时,最看重的似乎就是他的“平视鲁迅”的态度。另一方面,“鲁学”因为牵扯到不少敏感人事关系而被政治所利用。权力的介入,使人们在阅读鲁迅时,失去了平常心。结果,“鲁迅圣殿”造成了,而被供的鲁迅塑像因过于完美而显得冷漠,失去了生气。“走近鲁迅”问题的提出,仿佛就暗示了我们已“远离”鲁迅。为什么当鲁迅著作不再是“禁书”,而变为纳入体制的不可质疑的经典后,反而令人产生“鲁迅已死”的感觉?
其实鲁迅早就知道,人一旦上了“庙堂”,文字便无足取。在写给台静农的信谈及诺贝尔文学奖的事时,他说:“我眼前所见的依然黑暗,有些疲倦,有些颓唐,此后能否创作,尚在不可知之数。倘这事成功而从此不再动笔,对不起人;倘再写,也许变了翰林文字,一无可观了。还是照旧的没有名誉而穷之为好罢。”(1927年9 月)原本就习惯于在野地里游走彷徨,反而能从容面对国民党权力的压制,在压力下他能像安泰匍匐在大地上,获得极大的力量。事实上,后来被抬上神坛的鲁迅,他的野气,他的活力,确实在频繁的仪式性的诠释和诵读当中,被悄悄地“瓦解”了。鲁迅1932年11月7日写给增田涉的信中, 曾谈到把他的著作翻译为日文的井上红梅,实际上与他“并不同道”:“井上红梅翻译拙作,我感到意外,他和我并不同道。但从译书上说,也是无可如何。看到他以前的大作《酒、鸦片、麻将》,令人慨叹。然书已译出,只好如此。今日拜读《改造》刊登的广告,作者(指鲁迅本人)被吹得很了不起,也可慨叹。你写的《某君传》(指《鲁迅传》)也成了广告课题,世上事总是那么微妙”。以鲁迅的敏锐,对这类借机“炒作”之背后种种,是相当清楚的。
我们这一代是在“文革”中与鲁迅“相遇”的。凡是成长于“文革”的人们大抵都有过早晚读毛著的经验,甚至在购物、过马路等非常普通的生活里,都要靠背诵领袖语录来当作必要的“签证手续”,使得阅读毛著成为日常生活中最重要的“仪式”。领袖像,“红宝书”,“红袖章”,革命歌曲《东方红》与《大海航行靠舵手》,是使这种“仪式”显得神圣并产生“快感”的必要组成部分。在这种情形下,经过领袖褒扬的鲁迅,也就连带具有了“神圣性”、“经典性”,很自然地成为政治性的“阅读体制”里的重要部分。鲁迅的平头,深自凝视的目光,很“酷”的面孔,配上黑体字的毛主席“三个家”的定论和总是被选入高中课文里的诸如《“友邦惊诧”论》、《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等杂文,渐渐构成了鲁迅的固定形象。在只能阅读鲁迅的年代,我们确实借助他才走近了五四时代,走近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文坛,但借助他的叙事,也只能窥见一群“资产阶级”的“正人君子”被当作“落水狗”痛打一顿的狼狈相。通过这种政治性的阅读,我们也不知不觉地在心里“参与”了建造“鲁迅圣殿”的工作。但当我们自以为在走近鲁迅时,鲁迅的面容却好像越来越模糊。我不只一次地听到有人假设:假如鲁迅仍然健在,他能否躲过“反右”、“文革”的惊涛骇浪?现在,我更听到另外一种假设:假如鲁迅仍然健在,他看到他的著作已成为大学中文系的必读经典,“鲁学殿堂”门口站着许多面目严峻的权威,一代学子精心制作的“敲门砖”都需要经过他们严格审核之后,才能确认能否盖章签证,不知他是喜是忧?
像我这样只能从相片上看到他的形象,又在“文革”的神化浪潮当中开始阅读鲁迅的人,也只有“文革”结束之后,才有过小心翼翼地“走近鲁迅”的经验:除了阅读他的文字,还想在他的伟大著作和平凡的“写真”中找到一种平衡,这位身材矮小,留着平头和日式胡子,爱抽烟,喜欢穿中式衣服的世界性文化伟人,说起方言来是什么样的?他讲“国语”时有什么口音?他走路的姿态,与亲戚或各类朋友聊天时的不同情景,在社交场合“应酬”与在家里放松的不同神态……是否如那些曾亲承謦欬的回忆文章所说的那样?为此我曾独自去绍兴这个“报仇雪恨之乡”,瞻仰大禹陵(有学者研究鲁迅深受大禹这样的实干家与墨家学说的影响),参观陆游的“沈园”、秋瑾的故居,然后走进鲁迅的三味书屋。听绍兴人讲的方言和普通话,到虚拟的“孔乙己”经常光临的“咸亨酒店”吃一两碟茴香豆,喝几两黄酒——这些细枝末节,看来都与鲁迅的“文本”(Texts)无关,也与“启蒙大义” 无关,但我却自以为是在用心去寻找和感受产生鲁迅文本的语境(Context ),我试图想象鲁迅作为一个“人”与他呼吸的空气,他生长的土地和人民的亲缘关系。对我来说,“走近鲁迅”,不仅是从字面上“解读”鲁迅,也是还原鲁迅“这个人”的“实感”从而深入他的内心的过程。
这种“走近鲁迅”的方式,纯粹是“个人”的阅读经验。我知道这与摆在台面上的阅读鲁迅的方式迥然不同。诚然,鲁迅著作之成为人们百看不厌的“经典”,恰由于鲁迅的写作从一开始带有“挑战”传统文化的启蒙主义姿态,因而阅读鲁迅,便必然地总是与批判中国社会现实、批判保守的文化心态、建设“新文化”、塑造新一代“真人”的心灵这样一些具有“启蒙”意义的大问题结合在一起。但当“权力”介入了阅读鲁迅的行为之后,在中国的特殊环境下,与其说是“走近鲁迅”,毋宁说是参与某种“集体仪式”,正如走进教堂,在牧师指导下领受某种“圣餐”。而当一种阅读行为变成“集体仪式”时,原本带有浓厚“个人性”的“阅读”就演变成“政治行为”,失去了它原有的意义和趣味。
鲁迅著作之“经典化”,本来是读书界自然选择的结果;而阅读鲁迅的“体制化”——半个世纪来已演化成为某种“集体仪式”——却似乎是“权力”介入的结果,后者才是最具有中国特色的。所谓的“权力”介入,有两个涵义。其一指的是在“权力”干预下的政治性阅读行为;其二指的是当某人被权力神圣化之后,他的作品也随之成为“钦定经典”而纳入体制,远的譬如孔子,近的则如鲁迅。当某人的著作被“权力”惦记上的时候,不是遭到禁毁的命运,就是被巧妙地收编,对他的作品的阅读诠释也因而成为“权力”运作的重要方式,简单地说,争夺“诠释权”和获取“敲门砖”,这两个方面是相互联系的。由于鲁迅在“文革”期间及以后基本上成为“权力解读”的唯一对象,因此,种种“走近鲁迅”的方式,其实都颇有点借鲁迅而获得权力(包括知识权力)而不是获取思想资源的意味。对鲁迅的解读,一方面当然说明了鲁迅对于批判中国旧文化意识、建设“现代人意识”的意义,另一方面,也展示了鲁迅被“利用”的过程。而一旦被利用,“走近鲁迅”似乎便不可能了。
三
《后汉书·马援列传》记载,伏波将军马援在交趾征战时,得知他的两个侄子马严马敦,颇喜讥议,又爱与侠客交游,特意给他们写了一封信,告诫他们“闻人过失,如闻父母之名:耳可得闻,口不可得言也”,不要“好论议人长短”。他特意用当时人龙伯高和杜季良做了比较:“龙伯高敦厚周慎,口无择言,谦约节俭,廉公有威。吾爱之重之,愿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侠好义,忧人之忧,乐人之乐,清浊无所失。父丧致客,数郡毕至。吾爱之重之,不愿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犹为谨敕之士,所谓刻鹄不成,尚类鹜者也。效季良不得,陷为天下轻薄子,所谓画虎不成,反类狗者也。”据说杜季良后来果然被仇人密告免官,而谨慎如马援者,虽然生前功高一时,死后却仍被人陷害,不得安葬,“故人莫敢吊会”。马援能“戒人之祸”,不可谓不智,却“不能自免于谗隙”。读史至此,常感心寒。因而也就常想到我最敬重的也是“颇喜讥议”的鲁迅。刘半农曾用“托尼精神,魏晋文章”来概括鲁迅。而人们所注意的,更多是鲁迅身上的“尼采”的味道,或者所谓旷野上的“狼”的气息。我却想,耶稣也曾在旷野沉思过的,但并非就一定有“狼”气。鲁迅的本根还是他所深涵的托尔斯泰的精神,这是阅读过《祝福》、《药》、《故乡》的人们都深有体会的。我的一些性情激愤的朋友常说,他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读了鲁迅。这理由当然不是太靠得住,但我也因此想到,如果要让我为自己的孩子选择应读的书,我当然要选鲁迅,但也必不愿他过早读鲁迅,而宁愿他先读《新约》或托尔斯泰。因为学耶稣与托尔斯泰不得,仍不失其温蔼,学鲁迅而不得,恐怕只落得“画虎不成反类狗”了。
其实,鲁迅早就知道他所感到的寂寞有很强的“传染性”。1924年9月24 日他在给认识不久的青年李秉中写信时就非常坦率地说:“我喜欢寂寞,又憎恶寂寞,所以有青年肯来访问我,很使我喜欢。但我说一句真话罢,这大约你未曾觉得的,就是这人如果以我为是,我便发生一种悲哀,怕他要陷入我一类的命运;倘若一见之后,觉得我非其族类,不复再来,我便知道他较我更有希望,十分放心了。”“我很憎恶我自己……我也常常想到自杀,也常想杀人,然而都不实行,我大约不是一个勇士。……我自己总觉得我的灵魂里有毒气和鬼气,我极憎恶他,想除去他,而不能。我虽然竭力遮蔽着,总还怕传染给别人,我之所以对于和我往来较多的人有时不免觉到悲哀者以此。”面对一个真的“走近”他的青年,鲁迅的这番话像是拒人门外,其实是肺腑之言。他对来人说,如果你“甘心传染,或不怕传染,或自信不至于被传染,那可以只管来,而且敲门也不必如此小心”。
鲁迅似乎很有预见性,否则就是他太了解中国的环境了。凡是传染上鲁迅的“寂寞”或“毒气和鬼气”的人们,大多是英特卓识之士,然而从他们后来的命运看,几乎很少有因为鲁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而终于能跑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幸福的度日”,“合理地做人”的。在大陆,曾经与鲁迅并肩战斗的瞿秋白,胡风,冯雪峰……下场都不是很好。在台湾,凡是感染上鲁迅的精神的,不是遇上牢狱之灾,就是四处碰壁。被称为“台湾新文学之父”和“台湾的鲁迅”的赖和,曾因反日两度入狱;在鲁迅去世时,最早在自己创办的《台湾新文学》杂志上刊发悼念鲁迅文章的杨逵,也曾因在1947年二二八事变后发表“和平宣言”而被捕入狱;自称深受鲁迅影响的陈映真,同样被投入国民党的牢狱达七年之久;即使背后曾有蒋经国做靠山,却从自由主义的立场接受鲁迅的柏杨,也难逃劫运……为什么“走近鲁迅”——不论是以何种方式——总是带来不幸?
实际上,在某些现实条件下,从来就无法在纯粹个人经验的层面上去阅读与谈论鲁迅。因此一谈鲁迅,必然触及敏感的权力关系。因而不论是压制也好,崇仰也好,只要进入“阅读政治”体制的魔圈,鲁迅的效应就产生了。鲁迅的老师章太炎在谈到孔子时,曾引用日人远藤隆吉在其《支那哲学史》中的话说:“孔子之处于支那,实支那之祸本也。夫差第《韶》、《武》,制为邦者四代,非守旧也。处于人表,至严高,后生自以瞻望弗及,神葆其言,革一义,若有刑戮,则守旧自此始。故更八十世而无进取者,咎亡于孔子。祸本成,其胙尽矣。”(《訄书·订孔第二》)太炎先生评论道:“凡说人事,固不当以禄胙应塞。惟孔氏闻望之过情有故。”“闻望之过情”,必然使原本具有革新意义的思想,反过来成为十分保守的思想,孔子原非“守旧”,但因后人过于崇拜他,不仅“神葆其言”,令人“瞻望弗及”,而且使之成为禁锢思想的新的借口,“革一义,若有刑戮”。年轻的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中也曾论及教皇获取权力之后,如何使本来带有改革倾向的耶稣思想“制御全欧,使列国靡然受圈”,结果“益以枯亡人心,思想之自由几绝,聪明英特之士,虽摘发新理,怀抱新见,而束于教令,胥缄口结舌而不敢言”。这也是用“权力”去解读“思想”造成的必然结果。然而具有讽刺意义的是,鲁迅本人的著作在大陆近五十年的阅读史中,竟也几乎遭遇到类似的命运。
因此,要“走近鲁迅”,似乎意味着摆脱“阅读政治学”的纠缠,把阅读鲁迅重新还原为个人行为,而不再是一种“仪式”。鲁迅如果真是蔑视偶像的莱谟斯,那就让他在旷野里,不要把他建成一个新的“罗马城”。
2000年3月20日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