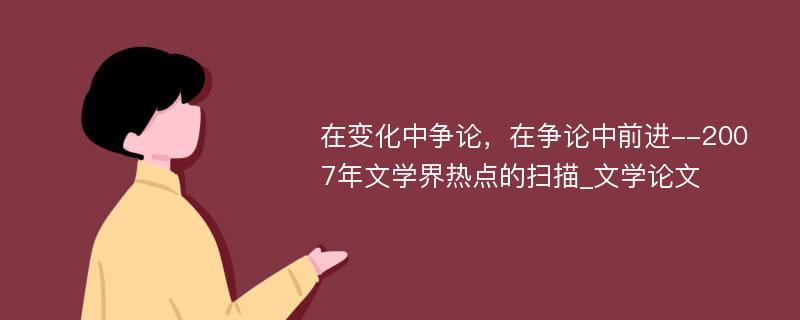
在变动中争议,在争议中前行——2007年文坛热点扫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热点论文,文坛论文,变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顾彬引发当代文学的评价问题
德国汉学家顾彬,在国际汉学界具有相当的影响。但他引起中国当代文坛的广泛关注,并非是他的翻译作品,而是他的批评言论。
2006年12月11日,重庆某报以《德国汉学家称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的醒目标题,称顾彬在接受“德国之声”访问时,以“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等“惊人之语”,“炮轰中国文学”。这篇报道转述道:对在国内红极一时的《狼图腾》,顾彬的评价是:“对我们德国人来说是法西斯主义,这本书让中国丢脸。”而对上世纪末在国内红极一时的“美女作家”,顾彬认为那“不是文学,是垃圾”。在上述报道出现之后,多家国内和境外媒体迅速转载这个报道,越来越多的学者也开始发表看法,认为顾彬“妄下结论”。
在2006年12月14日《成都晚报》所作的采访中,学者严家炎、作家张贤亮等都就此发表了不同的看法。严家炎认为,顾彬的观点太过片面,完全是妄下结论,“我们怎么可能没有伟大的作家?”他一口气向记者罗列了王安忆、陈忠实、陈建功、李锐等10多位当代中国文坛的知名作家,他还特别提到陈忠实的《白鹿原》,“《白鹿原》绝对经得起任何考验,建议顾彬去看看这本小说”。对于当代文学本身,严家炎表示:“随着社会进步,出书相对容易了,文学作品中也的确出现了一些垃圾,但这不是当代文学的全部。”而张贤亮对于顾彬的批评,则表现得相当宽容,他认为:“中国文学已经不再处于封闭状态,既然敞开了家门,难免会听到这样那样的声音”。说到顾彬,张贤亮表示:“他只是一个学者,这些观点也就只是学者的一种声音。”
2007年3月26日,顾彬在于上海召开的世界汉学大会发表演讲时,又一次因对中国当代文学给予了严厉的批评,再度引起争议。他在发言中认为:中国当代文学是二锅头,中国现代文学是五粮液;如果一个作家不掌握语言的话,他根本不是一个作家,所以基本上中国作家是业余的,而不是专家。顾彬还表示,包括莫言在内,许多中国作家是“蜉蝣”,只是一种短暂的现象。
与顾彬一同参加会议的北大教授陈平原当场表示:“顾彬对当代中国文学的批评是哗众取宠,根本不值得认真对待。”“顾彬对当代中国文学的批评不是一个学者对中国当代文学进行研究分析之后做出的学术判断,而是一种大而化之的,凭感觉说出来的话。因此,中国作家也没有必要太在意。”
对于顾彬从语言角度对当代文学的批评,学者们在争论中表示出了不同的反应。有的人表示肯定,如肖鹰在《顾彬不值得认真对待吗?》(《中国艺术批评》2007年第5期)的文章中认为,顾彬的当代文学整体水平不高的整体判断,是有具体分析的,他提示了当代文学的病根所在:第一,当代作家普遍缺少对文学坚定执着的信念,以功利和游戏之心对待文学,他们的文学生命短暂如蜉蝣;第二,当代作家普遍缺少外语能力,在这个国际化的时代,只能靠翻译获得国际文学资源,没有真正的国际视野;第三,当代作家普遍不重视写作语言的提炼和升华,没有达到一个作家应有的专业水平,因此是“业余写作”;第四,当代中国作家普遍缺少关注现实的勇气,回避问题,重复历史题材,不能成为当代中国社会(民众)的代言人。而同样着眼于语言问题,有的学者却从另外的角度对顾彬的看法提出质疑。如蔡翔在《谁的“世界”,谁的“世界文学”》(《文汇报》2007年4月24日)的文章里指出:“顾彬先生的说法很让人费解。首先我没弄懂他的‘外语’究竟指的是哪一种语言,揣测了半天,觉得顾彬先生不像是在要求中国作家努力去学习伊拉克语或者阿富汗语,很可能顾彬先生所谓的“外语”指的就是欧美语言,比如英语、法语当然还有德语,也就是‘西方语言’。另外,顾彬先生的‘世界’或‘世界文学’也不好懂,这个‘世界’或‘世界文学’到底意指何在,包括‘第三世界’或‘第三世界文学’吗?看了半天,没有读出‘全世界’的意思,倒更像是指的‘西方’或‘西方文学’。所以顾彬先生所谓的‘外语/世界(文学)’的真正表述也许应该是‘西方语言/西方文学’。因此,顾彬先生的‘世界文学’更像是他的自我表述,似乎和歌德的‘世界文学’不完全是一个意思。”
总体来看,顾彬有关当代文学的整体判断,动机无疑是积极的,因为他喜爱中国古典文学和中国现代文学,在两厢比较之中,就对中国当代文学很不满意,这其中蕴涵的“怒其不争”的意味是相当明显的。但是他受到身份、爱好及阅读等的局限,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了解不能说是皮毛的,至少是片面的;这实际上不足以支持他对当代文学来作整体判断,更不足以支撑他已得出来的简单结论。但他确实从他的角度,触及到了当代文学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而这些问题也确实值得引起我们的反思。所以,这样一场争议,实际上也有其相当的文学的和学理的意义。
2 媒体时代的文学批评成为焦点
2006年到2007年以来,有关媒体时代下的文学现状,尤其是媒体时代对于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的影响以及当代文学的处境与文学批评的出路等问题,成为当下文坛相对集中的热门话题。2007年上半年间,一些学者在署名文章中发表自己的相关看法,一些学术会议更以此为专题,进行集中而深入的现状考察与学术研讨,使得这一问题的研讨,较之前在深度与广度上都取得了新的进展。但总体来看,因为角度的不同与观念的有别,在一些问题的理解与观测上,看法还是众说纷纭。
从讨论中的一些意见来看,媒体时代既给文学批评造成了尴尬,带来了压力,又给文学批评带来了一定的契机,提供了新的可能,这大致上已成为多数人的共同认识与基本看法。但谈及这一背景下的文学批评的处境与策略,看法依然相当纷纭。
2007年4月末,由浙江工商大学人文学院、《文艺报》和《文艺争鸣》共同主办的“新世纪文学批评的建构”研讨会,围绕着如何建构新世纪的文学批评问题展开了广泛、深入的讨论与交流,一些与会者在怎样评估现状和建构批评的两大问题上,各自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谈到“如何看待当前的文学批评”,与会者认为,当下的文学批评还算活跃,但批评的品质不纯粹。市场化的包装和炒作等文艺之外的因素对批评写作影响过多,本应是公正的文艺批评被掺进了过多的媚俗味儿。一些批评家事实上已被书商或作者利用,作了广告代言人。还有学者认为,当前纯文学批评或曰审美批评的萎缩,主要来自于文化批评的挤压。文化批评重文化轻审美的方法模糊了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通俗文化与高雅文化的界限,影响了正常文化生态的建设,在取消文学的独立性时削弱了文学,特别是削弱了文学的批评力量。因此,重振纯文学批评既关乎文学自身的发展,也关系到人文精神的建设效应。在“如何建构新世纪的文学批评”问题上,有学者指出,必须强调文学批评的价值坚守,树立文学批评家的责任意识。今天的文学样式虽然越来越多,如网络文学、手机文学、图像化文学等,但文学之为文学的基本价值即非如此不可的价值、足以让她伟大起来经典起来的价值应该重新讨论和重新正视,这正是批评家的责任之一。同时,在文学边缘化和文学传媒化的时代,文学批评也应突破圈内的局限,也应有面向大众的一面,改变文风,用尽可能通畅生动的文字与读者交流。批评也应该是一种有生命感悟的写作,批评的文字背后必须有活跃的、丰富有力的灵魂支撑。
2007年7月6日,在上海举行的“文艺评论和媒体文艺传播现状与对策研讨会”上,来自京沪两地的文学评论家就媒体时代的批评建设热烈讨论,积极建言,提出了不少很有见地的意见与看法。雷达说,就文学批评而言,现在最突出的是如何保持文艺评论的精神品格。在某种意义上,主要看批评者个人的选择和追求,看批评者能不能在批评活动中把宝贵的精神价值解救出来,能不能完整呵护文学的审美特性,能不能把文学批评的功能充分发挥出来。而媒体如果能对批评者的独特发现给予支持,提供充分的空间,文学批评的面貌也许就会与现在大为不同。吴秉杰谈到,媒体批评是“热点”批评,文学艺术系统的批评是实践的批评,学院派批评是更注重学理的批评。他认为,文学只有坚持高端价值,才能和大众传媒所代表的娱乐性、休闲性、日常消费性文化区分开来;文学只有保持审美的高端价值,才能与大众传媒建立起一种积极的、交流的互动关系。陈晓明认为,文艺评论和媒体文艺传播的内在关系使人们感到困惑。网络时代就是个感性时代,在这个时代文艺评论的功能被弱化,我们被时代洪流的力量推着走。尽管如此,我们觉得也应尽这个责任。
2007年7月20日,在中国社科院文学所主办的“文学现状的文化解读——2007年上半年中国文学国情论坛”上,来自当代文学界的20几位专家学者在“文学现状的文化解读”的讨论中,怎样看待媒体时代的文学和文学批评,成为最为集中的话题。贺绍俊在发言中指出,大众媒体上的文学批评可以称之为“时尚化批评”,文学专业报刊这类小众媒体上的文学批评可以称之为“实质性批评”。“时尚化批评”影响大众的文学兴趣,“实质性批评”触及文学的实质,揭示文学的走向。两种批评模式都需要,但性质与分量明显不同,应予区别对待,至少要在文学自己的空间内清除一些不必要的杂音,让实质性批评的声音更加洪亮。解玺璋认为,媒体的性质与任务已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而传统批评与历史背景的纠结,新的媒体形式与新的传播方式的联手,也使得批评本身随着媒体的变化而发生微妙的变化。这里表现出来的矛盾,其实是媒体资源的权利再分配。而对于媒体批评,他则认为存在着“脱离作品妄发议论”,“圈子化乃至党同伐异”和“趋赶时尚”诸多问题。而真正具有生机的批评生态环境,应该多层次多形态地充分发展,平等对话,共生共存。张柠主张文学批评应该介入当代现实,不应该远离当代生活现场,不但要对文学作品的质量进行评价,更要对当代语言和想象的生态平衡进行监控,以文学批评特有的方式,对集中体现当代中国表达方式的文学话语进行批评。李建军认为,现在两者所以有问题,是媒体批评不仅在方法上缺乏文学批评的严肃性和规范性,而且还从精神上消解着文学批评的基本原则。他指出,王朔在《三联生活周刊》的访谈、于丹在“百家讲坛”的演讲、韩寒在“新浪博客”上的狂骂,就典型地表现了“媒体”与“批评”的紧张甚至对立的关系。他认为应该给“媒体”提出最低的要求,那就是不要僭越“文学”这个边界,不要用娱乐价值替代文学价值。杨早认为,文学批评与媒体批评互相区别,又互相依存。现在的问题,一是文学批评界必须严守文学批评的边界,不必奢望在所有领域都与媒体意志一争短长;二是媒体随着整个社会阶层的完善与族群的分化,从“大众化”进一步走向“分众化”,而文学批评缺少相应的针对性;三是媒体批评应该走向多元化与规范化,并破除“权威崇拜”、“市场崇拜”、“青年崇拜”,为公众文学阅读提供一种制衡作用,借以对抗作者的自恋、媒体的强势与广告的暴力。
3 “八○后”现象再次引起广泛关注
近年来一直被各种媒体关注的“80后”群体,在2007年再度引起人们的广泛议论,成为文坛内外各种媒体的新的热点。这种关注分为两种情形,一种是来自主流文坛的关注与研讨又有新的动向,一种是因为其中一些作者申请加入中国作协,敏感的媒体进行了跟踪性的报道,引起了多方面的关注与反响。
主流文坛尤其批评杂志对于“80后”一直较少关注,因此《南方文坛》在该刊第四期推出的“80后”写作评论专辑,就相当引人注目。《南方文坛》在这期“80后”写作评论专辑里,约请了一些评论家对张悦然、春树、李傻傻等“80后”代表作家作品进行了具体的文本评析。白烨以颜歌的《良辰》和《异兽志》为主,论析了作者难能可贵的特点所在,指出颜歌的写作,涉及的题材相当广阔,内涵的文学趣味比较高雅,这使她事实上成为了“80后”一代目前所能够达到的艺术成就的重要代表。但是,因为她的作品既常常淹没于青春文学之林,又具有明显的先锋性和靠近纯文学写作,因而既未在青年学生读者中真正火爆起来,也未能得到主流文坛的应有关注。这样的一个实际遭际,其实也正是颜歌当下写作的尴尬所在。徐妍在谈到张悦然的创作时认为,她的小说依靠的是对幻想的执着迷恋而不是对经验的忠诚书写,舍弃了经验世界的支撑而一味地在幻想世界里沉坠,这是张悦然小说最有争议的主要原因,然而这也造成了张悦然写作的缺失,这种依赖于语词的幻想与外界没有接通,是一个“精神的悬空之地”。张清华力图穿越“代际”隔阂,去理解年轻一代的写作,因此他认为,春树的写作与20世纪60年代美国文化有着内在的一致性:“我们可以把美国20世纪60年代的这些文化理解为现代主义和先锋,为什么不能给近在眼前的这些书写以认真的诠释和认识呢?这似乎是不公平的。”他同时认为,“80后”一代的才华和早熟是值得敬佩的,但他们需要在“成熟的叙事和艺术的言说”上下更大的功夫。张柠认为,李傻傻的写作是“一个乡下男孩的寓言”,包含了其他“80后”作家缺乏的生活体验,也就是他的乡村体验,并借助于奇异的叙事风格表现出来,这构成了他创作风格的基本色调。但他同时也提醒李傻傻“仅仅有对破碎经验的迷恋是不够的”。邵燕君在评论笛安的创作时,惊喜笛安忠实自己的青春体验。她说:“‘80后’作家需要尽快走出的只是‘青春写作’的青涩状态,而不是青春体验——如果青春体验仍是他们目前最重要的人生体验的话。说到底,深切而独特的个人体验永远是所有作家最珍贵的宝藏。”一直在广东东莞打工的诗人郑小琼,工余时间写作诗歌和散文,她的写作与底层打工的经历有着密切关系,因此谢有顺将其称为“一个意味深长的诗歌事件”。他认为,郑小琼“突出的才华,旺盛的写作激情,强悍有力的语言感觉,连同她对当代生活的深度介入和犀利描述,在新一代作家的写作中具有指标性的意义。”
2007年加入作协的新会员“80后”作者,除了张悦然、郭敬明、蒋峰、李傻傻等知名“80后”之外,还有一些也属于“80后”的新秀,如王虹虹、蒋盟、阿娜尔古丽、赵靓、李姗等。因为前边几个知名度高,人们更为关注罢了。据知,在作协会员专家咨询组讨论通过几位“80后”作者后,一些媒体便争相对当事人及有关人士进行了采访与报道,使此事一时间成为了当下文坛的一个焦点。
有记者就加入中国作协一事致电郭敬明时,他表示,能进中国作协自然好,能得到长辈的认可很开心。张悦然、蒋峰、李傻傻的入会介绍人为白烨与李敬泽、胡平、吴秉杰。张悦然对记者说,她这次申请加入作协是自然而然的,没把它当成特别的标志性事件。先是有作协的朋友推荐她去北京作协,后来白烨又推荐她进入中国作协,她填好上交,如此而已。“写作是很孤独的事情,如果作协能提供一个周围有做同样事情的朋友的环境,真的很重要的。”
介绍张悦然、蒋峰、李傻傻入会的白烨等人认为:这几位作者加入中国作协,无论对于中国作协,还是对于这些“80后”作者,都是一件好事。“80后”加入中国作协,看得见的影响是增加了“新鲜血液”,使作协相对年轻化了,同时会带来一些新的文学气息,使作协可能通过他们取得与年轻作者的联系;而对其他“80后”和那些游弋在体制之外、寄身于网络之中的青年作者,会传达给他们一个确定的信息,那就是包括中国作协在内的现有体制其实都是向他们敞开着的,是关注着他们的,而他们除去在网坛上、市场上打拼之外,也可加入作协这样的组织,在体制内获得生存与发展。这会使他们的文学之路更加宽阔和宽广。
作家陆天明和陈村对“80后”加入作协均取肯定态度。陆天明说:我非常赞成作协吸收“80后”作家,他们绝对是中国文学未来不可忽视的力量。他们一定会长大,会成熟,会挑起重担。中国文学肯定有一天是属于“80后”的。但同时我认为,具体到“80后”的每个个人是否有资格加入作协,这一点是需要讨论的。他还认为,作协工作的视野应该更宽广一点,在帮助未成名的文学青年上多下些工夫,更多关注在文化道路上挣扎的人。陈村指出:“80后”有人加入作协,有人不加入,这都是个人选择。作协现在也很愿意吸收一些年轻人,让他们能在一个相对好的环境里坚持写作,因为现在进行纯文学创作的人是很困难的,书不畅销,收益不大。其实“80后”里面大部分人的作品不是畅销作品,他们单纯靠文学谋生会比较困难。我们希望作协能够提供他们一些帮助。
4 《色·戒》从小说到电影众说纷纭
李安导演的电影《色·戒》,于2007年9月在威尼斯电影节上夺得金狮奖最佳影片奖,随即影片在香港和台湾公演,两周左右,分别在两地突破3000万港币和2亿台币;10月,该片为了达到大陆电影检查的要求和适应内地观众观赏,影片剪掉七分钟的性爱片段开始公映。短短三个多星期内,其国内票房收入已超过1亿元人民币。
电影《色·戒》改编自小说家张爱玲同名短篇小说,以上世纪40年代,被日本占领的上海为背景,描写了一个卧底的女抗日分子本想暗杀一名亲日的情报官员,但反而陷入了自造的情色诱惑中难以自拔的暧昧故事。但正如一些评论所指出的:“李安的《色,戒》,不一定非得是张爱玲的《色·戒》。小说改编成电影,导演完全可以将原著推倒重来。其实李安正是这样做的。”
随着《色·戒》的公映与火爆,也在影评界和观众中引起了极大的争议。在网络论坛上,有关电影《色·戒》的争论一直是持续不断的一个热点,争议的内容从电影的性爱场面到与张爱玲原作的异同,从作品的政治倾向到我国的电影评级制度,话题相当丰繁,争论极其热烈,不同的看法甚至针锋相对,相持不下。
有关电影《色·戒》的争论,概要来看主要是围绕着性爱的内容和政治的取向两大问题而展开的,因为立场的不同、观念的迥异,面对着同一问题,看法却迥然有异,甚至尖锐对立。从大的倾向上看,大致以下三种看法最具代表性。
一种是肯定派。这种看法也有角度上的差异,如李欧梵从电影艺术风格的角度着眼,认为“改编后的《色·戒》比张爱玲的原著更精彩,李安从张爱玲的阴影下走出他自己的一条道路来”。有人从娱乐的角度来解读,认为“这本来是很娱乐的一部电影,却被某些一本正经的人们解读得不够娱乐了”。有人从个人与历史的关系上来解读,认为“《色·戒》是一部表现‘人’被‘绝对国家’所挟持的悲剧。在此悲剧的终局,则又以罪恶者的悔恨暗示最后的救赎”,“《色·戒》是一部秉心纯正、微言大义的杰作”。更有人从影片的暧昧意味入手指出,从李安导演在这部影片中所要诠释的人性和在特定背景下产生的特殊情感以及导演在通篇中布下的无处不在的玄机来看,“李安是个伟大的导演,《色·戒》是一部很棒的电影”。
一种是否定派。持这种看法的人,有人从情色上予以指斥,认为:“家庭片、同性恋都拍过了,李安要拍一个情色片,翘首以待者何止千万。”“《色·戒》的确大大超过了这些电影史上的情色经典,它将情色表现推向了三级片的程度。”“问题在于,这样‘变态和暴露’对于电影是否是必须的?”比较多的人则从作品的历史背景、政治蕴涵立足,批评与批判电影作品的政治倾向的模糊与偏离。12月4日的《文艺报》在“观众评说《色·戒》”的通栏标题下,发表了陈辽、姜德锋、邵明、李保平署名的文章,在与原作的比较分析中,批评电影《色·戒》“以性易爱”,以“人性”遮蔽“爱国心”的错误倾向。在这种看法中,以阎延文的观点和“乌有之乡”讨论会的意见最有代表性。阎延文先后写了三篇文章,在文章题目中就鲜明地亮出自己的观点,如“《色·戒》色情污染,李安导演应向国人道歉”,“撕碎人性与轰毁艺术”,“欲望彰显的人性之毒”,“人性之毒与欲望暴力”。她并郑重地提出:“导演李安能否以佛门的‘忏悔业障’,向大众作出负责的道歉,达到心灵的净化与升华?”设在北大资源楼的乌有之乡书社,于2007年11月和12月,分别举办了两次“《色·戒》影评沙龙”活动,讨论的焦点集中于“《色·戒》是不是用肉色混淆了近代以来的大是大非”?与会者的基本看法是:“《色·戒》描写的不是人性,而是动物性。”“《色·戒》是一种政治隐喻,反映的其实是一种‘皇民史观’。”
还有一种观点可以看作宽容派。持这种看法的人比较多地着眼于作品本身,以及导演本人。如针对有关情色的批评,有人就指出:“情色以及色情的电影类型在全世界的范围内是客观存在普遍存在的,欧美国家以及港台地区用限制级标签的形式保护并支持了该类型电影的发展及其受众群体的利益。李安作为一名国际导演,其所作所为是符合国际视野下该类型电影的题材要求的,并非过分之举。”有人就影片遭人诟病的政治问题指出:“《色·戒》并非要抹去抗战中我地下工作者甚至是我们国家民族悲壮抗击的历史底色。它不过是对于大时代下各色人物的一种比较个人化的记录而已。因为这种个人化的叙述,它所产生的震撼和所引起的不适几乎是同样当量的。”在这种看法中,长期从事文化批评的戴锦华的文章较有代表性。她在文中详细介绍了张爱玲小说创作的发展轨迹,比较了张爱玲的原作与李安的电影的异同。在小说与电影的比较中,她认为“电影比小说好”,“张爱玲以她的练达,以她的精明,以她的灰黑色的人生视野,以她的冷酷,写出了一个决绝的故事。而李安以他的温存,以他的敦厚,以他的敏感,以他的细腻,重写这个故事。在这个故事当中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结局的改写。张爱玲的结局是‘生是他的人,死是他的鬼’。李安最后给出了一个古老的阐释——个人是历史的人质”。谈到对于电影《色·戒》的总体评价,她指出:“我并不认为这是一个国耻之作,我也不认为它是一个非干政治之作,我也不认为它在歌颂汉奸,但我也不认为它在谴责汉奸。李安用一个张爱玲故事,极端准确地踩到了一个富于张力的点,他用身体政治,用性别政治,用身体的表述,来找到了一个不是真的突围。”“这个张力状态关系着大政治,关系着小政治,关系着历史,关系着国族,关系着个人,关系着身份,关系我们岌岌可危的个人的状态,而影片当中提供的所有的丰富的入口、丰富的阐释可能,给我们进入它的可能,也给我们从影片所提请的问题当中逃逸出去的可能”。“没有不干政治的艺术,也没有只干政治的艺术,艺术当然首先是艺术,但是艺术始终永远是它时代的镜子,或者是潜意识的储藏体。”
(执笔:白烨)
标签:文学论文; 文学批评论文; 世界语言论文; 艺术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电影语言论文; 色戒论文; 张爱玲论文; 张悦然论文; 李安论文; 李傻傻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