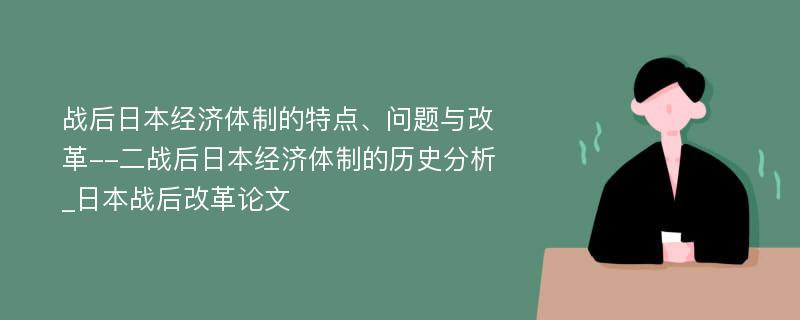
再论战后日本经济体制的特征、问题及改革——对战后日本经济体制的历史学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论战论文,历史学论文,日本论文,经济体制论文,对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日本研究》2003年第4期刊载了刘红写的论文《战后日本经济体制的特征、问题及改革》,对影响日本经济发展的关键——经济体制特征——作了扼要的阐述和分析。刘氏指出:“具有长期、持续性交易关系本质的日本经济体制,其形成并非是根植于日本文化和传统的,究其根源是为适应战后的经济环境而形成的。”这种观点带有相当普遍的代表性。笔者认为,上述观点颇值得商榷。本文扼要阐述了日本史坛最新的研究动向,考察了日本经济体制的几项特征,分析了经济体制对日本经济发展的重要影响,指出战后日本经济体制的特征形成于战时而非战后,因此通过改革解决当今日本经济体制所面临的问题的根本前提,就是对包括战时体制在内的那场侵略战争,进行彻底清算。
一、学术热点:日本战后经济体制源于何时?
对战后日本经济体制形成于何时,日本学术界尚未达成共识。概括而言,主要有两种论说,一种是“文化传统说”,另一种是“战后改革说”。前者认为:“日本的经济制度具有日本固有的文化背景,根植于民族特性。日本型企业和官僚制的原型,可以追溯到江户时代的‘藩’和‘家’。可以认为连带意识和平等主义的根源,早在农村共同体中就已经存在。”后者则强调:“战后的日本是在战争的废墟上站起来的‘新生的日本’,同以往的日本有本质的差异,同以往的历史没有联系。就这个意义而言,‘我们的生日是终战日,我们的父母是战后改革’。”[1]由于“战后改革说”代表了长期占据日本史学主流地位的“战后史学”派的观点,因此在日本最有影响。
但是,早在20世纪70年代,否定“战后改革说”的动向在日本学术界已经出现。1977年,榊原英资、野口悠纪雄发表了《大藏省·日银王朝的分析——总体战经济体制的终焉》一文,提出了强调战时和战后经济体制存在连续性的“假说”,认为“战争结束时,日本社会的形式和理念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另一方面,经济体制,特别是作为实行金融统制之基础的战时经济体制,却基本上得以存续”,“支撑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体制,基本上是战时总体战体制的继续”[2]。1978年,中村隆英在《日本经济——其成长和结构》一书中指出:“战后和战前,不是飞跨战时联结起来的。战时形成、战后继续保持的社会制度、经济制度、技术、生活方式、习惯等,实在是出人意料之多。虽然这些东西在形成的时候,以后会变得怎样没人能够预料,但它们却构筑了战后的企业形式、生产组织乃至生活方式。”[3]1988年,山之内靖发表了题为《战时动员体制的比较史考察——为了了解今日日本》的论文,认为日本为进行“总体战”而进行的战时动员,“形成了某种‘全体主义’。这种‘全体主义’,是形成战后日本‘体制社会’的起点”[4]。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以日本面临种种经济难题为背景,诸多学者对战后日本的经济体制进行了深入分析,得出了“日本战后经济体制是战时经济体制而延续”的结论。1993年,冈崎哲二、奥野正宽编纂出版了由8位学者共同撰写的《现代日本经济体制的源流》。该论著撰写者对日本金融体制、企业体制、劳资关系、业界团体、财税政策、农业状况等各经济领域在战时和战后的变迁,进行了详尽的历史性考察和比较分析,指出日本至战前30年代的企业统治,即由财阀家族确保股东主权的经济体制,是盎格鲁-萨克逊型的自由主义经济体制。但是在战争时期,这一经济体制转变成了“日本型经济体制”。正是这种转型后的体制,构成了促使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经济体制的原型。他们通过各项考察后最终得出结论:“构成现代日本经济体制的大部分要素,都是在中日战争和太平洋战争时期,为了对国家资源进行总动员而实施‘计划经济化’的战时经济的需要,以及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而实施‘统制经济’的需要而制定的。”[5]1995年,山之内靖、J·维克特·考希曼(J.Victor Koschmann)、成田龙一主编了作为13位日美学者共同研究成果的论著《总体战和现代化》。该论著同样对构成战后日本政治和经济体制的几个方面进行了颇为详尽的考察,并最终得出结论:“战后各项改革的基本方向,和战时的各项改革是共通的,这些改革使战前经济体制的制度性基础彻底解体……使战后体制向战前体制回归的道路被封闭。日本的经济虽然也算是市场经济,但是其制度性基础中,包含着在战时计划、统制经济的基础上导入的要素。可以说,日本的经济体制是一种独特的经济体制。”[6]同一年,野口悠纪雄发表了《1940年体制——再见了,战时经济》(按:他所谓的1940年体制,即战时体制),考察了“1940年体制”即战时体制的形成过程、日本经济高速增长和“1940年体制”的关系、“1940年体制”的基本理念、日本经济体制面向未来的选择等几个方面,明确指出了战时和战后经济体制的存续关系:“在战前具有浓厚古典的自由主义经济性格的日本企业和金融市场,在战时经济中发生了巨大变化。现在的日本型企业、间接金融体制的原型,存在于战时经济之中。”[7]
总之,20世纪90年代后,以日本经济风光不再为背景,对日本战时和战后经济体制是否存在连续性的探讨,构成了日本学术界一个持续的热点,其影响波及日本现代史研究的各个领域。通过初步的历史考察,笔者认为至少就日本经济体制而言,战时和战后无疑存在连续性。
二、历史考察:日本战时和战后经济体制是否连续?
按照《现代日本经济体制源流论》中的论述,战后日本经济体制具有五项特征,即:(1)不是股东,而是经营者主权的“企业所有和经营的关系”;(2)以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制、企业内工会为代表的“企业内的雇佣关系”;(3)以下包制或系列企业为代表的“企业间交易关系”;(4)以银行借贷为中心的“和金融市场的关系”;(5)以行政指导为中心的“企业和政府的关系”。[8]如果我们认同该论著对战后日本经济体制之特征的概括并逐项进行历史考察,那么当不难发现,这些特征都是在战前呈现雏形、在施行战时计划和统制经济时期最终形成、在战后得以延续的。
就第一项特征而言,战前的日本企业也曾经是股东主权。但是1937年侵华战争的爆发,使前此日本“股东主权”的古典资本主义企业经营模式受到了极大冲击,“使日本企业在大约30年的时间里,完成了从极端的股东主权,向极端的从业人员主权180度的转变”[9]。曾赴美就职、后任日本电源开发总裁的高碕达之助,在1954年曾对他1916年和1947年两度回国时获得的不同印象作了生动描述。对前一次印象,他这样写道:“我首先没有料到的是,第一,在会社从业员不知情时,会社的股票已经从A大量流向B,而在股票流动时主要经营首脑已发生更换,经营方针很不稳定。第二,经营首脑主要不是着力巩固会社的基础,而是竭力博取股东的欢心和获取高额红利,以及竭力使股价上扬。”对第二次印象,他却这样写道:“股东的权益完全被无视,事业的经营由从业员执其牛耳,恰好同我大正五年(1916年)第一次回到日本时截然相反。”[10]
日本经济体制的第二项特征同样是战时的产物。在战前,日本的劳动力流动曾经相当普遍。在明治时代,熟练的机械工人在全国到处流动的状况,至大正时代仍得以继续。大正年间大阪市的《劳动调查报告》曾这样写道:“不管怎么说,我国劳动者的最大缺点,就是在同一个企业里工作的时间太短。这种状况无疑使我国工业不断蒙受极大损失。”[11]没有终身雇佣,也就没有与之密切相关的年功序列。但是,同样由于侵华战争的爆发,为了摆脱通货膨胀的困境,日本政府对经济进行了战时统制,并发布了一系列法令。其中对形成终身雇用和年功工资序列产生重要影响的法令,有1939年颁布的《从业者雇入制限令》、1940年颁布的《从业者移动防止令》和《工资统制令》。前两项法令禁止随意招募员工和随意离退职,使职业流动现象几近消失,后一项法令则不仅扩大了工资中的定额部分,而且使基本工资定期、自动提高作为一种惯例在全国迅速普及。1939年3月,作为施行上述法令的具体措施,日本政府又规定了“初任给”,即对刚参加工作的员工的工资数额,根据地域、年龄、性别进行统一规定。另外,自1939年9月开始,又施行“工资冻结”,即一律不准擅自加薪的工资统制。1942年,日本政府又颁布了《重要事业所劳务管理令》,规定在某种条件下,如果获得厚生大臣的许可,企业可以不施行“工资冻结”。所谓的“某种条件”,就是制定加薪规则,事实上,日本政府“规定一年一次必须以所有从业人员为对象,按照最高、基本、最低基准额进行加薪”[12]。如尾高煌之助和中村隆英所指出的:“正是因为经历了这一过程,年功序列工资和根据工作年限升职制度,在全国得以普及。”[13]构成“企业内的雇佣关系”另一个侧面的企业内工会,也是在战前工人运动的推动下呈现雏形,在战时最终形成的。在这方面,为战时经济需要而组建的“产业报国会”,可以说是战后企业内工会的母胎。按照中村隆英的观点:“战后按照占领军的指令迅速组成的许多工会,均以该组织(产业报国会)作为母胎。”“按企业形成并存续至今的日本工会,事实上只不过是战时产业报国会等组织变换了一下名称。”[14]
日本现代经济体制的第三项特征(同时也是日本制造业的一大特征)也是在战时形成的。在战前,日本的大企业即使零部件一般也自己生产,并不采取下包的形式。但是,由于战争,很多企业的生产规模急剧扩大,作为一种紧急措施,不少企业采取了将部分产品,特别是零部件交中小企业生产的“下包”方式。由于这种紧急措施不仅强化了大企业和中小企业的关系,提高了中小企业的生产技术水平,并且使中小企业因能够比较稳定地获得订单而减少了破产和被大企业挤跨的风险。所以,下包制或系列企业在战后作为一种理想的生产方式而得以保留。例如,根据美国学者约翰·多尔的研究,至20世纪60年代末,向丰田汽车公司供应零部件、作为其子公司的企业,40%以上都是在战时通过下包制,和丰田公司构筑起这种关系的。”[15]
作为日本经济体制的第四项特征,即主要通过向银行借贷,而不是发行股票或企业债券融资的“间接金融”体制,更是战时的产物。在明治时代,日本企业基本上是依靠股份和企业内部资金储备进行扩大再生产的,属内部金融时代。在这一时代,由于财阀占有矿山开采和对外贸易等高收益产业,拥有充足的资金储备,因此一般均以企业内资金进行再投资,扩大再生产。不受财阀支配的一些产业,如棉纺织业和铁道运输业,则依存于以股东的股份担保金额支撑的内部金融机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正式进入了重工业和化学工业的迅速发展期,以往通过内部金融机制筹措资金的做法逐渐捉襟见肘。于是,企业通过外部筹措资金的做法开始被普遍采用。日本金融体制开始呈现直接金融和间接金融二者并重的状态。不过,当时主要仍以直接金融为主。1937年侵华战争爆发后,随着日本当局金融控制的全面强化,日本进入了“时局金融”时期,上述情况开始发生显著变化。据统计,1936年,日本企业通过发行股票筹措的资金,占其资金总额的63.8%。但是战争爆发后,这一比率逐年下滑,再至1939年占33.6%,至1945年则仅占0.61%。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向银行借贷作为取代股票发行筹措资金的方式的比重,则自1939年呈显著上升趋势:1936年为40.6%,1945年达到93.2%,即企业已几乎完全以向银行借贷作为基本融资方式。[16]不言而喻,间接金融体制是在战争时期形成的。
最后,以行政指导为中心的“企业和政府的关系”,不仅是战后日本经济体制的一项重要特征,也是“东亚模式”的两大特征之一。但同样必须指出的是,尽管在实现近代化的历程中,日本政府在推进产业发展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但是在侵华战争以前,日本政府事实上并不直接、全面地介入民间的经济活动。即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概览当时一系列“统制立法”,我们便不难发现,日本政府在战时经济活动中所扮演的主要角色,仍是保护、扶持乃至救助民间企业。只是为了发动对华侵略,日本当局开始真正将国民经济转入“战时经济”,才通过各种方式和手段,广泛介入民间经济活动,密切企业和政府的关系。“正是在这一阶段,战后政府和业界团体双向关系或者说行政指导体制的原型,开始出现”[17]。
三、福兮祸兮:如何认识日本“战时经济体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一般认为,战后日本经济的发展,主要得益于因日本向和平国家转型而摆脱了军费负担,以及农地改革、解散财阀、禁止垄断、劳动立法等经济民主化政策对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但是,按照野口悠纪雄的观点,日本经济所以在战后迅速恢复并马上实现高速增长,主要归因于在战时形成的经济体制。他这样写道:“‘日本型企业’的各种特征,对经济高速增长的实现,起了发动机的作用。”“正是由于实行了金融统制,才可能对资本集约性战略产业实行重点资源分配,才可能在作为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支柱产业的重工业和化学工业中,实现工业化。就这个意义而言,可以说在金融体制中维持‘战时体制’,是推动经济高速增长的最大原因。”[18]不过,野口悠纪雄对“战时体制”的评价,绝不仅止于肯定它的积极作用,绝不意味着他称颂乃至推崇这一体制。相反,他认为这一体制已经落后于时代要求,应该退出历史舞台。他明确指出:“迄今为止,虽然日本政府几度试图进行改革,但是这一体制依然没有改变。在日本走向未来的今天,1940年体制已经成为一大桎梏。”[19]
野口悠纪雄的观点,有助于启发我们对日本创造经济“奇迹”的进一步思考。众所周知,1968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超过了英国和德国,成为仅次于美国和苏联的世界第三经济大国,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以此为背景,西方国家的政界和学术界开始探寻日本为何能创造“奇迹”,而上述现代日本经济体制特征的核心内容,曾被视为日本创造“奇迹”的要因。
首先,将日本经济“奇迹”的产生,主要归因于日本特有的企业用工制度和机制的观点,曾经倍受推崇并非常流行。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埃兹拉·沃格尔于1979年发表的《日本名列第一:对美国的教训》,就是这方面的代表。沃格尔在该论著中通过对日本战后的政治、经济、科教和社会生活作了详尽的考察后得出结论:日本所以能取得成功,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日本企业拥有一大批愿意为企业尽心尽力的职工;而日本企业所以能拥有这样的职工,就是因为日本企业具有“对企业忠诚,对工作热爱,以及为企业献身”的激励机制。[20]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和外交家埃德温·赖肖尔和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马里厄斯·詹森也认为:“终身雇用制度在日本发挥着良好作用。”“年功序列制度,也为经济发展起了促进作用。”“日本的雇用制度和工资制度显然对该国的工会发展产生影响。”[21]
其次,就间接金融体制而言,国际学术界普遍认为,在日本战后的经济恢复和高速发展时期,银行一直充当了资金的提供者和企业经营风险监督者的角色。所以,尽管战后日本经济发展速度惊人,企业规模急剧膨胀,但整体上金融秩序井然,没有出现大的金融动荡。之所以如此,战时形成、战后延续的金融体制具有稳定性,是一大要因。寺西重郎提供的一个数据为此提供了证明:在战前,银行破产是寻常的现象,1902年至1919年的18年间,经营出现破绽的银行年均24.6家,1920年至1932年的13年间为43.5家,1933至1945年的13年间为7.8,但是在战后,直至70年代,没有一家银行倒闭。[22]
再次,认为日本经济“奇迹”的产生,主要得益于政府和企业间的“密切协作”的观点,也曾经盛极一时,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1970年美国学者吉姆斯·阿布格伦在《探讨日本式经营——株式会社日本》一书中提出的“日本株式会社论”。在该论著中,阿布格伦将日本比喻为一个综合企业——日本株式会社,日本政府是“总公司”,各日本企业是分公司。[23]虽然阿布格伦的原意,是讽刺日本依靠官民一体的体制追求经济利润,但是,这一比喻,又被视为官民密切协调发展经济的范例,是“东亚模式”获得成功的一条经验。
确实,对战后日本历史作一扼要考察,我们不难发现具有战时经济体制余影的要素,对日本经济的恢复和高速发展确实产生了巨大推动作用。就战后经济的恢复而言,如国内的许多教科书所言,有泽广巳提出的“倾斜生产方式”发挥了重大作用。但需要指出的是,“倾斜生产方式”的第一个要素,是政府在物资资源的重点投入时,制定“物资需给计划”和“临时物资需给调整法”,这种做法和战时作为经济运营基础的《物资动员计划》,几乎一脉相承。“倾斜生产方式”的第二个要素,是资金的重点分配机制,这一机制和战时企画院和军需省制定的《资金统制计划》、《国家资金计划》可谓异曲同工。就战后经济的高速增长而言,1957年岸信介内阁制定的《新长期经济计划》、1960年池田勇人内阁制定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作为对日本国民经济发展具有关键影响的计划,无疑特别值得关注。但同样值得关注的是,岸信介和池田勇人均是“统制经济”的亲历者:岸信介1942年任商工大臣,1957年后连任两届首相;池田勇人在战时曾任职于通产省的前身商工省和军需省,1949年出任吉田茂内阁的通产大臣,1960年任首相。换言之,由他们主导的“计划”本身,即显示出战时具有经济统制性质的“计划经济”对他们的影响。
然而,正如中国的古语所言:“祸兮福之所依,福兮祸之所伏。”当今日本经济所面临的问题,无疑同日本经济体制具有密切关系。因此,日本学术界就是否应使战后日本经济体制彻底解体这一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作为历史学工作者,笔者认为,只有认清历史,才能面向未来。只有正确认识日本现行经济体制的根源,才能通过改革使日本经济真正走出困境。舍此没有其他出路。
